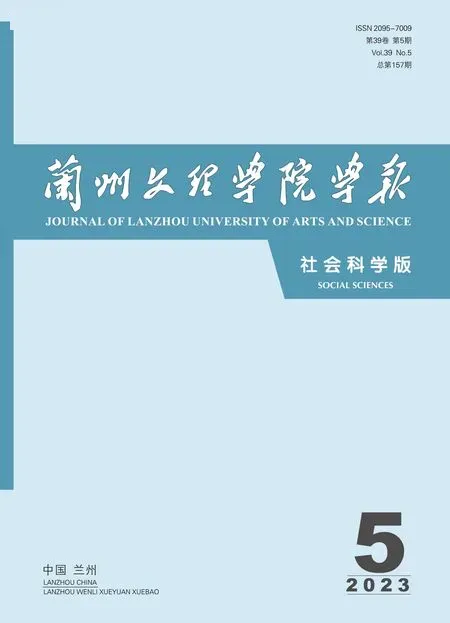晚清与五四的“断裂”与“延续”
——评《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
刘 永 睿
(兰州文理学院 学报编辑部,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言
19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也出现了不少的“重写”实践。在我看来,在这众多的“重写”理论倡导与实践中,最具颠覆意义的两种“重写”,一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二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前者拆解了在现/当代文学之间人为设置的“隔板”与“阶梯”,后者则破除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创世神话”。
当然,要重写文学史,只提出宏大的命题是不行的,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去。不论是打通1949这个时间“隔板”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还是追溯五四文学革命“前史”的“重写晚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以前被忽略了的文学史的“延续性”。所以“当代文学史”起点和源头就不是“第一次文代会”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是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文学或此前的左翼文学;“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不再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是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的1902或1898年。更有甚者,在周作人所追溯的新文学“晚明”本土源头之外,另寻得晚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等对“文学”赋予的新义,于是有所谓“没有晚明,何来晚清”[1]的进一步追问,并将杨廷筠在《代疑续编》中以“文学”一词定义“literature”的1635年当作现代文学史的源头[2]。
不管这些新追溯到的关于现代文学(或新文学)不同源头是否科学、有理,我们都从中看到了文学史演变过程中缓慢而渐进的历史“延续性”。文学史演变过程任何一次看似“飞跃性”的变化(或称为“质变”),都有着此前或多或少的、或长或短的历史铺垫和渐变的累积。如果我们无法发现这种历史铺垫或累积,那只能说明这种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比较隐蔽,或者这种铺垫或累积的历史文献没有得到保存和流传。
在解放前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往往点到为止地叙及清末文学变革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在1949年以后、新时期之前的新文学史叙述中,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史”基本上淡出了文学史的视野。新时期以来,“晚清”或“清末”的文学变革,逐步与五四文学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学者们从文学媒介、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主题、美学风格、文学语言等各个层面,从微观的视角与具体的问题入手,探讨从晚清到五四文学演进的诸多历史关联,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宏观思路,一步步落到实处。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是清末以来数十年时间中,社会环境和文学自身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清末以来的白话报刊,是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最直接因素之一。清末白话报刊驱动与孕育了五四文学革命。但清末的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前后演进关系,而是在曲折发展中的螺旋上升。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清末白话报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性继承的结果。
晚清与五四的历史关联,涉及方方面面。但在晚清的诸多文学变革中,白话报刊无疑是最为重要且与五四文学革命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方面。已有的晚清以来的白话报刊的研究,多为表面或粗线条的论述,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无论是逻辑的严密推演,还是史料的细致梳理,都还存在诸多疑点和疏漏。比如晚清以来为数众多的白话报刊作者、读者,在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后来的新文学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晚清白话报刊文的语言、文体与五四新文学的异同;晚清白话报刊中各种文学类型的地位与五四文学革命所确立的新文学格局之间的关系等,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思考、分析、梳理,都会挑战、细化既有的文学史论述。
《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的学术价值,正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细化和落实。正是这种细致的描述,使我们对这一文学史演进过程获得了一种真切的认知和感受。
二、清末白话报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贡献
清末的白话报对文学革命的前驱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如何将这些影响落到实处,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工作。例如,学界多以陈独秀、胡适是清末的白话报人,又是文学革命的发起人,来证明清末的白话报与文学革命的演进关系。但是,用这个逻辑,就无法解释同样是清末白话报人的林纾与刘师培,何以成了文学革命的反对者。所以,清末白话报对文学革命的影响,需要建立在细致的考辨基础上,需要落实在对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以白话报人与作家、读者、语言与文体、文学格局、主题等几个问题为支撑,以具体的问题和文本分析为抓手,来分析清末的白话报与文学革命及其新文学之间的关系。
概括而言,作者对清末白话报与文学革命的历史关联,做了六个方面的考辨、分析:
(一)白话报刊对新文学作家和读者的培养
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的贡献,首先是新的作家和读者的培养。受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作者),基本上有五种情形:一是直接由清末民初的白话报人演变而来的新文学作家,如胡适、刘大白等;二是受过清末白话报刊影响,在文学革命前后成为新文学作家的,如郭沫若等;三是受清末白话报刊影响,在文学革命前后从事新文学写作,但并不以此为主要职业的新文学作者,如恽代英、舒新城等;四是由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培养的有名或无名的白话文普通作者;五是受五四前后新兴白话报刊及其白话文的影响,开始新文学写作的作者,如曹聚仁、陈范予等[3]。
既有的研究,对其中第一种情况,论述较多,对后四种情形,多有忽略,尤其是对白话报刊培养的普通新文学作者和以新文学写作为副业的“边缘”作家。作者通过对清末民初相关文献的考查,以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的贡献,除了那些叱诧风云的文学革命领袖人物和声名显赫的作家之外,还在于它为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普通作者,或容易被人遗忘的“边缘”作家。
另外,白话报刊也培养了一大批白话文的读者。五四文学革命借助五四学生运动骤然取得成功,看似有些意外,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即是清末以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白话报刊为新文学培养了广大的读者群体,这才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2015年《民诉法解释》对二审撤回起诉问题的明确规定不应成为对这一事项的终结性回应,二审能够撤回起诉且撤诉后不得再诉之制度规定面临的理论障碍应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足够关注与重视。二审撤回起诉为诉讼实践中需要处理的普遍问题,该问题的如何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不同程序及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合,也必然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走向模式有着辐射效应。尽管二审撤回起诉为民事诉讼领域老生常谈的问题,期待以本文的讨论研究为视角,能够激发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对2015年《民诉法解释》规定的二审撤回起诉制度予以进一步讨论及关注,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最终促使我国撤诉制度向深层化和成熟化运作模式的逐渐靠拢及过渡。
(二)清末白话报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角色与作用
清末的白话报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推动者:其中核心的力量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外围的成员有蔡元培、裘廷梁、吴稚晖、林白水、彭翼仲、陈荣衮、马裕藻、张九皋、包天笑、张丹斧、傅熊湘、黄伯耀、李辛白、高语罕、刘大白等;二是“游离者”:其中王法勤、刘冠三、景梅九、杭辛斋、詹大悲、温世霖从事于革命工作;另外章仲和、叶瀚、王子余、方青箱、房秩五、欧博明,则从事具体的外交、军政或教育等工作;而秋瑾、黄世仲、郑贯公、范鸿仙、韩衍、冯特民、赵尔丰则在文学革命之前已离世;三是反对者:仅有林纾、刘师培二人[3]111。
这些白话报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由于年龄、观念、职业、文坛地位、社会地位、所处地域等因素的不同,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学的态度、作用也各不相同,但除了林纾、刘师培之外,其他的白话报人,均以他们的精神或行为,为文学革命的发生和新文学的成长,给予了精神上的支持或行动上的赞助。
在这里,作者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但长期被学界含混认识的问题:一是林纾为什么由清末颇为活跃的白话文作者,变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反叛者;二是刘师培为什么由清末的白话文鼓吹者,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变成一个沉默者。我相信作者对这两个问题分析,为我们廓清了白话文写作阵营内部的裂痕与复杂性。这一历史事实启示我们,我们绝不能笼统、含混地认识白话文写作革命性、进步性,而是要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写作行为作具体的分析。
(三)白话报刊与语言变革
清末的白话报刊本身是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既有对语言变革的理论倡导,但更多则是语言变革的诸多实践。
清末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如“崇白话而废文言”等,都是由白话报人提出的,而且他们在语言意识的层面,将白话文与个性解放、国家意识相联属,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中的个性意识、国家意识,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实践的层面,清末的白话报刊,一是宣传“国语教育”和“简字运动”,二是开始方言调查、研究,并尝试运用方言来写作。这两个方面,均与文学革命的主张和新文学的写作实践相一致,可以说是新文学的早期尝试[3]213~232。
对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文学语言层面区别,我们向来的研究,多笼统地指出新文学对白话的使用,多强调五四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合流而取得的成功,但较少提到清末的国语运动,尤其是很少谈到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由于清末的“简字运动”所倡导的“简字”,并未成为后来新文学所使用的“文字”,所以,学者对它对文学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向来存而不论。但事实上,在清末白话报刊与“简字运动”的结合,这本身就说明这两者在观念与运思上的一致性。“简字运动”并未为五四新文学创造可供写作使用的文字,这一运动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是在“语言观念”层面,我们看胡适在文学革命的重要论述中对语言功能的认识,与清末的“简字运动”对此的认识基本一致。同样,我们知道五四文学革命及其之后的新文学创作中,对方言的重视,是被当作新文学语言贫乏的救急之策而提出来的。考查清末白话报刊就会发现,对方言的重视与写作尝试,在清末就已经开始了。
(四)白话报刊与新文学的文体
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一方面与白话这一通俗语言的采用有关。但同时,与白话文运动相伴而来的标点、分段分行的实践,对现代文体的形成,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没有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分行这些辅助的写文手段的运用,新式的白话文绝不是现在这样的文体。
新文学中的写实与讽刺两种风格,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中已成为一种显著的特征和潮流,并且在五四后的新文学中得到延续和壮大[3]268~298。
从文体革命的角度来说,清末的白话文,是要打破古代文学“正宗”文体的浮华虚饰和各种形式的拘牵,客观真实地呈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使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启蒙作品的写作与阅读中来,从而激发人们改变现状的革命意识。
清末的白话文作者,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无拘无牵的讽刺文体。这种文体,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大放异彩,为新文学的文体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刊物的“随感录”“杂感”等栏目中,登载了难以计数的庄谐杂陈的散文小品和杂文。这种讽刺的手法和文体,同时也渗透到小说、戏剧甚至新诗作品中去。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作家自身的分化,这种滑稽讽刺的潮流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以鲁迅的杂文为代表的尖锐的讽刺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温和的幽默风格。
(五)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除了思想主题、语言形式等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古代文学是以诗文为核心(“正宗”)的包括各式应用文在内的泛文学格局;而现代文学则是以小说为核心(“正宗”)的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大文类构成的现代文学格局[3]299。现代文学这一格局的最终形成,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倡导者借鉴西洋“文学”的概念,经过激烈讨论而确定的。但这一新的文学观念中所包含的各种重要文学种类,都在清末的文学变革,尤其是在白话报刊中,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或者说,现代文学观念与格局的形成,是以清末白话报刊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为基础演化而来的。
通过对清末白话报刊中文学栏目设置和各文学门类发展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所确定的新文学格局,在清末白话报刊中,已有明显的迹象和发展趋势。由诗歌、小说、散文、戏曲所构建的现代文学格局,与代表清末文学革新力量的白话报刊的实践与推动大有关系。
(六)风俗改良和“国民性”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文学中那种强烈的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与国民性批判思想,正是发动自清末的白话报刊,它虽历经辛亥革命前后的挫折而陷入低潮,但终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得以接续,并经五四启蒙群体的共同努力而结出硕果。所以,要论清末的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则风俗改良与国民性批判,是其前后演进中最重要、最密切的一环。
清末白话报中关于揭露陋俗之弊与劝解改良的文字之多、用力之勤,真是令人惊异而又感动。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扶乩(算卦)、烧香、拜佛、讲风水、敬鬼神、缠足、留辫、早婚、承继以及种种礼俗等等。白话报刊对它们的批判,或设专栏,或设专论,或作新闻,或穿插于小说、戏曲、诗词歌谣、图画等各式文艺作品之中[3]361~426。
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是启自晚清,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个宏大命题。甚至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搁置的跨世纪课题。清末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及其以后很长时期新文学对国民性问题思考和表达的连续性,充分说明清末白话报刊对五四文学具有先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的内容富有开拓性。当然,该书在对清末白话报刊语言的研究,还有深化的空间,还可以做得更细。如近几年来,语言学研究领域对清末白话报刊中所用词汇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多启示,我们可以从词汇学、语法学的角度,更细致地分析清末白话报刊在语言的革命性变化,这样我们就会对在语言层面,清末白话报刊在连接文言与五四新白话之间变革作用,有更清晰、具体的认识。
另外,《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在方法论的层面,也有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如作者对白话报刊史料的梳理和考辨,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作者运用文学之外的传播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尤其是利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阐释五四文白之争,对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总之,《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对清末白话报刊与五四文学革命关系的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在清末的萌芽和演进过程,可以进一步拓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文学革命发生背景和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