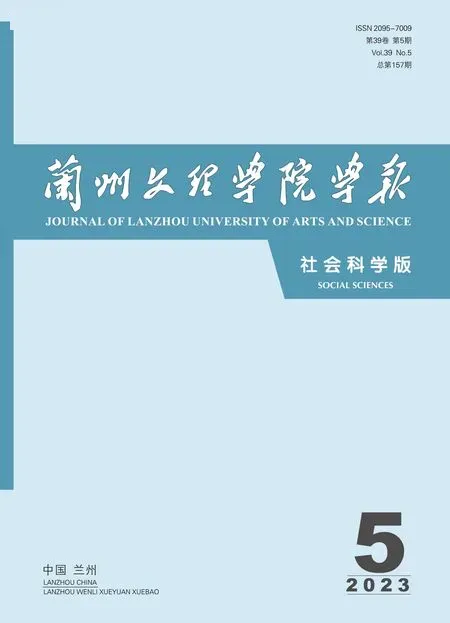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的社交媒体动员模式探析
——以自然灾害事件“重庆山火”为例
胡 玥张 泽
(1.兰州文理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3.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以技术发展为依托的社交媒体动员为大规模群体动员的发生提供了新路径,也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挑战。在“重庆山火”救援中,除了传统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动员外,社交媒体平台上个性化、离心化和扁平化的社会动员模式也得以显现。本文以“重庆山火”事件为例,探析在灾后救援过程中“全民动员”背后的社交媒体动员机制,以期为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灾后救援中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积极社会动员的引导提供可操作性参照。
一、过程与图景:“重庆山火”事件中的社交媒体动员机制
不同于大众媒介动员自上而下的理性认同机制,社交媒体动员偏向于自下而上的感性认同,即社交媒体的动员力量源于社会情绪,而从情感因子落实到群体行动通常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信息与情感的传播、受众接受信息并引发一定范围的心理波动、心理波动转化为实际行动[2]。截止2022年10月31日,以“重庆山火”为关键词在微博平台进行检索,共有491家媒体蓝V账号进行相关报道,累计达到28.7亿阅读量和58万次讨论量。在整个灾后救援中,社交媒体平台的动员力量通过三个阶段的逐步递进得以实现:首先,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报道通过还原现场、直击前线等时空路径从一线救援情况、后方物资支持、各界倾囊相助等方面向公众提供大量真实信息,为社交媒体动员的形成奠定事实与情绪基础;其次,“救援”“互助”等情感因子通过社交平台便捷的分发与扩散机制,短时间内在公众当中引发“感同身受”的心理波动,为社交媒体动员的全民行动奠定情绪共识;最后,形成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线上线下并存的社会动员力量。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队员张瑞坤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到:“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很多场‘打火’,但是像重庆这样全民上阵,如此尽心尽力为一线救火队员提供后勤保障的场景我还是头一次遇到。”[3]
(一)共情刺激:情感因子传播影响公众心理认知为社交媒体动员奠定基础
重大突发自然灾害的公共性、突发性、复杂性和危害严重性,一旦发生极易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在重庆山火相关报道中,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一方面通过情境构建使互助、救援、感动等情感性因子融入公众的共情机制中,另一方面积极塑造“救火英雄”和“逆行者”的典型形象为公众透过真实可感的救援形象了解现场提供可能,也为公众产生“和衷共济”的心理认知奠定情感基础。
1.情境构建使情感因子融入共情机制形成“全民动员”的情绪积极性
情感动员是贯穿于集体行动的主心骨和灵魂支柱,被视为集体行动的基础和开始[4]。同情心是人类最朴素的道德原动力,在“重庆山火”事件中,来自于一线救援的真实、朴素、本真的爱心和奉献极大刺激了公众本有的“同情心”。“重庆山火”发生后,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的救灾感人场景相关信息,以图文、视频等多种新闻报道方式让身处在不同时空的公众感同身受,产生“共克时艰 患难与共”的共情情愫。“休假武警挺身而出”“女骑士山火逆行”“社会力量集结驰援”等“苦难”叙事报道,让“共情”因子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传播,架构了从“感同身受”到“情感共振”的情感传播模式。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了便捷的意见表达渠道,为民众情绪的表达和传递提供保证,进一步巩固共情情境、扩大共情传播效果,最终形成了“全民动员”的超高情绪积极性。
2.典型形象塑造使救援现场真实可感实现共情情绪的延续
“榜样先锋”这一动员象征符号的运用对于说服、引导公众参与实际行动发挥着建设性作用。社交媒体平台中对逆行者“英雄主义”的叙事传播,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范畴而在更高境界上形成了公众的某种“精神信仰”进一步深化动员的形成。在“重庆山火”事件的社会动员中,专业媒体充分发挥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特点,根据不同行业领域选择最适宜的“领飞头雁”,渐已形成行动示范和号召,例如《重庆日报》8月23号在抖音发布的短视频《我就休息这一下,马上就好了》24日收获了844.6万+阅读量、3.4万+条评论,短视频中对摩托车志愿者群体冲锋在前的呈现,引发众多市民踊跃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给前线送物资。微博平台的话题互动中,众多志愿者的无畏精神也感动了不少网友,“小伙骑摩托车送物资”“重庆娃儿绝不拉稀摆带”“重庆山火市民踊跃报名志愿服务”等话题一次次冲上热搜。不同角度、不同体裁、不同平台的呈现与报道在舆论场中形成了“头雁”交替、“多雁领飞”的动员局面,保证了社交媒体平台海量信息中公众针对“重庆山火”救援共情情绪的延续。
(二)群体共识:杠杆两端共同作用构筑社会共识推动社交媒体动员
社交媒体基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现实社会人的身份、年龄、地域等具身特征,而形塑了“我们”的共同图景。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这类情感认同度相对较高的共同图景中,政府和公众、大众媒介和社交媒介的界限被打破,通过议程互动凝聚共同价值观成为在抽象化群体中建构广泛共识的有效手段,而这也恰恰是撬动社会动员这一省力杠杆的精准支点。
1.发言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凝聚共识,彰显家国情怀
在社交媒体动员中,少数人是指能够熟练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的主体,包括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体账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意见领袖账号以及一些个人自媒体。在“重庆山火”救援阶段,肖战、陈坤等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粉丝效应的明星艺人相继在微博社交平台上发文,助力重庆救火行动,彰显家国情怀。这些明星艺人作为媒介新形态中的“扭转博士”或“公关大师”,在“众志成城抗山火”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淘析作用。“一起守护这座城”的话题经由他们得以进一步广泛传播,并通过跨界、跨平台、跨圈层的形式自上而下在公众群体中产生现实力量,并与网络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级传播形成合力,最终促成转发聚力、众筹捐款、共同守护等线上线下一致行动,凝聚起“让我们一起为重庆助力”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2.沉默的大多数:甘于奉献道义担当,共绘互助共识
社交媒体平台的强扩散性,使得社交媒体动员的参与者不仅有与事件直接相关的群体,还有与事件无直接联系的其他公众[5]。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与事件无直接联系的公众愿意积极参与到社会动员中更多是源于人们朴素的同情心和甘于奉献的道德担当。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评价尺度历来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深受这一道德评价尺度浸润的中华儿女也形成了甘于奉献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在“重庆山火”救援中,“看到母亲的朋友圈里面,东城社区在招募志愿者”——18岁的余秋朋第一个走出高考考场,又第一时间报名志愿者;“听朋友说在北碚参与灭火的志愿者比较缺毛巾”——一位宝妈带着萌娃,连夜赶往歇马镇送物资等,具有朴素同情心和道义担当的公众共同描绘出“中国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最大的同心圆。
(三)集体行动:全民行动与圈层行动并存使线上动员在现实空间凝聚力量
个人个性化和集体微动员的聚合是社交媒体动员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社会关系网的多级传播叠套中,个人只需贡献星火之力就能参与到动员中。社交媒体作为网络集体行动的便捷沟通工具,在激活用户和提升参与度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6]。且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之间形成的“弱联系”有效舒缓了网络“搭便车”问题和对政治动员“强关系”的依赖。
1.圈层行动:价值认同、情感共鸣为依据的人群聚合的必然结果
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以地缘和血缘为主的人群聚合,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化、信息服务的多样化和信息需求的差异化,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群聚合的主要依据。相较于现实社会的人群聚合,网民能够更自由地选择是否加入某一网络社群,而一旦因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形成圈层,圈层内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会呈现出显著的同质性与排他性,但圈内网民对所在圈层具有高度依赖度和信任感,信息传播也更加高效[7]。在重庆山火事件媒体报道中,不同圈层之间的关注焦点不尽相同,但在圈内“意见领袖”信息筛选后,则更易获得特定圈子的好感和认同,并引发更具信任感的“二次传播”。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用户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信息互通与链接互动,8月17日至26日的十天时间中,21个关于重庆山火的话题登上热搜[8],重庆山火的议题迅速被动态扩散,网民之间的讨论也开始在不同群体或圈层间实现情绪共振,进而发展为线上或线下的集体行动。
2.全民行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核心的中国精神的内在要求
社交媒体动员的平民化、草根化倾向中和了政治动员的权威化、程序化与制度化机制,在社会媒体动员中少有自上而下的阶梯式精英动员,更多是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圈层化传播。但在灾难面前,中国精神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无形中凝聚着民众与中国力量,公众线上在社交媒体平台自由表达看法、倾诉情感,线下各样志愿者既组“兄弟连”、又组“夫妻档”的爱心和坚守,普通市民主动请缨、能帮尽帮的热血与热情,各种职业人发挥专长、做好“必须要做的事”的奉献与坚守,丰富了重庆救火议题并促进了信息“线上线下同心圆”的交互传播。同时,主流媒体在各类社交平台的推送、各种“头雁”示范的带动以及重庆人民在微信朋友圈、视频直播圈、组织兴趣圈等多维度、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五行八作、男女老小云集响应“为重庆加油”的动员力量传递和层层高潮。天灾面前,通过社交媒体串联起的社会救援力量发挥出了关键的作用。包括一线武警、消防、各个地方的党政干部、民兵,以及志愿者,本次共计有2万多人投入了重庆的森林灭火战斗。
二、祛魅与反思:“重庆山火”社交媒体动员的潜在风险探析
在“重庆山火”救援中,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与社会动员为救援力量和物资的聚合提供了便利的通道,但社交平台上碎片化信息的传播难以完整描述事件信息、自由场域的弱监管导致谣言不止、圈层化传播中的松散连接难以形成真正一致的社会共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庆山火”的高效救援埋下隐患。
(一)情感元素运用易引致善恶两极
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交媒体平台叙事体系呈现出明显情感转向表征,要实现通而乐受的信息传播效果也需要更多关注情感性语言的运用。在重庆山火的报道中,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平台都充斥着围绕个人或群体动人故事展开的“感性语言”,通过征引“守护”“付出”“爱心”“感动”等情感元素,在事件“当事人”与受众、报道与受众之间形成情感共振,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到集体救援中的积极性。但低门槛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为公众宣泄情绪开凿了另一扇窗,网民可以在相关平台上更便捷地观看爱恨情仇、更自由地发表酸甜苦辣、更舒服地表达喜怒哀乐,在灾害发生后也更容易导致负面情绪的迅速传播和累积,直接导致集体行动中夹杂着偏激的个人情绪。同时,社交媒体以情感为纽带在发挥首发动员作用时,也存在着过于感性而偏离理性的“离心”风险:在社交媒体上,随着容易失真、情绪化色彩强烈的“民意”在拟态环境下的迅速传播,传、受双方更容易以游戏的态度随意地表达意见,随之轻而易举地完成关于公共事务的集体偏执性想像,甚至产生“网络多数人的暴政”。“重庆山火”救援期间,IP地址显示在北京的一个微博账号“天马独行121”故意用“山火那么厉害,空军不是也很牛的吗?怎么不去灭火呢?”“运20大肚子装上水,来个几十几百架次的,扑灭山火,应该是个好主意,您说呢?”等阴阳怪气的语言诋毁党和政府的救援方式。不仅有境内的,还有地址来自境外美国的账号“村民阿贵2022”称“最珍贵的是人民,就应该疏散而不是上山救火”;来自英国的账号“老曲-LQ”也叫嚣“人民已经交税了,此时政府责无旁贷”[9],皆把人民与政府撕裂开来拉仇恨,“离心”风险不可回避。
(二)谣言极易传播易引发是非难辨
建立共识是规范和约束人们采取一致行动的基础,行动一致性是人类应对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关键所在[10]。与传统“封闭的”空间相比,在社交媒体公共领域中多元主体可以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协商、发表言论、宣扬立场,在交流中整合成为真实民意而主导虚拟空间,并进而影响现实生活。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发生后,巨大的恐慌和短期的信息真空导致公众情绪极度焦虑而成为谣言传播的黄金时间,多主体、多渠道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助力”谣言的迅速传播。根据1953年克罗斯提出的谣言产生的公式:R=I*a*c显示,人们对事件越重视,信息越模糊,谣言的流量就越大,影响就越广。自然灾害事件的突发性和严重性,使谣言容易借社交媒体的“熟人空间”迅速传播,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且极具蛊惑性。低门槛的多主体传播夹杂着后真相时代弱信息而强情绪的显著特征,使得社交媒体平台的虚假信息极易传播而导致是非难辨,进而影响到社交媒体动员的有效性和有序性。“重庆山火”发生后,从8月21日开始谣传的山火导致停电到火灾扑救过程中许多微信群号召居民进行募捐,流传无人机将志愿者砸致重伤、挖掘机翻倒砸伤志愿者、北培区扣押志愿者车辆等,谣言借着社交媒体的便车无孔不入,使得网民因为难辨真假而不知如何指导行动,直接影响救援有效性。
(三)松散连接行动易导致难于管控
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媒介权力的增加总是伴随着媒介掌控信息的权威弱化,网络用户之间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裂变性和及时性对“把关”的消解,逐渐作为独立的“网络节点”形成了松散的自组织联盟,其连接与互动形式表现为一种“网格化”“扁平化”的网络组织结构[11],此结构下的网络集体行动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由科技手段而组织起来的,在实施时不需要集体性身份认同和不同层次的组织性资源的“连接性行动”[12]。“重庆山火”救援动员中自发性的社会大众组织作为政治动员的后援支撑,开展疏松的组织性协调工作,再借助社交媒体场域中的“共享与同产”来交结不同参与主体,形成一种“弱关系”型的人际联结,通过公众个人化的路径来协调彼此行动。但过度松散的社会动员在制度化、组织纪律性不高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使执政者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弱关系的“连结性行动”作为一种集体操纵行为,容易引发新形式的“搭便车”行为和产生危机时刻的动员秩序混乱现象。扑救山火期间,《东方网》8月26日报道了原本是十几个人假冒志愿者带女性上山围观山火,被交警发现制止并暂扣了摩托车的事件,却被造谣称“重庆志愿者骑摩托车上山送物资未戴头盔被交警罚款”,造谣者甚至还出现在灭火现场,穿着志愿者衣服假冒志愿者进行直播,并重复着谣言[9]。由于社交媒体动员没有具体成文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性,别有用心的人不仅在线下给集体行动添乱,而且在线上也造谣生事污蔑官方形象,对此网友们评论道:“去添乱还造谣,真是想红想疯了,真丢脸。”勒庞指出,“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他们目前的组织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力量。”“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13]
三、守正与创新:社交媒体动员正向效能运行之路
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在带来显性实体伤害的同时,也会给公众心理造成无形的隐性损害。社交媒体介入动员积极作用的发挥能够更好促进公众民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治理,但面对社交媒体动员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政府、平台与公众也需要及时改弦易辙。
(一)政府:冲破传统思想束缚,以系统观念凝聚社会力量
1.完善社交媒体法制建设,传播正能量凝聚理性共识
以情感动员为首发的社交媒体动员易受到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过激、片面、充满圈层对立的舆论环境容易将无助、愤懑等负面情绪过度放大,导致在社交媒体动员过程中出现不理智的过于愤怒倾向。社交媒体在社会动员上发挥的正面功效得到充分认可的同时,其情绪过激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规范的有效管束,例如敏感词规避制、实名准入制、煽动言论责任追究制、网络舆情监测制等,以规制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情感动员行为的负面效应。此外,充满正能量、奋发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有助于社交媒体情感动员更加理性化,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保持谨慎、客观的立场。为规避情感动员风险,防止情绪极端化风险产生,也需要尊重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加强对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引导,营造心正气和的社交媒体舆论氛围。
2.善用社交媒体舆论资源,提高制度化聚引民间力量
媒介化社会的逐渐形成与发展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具体工作中,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更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注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14]。一方面,政府要主动通晓社交媒体平台发展的情势,了解社交媒体平台公众的真实诉求,建立健全政务社交媒体体系,打造自己的发声筒,争夺网络话语权。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在社交媒体上及时开辟“谣言诊所”,建立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减少大众的信息盲点、凝聚大众对突发事件的认知共识,引导大众正确、理性的集体行动。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政府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做好公共服务,注重采用组合式的动员策略,加强对民间组织力量的汇聚和引导,进而形成“融合动员”的合力交叉覆盖更多的人民群众,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理想效果。
(二)平台:坚持共建共享机制,以问题导向履行主体责任
1. 以算法机制为依托疏通信息传输渠道,打破信息壁垒
网络圈层内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呈现出显著的同质性与排他性,当前大多平台借助算法推送技术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兴趣和爱好的新闻产品,以匹配受众需求增强用户黏性,但不可否认这一推送技术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在以海量信息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反而将受众“封锁”在特定信息范畴内。因此要打破信息壁垒,就需要平台以算法机制为依托,在追求用户黏性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效益,疏通信息传输渠道,引导圈层间信息互通有无,将圈层的小众文化观点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相结合,为百花齐放提供渠道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发挥内容优势和通达优势打造优质信息大环境,为高效的社会动员奠定聚力基础。
2. 合理监管做好平台信息内容治理,完善辟谣机制
社交媒体动员的高效运行以准确、及时的信息传播为前提,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公众等多主体发布、传播信息的聚合平台,在多主体信息协同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要及时制止谣言的传播,平台需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首先,需要基于平台技术优势,识别虚假信息,不断完善谣言识别体系和辟谣机制。其次,平台也可以借助广大公众的监督力量,建构有效的反馈监督机制,鼓励每一位用户主体参与到信息监督中。最后,社交媒体平台也需要结合平台自身信息传播特点,形成一定的处罚机制,例如限制发言甚至永久销户等。
四、结语
在后工业民主体制与社交媒体时代的双重裹挟下,社会发展变得破碎无序,情绪化表达和追求瞬间效果的碎片化传播使得社会难以理性整合,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单纯依靠传统政府的组织力量难以形成有效应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社会动员也需要顺应时代环境的嬗变将社交媒体充分考虑与吸收,利用其极易生成的共情传播、省力杠杆和圈层传播在动员组织形态与人际网络层面不断尝试改变,渐渐框架起一种弱关系“连结性”的社会动员机制,有助于将处于“脱嵌”危机的个体“再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解决现代社会液态性语境下的个体困局,重塑人与社会的互动嵌入关系,进而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全新集体行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