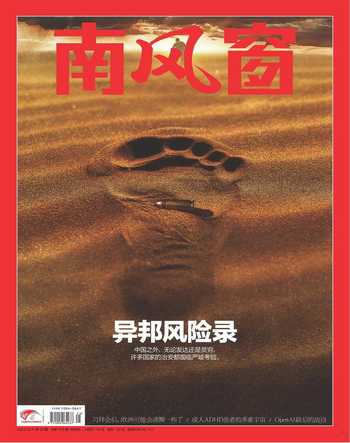背包闯天涯,毒贩、枪口与黑警
张侃

从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来到一个“总统府装防盗网”的国家,看到街上多是被杂乱涂鸦破坏的公共设施,我在很多地方甚至都不敢拿出相机。
这就是号称“南美最发达国家”的智利。那些依旧彰显着昔日荣光的精致欧式建筑,对比跟经济状况极不相称的城市安全问题,显示出极度反差与讽刺。我没想到,4年前智利因游行骚乱取消APEC会议的荒诞剧,到今天依然留有余绪。
对陌生国家的传统印象往往并不可靠。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领事服务网”不断更新着旅行警告,从中可见一个仍然充满动荡、战乱,处于风云诡谲之中的世界。谨慎、暂缓或避免前往警告名单上的国家,是绝不能大意的。即使是去未出现在警告名单上的国家,出发前也要多搜索当地新闻,防备当地刚刚发生变乱,最好是提前购买旅行保险,并时刻谨记“财不外露”。
作为职业旅行撰稿人,我对于“数字游牧民族”的装备经验丰富,但本文的写作还是遭遇了“连日断网”的不测。原本,驶往“南极三岛”的船上有星链提供的免费网络,我就想着在船上交稿,结果在见到南极洲后不久,网络就突然断了;海上漂了多日,回港后这才有网,许多事已耽误。当然,这跟我近10年旅行中遭遇的下述安全事件相比,还不算什么。
在马来西亚公墓误入险境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一直是中国人喜欢的出国旅行目的地。通常来讲,这三国的社会较为安全,游客一般不会遭遇太大的危险。但此话并不绝对,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我就与一次实实在在的风险擦肩而过。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华人义山(公墓),是近几百年间移居到当地的华人最集中的安葬处,內部又分为广东义山、福建义山等,占地面积巨大,几乎可谓一望无际。而几乎所有当地华人历史中的著名人物的坟墓,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在除清明节这样的公共祭扫日之外,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整片华人义山区域几乎不见人影。在吉隆坡这样一座国际都市的市中心,竟有这样一块专属于已过世者的大片空间,是吸引我来到这里的最主要原因。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流连于周边的各座义山,细细辨读那些凝聚了整个吉隆坡华人史的墓志铭。当时,身处在这个安详的环境之中,我没有感到任何不安全。
直到天色渐暗,我也准备离开义山时,我才发现了一点点不对劲:一座墓碑前,几个相貌明显不是华人的人,似乎在一边抽烟一边低声聊着天,而旁边停着几辆摩托车。我不知道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尽管一些民族并不像华人这样忌讳坟墓,但似乎也没有必要特地跑到外族的坟墓前聊天。
起初,我并没有太多去联想这个奇怪的场景,以为只是个巧合,直到我又遇到了一位华人大姐,她说自己是受托来维护坟墓的。“你赶紧离开这里!”当得知我只是一个来这里的中国游客,她惊恐地冲我喊道。她指着刚刚的方向,压低声音问:“你看见那几个人了吗?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我说自己一无所知。她叹了口气,告诉了我那些外族人出现在华人公墓的真实原因—他们在趁着黄昏交易毒品。“如果你让他们看见了,而你又是个外国人,不会讲马来语,那一定会产生误会的。轻则你被抢,重则……唉……就是很不好的事情。你赶紧走,赶紧走啊!”
越野车突然停了下来。在我微弱的车灯照射下,我只见左右两侧车门同时打开,两个武装人员拿着各自的步枪和手枪下了车,向我走来。而他们的脸上,是那种专属于军人的冷峻。
我从未想过,在被认为安全的吉隆坡,在这座安静的华人公墓中,竟然正在进行着在中国只有电视剧中才存在的毒品交易。我谢过她,惊恐地朝墓园的门口奔去,用最快的速度,在几分钟内离开了那里。而就在那几分钟里,我又看见好几辆摩托车,载着同样明显不是华人的人进入这座墓园。
在白俄罗斯深夜遭遇枪手
2018年,我在欧洲跨国自驾旅行。那时白俄罗斯尚未对中国公民免签,但得益于2018年世界杯期间俄罗斯的“持球票可免签入境,并可经白俄罗斯过境”的优待政策,我临时决定从立陶宛折向之前从未计划要访问的白俄罗斯。
亲俄的白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向敏感,因而我开车入境白俄罗斯时,遭遇的检查也格外仔细。当时世界杯的免签政策刚刚发布,让边检人员弄明白我为什么可以免签入境,以及等待他向上请示,并最终办完所有手续,足足花了5个多小时。当我正式进入白俄罗斯境内时,已是深夜10时多。
最初,我的计划是在边境附近寻找安全的地点,在车上过夜。这是我在欧洲时惯用的方法,然而漆黑的夜色让这个想法变得毫无可能。离开了欧盟,手机也不再有信号,我也无法临时寻找并预定附近的住宿。无奈之下,我只好开车驶向本计划第二天入住的民宿,希望老板还能接待客人。
前往那里需要途经的公路,正位于白俄罗斯与立陶宛的边境线附近。那里不仅是北约与“俄白联盟”剑拔弩张的对峙点,也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欧洲难民潮”中难民最常选择的非法过境地点之一。起初,深夜的公路上见不到一辆车,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有一辆越野车始终不紧不慢跟在我身后。
又过了一会儿,那辆车一脚油门冲上来,将我逼停。车身上并没有明显标志,而从车上下来的两个武装人员,尽管都穿着迷彩服,但我也无法识别他们的具体身份。其中年轻的那个人会讲一点英语,我向他解释了我是刚入境的游客,正在寻找预定的民宿,并给他看了地图上的坐标。
“跟我走。”他冷冷地说道。我不知道他们要带我去哪,但跟他们走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那辆越野车带我沿公路又向前开了一段,直到他们突然向左转进了一条泥泞的土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入这条几乎无法行驶的小路,而当继续行驶了一段时间后,路更是开始泥泞得完全无法通行,似乎已到达整条路的终点。
就在这时,越野车突然停了下来。在我微弱的车灯照射下,我只见左右两侧车门同时打开,两个武装人员拿着各自的步枪和手枪下了车,向我走来。而他们的脸上,是那种专属于军人的冷峻。
如果说我在旅行途中有那么几次感到“濒死”的瞬间,这绝对属于其中之一。时光似乎在那一刻停滞了,我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在这泥泞得几乎随时都能将车陷住的路况下,调头或倒车逃走完全不可能。而在这咫尺之间的距离下,他们只要一发子弹,就能立刻结束了我。
“先生,先生!”年轻人敲车窗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他没有对我举枪,而是用有点愧疚的语气说道:“真抱歉,我们也找不到您说的那个地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刚刚他们只是想带我去找那家民宿。而这时,我也看清他身穿的制服—他们是白俄罗斯的正规边防军人,而不是什么不明武装分子。我悬着的心终于算是放了下来。
我请他们帮我推荐附近其他住处,他们随后将我带到了一座网上查不到,似乎本地人才知道的度假村。当我第二天开车寻找之前定好的那家民宿时,我才发现—他们前一天带我走的那条泥泞小路是对的,只要再向前开一点,就是民宿所在的位置了。
令人咬牙切齿的蹲点黑警
在很多国家,游客遇到的麻烦可能不仅来自那些犯罪分子,而且有可能来自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府人员。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2018年跨国自驾期间,当时我刚刚游历了摩洛哥,打算开车越过边境,进入同样位于非洲,但属西班牙管辖的飞地休达(Ceuta),从那里搭船回到欧洲大陆。
在距离边境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两个躲在路边的警察拦下了我前面的那辆车,当时我正紧跟它行驶。在简单对话几句后,警察挥手示意前车可以离开,却向我的车走来。
“护照和驾照。”一个警察用英语对我说。我以为只是常规的边境检查,没有任何怀疑,就将证件递给了他。他拿到了我的证件,却接着说道:“你超速了。这里是城市,限速60,你开到了72。”严肃的表情之下,他的嘴角却有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
距离当天的末班从休达开往欧洲大陆的渡轮起航,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算上过境的时间,如果不立刻交上罚款,拿回证件走人,就意味着我可能要在摩洛哥或休达额外滞留一晚了。
我跟着他的指引驶向路边,随后试图质疑他处罚的依据—我刚刚紧紧跟着前车行驶,为什么只有我超速了,而它却没有?没想到,这时那个警察却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刚刚解释得一清二楚的英文却变得一个字都不会说了。他装作听不懂一切我的质疑:“要么阿拉伯语,要么法语,这里是摩洛哥!”他用鄙夷的语气对我说道。随后,他给了我一张写满阿拉伯文的“罚单”,我唯一能看懂的是上面写的:300迪拉姆。“交钱。”他对我说。
正当我绞尽脑汁盘算该怎么向他解释,去除这个误会的时候,我发现后面更多的车,正被他的同伴不断引向我们所在的路旁。有趣的是,这些车都有同一个特征:挂的都是外国牌照。我看了下手表,距离当天的末班从休达开往欧洲大陆的渡轮起航,只剩下一个多小时。算上过境的时间,如果不立刻交上罚款,拿回证件走人,就意味着我可能要在摩洛哥或休达额外滞留一晚了。而这,应该就是他们在这个时间集中拦下挂着外国车牌的车辆,肆无忌惮地索要罚款的原因。
我不得不交上这相当于200元人民币的罚款,拿回我的证件,并最终赶上了当天最后一班船回到欧洲。而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后面:根据我查到的摩洛哥法律,为了避免腐败,罚款应该是拿到罚单后直接交到政府的银行账户的。于是,我又仔细看了一眼手中那张“罚单”,发现上面既没有我的身份和车牌信息,也没有汇款银行账号的信息。也就是说,所有我们用现金缴纳的“罚款”,其实都是到了那些警察个人的腰包里。
怀疑感染新冠,焦灼万分
旅行中遇到的危险也包括身体健康问题,而由于对当地医疗机构的不了解,在海外就医往往很难获得与国内就医类似的效果。而若感染的是一种未知的传染病,则可谓是其中最糟的可能性。
2020年2月,就在国内武汉新冠疫情乍起、世界多国纷纷对从中国入境人员采取限制措施之时,由于我已计划好前往美国的采访任务,而美国又限制入境人员必须离开中国满14天方可入境,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先前往欧洲,打算等到离开中国满14天再去美国。
我在欧洲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一场寒流刚侵袭了那里,而此时的我也“适时”咳嗽了起来。放在平时,没人会在意降温后的咳嗽,然而,我当时却是刚从中国离开。尽管我国内所在的城市当时并没有严重的疫情,但没人敢说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与此同时,我还感觉自己在发烧,然而去买了体温计却只测出正常体温,而我又开始怀疑体温计有问题。在童年时代听闻“非典”严重症状带来的恐惧下,我越发怀疑自己就是感染了新冠。

我在宾馆房间躺了两天,只感觉症状在不断加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一家当地声誉不错的私立医院。当大夫听说我刚离开中国,而自述症状又与新冠如此相似,立刻礼貌地要求我前往罗马尼亚治疗新冠的定点医院—国家传染病中心。
与那座整洁明亮的私立医院相比,这座罗马尼亚最中心的传染病研究与治疗机构,却破败得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在一个拥有中等收入水平的欧盟国家。对于新冠疑似患者的治疗,那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指引。经过多番询问,我才被引导到了负责的部门:传染病实验室。没有任何严格的隔离措施,甚至其中的工作人员在面对面听我讲完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的经历后,才不慌不忙回到房间,草草穿上了防护服。
我在那里从早等到晚,无数人在我这个“疑似新冠患者”面前进进出出,其中也包括一些看起来明显有症状的病人,让只戴着一层N95口罩的我更加慌乱。
他拿棉签在我鼻腔和口腔各转了几圈(我当时尚不知道这就是“核酸检测”),然后便让我在门口座位上等待。我在那里从早等到晚,无数人在我这个“疑似新冠患者”面前进进出出,其中也包括一些看起来明显有症状的病人,让只戴着一层N95口罩的我更加慌乱。直到傍晚,我才拿到了他们的检测报告,显示新冠、流感等病毒的核酸检测都为阴性。我这才如释重负。
奇怪的是,等回到宾馆,那些奇怪的感觉居然自动消失了!由此证明,我之前对自己病症的怀疑,只是在国内铺天盖地新冠相关新闻的包围下,自己的心理暗示罢了。然而对罗马尼亚国家传染病中心一天的近距离观察,却让我心中隐隐产生了怀疑:这样简陋的机构,这样敷衍的工作人员,真的能应付得了万一入侵的新冠病毒吗?
区区一个月后,新冠病毒便在欧洲开始肆虐,与病毒在国内短时间内得到控制不同,欧洲的疫情一直反复持续了几年。而从在罗马尼亚观察到的情况看,这几乎可谓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