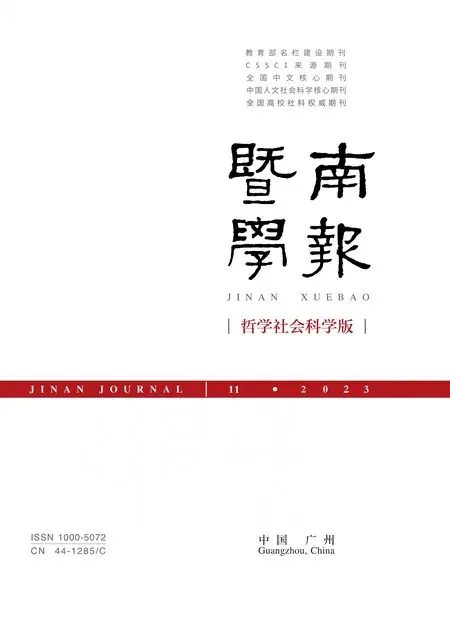振衰起敝:西夏至元代敦煌的凋敝与繁荣
杨富学
关于晚期敦煌的历史,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敦煌在西夏时代非常繁荣,在元代却相当荒芜。这一认知对晚期敦煌石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人多由此为出发点而得出结论,认为西夏时代有条件大规模营建石窟,元代则不可能。其实,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晚期敦煌的兴衰历史恰巧颠倒了。若不能纠正这一错误认知,便无法正确认识在西夏与元代,敦煌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也就难以走出敦煌晚期石窟研究的困局。有鉴于此,笔者不避浅陋,意在让证据说话,还敦煌历史以真实。
一、西夏至元前期敦煌之荒败
西夏曾于1036年击灭曹氏归义军政权,占领瓜沙地区,但由于瓜沙一带回鹘势力强大,加上地域偏远,对初立国的西夏来说战略地位并非那么重要,故西夏的战略中心一直在东方地区,且一度容忍沙州回鹘国政权的存在,直到1067年以后才取代回鹘而实际统治瓜沙二州。(1)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299页。1227年,瓜沙入蒙古。
至于瓜沙地区在西夏国时代的经济文化状况,史书罕见记载,《宋史·夏国传》仅提到沙州二次、瓜州四次,而且都无关紧要。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当高于沙州,但总体而言,二者均显得无足轻重。(2)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西夏统治时期的瓜沙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尤其是大安八年(1082),西夏将瓜、沙州之民外迁,“十人发九”,使本来地广人稀的瓜沙二州的经济雪上加霜,传统的农业生产不复存在,变成“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3)(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六、三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370页。的牧业经济区。夏仁宗所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西夏各地要按期上报财政收支情况:“两种一年一番当告:沙州、瓜州。十六种六个月一番当告:肃州、黑水……京师界内、五州地、中兴府……一律三个月一番当告。”(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531页。西夏辖境诸州每个季度或半年要向西夏中央申报一次财政状况,独沙州、瓜州例外,一年申报一次,足见西夏时期瓜沙二州经济地位之不彰。宋元之交史学家马端临言:自河西被西夏占领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5)(元)马端临:《舆地考八》,《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7页。诚切中肯綮之论。
令人称奇的是,在既往的研究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西夏时代瓜沙地区繁荣,故而有能力大规模营建石窟,元代敦煌衰败,故不可能大规模营建石窟。如谢继胜先生即曾断言:“北区的一系列石窟都是出自西夏人之手,计有462、463、464和465,此外B77窟也是西夏窟。南区的第3窟作为元窟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一系列窟室的建立、规模与西夏人尊奉佛教的热诚才能适应,以前学者认为的元窟很可能是元代修补的西夏窟。”(6)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大致相同的观点,又见于沙武田教授的论断,认为元代敦煌荒无人烟,不具备修建大型石窟的条件。(7)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上述论断依据何在?未见论者列举,不得而知。
言西夏时代敦煌地位重要,主要证据出自清人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的有关记载:
[天盛十七年(1165)]夏五月,任得敬营西平府。任得敬志篡夏国,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论者认为,既然西夏权臣任得敬“想把西夏皇帝夏仁宗安置在瓜、沙,说明瓜沙地区主要是夏仁宗的地盘,尤其是西夏自建立政权以来就开始长期经营的瓜州,可以作为夏仁宗分国后的首都,证明夏仁宗对瓜州的情况很熟悉,甚至喜欢此地,也很可能到过榆林窟礼拜供养”。(9)何卯平、宁强:《敦煌与瓜州西夏时期石窟艺术的比较研究》,《敦煌研究》2016年第6期。
关于任得敬分国事,吴广成未注明史料出处。检诸古代文献,可与之呼应的记载有二,均见于《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其一,“大定十年(1170),[仁孝]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10)(元)脱脱:《夏国传》,《金史》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69页。其二,大定十年(1170)“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上表谢。其谢表曰……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11)(元)脱脱:《夏国传》,《金史》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70页。
梳理史料,不难看出,任得敬分国确有其事,事发天盛十七年(1165)夏五月至大定十年(1170)八月之间。夏仁宗迫于无奈,假意与任得敬分国,调虎离山,而后斩之。这是古代帝王对付权臣的惯用手法,安可言夏仁宗曾居瓜沙哉?退一步讲,设若任得敬篡权成功,则夏仁宗自为废帝。篡位者不杀旧主,已属万幸,安有主动割地让其在瓜沙自立为国之理?
观《西夏书事》之记载,与“瓜沙”对应的地方是“灵夏”。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四日,司马光上《横山疏》,其中有言:“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12)(宋)司马光著,王根林点校:《司马光奏议》卷二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这里同样将“灵夏”与“瓜沙”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又将“幽蓟”和“蔚朔”相对应。天福元年(936),后晋石敬瑭以幽、蓟……朔、蔚十六州割让契丹,次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成为辽朝五京之一。以辽帝国政治中心之一的“幽蓟”与最偏远的“蔚朔”相对应,其状与作为西夏中心区域的“灵夏”与最偏远的“瓜沙”相对应的对比排列何其似也。言仁宗居瓜沙,乃古代史家常用的“绕笔”写法,不可曲解。
质言之,西夏国时代的瓜沙地区是相当荒败的。言其繁荣,实出无据,最起码从现有的史料与考古证据看,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西夏时代敦煌的繁荣与昌盛。
西夏时代敦煌衰败之状,在元代前期得到延续,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瓜州在西夏时已“州废”,沙州于1227年入蒙古后,依照“西夏故地全部被赐作诸王驸马分地”(13)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的传统,以沙州“隶八都大王”,(14)(明)宋濂:《地理志三》,《元史》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0、1451页。成为术赤子拔都的分地,沦为牧场。蒙古在攻灭西夏的过程中,“戈矛所向,耆髻无遗”(15)(明)宋濂:《文宗纪二》,《元史》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39页。,导致河西地区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瘠野圹,十未垦一”。(16)(明)宋濂:《朵儿赤传》,《元史》卷一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55页。在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河西地区又作为“分地”被赐给了阔端亲王。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之位后,开始将内地人口移入河西,以充实空旷的土地,但雄踞西域地区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诸藩王因不服忽必烈之继大汗位而倡乱西北,嗣后四十年,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西域地区战乱不已,致使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整个肃州路仅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17)(明)宋濂:《地理志三》,《元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0页。敦煌的情况可想而知。1275年,景教僧拉班·扫马(Rabban Sawma)由大都房山十字寺出发,西行欧洲,行记中完全没有提到敦煌,只是说他们从河西到于阗,“沿途偏僻荒凉,万物不生,沙漠中更是荒无人烟”。(18)E. A. Wallis Budge,The Monks of Kbili Kha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Mongol Khan to the Kings of Europe,and Markosn who as Mar Yahbh-Allaha III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Asia,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28,p. 138.大致在此前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履践敦煌,记当地“无商业,唯农人,多小麦”。(19)Thomas Wright,Travels of Marco Polo,London:Henry G. Bohn,1854,p.105.彼时敦煌衰败之状,可见一斑。
二、蒙古豳王家族入居与元后期敦煌之振兴
关于元代敦煌的社会经济状况,论者或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敦煌走向衰退”,(20)沙武田:《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绘于西夏时代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或言元代的敦煌“是元帝国一个为流沙掩映的边城”。(21)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如果将这一观点限定在元代早期,完全符合史实,但推诸元代晚期的敦煌历史,则不免方枘圆凿矣。
忽必烈于1260年继蒙古大汗之位,绳其祖武,继续征伐南宋王朝。1276年,元军占领杭州,宋政廷南渡。1279年,宋帝赵昺在崖山自尽,宋亡。彼时西北地区正经历叛王的蹂躏。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载,回鹘国都高昌于1283年陷入蒙古叛军笃哇、察八之手后,回鹘王被元政府迁至今甘肃永昌一带居住。嗣后,哈剌火州一带成为元政府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争夺西域控制权的主战场,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
正当蒙宋激战方酣的1276年,原属于西域察合台汗国的哈班、出伯兄弟因不满西北藩王的叛乱,率部投于忽必烈麾下,受到重用。至元十九年(1282),世祖命令大将旦只儿“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叛王兀卢等战,胜之”。(22)(明)宋濂:《旦只儿传》,《元史》卷一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31页。至元二十年(1283)春正月“赐诸王出伯印”。(23)(明)宋濂:《世祖纪九》,《元史》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9页。大德八年(1304),又“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24)(明)宋濂:《成宗纪四》,《元史》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1页。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进封豳王,(25)(明)宋濂:《诸王表》,《元史》卷一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38页。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思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Quyātmïš)被封为西宁王,驻于沙州。是年,豳王喃答失(Nūm-Tāš)去世。十二月,忽答里迷失晋封豳王。(26)(明)宋濂:《文宗纪二》,《元史》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45页。其位由出伯孙速来蛮(Sulaimā)继袭。(27)(明)宋濂:《诸王表》,《元史》卷一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39页;《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亦载至顺元年(1330)三月“甲戌,封诸王速来蛮为西宁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55页。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īliqjī)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28)(明)宋濂:《顺帝纪一》,《元史》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22页。驻于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子宽彻(Kūnchek)于天历二年(1329)八月被封为肃王,(29)(明)宋濂:《文宗纪二》,《元史》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39页。驻于瓜州。(30)[日]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ャガタイ家」,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版,第677—686頁;[日]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年版,第312—321頁。出伯家族拥有豳王、肃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四个王号,其中豳王和肃王都是一等王,可谓显赫一时。
至元十四年(1277),废弃已久的瓜州被重新设立,属沙州路。(31)(明)宋濂:《地理志三》,《元史》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1页。至元十七年(1280),升沙州为沙州路总管府,隶属于甘肃等处行中书省。(32)(明)宋濂:《地理志三》,《元史》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0页。至元二十六年(1289),因“瓜、沙二州城坏,诏发军民修完之”。(33)(明)宋濂:《世祖纪十二》,《元史》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7页。今天所见到的瓜州锁阳城,就是元代的遗物,其四个城角均呈圆形,与中原传统的方型城角不符,当系受到西亚、中亚伊斯兰文化影响所致。出伯家族由中亚东迁而来,有着浓重的伊斯兰文化情愫。推而论之,元政府于1277年在瓜沙地区的举措,当与1276年出伯家族的东归及其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活动不无关联。(34)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
元朝灭南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唯有西北地区仍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那就是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旷日持久的叛乱。世祖、成宗二朝,元帝国实际辖区西部与海都、笃哇叛王军事对抗的前线主要在新疆东部地区,尤其是哈密一线。(35)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为因应这一形势,元政府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比较特殊的政治、军事管理体系。至元十八年(1281),甘肃行省设立,治甘州路(今甘肃张掖市)。元贞元年(1295)后辖境稳定下来,统辖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州路、亦集乃路、宁夏府路、兀剌海路和山丹州、西宁州,(36)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4—460页。相当于今甘肃黄河以西、宁夏大部和青海黄河以北,日月山以东地区。元代诸地行省主要掌国庶务,“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37)(明)宋濂:《百官志七》,《元史》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05页。至元二十五年(1288)至武宗初期,豳王家族“总兵西陲”,(38)(元)张养浩:《析津陈氏先茔碑铭》,《张文忠公文集》卷一八,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背。以肃州(酒泉)为大本营,与沙州、瓜州互为掎角,以哈密为前锋,以玉门为屯兵之所,防守范围西起吐鲁番,南至青藏高原北部,东至巩昌府(陇西),北包黑水城,统辖范围远超出甘肃行省之外。(39)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该家族还曾受命管理驿站、屯田、仓库、采玉诸事,权势炽盛,侵夺了不少原本属于甘肃行省的职权。
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蒙古豳王家族与甘肃行省官员构成主仆关系,前者为主,后者为仆。1246年出访蒙古汗廷的柏朗嘉宾(John of Piano Carpini)曾言:
鞑靼皇帝对任何人都有非凡的权力……应该懂得,所有事物皆操于皇帝之手,没有任何人敢说这是属于我的或他的东西,而是什么都属于皇帝。就是说,财物、人口和牲畜都是如此。(40)Ch. Dawson,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New York:Ams Pr Inc,1955,p. 28.
就元代河西地区而言,包括豳王家族在内的蒙古黄金家族成员是主,余者皆为仆。《元史·文宗纪五》载:至顺三年(1332)正月壬午,“命甘肃行省为豳王不颜帖木儿建居第”,(41)(明)宋濂:《文宗纪五》,《元史》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99页。二月,“给豳王及其王傅禄”(42)(明)宋濂:《文宗纪五》,《元史》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01页。。甘肃行省要为豳王家族修建府邸,要提供给养,言蒙古豳王家族地位崇高,得无可乎?
黑水城出土《大德四年军粮文卷》(编号F116:W552)记录了亦集乃路、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出伯大军筹集军粮的过程:
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六月□/,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赴术(出)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在仓粮斛数少,旦夕不□。□大王大军经过迤北征进,到于本路支请口粮,委是不敷支遣。又□处人民所种田禾将欲出穗却被蛆虫食践,未见收成□□。特已于五月廿四日、六月十八日两次差人赍解,赴省计禀,攒运粮斛,准备支持,去后,今有廿二日,有使臣帖失兀阿鲁灰、术伯大王位下复回说称,术伯大王军马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等事。本路□/系小麦一色,又兼数少,委是不敷申禀,早为于甘州等□/。术伯大王位下使臣也帖立秃思不花赴晋王位下,传奉脱忽帖木儿大王、脱忽答大王令旨,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面□/。(43)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大德四年军粮文卷》现存文书六件,每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大致记录了亦集乃路、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出伯大军筹集军粮的过程,同时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伯率领诸王军马征讨海都叛乱的战役。(44)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由文书可证,大德四年(1300)奉命率军经亦集乃路出征岭北,平定海都叛乱的正是诸王出伯,而驸马蛮子歹、太子海山、脱忽帖木儿大王、脱忽答大王等均受其统辖,亦集乃路则为以出伯为首的诸王大军的集结地与粮草供给地。兹后,总领甘肃兵柄的出伯在晋王甘麻剌、太子海山等人的协助下多次击败海都军队,出伯所部因此先后多次获得赏赐。(45)(明)宋濂:《成宗纪三》,《元史》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436页。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西宁王牙罕沙曾受命赴四川戡乱,(46)(明)宋濂:《顺帝纪五》,《元史》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95页。翌年返回沙州,(47)(明)宋濂:《顺帝纪六》,《元史》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12页。以其“镇御有劳”,得置王府。(48)(明)宋濂:《文宗纪五》,《元史》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02页。从中不难看出出伯总领甘肃兵柄的角色。
出伯家族镇守河西之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元史》卷二一载:“[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49)(明)宋濂:《成宗纪四》,《元史》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52页。出伯以宗王身份出镇河西,使河西之政治、军事地位大为提高,西夏至元前期原本日渐式微的局面大为改观,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呈现出“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的良好局面。(50)(民国)屠寄:《出伯传》,《蒙兀儿史记》卷四二,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337页。至大二年(1309)八月,中书省臣言“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51)(明)宋濂:《武宗纪二》,《元史》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13—514页。《经世大典序录》“屯田”条言:“甘肃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泽,皆因古制,以尽地利。”(52)(元)佚名:《经世大典序录》,(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97页。说明元后期瓜沙屯田获得较大成功,如同江淮芍陂、洪泽屯田那样,成为元代屯田之典范。
瓜沙属于干旱区,屯田必须有水利保障。在至正八年(1348)勒立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至正十一年(1351)勒立的《重修皇庆寺记》碑中都明确提及“沙州路河渠司”(5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此乃沙州路总管府下属机构,“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54)(明)宋濂:《河渠志一》,《元史》卷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88页。二碑的施主都来自河渠司,但功德主却是西宁王速来蛮家族,不难看出蒙古豳王家族地位的高高在上。
通过对点滴史料的爬疏,可以看出,元朝后期,随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入驻和西宁王、肃王乌鲁斯的设立,敦煌、瓜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甚至凌驾于甘肃行省之上,社会安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为大规模石窟的营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以瓜州榆林窟第2、3、4、6窟(明窗)、27;敦煌莫高窟第3、61(甬道)、95、463、464、465窟;瓜州东千佛洞第2、4、5、6、7窟;肃北五个庙第1、3、4窟为代表的大中型石窟的营建(包括石窟的开凿、重修与重绘)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三、元后期敦煌多民族聚居与文化之繁盛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早在汉代就有“华戎所交一都会”(55)(南朝宋)范晔:《郡国五·敦煌郡》刘昭注引《耆旧记》,《后汉书》卷一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1页。的称谓。及至元代,众多来自不同地域的民族在敦煌活动,对敦煌的民族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可波罗记载沙州“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斯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56)Thomas Wright,Travels of Marco Polo,London:Henry G. Bohn,1854,p. 105.。宗教的多样性,往往和民族的多样性相交织。
勒立于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上刻有分别由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六种文字书写的六字真言。其中出现人名95个(包括沙州路河渠司59人),兹依据其身份简列于下:
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妃子屈术、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卜鲁合真、陈氏妙因;
立碑者:僧人守朗;
刻碑者:奢蓝令栴;
长老:米米、耳立嵬等十二人;
在碑的下方刻有来自沙州路河渠司59名官员的姓名,分别为:
提领:威罗沙、哈只;
大使:逆流吉、兴都;
百户:宜吉、利忍布;
善友:脱脱木、答失蛮、杨若者等二十四人;
僧令:栴监梭、令只合巴,公哥力加等九人;
院主:耳革、义束、义立即等二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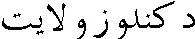
还有一种情况,速来蛮家族成员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自然应为蒙古人,但由于受到不同宗教的影响,依宗教信仰而取名,如来自察合台汗国的西宁王速来蛮父子,其姓名即有伊斯兰教文化的痕迹。速来蛮为穆斯林常用名,是阿拉伯语Sulaimān的音译;速丹沙(Sultān Shāh)中“速丹”亦称“苏丹”,意为“权柄、力量”,通常用来称呼伊斯兰国家掌权者;牙罕沙(Yaghan Shāh)中Yaghan为突厥语音译,意思是“大象”,而“沙”则来自波斯语,均含有穆斯林常用名之元素(57)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诸如此类,难以一一考究。
可见,在元朝后期,敦煌境内生活着汉、蒙古、党项、藏、回鹘等中国固有民族,更有来自中亚、西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及其他民族。
汉人自汉代以来即为敦煌的主体民族之一,自不待言。藏、回鹘则自唐代以来即长期活动于敦煌地区,并一度成为敦煌的统治者,吐蕃帝国曾于786年至848年统治敦煌,回鹘则于1036年至1067年以沙州、瓜州为中心建立沙州回鹘国政权。1067年,回鹘对敦煌的统治让位于西夏,1227年西夏又让位于蒙古。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灭国后,遗民大量入元,成为元王朝倚重的力量。敦煌亦不例外,在元代发展成为重要的民族势力,众多元代西夏文文献和西夏文题记在敦煌的发现,都可证明这一点。西夏文在元代敦煌是非常流行的,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本身即以元代居多,榆林窟第3窟甬道蒙古女供养人服装上书写有西夏文“佛”字,(58)杨富学、刘璟:《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新证》,《敦煌研究》2022年第6期。莫高窟第61窟甬道有十位西夏助缘僧,均以汉文、西夏文合璧的形式书写榜题,其中一位助缘僧叠压在蒙古文题记之上,足证这些西夏文榜题都是元代之物。(59)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敦煌研究》2023年第4期。榆林窟第2、3窟、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侧都留下了不少元代西夏供养人像。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年间将《西夏文大藏经》三十余藏,施与敦煌诸地,足证元代敦煌的西夏遗民数量众多,否则管主八绝不会将如此难得的西夏文经藏施于敦煌,毕竟当时印造的仅有三十余藏,数量极少,且非常珍贵。(60)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初探》,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4页;孙伯君:《元刊〈河西藏〉考补》,《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从敦煌发现的西夏文题记、西夏文六字真言铭刻、西夏供养人像,尤其是莫高窟第61窟甬道、榆林窟第2窟、第3窟等大型元代西夏遗民窟的兴建,都足以证明元代敦煌西夏势力的强大。
蒙古族的来源比较复杂,大体可归为三端。一者,1276年由西域察合台汗国东归的蒙古军队,为哈班、出伯兄弟的属部,东归后被忽必烈安置在河西走廊西部,抵御来自西域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进攻,后来忽答里迷失、速来蛮、牙罕沙先后受封西宁王,长期驻扎敦煌。这部分东归蒙古人后与河西回鹘相融合,以瓜沙为中心,于明初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黄番,(61)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即今天的裕固族。二为由中原前来的屯戍者,忽必烈十分重视屯田,尤其是军屯,这就使得元时的探马赤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62)(明)宋濂等:《兵志一》,《元史》卷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08页。元代的探马赤军往往是蒙古民族和各色目人以及部分汉族所组成的军队。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在山东、河南的蒙古军队,跋涉万里前往甘肃屯戍。《经世大典序录》“屯戍”条记载:“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吾、河西、辽东、扬州之类。”(63)(元)佚名:《经世大典序录》,(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597页。其三乃大漠南北发生灾荒时,一些蒙古饥民为了避灾南下进入敦煌,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八月,“诸王拜答寒部曲告饥,命有车马者徙居黄忽儿玉良之地,计口给粮,无车马者就食肃、沙、甘州。”(64)(明)宋濂等:《世祖纪四》,《元史》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0页。
元代敦煌还有另外一支特殊人群,即来自中亚、西亚的色目人。蒙古汗国的三次西征,打通了贯通东西方的国际交通线,大量来自西亚、中亚的工匠、俘虏等入华(西北地区是其最重要的去向之一),带来了先进技术与文化,为元王朝经济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莫高窟第3窟、东千佛洞第5窟观音散施钱财图中不见唐、宋、西夏通行的圆形方孔钱,均为金银珠宝,非中华文化固有传统,当受阿拉伯世界财富观念的影响所致。(65)杨富学:《由观音散施钱财图看莫高窟第3窟的时代——兼论武威出土银锭的铸造地》,《青海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莫高窟第61窟甬道出现有西亚伊斯兰风格的恶龙形象,当亦与西亚色目人的入居息息相关。(66)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敦煌研究》2023年第4期。
敦煌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及其文化状况,借由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文献即可见其端倪。1988—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清理发掘,出土文献众多。在莫高窟北区248个洞窟中有131个发现了遗物,其中文书碎片2 857片。(67)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在这些遗物中,时代明确或相对明确者107项(同窟所出凡无法确定归属的小残片,均合并为1项),其中,属于元代者占87项,其余时代仅占20项。在元代出土文献中,以回鹘文数量最多,占36项,其次为蒙古文,25项,继之为藏文,8项,再次为汉文,6项,又次为西夏文,5项,再下八思巴文,3项,复次之为梵文,2项,最后为叙利亚文,1项。回鹘文、蒙古文计有61项,又占全部出土文献之大半,占元代文献的三分之二以上,如实地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蒙古人与回鹘人的绝对优势地位。(68)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
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数量较多,在38个洞窟中掘得回鹘文文献128件,另有回鹘文文书碎片1 241片,除少数为信件、世俗文书外,大部分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如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大乘无量寿经》《长阿含经》等。莫高窟北区第59窟所出B59:69文献为元人念常所撰《佛祖历代通载》第5、6卷内容的选译,证明该文献至少有部分文字在元代即曾被译为回鹘文,只是翻译者赋予了自己的发挥。(69)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叶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体现了元代敦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莫高窟北区还发现有藏文《量学》《因明量学》等内容,更有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圣经·诗篇》,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版本。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四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版式与前三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70)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尤有进者,在敦煌还发现有许多已失传的西夏文佚书,如西夏文《碎金》、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
不难看出,元代后期,敦煌地区民族成分极为复杂,各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促进了元代敦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四、元后期敦煌与周边交通之发达
关于元代敦煌之交通,日本学者大岛立子根据拉班·扫马和马可波罗等人的行记,得出结论:“在蒙古时代,敦煌在东西交通路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与往昔不同,其声誉毫无疑问随之下降。”(71)[日]大岛立子:「元時代」,榎一雄編:『講座敦煌 二 敦煌の歷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版,第367—368頁;[日]大岛立子著,高然译,乌晓民校:《元代的敦煌》(上),《民族译丛》1984年第2期。揆诸元代敦煌的交通状况,由于多条东西方交通大道的开通,敦煌不再成为必经之地,故其地位下降,不复汉唐时代之盛,言其交通地位降低,当无大误。但应注意到,就元代敦煌的交通地位言,早期和后期应有所不同。
蒙元时期大力发展驿站制,太宗即位(1229)之初,“以按竺迩为元帅。戊子,镇删丹州,自敦煌置驿抵玉关,通西域,从定关陇”。(72)(明)宋濂等:《按竺迩传》,《元史》卷一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82页。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丙午,“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73)(明)宋濂等:《世祖纪五》,《元史》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3页。由于西北地区地处边陲,道路闭塞不畅,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加上西北地区又频繁深陷战火,“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罢于讨伐,无有已时矣”。(74)(元)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二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90页。直到出伯家族驻守西陲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1281年,甘肃行省设立,境内驿道主要由长行站道、诸王乌鲁思站道、纳怜站道组成。其中的诸王乌鲁思站道主要是指分封于甘肃地区的阔端后王乌鲁思和察合台后王乌鲁思所辖驿道,而察合台后王主要涉及的是酒泉、瓜州、沙州和哈密的蒙古诸王。(75)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察合台后王乌鲁思站道当为甘州以西至沙州一线,即设立于河西走廊的边陲重地之内。纳怜道,据载共设47站,因大部分在甘肃行省境内,故称甘肃纳怜道。纳怜道以亦集乃路为中心枢纽,由此北行即可入岭北行省而至和林;南连甘州;西出沙州路,抵察合台汗国边境;东经中兴府,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而至大都。
按照规定,宗王自立自管站赤,豳王出伯家族在其领地内不仅享有设立、管理及使用投下乌鲁思驿道的权利,同时还曾使用和管理甘肃等处站赤。大德十年(1306)后出伯获得了管理甘肃等地军站事的权力,同时出伯家族还负责管理甘肃行省境内诸王、驸马辅马令旨、辅马差札的发放与使用。出伯之子喃忽里、哈班之子宽彻也曾奉命管辖镇戍地的站赤事。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诸王宽彻暨司徒阔阔出、太傅铁哥塔失、铁木儿知院等,会议川地东西两界所置驿站,预宜斟酌给钱买与马驼……至于缺役蒙古站户,从行省,与诸王南忽里、宽彻委官追收,以复初役”。(76)《站赤五》,《永乐大典》卷19420。元代后期,肃王宽彻、豳王喃忽里皆负有兼管驿站、签补站户等事宜,以确保西北边陲的交通秩序。驿站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东西南北人员的流动,为敦煌地区带来了不同的物产和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带动了敦煌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文献中,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及双语文献等元代印本共39件,根据其中一些有明确信息可考的印本得知,其刻印地主要位于元大都和杭州等地,而且大都是元代后半期之物,说明元代后半期的敦煌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往来密切,且这批印本以佛经为主,体现了元代后期敦煌佛教发展的盛况。(77)刘拉毛卓玛、杨富学:《元代印本在莫高窟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兼论元代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存世甚稀的《金藏》残片也在敦煌有所发现,现已甄别出其中的6件,即B53:1-1/2、B57:1、B59:4、B464:77、B127:17和B168:1。其中前5件为经折装,属于《八十华严》,最后1件为蝴蝶装,属于《大宝积经》。至于《金藏》传入敦煌的时间,论者认为应在金代。(78)竺沙雅章:《莫高窟北区出土的版刻汉文大藏经本》,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页。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敦煌与金朝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直接联系,《金藏》传入敦煌的时间最大概率应为元代,应系元政府对驻守敦煌的蒙古豳王家族的颁赐。(79)薛文静、杨富学:《敦煌本〈金藏〉若干问题考辨》,“第二届东北亚古丝路文明论坛”,燕山大学,2023年4月21—23日。敦煌本《金藏》的出土,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期丝绸之路畅通及敦煌高度发展的佛教文化提供了佐证,以出土实物证实了《金藏》在元代敦煌的流传,体现了敦煌与中原王朝间频繁深入的佛教文化交流。敦煌发现的元代著名回鹘学者安藏、必兰纳识里和智泉的作品被装订在一起,三者尽管分别来自北庭、哈密和吐鲁番鲁克沁,但同样都生活于元大都。其作品何以由大都传入敦煌,不得而知。即便如此,这些作品在敦煌被发现,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大都与敦煌间密切的联系。
莫高窟北区B64窟和B137窟共出土12片汉文《资治通鉴》残片(编号B64:1、B137:4-1/11),与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资治通鉴》为同批次刻印,为南宋建本的元代覆刻本,因为B137:4-3号残片最左行下方有刻工之名——“登”,在涵芬楼本《资治通鉴》相同位置亦可见“登”字,故判定其为建本,刻印地在今福建建阳地区,刻印年代约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前中期,说明福建刻印的书籍曾在元代传播到敦煌地区。(80)徐畅:《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
在莫高窟464窟出土的回鹘文中有qïngsai tavar,其中的qïngsai,乃“行在”的音写,即南宋都城临安,今日的杭州。qïngsai tavar即“行在缎子”之义,表明杭州产的缎子在元代已经流通于西北地区的敦煌等地。(81)[日]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ウイグル文書中のキンサイ緞子」,『榎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版,第427—431頁;[日]森安孝夫著,冯家兴、白玉冬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吐鲁番与敦煌两地间,古来佛教文化交流密切,元代尤甚,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蒙古文令旨(B163:42),是由察合台汗国辖下吐鲁番地区的长官克德门巴特尔(Kedmen-Baγatur)签发给具有“灌顶国师”称号的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Dori Kirešis Bal Sangbo lam-a)的,以保障其在高昌、北庭、巴里坤等地举办佛事活动并向敦煌移动时的安全。(82)[日]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仏教徒——敦煌新発現モンゴル語文書の再検討から——」,『內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3号,2008年,第25—48頁;[日]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族与回鹘藏传佛教徒》,杨富学编:《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16页。敦煌回鹘文写本p.4521记录了14世纪早期至中期,敦煌莫高窟回鹘僧侣与定居河西或西回鹘王国回鹘僧侣间的佛经交换情况及商业事务。(83)Moriyasu Takao,“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40,1982,pp.1-18;[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1350年,沙州西宁王速来蛮(Sulaimān)亡故,其子阿速歹(Asuday)特请元代回鹘佛教圣地吐鲁番鲁克沁(ÜLükün Balïq)的高僧萨里都统(SarïTutung)来为其父抄写其中含有《度亡书》的Or. 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ri-cakrasamvara)》,为其父度亡。(84)杨富学、张田芳:《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呈现与成因》,《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作为《金藏》第五种印本——蝴蝶装《金藏》残片在敦煌、吐鲁番的共见,抑或即为二地文化联系密切的历史见证。
在莫高窟北区B121窟发现女性遗骨一具,伴出各类织物十余件,其中编号为B121:10a、B121:10b和B121:13者,经赵丰等学者研究,分别定性为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黑地牡丹纹纳石失锦、红地花间翔凤纳石失锦。此外,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出土有琐纹地滴珠窠花卉纹纳石失锦(B163:66)和红地鹰纹纳石失锦(B163:65)。(85)赵丰、王淑娟、王乐:《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元代丝绸研究》,《敦煌研究》2021年第4期。莫高窟北区116窟出土有鹰纹捻金锦,系由两件纳石失织物缝制而成(B116:5)。(86)杨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西夏至元代丝绸的研究》,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1页。纳石失,又译“纳石失”“纳赤思”,为波斯语Nasich的音译,意为“织金锦”,又称“波斯金锦”。虞集《道园学古录》曰:“纳赤思者,缕皮傅金为织文者也。”(87)(元)虞集:《曹南王勋德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70页。元代纳石失的织造主要集中在官府的5个作坊,大都(今北京)、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遗址)、弘州(今河北阳原,一说山西大同)、荨麻林纳(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各居其一,另有“纳失失毛段二局”所在地失考。有论者言其地可能在弘州,由镇海家族管理。(88)尚刚:《纳石失在中国》,《东南文化》2003年第8期。纳石失的生产主要是由官府作坊完成的,但主要技术人才一般都是西来的回回,“纳石失的高贵体现了蒙古族上层对伊斯兰文明的倾慕”。(89)尚刚:《纳石失在中国》,《东南文化》2003年第8期。敦煌所出6件纳石失锦残片不管来自波斯还是元朝境内的制造局,都有助于证明元后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交往的频繁,同时也有助于证明沙州西宁王家族地位的尊贵。
五、结 论
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敦煌在西夏国时代保持繁荣,至元代衰落,但都未能给出证据。通过翻检史料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史实,真实的情况是在西夏国时代和元代早期,敦煌都是非常荒败的。元代敦煌的发达主要局限于后期,其时间节点可以1276年蒙古豳王家族的东归为标志,此前为前期,此后为后期,而敦煌、瓜州因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而走向高度繁荣,则应始自天历二年(1329)沙州西宁王和瓜州肃王的设立,而西宁王速来蛮对敦煌长达21年(1329—1350)的统治,应为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期。
元代后期,敦煌、瓜州成为豳王乌鲁斯抵御西域叛王的军事重镇,西宁王与肃王作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社会地位很高,即使甘肃行省都要受其节制,加上元后期敦煌、瓜州因屯田高度发展而经济繁荣,为石窟的大规模营建提供了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故而元代敦煌出现了众多大中型石窟。
元代后期敦煌文化繁荣,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这与敦煌、瓜州境内民族成分众多息息相关,既有汉、蒙古、党项、藏、回鹘等中国固有民族,更有来自中亚、西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及其他民族。各民族间密切交往,不同文化互动交流,共同创造了元代敦煌地区灿烂多元的文化。
元代早期敦煌虽已有驿站之设,但因为战略地位的下降和经济的凋敝而长期未受到重视,直到13世纪下半叶蒙古豳王家族入居后,豳王家族成员,如第一代豳王出伯获得了管理甘肃等地军站事的权力,第一代肃王宽彻和第二代豳王喃忽里也皆负有兼管驿站、签补站户等事宜,使得敦煌的驿站交通得到较大改善,可以四通八达。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敦煌与元大都、杭州、福建、吐鲁番、肃州、亦集乃路等地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