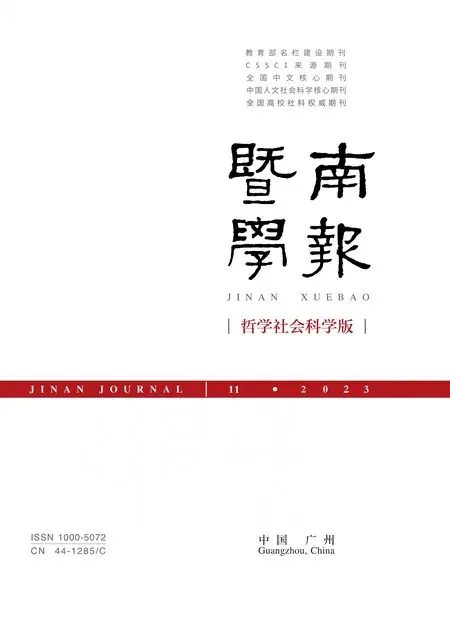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
周晓坤,王兆胜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近些年的儿童文学异军突起,显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动能与活力。据开卷公布的图书销售数据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少儿板块占12%的码洋份额。其中,少儿文学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据整个少儿图书市场近40%的码洋份额。杨红樱的系列儿童小说“淘气包马小跳”(30本),竟创下3 000万套的销售神话。曹文轩、郑渊洁、沈石溪等人的作品动辄创下销售千万册的奇迹。(1)参见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但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研究则比较滞后,作为相对弱项的儿童散文研究更显冷落,至于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几乎无人问津。其实,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以现实笔触向社会生活与自然万物敞开,搭建起童年视角通向客观实在之桥梁,其文化意蕴、教育功能、美学价值为儿童成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基于此,梳理、分析、概括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并对其价值进行重估,对儿童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以及整体文学创作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的历史演进
动物以动感、憨态、真诚天然地吸引儿童,加之儿童散文的非虚构、拟人化手法,趣味性、真性情等特点,使得,儿童动物散文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争相书写的文类。概括起来,它走过了一条不断显示主体性和理性自觉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受儿童本位论影响,文坛上出现冰心、丰子恺等有意识耕耘儿童散文的作家。冰心敞开心扉与儿童直接交流,如《寄小读者·通讯二》以拟儿童视点贴近对小鼠的观察,对微小生灵之灵动与无心机进行细致刻画,表现出澄澈善意的童心,也呼应着冰心以童心、母爱救赎人心的理想。丰子恺的儿童散文注重童心与艺术美育,如《蝌蚪》采取拟人化手法极为传神地写小蝌蚪钻泥的动作曲线,显示出孩子挖池塘的乐趣。另外,与动物相处的回忆散文大量涌现,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王鲁彦《父亲的玳瑁》、叶圣陶《骑马》、吴伯萧《马》、陆蠡《蟋蟀》等。如果说童年的记忆书写以趣味取胜,那么,现实生活的动物书写则更注重儿童成长的关爱与思考,如孙福熙《小猫(萤火之一)》、老舍《小麻雀》都是如此。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董纯才等创作的科学小品写到动物,比如贾祖璋《鲫鱼》。值得注意的是,儿童世界的不快、底层儿童的悲苦也得到了关注,如李广田《悲哀的玩具》、郭风《耍猴》均属此类。总之,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亲切自然中并未陷入低幼化与浅表化,能够快速提高儿童心智。
1949年后,祖国建设的蓬勃发展深切影响了文学,此时的儿童散文清新明快、积极进取、热情洋溢。其中,特别突显了劳动与宣传教育功能。首先,农业生产动物如牛羊、家禽、鱼类等成为绝对的主角,与此相关的儿童散文充分发挥了教育功能,陈伯吹《团结》、青林《护秋小队长》、鲁彦周《送鹅》等可为代表。金近散文集《迎接春天》中的《春天的歌》写道,布谷鸟是“播种早稻的监督员”(2)金近:《迎接春天》,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知了提醒春耕接近尾声。不过,也应该承认,部分写动物的儿童散文也存在政治超载的情况,如1958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思想检查中,出现了针对动物书写的批判口号,如“古人动物满天飞舞”(3)张瑛文:《方轶群同志的创作道路》,《儿童文学研究》1958年第6期。,“麻雀、老鼠何其多”(4)《儿童文学研究》二编室:《业务思想批判展览会大字报选刊》,《儿童文学研究》1958年第6期。等。但始终存在对偏向进行调整的力量,1956年“双百”方针、1959年周恩来提出的“十条正确意见”等,使一些别具情趣的动物儿童散文得以发表,如鲁风《童年生活点滴》、任大霖《芦鸡》与《童年时代的朋友》、菁莽《红鲤斗水》、郭风《搭船的鸟》与《避雨的豹》都充满童趣,没有概念化、功利性、形式主义的不足。
新时期以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较大提升。在百废待兴、科学发展的时代形势下,儿童科学散文的文学性得到显著提升,动物常识隐匿于儿童活动的故事框架中,显得更加平衡和谐。如宗介华《带刺的朋友》与《蛛网上的谜》中有探险游戏般的身临其境感;另如刘先平《山野寻趣》、吴然《歌溪》、乔传藻《星星寨》等开始探索自然中的原生态动物,为拓宽儿童视野做出了贡献。此时,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有所回归,儿童动物散文更注意平衡儿童喜好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在探索适合儿童的表达方式上有了新的进展,如秦牧的儿童动物散文一向比较注重动物的教育意义,其《猴戏散场之后》以观看训猴的趣味过程,提出保护儿童好奇心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已有整理优秀儿童散文的自觉,如《儿童时代》社在1981年打捞出49篇优秀儿童散文,并将之编为《珍珠》集,其中的动物题材占13篇。20世纪90年代,书写动物的儿童散文明显有所增加,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红蜻蜓”少年随笔丛书中,孙幼军《怪老头儿随想录》、北董《孤蟹》都有大量生趣盎然的动物书写。该时期散文文体、儿童读者、动物书写中的动物主体性都受到了更多尊重与关注。
新世纪以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更加多元化,呈现出诸多新变。第一,可看到生态观念的逐渐更新。越来越多的散文走出了传统的生态观,即简单的动物工具化或动物中心主义的道德判断,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程式化地塑造动物形象,而是以更平和客观的心态聚焦于生态共同体这一整体。如黑鹤《我的狗,乳白色的狼犬》不再简单塑造犬与人的伙伴关系,而是着眼于狼犬自身的野性生命力;李小麦《鹪鹩住在哪里》客观呈现了城市中各种鸟类如何依靠自身的能力御寒,其中完全没有人类活动书写的干扰。第二,动物种类、性格的丰富性和地域风格的多样性得以凸显。新世纪儿童散文的宠物书写显著增加,其中,高洪波散文集《好狗高气鼓》介绍了自家孩子般的几只宠物犬的故事,结尾对人的责任道德进行了深度反思。此外,云南神秘野性的高原山兽、北方原始森林里华美的珍禽啼莺、江南水乡多彩的花鸟鱼虫等独具特色的地方珍奇动物也大量浮现。第三,借助儿童的奇思妙想在动物书写中凝聚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如张绍民《有思想的蚂蚁》流露出童真状态下大胆的思维发散,从蚂蚁视角思考造物、宇宙、向上的攀登,开拓出更广阔的思想空间。2022年薛涛长篇散文《山林史诗》更体现出一种关于时空的哲学:东北森林空间中时间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四季都没有生命的颓败。小男孩“我”与万物互为彼此存在的原因和见证,在空灵而哲理化的时空中寄予作者对林中生灵的爱与祝福。第四,以更多元跨文体的艺术手法进行探索。如赵凯《想骑大鱼的孩子》获2008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其中,亦真亦幻的大鱼体现出残疾儿童对畅游的向往,也是对父爱的怀恋。湘女《雪门槛》2011年入选《中国儿童文学年选》,它融入雪狼形变的神秘传说,展示了滇藏高原马帮生活的奇幻。
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经历了一个主体性不断增强、艺术性趋向多元、童心更加自然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走出动物主体性缺乏与动物泛道德化的两极对立,基于此,儿童散文也就蕴聚了更多的革新力量。
二、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价值阶段论
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最大程度保存了中国的文章传统,儿童动物散文由于注重对动物的静观,成为儿童文学诸文体中非常注重造境的一种。境、境界、意境等概念,自唐朝以降便被广泛运用并延续至今,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内涵,即如有人说的“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5)朱立元主编:《艺术美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然而,儿童散文中的“境”也有其特殊性:境,看似是一个偏向静态的概念,但在儿童散文中,更偏重它的生动性与活力。另外,应关注儿童的主体性参与、物我关系的深化、代际间抒情的沟通共鸣,过滤客观图景中过于复杂的情愫和直观暴力的场景。具体到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也可考虑儿童发展心理学,根据其年龄与审美接受力予以阶段性考量。
第一,关于儿童散文动物书写的常识与浑然之境。儿童总是从自我中心慢慢发展为具有移情能力的主体,按照拉康的判断,在镜像阶段,动物对处于想象界的儿童来说只是小他者,即自我的相似物或者镜像。处于这一阶段的儿童相信动物可以说话,他们并没有把它们视为结情之物的意识。所以,对于低幼期的儿童而言,童话依然是最合适的文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幼儿童就不能在成人帮助下接触简单的散文。低幼散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塑造常识之境,即以自然与动物书写跃出家庭环境,拓宽儿童的认知世界,并使儿童获得自身在整个世界中的确定性定位。另一方面,塑造浑然之境,使儿童认识到除了自己、家庭、小朋友,还有自然与动物,产生心灵的一致性,从而建立和保护儿童与自然的天然联结。动物习性与人类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足以激起儿童的亲近感,在潜移默化中保育生命的完整性,从根源处联系到人生甚至人类的发展基础。埃里克森认为,对自我同一性的追求从出生始而贯穿一生。(6)参见[美]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90页。儿童散文中,相对于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环境,动物与孩子的融融之境表现得更加稳定,能提供和谐同一感,维护自我内在的连续性。
另外,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对儿童初期的感官开发和道德培养也有重要作用。基于儿童散文的纪实性,动物不会像童话那样和儿童对话,但对动物的形态描写能调动儿童的多重感官,为想象增添具象化能力。如郭风《搭船的鸟》与吴然《歌溪》都是儿童散文集,它们篇幅短小,易于被幼童理解,动物种类繁多,描写精细简洁,具有灵动感和色彩美,一些版本配有动物简笔画,与散文相得益彰。相对而言,当今城市儿童缺少动物的日常陪伴。有感于此,童话作家汤素兰同样开始致力于儿童动物散文创作,她认为相对于童话,动物主题儿童散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其真实性能开拓视野,开启向动物学习的慧心。通过共情与细致观察,在《江湖老猫》《聪明的办法》《向狗学习》中,汤素兰能看到动物的智慧与热情的生命力;在《雏鸟殇》《我们周围的仙境》中,她能尊重动物的主体性与自由,教会孩子细心观察,体味动物的陪伴与直观的生命启示。总之,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有利于儿童从小建立对自然的感受力与浓郁的兴趣,在童年的编码阶段得到美好道德心灵的浸润,对于塑造同情、耐心等美好品格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关于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的结情与间性之境。“结情”,指的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随着思想认知水平与智能的提升,逐步具备了移情能力。也就是说,能将物作为凝结情感的载体,理解自己与身边事物除了简单辨认、共存外,还有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并与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这不仅是第二重境界与第一重境界的最大区别,更是儿童审美力发展的关键进步。相对于其他文体,儿童散文更擅长引导儿童关注作为审美对象的物,在儿童美育层面的意义至关重要。而间性指的是儿童通过感性认知的进步,以及社会性经验的增长,与动物之间产生深层的对话关系。有学者认为,人类在童年期就有天然的间性趋向:“建立情感连通性或主体间性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7)李利芳:《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结情与间性对话同属一个逻辑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具备理解复杂感情的能力,才能走出儿童早期的自我中心状态,与他人共情、与动物对话。在这一阶段,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不再单纯侧重于简单表现幼童置身于大自然的和谐融通关系,儿童也需要体会与动物的分离、矛盾、亲密关系,以及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所展现出的精神品质和启示。鲍姆嘉滕认为,美育与感性认识的发展紧密相关,此处美育的核心就是情感教育。(8)参见[德]鲍姆嘉滕著,简明、王旭晓译:《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0页。而抒情性正是散文文体的显性特征,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有助于儿童健全心理与情感能力的养成。
成功的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往往能通过动物展现个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如被选入语文课本的梁实秋《鸟》。在此文中,作者的喜悲并非各自分段陈述,而是通过回环交错穿插书写的。作者在开头简单陈述了爱鸟之情、为鸟之不自由感到悲苦,之后写到在四川为鸟之自由活力与雄姿而喜悦,为东北所见麻雀的饥饿狼狈而哀伤。其间有对比、递进,展现出感情的多层次生发。结尾以悲哀收束,也只有细心体味作者对垃圾堆中饿殍遍野惨状的描述,才能体悟他以喜写悲的深层心理动因。谢华英《母亲的喜鹊》则发掘喜鹊和母亲的共通精神品质,即面对苦难依旧保持坚韧乐观,充满为自己鼓劲的喜气。在这些动物书写中,动物作为情感载体,展现了人或人与人之间的多重情愫。也有一类儿童散文凸显了动物的主体性,着力于动物与人的情感、精神互动。如韩少华《蝈蝈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蒙冤入狱者依靠一位好心老人挂在他窗户的蝈蝈才坚持活下来。又如乔传藻《哨猴》与《雁鹅》等表现出人对动物之勇敢、负责、奉献精神的礼敬,尤其是《山野之魂》以第二人称带入“我”作为母獐子为救同伴而牺牲,呈现出动物在精神品质层面能超越人类的境界。殷健灵《一只蝈蝈的老去》、肖憧《紫色蝴蝶》等则真实展现了动物的死亡与错位之爱的后果。正如狄德罗的关系论美学,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是主体间性互动的一个重要介质,同时,不同于成人对山水、植物、器物的静观,小动物的动态对于儿童阅读不至于枯燥,起到了过渡性作用。
第三,关于儿童散文动物书写的语言与文化之境。在诸多文类中,散文最能见出作者的语言与文化功底。此处的语言之境,不仅指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表达,也象征着一种结构体系,譬如文章结构的章法,也即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能否在有限表达中凝聚更多的智慧与审美价值。语言结构的习得,对儿童的团体化、社会化及其后续认知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也与儿童语文教育密切相关。曹文轩说:“散文对少年儿童,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比诗歌与小说还要重要。因为散文这一文体更能影响他们的格调。人们不知是否看到这一点:散文还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语文水平与写作能力。”(9)曹文轩:《私人性的文体——论散文和桂文亚的散文》,金波主编:《读她 写她:桂文亚作品评论集》,台北:亚太经网1996年版,第35页。在此,曹文轩敏锐指出儿童散文在辅助语文教育与涵养儿童文化品格的意义。事实上,散文贯穿着儿童语文教育的全过程,在阅读理解、写作等练习中,散文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林良认为,“只有在散文的欣赏中,我们才能观察到人人共同使用的一般语言”(10)林良:《浅语的艺术》,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优质的儿童散文语言绝不是成人散文语言的简单化,相反,它更有难度,不仅需要生活化、生动而深入浅出,适于儿童阅读,也要具备一定的可模仿性,承担儿童文法习得和语言表达的使命。在文章结构层面,儿童初学写作需要良好的范例,但“从前的那种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煞尾的散文,曾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这拙劣的文风仍在中小学的语文、作文教学中弥漫”(11)曹文轩:《私人性的文体——论散文和桂文亚的散文》,金波主编:《读她 写她:桂文亚作品评论集》,台北:亚太经网1996年版,第36页。。如今,不少儿童散文摆脱了这种陈旧的写作程式,塑造出各种既有性格又具有现实真实性的动物形象。如刘先平《黄山山乐鸟》写出山乐鸟之灵韵和黄山奇特地理结构的相生状态,作者从传说入手,顺着探寻的脚步展开想象,声音描述、动物神态刻画达到了虚实结合、不落窠臼的高度。同时,它在常见的命题范围下拒绝程式化表达、夯实语文能力的基础,对于儿童写作与未来思维的创新性生发有重要作用。
此外,对于阅读能力更强的高年级儿童而言,儿童散文也能提供一种文化之境。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审美性文化,而绝圣弃智的童心、蒙初状态也一直为传统道德所向往。在这个程度上,儿童散文也是成人与儿童交流、对话,甚至互相学习的一个平台。丰子恺说:“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他们所见、所感、所思都与我们不同,是人生自然的另一方面。这种态度是什么性质的呢?就是对于人生自然的‘绝缘’的看法。”(12)丰子恺:《学会艺术地生活》,金雅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丰子恺卷》,杭州:浙江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王国维也认为,怀有赤子之心才能达到审美的真境界。(13)参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传递的格调与灵韵,将伴随儿童成长,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方式。韦伶同时精通于中国画与儿童散文创作,并把前者的文化意蕴代入儿童散文。如《鹤与鹿的意象》中画卷的鹤与鹿深深印刻在“我”的梦里,使“我”沉醉于松下女孩与鹤共处的静谧超逸,有语言的古典美,亦有中国文化情怀。班马在《山顶的大悟》中写道,正是登山途中不起眼的小昆虫、软体动物唤起了自己对人与自然的思考,体会到人与天地齐一的意境。徐鲁的《湖上黎明》中,清晨时光与湖面只属于“我”、小野凫和水蜘蛛,这种沉浸体验超越了生态角度的二元判断,颇有物我合一、坐忘功利的天地情怀,达到了质朴而超越的审美境界。这些作品的成功启示我们,儿童散文的平易浅近与文化厚度并不相斥。另外,在中国宇宙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念中,人最为尊贵,但万物的生命同样被肯定,这份文脉契合于现有的生态思想,中国气派的儿童散文也值得进一步挖掘与研究。总之,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连接着天地自然与中国寓言传统,可谓大道至简,沟通今古,接续了东方人的思维智慧。
三、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局限及改变路径
目前,制约儿童散文发展的首要问题已不是创作数量,而是艺术水平的良莠不齐。不容讳言,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仍存在一些缺憾,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动物权利与主体性的态度失当,动物书写呈现同质化,这必然导致创新性表达的缺失。
首先,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最应重视价值观。对待动物,创作者有一颗悲悯与光明的心灵至关重要,他们应传递健康、道义、活泼的文学趣味,不应过度成人化,将不适宜儿童接受的成分混入抒情,过度表现动物世界的兽性血腥场面。沈石溪《闯入动物世界》提到自己喜欢驯养弱小动物,改变其习性,如强行将鸭子训练成狗,以此“扮演随心所欲的强者角色”(14)沈石溪:《闯入动物世界》,《少年文艺》2011年第1期。,弥补自己幼年自卑的心灵缺憾。这种观念渗入其儿童散文与动物小说创作,时常体现为以己度物,把人类社会中的异化心态、行为带入动物世界。不过,强力制胜的丛林法则并不是“真”的全貌,也不适合向幼童反复展示。一种无法善待弱者的创作观,对于儿童也寄予了更多教化与规训姿态。此外,仍有一些儿童散文存在血腥的直接描写,如刘国霖《十四岁那年,我逮住了只山狸子》写到肠子的拖拽、内脏的外流、扣出眼珠等,都没考虑儿童的心理承受力。儿童散文的成人意识往往通过隐含叙述者呈现,却对作品的意旨与氛围起到决定性作用。如侯德云《冬季的葬礼》写野鼠集体自杀的惨剧,但带给读者的并非震慑而是心灵震撼,因为它略去了刺激性书写,代之以大幅的整体性感受,且隐含作者将真实的反讽与敬佩融入“我”与父亲等不同叙事者的言行。在此,刘先平、黑鹤、鲍尔吉·原野等人展现的自然主义动物世界,或乔传藻、金曾豪等呈现的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都有更多可取之处。
其次,动物形象存在象征化、固定化、同质化现象。动物的象征性意义升华和刻板印象不只存在于特定时代,如不彻底转变创作思维,一些政治超载或形式主义创作就很难避免。如杨羽仪《知春鸟》中,知春鸟与老博士在结尾突兀出现,用以象征科学的春天到来,此类作品的动物依然是工具性、象征化的。新世纪以来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象征化问题明显好转,但不少作品仍停留于书写相似的动物习性,抒发千篇一律的感情,缺乏创新性。如燕归巢与乡情、狗与忠诚,正如折柳送别一般,几乎成为当代版的固定意象结构模式。如何为儿童写好动物成为一个新的挑战。在此,不妨对毛云尔《鹞子》进行细读:鹞鹰在过去的儿童散文中常作为恶霸形象出现,但此作一反刻板印象与知识介绍,用比喻让鹞子作为一个墨点出场,不仅有新意,也传神地体现了鹞子悬停空中的状态。书写鹞子抓鸡,忽然由写意的水墨天空转为动态,张力中更显风驰电掣。最后,作者联系自己童年成长中仰望天空的真实孤独体验,将墨点化为天空的诗句,塑造了一种温暖的共情以及广袤的中国诗学意境,可谓别具一格。可见,修辞、语言的当代新质及童年经验的精准表达,有助于塑造不落窠臼的动物形象。
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虽然存在不足,发展势头也远不如动物童话、动物小说,但新世纪以来,其创作丰富多样,艺术水平日趋成熟,种种现象决定,现今已不能再简单用边缘化对儿童散文进行概括,研究的惯性忽略理应得到纠正。在此,可从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对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发展路径进行整体性勾勒。
第一,明确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的概念意涵,是文体归位与意义讨论的基点。
儿童散文概念的模糊性是文学史的遗留问题。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的文类研究逐步展开,然而在诸如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魏寿镛与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等众多重要文献中,均未提到“儿童散文”这一文类。纵观众多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儿歌、童话论占绝对主流,寓言、儿童剧、儿童电影也有不少论述,但针对儿童散文文体的专论实属罕见。即便有零星论述,也与语文学概念如记叙文、说明文相杂糅,将简单的文章分类等同于儿童散文的现代转化和建构。(15)参见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王泉根:《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下编),太原:希望出版社2015年版。这说明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学界对儿童散文研究的文体自觉意识不强。与此同时,对动物书写的讨论也多集中在童话文体,主要关乎儿童本位与动物教义的权衡辨析。
当代文学时期,儿童散文的定义得到了更多讨论。林良、蒋风、方卫平等人在儿童散文的现代性、文学性、儿童适用性层面达成共识,但不同学者在概念的细微处仍有一些分歧,导致儿童散文的定义至今仍不够明确。在一些儿童刊物与研究论文中,文本归类的混乱现象也很常见。比如,从写作主体看,儿童习作是否属于儿童散文?从主题内容看,儿童散文的文学性能否兼容知识性与教育性?从创作目的看,一些不是专为儿童创作,但经实践证实适合儿童阅读的散文,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部分篇目是否也可归于儿童散文?笔者认为,儿童散文是一个复合型结构概念,出于儿童概念的文化建构性(16)参见Philippe Ariès,trans. Robert Baldick,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2,pp.128-133.及散文概念的开放性,可以容纳差异,尊重儿童日益多元的个体差异性需求,允许多元主题的发展,兼容儿童散文不同程度的抒情性、知识性。但有一些底线必须坚持和明确,即概念的现代性、适于儿童阅读的题材与表达方式、作为散文底色的非虚构性、作者的成人身份。同时,儿童散文中的动物书写虽可有生动的拟人化,但绝不能脱离动物的习性,凭空想象和进行人格化。概念的明晰是文体独立发展及后续创研的根基。
第二,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研究亟待理论的充实与方法论的开拓。未来理论体系建构应把握当代视野、中西兼容的总体方向。同时,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在凸显中国文化品格方面有独特作用,中国天人哲学与物我情感联结模式是散文文体独特的理论武库。
儿童散文理论一直未得到充分发展,一是由于儿童散文在西方理论话语中也不受到重视,没有直接的理论来源;二是与本土散文和儿童文学理论建构不完善的现状有关。一方面,应注重国内现有资源的当代转化,以现代性视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及现代儿童文学研究遗产,联结当代儿童日常生活与真实情感,以中国式语感与风骨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兼收并包,注重中西方理论的对话。虽然说西方文论中神话学、话语装置的结构化分析等,并不十分适用于儿童动物散文的研究,但儿童权利、动物权利、人本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等,同样有可以借鉴吸取的宝贵养分,这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
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传递了中国万物共生、人类灵而不主的生态哲学意蕴。天人合一是其哲学内核,这与童话中受到西方泛灵论影响的动物书写有着根本不同。在童话中,动物通过模仿人类情感与行为才有了灵韵,但中国儒家的正名与天道传统、道家气论与齐物旨趣的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给予动物与人相对平等的生命地位,其差异只在于伦理学层面。同时,西方抒情模式中人类中心意识浓厚,如笛卡尔高扬人类理性,将动物比作机器;但中国文化与兴象传统却特别注重观察具体的物、在物我之间的贯通与相互依存中获得审美体验。至今,中华儿女依然受到感物生情的诗学传统影响,有自己独特的及物的情感表达模式。这种天人哲学和情感方式乍看似乎老成,但人类原初的智慧与感受力其实与儿童的纯真、活力相通。笔者认为,这种和谐融通的感性表达,比丛林法则更适于儿童心灵。当然,在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中,不宜过分强调文化表达和思想含量,重要的是作家如何以潜移默化方式,浸润而非漫灌儿童心灵世界。如黄文军《喓喓草虫》在生动的童年虫趣讲述背后,别有一种悠远未尽的醇厚意境。表面上看,作者传递了生态友好的态度,实际上也有和稳、典雅、睿智的文化韵味。但这种表达是以儿童接受能力为中心的,穿插在游戏、儿童心理活动、小学语文学习的脉络中。因此,中国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或可在此打开本土化发展的新路向。
第三,儿童散文借助动物书写实现文体归位,离不开出版行业助力以及价值体系重建。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家庭结构特征的转变,儿童文学的知识性、娱乐性、审美性日渐平衡,更多作家专门以散文文体书写现实中的动物。新世纪以来,专为儿童创作的动物散文集大量出现,如金曾豪《蓝调江南》(2003)、史伟峰《野鸽子》(2006)、高洪波《好狗高气鼓》(2020)、黄文军《喓喓草虫》(2022)都很有代表性,它们分别以细腻的动物性格、儿童心理的解剖式呈现、亲密关系的书写、知识性与文学性的相得益彰取胜。尤值一提的是,云南昆明晨光出版社2017年推出十位儿童散文作家的散文集。其中,毛云尔《盛满月光的陶罐》在第三辑“动物的乐园”专写动物,以诗性语言展现了动物的天然状态;徐鲁《谁从我童年的窗外走过》辑二、张国龙《一个落雪的午后》辑二也记录了作者童年与故乡动物相处的往事。此外,一些以主题、奖项为依据编纂的儿童散文集已经出版,动物题材在其中占主要位置,其中较重要的有历年冰心儿童文学奖散文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者丛书、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散文卷等。如2006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挖掘出川西作家蒲灵娟《童年的云彩》,拓宽了儿童散文动物书写的地域与民族版图。
当下,中国儿童散文的发展具有区域性、散点化的特点,远未呈现出整体性繁荣。在区域成就层面,较突出的仅有以林良、桂文亚、谢武彰为代表的台湾儿童散文作家群,及以乔传藻、吴然、普飞、湘女为代表的云南“太阳鸟”儿童散文作家群;还有个别少数民族作家为儿童散文贡献了别样的风土人情与动物书写,如满族作家佟仁希、蒙古族作家黑鹤、彝族作家吉布鹰升等。总体上,像郭风、刘先平、金曾豪这样专门致力于儿童散文创作的作家不多,作为现象受到关注的作品、散文集也零星可数。儿童散文的篇幅决定了它散见于报刊的传播载体特点,短期内也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热门文体。如果没有出版市场、评奖、研究和评论界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加持,所有设想终将成为空中楼阁。譬如,台湾儿童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离不开桂文亚等人的奔走及《民生报》的固定阵地、资金来源。但是,相对的寂静未必全是坏事,有人在谈及儿童散文时说,虽然儿童散文的文体地位算不上文坛主角,但由于受市场追捧、浮躁之气影响较小,“散文几乎不向读者提供艺术品质低劣的东西”(17)方卫平、孙建江:《〈这一路我们说散文〉座谈纪实》,桂文亚主编:《这一路我们说散文:96江南儿童文学散文之旅》,台北:亚太经网1996年版,第109页。,它也不会像儿童校园小说的琐屑化、情境喜剧化,以及幻想文学的娱乐宣泄化,存在严重的文化缺失问题。事实上,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注重现实童年,不以游戏娱乐和打斗等感官刺激、丛书化的形式引导消费,更有望作为新的突破点,打开中国儿童文学更高的艺术境界。
佳作的积累沉淀将是儿童散文归位的根本推动力。对于作家、研究者、出版方、家长群体而言,有必要提升对当代儿童的认知水平,重新思考以儿童为中心与教育引导的关系,从而建立更科学的价值判断。儿童对书籍的判断尚没有辨别消费引导的能力,不能完全听凭其喜好而放弃情节性较弱的动物散文。不少人曾认为,散文文体是老年文体,与儿童的游戏精神格格不入,这种观点应得到根本改变;同时,也要摒弃教育的过于功利思想,避免只将儿童动物散文当作提升应试写作能力和补充常识的工具,而弃掷更重要的文学性熏陶。
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典型地切合于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但在以往研究中却被边缘化了。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以独特的境界和文化含量,弥补了其他儿童文学文体的不足,从而在儿童美育、心理发展、彰显儿童文学独特品格等层面都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与价值。其创作日渐丰富成熟,充满发展势能,但仍有不少局限。对儿童散文的动物书写研究,契合于当下儿童发展需要与文化建设语境,有待于超越零散式的批评与研究现状,进行整体性与更有学理化的深入开垦与探讨。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