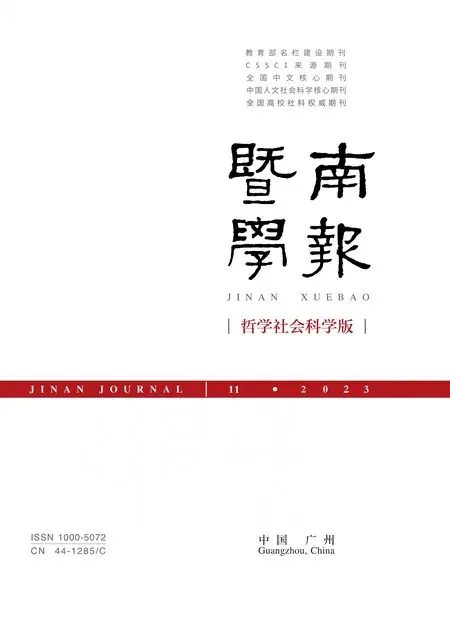商法的“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
——基于比较法的观察
夏小雄
在21世纪的当下,“商法典”似乎是一个过时的提法。当部分商法学者提出制定商法典的倡议时,(1)明确提出制定商法典的商法学者主要包括刘凯湘教授、范健教授、王涌教授、蒋大兴教授等。典型的文章如范健:《编纂〈中国商法典〉前瞻性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蒋大兴:《〈商法通则〉/〈商法典〉的可能空间?——再论商法与民法规范内容的差异性》,《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蒋大兴:《〈商法通则〉/〈商法典〉总则的可能体系——为什么我们认为“七编制”是合适的》,《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期。很多学者对此持质疑态度,认为在当下没有必要再制定商法典(包括商法通则)。(2)参见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 4期;王轶、关淑芳:《民法商法关系论——以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4期;许中缘:《论商事规范的独特性而非独立性》,《法学》2016年第12期;许中缘:《我国〈民法总则〉对民商合一体例的立法创新》,《法学》2017年第7期;孟强:《经由编纂民法典实现民商合一——兼评〈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与〈商事通则立法建议稿〉》,《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夏沁:《私法合一抑或民商合一——中荷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比较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对于为何反对商法典的制定,学者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供了一定的理由。总结而言,反对制定商法典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对于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进行了一体化调整,特别是总则已经对商法的一般规则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二是在维持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中,即便还存在商法典,“解法典化”运动已使其失去了“中心地位”,商法体系发展已经呈现出“去法典化”“去中心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势。从当下中国商法体系构成来看,特别商事立法虽然不甚完善,但是已经发挥了规范调整商事关系的功能,在此背景下没有必要另行制定商法典。(3)刘凯湘教授在2017年北大商法典圆桌论坛“制定商法典——商法典编纂的全球印象”学术研讨会上对于反对制定商法典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具体包括: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不需要商法典;商法典已经过时;商法典是商人阶层的特权法典;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典差异性太大,缺乏统一性和体系性;商法难以提炼总则性规范;商法公法化趋势使得商法难以法典化;只需要商法通则,不需要商法典。通过全面深入的辨析,他认为这些反对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制定商法典——商法典编纂的全球印象”会议实录》,第5—7页,https:∥www.docin.com/p-2098492775.html。
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当下中国私法体系建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如果从更宽广的历史时空、更全面的体系视角加以观察,这些反对理由或许值得进一步商榷。从比较法维度来看,商法典似乎有着不一样的“命运”。在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虽然已经不复有商法典的存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认识到民商合一的民法典不足以全面规范调整商事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商法“再商法化”的理论主张,有的国家甚至准备另行制定商法典;在采纳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虽然所谓的“去法典化”或者“解法典化”的运动已经发生,商事特别立法不断增多,但商法典在调整商事关系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功能并未丧失。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维持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国家也在尝试将商法“再法典化”,将商法典改造为以“原则性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典,使其具有较好的开放性和适应性。(4)一个全面的总结参见意大利著名商法学者Giuseppe Portale在意大利林琴科学院为其举办的八十岁生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Cfr G.B.Portale,“Da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alle (ri)codificazioni:la ricerca di un nuovo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2019,pp.79-94.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立法调整并不是立法机构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长期深入的理论论证和制度研究,也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
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维度介绍民商合一国家和民商分立国家当下在商法立法层面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商法的“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改革,并对商法法典化的未来趋势和可能结构进行评述,以期为中国商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一些理论参照和经验借鉴。
一、商法的“再商法化”:民商合一国家的实践
“民商分立”本是19世纪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私法立法体例。法国在1804年制定民法典、1807年制定商法典进而确立民商分立立法体例之后,其他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德国、拉美诸国等)仿效法国分别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私法关系的整体商事化,学者们意识到了民商分立立法体系有其弊端,如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难以区分,商法典对于商行为的类型列举较为有限,商法典的扩张适用会强化商人特权,商事法院管辖权识别面临难题。(5)G.Levi,La commercializzazione del diritto privato:il senso dell’unificazione,Milano,Giuffrè,1999,pp.19-49.更为重要的是,在债法领域建立统一法律规范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6)C.Vivante, Per un codice unico delle obbligazioni,Tipografia Fava e Garagnani,1888,pp.169-176.在此背景下,有些国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转而采纳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将传统意义上民法典和商法典的规则整合到新的民法典当中,对于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实行一体化调整,特别是在债法领域实现了法律规则的统一。这种立法思路的改革尝试在1881年瑞士债法典当中率先得到实现,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当中则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在2002年巴西民法典中继续发扬光大。(7)参见徐强胜:《民商合一下民法典中商行为规则设置的比较研究》,《法学杂志》2015年第6期。毫无疑问,这种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实践需要,有利于促进对私法关系的高效调整。(8)参见夏小雄:《私法商法化:体系重构及制度调整》,《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
但是,民商合一的私法立法模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其中最为根本的挑战是对于商事关系规范调整的不足,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无法纳入民法典调整范畴的疑难争议问题。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受到了学者的持续反思检讨。其中,商法学者对于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商法规范的供给不足和商事关系的滞后调整更是提出了批判意见,在此基础上,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提出了将商法规范内容“再商法化”(Ricommercializzazione del diritto commerciale)的主张。
(一)商法“再商法化”:意大利的理论探索
意大利1942年统一民法典制定之后,围绕统一民法典是否使商法失去独立性、商事关系能否得到全面调整、商法自身的原则和方法是否还存在等问题,学术界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并将讨论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比如Greco、Ascarelli)认为商法在本体论层面的独立性已经不复存在,商法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只能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在学术研究层面加以探讨。私法商法化的调整实际上已使很多商法规则变成了私法一般规则,在私法体系下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学者应当基于统一民法典体系,超越民商区分的逻辑去探寻新私法的原则和方法。(9)P.Greco,“Il diritto commerciale tra l’autonomia e la fusion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 No.1,1947,pp.1-5;T.Ascarelli, Lezioni di diritto commciale,Milano,Giuffrè,1955,p.89.部分商法学者(比如Mossa、Valeri、La Lumia、Asquini)则认为民法典的制定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民法规则和商法规则,但并不削弱或者影响商法实质内容层面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特别是在Mossa教授看来,商法在原则层面和方法层面依然具有独立性。(10)G.Valeri,“Autonomia e limiti del nuovo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3,p.24;La Lumia,“L’automonia del nuovo diritto delle imprese commerciali”,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2,p.1;L.Mossa,La nuova scienz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1,p.439;A.Asquini,“Il diritto commerciale nel sistema della nuova codificazion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1,p.429.而在Giuseppe Ferri教授看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统一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实并且已被普遍接受,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了私法规范的现代化(也就是私法的商法化);但是私法规则的统一并没有影响商法的独立性。与之相反,统一民法典立法的“专断性”(11)统一民法典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制定的,商法学界实际上还是希望制定独立的商法典,这种理念诉求集中体现在1940年商法典草案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法和商法所调整的经济社会关系之差异性,特别是在“企业/营业”的规范上忽视了其特殊性。对于商法学者而言,应当把立法者所忽视的差异要素重新加以发现,并通过解释性路径去探索相应的商法规则,使其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12)G.Ferri,“Revisione del codice civile e autonomi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5,pp.96-102.换言之,私法商法化的体系变革并未影响商法规则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商法学者的研究应当致力于探究统一民法典体系下商法规则的差异性,并进一步研究商法原则和商法方法的独特性。这也成为了意大利统一民法典制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商法学者的主要任务。(13)M.Libertini,“Diritto civile e diritto commerciale. Il metodo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in Italia”,Rivista delle società.,2013,pp.1-41.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商法独立性的讨论得到了学界进一步的重视,学者们对商法规范内容的独特构成、商法规则生成的特殊机制、商法规范体系的重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深度阐释。
1971年Mario Libertini教授出版了专著《有价证券理论中的类型逻辑和规范结构》(Profili tipologici e profili normativi nella teoria dei titoli di credito),尝试重新论证商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的探讨不是建立在民法典个别规则的分析上(例如第2558条关于企业转让的规则),而是基于对商法具体原则的深入研究。1974年Giorgio Cian教授在《民法杂志》(Rivistadeldirittocivile)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超越法典体系的民法和商法》(Dirittocivileedirittocommercialeoltreilsistemadeicodici),试图建构全新的商事企业合同法律规则体系。1981年Giuseppe Portale教授则在JUS杂志上发表了《银行责任和商法的再商法化》(Traresponsabilitàdellabancheericommercializzazionedeldirittocommerciale),随后在1984年又发表了《共同私法和企业私法》(Dirittoprivatocomuneedirittoprivatodell’impresa)一文,将“商法的再商法化”(Ricommercializzazionedeldirittocommerciale)这一命题继续加以提炼总结,激发了学界对于该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在这些学者看来,必须超越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所确立的规范体系框架,通过研究并证立新的概念、新的责任、新的体系来推动新商法体系的形成,尤其是阐释“商法作为企业法”的理论逻辑和体系路径。“再商法化”之后的商法体系应当有自身独立的原则和方法,尤其是“类推适用”方法可以普遍适用,在私法体系下商法应当与民法具有平等的地位。
“商法作为企业法”的观念进一步凸显了商法规范的内容特殊性,特别是确认了与企业有关的规范在私法体系下的重要性。实际上,Lorenzo Mossa教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展了“企业法”研究,并提倡以“企业”概念为基础重构商法体系。这一研究对于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的制定和20世纪后半期商法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14)L. Mossa,“I problemi fondamentali del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26,p.33 ss.;“La nuova scienz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1941,p.439 ss.在“商法再商法化”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将Mossa教授的学术主张进一步加以深化,并结合商事实践的进展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加以了完善。
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民法典并未明确哪些规范属于商法规范,但是也应当通过解释性路径探寻与“企业”相关的独特规范体系。在处理私法争议问题时,应当区分企业法律关系和个人法律关系,对于两类法律关系应当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和规制策略。统一民法典中法律规范的解释必须根据其调整的法律关系类型(企业性的或个人性的),适用不同的原则和方法,贯彻不同的利益衡量逻辑和法益保护路径。商法相对于私法一般法而言是特别法,但其特殊程度较高,以至于具备自身独立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比如类推解释的灵活运用)。在赋予商法规范自治性价值的同时,也应赋予其真正的建构性价值。(15)G.Cian,“Diritto civile e diritto commerciale oltre il sistema dei codici”, Rivista di diritto civile,No.1,1974,p.524 ss;G.B. Portale,“Tra responsabilità della banca e ‘ricommercializzazione’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Jus,1981,p.141 ss.;ID.,“Diritto privato comune e diritto privato dell’ impresa”,Banca Borsa Titolo di Credito,No.1,1984,p.14 ss.同时,传统民法所采纳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的分析范式、“行为模式—法律效果”的规范结构也不能有效适用于企业法律关系的分析。“企业”概念更强调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有组织性,在企业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易的多数情形下并不能完全遵循既有的民法解释逻辑,很多企业法规范属于权力分配规则、组织结构规则、程序行为规则,很难纳入传统的民法规范分析框架。(16)C.Angelici,“La lex mercatoria e il problema dei codici di commercio”, Giurisprudenza commerciale,No.1,2010,pp.372-373.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于与企业有关的组织法、合同法、侵权法等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了这些规范的特殊性并提出了新的法律规范解释适用路径。民法典确立的规范体系和调整模式已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实践需要,不能有效适用于与“企业”和“企业主”有关的法律关系,必须建构适用于上述法律关系的商法规范体系,包括独立的商法原则和商法方法。(17)G.Terranova. “I principi e il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2,2015,p.1 ss.商法如今已经转换为以“企业”法律关系为基础构成事实的自治法,这不仅符合比较法维度全球商法发展的共同趋势,而且切近意大利商法发展的实际情况。(18)L. Buttaro,“L’autonomi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2,2002,p.421 ss.
意大利学界有关“商法再商法化”的研究对于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法院对于商事习惯法源地位的重视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从法源构成的角度而言,1942年统一民法典实施后商事习惯在商事实践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商法规则都是基于商事习惯而产生的,意大利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对此加以确认。例如,独立担保合同在实践中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但是在1942年民法典当中却没有得到详尽的规定,法院基于商事习惯在传统商法法源体系下的功能承认了其效力。(19)G.B. Portale,“Lezioni pisane di diritto commerciale”,Pisa:Pisa University Press,2014,p.20.“商法再商法化”工作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承认商事习惯相对于民法规范的法源优先效力,使得商法规制能够不断面向实践问题,确保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安全。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看,虽然意大利的商事法院制度已经被废除,但随着“商法再商法化”理论的影响,商事审判的特殊性也得到了重视,与企业有关的诉讼程序得到了特殊对待,以提升效率、保障公平。2012年3月24日通过的第27号法律引入了所谓的“企业法庭”(Tribunale delle Imprese),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商事法院”的制度理念,强化了企业诉讼的特殊性和商事裁判的独立性。
事实上,在1942年民法典制定之后,私法规范体系的发展一度出现过“解法典化”(Decodificazione)的现象,特别立法不断增加使得私法规范体系日益碎片化。(20)N. Irti. “L’età della decodificazione”,Milano:Giuffrè,1989.但是,进入到21世纪后,“再法典化”的现象在意大利又得到了复兴。(21)Patti S. “Ricodificazione”, Rivista di diritto civile,Vol.64,No.2,2018,pp.435-453.在2005年,意大利立法机构就分别制定了保险法典、消费者法典、工业财产权法典,在2003年对民法典中的公司法规则进行了大幅修订,实现了民法典局部的“再法典化”。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以企业法体系重构为核心的“商法再法典化”是意大利私法体系发展的趋势。Portale教授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从1942年《民法典》到再法典化:寻找新商法”的论文中,也在比较法分析基础上对意大利商法“再法典化”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展望。(22)G.B.Portale,“Da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alle (ri)codificazioni:la ricerca di un nuovo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2019,pp.79-94.
(二)商法“再商法化”:巴西的立法尝试(23)对于巴西从民商分立立法模式迈向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介绍,以及在民商合一民法典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制定商法典的讨论,本人已经撰写论文详加讨论。参见夏小雄:《民商合一民法典和商法典的生存空间——以巴西私法立法结构变迁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本部分的讨论与上文的内容有所重叠,特此说明。
在19世纪欧洲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影响下,巴西也曾选择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不过是以先制定商法典(1850年)、后制定民法典(1916年)的方式加以确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大陆的民商合一立法理念传播到巴西,对巴西私法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过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立法讨论,巴西在2002年制定了一部完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将商法规范也纳入到民法典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商法制度的现代化。(24)D. Castro,M. A. Soares,“A teoria da empresa no Código Civil de 2002”,Revist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FMG,No.42,2002,pp.165-189.就商事关系的规范而言,统一民法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依据现代商法的发展趋势,以“企业”概念为核心建构商法规则体系,对于“以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而从事的有组织经济活动”加以全面调整,扩展了商法规范的适用空间,使其不再局限于“商人”或“商行为”的范畴。(25)L.M. Medeiros,“Evolução histórica do Direito Comercial,Da comercialidade à empresarialidade”, Jus Navigandi, No.16,2011.
尽管统一民法典对于商法体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固有的规范不足、制度缺陷、体系漏洞等问题也值得关注。首先,由于统一民法典的篇幅有限,“企业编”不能纳入全部的商法规范,由此导致很多商法制度在民法典之中没有得到规定或未能充分规范。比如,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规范较为简略,破产和重整未能纳入调整范畴,对于商业代理、特许经营、商事许可等重要商事合同类型未能加以规定,有价证券的法律规则不够全面完整。其次,民法典中的部分商法规范和特别法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关系,例如“企业主”概念未能充分考虑专业技术人士执业活动的规范调整,债法编有价证券的一般规定和票据特别立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再次,民法典对于商法规范的选择性纳入使得大量商事特别法不得不继续发挥其规范功能,比如1966年票据法、1976年股份公司法、1985年支票法、1996年不正当竞争法等。(26)G.M.Taddei, O Direito Comercial e o novo Código Civil brasileiro,Jus Navigandi,https:∥jus.com.br/artigos/3004/o-direito-comercial-e-o-novo-codigo-civil-brasileiro,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8月6日。
为了克服统一民法典在商事关系调整层面的上述弊端,巴西商法学界在统一民法典制定之后不久就提出了“制定商法典”的主张。在法比奥·乌尔荷拉·科尔勒荷(Fabio Ulhoa Coelho)教授的领导下,学界从2003年开始逐步推进新商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经过商法专家的长期准备和社会公众的充分讨论,商法典草案在2011年最终“出炉”并提交给了立法机构。
根据立法机构公开的“立法理由书”,民商合一民法典背景下另行制定商法典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商法规则的确定性,明确商法的独特原则和特别规范,更好规范调整以企业内外部关系为核心的商事关系;二是促进商事法律制度现代化,增强商事制度的科技化属性,以期提升商事交易效率、降低商事交易成本;三是确认商事习惯和自治规范的功能,充分肯定企业主自治法(自治规则和习惯规则)的重要性,强化它们作为自治性法源的功能;四是简化企业运营的法律规则,剔除不合时宜的制度约束,改变不够合理的规范安排;五是提升巴西商法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促成商法规则同国际标准接轨,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27)F.U.Coelho,“O Projeto de Código Comercial e a proteção jurídica do investimento privado”,Revista Jurídica da Presidência, Vol.17,No.112,2015,pp.237-255.概而言之,需要通过新商法典的制定,重申商法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推动商法体系现代化并促进巴西经济发展。(28)关于巴西商法典草案的立法说明参见Comissão De Juristas Para Elaboração De Anteprojeto De Cdigo Comercial No mbito Do Senado Federal,http:∥legis.senado.leg.br/sdleg-getter/documento?dm=4232146&disposition=inl.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7月10日。
整部商法典(草案)包括1 103条规范,分为三个部分:总则、分则和补充细则。“总则”分为四编:商法一般规则、企业主、企业财产和企业活动、营业法律关系。“分则”分为五编,分别为:公司、企业合同、农业法、海商法、企业程序法。从体系构造的角度来说,在民商合一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本身面临着较多的理论挑战和体系争议,但巴西商法典草案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回应了诸多质疑,这也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肯定。(29)关于巴西商法典草案的体系化评析参见T.A.R.Lima,F.U.Coelho,Reflexões sobre o projeto de código comercial,São Paulo:Editora Saraiva,2017.
首先,对于商法基本原则作出了全面的规定。鉴于商法实践中争议难题越来越多,而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最终都需要回到商法基本原则层面,司法实践也日益认识到“原则性裁判”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商法典对于商法基本原则(第5~9条)、公司法基本原则(第10~16条)、企业合同法基本原则(第17~21条)、有价证券法基本原则(第22~25条)、农业交易基本原则(第26~31条)、企业破产重整基本原则(第32~36条)、海事法基本原则(第37~43条)、企业程序基本原则(第44~48条)等加以了提炼总结。通过商法原则性规范的引入,可以更好保障商法规范适用的稳定性和预期性,特别是通过原则性论证消除民法典的“体系内漏洞”,促成商事争议案件“个案正义”的实现。同时,商法典也对商法原则的适用进行了适当的限定,以回应批判者所提出的“原则爆炸论”理论。(30)F.U.Coelho,Princípios do direito comercial. São Paulo,Editora Saraiva,2012.
其次,在统一民法典基础上继续发展“企业主”概念,采取“混合标准”认定“企业主”。“企业”和“企业主”是现代商法体系建构的核心概念,也是巴西统一民法典推动商法体系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标志。但是,在“企业主”的认定问题上始终存在形式主义标准和实质主义标准的论争,巴西商法典对于这一问题选择了“混合标准”方案(第49~50条),对自然人企业主采取实质主义标准,只要其开展了营业活动就有商法规则的适用空间;对于组织型企业则适用形式主义标准,只要企业组织形式符合商法典第184条所列举的企业组织类型,就可以认为其属于“企业主”,应当受到商法典规范的调整。
再次,继续推动公司法规则的现代化改革。商法典强调重构有限责任公司法制,简化相应法律规则构成,使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回应性,比如完善法人格否认制度、增加股东退出时的股权份额清算规则;简化和统一不同类型公司的分立合并、形式变更法律规则;简化公司组织类型,调整一般两合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的制度构成。
最后,继续完善商事合同法律制度。商法典认为商行为和一般法律行为存在差异,在效力评价、法律解释方面需要确立特殊化的规则,以买卖合同为核心的商事合同法律规则需要同国际规则接轨,对于统一民法典未能规定的供应合同、直销合同、信托合同、保理合同、共同投资合同、容量运输合同、船舶拖曳合同等重要商事合同类型需要提供明确的法律规则。同时,应当根据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实践需求,加强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及其交易的规制,明确企业之间缔结电子商务合同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并要求电子商务平台公布隐私政策,以强化对客户隐私的保护和对不当行为的规制。(31)G. L. C. Branco,“As obrigações contratuais civis e mercantis e o projeto de Código Comercial”,Revista de Direito Civil Contemporaneo, No.1,2014,pp.849-887.
(三)小 结
事实上,近年来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在推动私法立法改革时也不得不考虑商法的“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问题。以2014年生效的《阿根廷民商法典》为例,该立法没有采取“民法典”的传统命名方式,而是采取了“民商法典”的名称。(32)对于阿根廷民商法典的介绍,参见徐涤宇:《解法典后的再法典化:阿根廷民商法典启示录》,《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1期。同时,立法机构也放弃了将民法规则和商法规则全面纳入法典的想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法典的“原则性立法模式”,把对民商事关系的具体规范调整交由特别立法,在民商法典内部只是对民商法的基本规则进行了规定。尤其是从商法角度来看,通过采纳“企业”和“企业主”的概念重构了商法体系,把商法基本规则加以提炼,但是并不否认特别商事立法的功能。在阿根廷学者看来,私法体系下除了民商法典之外,还隐藏着很多由商事特别立法组成的微观法律系统,每个微观法律系统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路径,没有必要将其全部纳入到统一民商法典之中。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私法法典化思路,代表了民商合一立法的新路径和新趋势。(33)M.C.Araya,“El contenido del derecho comercial a partir del Código Civil y Comercial”,La Ley.,No.4,2015;E.D.Favier,“La‘autonomía’y los contenidos del Derecho Comercial a partir del nuevo código unificado”, La Ley.,No.2,2014.
可以看出,民商合一民法典与商法典立法并不矛盾。民法典立法大量吸纳商法规则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这是私法关系整体商化之后立法者的应然选择。但是,将所有的商法规则都纳入到民法典当中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一方面会导致民法典体系的臃肿,另一方面会导致商法规制独特性的消失,甚至会损害到商法的自治性,影响商事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就意大利和巴西的经验可以看出,民商合一民法典之外还需要考虑商法的“再商法化”问题,在此背景下商法典立法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和功能职责。
二、商法的“再法典化”:民商分立国家的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很多国家依然维持了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有些国家的商法典制定于19世纪,在商事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34)根据《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的研究,截至20世纪末,在其统计的107个国家中,制定了商法典的国家有59个。以上内容转引自赵万一:《民商合一体制之困境思考》,《法学杂志》2020年第10期,第48页。为了规范调整商事关系,越来越多的商事特别立法得以制定,商法典的功能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商法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或“解法典化”的现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去法典化”或“解法典化”只是一种学术语言描述,如同Portale教授所说的,在实践中从来没有真实地发生过。商法典在实践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商事特别立法虽然大量存在,但是它们只是把商法典当中所蕴含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加以具体化,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商法典所确立的基本规则框架。(35)G.B.Portale,“Da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alle (ri)codificazioni:la ricerca di un nuovo diritto commerciale”,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1,2019,pp.79-94.
当然,在商法典体系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在考虑更新商法典或重构商法典,实质性推动商法的“再法典化”。有的依然维持传统的制度体系,只对商法典进行“小修小补”或“重新编排”;更多国家则对既有商法典进行体系性重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法国商法典的修订、西班牙新商法典(草案)的制定、奥地利企业法典和比利时经济法典的制定。
(一)法国商法的“再法典化”:“恒定法”理念的实践
1807年法国商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1673年陆上商事条例的“翻版”,虽然在体系上有所创新,但其革命意义显然没有法国民法典那么显著。此外,法国商法典制定于19世纪初期,当时工业革命并未普遍开展,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反映了农业经济时代而非工业经济时代的商法规则。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立法机构不得不制定大量特别商事立法去弥补商法典体系的不足和缺陷。到20世纪末,商法典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商事特别立法所替代,仅留下一百五十多条有效规范。商法典的“空洞化”以及特别立法的不断增加给商法适用带来一定困难,也损害了商事交易的稳定预期。在此背景下,对于商法典进行体系重构、对商法规则进行整体更新具有现实必要性,2000年法国商法典重编工作就是基于这些考虑加以展开的。(36)参见王建文:《法国商法:法典化、去法典化与再法典化》,《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
但是,2000年法国商法典重编采纳了所谓的“恒定法”(droit constant)技术,立法机构已经意识到将所有的商法规范纳入到商法典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实现商法体系重构则需要更长准备时间,因此商法典重构的任务仅仅是将既有的商法规范重新加以汇编,并不需要从体系上对1807年商法典进行根本性的调整。(37)Y.L.Sage,“Methode de Codification a Droit Constant:Sa Mise en Oeuvre dans l’Elaboration du Nouveau Code de Commerce et Ses Consequences sur le Droit Applicable en Polynesie Francaise”,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33,No.1,2002,p.153.在此理念指导下,2000年法国商法典在体系上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此前已经存在的商法规范被重新“汇编”在一起。在“总论”部分,2000年商法典依然延续了1807年商法典的构造,其内容包括商行为、商人、商业资产三个部分,也就是说依然是以“商行为”概念为核心,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以“企业”(“营业”)概念为核心重构商法体系。(38)参见聂卫锋:《法典化与〈法国商法典〉的最新发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000年商法典这种汇编式的法典重构思路也遭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批判。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汇编式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商法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实践难题,其所建立的商法规范体系并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商法典之外依然存在银行金融法典、知识产权法典等,这些法典当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商法规范内容。更为重要的是,2000年商法典重编工作完全忽视了世界范围内商法的变迁发展趋势和最新立法动态,没有彻底实现商法规则的现代化。(39)参见尚尤、孙涛、吕文杰:《法国商法典两百周年纪文》,史际春:《经济法学评论》(第十二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36页。
事实上,法国商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注意到了传统商法典在体系建构层面的缺陷。特别是相对于复杂商事实践,立法机构没有意识到商法规范适用的主体范围和行为范畴有明显的扩张,传统商法典所坚持的“商行为”概念或“商人”概念已经不足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商事关系和商事主体,比如,对自由职业者、农业企业主等主体的活动不能加以有效调整,对于企业的复杂内外部法律关系也缺少充分关注。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将商法从“商行为法”、“商人法”改造为“企业法”的建议,进而对各种类型商事企业的内部法律关系和外部法律关系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调整。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法国学者之间并未成为共识。从商事审判的角度而言,更需要通过商法典的重构准确界定商法典的调整领域和商事法院的受案范围,2000年商法典在这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做得并不够,实践中诸多复杂疑难争议在商法典重编层面并未得到充分回应。
当然,在法国商法学者看来,2000年商法典重构“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法典化的方法运用不当,立法机构只考虑将现行商法规则加以重新整理,却忽视了这些商法规则是否符合实践需求、能否发挥规制功能。同时,对于司法实践所续造出来的商法规则也缺乏足够的重视;二是对于商法典的理想结构缺乏充分的认知,对于哪些内容应当纳入商法典、哪些内容不应当纳入商法典,立法机构没有明确的方案,这也导致商法典的内容和其他法律存在较多交叉重叠之处。上述原因导致重编后的商法典在其制定之后就显得“过时”。如果想要克服上述缺陷,必须继续推动商法典的改革工作,将商法典的规范构造聚焦于“核心内容”,制定一部能够切实发挥效用且能充分回应实践需要的商法典。(40)J. Monéger,“De l’ordonnance de colbert de 1673 sur le commerce au code de commerce français de Septembre 2000”,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économique,Vol.18,No.2,2004,pp.171-196.
(二)西班牙商法的“再法典化”:“企业法”的体系重构
西班牙目前适用的商法典是在1885年制定的。在1885年商法典施行之后,立法机构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对以商法典为核心的商法体系进行了调整:对商法典中的一些条款进行了修订,优化了商事登记、破产商人、会计制度等;制定了一些商事特别立法,比如有限责任公司法、竞争法、工业财产权法、消费者保护法、电子商务合同法等;以特别立法“变通”调整商法典规则,比如股份公司、证券市场、陆地运输、担保、汇票、支票、破产等方面的特别立法改变了商法典的规范立场。与日新月异的商事实践相比,1885年商法典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滞后性”。(41)Bercovitz,Presentación del Anteproyecto de Código Mercantil,en Hacia un nuevo Código Mercantil,en Bercovitz Rodriguez Odriguez-Cano,A. (coord.),Thomson Reuters,Editorial Aranzadi,2014,pp.37-54.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西班牙新宪法采纳了“市场经济条款”,并把商事立法权限归属于国家,强调通过法典化的方式对既有的商事特别立法加以体系性的整合,进而服务于统一市场体系的建构。商法“再法典化”成为统一西班牙商法规则的“政策工具”,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制定新商法典才能实现上述目的。(42)I.F.G.Juan,Proyecto de Código Mercantil y paradigma constitucional,Estudios sobre el futuro Código Mercantil:libro homenaje al profesor Rafael Illescas Ortiz,2015,pp.65-85.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以Garrigues、Uría、Menéndez、Olivencia等为代表的商法学者一直致力于商法前沿问题研究,对商事实践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加以体系化阐释,推动了商法学术的发展和特别立法的制定。对于商法典所存在的体系缺陷和所面临的实践挑战,他们也呼吁重构商法典,推动商法规范体系的现代化。
2006年西班牙司法部部长Juan Fernando López Aguilar最终提出了制定商法典的立法建议。在以Alberto Bercovitz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准备最终形成了商法典草案。西班牙商法典编纂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重新整理和更新商事法律。1885年商法典已经无法适应西班牙经济发展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增加的商事特别立法缺乏连贯性和体系性,使得商法体系日益碎片化。商法的“再法典化”可以实现对既有商法规范的体系化重构,可以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当然商法典立法并不需要将既有的商法规则全部加以纳入,而只需要将商法核心的、实质的内容加以规定即可。其次是为了推动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如同上文所述,这是西班牙宪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复杂中央—地方关系背景下促进规则一致、加强监管协调的重要手段。(43). G. Moreno,“Reflexiones sobre algunos aspectos relevantes del proyectado Código Mercantil”,Estudios sobre el futuro Código Mercantil:libro homenaje al profesor Rafael Illescas Ortiz,Getafe:Universidad Carlos Ⅲ de Madrid,2015,pp.182-201.
从结构上来看,商法典(草案)分为七编:第一编包括了商法的一般性规则,尤其对于商法典适用的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商法典的调整目标,具体包括企业主、企业交易、商事登记、会计制度等内容;第二编是关于商事公司的规范;第三编是有关竞争法规则的内容,包含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规则,也包括有关工业财产权的规范;第四编规定了商事债务和商事合同的一般规则;第五篇则涵盖了具体商事合同的法律规则;第六篇主要涉及证券和金融工具、支付工具的法律规则;第七篇则包括了时效和期限的相关规定。
和1885年商法典相比,商法典(草案)的最大创新在于它将商法体系完全加以重构,使其建立在新的概念基础之上。恰如“立法理由书”中所提到的:“商事法律关系的界定是基于一个基本概念:市场是商事交易主体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场所,并在其中建立受特殊法律规则约束的私人性法律关系”。立法者从“市场”这一概念出发探讨商法典的规范体系结构,尤其是对商事活动主体——“企业主”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等“企业”活动进行全面规范调整,这种体系调整也将使西班牙商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种法典化思路充分吸纳了现代商法学术研究的理论成果,也考虑到了1978年西班牙宪法中相关“市场经济条款”的要求。
在商法典(草案)的起草者看来,以“市场”、“企业”、“企业主”等概念来“统帅”商法典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活动就是“企业主”在“市场经济”秩序下所开展的以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为内容且有组织的经济活动。通过这些概念的引入,实际上扩展了商法典的调整范围,尤其将那些旧商法典没有调整的法律关系也纳入规制范畴,比如农业经济活动和手工业活动。另外,“企业主”概念实际上也对商法典的主体调整范围进行了扩张,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也涵盖了提供科学、文化、艺术、会计、律师等专业性服务的主体。同时,商法典(草案)对于企业主的市场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第三编规定了竞争法规则特别是对不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在立法机构看来这是“宪法所承认的市场经济模式下调整商事交易和市场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当然,这并不否认竞争法特别立法的重要性。(44)M. C. G. Calera,“Las nociones de mercantilidad del Proyecto de Código Mercantil:una deconstrucción a modo de denuncia o crítica”,Revista de derecho civil,Vol.1,No.4,2014,pp.27-6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商法典(草案)并未完全“放弃”对商事债务和商事合同进行规范,在第四编和第五编对商事债务和商事合同的法律规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其中,第四编在充分参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欧盟合同法”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对商事合同履行各个阶段的法律规则进行了优化,比如针对合同缔结阶段商事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完善了相关规定,也增加了电子合同的相关规定。第五编则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分销、供应、特许经营、广告、旅游、电子服务提供、金融合同等纳入商法典的调整范畴,也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规则,扩张了商法典在商事合同领域的调整范围,弥补了传统民法典和商法典规范体系的缺陷。对于未纳入第五编的非典型合同类型,也强调可以适用第四编的法律规则解决实践争议。(45)M. P. G. Rubio,“Algunas consideraciones sobre las normas de obligaciones y contratos de la propuesta de Código Mercantil”,Revista de Derecho civil,Vol.1,No.1,2014,pp.7-27.
也有学者对立法者的“雄心”表示质疑,认为“人人享有咖啡”的问题并不能通过“人人适用商法典”的方式加以解决。实际上,要想实现“人人享有咖啡”的目标,除了法律层面的努力之外,还需要经济维度的改革和政治层面的争取,有些政治层面的问题并不适宜通过商法典立法的方式加以解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法典立法要放弃自己的目标,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商法典立法确立更多的原则性条款和一般性条款,整合商法规范、重构商法体系进而实现商法的动态平衡发展,在涉及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具体问题时则可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解决。(46)A.L.Carmen. “El Derecho mercantil del siglo XX:balance general de un siglo que se agota”. La Ciencia del Derecho durante el siglo XX,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1998,pp.541-591.
(三)商法的“再法典化”:奥地利企业法典
奥地利商法发展深受德国商法的影响。与《德国商法典》一样,1938年《奥地利商法典》也是以“商人”概念为连接点,但这一概念“被”置于历史之中才可被理解,且与其他经济法规使用的现代化“经营者”概念相冲突。同时,《奥地利商法典》内容较为复杂,很多法律规则也被证明已经过时,不再充分适应经济的发展,并造成法律适用困难。在此背景下,奥地利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改革推动商法规则的全面现代化,促进企业法规范的自由化和便捷化,增强商事交易的法律稳定预期。经过长期的准备,2003年奥地利司法部提交了《〈奥地利企业法典〉司法部草案》,随后立法机构审议通过。2007年生效的奥地利企业法典实际上对1900年德国商法典所确立的商法体系进行了重构,特别是抛弃了传统的“商人”概念,转而以“企业”、“经营者(企业主)”概念作为法典的基础事实构成。通过这种调整,商法典的调整范围得以扩张,自由职业者、农林业者、形式经营者也纳入企业法典的规制范畴。同时,企业法典也推动了商号法的自由化,调整了人合公司法的构成,修订了企业会计法,对于与商事交易有关的特别债法规范和物权法规范进行了内容简化和体系调整。当然,在奥地利立法机构看来,企业法典并不是一部全新的商法典,而是对于商法典的“再法典化”——对于旧商法典仅做体系调整而已。因为商法典已经涵盖了专业化商事交易的根本性内在原则,保留这些既有规则对于法律适用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47)参见“《奥地利企业法典政府草案》立法理由书节译”,葛平亮译:《中德私法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41页。
(四)商法的“再法典化”:比利时经济法典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在2013年制定并在2019年修订的比利时经济法典(Code de droit economique),该法典采用了全新的“企业”概念取代传统的“商人”、“商行为”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拆解了传统的商法典体系,比如将“商事法院”(le tribunal de commerce)改造为“企业法院”(le tribunal de l’entreprise),将部分商法典内容“转移”到其他立法或者重新加以整合,将“商法典”更名为“经济法典”。(48)T.Nicolas,ed. Le code de droit économique:principales innovations,Primento:Larcier,2015.对于该法典立法,立法机构对于其功能和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特别提到了“必须对传统商法规则进行重新检讨”,以维护营业自由、保障商业交易的可靠性、确保消费者得到保护。立法机构也同样提及了两种法典化思路,一种是形式化法典,对既有商法规则进行重新编排,但不从根本上调整其概念基础和体系结构;一种是实质化法典,也即对既有商法规则进行根本性反思,重新建构商法的原则体系并实现商法规则的现代化。比利时经济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两种法典化思路,既重构了商法的原则和体系,又把既有的商法规则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模块立法”(“législation en modules”)技术手段实现了商法规则现代化,其经验也值得借鉴反思。
(五)小 结
事实上,除了上文所讨论的国家之外,采纳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49)2021年埃塞俄比亚对1960年制定的商法典进行了“重构”,新商法典包括“商人和企业”、“企业组织”、“破产”三编,并采取了以下改革举措: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允许非股东担任董事、加强小股东保护、承认集团公司、引入登记豁免制度、增加网络化要求、允许视频股东会、优化破产程序等。参见https:∥home.kpmg/content/dam/kpmg/ke/pdf/tax/Tax%20Alert%20-%20Revised%20Commercial%20Code%20of%20Ethiopia_final.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5月12日。)也均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商法典,依然强调商法典在商事关系调整规范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功能。(50)V. M. C. Luna. “La recodificación sustantiva del derecho mercantil”,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No.7,2004,pp.3-47.值得注意的是,再法典化后的商法典体系构成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规则性规范集合体”变成了“原则性规范集合体”,这种调整使得商法典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开放性。就具体内容而言,商法典的重构不再以传统的“商人”或“商行为”概念为基础,而是以“企业”概念为基础。即便是那些没有对商法典进行“大修大补”的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承认商法已经转变为以“企业”概念为核心的法律体系。(51)R.Goldschmidt,M.A.P.Ricci,G.Rodríguez,Curso de derecho mercantil,Universidad Catolica Andres,2001,pp.81-92.这种调整代表了商法典立法和商法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三、理论总结和经验启示
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商法发展趋势尤其是商法的“再商法化”、“再法典化”问题可以做一个理论性的总结,并可基于这些经验讨论对于我国商法体系完善的可能借鉴意义。
(一)理论总结
首先,商法典立法依然是当代商法发展的主导形式。从统一商法规则、促进商事交易的角度来讲,以法典化的方式对商事法律规则进行体系化整合,对于保证商法的独立性、提高商法规制效率、节省商事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上文的比较法考察来看,商法典立法依然是当下各国商法发展的共同趋势。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商法发展层面,商法的统一主要是通过法典化的方式加以实现。非洲区域的统一商法运动基本上是以制定商法典的形式加以呈现,当然就其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是学习了法国的商法典立法模式;(52)[美]克莱尔·莫尔·迪克森等著,朱伟东译:《非洲统一商法:普通法视角中的OHADA》,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2页。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层面目前也在讨论统一商法典的制定。(53)Anne Marmisse d’Abbadie d’Arrast,“Droit européen des affaires”,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ommercial et de Droit Economique, No.1,2019,pp.253-258.
其次,民商合一的民法典与商法典可以“并行不悖”存在。民商合一民法典的制定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它吸纳了较多传统商法典中的商法规则,但并不排斥商法典的存在。因为商法典的体系构成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像19世纪商法典那样以“商行为”作为商法体系建构的概念基础,而是转换为以“企业”概念为核心基础事实。就此而言,民法典即便是采取民商合一体例,其与商法典的规范内容、调整对象相对而言依然完全独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矛盾之处。通过商法典的制定可以使得商法价值、原则、方法等要素的独特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进而更好突出商法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再次,在当下私法体系下商法典依然是商事法律体系的“中心”。商法典作为商法规范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的法源、原则、方法等问题,并对商事部门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基本制度加以了确认。以原则性规范为主的商法典体系对于商事关系的调整有重要的意义,它既确立了基本商法规则,同时也能使得自身与商事实践保持一定的适应性,商法体系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未来的商法规范解释适用过程当中商法典的原则性条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适用,尤其是涉及疑难案例的时候,必须通过原则性条款的解释才能有效处理疑难问题、填补法律漏洞。(54)G.Terranova,“I principi e il diritto commerciale”, Rivista del diritto commerciale e del diritto generale delle obbligazioni,No.2,2015,p.1.ss.
最后,商法典与特别商事立法之间并不冲突。法典化技术本身有其缺陷,商法典立法同样如此,希望通过一部商法典的制定“纳入”所有商法规则的想法根本就不现实,因此必须正视法典化立法在本体论层面的根本缺陷,“理解”商法典的功能限度并在立法技术上作更为成熟的处理。对于具体商事关系的调整和商法争议问题的解决,无疑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制定更多的特别立法,尤其是现代商业交易和商事监管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商法典立法之外还需要更多特别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商法典本身能够作为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甚至具体监管政策文件的“指引”,既可能构成抽象的授权,也可以形成具体的约束。当然,具体的商事特别立法不能同商法典构成根本性冲突,这是现代法治体系的一个根本要求。
(二)经验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商事法律规范体系,但是立法机构主要以制定商事特别立法为主要任务,立法过程中的理论论证和制度研究有所不足且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目的,这就使得商法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均存有缺陷,一些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和体系性不足甚至影响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55)参见赵旭东:《改革开放与中国商法的发展》,《法学》2018年第8期。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既有的商法规则加以体系化梳理,消除商法规范层面的冲突和矛盾,弥补商法体系维度的不足和缺陷,澄清商法适用视角的分歧和争议,这是当代中国商事法治发展应当致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从上文的比较法检讨可以看出,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民法典必然会带有较强的“商法品格”,这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所决定的。民法学者强调民法典对于商事关系的“一体化调整”有其合理性,民法典立法在总则、分则层面的具体构造也体现了这种要求。但是,应当注意到这种“一体化调整”有其功能限度,要想实现对商事关系更有效率的规范,需要对商事关系的本质和构成重新加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适应商事实践需要的商法规范体系。(56)参见施天涛:《商事关系的重新发现与当今商法的使命》,《清华法学》2017年第6期。
就商法规范的具体立法表达而言,应当认识到“商法典”仍然是实现商法规则体系化和科学化的最佳工具,其所能发挥的功能、所应占据的地位绝非任何一个特别商事立法所能取代。“中国需要编纂一部《商法典》,这是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稳定并有序发展、保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创新工程”,(57)参见范健:《编纂〈中国商法典〉前瞻性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商法典的制定将充分解决我国商法存在的缺乏预见性、碎片性分布、法律规范冲突、理论基础薄弱、一般法缺位等问题。(58)参见范健:《当代中国商法的理论渊源、制度特色与前景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当然,我们也需要更新法典化立法观念。如同在比较法层面所观察的经验一样,未来的中国商法典同样不需要将所有商法规则全部纳入,而应尽量全面提供调整商事关系的“原则性”法律规范,同时预留商事特别立法的空间。在商法典具体体系建构上,可以以“企业”、“企业主(经营者)”概念重构商法规范体系,(59)参见叶林:《企业的商法意义及“企业进入商法”的新趋势》,《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适当扩展商法典的编制构成,将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规则(包括竞争法律规则、程序法律规则等)妥当纳入到商法典框架,以原则性规范为指导促成各领域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进而实现对商事关系和商事争议的全面高效调整。(60)蒋大兴教授认为未来的商法典总则应由“七编”构成:立法目的与原则、商人及商号、营业行为、商事登记/备案、不当交易规制、纠纷解决、附则。参见蒋大兴:《〈商法通则〉/〈商法典〉总则的可能体系——为什么我们认为“七编制”是合适的》,《学术论坛》2019年第1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言,商法的“再商法化”和“再法典化”迫在眉睫,我们期待中国商法典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