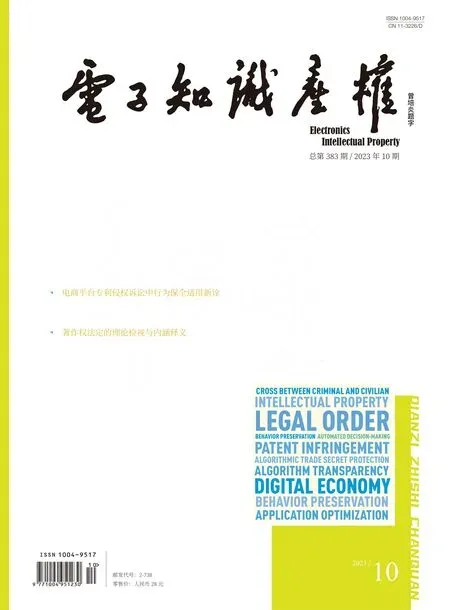专利间接侵权与许可费定价问题之体系化研究
文 / 李春晖 陈英豪
一、引言
体系化思维是立法、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的必然要求。体系化包含逻辑性与同一性这两个必备要素,逻辑性强调系统整体的协调统一,同一性则意味着系统组成要素的目标一致性。1.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33页。体系化思维在不同层面都有体现。例如,法治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在内的各个环节,每一环节内部都应贯彻体系化思维;同时,对于特定立法目的的实现,每一环节可能存在多个殊途同归的路径,若一个环节采用不同路径,其他环节即应相应配合。
作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体系解释是体系化思维在立法之后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体现。体系解释不仅仅是简单地“联系上下文”,而是要关注到法律制度的“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两个方面。2. 宋保振:《体系解释的中国运用》,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第31-35页。“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在执法或司法中完成具体法律的再次体系化(因为立法的时候,法律已经有一次体系化)”,3. 陈金钊:《体系思维的姿态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2 期,第69-81页。并再次反馈到立法活动中。更为重要的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体系化思维,亦可帮助发现和弥补立法中本来存在的有违体系化思维的缺陷和漏洞。
对于经由行政确认的知识产权,一致的理念和原则应贯穿立法上的权利设置、行政上的具体权利授予以及包括司法上的权利保护在内的权利行使这三个阶段。专利制度中即存在两个尤应体系化思考的研究课题。
其一是间接侵权问题,即故意以便利他人实施专利技术方案为目的而实施权利要求的并非全部(但却是关键和核心的4. 如“专门用于实施专利的材料、设备、零部件、中间物等”,即专用品。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6 年1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6 次会议通过(法释〔2016〕1 号),根据2020 年12 月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 次会议修正(法释〔2020〕19 号),第21 条。)技术特征,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进一步,即使不存在直接实施主体或直接实施行为不构成或不视为直接侵权行为,该部分实施行为是否仍构成侵权且承担赔偿责任。现有研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专利权人利益保护是否充分、5. 刘友华、魏远山:《欧洲系统专利间接侵权认定及其借鉴》,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11 期,第87-96页;李照东:《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多维度解读》,载《山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8 期,第185-192页。直接侵权、间接侵权和共同侵权归责原则的冲突和协调、6. 何培育、蒋启蒙:《回归抑或超越:专利间接侵权与共同侵权理论之辨》,载《知识产权》2019 年第5 期,第54-55页;蔡元臻:《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专门化研究》,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5 期,第1227-1245页;彭官棋:《创新视域下专利间接侵权规则的体系建构与内容优化》,载《中国科技论坛》2021 年第4 期,第118-127页。专利法有关权利要求解释和侵权判定的原则是否得到遵循7. 张初霞、王东:《对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理论构建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 年第5 期,第70-80页;及前注6,彭官棋文,第118-127页。等。
另一问题是专利许可费的计算,这在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SEP)许可中尤其突出。虽然SEP 许可费问题的难点在于合理公平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ion, FRAND)承诺与专利劫持和反向劫持之矛盾的解决,其最终仍表现为司法决策中对许可费的计算方法,这包括费基和费率两个因素。费基方面主要有整体市场价值(Entire Market Value, EMV)原则和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Smallest Salable Patent Practicing Unit, SSPPU)原则两个选择。也有学者采折中路线,认为应综合考虑SEP 专利组合涵摄的技术领域、贡献,以及不同技术主题在终端产品各功能中的关联或互补效应,在两种费基之间确定更符合权利人技术贡献的许可费计算基础。8. 参见刘影:《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计算:理念、原则与方法》,载《清华法学》2022 年第4 期,第166页;龚炯、熊凯军:《手机蜂窝通信功能价值影响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费基问题研究》,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 第6 期,第39-43页。
上述争论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实际上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例如,对于间接侵权问题,无论是迫使权利人撰写更好的权利要求从而摒弃间接侵权,还是容忍权利要求的撰写瑕疵而出于实质公平等考虑规制间接侵权,都能在其他配套制度做出相应调整的情况下实现保护实质性创新的结果;对于许可费定价问题,如果专利技术的价值存在客观标准,那么无论以SSPPU 来计算还是以EMV 来计算,最终结果都应趋同;反之,若法官或行政机关具有倾向性,也难以有效阻止其通过对诸多原则“各取所需”地适用,“排列组合”后得出任何一种声称符合FRAND 承诺的费率结果。9. 同前注8,刘影文,第159页。如此,各种争论不过是考虑具体个案利益的博弈,就整个制度而言其实无关痛痒。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路径不同将导致制度成本不同。究竟何种路径最优,须以综合考虑法治的基本特征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等的体系化思维进行考察。对体系化思维的破坏,必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付出更高的制度成本或者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
间接侵权理论和许可费定价问题往往聚焦于权利行使时的利益平衡和博弈,容易忽视权利行使是立法、申请、授权确权的延续。其中部分原因是缺乏体系性思考的自觉,还有部分原因则是利益的拉扯而致体系的千疮百孔。在各自的问题研究中缺乏体系性思维,自然也就没有发现两个议题的关联性和统一性。本文将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与间接侵权理论结合起来以体系化思维加以审视,以期为在这两个议题上尊重权利要求,同时为《民法典》之共同侵权、帮助侵权有关法律规范提供强有力的体系解释支撑。
二、专利间接侵权理论综述与初步批判
(一)专利间接侵权理论综述
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在中国立法、司法实践与学术研究中呈现相互背离的状态。学术界主张采纳间接侵权理论的呼声较多,而立法和司法采取审慎态度,但也有部分法院的判决尝试突破立法和司法解释。
该理论源于Wallace et al. v. Holmes et al.案10. Wallace et al. v. Holmes, 29 Fed. Cas. 74, No.17100 (C.C. Conn. 1871).。基于该理论,专利权人得要求特定场合下的行为人对其未全面覆盖权利要求所载全部技术特征的实施行为承担专利侵权责任。其在中国的司法应用始于1993 年,自此有关争论便持续不断。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前后形成了一个讨论高潮。原本包括在2009 年6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规定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2009 年6 月18 日发布,其第16 条:“行为人知道有关产品系只能用于实施特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设备等,仍然将其提供给第三人以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权利人主张该行为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第三人的实施不是为生产经营目的,权利人主张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征求意见稿是最高人民法院因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工作而暂停的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 2003.10.27-2003.10.29)的延续。,在最终通过的司法解释当中被取消1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 号)。。因此,该问题交由《侵权责任法》和后来的《民法典》在共同侵权或帮助、教唆侵权(广义的共同侵权)范畴下解决。推论之一是,间接侵权以直接的共同侵权为前提,因而不存在或不宜规制不存在直接侵权情况下的专利间接侵权,此为“共同侵权说”或“从属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纠纷解释(二)》)即遵循了这一理解。
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存在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即其不以专利直接侵权为前提,为“独立说”。“折中说”仍可划入“独立说”范畴,认为一般而言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需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但当直接实施专利之行为进入法定“不视为侵权”(例如非营利目的)范畴而不构成直接侵权时,可直接追究所谓间接侵权人的责任。13. 张玉敏、邓宏光:《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三论》,载《学术论坛》2006 年第1 期,第143页。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 年《专利侵权判定指南》虽碍于《专利纠纷解释(二)》的规定不得不在共同侵权框架下处理所谓间接侵权问题,但规定了当直接实施者为非生产经营目的而不构成侵犯专利权时,或者为专利法规定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临时过境、科学研究和实验以及Bolar 例外)时,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第119、130 条)。14. 另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一中民初字第133 号民事判决书。这种处理方式看似遵循了间接侵权以直接侵权为前提,但其所谓的“直接侵权”,完全与我国专利法中的“侵犯专利权”概念不符。该观点的一个延伸是,即使同时存在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也未必追究直接侵权人,可径行单独追究间接侵权人。15. 参见闫文军、金黎峰:《专利间接侵权的比较与适用——兼评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载《知识产权》2016 年第7 期。另,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 Paper Co. v. International Paper Co.案中指出,为专利权人因间接侵权行为提供救济,无需以直接侵权行为既已着手作为先决条件,只要具备专利被直接侵害危险即符合条件,Graham Paper Co. v. International Paper Co., 46 F.2d 881 (8th Cir. 1931). 也就是说,尚不存在直接侵权人,只是有产生直接侵权的危险。韩国亦有类似实践。16. 申惠恩:《韩国专利权间接侵权制度研究》,载《知识产权》2015 年第4 期,第143-148页。
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语境下,对专利间接侵权的讨论首先应排除本可为《民法典》之共同侵权和帮助、教唆侵权的最正统解释所能涵盖的侵权类型,即具有意思联络的“共同故意”或“故意加过失”专利侵权,存在直接侵权人实施的或共同侵权人共同实施的直接侵权行为。这包括《专利纠纷解释(二)》第21 条规定的全部教唆型侵权和部分帮助型侵权,但也包括更多情形,如“专用品”只是考察是否构成故意帮助的因素之一,而非仅限于此。因此,尽管很多讨论可能在各个概念之间混淆不清,但本文讨论的专利间接侵权,是《专利纠纷解释(二)》第21 条第一款(帮助)的部分情形以及部分学者所主张的变体。这包括两个既可独立也可结合的要点:一是行为人虽然明知有关产品系专用品,但行为人与直接实施专利的实施人并无意思联络(以下简称“情形1”);17. 参见前注6,蔡元臻文,第 1227-1245页;吴汉东:《专利间接侵权的国际立法动向与中国制度选择》,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2 期,第30-45页;前注6,何培育、蒋启蒙文,第46-57页。二是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或直接实施人的实施行为并非侵权行为,如非生产经营目的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不视为侵权的情形(以下简称“情形2”)。
间接侵权理论支持者(即独立说和折中说)的最根本理由在于,因专利权人的“微小”失误而不保护其创新贡献对专利权人并不公平,18. 同前注5,李照东文,第185-192页。即追求一种实质公平,或谓对专利侵权的实质解释。19. 同前注7,张初霞、王东文,第70-80页。简言之,支持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那些理由,也在论证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在认定了保护正当性的前提下,能否被共同侵权制度所覆盖,20. 参见张晓霞:《论间接侵权行为的独立性》,载程永顺主编:《专利侵权判定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 年3 月第1 版,第258-265页;张玉敏、邓宏光等:《专利间接侵权问题》,载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下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4 月第1 版,第1613-1614页。对共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尤其是共同过错的各种讨论,以及对专利法种种原则的违反与否,21. 参见于立彪:《关于我国是否有专利间接侵权理论适用空间的探讨》,载《专利法研究(2007)》,第439-442页;魏徵《我国不应该有专利间接侵权理论的应用空间》,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08 年第1 期,第37-39页。均属细枝末节。
间接侵权理论反对者认为,该理论实为放任权利人的撰写失误,破坏专利制度的稳定性、严肃性和第三人对法律和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权的信赖,扼杀公众回避设计的权利,不利于申请人撰写水平和专利质量的提升以及司法标准的统一。22. 同上注21,于立彪文,第37-39页。即使对帮助、教唆侵权,其前提也应是存在第三人直接侵权,23. 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08页。以及存在指向共同实施的意思联络。24. 参见李春晖:《专利丛林中的食人树——也议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载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提升专利代理服务能力——2011 年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年会暨第二届知识产权论坛论文集》,2011 年,第1033-1034页。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德国专利法》第10条规定了间接侵权,结合第11 条可知其中包括向非商业目的的私人使用、科学实验、育种、Bolar 例外以及按处方临时配药等提供专用品以帮助实施专利的情形。《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613-4 条和 L613-5 条的规定基本相同。
《美国专利法》第271 条(c)对间接侵权(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的规定在字面上以直接侵权为前提。特殊情形是,第(f)款规定的拆散部件跨境组装也包括第(2)项间接侵权的情形,但第(1)和第(2)项实际上均未实际发生在美国境内的直接侵权。不过,与其他情形不同,这是货物跨境因为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而产生的特殊情况。除此之外,美国法院始终坚持专利间接侵权的从属性,如Akamai 案。25. Limelight Networks, Inc. v. Akamai Techs, Inc., 572 U.S. 915 (2014).
但我国的间接侵权理论支持者指出,德法等国看似认同专利间接侵权之独立性,不同于美国认为专利间接侵权从属于直接侵权,但若考虑到在美国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个人擅自制造、组装专利产品也构成对专利权的侵害,而德法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个人制造行为并不构成专利侵权,则两种策略实际上具有一致性。26. 王国柱:《多数人侵权视野下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制度》,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3 期,第108页。
(二)体系化思维对专利间接侵权理论之批判
1.未遵循民法一般理论中侵害与损害之关系
间接侵权理论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深刻有力的正当性论证,将对所谓专利间接侵权的规制视作理所当然之事,所需争辩者不过实施细节耳。27. 同前注24,李春晖文,第1019页。其前提是“专利权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进而认为仅追究专利直接侵权者的责任不足以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这实际上割裂了利益的损害与权利的侵害,在并无侵害专利权的情况下,行为人要为专利权人的某种利益损失负责。
从绝对权保护角度看,法律已明确界定了绝对权边界,损害须以侵害此边界为前提。有学者为自圆其说,将《专利法》第11 条把专利侵权限于“生产经营目的”的规定,解释为该条表明专利侵害行为遵循客观认定的基本原则,即只要他人实施的行为落入专利权范围之中即构成专利侵害行为,而第11 条规定的“生产经营目的”的实质即是对专利侵权赔偿责任主观过错推定规则的明确。28. 宋戈:《方法专利分离式侵权的判定——以“西电捷通案”为视角》,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 年第11 期,第74页。这种解释既无法满足法条的文义,也不符合绝对权的原理。越过法律划定的权利边界即为“侵害”,即使没有损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也应停止侵害,而第11 条的含义显然是若非生产经营目的,则可以制造、使用等,不存在停止侵害的问题。实际上,在传统物权法中,由于很多情况下利益与客体物本身的合一,侵害与损害,进而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之债请求权有时难以区分。但是在如专利权这一类绝对权中,侵害与损害反而有清晰的界限,因为权利边界由法律划定而与实体物无关,越过边界未必立即产生损害。在法定绝对权中,有关客体和行为的界定,皆为权利本身是否被“侵害”的边界,涉及赔偿时,所关涉的才是“损害”。毫无疑问,是否有“生产经营目的”,界定的是权利侵害的边界,而非关于损害赔偿的过错推定规则。《专利法》第75 条与此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2. 未尊重绝对权保护、法益保护与利益之区别
从绝对权保护角度看,对专利间接侵权的规制缺乏正当性。若要规制,须从法益保护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法”)入手。但这一路径也不通,因为法益即权利,即便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也需要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受保护的权益基础,或是否存在行为人必须承担的义务以及此义务是否被违反,29. 李春晖:《绝对权、绝对义务及其相对化——民事权利与法益保护的单一框架》,载《中外法学》2023 年第3 期,第646-667页。包括有关诚信原则、守法和商业道德的一般条款。
从权益基础来看,专利权人的有关利益无疑首先要以《专利法》来界定。但在间接侵权问题的情形2 中,直接实施者的行为是合法的,因此对该合法行为的帮助并未造成专利权人的利益损失,相应地也就不存在违法或背俗。支持者的逻辑在于,帮助直接实施者这一行为,本来也应由专利权人来实施以赚取其利益,因此或可认为这种帮助行为不符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然而,于此《专利法》已经界定了权利的范围,在权利范围之外,任何人本来就具有全面的行动自由,包括“回避设计”的自由,因此帮助行为并未违法或背俗,除非认为对专利的回避设计均构成不诚信行为。
这里涉及反法与具体绝对权的专门法(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作为专门法保护之兜底的反法,是一般法的地位,应优先适用专门法。就法律规范中相同的行为模式前提,若专门法已经规定了权益和行为的界限以及相应的后果,那么在一般法下不应再出现相反或重叠的规定或司法适用,若有必要,应由立法机关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在专门法中予以规定。
3. 未协同考虑专利法诸原则:“最小保护单元”问题
专利法(包括其细则和审查指南)的若干撰写和审查规则,根本目的是清楚地界定专利权边界,即专利或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这包括撰写、申请和审查阶段的权利要求架构方式和有关可保护客体、必要技术特征、清楚、简要、说明书的支持、“三性”(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要求,以及侵权判定阶段的权利要求解释规则和侵权判定规则,包括折中解释原则、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反向等同原则、捐献原则等等。30. 参见李春晖:《权利要求解释原则、规则与案例梳理》,载《专利法研究(201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版,第39-63页。所有这些要求和原则中,撰写、申请和审查阶段的各种要求旨在限定“最小保护单元”,31. 陈庆超:《论权利要求主题的确定》,载《专利代理》2019 年第1 期,第22-26页。侵权判定阶段的各种规则和原则仅限于解释该“最小保护单元”而不能再实质性改变之。
专利法诸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专利权的权利内容不仅由法律确定,具体的权利实例的客体亦系基于法律规定,由申请人和专利局通过“申请-审查”这个互动过程共同界定,而非由不可控制的客体本身界定。32. 参见易继明、李春晖:《知识产权的边界:以客体可控性为线索》,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4 期,第135页。自然,权利行使之时,即应以获权时界定客体的相同方式来解释客体,此即权利公示原则的意义,其实际上是要求申请人/权利人和以专利局为代表的政府双方均不得反言。
而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已超越上述诸解释原则规则,相当于直接改写撰写、申请和审查阶段已大致确定的“最小保护单元”。究其原因,权利要求在撰写和审查时错误地包括了非必要技术特征、不简要,从而不符合修建准确完善的“篱笆”以完整保护专利权人之利益的需求,而欲以专利间接侵权理论来弥补。
4. 未全局考量不同路径选择的制度成本与效率
是否规制所谓专利间接侵权,本质上是不同路径选择之间的权衡。不能单纯观察能否最终实现保护专利权人的目的,还要考虑社会公众之利益,并观察不同路径的制度成本和效率差异。这既要求路径中每一环节本身考虑制度成本和效率差异,又要避免不同环节的制度设计互相龃龉,使得整体制度相较于立法目标而言在每一阶段均发生相互加剧的偏离而非相互弥补彼此的不足,从而不公平地损及某一方的利益,或加大制度运行成本。
间接侵权理论的收益,是令权利边界划得不够清晰的专利权人的利益仍然得到保护(因而对可能具有足够创新却对专利法规则不是很熟悉的申请人仍提供专利法激励);其成本则是令专利权在法律上的边界模糊化,违反权利公示原则,降低专利权和专利制度的可预期性,进而降低公众对之的信赖,提高制度运行成本和权利的流通成本。
否定间接侵权理论的收益和成本则与上述相反。问题的实质是两种利益的衡量:可能具有足够创新却对专利法规则不是很熟悉、或不是很尊重专利法规则的申请人的利益,与对法律怀有信赖的广大社会公众及其他严格遵守专利法规定的广大申请人的利益。如此陈述问题,孰重孰轻便一目了然。然而在现有研究中,片面强调权利人利益有道德制高点的优势,但是其忽略了间接侵权理论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和无效率。
三、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研究综述与初步批判
(一)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研究综述
与间接侵权问题一样,许可费/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的SSPPU 问题同样出现司法和学界背离的现象。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SEP)许可费问题争议更为激烈。在美国,立法和司法虽无一刀切的定论,但大多数案件不同程度使用了SSPPU 原则,引起产业界一片反对之声;相反,在中国,行政和司法都适用EMV 原则,而学界和实务界多主张SSPPU 原则,至多主张折衷的标准。33. 同前注8,刘影文,第166页。
美国法院早已认为专利权人应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主张“分配”至被控侵权产品的对应专利部件上,排除非专利部件的贡献,34. See Garretson v. Clark, 111 U.S. 121 (1884).此即“分配原则”(Apportionment Principles)。同样,在许可费计算中,若专利仅涉及包含多个零部件的产品中的某一零部件,若以该整件产品为基准来计算专利许可费就会让专利权人不公平地获得非侵权零部件的贡献价值。35. See Laser Dynamics, Inc. v. Quanta Computer, Inc., 694 F.3d 51 (Fed. Cir. 2012).SSPPU 概念是分配原则的进一步发展,由雷德法官(Judge Rader)在康奈尔大学诉惠普公司一案中首次提出。他认为,为了避免错误地将非专利部件部分纳入许可费计算,应将SSPPU 作为分析和计算专利许可费的起点,而非以终端产品的整体价值作为计算专利许可费的依据。36. See Cornell Univ. v. Hewlett-Packard Co., 609 F. Supp. 2d 288 (N.D.N.Y. 2009).自此至2017年,约75 个联邦地方法院在陪团审判中使用了该概念,而Innovatio 案37.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LLC Patent Litigation, 956 F. Supp. 2d 925 (N.D. Ill. 2013).是唯一在法官审判中使用SSPPU 概念的。38. 参见David .J.Kappos&Paul R.Michel:《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的起源、沿革及走向》,载《竞争政策研究》2017年第2 期,第92页。
与之相对,存在终端产品EMV 原则的主张,认为应以终端产品的市场价格作为计算专利许可费的依据,条件是“专利权人必须证明‘与专利有关的部件是用户需求的基础’”。39. See Lucent Technologies v. Gateway, 580 F.3d 1336 (Fed. Cir. 2009).但每一部件都会对用户需求作出相应贡献,故问题在于专利有关的部件在多大程度上作出了更突出的贡献。在CSIRO 诉思科案中,虽然地区法院没有采用根据许可费基础进行分配的计算模式,但其论证“专利的价值在于创意,而不是执行创意的硅片”,40. See Scientific v. Cisco Sys.,Inc., 809 F.3d 1295 (Fed. Cir. 2015).可认为是对EMV 原则的支持。但综合全美相关案例,基本可认定美国以SSPPU 原则为基础,而整机价格为例外。
在美国以外的地区,SSPPU 概念对法院影响甚微,尚无任何欧盟法院依据SSPPU 原则计算并裁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金。41. Haris Tsilikas、胡盛涛:《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概念及其在FRAND 判定中的局限性》,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20 年第12 期,第13-24页。在 FRAND 相关争议案件诉讼中,英国法院在 Unwired Planet案中认为自上而下法可为可比协议法的交叉验证。42.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017] EWHC 711 (Pat), Case No. HP-2014-000005, April 2017, affirmed in Unwired Planet v.Huawei, [2018] EWCA Civ 2344, Case No: A3/2017/1784, 23th Oct. 2018, and affirmed in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020]UKSC 37, Case ID: UKSC 2018/0214, 26th August 2020.在InterDigital v. Lenovo 案中,法官采用了可比协议法,而对InterDigital 用自上而下法予以交叉验证的要求完全未予理会,因为法官认为InterDigital 欲通过交叉验证予以佐证的可比分析法所确定的费率在可比协议分析中即明显不合理。43. InterDigital v. Lenovo, [2023]EWHC 539(Pat), Case No.HP-2019-000032, 16th March 2023. 此案仍未终局,InterDigital据称决定上诉。此外,在荷兰海牙地区法院审理的Archos v. Philips 案中,法院指出SSPPU 概念具有争议,且不能仅仅因为许可费率未采用SSPPU 作为计算基础即认定许可要约不符FRAND 原则。44. Archos S.A. v. Koninklijke Philips N.V., The Hague District Court (Rechtbank Den Haag) Case No. C/09/505587/HA ZA 16-206 (2017).
迄今为止,在本身数量有限的案件中,中国行政和司法机关事实上采用了终端产品价格作为费基。例如,在高通涉嫌在无线通信SEP许可市场及无线通信终端基带芯片市场滥用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的调查中,及高通与魅族的垄断纠纷中,高通的整改措施及索赔基础均以终端产品为定价基础。在华为诉交互数字公司(IDC)滥用市场地位垄断案中,深圳中院的裁判也以终端产品作为计算基数。45. 孔繁文、彭晓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计算基数之初步法律研究》,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 年第3 期,第94-98页。
中国、欧盟的行政、司法机关的选择事实上符合SEP 权利人如高通公司的偏好。针对美国司法诸多以SSPPU 为费基的判决以及拥护SSPPU 原则的学者观点,高通公司时任专利委员会资深副总裁的马克·斯奈德(Mark Snyder)撰文认为,美国法院陪审团在运用 SSPPU 计算时,可能会忽略经济学家在计算损害赔偿时本来会考虑的许多其他潜在基数所带来的收益,因此SSPPU 远非一项实体法律规则,而仅是特定情况下使用的狭义工具,适用于陪审团审判而非所有审判,更不能适用于所有私人交易,46. 参见【美】马克·斯奈德著:《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位:避免陪审团误判的工具》,沈娜译,载《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第3 卷(2017 年),第102-116页。不应转化为一项强制性法律规范。47.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 773 F. 3d 1201, 1226-27(Fed. Cir. 2014).
斯奈德认为,SSPPU 原则更多是用来解决许可费堆叠问题,而非排除SSPPU 对产品整体带来的增量价值。斯奈德列举了种种反对SSPPU 实体规则化的理由,包括但不限于:(1)SSPPU 概念会将合理许可费的许可费基数限制在专利发明主要发挥作用的产品部件的成本价格内,这与分配过程要求的,以专利发明对终端产品产生的增量价值作为专利许可费的要求相左。48. See supra note,, 1226.(2)在有市场证据表明已经存在既定许可费的情况下,SSPPU 概念的强制适用可能排除此最优估价证据。49. See Monsanto Co. v. McFarling, 488 F. 3d 973, 979( Fed. Cir. 2007) .(3)在私人谈判中适用 SSPPU 概念需要组织单项专利谈判和单项产品部件谈判,这在涉及多项不同专利的交易中很难实现。(4)SSPPU 概念将导致实施者迫使 SEP 持有人签订低于市场许可费价格的协议,从而在根本上改写FRAND 许可原则,扼杀创新。50. 对干扰市场运行机制的担忧,又见前注41,Haris Tsilikas、胡盛涛文,第13-24页。
此外,有人认为,“在实际操作上,几乎所有产品都可以视为一堆组件构成的”,51. Richard Posner 法官语,See Jack Walters & Sons Corp. v. Morton Bldg., Inc., 737 F.2d 698, 703 (7th Cir. 1984).因此各层级的元器件几乎可以无限分解,以至于判断何谓“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并不如乍看之下那样简单。52. See J. Gregory Sidak, The Proper Royalty Base for Patent Damages, The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Vol.10(4):989, p.1019-20 (2014).因此SSPPU 尤其不适用于对复杂专利组合的侵权损害赔偿和合理许可费计算。53. 赵启杉:《标准必要专利合理许可费的司法确定问题研究》,载《知识产权》2017 年第7 期,第10-23页。而在经济上,SSPPU 无法反映发明对整个产品的贡献,而且专利价值从来就不是客观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用户的主观认知54. Layne-Farrar A & Padilla J & Schmalensee R., Pricing Patents for Licensing in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s: Making Sense of FRAND Commitments, Antitrust Law Journal, Vol.74(3):671, p. 675-676 (2007).——言下之意,若整体产品收取“愿打愿挨”的“主观”高价,专利权人亦有权分享。
(二)体系化思维对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研究之批判
1. SSPPU 原则反对意见的一些默认前提同为体系之变量而非常量
当反对者认为SSPPU 的(低)成本无法反映专利发明对终端产品产生的增量价值时,其默认前提是SSPPU(例如芯片)当前向终端产品制造商销售的价格较低,基本上取决于材料成本、人力成本和合理利润,无法涵盖充分合理的专利许可费。然而这一现状并非不可更改,现状的形成是由现行许可模式造成的(后文详述)。若以SSPPU 原则来考虑增量价值和许可费,则SSPPU 价格将上升,即包括专利许可费成本。
当反对者认为SSPPU 概念将导致实施者迫使SEP 持有人签订低于市场许可费价格的协议从而扼杀创新时,其默认的前提除了上面讨论的SSPPU 所谓低成本外,是认为形成既有许可协议的现有市场机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可能只是反映了专利权人希望把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谈判优势顺利嫁接到SEP 中的企图,其实际效果可能远超SEP 的价值。标准以及有关SEP 的FRAND 许可,正是为了解决而不是维持甚至恶化此问题。或者,如果说因为价值的主观性导致专利权人可对类似的终端产品收取或高或低的许可费,那么还能说许可费是来自专利的客观技术贡献吗?
2.许可费不能脱离权利要求及其创造性贡献:“最大保护单元”问题
EMV 原则意图把发明所惠及的终端产品作为许可费定价基础,相当于把专利保护的权利客体确定为终端产品而非发明方案所在的较底层部件——对应于专利中保护范围最大的权利要求。然而,无论是把劳动作为权利归属的依据,55. 同前注32,易继明、李春晖文,第137-138页。还是考虑专利法的功利性目标——激励创新,都意味着专利权人的(基于发明人的)权利源于且必然限于发明人的创造,因此,专利权人作为其收费基础的产品层级,应当是做出技术贡献的发明创造所在的产品层级。假如具有创造性的技术方案的所有技术特征存在于一个较小的部件中,那么,欲以比其更大的部件(或终端产品)为费基,则该部件应当包括除了该较小部件之外的额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换言之,合理的费基所涉及的,是有“最广泛”创造性(而不是最低程度创造性)的权利要求,其对应于“最大保护单元”。如此,则应将关于SSPPU 原则和EMV 原则的讨论,与权利要求的撰写、审查和解释联系起来。
3.体系化思维意味着SSPPU 原则本来并非单一而充分的标准
应当承认,即使在SSPPU 中,仍有可能并列存在多个同时实施(而非可相互替代)的专利权,仍存在许可费堆叠和专利劫持风险,且很难对每一专利的贡献一一拆分。但这并不等于SSPPU 原则是错误和不必要的。
首先,SSPPU 原则既包括对费基的纵向限制,也包括对费基的横向拆分,因此并不必然要求一个SSPPU 中只能有一个专利。在终端产品及其不同层级的零部件中,可以各自存在以该层级为最大保护单元的多个专利,尽管该多个专利之间需要避免许可费堆叠问题,但该多个专利各自或作为一个整体,仍须遵守SSPPU原则的纵向限制,其相应的许可费(份额)不能越过该层级而到达上一层级或甚至终端产品。
其次,SSPPU 原则并不必然意味着计算方法的刚性,相反,无论对哪种计算方法,都可认为SSPPU 原则是一种约束,或贯穿于每一种计算方法的理念。比如,对可比协议法,可考察各协议是否接近或背离SSPPU 原则,从而确定合理的“可比”协议;或者在SSPPU 原则指导下妥善地拆解既有许可协议。又如,在自上而下法中,如何解决武断而无根据地决定整体许可费率的问题,如何判定SEP 所有权份额的问题,56. 参见王亚岚:《从欧美案例分析判定FRAND 许可费率的最佳方法》,载《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研究》2021 年第1期,第275-295页。如何考虑专利与专利之间的价值差异问题,57. See J. Gregory Sidak, Judge Selna's Errors in TCL v. Ericsson Concerning Apportionment, Nondiscrimination, and Royalties Under the FRAND Contract, Criterion Journal on Innovation, Vol.4:101,p.158-161(2019) ; J. Gregory Sidak, The Meaning of FRAND, Part I: Royalties, J. Competition L. & Econ,Vol.9:931,p.1019-1020, 1049-1052 (2013); and Supra note 54, pp.682-683.均可且应当基于SSPPU 理念来予以适当调整。比如虽然在同一终端产品中,但各专利的创造性技术方案本来处于不同层级的部件中,层级则可能对权重产生影响。最后,在自下而上法(又称增量价值法)中,对增量价值的考虑可有不同选择:现有实践多考虑对终端产品的增量价值,而按照本文观点,只应考虑对SSPPU 的增量价值。换言之,SSPPU 的一切贡献,都应体现在其本身的定价中,进而令其足以作为许可费费基。
四、专利间接侵权问题与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的统一
(一)体系化研究的逻辑连接点:同一权利基础
在以上对专利间接侵权和专利许可费定价的体系化思维检视中,可发现在其他理由之外,二者各从不同方向涉及专利权利要求的“最小保护单元”和“最大保护单元”,从而均与权利要求有关。这正是对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和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共同进行体系化研究的理由和基础。两个议题各自的体系化研究将二者推向一个共同的体系化连接点,从而实现协同考虑二者的更广范围的体系化研究。
两个议题对权利要求的考虑是相反的:间接侵权理论将保护范围扩展到完整权利要求的不完整的局部,EMV 原则将许可费基础扩展到比权利要求(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技术方案)更高层级的部件或终端产品。换言之,专利间接侵权理论的争议是因为技术特征较少的最小保护单元未能成为独立权利要求,而SSPPU 原则与EMV 原则的争议,则是因为技术特征较多的保护单元并非独立权利要求,或者并非具有创造性的最小保护单元。
专利间接侵权问题与专利许可费定价问题在专利法理念和原则上是矛盾的:专利权人既需要通过缩小保护单元来获得大的保护范围,又需要通过提升保护单元层级来获得高的许可费。体系化思维要求我们必须把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下来考虑:同样的权利,不能在同一部法律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的行使场景,产生方向相反的解释。
以权利要求为中心,间接侵权问题和许可费定价问题的体系化思维涉及三个阶段:立法阶段涉及有关专利审查和保护的一些基本原则;权利的行政审批和确认阶段涉及对具体权利边界的划定,包括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则和专利局的审查标准两个方面;权利的行使和司法保护阶段涉及对权利边界的理解,这包括权利要求解释和侵权判定标准,以及许可费或侵权赔偿基础。基于体系化思维的一般要求,间接侵权问题和许可费定价问题的体系化思维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如前所述,无论是把劳动作为权利归属的依据,还是考虑专利法的功利性目标——激励创新,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则、专利局对权利要求的审查标准以及权利行使时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三者均须匹配于发明人的实际贡献。第二,基于专利权的法定权利属性,上述三个阶段的法律原则、制度和实践须自始至终协调一致,相互支持而非相互龃龉、抵消,予公众以稳定的预期,激励申请人守法。第三,基于具体权利实例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各个阶段内部和之间,都应遵循禁止反言原则。对此三方面,将在随后的展开中予以体现。
为方便论述,构造示例如下。独立权利要求具有n 个技术特征,间接侵权理论试图将仅仅实施其中m 个(m 1.(未写在权利要求中但在间接侵权理论中寻求保护的)一种零件A,包括特征1,特征2……特征m。 2.(真正的独立权利要求)一种部件B,包括特征1,特征2……特征m,特征m+1……特征n。 3.(可能没有权利要求但是被要求为费基的)一种集成C,包括权利要求1 所述的部件B,以及x 个有创造性贡献的附加技术特征。(隐含y1 个无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 4.(可能没有权利要求但是被要求为费基的)一种终端产品D,包括如权利要求2 所述的集成C。(隐含y2 个无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 间接侵权理论与EMV 原则的冲突在于,前者为了侵权判定的目的,意图把具有n 个创造性技术特征的部件B,降为仅具有m 个创造性技术特征的零件A;后者为了提高许可费费基的目的,意图把具有n 个创造性技术特征的部件B,提升为具有n+x 个创造性技术特征的集成C,甚至不再增加有创造性贡献技术特征的终端产品D。 基于体系化思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两方势力的拉扯之下,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如图1 所示,专利文件之权利要求所记载的保护范围应对应于专利产品中实际获得保护的单元层级,其由必要技术特征所决定的最小保护单元(保护范围最大)与发明之产业实施效果所决定的最大保护单元(费基价格更高)折中而得。折中过程要考虑权利范围的大小(技术特征的多少)对权利要求创造性的影响,以及对预期利益(包括对侵权判定的预期和对许可费的预期)的权衡。 图1 权利要求在保护范围和费基考虑之间的平衡 因此,基于申请阶段的意思自治,申请人须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选择恰当的保护层级,从而在得到较大保护范围的同时,还能获得较高的许可费预期。但必须遵守其与专利局通过“申请-审查”这个过程所建立起来的合意,禁止反言,不能在具体侵权行为或者许可发生时,意图降低保护单元层级来获得更大的保护范围,或提高保护单元层级来获得更高的许可费或侵权损害赔偿,更不能同时获得二者。尽管孤立地看,所谓间接侵权人所实施的技术方案确实也是发明人做出的贡献,其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或者终端产品的整体市场效益亦得益于发明的贡献。但从体系化思维出发,二者必须折中,折中点何在系由当事人选择,那么无论是基于权利法定原则,还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禁止反言原则,都应尊重行政授权和确权时所确定的权利边界。否则,就会鼓励权利要求撰写和审查授权的不严谨和许可费/侵权损害赔偿的随意性,破坏社会公众对权利边界的稳定预期,有悖于行政授权、确权制度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例如,若权利要求的撰写选择了集成层级C,则下位层级的部件B 和零件A 的生产制造便不存在侵权或间接侵权问题,专利权人也不能向A 和B 的生产商征收许可费。因此申请人/专利权人必须基于其对侵权判定标准和许可费费基的综合考虑,来要求保护折中的权利范围。或反之,如果专利权人为了更容易证立侵权而撰写了保护范围较大但是产品层级更低的零件权利要求A,则其只能针对独立的或存在于B或C 中的零件A 的销售和盈利主张许可费/侵权损害赔偿,而不能针对B 或者C 整体的销售或盈利来主张权利。 上述选择发生在申请与授权之时。那么,对已授权专利,平衡点就是申请人选择、专利局同意而授予的权利要求。因此,就间接侵权理论而言,本文的观点是,只应存在《民法典》下标准的专利共同侵权——其性质是共同直接侵权,而不应存在任何形式的间接侵权。这是因为,鉴于权利要求构成权利基础的功能,其权利客体界定功能不能有任何减损,因此就第二部分所述的情形1 而言,专利共同侵权人必须具有共同实施的意思联络,58. 同前注24,李春晖文,第1019页。构成共同过错,方能弥补帮助人单独来看并未实施权利要求全部技术特征的缺失,确立其连带责任;就情形2而言,若在特定场景下对全部技术特征的实施并不视为侵权行为,那么帮助人的部分实施行为完全是正当的回避设计。 就许可费费基而言,结论则是应遵循SSPPU 原则,且其应对应于具有创造性技术特征的最小可售单元,即最低可售产品层级。 在现有权利要求撰写和审查实践中,有一种申请人选择的“最优”情形:以最少的必要技术特征m,支撑最高层级的主题即终端产品D。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不需要因为权利要求有n 个技术特征而主张m 个技术特征的间接侵权,但可基于最高层级的主题D 来主张许可费和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上,权利人此时也不应该主张包括m 个技术特征的主题A、B 和C 侵权,但权利人可通过许可模式的策略来解决此问题。 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同一专利中,同时包括具有m 个必要技术特征的主题A、B、C、D,这就是最完美的匹配:既无无法制止间接侵权的担忧,又能解决费基问题。这种情形可比喻为俄罗斯套娃,是当前各国实践通常都允许的。例如,只要芯片级的权利要求具有创造性,那么包括该芯片的部件、该部件的集成、该集成的设备、该设备的系统,均具有创造性而能够被授权。这种专利撰写和审查实践给专利权人以何种层级的权利要求和产品的何种层级的部件来主张许可费或侵权赔偿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往往核心的创新只是最底层的权利要求,即最小保护单元A 的具有最少技术特征m 的独立权利要求。 这是不合理的。许可费费基应系发明人之贡献所在,应对于作出技术贡献也就是具有创造性的权利要求,而不能是超出权利要求主题的更宏观单元。在假设的例子中,发明人并未对B、C、D 的技术方案除A 之外的其他部分做出创造性贡献,因此其权利应仅限于主题A。事实上,任何发明都会对所有下游产业链甚至国民经济产生影响,不能因此让专利权人的权利和利益主张无远弗届。从另一角度看,若说主题A 的创新对例如主题C 的贡献确实非常可观的话,可从两个方向加以考察:第一,主题C 中是否存在产生所述贡献的、与主题A 的技术特征匹配或者不匹配的其他x 技术特征,也就是说A 或B 之外的x 个技术特征做出了额外的创造性贡献;第二,假如没有这样的技术特征,那么对主题C 的贡献仍然是主题A 之效益的体现,应当在主题A 的费基中加以体现。 因此,应当对不恰当拔高主题层级的行为予以规制。无论权利要求中是否明确包括了主题A,对于更高层级的主题B、C 或D 的权利要求,应考察其主题是否过大,是否匹配于做出创造性贡献的m 个技术特征,即权利要求应限于最小保护单元。如果主题B 或者C 有额外的技术效果,则应当在其权利要求中体现出不在主题A 之内但是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相应地,在许可或者侵权纠纷中,如果某个层级的权利要求要作为费基的话,应当考察其相对于包括必要技术特征的最小保护单元是否具有额外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的审查及其作为诉讼或许可之权利基础的情形可作类似考虑。实际上,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计算权利要求超项费用时),俄罗斯套娃式的权利要求即便形式上是独立权利要求,但也会视作从属权利要求。 当然,是否对所有俄罗斯套娃式的权利要求和所有从属权利要求进行额外创造性的审查,还存在制度成本问题(权利要求超项费可视为一种制度上的遏制),本文不详细讨论。但是,即便不在专利审查阶段解决,也应在专利确权、侵权诉讼和许可费确定中对此予以考虑,从而反馈到申请人的撰写实践中。例如,可在需求产生时,请求专利局或独立机构对不同层级权利要求之技术特征的额外创造性贡献做出评估,或由法院直接审理判断。 反对SSPPU 原则的理由,很多是现有许可模式造成的。比如高通公司纵横江湖,其基本许可模式就是“芯片+专利”,即在芯片销售之外再次向客户授权其专利技术。其销售的芯片可能是其自身或者在其控制下生产,或者其他厂商生产——严格来说,高通并不销售这些芯片,而是允许这些芯片的销售,但向这些芯片厂商的客户——整机生产商,收取专利许可费。高通收取的专利许可费包括固定费(license fees)和提成(royalties)两部分,后者按照整机产品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3%—5%)收取,被业内称为“高通税”。 最主要的反对理由,即基于SSPPU 成本价格的许可费无法反映专利发明对终端产品的增量价值,即因上述许可模式造成:许可费系向整机生产商收取,SSPPU 价格自然不必计入知识产权成本。显然,如果基于SSPPU 价格确定许可费且向芯片制造商收取许可费,则SSPPU之价格显然就会把许可费考虑在内,而不必是“成本价格”。59. 赵军、张建肖:《通信行业FRAND 原则实现困境及其解决》,载《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 年第10 期,第13-17页。 这一许可模式还有其他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好处据称是专利权人可避免“付出更大的成本去发现和监督最小可销售单元的价格和利润信息”。60. 朱理:《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分摊原则的经济分析》,载《现代法学》2017 年第5 期,第58页。然而,所谓“终端产品的制造者可能将被迫接受就每个专利或者最小可销售单元分别进行谈判,专利许可的交易成本将可能大幅增加”61. 同前注60,朱理文,第58页。的说法,则涉及权利用尽问题。显然SSPPU 原则并不必然要求专利权人就每一个专利单独与实施者(可能是部件生产商也可能是终端产品制造商)谈判,他们当然也可以一揽子谈判,问题只是SSPPU 原则应当成为一种指导性理念,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权利人已与部件生产商解决了专利问题的话,则基于权利用尽原则,终端产品制造商完全可以放心使用采购的部件,不必考虑专利许可谈判问题,从而降低而不是升高交易成本。因此,问题的实质是,现有许可模式不过是方便了权利人而已。然而,专利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整个制度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因此并没有可靠的法律或者道德前提要求必须一味地亲专利权利人,相反,面对专利丛林,终端产品制造商的守法便利性也非常重要,这种便利性也涉及终端产品制造的市场后入者所面对的专利丛林壁垒高低。 此模式的关键,在于权利人(如高通)越过零部件生产商(自己或他人),即不认为自己或其他零部件生产商在实施专利,否则终端产品制造商就可受权利用尽原则的保护。这实际上是权利人对权利用尽原则的规避,相当于重复地向不同层次的制造商发放许可。 事实上,权利人自己生产也是对专利的实施,其产品的销售构成权利用尽,不应再向产品的购买者收取专利许可费(权利用尽范围包括与产品权利要求实质上等同的方法权利要求,不赘述)。对于他人生产零部件但是权利人向终端产品制造商收取许可费的模式,同样不符合权利用尽原则。一方面,终端产品制造商可以主张产品合理来源;另一方面,专利权人明知零部件生产商的存在而不主张许可费,应视为默认的免费许可,构成权利用尽。因此,权利用尽原则应将基于相同的创造性技术特征的不同层级的部件或者产品A、B、C、D 视为同一权利(这也符合专利申请的单一性原则),即:即使专利权人拥有多个层级的权利要求,其也只能就其中一个层级向相应的主体主张权利,不能重复收费62. 参见黄武双、谭宇航:《物联网背景下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层级的选择》,载《知识产权》2022 年第9 期,第25-52页。(除非如前一小节所述不同层级上具有额外的创造性贡献),而且按照权利用尽原则,许可对象只能是SSPPU生产商,63. 参见前注59,赵军、张建肖文,第13-17页。而不能是产业链下游主体。 可见,不仅在间接侵权问题内部和许可费问题内部分别存在体系化思维的问题,而且两个议题之间也是相互矛盾和制约的,体系化的思维能够为反对间接侵权理论和支持SSPPU 原则提供更强理论支撑。如此,专利权利要求的撰写、审查,以及专利权人对权利的主张——向产业链中的什么主体主张权利以及基于什么层级的主题主张许可费或侵权损害赔偿,即统一于一以贯之的原则之下,从申请人、权利人到社会公众和实施行为人,皆可对各方行为有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效率。(二)两个议题在获权确权与专利权行使原则规则上的均衡

五、基于体系化思维改革专利立法与实践
(一)权利要求撰写规则和审查标准的改革
(二)对专利许可模式的规制和权利用尽原则的优化
六、结语
——基于美国法院的几个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