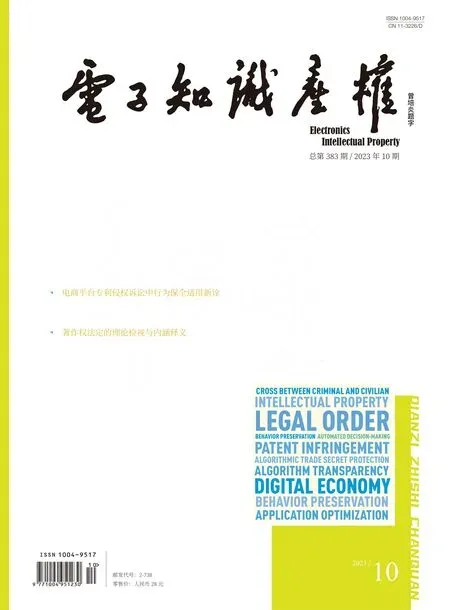著作权法定的理论检视与内涵释义
文 / 孙松
一、问题的提出
在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所谓的“著作权法定”或者说“著作权法定原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一方面,支持“著作权法定”的学者认为,基于著作权作为绝对权的属性,作品类型法定应是著作权法定的应有之义;1. 参见王迁:《论作品类型法定——兼评“音乐喷泉案”》,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3 期,第11-12页。作品类型、权利内容的兜底条款既无必要的立法权力基础,也无必要的正当性。2. 参见刘银良:《著作权兜底条款的是非与选择》,载《法学》2019 年第11 期,第127-128页。另一方面,有学者则认为“作品类型法定”没有正当性,不符合著作权法的宗旨;3. 参见李琛:《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8 期,第3-7页;卢海君:《“作品类型法定原则”批判》,载《社会科学》2020 年第9 期,第95-103页。著作权权利内容的兜底条款,说明我国在著作权领域并未恪守权利法定的传统;而权利内容兜底条款的设置,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有其相应的法哲学基础。4. 参见熊琦:《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悖论调和》,载《政法论坛》2017 年第3 期,第83-84页;参见李琛:《论“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载《知识产权》2022 年第6 期,第29页。由此可见,如何界定和看待“著作权法定”的内涵和地位,不仅关乎著作权法律规范的科学配置,而且影响著作权法律规范的有效适用。然而,何为“著作权法定”,学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认知和原则共识。
事实上,关于“著作权法定”的相关争议,可追溯至21 世纪初国内学界对于“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或曰“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争论。5. 相关代表性论述,可参见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郑胜利主编:《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51-66页;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应用》,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第110-125页;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第3-16页。然而,与当时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争论不同的是,当下“著作权法定”的争论,俨然已超出知识产权权利来源属性的内在争论,而升级成为“著作权法定”对于著作权法律构造和法官释法的重要影响。对此,有学者援引民法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权利法定原则中的“权利”仅为绝对权,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保护的,是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6. 孙山:《重释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载《当代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60页。然而,上述阐释虽保全了所谓“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既有逻辑,却回避了知识产权扩张与限制过程中立法和司法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无论是通过类比“物权法定原则”得出的“著作权法定”,还是通过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所得出的“著作权法定”具有约束立法和司法行为的特定内涵,都存在着解释力不足和回应性欠缺的现实困境。进言之,在我国著作权法的文本语境下,“著作权法定”的理论观点既无法弥合其与立法原意之间的割裂,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立法技术的现实存在,以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职责担当。鉴于此,考察“著作权法定”的理论内涵和地位问题,进而回应上述现实争议,一是需要借助“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分析,梳理物权与著作权制度在规范设置和制度适用上的差异性,进而回应“著作权法定”类比“物权法定原则”的理论争议;二是需要依托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回溯,求证著作权制度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规律,进而得出“著作权法定”的内涵新解。
二、物权法定原则与著作权法定的类比检视
按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 条。由此可见,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有着明确的立法表达。然而,所谓的“著作权法定”却没有法律文本上的规范依据。因此,类比物权法定原则而得出的“著作权法定”,存在着立法依据上的先天不足。当然,上述论断并不是说物权与著作权法律制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而是意在说明“著作权法定”的内涵认知,需要基于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自身特点,而不是与物权制度亦步亦趋。基于此,需要解答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物权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以廓清“物权法定原则”与“著作权法定”类比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著作权法定”类比结果的论证问题,以回答上述“著作权法定”判断的合理性问题。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解读
我国学界对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认知,存有一定的理论争议。正如有学者所言,即使在物权法定的语境下,围绕是否法定、“法”的范围、法定对象以及如何法定的争议仍不绝于耳。8. 夏沁:《论私法自治中物上之债对物权法定适用的缓和》,载《清华法学》2021 年第6 期,第132页。更不用说,在“物权法定原则”之外,还有学者主张“物权法定缓和”方案,甚至提出“物权自由”方案。9. 相关代表性论述,可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 年第1 期,第1-42页;张永健:《再访物权法定与自由之争议》,载《交大法学》2014 年第2 期,第119-135页;杨立新:《民法分则物权编应当规定物权法定缓和原则》,载《清华法学》2017 年第2 期,第14-27页。当然,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支撑物债二分架构的基础性机制,10. 张鹏:《物债二分体系下的物权法定》,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6 期,第67页。有着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财产交易的功能价值。在上述目标功能的背景下,物权法定原则包括权利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并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有待进一步澄清的是,物权法定原则是否限制法官造法,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对此,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在学说原发国,还是在继受国,物权类型封闭原则都仅仅是限制当事人的私法自治,而不限制法官造法。11. 黄泷一:《物权法定原则:普遍理论与中国选择》,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6页。可以说,法官适用法律,并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裁判自由,既是法律适用的需要,也是法官职责的担当。一方面,“法官应该是制定法的奴隶”的观念早在19 世纪已被动摇,代之而起的是在合乎制定法原则的基础上,法官享有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的自由,尤其是在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裁量条款、一般条款等制定法表达形式上。12. 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0-132页。另一方面,允许法官造法既来自法治国家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也源于法律中存在的漏洞。13. 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388页;【德】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第6 版),蒋毅、季红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8-140页。更何况,制定法不可避免地“有漏洞”,法院填补制定法漏洞的权限也被承认已久。14.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6 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 年版,第460页。由此可见,在物权法定原则下,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法官造法,不仅可以消解物权法定原则本身所存在的封闭性,而且可以发挥法官在漏洞填补上的积极价值。实际上,即使在物权法定原则的语境中,物权制度也通过地役权这一法定的兜底条款或制度的设立,来保证当事人设定权利内容的较大空间。15. 参见张鹤:《我国物权法定原则与地役权:宏观法定与微观意定之融合》,载《法学杂志》2007 年第6 期,第46页。此外,伴随着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的纷至沓来,诸如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准物权或者说新兴权益的出现,还会使得制定法所存在的“嗣后漏洞”更加明显,进而更加需要法官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中发挥出相应的能动性。鉴于此,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认知,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不宜扩张解释为对法官造法的限制;二是其在权利种类和内容上的闭合,也不宜理解为完全排斥兜底条款的规范存在。
(二)“著作权法定”观点的类比检视
根据前文有关“著作权法定”的理论争议,可以发现上述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物权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属性的类比参照。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著作权与物权同为财产权的基本逻辑;二是著作权与物权皆表现出绝对权的权利属性。然而,两者在呈现上述制度关联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无体财产权与有体财产权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相应的制度规范在反映绝对权属性上的形式区别。
首先,著作权与物权同为财产权序列的制度关联,无法支撑上述“著作权法定”的类比结论。在物债二分的体系结构下,传统物权制度遵循“物必有体”的权利客体理念。然而,著作权乃至知识产权的法律建构,却是“知识的财产化”和“财产的非物质化”的变革结果。16. 参见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第125-128页。具体而言,物权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是在“先占”的基础上,依托于“有体物”的形式概念分类,来实现物权种类和内容的类型化构建。然而,从著作权制度的起源来看,其却是建立在远离以原稿为载体的物质性基础,进而实现“以作者创作的作品”为受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构建。17. 参见【美】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74-81页。申言之,物权制度的确立,是将“无体物”隔离在物权客体的形式概念之外,进而围绕先行存在的“物”,实现产权界定、归属、利用和保护等内容的制度架构;而著作权的生成和扩张,则是建立在脱离“所有权”的概念束缚,进而通过拟制的“作品”概念,以及“作品”的利用方式,来确立著作权的产权地位和制度体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著作权在融入财产权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得益于借用物权制度的相关概念。但是,随着现代著作权制度的确立,尤其是著作权的不断扩张,两者却越发呈现渐行渐远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在著作权的权利扩张过程中,如何在权利人、使用者和社会公众这一特殊的权利主体结构中,维系著作权制度的利益平衡,已经成为现代著作权制度在确立财产权地位之后,又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知识产权权利结构中使用者的特殊介入,使其与其他财产权相比,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即如何处理好面对使用者时权利行使与权利保护的问题。18. 张凇纶:《财产法哲学:历史、现状与未来》,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256-258页。进言之,由于著作权主体结构的特殊性,著作权法在权利扩张和限制的动态化过程中,需要及时根据作品利用方式的变化,通过著作权的权利内容、许可机制和限制制度灵活调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纵使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也不宜直接类比得出“著作权法定”的论断。事实上,即使认可“物权法定原则”的学者,也断定“物权法定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可能是最弱的,且法官造法在塑造新的知识产权利益方面是应该受到认可的。19. Thomas W. Merrill & Henry E. Smith,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110 YALE L.J.1,p.19(2000).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著作权权利边界的划定,无不随着商业模式的更迭、作品利用方式的创新,呈现出权利扩张和限制因应的动态化发展趋势。换言之,权利人通过著作权的扩张,正是出于克服著作财产权类型化不足的目的。20. 参见熊琦:《著作权激励机制的法律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74-75页。更何况,由于著作权许可和转让的实现,主要依托于合同形式,而不涉及有形客体“占有”的权利范围确认。因此,一定程度上的权利行使自由,既契合著作权人私人自治的私法理念,也符合著作权交易效率的市场逻辑。正如有学者所言,知识产权的类型化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而支撑其类型化或法定化的论证理由,如促进信息传播和限制司法裁量,都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不算成功的。21. 张凇纶:《财产法哲学:历史、现状与未来》,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262-267页。综上所述,著作权法在制度生成、权利结构等方面的特殊性,很难使其得出“著作权法定”的类比结论。
其次,著作权与物权皆带有绝对权的属性,也无法证成上述“著作权法定”的类比结论。就权利的效力而言,所谓“权利法定”的判断,实则取道于权利的绝对权属性。具体来说,物权的特点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和绝对的对抗力。22. 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页。然而,与物权不同的是,著作权在权利属性和效力层面,却不具有物权那样圆满的支配性和对抗力。作为无体动产而存在的知识产权,实质上是法律永久性的或在一定期限内进行保护的一种独占权。23. 【英】劳森、拉登:《财产法》(第二版),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1页。借用亚当·斯密在其《法理学讲义》中对独占权的阐释,对独占权的侵犯是指一个人追逐并侵占了别人侦察和追踪的船,而非在他人先占的基础上,对船主所有权的侵犯。24. 参见【英】亚当·斯密:《法理学讲义》,冯玉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10-112页。进言之,尽管独占权的享有,也表现出一定的支配性、排他性和对抗力,但其与物权所呈现出来的绝对权效力,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事实上,国内多数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描述为“专有性”,25.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21-23页;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7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7-9页。而非“直接支配和排他权利”,即认识到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属性和效力层面的重要区别。正如有学者所言,知识产权强调其在成为产权后在法律上获得的排他性,而并不要求具有事实上的排他性。26. 参见文禹衡:《数据产权的私法构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9页。申言之,著作权作为法定权利,虽然有着法律赋予的独占权或者说垄断权特征,但其在权利来源、权利行使等方面却有着相对势均力敌的法律限制。如果版权人的权利超出了排他性的版权内容,并成为一项绝对财产(自然法)权利,则版权制度将会抑制知识的传播,因为财产的实质是排他的。27. L. Ray Patterson ,Understanding the Copyright Clause, 47J.COPYRIGHT Soc'y U.S.A.365,p.369 (2000).换言之,著作权法应当从自然法的神坛,走入实证法的俗境,其价值原则应当从绝对权利走向灵活的利益结构。28. 付继存:《著作权法的价值构造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年版,第65页。鉴于此,著作权的权利属性,不宜赋予“绝对权法定”的效力,否则将会破坏著作权法律制度所建构起的利益平衡。
一方面,就权利属性的分类而言,绝对权是相对于相对权而言的,绝对权的效力所及之范围在于一切人,而相对权的效力所及之范围在于特定人。29. 金可可:《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 年第11 期,第137页。然而,著作权的历史脉络和政策目标表明,其是一项由专门职业者享有,并针对其他专门职业者行使的权利。30. Daniel J. Gervais, Towards a New Cor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Norm: The Reverse Three-Step Test,9MARQ.INTELL.PROP.L.REV.1,p.7(2005).质言之,在著作权制度利益平衡的理念下,著作权的效力范围,难言是针对“一切人”,还是“特定人”。另一方面,仅从权利的定分性质,并不能导出物权法定的必要,甚者具体到知识产权的层面,还可以认为权利人享有某种“次类型”的形成自由。31. 参见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 年第1 期,第15页。事实上,除物权、知识产权之外,人格权亦具有绝对权的属性,但其权利边界却不存在类似于“物权种类和内容法定”的闭合式特征。可以说,无论是物权法定的导出,还是权利法定的确立,必须契合所涉财产权制度本身的立法目的。质言之,就著作权制度的立法目的而言,客体类型、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的法定性和闭合性,将不利于著作权制度更好地激励创作和促进传播。综上所述,就权利属性的内在差异而言,著作权法律制度也不宜得出所谓“著作权法定”的结论。
三、著作权法定的内涵新解
抛开著作权正当性论证的学理基础,著作权是为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已成学界共识。事实上,上述结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18 世纪“唐纳森诉贝克特”一案,即英国上议院法官在那时就否认了永久的普通法版权的继续存在,并认为版权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其保护期限也是受限制的。32. Donaldson v. Beckett,2Brown's Parl.Cases129,(1774).然而,“法定权利”,与上述所谓的“权利法定”,却不能简单地等同视之。“法定权利”意在说明著作权的权利来源和属性,而“权利法定”意在强调权利种类和内容等方面的类型化或闭合性。质言之,著作权是为法定之权,但不宜将“物权法定原则”强加于著作权法律制度,进而形成“作品类型法定、权利内容法定和权利限制法定”等认知。正如有学者所言,物权法定原则几乎缺席于知识产权法,因为知识产权的享有和转让不受形式上的限制。33. Christina Mulligan, A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80 TENN.L. REV. 235,p.249 (2013).基于此,关于著作权法定的内涵新解,应解读为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不宜采取“权利法定”的“物权化思维”;二是不该排斥“兜底条款”的规范设置;三是不应限制一定范围内的法官造法。
(一)不宜采取“权利法定”的“物权化思维”
著作财产权观念的确立,源于文学产权与载体物所有权的脱离;著作财产权制度的构建,得益于对物权制度概念和结构的类比借鉴。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著作权与物权的内在差异,著作权制度的发展不必囿于传统财产权制度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言,知识财产之上的多种权利形态与多重主体设定,使得传统的财产权理论与规则捉襟见肘,在私法领域中,知识财产理应建构与有形财产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34. 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4 期,第127页。由此可见,在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的当下,继续类比借鉴传统财产权制度所沿用的概念术语和结构理念,不仅将会有碍作品利用方式的技术发展,也会束缚著作权制度的规则创新。换言之,著作权制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类比借用传统财产权相关概念、结构的制度成长期,进入了网络时代著作权理论沉淀与制度发展的成熟期。鉴于此,著作权制度的法律构造,应突破物权制度所恪守的“权利法定”的“物权化思维”,来充分保障著作权人的私人自治。一方面,与物权作为自用型财产权不同的是,知识产权主要是交易型财产权。35. 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版,第48页。就著作权的权利行使和利用而言,其无需恪守“物权法定原则”这样的财产权规则。著作权权利内容的享有和扩张,带有浓厚的私人自治色彩和市场化运作逻辑。例如,被当下视为重要著作财产权之一的公开表演权,曾被认为只是一种创造需求的方法和促进实体乐谱销售的手段。36. Kevin Parks:Music & Copyright in America: Toward the Celestial Jukebox,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ress,2012,P.40.质言之,著作权法“以用设权”的路径,不宜采取权利内容封闭的“物权化思维”。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著作权许可效率与传播效率的脱节,以及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法律认可,也使得权利人在法定安排之外采取了更多的私人创制规则和救济方式。质言之,无论是依托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而私人创制的集中许可方式,还是秉承信息自由传播而私人创制的公共许可方式,以及通过合同形式而自力救济的技术保护措施,都表明上述所谓的“物权化思维”,将与著作权人的私人自治呈现出格格不入的局面。鉴于此,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不宜继续沿用“权利法定”的“物权化思维”。
(二)不该排斥“兜底条款”的规范设置
承前所述,即使在物权法定的制度设计中,亦存在“地役权”这一法定兜底条款或制度的创设形式。无独有偶,即便在刑法领域,兜底条款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且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强大的堵截法律漏洞的功能。37. 马东丽:《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279页。因此,在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更没有理由去排斥“兜底条款”的规范设置。就本质而言,兜底条款的存在,是立法技术的集中展现。正如有学者所言,兜底条款是立法者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理性后采取的一种积极技术措施。38. 李雨峰:《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造法——司法能动的可能及限度》,载《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2011 年12 月26 日,第1208页。由此可见,“兜底条款”的法律设置本身并不存在立法上的禁忌,反而颇具现实意义和价值。基于此,著作权法没有理由排斥“兜底条款”的设置。第一,采取作品类型的开放模式,是作为“技术之子”的著作权制度的基因体现,其既契合著作权制度激励创作的内在目标,也无损于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领域对于作品创作的文化涵养。此外,与物权客体不同的是,“有体物”的概念可以周延地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等不同类别,而著作权的客体概念“作品”,则不仅无法涵盖邻接权的客体样态,更无法周延地做出“作品类型”的细分。因此,通过“兜底条款”的形式,发挥作品类型开放的功能模式,既是立法技巧的呈现,也是立法价值的遵循。更何况,立法中的作品类型是例示性而非限定性的,在知识产权法教义中已成共识。39. 李琛:《论作品类型化的法律意义》,载《知识产权》2018 年第8 期,第5页。第二,与物权不同的是,著作权的权利内容主要依据作品的利用方式,采取“以用设权”的路径来调适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而不能像物权那样可以通过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形态,预先实现较为稳定的制度安排。进言之,著作权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确认和划分财产的范围。故与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比,著作权法常常被新的对象种类抓住。40. 【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英国的历程(1760-1911)》,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9页。鉴于此,在“以用设权”的路径依赖下,为避免法律规定的列举不全,立法者难免采用“兜底条款”的立法技术,以求权利内容的开放。41. 参见黄薇、王雷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 年版,第98-99页。此外,从相关的司法实践来看,倘若权利内容的法定安排不足以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诉求,还将会增加技术保护措施等私立规则的适用,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援引。因此,权利内容“兜底条款”的存在,不仅符合著作权法的目标价值和形式意义,也有利于将著作权纠纷化解于著作权制度的法定安排之中。第三,就著作权限制制度而言,其边界和范围也不该采取“权利法定”的闭合式安排。一方面,著作权的扩张和限制,是一个调和不同时期各主体利益分配的动态化过程。例如,在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权利限制的内容范围和程度远远超出物权法律制度中零星的权利限制规则。另一方面,无论是著作权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等内部限制制度的界定,还是合理使用等外部限制制度的适用,无不都在灵活地发挥着框定权利边界的规范功能,而非以恒定或封闭式的规则安排为相应的设计理念。
(三)不应限制一定范围内的法官造法
诚然,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司法活动需要严格接受立法的制约,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不能脱离法律,任意解释法律,进行“法官立法”。不过,与“法官立法”截然不同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法官造法或者说在立法授权下的法官释法,不仅具有法治现代化上的理论基础,而且存在法学方法论上的适用依据。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官造法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法的正义功能。42.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3页。法官面对具体的司法案件,理应在实现矫正正义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裁量自由。另一方面,法官造法的适用性前提和价值,在于制定法存在漏洞,而法官造法则可以弥补制定法的漏洞。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法官就相关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在立法授权的维度下正当进行法律适用的司法裁判活动。进言之,著作权制度因应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更迭的逻辑规律,已经使得法官在法律授权下予以相应的造法行为成为制度适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然而,较为吊诡的是,在法学方法论和传统财产权制度层面已被认可的法官造法行为,却曾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即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只能由特别法创设,反对法官在特别法之外行使自由裁量权创设知识产权;而坚持劳动基础上的知识产权自然权利观念的学者认为,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在知识产权特别法之外创设知识产权。43. 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第3-4页。事实上,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推不出应当反对司法能动,限制法官造法的结论。44. 应振芳:《司法能动、法官造法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7 期,第56页。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宁愿选择不造法,因为其带有很大的裁判风险。45. 李雨峰:《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造法——司法能动的可能及限度》,载《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2011 年12 月26 日,第1211页。质言之,对于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出现的裁判错误,不宜过度发展为对法官造法的本身恐惧和意义否定。当然,值得说明的是,法官也不得随心所欲地宣告他所喜欢的规则。46.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59页。鉴于此,“著作权法定”的内涵,不应解读为限制法官在一定范围内的造法行为。
四、结语
“著作权法定”的内涵澄清,关乎立法规范与司法适用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作为所谓的“著作权法定”参照物的“物权法定原则”,并不排斥兜底条款的立法设置,以及法官造法的司法适用。换言之,所谓“著作权法定”的论断,缺乏来自同为财产权和绝对权的物权法律制度的类比基础。另一方面,基于著作权在制度生成、权利结构、权利属性上的特殊性,更不宜得出所谓“著作权法定”的结论。因此,在著作权的法律构造中,法定权利的基本属性与兜底条款的立法表达,是能够和谐共存的。当然,值得说明的是,厘清著作权与物权之间的制度差异性,并非隔绝著作权与物权之间的制度关联,而是意在打破著作权领域中“物权化思维”的束缚,进而更好促进数字时代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创新发展。基于此,“著作权法定”的合理解释应理解为法定权利的来源之义,而不是权利类型、权利内容和权利限制的类型法定和体系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