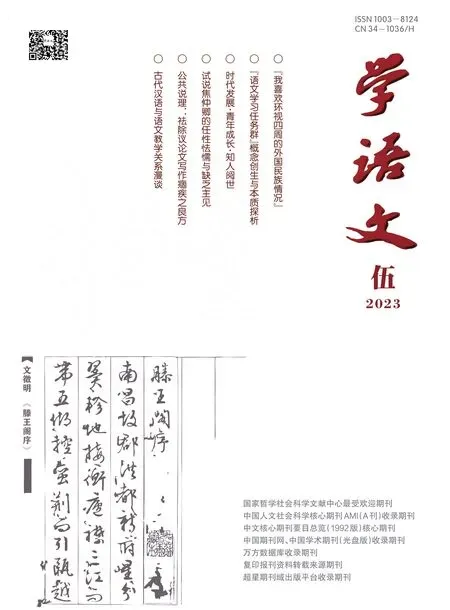试说焦仲卿的任性怯懦与缺乏主见
□ 赵文建
汉乐府著名长诗《孔雀东南飞》,一般人都认为封建家长焦母和刘兄联手制造了一场婚姻爱情悲剧。后人在为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婚姻悲剧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指出了焦仲卿缺乏主见,在《孔雀东南飞》故事故地,现在的安徽怀宁、潜山一带,据说焦仲卿老家的人依旧把缺乏主见的男人呼作“焦二”,“焦二”就是焦仲卿。如果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化解家庭内部矛盾摩擦的角度,审视焦仲卿作为一家之主所该有的主见与担当,就可以发现焦仲卿面对家庭琐事冲动任性,激化婆媳矛盾,坚定了焦母逼走媳妇刘兰芝的决心;刘兰芝被遣回娘家,焦仲卿缺乏主动挽救的主见与作为,怯懦回避矛盾,放任事态滑向悲剧深渊。可以说焦仲卿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促发人。
一、任性倔强,激化矛盾
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往往是遇有大事男性当家做主,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作是对女性的压制,其实有内部的根本原因存在。因为性别天性的差异,女性一般比较感性,遇事往往容易情绪化,处理问题失之周全;男性相对比较理性,遇事能够忍得住,冷静理智地周全应对。至今在生活中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人家突然遇上大事,女人们大多是鼻涕眼泪一把抓,六神无主,只会哭,倒是男人们在旁边沉着气,冷静地商量应对。从全诗来看,焦家母子堂上争吵、焦仲卿休妻与自杀,焦家经历如此变故,焦父一直没有现身,显然焦父应该已经不在人世。父亲不在人世,已经成婚二三年的焦仲卿,在家中应该当仁不让地是一家之主的角色了,负有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化解家庭内部矛盾摩擦的责任。一边是寡居的生身之母,一边是挚爱的枕边娇妻,夹在中间的焦仲卿确实难做人。他需要用智慧,既要做黏胶,黏住她们,不能让她俩离散,又要夹在中间两面周旋,做润滑剂和减震器,不让她们直接相对抗,恶化关系。焦仲卿作为府吏,“守节情不离”,平常多在外少在家,与家人“相见常日稀”,不仅焦家婆媳之间磨合磕碰缺少润滑剂,焦仲卿也缺少化解婆媳隔阂的切实历练,缺乏左右逢源的机智。焦仲卿难得休假在家,刘兰芝向丈夫倾诉“君家妇难为”,请求“及时相遣归”。这本是小两口私房话,人之常情,借诉苦抱怨撒娇,讨要丈夫的抚慰疼爱。作为既是丈夫又是儿子的焦仲卿,在听了妻子一面之词的诉苦抱怨之后,不是一面先柔情入微地去理解安抚妻子受累受伤的心,求她从长计议,暂时忍耐性子委屈自己;一面再私下找个机会,心平气和并巧于策略地询问母亲个中缘由,窥察矛盾症结所在,寻求化解的策略,并柔言宽慰母亲消除心头的怨气,引导母亲放大器量,看在儿子长期在外,媳妇劳作持家、代儿尽孝、含辛茹苦的份上,包容谅解媳妇。焦仲卿却是“堂上启阿母”,直接在家庭堂屋这处庄严尊贵、本该是子女接受父母训教的场合责问母亲。这一般是在外饱受压制,回家仍不得耳根清净,情绪冲动的人典型的任性过激表现:遇事不经大脑掂量轻重利弊,不看场合对象,不考虑有无必要,心气急躁,不计方式,不顾后果,一味地由着性子来。
高堂之上,母子俩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第一回合,焦母本就已经厌恶刘兰芝,焦仲卿不揣摩母亲的心意,直接自己躺平“薄禄相”,反夸刘兰芝“幸复得此妇”,发誓“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责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似乎要替刘兰芝讨还公道。面对儿子任性暴躁,所幸焦母还算冷静,一面教育儿子做人格局太小,一面说自己早就不能容忍刘兰芝处处自作主张,深怕儿子会闹,还安抚儿子要替他讨邻家美女秦罗敷做媳妇,劝儿子赶紧将刘兰芝送走。第二回合,焦仲卿“长跪告”:“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不陈情不说理直接犯倔,顶回去把话说绝。招惹得焦母槌床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也把话说绝。
老话说“哪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性误会与矛盾摩擦,在所难免,很多情况下很难也没必要分出个谁对与谁错,非穷究出一番冷冰冰的道理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主要靠相互体谅包容与忍耐沟通,用暖暖的温情来化解。如此,则彼此说话的场合、方式、态度和声气就成为消除隔阂、化解矛盾或激化矛盾的最为重要的关键。焦仲卿明知焦母心中有气,却简单粗暴,不知进退,针锋相对一句不让,态度倔强,尽挑焦母不乐意听的话说,屡犯焦母忌讳。在焦母来看俨然就是偏袒媳妇,上门问罪,忤逆不孝,怎能不伤心至极而勃然震怒。在一般生活方面焦仲卿任性犯倔,对焦母来说,可以忍耐迁就,但现在焦仲卿竟然站在媳妇一边,粗暴地偏袒媳妇,公开与自己叫板为敌,这让与儿子相依为命,把儿子作为自己唯一生存支柱的寡妇焦母,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她必须铁了心逼迫儿子休妻,赶走媳妇,因为媳妇刘兰芝破坏了他们母子关系,刘兰芝的存在已经危及焦母余生的幸福。如此结局,焦仲卿不仅没有发现家庭问题的症结,消除误会隔阂,化解婆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催发戾气,并且还把自己搅进去,造成母子直接对立对抗,把寻常家务摩擦搅得没有转圜的余地。
二、任性与怯懦的由来
焦仲卿遇事如此不能冷静练达,任性暴躁,其实是其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造就的。既然焦父不在人世,除媳妇刘兰芝以外,寡母带着一双儿女生活,三口之家,在当时社会,境况有点凄凉。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考证,汉代结婚年龄一般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1]17-18。刘兰芝明确说自己“十七为君妇”。同为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秦罗敷夸说自己丈夫的出仕履历时说“十五府小吏”,焦仲卿在庐江郡府衙做小吏,他自诉与刘兰芝成婚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由此可以推知离异时刘兰芝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上下,焦仲卿的年龄应该与妻子相仿。可见焦仲卿与刘兰芝成婚的这几年,焦仲卿可能还处在他人生成长中的心理断乳期,思想上急于自主独立,总觉得对父母的依从是一种压力和束缚,父母的过多关爱可能招致焦仲卿激烈反抗的表示。传统社会从来都是母以子贵,一般情况下,母亲对独子都比较娇宠,而丈夫不在人世的单亲寡母尤甚。不讲规矩,百依百顺,事事哄着他,因为儿子成了她此生唯一的靠养与指望,深怕儿子再有闪失。然而少不更事的独子往往不能体谅母亲的凄凉惶恐,恃宠而骄,在家里尤其是在母亲面前,遇事没耐心,稍微不如意就乱发脾气,犯倔,而寡母又每每迁就,久而久之,独子变得任性倔强,寡母也好生无奈。然而年轻的独子一旦走出家门踏上社会,如果头顶没有强势的后台靠山罩着,社会上的人与事也不可能像家里那样迁就他,因为担心受挫折伤害,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就很敏感,遇事惶恐,缺乏直接面对的勇气,显得胆怯懦弱。这种现象本是人之常情,而在溺爱家庭出身的孩子身上往往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基本的人情人性古今几乎没什么变化,当今社会独生子女中那些“家里横家外怂”的小霸王就是这样养成的。察今以揆古,焦家母子应该就是这种母慈子娇的关系。焦父已然不在人世,焦仲卿在家中的角色既是儿子又做丈夫,已经是一家之主了,但因为焦仲卿身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平常多在外少在家,与母亲妻子“相见常日稀”,所以在母亲与媳妇之间,至今仍然没有学会相处之术,还是个处在心理断乳期的任性大男孩。从“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来看,焦妹还幼小,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焦母对独子焦仲卿一定倾注了更多的关爱,自然也在焦仲卿的内心深处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反抗原始冲动。
东汉地方郡守县令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根基,一般挑选当地的豪族子弟作为自己的佐吏,或者与豪族联姻,这在正史两“汉书”及各种典籍中都有记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刘兰芝被驱遣回家,县令太守随即派媒人登门求亲,可见焦刘两家应该都是在庐江郡有一定名望的豪族,只是因为父亲过早下世,家道中落。汉末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豪门权贵把持着地方为所欲为,这是平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离乱时代。据《后汉书·陆康传》与《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建安年间,庐江郡曾是袁术、孙策与陆康之间以及后来曹操与孙权之间缠斗混战的地方,战乱惨烈,“城头变幻大王旗”。在汉代,小吏出身官员的升迁之路实际上非常坎坷,只有因缘际会或者恰逢其时才有可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二十岁上下作为庐江府小吏的焦仲卿在母亲面前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不仅说出了作为郡府小吏的仕途升迁之难,也暴露了焦仲卿没有英雄出乱世的豪气雄心,只是在乱世苟且偷生。人在乱世,连基本的身家安全都没有保证,普通豪族出身又失去父亲庇护,寡母孤儿势单力薄,身边还有一干同事以及地方其他强族的觊觎倾轧,焦仲卿只能“守节情不离”,用尽职奉公来依阿取容,自然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胆怯怕事。另外,在外胆怯受欺的人,往往会把在外积聚而不敢发作的怨气带回去撒在亲人身上,变得越发任性。
三、怯懦回避,事坏不救
焦仲卿已经把普通的家庭矛盾搅得不可收拾。硬抗没能如愿,焦仲卿就继续软顶,“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在焦仲卿的眼里离婚复婚即成一般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刘兰芝没出焦家门,所有矛盾还局限于焦家内部,属于婆媳矛盾与母子矛盾。刘兰芝休出焦门回老家,矛盾就扩大化了,由焦家内部矛盾变成焦刘两姓豪门之间的矛盾,矛盾性质变了,而且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其掌控和化解的阻碍就更大、变数就更多。婚姻说起来应该以爱情为基础,其实更多的意味着责任,不讲责任的爱情婚姻与一般动物的交媾几乎没啥本质区别,从根子上就不可靠。焦仲卿既然拗不过母亲,又认定让刘兰芝回家是暂时的,不久要迎刘兰芝回来,那就必须拿定主意,对刘兰芝负责,做好周全稳妥安排。这不仅需要设法消除焦母心头的戾气,抓紧化解与焦母的矛盾,赢得焦母接受刘兰芝,还得主动沟通焦刘两家,争得刘家的谅解配合,有效防止岔出新的矛盾、出现新的变故。焦仲卿与刘兰芝成婚已经二三年,又身为庐江府小吏,应该明白这些道理,晓得自己该怎么做,况且刘兰芝在回家的道上就已经提醒焦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焦仲卿遵从当时流行的“出妇之义”[2]267送刘兰芝回娘家,就该顺道陪刘兰芝直奔刘家,当面向刘母刘兄说清楚让刘兰芝暂时回家是权宜之计,并表达“誓天不相负”的决心,以及今后的安排,努力争取刘家的谅解支持。但焦仲卿半道回府当差去了,没有去刘家,这就失去了及时补救机会。刘母婉拒县令求亲之后,太守媒人进刘家之前,这数日中间,县令太守先后打算为儿子向一个刚被夫家驱遣回家的弃妇求亲,在当地应该是一个影响不小的新闻。作为衙门府吏的焦仲卿应该有所耳闻,就该立即有所行动,但焦仲卿仍没有去刘家,再次失去挽救机会,无奈此后事态发展太快,终于无可挽回。
传统社会认定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是人生大事,向来慎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都是公开在严肃神圣的台面上敲定的事情。尽管焦仲卿对刘兰芝再三“誓天不相负”,但那毕竟是男女私下口头约定,没有与刘家家长当面说定,不足为凭据,况且焦仲卿的一纸休书就已经让焦刘两方恩断情绝,刘兰芝此后何去何从,即有刘家决定,与焦仲卿无关。所以即便刘兰芝极力抗拒,刘母也爱怜“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的请求婉拒县令媒人,但终究没能坚持下去。如果焦仲卿对刘母刘兄把事情摆在台面说明白,料想即便刘兄势利,有心逼嫁刘兰芝,刘母也不会默许。汉代社会对各类婚配现象总体上是包容的。《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娶阴丽华,因为阴丽华随军不方便,就让阴丽华回家乡新野随家人居住,三年后刘秀才把阴丽华接回来。[3]405汉桓帝时,秦嘉为郡吏就曾将妻子徐淑寄在岳家养病,夫妻俩留下诗文传诵千古。即便离异,在两汉书中也多有与出妻复婚的记载。焦刘联姻已经二三年,焦仲卿已然不是新女婿,相互间的来往,对刘家应该多有了解,彼此既是亲戚,有话就可以当面商量,毕竟婚姻离散对两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再说焦家父亲故去只有老母,焦仲卿已经成婚二三年,对外说起来也是一家之主了,他有资格也有责任拿定主意,去刘家应该有能力有办法办好这事。焦仲卿的不作为而一再失去挽救机会,固然可能是庐江府公务实在紧张,焦仲卿恪守吏职,不敢以私废公,但更多的可能是焦仲卿像今天的巨人婴一样,看起来人高马大而其心智仍然是孩童状态,不明事理不通人情,遇事缺乏主见,家里任性家外怯懦,惧见刘家人,回避矛盾。毕竟无辜驱遣刘兰芝回家,不仅是姻亲关系的断绝,焦家不义,打了刘姓家族的脸,意味着将导致两家豪族政治利益的切割。焦仲卿对刘家难交代,何况刘兄“性行暴如雷”,去刘家争取谅解和支持,难度一定很大,焦仲卿没勇气直接面对。也许焦仲卿压根就没有想好下面该咋办,只是延宕,因为过去母子相处的经验告诉他,只要他坚持拗下去,不退让,不用多久母亲就会主动退让,迁就自己,同意他把刘兰芝再接回来。所以面对刘兰芝“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的叮嘱,焦仲卿一直没有兑现的行动,他是在等母亲让步。得悉刘兰芝改嫁太守郎君,请假回来的焦仲卿骑马已经到刘家附近,只私见刘兰芝,语带讥讽,抱怨刘兰芝背弃誓言,待家人任性一如既往,仍然没进刘家门,没见刘家人。在当时弃妇回娘家,家长有权让其再嫁,弃妇本人不能作主。焦仲卿私下对刘兰芝反复发誓,指望着刘兰芝能顶住各种压力,“慎勿违吾语”,自己却没有拿出主见直接面对矛盾,怯懦不主动作为,注定指望落空。
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死得毅然决然;万念俱灰的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与心爱的人一同去死并无可怕,况“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本是焦仲卿的宿愿,焦仲卿所以“徘徊庭树下”,不是他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表现,而是因为焦仲卿不同于刘兰芝。刘兰芝在焦家是逐出门的弃妇,在刘家是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即便还有刘母在堂,但那有刘兄照应,刘兰芝了无牵挂。而焦仲卿却有太多的牵挂顾虑,与义无反顾践行“黄泉下相见”殉情诺言相纠结矛盾。焦仲卿尽管身份只是庐江府小吏,但终究还能算是个豪族出身的士大夫,饱受过儒家礼法思想的规训。汉王朝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汉惠帝、汉文帝躬行垂范,汉代皇帝死后的谥号前面都加了个“孝”字,以孝思想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焦仲卿知道自杀,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4]221教训的背叛;就此抛下寡母幼妹不顾,“令母在后单”,无依无靠,不仅于心不忍更是大逆不道。尽管死亡可以逃脱汉代“不孝”律法的严惩,然而不孝的罪名、道德的谴责以及对老母幼妹太多的不舍牵挂,让焦仲卿的良心苦受煎熬。
过去人们解读焦仲卿,多因为他是悲剧的直接受害者,而且又以自缢殉情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礼教压迫的彻底反抗,给予焦仲卿更多的同情和礼赞,却没有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化解家庭生活内部矛盾摩擦的角度,来审视焦仲卿作为一家之主所该有的主见与担当。正是焦仲卿的冲动任性激化婆媳矛盾,坚定了焦母逼走媳妇刘兰芝的决心;刘兰芝遣回娘家,焦仲卿缺乏主动挽救的主见与作为,怯懦回避矛盾,放任事态滑向悲剧深渊,硬生生把家庭婆媳之间的普通摩擦弄成不可收拾。焦仲卿既是悲剧的受害者,也是悲剧的促发人。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是诗末“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题中之义。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