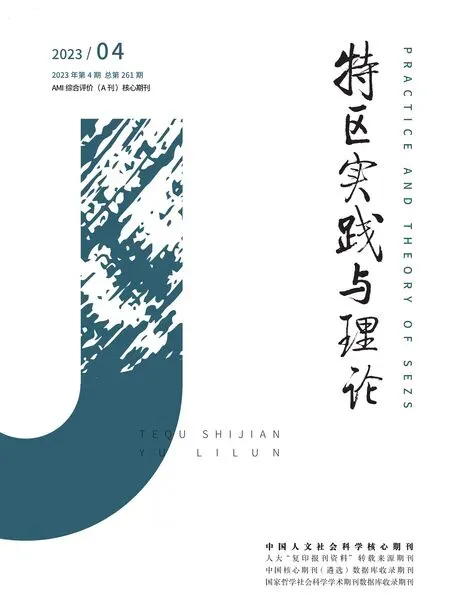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人文
卢 风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人类知识在飞速进步,但人类缺乏正确使用其知识(力量)的智慧。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荣誉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认为,人类面临着两大学习问题: 一是了解宇宙的本性以及作为宇宙之部分的我们自己和其他生物的本性,二是学会如何变得文明。随着17 世纪现代科学的创立,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未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便置人类于巨大的危险情境之中。眼下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产生于这种情境。人口的增长、现代战争的致命特征、物种的灭绝、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在现代工业和农业、现代卫生和医疗、现代武器出现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而现代工业和农业、现代卫生和医疗、现代武器又只能在出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应对这些危机,我们需要像学会解决第一个问题那样学会解决第二个问题[1]。麦克斯韦还认为,能否解决如何变得文明的问题,取决于我们能否获得智慧。智慧涉及“愿望、实现价值的积极努力、发现实际或潜在价值的能力、体验价值的能力、帮助自己和他者实现价值的能力、帮助解决与价值实现休戚相关的生活问题的能力,以及使用和发展价值实现所需的知识、技术和知性的能力”[2]。显然,获得智慧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对价值的全面深刻洞见。人文学科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展示宽广的价值谱系,让人们享受精神自由,并展现人性之美善。迄今为止,人类知识加速进步,力量倍增,但缺乏正确使用其力量的智慧,人文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经济学为典范)的明显弱势是主要原因。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亟需提升智慧,强化人文学科研究,同时人文学科也亟需创新。
一、人文创新的思想背景
在卡尔·波普(Karl Popper)看来,必须通过暴力冲突(包括宫廷政变)甚至血流成河的战争才能实现政权更替的社会就是封闭社会。与之不同的开放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其政权更替无须经过暴力冲突。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而逐渐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一历史过程便是西方的现代化历程。西方在现代化中迅速崛起,就在同一历史时期,满清政府因不肯放弃“家天下”而抱残守缺、闭关锁国(相比日本而言),致使曾是世界最富强国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至此,中国的志士仁人才意识到,中国也必须走现代化之路。
自“新文化运动”(20 世纪初)开始,现代化便是国人的梦想。现代化的“硬件”标志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物质生产(包括农业生产)越来越机械化,城市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就标志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工业化也就是物质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指导现代化变迁(从前现代社会变迁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现代性。中国仍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党的二十大仍在凸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且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实,任一国家的现代化,都必定是有其特色的现代化,即日本的现代化必是日本式现代化,韩国的现代化必是韩国式现代化……
现代性有两大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都重视自由(抑或解放)、平等,但对人能自由(或解放)到何种程度,能以何种方式平等,双方分歧很大;两派都重视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都对科学理性之进步怀有乐观信念。两派的根本分歧是,前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废除私有制而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而后者主张通过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产权清晰是其运行条件)而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或自由)。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目标,并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意识形态,采用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但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没有那么简单。
世界“冷战”时期,是两种现代性和两种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激烈竞争时期。在经济领域,主要凸显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两种模式的竞争。那时,共产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每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生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必然会在由生产过剩而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灭亡。他们认为,采用计划经济模式,逐渐采用“公有制”而消灭“私有制”,抑制货币的作用(如杜绝金融市场),有利于人们抑制私欲,甚至会逐渐使人们变得公而忘私;计划经济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确保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然而,从1949 年到1978 年的中国历史表明,计划经济没有那种优越性。哈耶克(F.Hayek)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委员会能确切预知,一个社会的人们需要哪些物品,对特定物品的需求量有多大,从而能制定出合理的经济计划,以确保经济活动井然有序地按计划进行。人的知识具有“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4],“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是一项在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中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5]。短期看,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有利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但长远看,这势必窒息人们的劳动和创新积极性,从而严重降低经济效率。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重视科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给人们以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经济逐年快速增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中国20 世纪初开启的追求现代化的时代是相对于2000 多年“家天下”历史的大时代。现代性是这个大时代的主导性思想范式。现代性所彰显的基本人文价值是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等。中国因19 世纪以来曾在国际上连连受辱而特别凸显了富国强兵,至今,“富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仍居首位。
国际上关于新时代的讨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根据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或数据之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信息技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渗透,而称新时代为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新星世”[6];一类则根据现代工业文明深陷生态危机的事实和走出生态危机的迫切需要,而认为新时代是低碳(或零碳)时代或“生态纪”[7],取代工业文明的将是生态文明,故亦可称人类正将走向的时代为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两类呼唤新时代的话语都有其哲学凝练,前者是信息哲学,后者是生态哲学。这两种哲学都宣称自己不是任何一种既有哲学的分支学科,而宣称自己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因为都在呼唤一个崭新的大时代,都试图为一个呼之欲出的大时代凝练“精神精华”①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两种哲学显然都可以归入新人文学范畴;二者都对现代性哲学有所批判。
这里讲的大时代非指特定国家的纪年时代,而是世界史意义上的大时代。现代化显然是全球性的,现代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我们说即将来临甚至我们正日益进入的大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大时代,那便意味着这个大时代是对现代化的超越。超越现代化的变迁也必将是全球性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被全球应用,生态危机也是全球性的。故以上两种关于新时代的讨论都是针对全球文明变迁的。迄今为止,现代化是人类生活的时代背景,现代性则是思想创新(包括人文学创新)的思想背景。
二、生态哲学:超越现代性哲学的努力
(一)批判机械论或物理主义自然观(世界观),阐扬生机论自然观(世界观)
起初,现代性自然观是机械论自然观,后来又演变为物理主义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深受牛顿物理学的支持,它把世界看作一座巨大的机器,其运行遵循牛顿力学定律。根据机械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必然的,弄清楚一个系统(如太阳系)初始条件,则其未来的一切都可根据牛顿力学加以预测。这便是机械决定论,19 世纪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有对这种决定论的经典表述。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问世,机械论渐显粗略,物理主义取而代之。物理主义宣称万物都是物理的,所谓“物理的”就是归根结底可被物理学所说明的,例如,人的意识似乎难以归结为物理现象,但物理主义者深信,随着脑科学的进步,总有一天,可以用物理学定律去清晰说明人的意识。物理主义继承了机械论的决定论,也继承了西方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的还原论。现代还原论是数理还原论。根据这种还原论,世界的纷繁复杂、千变万化都是由永恒不变的规律决定的,这些永恒不变的规律就是可用数学语言(如微分方程)加以表述的物理学规律。所有的科学理论都必须奠基于物理学定律,例如,脑科学必须通过生物学、化学而最终奠基于物理学。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物理学体系(就是自然定律或宇宙规律)是具有逻辑简单性的,或说是具有对称性的。
无论是机械论,还是物理主义,都认为人与非人事物(包括一切非人自然物)之间有天壤之别。人是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而非人的一切是没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客体,人有认知能力,非人的一切没有认知能力,人具有自由意志,而非人的一切都没有自由意志。正因为如此,人具有权利、尊严、内在价值和道德资格,而非人的一切都没有权利、尊严、内在价值和道德资格。
生态哲学从蕴含生态学的复杂性科学以及量子物理学获得了支持,提出了生机论自然观(世界观)。生机论与机械论以及物理主义针锋相对。
20 世纪最重要的三大物理学发现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混沌理论的问世是20 世纪物理科学中的第三次革命。就像前两次革命性发现一样,混沌理论颠覆了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相对论排除了对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制的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狂想。”[8]事实上,量子物理学和混沌理论共同否定了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决定论。混沌理论就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复杂性科学。
现代科学家们总认为,大自然的基本规律都可以表达为线性方程。“线性方程总是可以求解的,……线性方程具有一种重要的叠加特性:可以把它们分开,再把它们合并,各个小块又浑然成为一体。”[9]线性方程制约的事物或系统是简单的、确定的,整体不多不少就是其各部分之总和。现代科学家们往往对复杂性和无序视而不见,但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着复杂性和无序,在大气中,海洋湍流中,野生动植物种群数的涨落中,以及心脏和大脑的振动中,都有复杂性和无序。“19世纪和20 世纪的科学家知道,在很多情况下,特定的方程式没有解析解,他们致力于在可决定的部分求出解,然后利用近似的方法处理其他部分。至于更难的谜题,通常就置之不理了。”[10]“无序”也便是“混沌”。现代科学家遇到混沌,不是避开就是认为它不过就是有序现象的多重叠加。于是,一旦面临非线性系统,就代之以线性近似。“只有很少人能记得,原来那些可解的、有序的、线性的系统才是反常的。这就是说,只有很少人懂得自然界的灵魂深处是如何地非线性。”[11]
量子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蕴含生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机械论和物理主义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大自然既不是一座巨钟,也不仅是物理实体(基本粒子、场、暗物质等)的组合;在大自然中普遍存在复杂系统(非线性系统);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即随时都在涌现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12];许多非线性系统的状态都是不可预测的;对复杂系统的一个微小的人为干预,经系统不同层级的放大,可产生巨大的、骇人的效应;人与非人事物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康德认为非人事物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只有人才具有内在的自由,但量子物理学和复杂性科学表明,非人事物本质上并不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并非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非人事物也具有主体性,正因为如此,非人事物也可以具有道德资格。这就是生机论自然观。
(二)批判独断理性主义,阐扬谦逊理性主义
认识论是笛卡尔和康德开创的现代性哲学的主干部分,但大部分生态哲学家针对现代认识论的论述较少。笔者之所以称现代认识论为独断理性主义,是因为它蕴含两个信念:一是以上提及的数理还原论,一是乐观可知论,二者是相互支持的。如果变化、生成(或涌现)、复杂性、混沌等只是世界的表面现象,而一切都受永恒不变的数学规则制约,而且人类具有逐渐揭示这些数学规则的能力,那么就意味着世界是完全可知的。因为科学家去发现这些规则就像农民收割一垄小麦(多割掉一点则少剩下一点)一样,多发现一条规则就意味着未被发现的规则少了一条。科学家们或许不可能在特定时日把所有规则都完全揭示出来,但可以确信,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知识将无限逼近对所有规则的完全揭示。这就是现代的乐观可知论,也是完全可知论。事实上,霍金[13]和温伯格(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4]都表述过这种乐观信念。
反驳独断理性主义的基本理据已包含在复杂性科学和生机论自然观中。如果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如果大自然的“灵魂深处”是非线性的,那便意味着数理还原论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大自然既然随时都在涌现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那便意味着大自然随时都可能产生新规则。这便意味着,制约事物演变的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并非多发现一条,未知规则就少一条。人类永远都不可能穷尽对大自然的探索,著名物理学家罗韦利的一段话,代表着对完全可知论的否定:“我们正在探究的领域是有前沿的,我们求知的热望在燃烧。它们(指人类知识)已触及空间的结构,宇宙的起源,时间的本质,黑洞现象,以及我们自己思维过程的机能。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知的边界(我们)触及了未知的海洋,(这个海洋)闪耀着世界的神秘和美丽。会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15]
现代人征服自然的信心奠基于物理主义自然观和乐观可知论。既然大自然是完全可知的物理实在,知识就是力量,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技术会日益发达,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会逐渐增强,从而渐入在自然中随心所欲的境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弦理论创立者之一加来道雄(Michio Kaku)在访谈了300 位一流科学家之后预言:“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自然之舞的编者,能够在这里或那里调整自然法则。到了2100 年,我们将转变为自然的主人。”[16]“到了2100 年,我们注定要成为我们曾经敬畏的神(gods)。但我们的工具不会是魔杖和魔药,而是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最重要的是量子理论,它是那些技术的基础。”[17]
认为人类将凭科技之力而成为神的人们必定信仰数理还原论。但数理还原论不是可检验的科学命题,而是一种哲学信念,且是一种独断信念。自18 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确实在飞速增长,目前也正呈现指数增长态势。人类干预外部环境的力量也确实在迅速增强。但有一个重要事实是独断理性主义者们所忽视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愈烈,自然对人类的反弹力越大。科技探索永远都是试错式探索,没有任何人类活动是万无一失的。人类干预自然的力度越大,其意外事故的后果越严重。物理主义、数理还原论、完全可知论激励人类产生自豪感和征服欲,甚至激励人类的狂妄,而让人们忍不住宣称:人就是神。但是,大自然并非基本粒子、场和暗物质的线性组合,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与大自然的创造(从宇宙、银河系到太阳系、地球)比较,包括“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的创造都只是小制作,人类无论如何发明创造,无论可否冲出地球,飞向太空,都脱离不了大自然的怀抱。
拒斥独断理性主义,并不意味着拒斥理性和理性主义。生态哲学着力阐释谦逊理性主义,其基本信念是:理性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理性能力典型地体现为在公共领域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体现为对极端情绪的调谐和对极端行动的控制。人类凭理性可以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但不可能征服自然。保持理性的谦逊是人类的本分,谦逊理性主义要求人们敬畏自然,要求人们在设计种种人工系统时注意与自然物和谐共存,多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18],并着力提升人类实践的韧性。2019 年发现且至今仍未消失的新冠病毒正是对人类韧性的考验。
生机论和谦逊理性主义是生态哲学最重要的思想,但远不是其重要思想的全部。生态哲学还包括吸纳个体主义合理思想的共同体主义,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幸福观、人生观,超越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强调自然美优先的美学等等,生态哲学的努力是一种人文学创新。
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人文创新
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辉煌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巨大的飞跃。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曾说:“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 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19]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人民的福祉从石器时代到1800 年”没有任何进步,“甚至不进反退”[20]。这是就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下的判断。工业革命之后,物质生产力迅速发展,才有了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现代民主法治无疑代表着政治文明的新境界,现代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梦想。
讨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人文创新,既要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又要考虑现代化的要求。当代中国人亟需的新人文应包含如下几点:
仍需接过康德的启蒙口号:要有勇气公开地使用你的理性!即摆脱我们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每个人都要有勇气为自己做主,而不要任何“大人”为之做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之谓也。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是以参与公开辩论的方式就公共事务摆事实、讲道理。人人有勇气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是现代化的要求。工业化、城市化是 “硬件”的现代化,人人有勇气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则是人的现代化,是“软件”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会成为人的新枷锁。
重视《中庸》所特别凸显的“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在媒体和自媒体无比发达的今天,不能忘记“不诚无物”这一至理名言。立场对立的人们应该有超越自己立场而追求客观性的努力,不能只一味利用未经核实的“事实”去捍卫自己的立场,“驳斥”对方的观点。《中庸》所讲的“诚”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天作为终极实在对万物皆无偏私,“诚者,天之道也”,意指天生万物,绝对公正无偏。“诚之者,人之道也”,意指人不可背离天道,应该努力做到真诚无私。
重新理解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说,只有“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今天,我们当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与民主之间的一致性。“科学也是一项民主事业,因为它假定在真理与对真理的发现面前人人平等。”[21]科学和民主的实质都是通过论辩、说理(重视来自实验或实践的数据)的程序去寻求最佳解难题办法,二者都反对暴力的肆虐和权力的傲慢。全球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实践再一次验证了科学与民主的必要性。
吸取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黑色发展”的严重后果,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改变发展模式,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放弃对自然的征服,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语词以及其他语义结构可以有意义,而对象、事件、事态或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人生意义或者是宗教领袖们热衷于谈论的,或者是“心灵鸡汤”烹调者所贩卖的,而不是正经学术研究所应该严肃对待的。这是人文学的严重失误。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人类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宗教是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理解,不同的生存哲学(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可归入此类)也是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无法统一的。人文学的任务不是提供统一的人生意义,而是审视对各种不同宗教和哲学的践行是否既有利于人类共同体的和平与繁荣,又有利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与繁荣。笔者认为,超越物质主义——为人们提供超越物质主义的人生意义——是新人文的核心任务。现代化为超越物质主义创造了条件。在实现现代化之前,任何形式的反物质主义话语都不免显得虚伪。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是反物质主义的。在古代中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能在言辞上反对物质主义的人们身在“朱门”,制度保障他们衣食无忧,广大劳动者却时常面临物质匮乏的威胁。统治阶级恰恰通过横征暴敛而掌控物质财富,进而实现对劳动人民的控制和奴役。古代意识形态反物质主义的虚伪也主要表现于此。经过现代化,有了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出,物质财富增长不是人的根本需要。
大前研一对日本“低欲望”一代的描述,能说明这一点。大前研一说:“如今日本年轻人当中,成为话题的流行新语就是‘穷充’(poor 并充实)。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金钱和出人头地而辛苦工作,正是因为收入不高,才能过上心灵富足的生活。”[22]这种“穷充”心态在欧洲富裕国家也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发达社会“穷充者”的穷与古代劳动者的穷不可同日而语,自愿选择“穷充”的人们无饥寒之苦。“心灵富足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生活,人生意义才是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的根本需要。超越了物质主义,人们就不会攀比物质消费,就能理解“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当绿色生活方式成为主导性生活方式时,生态文明建设就水到渠成了。中国要在走完现代化历程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其人文学既要吸取现代性的思想精华,又要对现代性有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