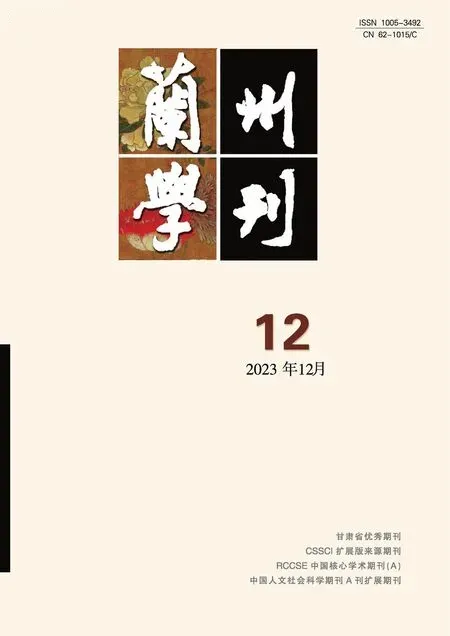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与模糊”
——基于四川省G村的调查
阮海波
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在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后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加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构建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处理、更新、反馈、干预、阻断等程序,收集返贫监测信息是治理返贫的基础性工程。(2)范和生:《返贫预警机制构建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返贫监测信息的收集与处理直接关系风险对象的识别、风险类型的判断以及风险治理,需要接续精准扶贫的精准理念(3)左停、李泽峰:《风险与可持续生计为中心的防返贫监测预警框架》,《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实现“精准识别”“精准防治”。国家获取精准的信息是进行精准返贫治理的前提。但是,在G村调研发现,国家需要的返贫监测信息并未走向精准化,而是走向模糊化。那么,为什么国家需要的精准返贫监测信息在实践中走向模糊化?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文献梳理与分析视角
返贫监测信息的关键在于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根据收集的脱贫户信息建立信息库,对脱贫户动态监测,实现返贫对象的精准识别。脱贫户监测表是收集脱贫户信息的有效载体,在G村,村干部将填写脱贫户监测表的过程称之为“算账”,家庭人均年收入是算账的结果,并转化为监测信息。算账一词来源于经济学与会计学,是指对运营成本进行核算。算账也见于日常生活,表示家庭生产经营情况,也用于表示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关系。日常生活用语的算账遵循的是经济逻辑,扶贫事业中的算账赋予其政治逻辑。既有文献从三个方面对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进行了研究。
(一)文献梳理
一是目标责任制与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现代科层体制采用目标责任体系推动政策执行,以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评奖惩的依据。官僚考核的数字化挤压导致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家庭收入的核算指标被简化。(4)方菲、张恩健:《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上级政府的目标约束与激励压力会催生数字脱贫(5)李小云、吴一凡、武晋:《精准脱贫: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在填写的数字上“下功夫”(6)章文光、刘志鹏:《注意力视角下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基于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年第4期。,忙于“巧算账”,有意扩大贫困户基数(7)曾智洪、毛霞维:《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拆解与立体化重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精准识别走向模糊化(8)彭桥、肖尧、陈浩:《精准扶贫与扶贫对象识别——基于信号博弈分析框架》,《兰州学刊》2020年第12期。。同时,地方政府为彰显脱贫政绩,提高任务完成度,虚报农户收入水平(9)吴继英、薛艳杰:《我国脱贫攻坚指标数据质量检验——基于Benford法则和面板数据模型》,《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贫困群众“被脱贫”(10)沈费伟:《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数据失真,影响扶贫精准性(11)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数字脱贫”“计算脱贫”“文本脱贫”的本质都是脱离实际的算账(12)张琦、万君:《“十四五”期间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策略》,《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6期。。
二是返贫监测机制与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返贫信息监测机制包括制度安排、责任划分、信息技术建设等,是返贫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将返贫问题的事后治理逻辑改为事前治理逻辑。但是,地方的返贫监测机制尚未构建,缺少常态化的返贫监测制度安排,返贫监测主体单一,监测队伍人员力量薄弱,监测专业技术水平不高,呈现机械式监测,无法获取风险数据,导致信息数据质量不高、信息碎片化,出现返贫监测迟缓现象。(13)胡世文、曹亚雄:《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目前的返贫监测机制多是以信息技术为凭借,但标准化、统一化与模板化的信息识别格式难以挖掘“隐性”的贫困因素,价值技术提取的有效性,阻碍信息的精准识别,使得大数据信息监测走向模糊化,出现“拖曳效应”。(14)Azeem M M, Mugera A W, Schilizzi S, “Do Social Protection Transfers Reduce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Pakistan? Household Level Evidence from Punjab”,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No.8,2019, pp.1757-1783.
三是制度约束与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返贫监测信息的目标偏离并非个体有意为之,而是背后的制度性因素。(15)[美]詹姆斯·G.马奇、[挪威]约翰·P·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6-7页。制度为个体行为选择,实现目标路径提供了基本的框架。(16)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返贫监测信息应置于政府制度与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因素中进行考察(17)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返贫监测过程以及信息的生成过程受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形塑,前者以科层制度的约束为主,后者以地方性知识、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习俗为主(18)杨宇、陈丽君:《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正式制度设计不足导致监测本身存在缺陷,无法实现政策目标,而制度冲突降低了制度的约束作用,无法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转换为国家的制度优势以及治理效能(19)贺立龙:《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正式制度的落地往往遭遇非正式制度的抵制,弱化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出现“算账式扶贫”,致使信息监测走向国家制度规定的相反方向,同国家精准理念相违背。
已有研究从科层目标责任制、返贫监测机制与制度约束方面探讨了返贫监测信息走向模糊化的原因,有利于透视算账在扶贫事业中的多重面向。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返贫监测信息受到制度影响,算账具有多重属性,包括日常生活逻辑、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扶贫视野下的算账与国家、基层政府、村干部、农民相关,不同的制度逻辑带来目标冲突,进而导致精准理念偏离。(20)邢成举:《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方面,研究者没有切身参与村干部算账过程,整个研究缺少基层算账细节;另一方面,没有深层次地揭示国家的精准返贫监测信息为何会模糊化。基于此,本研究将从G村村干部算账的过程入手,以多重制度逻辑为分析视角来探讨返贫监测信息如何走向模糊化。
(二)分析视角:多重制度逻辑
人们对制度的遵守并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21)Little D,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pp.74-77.正如诺斯所言:“统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制定规则”。(22)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7.2010年,周雪光与艾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提出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作者认为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分别遵循不同的逻辑导向。多重制度逻辑的核心观点有三:一是强调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事件与行为是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化体现了国家逻辑,属于政治逻辑,基层政府(县、镇)遵从行政逻辑,农民遵从理性经济逻辑,村干部遵从实践逻辑,算账过程体现各主体之间逻辑的互动;二是宏观逻辑与微观逻辑的结合,宏观逻辑安排体现在微观个体行为中,从相互关系的变迁中也可以察觉宏观逻辑的存在,国家是返贫监测信息的宏观安排者,监测信息来源于脱贫户个人,村干部的算账过程可以发觉国家与脱贫户之间的互动;三是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各主体的利益导向不同,个体行为既要遵循个体逻辑的驱动,又要受到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的制约,行为反映利益,环境制约行为,村干部是算账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既有自己的实践逻辑,还要受到国家逻辑、基层政府逻辑、农民逻辑的约束(23)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由此,建立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图
本文使用的资料来源于2022年8月30日至9月10日本人在G村所开展的田野调查,包括脱贫户收入核查表填写过程资料以及同村干部、驻村干部、农户、普通村民等的访谈资料。选择G村进行研究具有两个理由:一是G村所属县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国家力量、基层政府、村干部与脱贫户在算账过程中的行为逻辑互动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G村于2017年就开启返贫监测信息的填写,其算账过程与返贫监测信息的收集已经较为成熟,符合案例研究要求。但是,案例研究与抽样调查始终存在不同,前者旨在进行“分析性概括”,展示更多理论推理的力量。(24)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表1呈现了主要受访者的基本信息与访谈编码,为遵守学术规范,对受访者的姓名进行匿名处理,调研中出现的其他村民,将以脱贫户1、脱贫户2的形式呈现。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采用“事件—过程”的叙述方法进行动态呈现。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二、算账过程:返贫监测信息的填写与生成
G村常住人口在1000人左右,2010年以前,大部分农户以务农与家禽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村民经济收入来源单一,乡村经济发展落后,无集体资产。2014年,G村61户被认定为贫困户,该村也被认定为贫困村。2016年,基层政府结合G村实际情况,选择以易地扶贫搬迁的方式脱贫,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为防止脱贫户返贫,国家要求对脱贫户进行动态统计监测。于是,从2017年起,G村就开始填写脱贫户收入核查表(监测表),每次填写都是一次算账过程。
(一)入户算账:脱贫户分类与算账的开始
2022年8月下旬,县政府下发通知要求脱贫村组织开展填写脱贫户收入核查表,截止时间为8月31日,这是今年第三次填写。这一次算账的时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算账内容包括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年收入与家庭年人均收入(这是本文所指的返贫监测信息)。县政府要求今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最低为7000元,且要比去年算的结果增长10%。G村接到任务通知后,村书记将算账时间定于8月30日下午至8月31日,用两天的时间完成算账任务。根据以往算账经验,村书记将58户脱贫户(截至2022年8月,有3户脱贫户死亡,剩余58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庭有外出务工的脱贫户,计38户;第二类是家庭老龄化的脱贫户,需要入户算账,计17户;第三类是重点监测脱贫户,无劳动力,家庭成员身体有疾病,家庭脆弱性十分明显,可持续生计能力不足,涉及3户。针对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脱贫户,村书记安排不同的村干部进行算账。
第一类脱贫户的经济收入容易计算,“我们这边在外边务工的老百姓,大部分的工资一个月基本上是在七八千到一万多”(RHB20220830WWJ)(为保留访谈与对话原文,文中部分数字没有统一为阿拉伯数字)。这部分脱贫户的家庭经济收入怎么算都能达到标准,于是,村书记安排两个综合专干与驻村帮扶干部负责,在村办公室参考往年算账的结果进行填写。第三类脱贫户的收入计算最为困难,由村书记个人计算填写。第二类脱贫户家庭经济收入困难,主要来源是务农,增长10%较为困难,由村书记与村副书记入户算账。
脱贫户1由两位70岁以上的夫妻构成,典型的老龄化家庭。2014年为申请认定贫困户,将子女从户口中分离,一户分为两户,家庭经济收入单独计算。在村书记的算账过程中,其开场并没有直接奔入主题,而是先讲明这次算账的意义,有意在做脱贫户的思想工作,规训农户思想意识,将农户家庭收入与乡村发展相结合,家户与集体相统一。在生产性收入中,将玉米收成折算成现金收入,并且以高于市场价格计算,玉米算的1.6元/斤,总计960元;谷子算的1.5元/斤,总计1500元。在转移性收入中,公益性岗位算的1200元,养老保险算的2310元,退伍军人算的2400元,残疾补助算的1200元。按照增长10%的要求,脱贫户1的算账结果要高于11000元,目前还差1400多元,村书记将缺少的部分计算为子女给予的赡养费。由此,脱贫户1算账结果由生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子女赡养费构成。
村副书记计算脱贫户2的经济收入,脱贫户2没有劳动力,无法获得乡村公益性岗位的转移支付,村副书记只能提高豆子与红薯的价格,并且提高红薯的产量,这种计算逻辑是为了让计算结果达到既定的标准。豆子计算的是3元/斤,红薯算的0.3元/斤,重量为500斤。但是,脱贫户也会对农产品计算的价格产生怀疑,认为村干部计算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同时,脱贫户自报农产品产量时,也会压低自己的产量,如脱贫户2自报红薯产量为200斤,以此降低家户经济总收入。对于村干部而言,生产经营收入与子女赡养费充当调节工具,起到调节效应,这在后面的计算中更为明显,其余村书记与副书记入户算账的过程与此类似。
(二)核对算账:帮扶人下村校对收入
根据国家扶贫要求,每个贫困村都有定向帮扶单位,G村的帮扶单位是县职工委。同时,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导向下,为有效识别与精准帮扶脱贫户,每一户脱贫户均分配有定向的帮扶责任人。按照上级要求,监测表本应该由帮扶责任人填写,属于其职责,但帮扶责任人并不驻村,对其帮扶对象并不了解,算账只能由村干部来完成。正如驻村干部所言:“算账这个以前是要求他们过来,要入户填,可他们并不了解情况,他们如何算”(RHB20220831ZX)。作为帮扶责任人必须知晓帮扶对象的整体收入情况,因此,村书记在8月30日晚向帮扶责任人约定31日到村办公室核对算账结果。对于帮扶责任人而言,一方面需要核对算账结果是否符合客观情况与上级要求,另一方面需要知晓帮扶对象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备上级检查。
职工委的帮扶责任人前来核对算账,发现脱贫户中的务工收入在3000元后又加了一个2000元,导致信息不明确,与ZZZ发生争论,并向填写表格的FXQ确认信息。FXQ反馈2000元是追加的务工收入,务工总收入为5000元,ZZZ的意见是将务工天数修改为41.6天,每天120元。帮扶责任人认为应该填写42天,ZZZ认为42天的务工收入为5040元,高于5000元,可以算为41.5天。帮扶责任人与ZZZ达成一致意见,算41.5天,并重新填写表格。帮扶责任人凭借其工作经验检查出监测表上不清晰的内容,并就该项反复向村干部核实,以使该项目明晰化。在核对算账中,帮扶责任人与村干部是合作共谋关系:一方面,两者需要共同完成算账任务,使得算账结果大概符合脱贫户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两者要在某些算账项目上达成一致,算账结果要符合上级政府要求。
(三)再次算账:绩效考核与计算收入增幅
在帮扶责任人核对算账结果的同时,村书记完成了第三类脱贫户的算账,ZQZ完成了第一类脱贫户的算账,并填写完成电子版。8月31日中午,其他贫困村在全镇干部工作群中公布了本村算账情况,电子表格中新增了一列脱贫户的具体增幅,并以10%为衡量标准。该村行为得到镇干部表扬,于是要求其他贫困村也需要计算。村书记安排31日下午计算脱贫户的具体增幅,计算人有村书记、FXQ与ZQZ。FXQ负责查找2022年算账的结果,ZQZ负责查找2021年8月算账的结果,WWJ负责计算具体的增幅数字,FXQ填写在表格中。在计算增幅过程中,对部分脱贫户算账结果进行了调整,以使其更符合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要求。WWJ发现脱贫户3的收入为6560元(2022年),其2021年计算结果为5560元,虽符合10%的增长要求,但不符合7000元的最低标准。FXQ将脱贫户的姐姐对其的帮扶从1000元调整为2000元,总收入为7560,增幅填写为36%。
计算增幅的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增幅达到了10%,符合上级政府考核要求;第二种是增幅位于0—10%之间,有增幅,但是没有达到10%;第三种是出现了负增长。统计发现,绝大部分脱贫户的收入都在10%以上,且分布于第一类脱贫户,增幅位于0—10%之间的脱贫户多为第二类,出现负增长的脱贫户多为第三类。虽然上级政府要求脱贫户都要达到10%的考核要求,但是村干部也会从脱贫户的实际情况出发,出现一部分增幅低于10%的脱贫户,针对少于10%的情况“可以写一个说明,说明为什么达不到,或者出现什么情况”(RHB20220831WWJ)。在计算中也对填写错误的表格进行修正与调适,减少计算中出现的原则性错误,“7000元的经济收入是脱贫的最低标准,低于7000元意味着没有脱贫,所以所有的脱贫户经济收入必须达到7000元”(RHB20220831WWJ)。
(四)调整算账:赡养费用的调节效应
8月31日晚,镇政府反馈算账结果,对经济收入的标准又进行了调整,将人均年收入标准从7000元调整至1万元,G村有20户需要调整。从名单上来看,20户脱贫户正好是第二类与第三类脱贫户,这两类脱贫户的经济收入来源绝大部分是转移收入,包括国家的财政转移收入与子女的赡养费用。对于村书记而言,全部脱贫户的人均收入都调整至1万元,显然不符合实际,因此,只能有选择性的调整。9月1日上午,村书记将重新调整的任务安排给ZQZ:“有一部分要改到9000多,有一部分是不改,低保那一些是不得改的,我们可能只改9000多,不到1万,这种差点的,给他加上去,给他改到一万以上,以免出现问题整改”(RHB20220901WWJ)。
将20户脱贫户分成两类,一类算到1万以上,另一类不能算到1万以上。无论能不能算到一万以上,都需要调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原来为7000元的调整至8000元,8000元的调整为9000元,9000元的调整为1万元以上。进一步的问题是,增加的收入从哪里来?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低保、养老金、公益性岗位、残疾补助等均在政府有备案,这部分收入是恒定的,调整这部分收入不符合政策规定。因此,赡养费就起到重要的调节效应。在申请贫困户与认定贫困村时,部分农户的户口一分为二,子女与父母的收入单独计算,现在以赡养费名义将子女的收入纳入父母的收入之中,既符合政策要求,又符合情理道德。同时,赡养费是一种既有根据又没有根据的收入项目。有根据是指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子女尽孝会转移一定的费用给父母,形成代际支持;没有根据是指子女给予父母赡养费的具体数目或过程不会留痕以作为证据,他人无法得知子女给予父母赡养费的具体金额,上级政府也无法核查。由此,对于村干部而言,赡养费就具有可伸缩性、可操作性与灵活性,进而使得赡养费具有调节性。
一方面,赡养费内容的可调节性。在村干部的计算中,赡养费包括的内容有子女过年过节给予的现金、平时给予的生活费、给父母购买的物品(衣服、手机与家电等)以及子女支付的医疗费用等,不同脱贫户计算的赡养费内容不同,如脱贫户1计算的子女支付的医疗费用较多,而脱贫户4计算的女儿给予的过节费较多。另一方面,赡养费金额的可调节性。村干部在处理赡养费时会考虑脱贫户的经济状况、子女的经济状况与政府制定的标准,寻找一个适中的平衡点,以确定赡养费的具体数目。如ZQZ在调整脱贫户5的收入中,将其从9416.6元调整为10516.6元,其理由是“脱贫户6有三个孩子,原来只算了两个孩子的赡养费,另外一个女儿也会拿赡养费”(RHB20220901WWJ)。但是,赡养费的使用也会受到约束,这种限制来自子女的经济条件,如脱贫户7的人均收入为7500元,ZQZ只是将其调整至8000元,“他的儿子没有出去打工,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再怎么算也不能多”(RHB20220901WWJ)。这种约束使得计算结果在标准与现状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
ZQZ对20户调整后的结果是,有10户脱贫户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有6户在9000元至1万元之间,有4户在8000元至9000元之间。针对没有超过1万元的10户脱贫户,ZQZ均写了相应的说明,原因有两类:一是家中老人有疾病,医疗费用开支大;二是家中缺乏劳动力,没有经济收入来源。9月1日下午,ZQZ再次将所有的材料交至镇政府,之后没有收到反馈,至此,这一次的算账任务得以完成。
三、算账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
多年算账经验的叠加使村干部能在几天的时间内完成监测信息收集。虽然算账时间很短,但是涉及主体很多,国家、基层政府、村干部与脱贫户均被卷入其中,各主体遵循不同逻辑。国家是返贫监测信息的发起者,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基层政府是监测信息表的下发者,遵循的是行政逻辑;脱贫户是返贫信息监测对象,遵循的是经济理性逻辑;村干部是返贫监测信息的执行者,遵循的是实践逻辑(25)原贺贺:《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多重制度逻辑在算账中实现互动与相互作用,导致返贫监测信息走向模糊化,与国家的精准信息要求相违背。
(一)国家的政治逻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反贫困是国家治理的大事,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贫困也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返贫监测机制是国家统一进行安排与部署的战略,旨在将事后帮扶变为事前预防,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与早预防(26)何菊莲、王善平:《脱贫攻坚效能审计:监管困境与机制完善》,《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兑现“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承诺。从2015年国家吹响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声起,国家就不断强调要对贫困户施行动态监测,以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如表2所示,2020年开始,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强调返贫监测机制与信息的重要性,对监测对象、监测范围与监测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提高治理返贫的预见性和精准性,返贫监测信息成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27)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6期。,必须高度重视返贫现象,及时有效化解返贫风险。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建立贫困监测信息遵循的是政治逻辑,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见,国家的政治逻辑链条是“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化—精准帮扶—防止返贫—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国家要求的是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化。
(二)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晋升锦标赛
现代政府按照科层制原则组建,正如韦伯所言,严密的官僚制架构能够保障信息的传递,科层之间按照非人格化的组织安排驱动。(28)Cerny P,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 No.4,1995, pp.595-625.压力型行政体制与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结合将行政工作压力层层传导,上级政府依据发包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政绩考核,塑造“强监控—强激励”的政府工作氛围。基于此,Lazear和Rosen提出“锦标赛”理论,上级政府作为委托人,下级政府是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业绩排序将会激励代理人积极工作。(29)Lazear E, Rosen S,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 No.5,1981, pp.841-864.国内学者将其引入政府治理领域(3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提出了经典的“晋升锦标赛”(31)Li H, Zhou L,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 No.9,2005, pp.1743-1762.理论,用于解释地方政府的“邀功”行为。用安东尼·唐斯的话来讲,“科层制的官员如同社会的其他代理人一样,很大程度上被自我利益所驱动”。(32)[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在扶贫事业下,基层政府的晋升锦标赛也有体现。
上级政府将扶贫压力与责任传导至基层政府,扶贫成效直接与官员的考核晋升相关,地方官员急于在任期内建设“政绩工程”突显业绩,产生“扶贫军令状”与“脱贫锦标赛”。在“脱贫锦标赛”中,基层政府“自我加码”,提高脱贫考核的要求(33)王刚、白浩然:《脱贫锦标赛:地方贫困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8年第1期。,以获取上级政府的稀缺资源。2021年,G村所属县的县委员会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这对县级政府起到极大的激励鼓舞作用。在此次返贫监测信息的算账中,县政府先是确定人均年收入为7000元,后又调整为1万元,大大超过既定的水平,也超过部分脱贫户的实际情况。为凸显增幅,基层政府要求计算每一户的增长幅度,这是在数字上产生竞争与对比关系。“就是XX(县名)这个要挣个先进,挣个表彰,所以要创新,17年到19年是一年一次,这后面是一年两次,今年最多搞了三次了,可能都还要搞一次”(RHB20220907ZZX)。“之所以我们这么辛苦,就是XX(县名)想搞一个先进,整这个脱贫攻坚方面,什么东西他们都要创新一些,他们倒是拿到了奖了,底下的累死了”(RHB20220907ZZX)。基层政府在行政逻辑的驱动下为出政绩,在数字算账上下功夫,要求提高脱贫户人均年收入水平,以加入返贫监测收入的锦标赛。
(三)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获取扶贫资源
理性小农认为农民具有经济理性,与资本家一样符合经济人属性,农民的行为受到经济理性原则支配。(34)[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48页。在市场经济的渗透下,农民的经济理性意识获得大幅度提升,出现“理性扩展”的现象(35)阮海波:《“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将经济理性嵌入行政场域、社会场域。在算账过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经济理性逻辑的支配。被入户算账的脱贫户在面对村干部的询问时会将家庭经济收入降低:一方面,脱贫户会降低种植业、养殖业的产量,如脱贫户2汇报红薯的产量不到200斤;另一方面,脱贫户会对村干部计算的价格产生疑问,甚至提出反对,脱贫户2对村干部计算豆子的价格提出疑问,因为豆子的市场价格没有高于3元/斤。同时,在说明家庭经济收入时,脱贫户偏好报亏损不报增收,如脱贫户1汇报自己的猪死亡,自己亏损了几千块钱而没有挣钱。
在脱贫户的生计记忆中,相对于非贫困户的身份,贫困户可以获取国家的一系列帮扶资源。在G村,贫困户可以免费领取鸡苗、猪仔、果苗等,医疗保险的费用由政府全部承担,过年过节可以获取政府的油粮礼品,甚至是直接现金补助。贫困户在身份名誉上不如非贫困户,但是贫困户的身份附着有经济资源的分配,能给贫困户带来经济收益。贫困户脱贫后给予的经济帮扶逐渐减少,如2021年缴纳的医疗保险只有部分脱贫户享受政府全额缴纳,其余脱贫户由个人与政府分担。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脱贫户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经济收入以获取更多的扶贫资源。“现在还算不起账,这个说我没有那么多,那个说我没有那么多,你瞒来咋子。不可能共产党扶了那么久了,还要给你扶好多钱来”(RHB20220908WWJ)。因此,部分脱贫户的逻辑是选择隐瞒收入、降低实际收入以谋取更多的政策福利,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四)村干部的实践逻辑:当好代理人与当家人
农村集体化解体后,乡政村治的局面出现,村干部扮演一体两面的角色。一方面,村干部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是村民的当家人,主管乡村公共事务,具有自治属性;另一方面,村干部是基层政权的末梢,需要完成上级政府安排的行政任务,在委托—代理模型中是代理人,具有行政属性。村干部是返贫监测信息填写的具体执行者,在算账过程中需要处理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理性逻辑之间的张力,在多元逻辑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从乡村政策执行来看,村干部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与自主施行空间,因此,村干部遵循的是实践逻辑,采取权宜性执行的策略(36)钟海:《权宜性执行:村级组织政策执行与权力运作策略的逻辑分析——以陕南L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2期。,针对不同的脱贫户采取不同的算账形式以在多元逻辑之间实现平衡。
在计算增幅中,村干部并不是将所有脱贫户的增幅都计算至10%,只有第一类脱贫户达到10%,第二类与第三类脱贫户没有达到10%。针对低于10%的脱贫户,村干部解释道:“我们给他们算多了,今年涨10%,你明年还要涨10%,在这个基础上,后年还要涨10%,后年还要在明年的基础上涨10%,你给我算一下,这个涨幅有多大,你给别人算死了,到时候我们这整来每家每户人均都算上两三万了,过两年每户就要增加到三四万,那么我从哪里去找,人家的收入基本上是恒定的”(RHB20220909WWJ)。针对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村干部并不是完全执行,而是根据脱贫户的具体情况选择性执行。面对脱贫户隐瞒收入或降低收入的经济理性逻辑时,村干部采取说服教育的形式克服,正如在给脱贫户1算账的开端,将家庭的发展与乡村集体的发展相结合,向脱贫户说明政策的变迁以获取百姓的支持与认同。
(五)多重制度逻辑的张力: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
表3展示了在算账中各主体遵循的制度逻辑、逻辑导向以及在算账上的要求。国家的出发点是收集精准的脱贫户人均年收入水平(实际收入水平),掌握返贫风险,及时干预,提早帮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基层政府为迎合数字指标,获取晋升奖励,要求村干部在算账时提高人均年收入水平(高于第二类与第三类脱贫户的实际收入水平)。第二类与第三类脱贫户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为获取更多的帮扶资源,会要求村干部降低人均年收入水平(低于第二类与第三类脱贫户的实际收入水平)。由此,基层政府的逻辑与脱贫户的逻辑呈现一高一低的张力,村干部为弥合两者之间的张力只能采取灵活的策略与措施,针对不同的脱贫户在高与低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既能满足基层政府算高的要求,又要满足脱贫户算低的要求。但是,这个平衡点的数字并非实际人均年收入水平,而是走向了模糊化。加之赡养费所具有的可伸缩性、可操作性与灵活性使得算账结果更具有模糊性,赡养费构成村干部权宜性策略的重要内容,加剧偏离脱贫户实际收入水平,与国家的精准化需求相违背。

表3 算账中多重制度逻辑的张力
四、找回精准:返贫监测信息的去模糊化
信息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要素,精准信息是国家治理贫困的前提,掌握精准信息才能实现精准识别,进而实现精准预警风险,采取精准帮扶措施,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但是,国家的精准返贫信息需求并未得到实现,而是在多重逻辑中走向模糊化,这个过程通过算账来完成。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与村干部的实践逻辑在算账中互动与相互作用,导致国家需求的返贫监测信息走向模糊化,不利于相对贫困治理,对国家政治逻辑的实现产生阻碍作用。因此,需找回精准,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化,为国家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高质量的监测信息。(37)赵普、龙泽美、王超:《模性返贫风险因素、类型及其政策启示——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一)价值理性复归:超越基层政府的工具理性
韦伯将人类行为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前者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后者是目的优先价值。(3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57页。现代政府以实现公共价值为首要目标,如自由、平等、安全、幸福等,在不同时空下形成“价值金字塔”,进行价值排序,并以此获得政府合法性。在本文中,基层政府遵循行政逻辑,提高返贫监测的标准是为实现“返贫锦标赛”,获取表彰与晋升机会,实质是对工具理性的追求,而忽视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返贫监测成为一种工具,而返贫监测本身的价值逻辑属性被遮蔽或忽视。因此,需要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直接负责返贫监测的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初心与使命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39)阮海波:《政治势能的阶梯:走出多重制度逻辑之困——以G县P村脱贫攻坚政策执行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将实现人民的幸福,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摆在第一位,弱化行政逻辑,强化政治逻辑。将党的理念与价值贯穿至返贫监测的全过程,适当调整上级政府目标考核中的数字化倾向,减少晋升奖惩中的以数字大小论英雄,以此避免基层政府的数字竞选、数字加码、自我加码等行为。
(二)健全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公开化
对于村干部而言,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倒逼村干部采取权宜性策略来调适。村干部凭借“地方性知识”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构成其权宜性策略的基础。从整个算账过程来看,对村干部的算账行为与基层政府的加码行为缺少必要的监督环节,导致国家获取的返贫监测信息走样,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此,应建立健全返贫监测信息填写的全过程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精准化的实现。一方面,充分发挥村民民主监督的作用,将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普通村民等纳入算账过程,跟随村干部入户算账,参与全过程监督。另一方面,将脱贫户返贫监测信息作为村务公开内容进行公开,包括生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赡养费收入等,接受其他脱贫户与非贫困户的公开监督,从而削弱村干部在返贫监测信息上的自由裁量权,约束村干部的权宜性策略行为,让返贫监测信息走向公开化、透明化与阳光化,确保数据的精准性与有效性。(40)黄承伟:《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防止返贫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逻辑、实践挑战及理念创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三)塑造道义小农:弱化农民的经济理性
斯科特研究东南亚小农社会后认为传统小农经济不仅塑造理性小农属性,还形成道义小农的特性,农民行为遵从乡村情理道德的逻辑,而不是充满经济的计算性。(41)[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6-42页。在本文中,脱贫户遵循的是经济理性小农逻辑,为获取国家扶贫资源,压低报告经济收入,不利于村干部获取精准的返贫监测信息。道义小农认为农民勤劳淳朴、邻里互助、乡村伦理规范有序、乡风文明、社会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强,是紧密的生活共同体。因此,可以挖掘传统乡村的道德美德,塑造道义小农,降低农民的功利性与利益性。第一,利用乡村“差序格局”网络重塑或巩固乡村社会网络结构,通过社会网络与社会交往增加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社会信任。第二,构建乡村社会责任体系,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填写返贫监测信息作为脱贫户、村干部的共同责任,而非仅仅是村干部的行政任务。第三,推动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塑造乡村道德体系,深入挖掘传统农耕文化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培育农民正确的义利观、道德观与价值观,从而弱化经济理性属性。
五、结论
在中国的扶贫事业中,精准扶贫被置于战略性地位,精准信息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国家的精准化返贫监测信息需求在实践中走向了模糊化,该过程涉及国家、基层政府、村干部与脱贫户等多元主体。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一是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在于通过精准的返贫监测信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之间存在张力,村干部为调适两者的张力采用权宜性策略进而导致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因此,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是多重制度逻辑作用的结果。二是基层政府遵循行政逻辑导向晋升锦标赛,脱贫户遵循经济理性逻辑,以弱者的武器要求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村干部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信息的平衡点,算账结果是多方主体的平衡点,而非精准数据。针对国家获取返贫监测信息模糊化的结果,需要找回精准信息。对于基层政府,需要超越其行政逻辑的工具理性,强化价值理性;对于村干部,需要健全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公开化,约束其自由裁量权与实践逻辑;对于脱贫户,通过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塑造道义小农,弱化农民的经济理性,以实现国家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化需求。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国家逻辑纳入分析框架,但重点探讨了基层政府、脱贫户与村干部之间的逻辑互动,对国家逻辑如何与基层政府、脱贫户与村干部的逻辑进行互动还有待以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