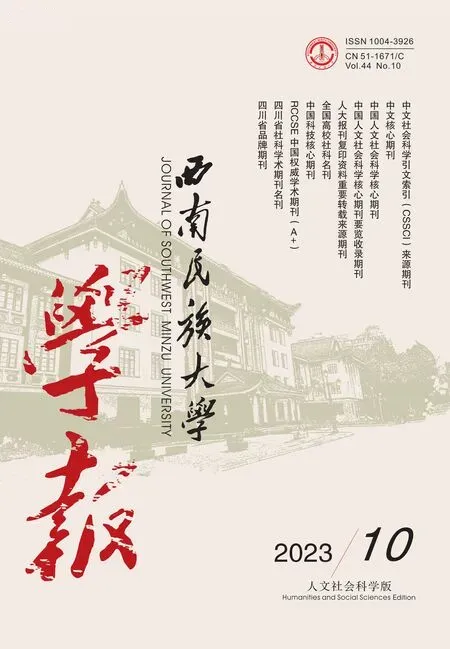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庞国华 谢晗孛 肖子敬
[提要]马王堆汉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大体概括为历史哲学文化、天文地理文化、饮食文化、服饰纹样文化、色彩图案文化等,涉及考古学、社会学、医学、美学、手工制造业等多学科。作为考古重要发现,出土的漆器是汉代漆器装饰的重要代表,其文化价值显著,主要体现在装饰语言的应用之中。本文从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延伸至装饰语言的内在规律和外化表达,以探讨其装饰语言的特征和规律,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具有八千多年历史的漆艺术提供参考和借鉴,以此凸显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引言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增添了新的素材,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瑰宝。在多年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中,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和研究极大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内涵的了解和传承。其中墓室建筑、壁画艺术、生活配件等方面的发现,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古代的生产、生活、文化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也为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文化旅游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马王堆汉墓也成为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长沙马王堆1、3号汉墓出土700多件漆器,数量之多、艺术水准之高令人惊叹,由此可见汉初的漆器文化之繁盛。汉代漆器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大高峰,以至于产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陈直在《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中说道:“两汉人对漆器的重视,比铜器要高几倍,器具之可以漆制的,无不做成漆器。”[1]据《盐铁论》记载:漆器乃汉代人“养生送终之具也”,汉代人在生活中和死后都要享用漆器,对漆器的普遍追捧造就了产业的兴盛,并从根本上推动了工艺技法的成熟与革新。汉代在继承战国的漆器工艺后又有很大的发展,产业规模颇为可观。其文化脉络也自战国发展而来,对楚地文化的承袭构成了其文化与装饰语言的主要特征,并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文化,形成新的文化面貌与装饰形态。
得益于大漆优越的材料性能,这些漆器虽已深埋地下两千年,但出土依旧光洁如新、色彩绚丽。马王堆出土了漆制的鼎、匕、盒、壶、钫、卮、耳杯、盘、奁、案、几和屏风等漆器[2](P.51),既有生活所用的实用器,也有墓葬器,虽功能有所不同,但文化内涵高度统一。
在战国时期,长沙位于楚国地界内,秦朝时期叫作长沙郡,汉初长沙王的封国也位于此。汉楚本为一家,且秦朝统治极为短暂,对楚文化的面貌没有太多的影响,故此汉初文化与楚文化有着很高的重合性。秦汉时期的思想与文化融合却也得益于秦的大一统,增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楚文化也就此吸收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外来文化,融合到自身的文化之中。
楚文化浪漫且神秘,想象力极为丰富,楚巫文化是楚文化的底色,因此楚地装饰中对神灵、神兽、永生等题材多有涉猎。汉初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加之对道教的崇拜,由此在漆器上形成了诸多神怪形象、升仙场景等装饰内容,这些文化在墓葬器的功能追求中也得以体现。虽从楚到汉经历了秦朝的统治,但由于秦政权存在的时间太短,对楚文化到汉文化的延续没有造成明显的改变。从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可领略汉初的审美,从实用漆器的功能中还原汉代生活图景,并从墓葬品的图案中探寻汉朝的墓葬文化与死后转生、升仙和追求永生的一系列幻想世界,是研究汉代文化、生活、观念的重要文物。马王堆漆器的墓葬品还包含棺、椁、木俑以及漆兵器等,品类很广。从漆胎来看,材质除木以外,夹纻胎的运用已十分成熟,造就了许多轻巧精美的漆器。从功能上看,礼教与祭祀作用减弱,实用性增强,这是汉代与从对前朝漆器的传承中,根据时代变化创新的设计。“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览中展出的双层九子漆奁、漆钟、漆钫等均为先秦墓葬所未见的新品类[3]。
汉高祖五年设立长沙国,定都于临湘,长沙首次成为诸侯国的都城。在建立都城之前,长沙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营造了较好的经商环境,各地商人与手工业者来往于此,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漆器取材珍贵、工巧时长,卖价不低,漆器产业的繁荣与否可以映射出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私营漆器作坊的存在也证明了此时漆器市场广阔,消费能力强,足可见该地区经济发达。其次,漆器带有很高的审美与文化属性,漆器市场的繁荣也反映出精神与文化的高度。经济是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石。从这些现象来看,长沙的文化与经济之繁盛可见一斑。另外,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与“漆”有关的记载,当时的漆工崇拜“漆王”[4],也从侧面印证了长沙漆器产业非常兴旺。
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马王堆的研究分布于帛书、帛画、漆器、图式、墓葬文化等方向,其中对漆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与艺术两个角度。
其中,以文化研究类数量最多,主要是概述马王堆文物的出土情况,记录并描述其造型、纹饰或功能,以此对汉朝的生活与墓葬文化进行文史、考古、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陈建明、聂菲主编的《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分三册详细讨论了马王堆汉墓漆器类型、铭拓释读、遣册考释等问题,并附文物检测分析报告,对马王堆汉墓漆器所涉及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一书收录了马王堆三座汉墓出土的髹漆工艺制品,既有生活所用的漆器,又包括棺椁、木俑等墓葬器,同时还有乐器与各种杂器,该著作对马王堆漆器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研究、图像艺术分析以及髹漆工艺和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这两部著作非常全面地记载、研究了马王堆出土的漆制品,从文史、考古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总览马王堆漆器的全貌。
另外一类是以艺术学为切入点,以对器物的装饰形式、图案内容的表现为重点,研究器物的空间表现与功能、图式、题材等视觉表现的方法论。代表性较强的有:贺西林在《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棺画与帛画》一文中研究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绘画的构图、象征意义和功能,得出从四层套棺由外到内再至帛画形成的不同空间、时间的结论,研究其表达形式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姜生的文章《马王堆一号汉墓四重棺与死后仙化程序考》也从重重棺椁与帛画图像之间的关系与象征意义入手,阐释其时空变化关系与象征,以及整个套棺对死后尸解成仙过程的完美表达。杨惠婷在《马王堆汉墓漆器所见狸猫纹初探》与《马王堆汉墓狸猫纹漆器相关图像续探》两篇文章中以马王堆漆器装饰中的图像为线索,观察、研究其图像,并对相关的寓意与文化背景进行探究。这些研究成果聚焦于马王堆漆器中的典型案例,从图像与艺术形式的表达、寓意等方面进行探究,并以点带面,以此进行当时墓葬观念的文化研究。在艺术学领域中,多有设计学方向的研究对其装饰的规律进行归纳,或将其中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如:陈剑在《马王堆漆器的纹饰构成法》、《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初探》、《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再探》三篇文章中对纹饰的构成规律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在现代设计中可转化使用的设计法则,将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转化到当代设计中,使文脉在当代延续。另有夏宾、张仲凤合著的《马王堆漆器云气纹在新中式家具中的应用研究》,将云气纹转化到当代的新中式家具中。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转化研究,多以马王堆漆器的纹饰、构成等装饰语言转化至当代的设计应用为方向,偏重应用性,但理论性与文化研究的深度普遍不足。
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实则为一个整体,通常研究图式和题材的目的是剖析汉代人在墓葬文化中的精神诉求与生死观念。而应用研究的路径则较为单一,是从事将汉代漆器技法转化到现代设计的应用研究,转化内容比较直接,都是从视觉到视觉的转化,较少从文化和发展的脉络出发形成跨文化和视觉艺术的综合研究。因此,本文从马王堆漆器文化到装饰语言进行梳理,追求更深层次的价值转化。
二、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
(一)文化价值的体现——装饰语言应用
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在当今的设计中体现为对装饰语言的应用。
“装饰”一词在《辞源》中解为 :“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加以文采也。”[5](P.13)此为字面意义的解释。放置于艺术实践的范围中解读,“装饰”是以美化与表现为目的艺术工作,“装饰语言”的定义比“装饰”更加精准,特指某一艺术形式的独特表现力。在马王堆漆器上,工匠利用天然漆在器物表面通过添加纹饰、色彩等方式达成美化的目的,部分墓葬器通过图案构成表现汉代人对升仙、永生的追求。这些时代特征鲜明、美学特征突出、材料特性优越的漆器装饰艺术以其特有的表现力构建了马王堆漆器的装饰语言。
马王堆漆器装饰语言有着设计性的内在规律,在图案构成上形成独特的表现特质,同时又通过漆艺的色彩、线性、贴饰等方面将设计内容外化,两者合二为一,形成装饰语言。装饰语言通过对图案和构成进行研究,延伸至漆艺的外化表现,以点带面,究其内涵,使马王堆漆器的文化价值凸显出来。
(二)设计——装饰语言的内在规律
从功能上划分,马王堆出土的漆器有实用器与墓葬器两大类。实用器装饰多以瑞兽、动物、抽象纹样等作为图案构成的基本题材,为满足赏玩意趣和装饰性而设计。墓葬器的装饰则以表达永生的欲望为目的,绘制各类神兽、仙人的形象对墓主人的灵魂进行守护或引导,主要展示汉代人对死后的世界的幻想内容。虽两类器物装饰图案与功能有所不同,但其内在规律是互通的,是由于汉代漆器已经发展至很高水准,拥有成熟的面貌,设计工作是在汉代装饰的程式中展开的,不为设计的类型不同所改变。
马王堆漆器的图案由具体图像和抽象纹饰构成。具体图像内容为再现或想象场景,抽象纹饰填补画面空白,并对色块进行分割和起到视觉引导的作用,各有表现与装饰的意图。在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常用多种图案构成整体画面,表现空间、时间等多个维度。
由于秦汉统治者多喜长生、升仙,此时的人们从楚文化好鬼崇神中逐步转向对道教文化的尊崇。马王堆墓葬漆器中的典型代表——朱地彩绘漆棺的头档上绘有腾跃的白鹿和云间的高山(图1),这座高山学界认为是昆仑山。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篇》:“昆仑之丘,登之而不死”。云上的空间符合汉代人想象中的天界,也就认为高耸入云的昆仑山是人间通往天界的途径,在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出现的意图很明显,正是希望墓主人死后可位列仙班,得以永生。此类题材的图案在马王堆的墓葬漆器中运用广泛。

图1 朱地彩绘漆棺的头档(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龙”与“凤”自古就被中华民族尊崇并膜拜,马王堆漆器中龙凤图案多有应用,尤其是凤鸟纹,在汉初广受追捧,图案运用广泛。凤的雏形早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已经出现,经过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汉代在凤的装饰中更加秀丽轻巧,更具灵气,正是受到楚文化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所影响,并且彩绘技巧更加纯熟。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已出现龙纹,形态几经变化,到了汉朝初期,龙形仍旧与蛇形的重合度比较高,但已有兽头、龙须、龙鳞、短角等显著特征,周围常伴随着云纹,象征着地位至高无上。在汉代,人们对凤的尊崇和喜好似乎比龙更甚。
从《后汉书·礼仪志》:“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可见云气纹在当时不是寻常人等可用之纹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云气纹是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大量使用的线性图案,通常伴随着龙凤、神兽一同出现,不仅有装饰意趣,更有表达所处空间的意图。云气纹的线条粗细变化强烈,组合灵活,在表现天地空间的同时也对画面起到分割和引导的作用。出土于马王堆的朱地彩绘漆棺(图2、图3)与《礼仪志》描述的特征相符,整体髹朱红漆,并加以云气纹装饰,其间穿插各神兽,意在护佑墓主人之魂免遭邪魅侵扰。

图2 朱地彩绘漆棺(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图3 朱地彩绘漆棺细节(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马王堆漆器装饰图案的题材多是汉代人幻想之产物,但其视觉形象多与现实物象相关,从现实的走兽、飞鸟中幻化而出,在楚文化的浪漫幻想与传说中构建马王堆装饰图案的基本内容。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土狸纹漆盘和凤鸟纹漆盒的构成方式在马王堆漆器中具有经典的代表性。这两件漆器在设计上利用“三足鼎立”式的构成方式,对狸、凤图案单体进行重构,在动物的动感中构成设计的平衡性,使图案稳重得体。图案的构成语言中,同一元素的复制性重构提供了稳定的视觉效果,连同对称与均衡构成法则的使用,形成马王堆漆器装饰语言的基础特性——稳定庄重。
如果说稳定庄重的构成语言为马王堆漆器装饰的设计奠定了基调,稳中求变则是将马王堆漆器从功能性器物升华为艺术品的关键。以黑地彩绘棺为例,在云气纹之间穿插着灵动的人形,动态强烈,随云而动,或向前奔跑,或身体后倾。上文提到的锥画图案也是如此,人与兽追逐奔袭,动作幅度强烈,肢体伸展至极,产生强烈的艺术张力。这些非对称性的、具有动感的图案则构成图案的生动性与韵律感。若是单有稳定而无韵律,则如同音乐中只敢用和弦内音反复弹奏,虽不出错但不免令人烦闷。稳中求变的构成语言是马王堆漆器装饰的突出特点。马王堆黑地彩绘棺(图4)装饰中云气纹的构成接近黄金比例的分割,但比西方“黄金比例”的提出早了一千多年,可见此时拥有高度成熟的构成法则,是工匠们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的构成定律。图案构成的首要问题是对元素的位置进行安排,马王堆漆器中的分割比例运用即是装饰的典型图案构成语言。

图4 黑地彩绘漆棺足挡(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图案构成的整体性设计思维是马王堆漆器装饰语言的一大特征,从局部的装饰图案到整体联系紧密,图案或对应或延伸或交缠,而非机械化地堆砌元素。我国现代文创设计中就时常出现元素照搬和堆砌的问题,图案没有考量与器型和功能的整体关系,图案各部分也没有关联性或互动性。马王堆漆器装饰语言中的整体性设计思维可以很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工艺——装饰语言的外化表达
漆器是以大漆对胎体进行髹涂与绘饰的工艺,其材料本色奠定了漆器整体的视觉效果,大漆色彩的稳重深邃是它的优势,但同时也是漆色之短板。调制色漆对入漆色粉极为挑剔,连同漆液本身色彩浓重等原因,相较于其它颜料,漆的色彩种类不算丰富。尤其是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可用的色彩不如后世多,但汉代的漆工们通过典型的色彩搭配构建了绚丽响亮的色彩语言。就马王堆出土的漆器来看,马王堆汉墓漆器的漆色包含黑色、朱红色、褐色、深棕色、金色、灰绿和白色等,以黑、红为主色调。
洪石在《战国秦汉漆器研究》中写道:“战国秦汉漆器一般外髹黑漆,内髹朱漆。”点明了这段历史上漆器最典型的色彩特征:由黑、红搭配构成主色调。虽至汉初器形、纹饰、色彩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战国时期漆器工艺的传承关系十分紧密。例如,马王堆漆器彩绘中所用明度较高的油彩,是用桐油代替漆液作为媒介调和色粉,后世漆工称之为“油饰”[6](P.76)。此技法在战国时期已有使用,只是尚处于探索期。到了汉代此技法趋于成熟,漆器装饰可用之色的数量大有提高,丰富了马王堆漆器的色彩语言。说明战国时期的漆工们已经认识到漆的色彩语言之局限,并在实践中试图拓宽其边界。
彩绘工艺在战国时已广泛运用,但绘饰精良的程度显然不如汉代。秦朝虽寿命短暂,但漆器生产数量不少,且写(刻)有产地或工匠(制造机构)的名字,显然拥有专业的漆器生产作坊,彩绘技法运用广泛。此时漆器的商品属性与经济价值都已经凸显,为汉代漆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根基。汉代彩绘仍旧是装饰的主流技法,马王堆漆器装饰中彩绘占据大半。战国时期的彩绘多用漆色,油饰工艺运用不算广泛。到了汉初由于产业规模的增长,对色彩丰富性的需求增大,油饰的运用与发展都大大提升。马王堆漆器的色彩语言相较于战国有了更丰富的面貌,但其主要色调没有太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以漆之本色——黑为主色,加以红、金等色装饰而成。
黑是漆之本色,也是最为素朴、本质的色彩语言。漆液初为乳白色,经与空气接触,逐渐转为深褐色接近黑,在漆中加入黑色色料或铁料可制成极致深邃的黑漆。漆之本色也决定了漆器多以黑为底色。马王堆漆器多以黑色髹其胎体,再加以装饰。黑漆深邃的质感带来极致的空间感,对追求神秘、庄重、稳定的视觉效果有着难以替代的材料特质。
漆液经过精制可得到半透明、黄褐色的透明漆。透明漆用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于金银箔上罩漆以隔绝空气,延缓金属氧化变色;二是与色料调和制成色漆,但由于天然大漆中含有漆酸,对入漆色料极为挑剔,若是色料中含有锌、钡、铅、铜、铁、钙、钠、钾等金属,遇漆则变暗甚至发黑。透明漆无论如何制作,始终带有黄褐色,无论是罩漆还是色漆的调制都会受到漆自身色彩的影响,也决定了漆深沉厚重的色彩语言。桐油可代替漆调制更明亮的色彩,在马王堆漆器中也多有运用,但多为点缀色,并无大面积髹涂的用法,对黑红搭配的主色调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汉初对朱红的喜好很可能与刘邦自认为是“赤帝之子”有着莫大的联系[3]。朱红色一般是用透明漆加入银朱(硫化汞)制成,天然银朱又名丹砂或辰砂,因盛产自湖南辰州(即今辰溪)而得名[7](P.4)。朱红是汉初漆器除了黑色以外运用最多的色彩,一红一黑奠定了马王堆漆器的面目。天然银朱入漆色彩鲜艳但不失沉稳,在马王堆漆器中与黑相称,以线绘之,在庄重沉稳的黑色之上形成灵动飞舞的朱红色漆线,将稳中求变的构成进行外化表达。
大漆黏性极佳,可作为黏合剂将其它材料贴敷在漆器上,极大地丰富了漆器装饰的色彩语言。众多材料中,金银的价值最为贵重,为权贵所追捧,因此在漆器中粘贴金银箔、片、粉是最常见的。金的性质稳定,不易变色,与千年不腐的漆是绝配。用金银片裁切出图案贴饰在漆器上的“金银平脱”和以铜箍加固口沿和底部的“扣器”工艺都是漆器运用金属的代表性工艺,汉代在前朝基础上有所发展,制作更加精良。在红黑底色之上,金属的质感提升了视觉层次,同时也增强了装饰的色彩语言层次。
除了红黑金经典三色之外,灰绿色也运用较多,常用于与暖色的金和红产生色彩对比。可见汉初的漆工已通晓色彩冷暖对比产生响亮感的作用,相较于西方美术史中运用冷暖色彩对比早了一千多年。绿色色粉入漆产生绿“灰”色是由于漆的本色性暖,棕褐色的漆液对冷色的绿色粉调和产生了降低纯度的效果。从色彩语言构建的角度来看,绿灰色在以暖色为主导的装饰中扮演好配角,起到丰富视觉层次的作用,同时避免喧宾夺主、色调混乱。除上述各色以外,其它色彩在装饰中只用于绘制线条而不会作为大面积的底色使用,同样是为了构建端庄稳重且色彩鲜明的装饰语言。
马王堆漆器典型的色彩语言主要为黑红相衬,通过配置底色、线条色彩、色块的位置与比例,构建响亮的色彩关系。其中,底色为黑色居多,漆黑具有强烈的空间纵深感,能够将色彩、线条、图案更强烈地映衬出来,同时也符合马王堆漆器追求庄重与神秘的视觉效果的需要。
史仲文主编的《中国艺术史·秦汉工艺美术》有此概述:“秦汉漆器装饰艺术是线的艺术,漆赋予线以个性,线又赋予漆以艺术生命,线成为漆器装饰的基本语言和主要的艺术形态,如行云流水转折不滞,粗细兼容刚柔相济,创造了一个遒劲古逸、舒展自如的‘线’的艺术世界。”[8]汉初漆器的线条弹性张力俱佳,粗细变化强烈,如同楚舞装束——细腰、长袖在舞蹈时翻飞回转之势。楚舞的灵动性与形体张力构建起楚人的艺术观与审美取向,从袅袅长袖、纤纤细腰、飘绕萦回的楚舞视觉特征来看,与汉初马王堆漆器的装饰在审美上是共通的。
作为汉初经典的视觉艺术载体,马王堆漆器装饰用线之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大高峰,漆工艺技法主要包括彩绘、堆塑、锥画等。
彩绘工艺在马王堆漆器中运用最广,漆工用弹性强的毛笔蘸取漆液,在漆胎表面直接绘制线条组成图案。彩绘线条灵活多变,圆润柔和,此技法在楚漆器中已有广泛使用。时至汉初,漆器装饰技法更加成熟,无论是线条的流畅度、弹性、张力都大有提高。马王堆漆器绘制用笔富于变化,有倒、顺、顿和甩等笔法运用。马王堆漆器彩绘中的线条与色块相辅相成,线韵律生动、细节丰富,色块提升色彩与明暗的表现,两者相合,视觉层次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马王堆漆器中的锥画工艺沿袭了战国的针刻纹漆器工艺,但技巧的精致度大有提高。锥画即是在漆膜刻划形成凹陷,以刀(针)代笔刻画线条,可做到线若游丝。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锥画狩猎纹漆奁(图5),将兽、人、云气纹等图案刻划在漆面上,人兽的追逐场面动感十足,周围环绕云气纹等装饰形成流动性的边缘,构成上追求动感。与3号墓的锥画狩猎纹技法稍有不同的是,马王堆1号墓所用的锥画技法在刻划后的凹槽内填入色漆,使线条更加鲜明,在线性语言的表现下丰富了色彩语言。后世在此技法之上加入了金银粉的使用,在刻划的凹陷处填入金粉,也就形成了《髹饰录》中所称的“戗金”技法。锥画的线性语言与所用工具和工匠的技巧直接相关。汉代的金属锻造技术发达,工具的进步与产业规模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汉代锥画的发展,在马王堆漆器中有着成熟的运用实例。或许是源于汉初金属工艺的发展,使工具的锋利度更佳,同时,也得益于当时漆器产业的繁盛,刻划的工具与漆工技巧都得以进步,为马王堆漆器装饰中的锥画对战国针刻纹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图5 锥画狩猎纹漆奁(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堆塑工艺的运用在马王堆漆器中也并不鲜见,这是汉初漆工们的创新技法。堆塑是通过在漆中调入其它物质(如蛋清、粉末等)提升漆线的厚度,使之在胎体上形成立体线条,然后再进行彩绘,形成线面结合的装饰形态。在马王堆漆器中,堆塑通常用于提升云气纹、兽眼、爪或手脚等局部细节,增强空间层次,引导观者的视点往堆起的细节处聚焦。马王堆1号汉墓的黑地彩绘棺(图6)和3号汉墓的粉彩云气纹长方形漆奁都是堆塑后再进行彩绘的,线条的立体感强,装饰意味浓厚。汉初的堆塑开创先河,后发展为我国漆器装饰工艺的主要装饰语言之一,《髹饰录》称“堆起”和“阳识”。

图6 黑地彩绘棺堆堆塑(图片来自《马王堆汉墓文物》)
漆的黏性卓越,故此有“如胶似漆”一词。漆器相较于中国画或西方的油画、水彩的材料复合性更高,是源于漆液将干未干之时黏性极佳,可粘贴金银、鸟羽、织物等其它材料丰富装饰语言。早在战国时期,漆工就已认识到漆色的局限,探索使用桐油调色、发展金银平脱、扣器等综合技法运用,漆与油彩、金属的质感相得益彰,产生新的视觉效果。这是材料语言拓展的初步探索。马王堆漆器中对复合性的材料语言有许多运用实例。
汉初漆器产业的壮大就在此时代背景中对漆器装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王堆出土的四棺套叠,与文献所云“棺撑必重”“棺撑数袭”相符,证明墓主人身份高贵,可能是诸侯。四棺之中,三具有华贵繁复的装饰。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贴铺绒和羽毛贴花绢[9]。这种装饰的木棺,迄今还是第一次发现。马王堆汉墓中的贴羽、裱绫等做法效果绚丽,借鸟羽或织物绚烂的色彩和质感,对漆的材料语言进一步拓展,将其它材料的视觉效果吸纳进漆器装饰语言中。
三、结语
装饰语言的应用是马王堆漆器的重要文化价值体现,装饰语言由内在的设计规律、外化的漆艺表现组成,图案构成的设计性与漆的色彩表达、线性表达、工艺技法等多方面融合的设计程式,是在汉初文化与漆器产业的催化下不断实践生成的高度概括凝练的设计法则,也反映出汉初文化的基本面貌。
马王堆漆器的设计程式与工艺技法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支撑,可见其“以用为美”的文化追求,装饰反映生活意趣,与当代设计的内核完全一致:通过设计概括、凝练或总结出美的程式,再通过生产方式将其实用之美进行外化,由器物装饰承载时代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服务于人,落脚于生活,达到装饰与人、设计与人、时代与人、生活与人多维度的融合,使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当代得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