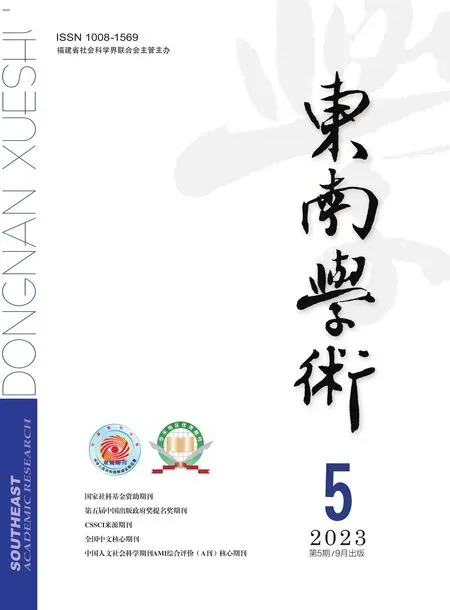“独尊儒术”新批判:今古辨异与董仲舒之真意
郑济洲
在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潮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学界概括董仲舒在汉武之世贤良对策的典型表述。学人对这一表述的认知,更多是在消极意义上评价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通过重构汉代政治秩序所造成的汉代以及后世王朝的政治专制。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成为学者和大众约定俗成的一种定见的背景下,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对这一表述进行分析性的批判。①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南京社会科学》1993 年第6 期。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辩》,《孔子研究》2000 年第4 期。秦进才:《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系新探》,《衡水学院学报》2020 年第5 期。近四十年来,学界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话语真伪、提出背景、思想本意等问题仍存辩争。②丁四新:《近四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三个阶段》,《衡水学院学报》2019 年第3 期。多数学者未能有效辨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国策“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①司马迁:《史记》第10 册,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224 页。的关系,且未能充分认识到从汉至清“独尊儒术”的话语仅在宋朝的《鄮峰真隐漫录》出现一次,②史浩:《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765 页下栏。这一事实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话语的成立造成合法性冲击。本文在挖掘、梳理从晋朝到清朝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比较近代“反专制”思潮中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古代话语“原型”的差异,论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指称时间、内容的差异,从“《春秋》为汉制法”的汉代历史背景走进董仲舒重构汉代政治秩序的思想旨趣。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近代的提出与今古之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话语表述是在近代“反专制”的思潮中出场的。1910 年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绪论”中指出:“我国伦理学说,发轫于周季。其时儒墨道法,众家并兴。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言始为我国惟一之伦理学。”③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绪论》,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6 页。他用史学智识对汉代儒家制度化所造成的中华民族伦理的塑形作出了阐释。在1934 年刊发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蔡元培又从追求自由、独立的学术思想的价值取向批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④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503 页。蔡元培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话语的提出者,其学术思想的取向之一是以开放的政治、学术生态取代具有专制色彩的“独尊儒术”。在他的古史认识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具有同等的内涵。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话语,而“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的连用是蔡元培的创造。纵观历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话语呈现和褒贬旨趣上存在着巨大的今古差异。
从话语呈现来看,“独尊儒术”作为近代的强势话语,在民国以前的史料文献中仅出现在南宋史浩撰写的《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之中:“下陋释老,独尊儒术。”⑤史浩:《谢得旨就禁中排当札子》,《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765 页下栏。其话语背景与宋代儒家排佛抑老紧密相关。正是由于“独尊儒术”所指称的内容与汉武帝时期的国策并不相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用法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班固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概括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的谏言,成为汉代以降学人们共享的话语,促成“独尊孔子”“独尊孔氏”等话语屡见古史。明代章潢在《图书编》中指出,《孟子》“七篇尊王贱霸辟杨墨为异端,独尊孔子正学”,⑥章潢:《三纲五常总叙》,《图书编》卷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02 页下栏。从非异端、主正学的角度提到了“独尊孔子”。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言:“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⑦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58-1059 页。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从“经术取士”的角度认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现实功用。清代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有言:“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性鉴正史》而外,不列于学宫,不用以课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盖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此所谓圣真,此所谓王制也。”①孙承泽:《正士习》,《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645 页上栏。基于上述,古人对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及其所衍生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等话语有一个内涵共识,即古代王朝通过运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学统一国家的“经术取士”。
以蔡元培所见,“独尊儒术”必然造成政治专制,但古人以“经术取士”的观点认知“独尊孔氏”,其政治旨归恰恰不是专制,而是“士治”(“贤治”)。《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汉武帝“力本任贤”的政治诉求,②班固:《汉书》第8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507、2513 页。董仲舒则回应:“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③班固:《汉书》第8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2507、2513 页。董仲舒的贤良对策贯穿着贤能佐职的理想,在他推崇官僚政治秩序中存在着君主与臣下的良性互动。基于汉代儒家制度化的现实,钱穆先生曾把汉武帝时期的政府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④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94 页。这符合汉代儒家制度化的历史现实。在古人看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内聚着汉代以降官僚体制的“士治”沿革,潜藏着士人参与国事的政治机遇。
从褒贬旨趣来看,古人往往从肯定的层面来认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与近代学人“反专制”思潮中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宋代林駉曾指出:“董仲舒推明孔氏,力挽正学。清净之说方息,而贤良之科始盛;百氏之术既罢,而六经之学益彰。文章彬彬,焕然有三代之风者,董氏之力也。”⑤林駉:《排异端》,《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85 页下栏。以此颂扬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为汉帝国所用,并促成儒家之学的兴盛。古代士大夫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视为汉武帝推进儒家制度化的宝贵历史经验,明代程敏政在《明文衡》中论及明成祖时期:“今天子以神圣英武之资,龙飞江左,扫荡群雄,不数年而天下定于一。乃罢黜百家,一用纯儒。岂非世道之将隆,斯文之大幸,而为儒者所宜致思乎!”⑥朱同:《舟行分韵赋诗序》,《明文衡》卷四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649 页上栏。清顺治年间也曾仿效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国策,《御定孝经衍义》有记:“儒臣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颁行两京六部及国子监、天下郡县学,庶几于汉之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功矣!”⑦爱新觉罗·玄烨:《天子之孝·崇圣学》,《御定孝经衍义》卷五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146 页下栏-147 页上栏。清代张廷玉、梁诗在《皇清文颖》载韩菼所撰《乙卯顺天乡试策问五道》,其中用“表章正学,罢黜百家”来颂扬康熙皇帝在“扶正道统”方面的积极作为。⑧韩菼:《乙卯顺天乡试策问五道》,《皇清文颖》卷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794 页上栏。
相较于古代学人对“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总体肯定,近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谓激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抨击了孔教一元所造成的政治独裁与学术专制,“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86 页。在追求“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中,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也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出了心绪难平的议论:“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①易白沙:《孔子平议》上,《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人民出版社1916 年影印本。在近代追求政治变革的知识分子看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代表着古代的帝制集权和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对皇权的依附。因此,这一话语在近代的高扬,既是对古代王朝的批判,也是对自身政治追求的表达。
在近代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思想体系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代表的不仅是崇尚政治与学术专制的汉武帝、董仲舒,而且被固化为反民主的古代中国和孔子思想。20 世纪以来,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学界、大众耳熟能详的一个惯用指称之时,鲜有学者注意到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并没有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推行政治与学术的专制,而是如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所记载的“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②司马迁:《史记》第10 册,第3224 页。质言之,汉武帝对于百家之学并未罢黜,而是以一种开明的学术格局推进社会思潮的开放。有鉴于此,吕思勉提到:“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靡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③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690 页。纵观汉朝及以后的历史,无一朝代曾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遂使百家之学得以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近代“反专制”的思潮无疑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然而面对着古今士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话语迥然有异的正、反认知,只有回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历史原点,才能真正认识其中的真意。
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指称事件的不同
近代以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话语渐强的趋势下,也有诸多学人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认为:“他的所谓‘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指的是不为六艺以外的学说立博士而言。”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3 页。徐复观坚持认为汉武帝与董仲舒对策后所推行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只是在博士官的人才筛选范围内实现儒家的纯化,绝非在官僚体制和国家学术层面的“独尊儒术”。他的观点在近代批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浪潮中无疑是一股“清流”,但仍不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留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推敲。
《汉书·武帝纪》中提到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前136 年)“置五经博士”,⑤班固:《汉书》第1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726 页。而在赞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如果班固所谓的“表章六经”就是汉武帝在即位五年之后的“置五经博士”,那么如何理解“孝武初立”这一具有执政之始推进政策的表述? 如果“表章六经”的国策意图早于“置五经博士”,那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治内涵必有他指,“置五经博士”的政策变革只是“表章六经”的一个政策衍生,而绝不是“表章六经”本身。更何况,从《汉书》的记载来看,“表章六经”与“置五经博士”在对儒家经典的表章数量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由此延伸出第二个问题,汉武帝时期所推进的儒家制度化,仅仅是“置五经博士”吗? 如果仅仅从“博士官”人才选拔的层面理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难免陷入以微观理释宏观政策的诠释难境。
事实上,徐复观对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研究存在一个疏漏,即混同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发生时间。从可供探赜的历史文本出发,“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汉代儒家制度化进程中依循递进的两个历史事件,前者的历史节点是建元元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40 年—公元前135 年),其指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重用儒臣的政策实绩;后者则是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董仲舒在汉武帝新政的基础上,面对历史和当时的政治问题,意欲实现“《春秋》为汉制法”,①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310 页。继而在治道与人事上构建儒家式的“大一统”汉帝国。董仲舒与汉武帝的政治主张虽然紧密联系,但在义理上有区别。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为汉武帝时期的一个重要国策,其起始时间是在建元元年,其发生背景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初有意重构汉代的政治秩序,用追求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取代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治国之术。汉武帝在即位伊始就接受了丞相卫绾的奏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②班固:《汉书》第1 册,第156、157 页。汉武帝重构汉帝国政治秩序的意图被班固称颂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中“罢黜百家”旨在对当时新举贤良中具有法家、黄老道家、纵横家等学派背景的士人的罢黜,而“表章六经”是通过表章儒家六经之学、重用儒臣,实现汉帝国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汉武帝的少年才识广为后世士人称道,元代胡一桂有言:“帝以少年英锐之姿,雄才大略得于所禀,即位之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又招选天下文学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史称其得人之盛。”③胡一桂:《史纂通要》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01 页下栏。在汉武帝与卫绾的共同推进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④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25、2202 页。为政府所吸纳的儒家“贤良”具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汉书·公孙弘传》载“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⑤司马迁:《史记》第10 册,第2949 页。公孙弘以花甲之年、白衣之身,尤能为博士之官为朝政谏言,可见当时“隆儒”之盛。
然而,汉武帝和众儒臣在推进政治秩序更化中受到了以窦太后为首的崇尚黄老之学的保守派的抵制。在政治的斗争中,卫绾受到朝中黄老派的诋毁,“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故者,而君不任职”,⑥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25、2202 页。终被罢免了丞相的职务,改革派中的“丞相婴、太尉蚡免”。⑦班固:《汉书》第1 册,第156、157 页。从建元元年至建元五年,汉武帝始终处于窦太后的权力掣肘之中。直到建元五年窦太后病逝,汉武帝实质主政,重启田蚡为丞相推进儒家新政,才重新推进汉帝国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置五经博士”所实现的博士官儒家化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经历早期挫折后的第一个重大实绩。“置五经博士”促进了士人开始专注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并形成了学人从儒家学说进行咨政的风向。建元六年,汉武帝支持田蚡“黜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⑧班固:《汉书》第9 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593 页。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重用儒臣,在人事层面积极推进汉代官僚队伍的儒家主体化。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之末申明:“《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术,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23、2505、2525 页。这一谏言被班固概括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发生时间和指涉事件上不同。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今临朝而愿治七十余岁矣”,②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23、2505、2525 页。已经提出一个学界普遍认可地考证,董仲舒的贤良对策的产生时间应当为元光元年,而非建元元年。③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224-225 页。
汉代以降的诸多学人都混淆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时间关系,没有清晰辨析二者的义理。元代郝经在《陵川集》写道:“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请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尊孔氏,明仁义,圣人之道,复立存人心于欲亡。”④郝经:《去鲁记》,《陵川集》卷二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81 页下栏-第282 页上栏。古代不少士人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作为驱动汉武帝隆儒的政治实践起点,忽略了事实上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制度化是汉武帝及其即位以来数名儒家政客、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宋代范祖禹在理解这段历史时同样存在认知的偏误:“汉武帝时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感其言,遂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⑤范祖禹:《封还差道士陈景元校道书事状》,《范太史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65 页下栏。在思想史的传承中,存在着一条对汉武帝和董仲舒推进儒家制度化进程的时间和话语的误解。
考察历史上的部分学人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混用,极有可能是没有辨析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谓的“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⑥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23、2505、2525 页。从班固“及仲舒对策”的表述可以洞察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发生时间与“武帝初立”存在时间差异,董仲舒政治思想的一个客观实践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而并不如部分学人所认识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⑦归有光:《河南策问对二道》,《震川别集》卷二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482 页下栏。董仲舒所建议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儒家制度化层面上有系统思考,它在“《春秋》为汉制法”的顶层制度设计下,针对汉武帝在社会层面“悉延百端之学”提出一个建议,即推进儒家教化的普适化实现汉代官僚队伍的儒家一元化,由此在稳定的意识形态中为国家善治提供源源不断的儒家贤能。
虽然部分学人混淆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发生背景,但也有诸多学人对二者有清晰的界分。宋代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载晁说之的上奏言:“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策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⑧邵博:《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78 页下栏。此处明确将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政治贡献予以辨析。对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言,诸多学人都揭示其并非董仲舒的对策所推进的。宋苏籀在《双溪集》中有言:“观公孙,辅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儒术光明。时尚侈靡而务兵刑,事业浅陋。平津之说不甚用也,其言故不大验。”①苏籀:《见秦丞相第二书》,《双溪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200 页下栏。此处提到了公孙弘辅助汉推进武“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新政。清乾隆年间《御览经史讲义》中载有“崇重儒术”的言语:“嗣位之初,即慨然有意于唐虞三代之盛,崇重儒术,罢黜百家,将立明堂以宏制作,修礼乐以兴太平。首用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聘申公而问以治道。”②齐召南:《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御览经史讲义》卷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版,第668 页下栏。其中记载了汉武帝“崇重儒术”,在建元元年开始的举贤良对策中请教申培公“治乱之事”的历史典故。
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话语内容比较中,可以窥见汉武帝与董仲舒在儒家制度化方面的意识差异。于汉武帝而言,其致力推进汉帝国意识形态的改弦更张,但绝不秉持整个社会思潮一元化的倾向,而是在“百端之学”与“儒家之学”中保持一个平衡。“武帝的‘尊经’有兼容百家的意味,儒家在其中只是处于主导地位,而未受‘独尊’的地位。”③王葆珐:《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98、201 页。而董仲舒则在“抑黜百家”中展现了他要实现汉代官僚系统儒家一元化的意志。如果以近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来考察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政治设计,汉武帝更像是一个坚持政治开明、学术开放的执政者,而董仲舒却是一个追求学术专制的儒者。但是,从董仲舒的学术旨趣来探查,他虽专攻《春秋》学,但绝不是一个追求儒家学术专制的士人。④参见汪高鑫:《论董仲舒对墨子政治思想的吸取》,《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 年第4 期。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 年第11 期。白延辉:《董仲舒对黄老道家价值理念的吸收融合》,《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6 年第5 期。为了走进历史的真相,董仲舒在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的内在旨归成为了我们理解董仲舒政治哲思的关键。
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中“《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因包容而广大精微,但五四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话语的愈发强势,导致学界对汉代儒学研究抑而不张。虽然冯达文、余治平从汉代儒学的信仰建构、两汉经学等角度逐渐开辟汉代儒学的研究新域,⑤冯达文:《儒家系统的宇宙论及其变迁——董仲舒、张载、戴震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10 期。余治平:《“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但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汉代儒学的探赜仍然弱势。丁四新老师作为近年来从思想史视域辨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学者,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一文中致力从“反对专制”的角度对近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既定思维进行“破题”,促进学界对汉代儒家学术思想的正面价值的探讨。⑥丁四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孔子研究》2019 年第3 期。重新发现汉代儒家的学术思想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共同致力研究的场域,将董子之学与近代以来因袭成惯的“董学专制说”相隔离已渐成大势。美国学者桂思卓在《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从圣人之作、道德权威、监督力量、变革力量、预言力量五个维度,分析了董仲舒对《春秋》的解读为儒家士人抑制皇权提供了理论工具。①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7 页。以“董学制衡皇权说”来为董仲舒乃至汉代儒学翻案的学术思潮,其运思目的是在一种“否定之否定”中建构对汉代儒学的“肯定”,仍旧没能跳出近代“反专制”的问题意识。如果从《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的贤良对策的经典文本出发,可以发现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治理想的内在旨趣并非“支持专制”,也非“制衡君权”,而是在“《春秋》为汉制法”中重构汉代的政治秩序。
董仲舒学术根基在春秋公羊学,他对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在西汉初期可谓首屈一指,曾经私淑董仲舒的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明确的表述:“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②司马迁:《史记》第10 册,第3128 页。董仲舒所秉持的春秋公羊学以“究天人”“大一统”“王正月”“改正朔”“通三统”“别内外”“诛不肖”为主要内容。在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站在儒家托古改制的观点上指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③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05、2495、2496、2499、2501-2502 页。在他看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所实现的汉代官僚队伍儒家主体化并没有触及汉帝国政治制度本身,为了实现善治,必须依据《春秋》学实现对汉帝国系统性的改弦更张,其对策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王朝的永续发展来看,董仲舒贤良对策的第一策文记载了汉武帝“永惟万事之统”的政治诉求,④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05、2495、2496、2499、2501-2502 页。武帝虽然追慕“五帝三王之道”,但追忆周秦更替,不禁心生感慨:“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⑤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05、2495、2496、2499、2501-2502 页。在汉武帝推进汉帝国儒家制度化的进程中,汉武帝尤为担心汉帝国会发生“后王之法”对“先王之法”的颠覆性变革,以致儒家制度化的中断和王朝万事基业的倾覆。董仲舒对此的回应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⑥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05、2495、2496、2499、2501-2502 页。汉王朝在推进儒家制度化的进程中必须明确治之道,以《春秋》之文对王朝进行顶层设计,继而运用儒家内聚的仁义礼乐之术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董仲舒的理想政治蓝图是构建一个儒家式的“大一统”帝国,而指摘以秦政为模板的法家式“大一统”帝国是其谏言汉武帝改弦更张的关键。董仲舒根据《春秋》之文,探索王道的根源,依据“元年,春,王正月”⑦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6 页。阐释“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⑧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05、2495、2496、2499、2501-2502 页。将天之道视为王制的根本依据,视帝王因循天道、践行政德为帝国合法性的充要条件。
“先正王”是《春秋》经的核心内容之一,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⑨司马迁:《史记》第9 册,第3297 页。孔子通过托古改制的方式,将建构德性政治体的责任赋予执政者,执政者的德性优劣由政治体运行的好坏来评判。在这一制度的设计下,天下之人可根据天下之制,对执政者进行褒贬。董仲舒试图以孔子所作之《春秋》为汉王朝立法,以儒家的法制秩序规范汉王朝的政治秩序,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儒家之道德规范最高执政者的施策行为。
董仲舒对于最高执政者道德修养之重视,不仅源于自身作为儒家学人的学术认知,也基于他对于“大一统”模式的思考。秦朝在推行法家式“大一统”的国家建构中,的确改变了周末封邦建国所呈现的分崩离析,但其所呈现的政治秩序是最高执政者在专制下的“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①司马迁:《史记》第1 册,第278、282 页。其所推行的“连坐”刑罚造成了个体存在的原子化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秦朝二世之亡的一个汉儒共识是“仁义不施”,②司马迁:《史记》第1 册,第278、282 页。董仲舒赓续着先秦儒家所推崇的政德观念,将最高执政者之道德视为构建现世道德共同体的根本,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③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董仲舒将儒家所倡导之德贯穿于君主政德、贤能佐政与社会教化之中,其所坚持的《春秋》为汉立法不仅关乎国家之道德,而且关涉人性之良知。董仲舒以天道作为其政治理念的遵循,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认为现实的政治秩序安排必须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现实的政治秩序应是儒家式“大一统”的道德政制。
第二,从王朝的善治理想来看,汉武帝即位以来虽然致力推行“扶世导民”等儒家治国之术,④班固:《汉书》第1 册,第156 页。但在“隆儒”之策大行的背景下,仍然存在“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的现实难题。⑤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面对帝国的现实治理难题,董仲舒认为,王朝善治的基本条件是得贤任事,“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⑥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董仲舒不是一个支持政治专制的儒者,在倡导“大一统”的汉朝政治模式中,他主张君主在儒家“无为而治”理念下贤能“辅德佐职”。汉武帝曾经问:“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 何逸劳之疏也?”⑦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在古代的政治秩序中,君与臣的地位高下之别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国家之善治的一个重要实践是君臣的相互配合。董仲舒指出:“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⑧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350 页。在董仲舒看来,贤士与君主所构成的现实政治的施政的两个主要方面,君与臣的良性互动才能符合天道。
董仲舒也不应被界定为推崇学术专制,他的贤良对策是以一个儒者的身份对国家建设的建言献策,其所针对的是汉武之世的社会流弊。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⑨司马迁:《史记》第10 册,第3224 页。的决策造成了“师异道,人异术,百家殊方,指意不同”⑩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的社会现实,汉帝国在这一社会思潮中无法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而“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⑪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的秦政影响更是造成了社会伦理的失序。在董仲舒看来,如此混杂的官员思想和社会思想,必然影响汉武帝政治决策上的判断,同时造成社会舆论在多元化中存留着法家影响下的好利恶害的思想倾向。因此,董仲舒“抑黜百家”的提议旨在将汉帝国的官员从儒家主体化变为儒家一元化,让官员队伍不再掺杂进非儒家的人员,推行大一统的儒家德治。
第三,从王朝的制度损益来看,汉武帝困惑的是“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⑫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因此对王制进行因革损益是势所必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儒家之道并非永恒? 董仲舒的回答是:“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⑬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在公羊学家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⑭班固:《汉书》第8 册,2508、2507、2512、2506、2523、2510、2518、2518、2519 页。天子之权来源于天道,天子在历史发展中不能去改变天道,而必须根据天道所内设的政教秩序来“改正朔”。“改正朔”涉及公羊学家的“三统”之说,董仲舒指出:“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①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18、2519、2502-2503 页。夏、殷、周三代是春秋公羊学“通三统”思想中的三个朝代,公羊学家以“三统三正三色”来对应这三个朝代,董仲舒认为夏朝是正黑统,建寅(以一月为正月),色尚黑;殷朝是正白统,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月),色尚白;周朝是正赤统,建子(以十一月为正月),色尚赤。“通三统”强调新朝制度对旧朝的损益,正如蒋庆所说:“通三统是指王者在改制与治理天下时除依自己独有的一统外,还必须参照其他王者之统。”②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243 页。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一个季节和月份都有着特定的政教内容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教形式。社会生活通过君王依节令变化颁布的与自然协调一致的政教法令而有序地进行。自然运行与政治生活同步,物质生产与文明教化相资。人们在这样一种生活秩序中获得秩序感和意义感。董仲舒从天道规律和历史发展判断,“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③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18、2519、2502-2503 页。为汉武之世明确了制度损益的历史遵循。
此外,孙承泽对于“春秋大一统”的论述可作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一个注脚:“《春秋》大一统者,统于一世,统于圣真,则百家诸子无敢抗焉;统于王制,则卿大夫士庶无敢异焉。”④孙承泽:《正士习》,《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 册,第645 页上栏。从建构多元思潮的社会格局来看,汉武帝从建元元年到建元五年的新政相较于董仲舒更为开放,但从实现长治久安的帝国政治来看,董仲舒直面汉武帝“隆儒”政策的系统性缺憾,通过指摘以秦政为模板的法家式“大一统”的短寿,阐释汉帝国所因承续的儒家王制,推进了汉武时期的改正朔。董仲舒“《春秋》为汉制法”理念对于汉帝国的立法意义重大,并成为后世王朝更制的一个重要理论遵循。
结语
董仲舒之真意是通过推进儒家式“大一统”重构汉代的政治秩序,运用立太学、兴教化、进贤士等模式实现儒家德制下的国家善治。近代知识分子在“反专制”“倡民主”的思潮下批判董仲舒为政治与学术专制的附庸,实际上是用一种现代性的理念对古代政治思想的“误解”。回到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所处的秦汉更迭、儒法之争的历史背景,可以窥探他在“《春秋》为汉制法”中对帝王进行了德性制度的规范,他希望“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⑤班固:《汉书》第8 册,第2518、2519、2502-2503 页。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自成一套天人学说,他坚持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天道,而君权的合法性亦是上天赋予的,“天”对“天子”的制约通过爱君示警来实现。然而,天对天子的制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天子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对天的畏惧,这一中国古代因袭的皇权制约理论的最大漏洞就在于天的作用是要通过天子的“承认意识”才能够生效,天在现实政治中是“被动的”,它并没有变化成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来直接制约君权。从这一理念的漏洞来看,近代学人从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角度对董仲舒的批判对于开启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价值。在传统与现代的辨义中,董仲舒之真意具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他的贤良对策从理论上推进了汉代的儒家制度化,其所推崇的德性政制彰显了儒家文明践行仁政的积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