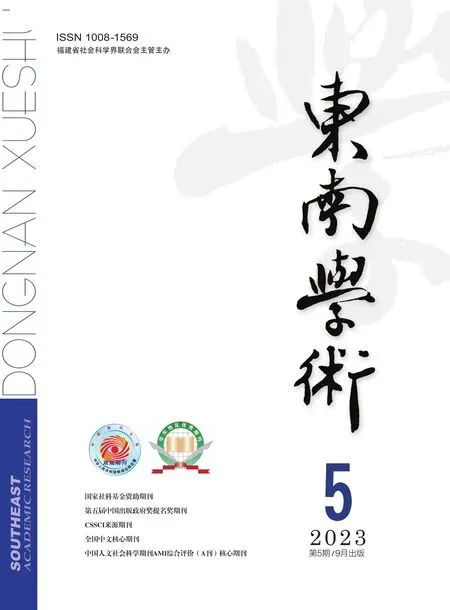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的形成、内容及其价值
——以MEGA2Ⅳ/1 为考察对象
杨宏伟 史文祺
近年来,西方所谓的“马克思学”在文献学语境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问题,经历了从“回到马克思”到抛出“恩格斯问题”的话语转向。如诺曼·莱文(Levine)和T.卡弗(Carver)等人都从文献考证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甚至认为马克思同恩格斯对立。在这一背景下,能否正确认识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要回应“恩格斯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础上“回到恩格斯”,而深入研究恩格斯早期思想和笔记是“回到恩格斯”的题中之义。相较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和笔记研究的“热”,学术界对恩格斯早期思想和笔记的关注明显不足,许多学者仅仅将之归为“传记材料”①如奥古斯特·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格姆科夫的《恩格斯传》、乌尔利希的《恩格斯的青年时代》等都以传记的形式反映了恩格斯早期资料与思想转变的关系,但缺乏对笔记的专门考察。而缺乏全面考察。MEGA2 第四部分第1 卷首次完整地收录了1842 年以前恩格斯撰写的两组摘录笔记,分别是爱北斐特中学学习时期留下的学习笔记和1841 年秋到1842 年秋服兵役期间的“新约圣经批判研究”(以下统称为《宗教批判笔记》)。
一、形成过程:从虔诚主义到青年黑格尔派
早期摘录笔记的形成是恩格斯对社会不断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是一个青年积累知识走出虔诚主义到青年德意志再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微观缩影”。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构成了恩格斯撰写早期摘录笔记的重要内驱动力,梳理早期笔记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对青年恩格斯成长发展进行全面回顾的过程。
恩格斯出生于巴门一个充斥着封建思想和宗教虔诚主义的普鲁士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恩格斯并未“随波逐流”,而是在其外祖父伯恩哈德·哈尔(Bernhard)的影响下对古希腊神话和古代历史中的英雄产生了浓厚兴趣和敬仰之情,②参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 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版。恩格斯在其诗作《献给我的外祖父》中就着重提到了忒修斯和阿尔古斯等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1834 年,恩格斯转入爱北斐特中学学习。爱北斐特中学是当时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与传统学校相比更为进步和开放,尤其强调学生在文学、历史、语言领域的学习。在那里,学生需要使用原文阅读古希腊文学和历史,因此恩格斯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也得以快速提高。③参见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中央编译局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在爱北斐特中学,教授古代史的是高级教师克劳森(Clawson)博士,他学识渊博且思想解放,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回忆的那样:“克劳森博士,第三个一级教员,他无疑是全校最能干的一个,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和文学。他的讲课非常动听;他是惟一善于启发学生们对诗的情感的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58 页。《历史笔记本Ⅰ·古代历史·公元前4000 年到公元前431 年》⑤根据笔记本的目录和教科书的讲授内容判断,还应有公元前431 年到希腊国家灭亡的第二个笔记本,然而这一笔记本没有保留下来。(以下简称《古代史学习笔记》)正是1835—1836 年期间恩格斯根据克劳森讲授的恩斯特·施米特(Ernst Schmidt)《中学古代史概论》教材所做的学习笔记。紧接着,恩格斯在1836 年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学,这门课程由艾希霍夫(Eichhoff)博士讲授,主要内容是修昔底德著作、柏拉图散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及欧里庇德斯的戏剧,⑥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936-937.《关于荷马〈伊利亚特〉的预习和评述》(以下简称《文学学习笔记》)正是恩格斯课前预习古希腊史诗和分析这些著作时留下的学习笔记。《文学学习笔记》展现了恩格斯两个学习重点:其一,提前预习了史诗正文,将上课所讲授的内容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写下了对《伊利亚特》的文学评论和部分解析;其二,借助文学文献加深对古希腊语语法和修辞的练习,提高语言水平。恩格斯高中时期学习笔记全面呈现了恩格斯借助书籍和资料奠定深厚历史和语言知识的过程,同时展现了一个勤学善思的青年恩格斯形象。总的来说,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中学的学习过程为其思想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正如高中肄业证书中对恩格斯中学时期取得成果所作的评价:“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无论是散文作家或诗人的作品……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整体的联系,清晰地掌握其思路,能熟练地把拉丁语课文译成德语……在全面发展方面获得可喜的进步。”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548、273 页
1838 年,恩格斯在父亲的要求下来到不来梅经商。由于中学时期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之对文学的喜爱和对自由精神的向往,恩格斯在诗歌创造上投入了更多精力并加入了“青年德意志”组织。在致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表明了对青年德意志的认可:“除了青年德意志以外,我们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142-143、224、276 页。随着时间的推移,恩格斯愈发渴望摆脱宗教和虔诚主义的束缚,时代观念在其心中激起了反叛与改变的欲望。恩格斯的朋友卡尔·哈斯(Haas)与阿道夫·舒茨(Schutts)的通信表明,1839 年起恩格斯便化名奥斯瓦尔德(Oswald)为谷兹科夫(Guzkov)主编的《德意志电讯》撰稿,③KarlMarx,Friedrich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Ⅲ/1,Berlin:DeGruyterAkademieForschung,1975,p.537.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接触了白尔尼和海涅的著作。与此同时,恩格斯开始“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并关注施特劳斯等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从《耶稣传》出发破除宗教对其思想的影响。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142-143、224、276 页。1839 年11 月,恩格斯开始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黑格尔的看法:“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142-143、224、276 页。在《不来梅通信》系列文章中,恩格斯已经不是以启蒙的理性主义而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来批判宗教。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恩格斯强调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步之处,“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548、273 页直到1840 年底,恩格斯已经完全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并坚定地支持施特劳斯对宗教的严肃审判,“《耶稣传》……已经成为把每一个非施特劳斯主义者逐出文坛的行为准则”。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6、142-143、224、276 页。
1841 年3 月底,恩格斯离开不来梅。在外游历6 个月后,恩格斯决定前往柏林“去履行公民义务”并“尽可能服完兵役”。在服兵役的同时,恩格斯也作为柏林大学的旁听生继续进行思考与学习。根据MEGA2 编辑的考证,《宗教批判笔记》正是恩格斯服兵役期间学习和研究的成果。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件事,这成为促使恩格斯深入研究宗教问题并撰写《宗教批判笔记》的直接原因:第一件事是1841 年谢林应邀来到柏林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驳。谢林试图将理性和信仰结合为一种宗教的“天启”,并以此来战胜黑格尔建立的体系哲学。然而谢林的启示哲学看似调停了理性和宗教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有神论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信仰的杂多,最终变成了一种充斥着神秘主义的混乱神学。第二件事是1841 年8 月鲍威尔被开除教职。鲍威尔出版的《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不满,最终以宗教观点反动为借口开除了他在波恩大学的教职。这一行为被青年黑格尔派看作是普鲁士政府对自由的侵犯,于是很快激起了他们的义愤并首先在宗教领域展开斗争。
这两件事情促使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恩格斯作出回应,《宗教批判笔记》的写作正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恩格斯虽然已经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但并不熟悉谢林宗教哲学,缺乏批判谢林所需要的知识。①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 卷,第284 页。这也就表现为恩格斯对谢林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并未深入谢林启示哲学本身进行反驳,而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反对,更谈不上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进行理论回击。另一方面,由鲍威尔被开除事件引发的宗教批判运动,已然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斗争的焦点。恩格斯建立起无神论并将研究兴趣聚焦于此,开始了针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和研究,《宗教批判笔记》的重要内容有三:一是摘录了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中宗教史及耶稣的生平和事迹的相关内容;二是因鲍威尔在其著作中提及恩斯特·吕策尔伯格(E.Lützelberger)所写的《论使徒约翰和他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②Bruno Bauer,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SynoptikerⅠ,Leipzig:Otto Wigand,1841,p.19.恩格斯很可能受到了鲍威尔这句话的启发而阅读并撰写了摘录笔记;三是恩格斯旁听柏林大学教授费迪南·贝纳里(Ferdinand Benary)关于约翰启示录的演讲所形成的讲义笔记。
综上所言,早期摘录笔记并非是恩格斯“心血来潮”的偶然产物,而是其自身思想在家庭、社会、研究目标的驱动下运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MEGA2 编辑所指出的,恩格斯的高中学习笔记使他摆脱了伍珀塔尔地区盛行的虔诚主义思想;宗教批判摘录笔记则证明年轻的恩格斯努力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性研究促使自己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③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26.这些摘录笔记充分反映出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向人们揭示了恩格斯是如何通过高中时期的刻苦学习奠定了深厚的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基础,又是如何一步步从虔诚主义的束缚中走出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最终与马克思踏上了同一条路。
二、内容缕析:文献结构与核心要义
恩格斯本人没有对早期摘录笔记进行系统的归类整理,MEGA2Ⅳ/1 根据写作的时间和内容的不同将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分为两组,并以高中时期的材料(Materialien aus der Gymnasialzeit)和新约圣经批判研究(Studien zur Kritik neutestamentlicher Schriften)为标题编排在附录和正文中。这样编排很直观地向读者反映出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的结构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一)高中时期摘录笔记的文献结构与主要内容
高中时期摘录笔记由两个笔记本构成,即《古代史学习笔记》和《文学学习笔记》。两个笔记本的内容虽然都是以记录上课的内容和研读教材为主,但写作风格和撰写方式截然不同。
第一本是《古代史学习笔记》,该笔记本总共有54 页,包含关于古代东方和古希腊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 年)的历史和地理的笔记。其中包括14 张地理图画和插图(包括地图和战役简图),笔记本扉页的四个角上分别写着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英文的“历史”一词,第2 页点明了笔记的主要内容“克劳森博士先生古代史讲义,弗·恩格斯记录”,第3 页是恩格斯将文字和地图部分分开后为笔记编撰的章节目录和对应的页码。据MEGA2 考证,克劳森博士使用的授课教材是恩斯特·施米特所写的《中学古代史概论》,①Ernst Schmidt,Grundriß der alten Geschichte,Barmen,1835.将恩格斯的笔记与该教材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断代方式和结构上的一致性。②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由此,《古代史学习笔记》显然是与课程平行构建的,主要涵盖了三部分内容:第一,对克劳森博士授课过程中的直接笔记,其特点是速记痕迹明显,大量运用了缩写和省略;第二,依据教材提供的历史材料进行细致分析及摘录,与授课内容相互呼应;第三,在教材之外恩格斯还作了有益的补充,尤其是古代中国、古埃及部分,这些很可能是在克劳森博士的指导和建议下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摘录过程中预留了页边距,用以在完成基本内容之后作必要的边注和补充,包括插图、年份、族谱以及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参考文献等,这些边注展现了恩格斯对材料的进一步思考。
具体考察正文部分的内容,恩格斯根据教材结构将古代史划分为亚洲史和希腊史两部分。首先是针对亚洲史进行的27 页摘录。导言部分讨论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即认为蒙古人、高加索人、非洲人是所有人类的起源。③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加之教科书中盛行的黑格尔和基佐历史观的影响,在大多数当代历史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关于人类起源和分类的类似概念,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恩格斯并没有摘录教科书及相关材料中的宗教创世传说。具体而言,笔记中介绍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最古老亚洲帝国的风土人情,页边上绘制了两国的建筑物(石柱和寺庙),在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摘录中恩格斯作了原教材之外的拓展,如他认为婆罗门本应教化民众,“但人民非常愚蠢,首陀罗甚至没有能力阅读吠陀经”。④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随后是对巴克特里亚、巴比伦地理和人文的摘录,第9 页上恩格斯将亚述(Assyrien)和米坦尼(Medien)的历史分为两栏,用比较的方法记述了巴比伦帝国的衰落与亚述得以趁机摆脱米坦尼的控制进而崛起的历史过程,页边是联系史料对美索不达米亚政治变化的整体分析。⑤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最后恩格斯分别摘录了腓尼基、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和阿拉伯)、波斯和迦太基的地理,政治与神话传说。值得一提的是,第12 页上恩格斯对以色列地理作摘录时,提到火山对阿拉伯湾附近会产生地震的影响,紧接着以括号的形式标注“所多玛和蛾摩拉? (Sodom und Gomorrha?)”,⑥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457-458.明显是联想到《旧约》中所多玛和蛾摩拉毁灭的神话而产生的疑惑,这种理性主义的“灵光一闪”正是恩格斯这一时期思想状态的最好写照。
紧接着是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希腊历史共计19 页的摘录。恩格斯在前言和对古希腊地理状况进行说明后,正式进入了对古希腊历史的摘录。恩格斯对古希腊史料和人物传记的收集与整理十分细致,第33 页的页边上他将这些史料提纲挈领地分为“A.神话时期:荷马、赫西奥德、诗人、神话搜集者”和“B.历史时期: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⑦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并进一步区分出立法者、军事统帅、政治家。恩格斯叙述了古希腊各氏族迁徙、定居并最后确立内部社会关系的过程。以此为线索,写明古希腊史具体可分为神话时期、历史时期、多利亚人的迁徙时期、斯巴达史、雅典史、非本土的希腊人、波斯战争。⑧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918,447,449,545,478,445.恩格斯着重摘录了古希腊社会内部各氏族的交往与解体过程,尤其是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描绘了早期古希腊国家和城邦形式,同时深入讨论了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第36 页中,恩格斯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摘录:“城邦的首领是两位国王……由公民议会的投票来选举元老院的主席、执政官或是战争时期的领袖。”①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第39 页中,恩格斯摘录了土地贵族的出现与王权的更迭的关系,“雅典历史初期出现了与贫民完全不同的掌管土地的贵族”,因此,颁布的法律“只会增加苦难,因为贵族只有更多的手段来压迫人民”,页边上是恩格斯对雅典氏族组织形式作的批注,即雅典氏族组织由“4 个部落组成,部落又下辖3 个胞族,每个胞族包含30 个小氏族”。②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对雅典议会与政治制度的摘录在该笔记中占有一定比例,说明恩格斯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较为关心并有所思考。
最后,恩格斯在摘录的过程中着重考察了战争史。他回顾了古巴比伦、希腊和波斯等战争,详细地叙述了战争双方的实力情况、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以及战役的过程。此外,笔记本边页中插入了大量地图、族谱,起到了帮助恩格斯更好地理解史料的作用。可以说,中学时的恩格斯已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尝试形成自己处理史料的独特手段。
第二本是《文学学习笔记》,该笔记本共有74 页,是恩格斯对《伊利亚特》的22 支圣歌的预习和课堂笔记。其中,课堂笔记主要包括古希腊语的释义、词语和短语的翻译、词源和构词法的注释、荷马式的句法特点以及对长难句的理解。笔记本还包括了对荷马史诗的文学史回顾和文学评注。据MEGA2 考证,恩格斯在学习古希腊语时使用的工具书是菲利普·巴特曼(Philipp Buttmann)于1825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这是一本关于荷马史诗的专用词典。③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936-937.笔记的开端是恩格斯在课堂上作的两个札记,是对老师口授内容的记录,完成于正式学习《伊利亚特》之前。④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第一个札记是从文学风格的角度上对“荷马问题”进行讨论,即荷马史诗的作者到底是谁,是民间作品集的收录还是出自于某一位作者之手。恩格斯认为文字结构和叙事诗的文风都指向了荷马史诗的作者就是荷马本人,“叙事史诗与抒情史诗完全不同”,“叙事史诗的目的在于表现外在事物。这种外在事物只能是自然、历史、事件,诗人本身不会出现在作品中”。⑤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第二个札记是对《伊利亚特》所包含的22 支圣歌的概括性内容,这些内容带有提示的作用。笔记中,恩格斯大量摘录了希腊语生词,这些词汇有的是《伊利亚特》中直接出现的,有的则是相关词汇。⑥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笔记的右侧经常出现词组和短语的解释性注释,这些生词和词组往往跟史诗中的段落一起出现以帮助记忆。
《文学学习笔记》的内容显示,恩格斯一方面对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为代表的古希腊诗作中的文学和语言进行系统学习与思考;另一方面详细讨论了地理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细节,笔记中关于希腊神话、宗教的内容都证明了这一点。⑦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81,484,937,512,936,937.恩格斯以摘录笔记的方式,借助史诗的原文全面提高了希腊语水平,就此而言,《文学学习笔记》同样是一部语言学学习笔记。
(二)《宗教批判笔记》的文献结构与主要内容
《宗教批判笔记》由三部分构成,即对鲍威尔的《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和吕策尔伯格的《论使徒约翰和他的著作》的摘录,以及贝纳里关于约翰启示录演讲的讲义。该笔记本共26 页,恩格斯未对笔记进行分页编码,这些书页曾被伯恩施坦插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因此书页上有铅笔书写的15-40。①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873-874,405-409.恩格斯对著作的摘录较为均匀地分布于全书之中,除了对内容的记录,恩格斯还对原有材料进行了相应补充,用以凸显自己的判断。可以说,《宗教批判笔记》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三份笔记中,对原始基督教教义的批判性研究都贯穿始终。
其一,是对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的摘录笔记。自从施特劳斯拉开了宗教批判的序幕,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们就对宗教史进行了多角度解读。与施特劳斯不同,鲍威尔认为《圣经》的故事不是实证的存在,而是叙述了一段历史,即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②参见Bruno Bauer,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SynoptikerⅡ,Leipzig:Otto Wigand,1841,p.54.如果说基督教把人性转移到人的外部,表现为神性和人性的分离,同时神所代表的普遍理性逐渐丧失了说服力,那么基督教国家就是用外化了的普遍性代替了理性主体的普遍性。因而,在该著作中,鲍威尔通过对耶稣生平和宗教史的考察来证明宗教中自我意识的异化与扬弃之路。基于此,恩格斯摘录笔记的关注点也必然聚焦于对宗教史与精神发展的考察。
笔记中,恩格斯摘录了耶稣的诞生和童年、约翰的诞生等部分。第2 页上,恩格斯提到鲍威尔在考证宗教史的过程中使用了宗教的“历史调解(geschichtlichen Vermittlung)”③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391,391,883,402.来描述宗教的作用,即宗教具有来世的调解力量。这种调解力量在不同时期有强弱之分,在宗教的衰弱时期,调解力量只有通过一种新的教义才能更好地实现,教义也就是因此被不断创造的。接着,恩格斯用着重号标注了鲍威尔对基督教所引发的混乱的解释,“对奇妙观点的完美解释是:犹太教中神性和人性的对立在基督教的观点中达到了最高的顶点”,“原罪是全体人类的,而不是个人的”。④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391,391,883,402.紧接着,恩格斯摘录了鲍威尔追溯的耶稣受洗、现世的过程。在第六页,恩格斯通过备注的方式引用了鲍威尔对旧约的总结性陈述:“旧约的宗教是在概念的历史发展中提出的。”⑤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391,391,883,402.该部分的最后,恩格斯摘录了鲍威尔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历史的看法,即耶稣的活动过程展示了精神与世俗的结合;同时,犹太精神从约翰的受洗礼为始,以耶稣的现世为终,正好说明了基督教是犹太精神当代发展的最后阶段。⑥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391,391,883,402.
其二,是对吕策尔伯格《论使徒约翰和他的著作》的摘录笔记。在这部著作中,吕策尔伯格考察了使徒约翰历史传说的可信度以及新约中约翰著作的部分内容,其作品的主基调是自由主义。吕策尔伯格回顾了原始基督教对约翰著作的记录,审思了其真实性,并在该书的最后探讨了“关于所谓约翰著作的起源”这一命题,其结论是使徒约翰的历史传说和他所谓著作的真实性都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摘录了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引文的释义和例证。另外,恩格斯凭借自身对《圣经》的了解增加了来自新约的证据。恩格斯首先摘录了吕策尔伯格发现的约翰传说中的矛盾之处。通过对同时代人的通信的考证,吕策尔伯格认为约翰根本没有出现在小亚细亚,约翰的很多经历是无据可考的,甚至在福音派的论述中都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⑦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873-874,405-409.第3 页中,恩格斯提到福音派对约翰传说张冠李戴的目的是将柏拉图式的逻各斯学说转移到基督身上,通过启示录将古希腊哲学和教义联系在一起。福音派希望强调基督教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因此将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等古希腊哲学家都与基督教建立了联系。摘录的最后,恩格斯通过对新约内容的考察,发现约翰传奇和著作的虚构是原始基督教企图对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吸收的结果,即其最终试图表明“逻各斯是上帝之光”。①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14,26.
其三,是贝纳里关于约翰启示录演讲的讲义。据MEGA2 考证,恩格斯记录的第一部分已经遗失了,而在前几次的演讲中贝纳里很可能已经将新约经文的内容和结构整体地勾勒出来了。恩格斯记录得比较潦草,内容也比较分散,可以看出是在演讲过程中快速写下的。笔记的第一页,凭借对历史故事、语言风格、思维形式的还原,贝纳里对约翰启示录的年代、作者真实性和历史性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些讨论揭示了启示录与圣经新约的关系,反映出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过程。从第4 页的下半部分开始,演讲集中于对启示录词句的解读。从讲义中可以看出,这种解读不同于传统宗教的布道模式,着重甄别启示录与现实矛盾的地方,将教义置于现实历史中加以考察。②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p.421-422.
三、价值意蕴:文本演进与思想嬗变
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既是研究青年恩格斯思想变化不容忽略的重要文献,也是破解“恩格斯问题”的锁匙。MEGA2 编辑认为恩格斯的早期摘录笔记仅仅是对外来思想的“吸收”,③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14,26.这样的评价不仅失之偏颇,且会掩盖早期摘录笔记的独特研究价值。一方面,MEGA2编辑没有看到早期摘录笔记创作的具体动机,只将其看作是恩格斯对知识的被动学习。通过前文对文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这一观点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另一方面,早期摘录笔记虽然以摘录为主,但这些笔记绝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砌”,在深入考察其结构和内容后可以清晰了解到摘录笔记独特的文献价值及其反映出的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
(一)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独特的文献价值
恩格斯的文章向来以材料丰富、文笔流畅、思维缜密著称,这与他高中时期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高中时期的摘录笔记充分反映出恩格斯的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天分,他能透过繁杂的史料发现历史背后隐藏的真相。系统考察其高中时期的摘录笔记,可以从三个维度总结该笔记的独特价值。
从宏观维度看,早期摘录笔记彰显了恩格斯处理史料的方法。在《古代史学习笔记》中,恩格斯对古代政治形式较为重视,着重考察了地理位置、民族结构、经济状况、氏族组织等内容。恩格斯对历史的考察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从不同侧面进行解剖,多方位、多角度地引申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处理史料的方法贯穿了恩格斯的一生,如在1870 年创作的《爱尔兰史》及其手稿中,恩格斯也是从爱尔兰的地理情况谈起,分析了爱尔兰民族组成与氏族结构,进而全方位地解剖了爱尔兰的历史发展及对英国的影响;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523 页。在1882 年的《马尔克》一文中,恩格斯同样从土地与民族发展的角度对马尔克制度进行分析,得出德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523 页即使此时恩格斯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但与《古代史学习笔记》对比,处理史料的基本方法还是极其相似的。同时,恩格斯并不限于对历史事件的线性说明,更不停留于简单的罗列,而是动态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与必然性,这从侧面反映出恩格斯的逻辑思辨能力,尤其是对历史哲学的认知水平。另外,笔记中恩格斯对军事史的研究方式也颇为独到。19 世纪50 年代,恩格斯应马克思之邀撰写了一系列军事研究的评论性文章,如《克里木战争》和《欧洲战争》等,这些文章与《古代史学习笔记》中利用插图进行战争说明的研究方式十分相似。可以说,高中时期处理史料的方法对恩格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从中观维度看,早期摘录笔记为恩格斯积累了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希腊氏族形式作了说明:“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9、74 页。这一观点与《古代史学习笔记》页边的注释完全一致,这说明成熟时期的恩格斯很可能利用了自己高中时期的笔记。另外,恩格斯还谈到了荷马史诗的内容:“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9、74 页。这些后期文本充分证明了高中时期摘录笔记对恩格斯的重要性,其内容不是随意拼凑,而是十分有价值的思想结晶,为他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从微观维度看,早期摘录笔记显示出恩格斯卓越的文学、语言能力。众所周知,恩格斯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等,后期能够认识并阅读20种语言,这与高中时期养成阅读原著的学习习惯是分不开的。另外,与马克思一样,高中时期恩格斯酷爱诗歌并痴迷于古希腊和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人物。高中肄业前,恩格斯用希腊语创作了一首充满英雄豪气的诗作——《伊托克列斯和波吕涅克斯决斗》,这首诗歌是恩格斯在《文学学习笔记》中刻苦练习希腊语的成果。这些笔记充分证明恩格斯深厚的文学、语言功底源自高中时期的勤学与善思。同时,对英雄不屈精神的敬仰,也使崇高和顽强的信念在恩格斯心中扎下了根。
与高中时期的摘录笔记不同,《宗教批判笔记》的指向性更强,在摘录的同时更加突显恩格斯的思想内涵。恩格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和宗教史,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加深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认识到了意识的辩证法是“强有力的、永不静止的思想推动力”。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273 页。纵向来看,《宗教批判笔记》开启了恩格斯长达50 余年对基督教问题的思考;横向来看,《宗教批判笔记》是恩格斯转入青年黑格尔派并投身理论批判的代表文献。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启发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和宗教问题展开研究。《宗教批判笔记》启发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及基督教发展过程中的宗教问题进行思考,这一思考过程不是浅尝辄止的,而是深刻影响了恩格斯的研究方向,并在40 年后成为其研究主题。1882 年,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指出:“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5、594 页。同时恩格斯提到:“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就可以有一个概念。”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95、594 页。1883 年恩格斯撰写的《启示录》一文,从侧面反映出其对宗教思考一以贯之的“问题域”,即“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 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 页。这与《宗教批判笔记》的内容一脉相承。在1894 年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恩格斯介绍了以鲍威尔和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宗教史阐释学,认为现代宗教就是基督教,而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只有走向消亡才能使宗教彻底被葬送。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明显利用了《宗教批判笔记》的内容,其中对基督教史料的运用甚至对约翰启示录撰写的时间、作者等考证都与摘录笔记相一致。
由《宗教批判笔记》开启的对原始基督教和宗教问题的思考贯穿了恩格斯一生。虽然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恩格斯对该问题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方法更为科学,但这一切的源头无疑来源于《宗教批判笔记》,正如1894 年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所言:“1841 年我读了弗·贝纳里关于《启示录》的讲义之后,就对这个题目发生了兴趣。从那时起我才明白,这是《新约全书》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这篇文章的酝酿构思已经五十三年了,出版无须过于着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65 页。
第二,成为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进行吸收的标志性文献。彼时,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学习与思考已经站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上,虽然他已了解施特劳斯对待宗教的观点,但对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尤其是鲍威尔的思想还不够了解。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的生成和历史过程具有同一性,自我意识不是一种可以直接把握和感受的特殊意识,而是过程的演绎,即只有对历史的反思才能使自我意识真正生成。《宗教批判笔记》的结构明确显示恩格斯考察了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以及原始基督教发展为世界宗教的过程,并发现了鲍威尔宗教理论的价值。虽然此时恩格斯尚不具备利用唯物史观考察宗教的能力,且摘录的内容也不是服务于历史的考察,但不可否认的是恩格斯对鲍威尔的观点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吸收:一方面是对原始基督教发展史的一般考察,另一方面是利用宗教史说明宗教对异化精神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很快吸收了鲍威尔对宗教历史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中。
第三,是恩格斯积极参与德国思想斗争的范例。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宗教批判理论矛头直指视基督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国家,现实的需要激发了恩格斯的斗争热情。鲍威尔通过对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考证,认为基督教是宗教及其局限性的最纯粹表现,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对一切普鲁士国家的批判。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是“大胆、尖锐、机智、透彻”的,尤其对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考察以及宗教问题的阐释是极其深刻的,宗教问题已经从神的领域回到人的领域。《宗教批判笔记》对鲍威尔等人的摘录显示出一定的革命性,其革命性不只体现在对宗教的一般反对,而是更多地触及了对普鲁士国家与现代基督教的反思。在摘录笔记的后半部分,恩格斯显然已经意识到宗教虚构和歪曲历史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并使其更好地控制人民的思想。③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402.
(二)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的思想史地位
由于对早期摘录笔记的忽略,恩格斯思想转向的关键问题长期无法得以阐明,如恩格斯如何从虔诚主义的束缚中走出,又如何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原则中转向哲学共产主义。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些关键问题,只有通过厘清早期摘录笔记的思想史地位并阐明其对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建构性影响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总的来说,早期摘录笔记揭示了青年恩格斯思想转变的细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回应关于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诸多“悬案”。
首先,恩格斯对虔诚主义的质疑发轫于高中时期。恩格斯对虔诚主义的拒斥发生于其加入“青年德意志”之后,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揭露了虔诚主义的伪善和反理性本质。然而自童年开始就受到虔诚主义影响的恩格斯,为何因为不来梅的社会考察就突然排斥虔诚主义并脱离了它呢? 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的。事实上,恩格斯对于虔诚主义的质疑可能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悄然开始了。第一个证据在《古代史学习笔记》的开篇,恩格斯摘录了人类起源的相关内容,可是如果对比教材就会发现恩格斯并没有摘录关于上帝创世的相关神话,这些内容似乎是被恩格斯刻意“忽略”了;第二个证据如前文所言,在对阿拉伯湾附近的地理情况进行说明时,恩格斯将地震与《圣经》中所多玛和蛾摩拉毁灭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理性主义的联想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让人们看到青年恩格斯在学习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质疑虔诚主义的思想“火花”。另外,在高中时期的摘录笔记中恩格斯不止一处地展现对古希腊英雄勇于挑战、敢于斗争精神的推崇。基于此,恩格斯很可能是在英雄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对虔诚主义产生了首次质疑,并在生活和思考中不断加深,最终彻底与虔诚主义分道扬镳。
其次,恩格斯在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存在一个“鲍威尔环节”。传统观点认为恩格斯是从施特劳斯切入青年黑格尔派,继而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向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靠拢。①参见霍尔斯特·乌尔利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马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版。《宗教批判笔记》表明恩格斯在其思想发展中隐藏了一个“鲍威尔环节”,即鲍威尔的宗教批判理论对恩格斯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鲍威尔对宗教史的研究帮助了恩格斯走向了费尔巴哈。具体表现为:其一,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391、535、446 页。恩格斯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是对宗教思辨学说进行补充,而当时对基督教进行批判性研究的人明显是指施特劳斯和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正是对该论题的延续,且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其二,恩格斯利用鲍威尔关于基督教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现代普鲁士的国家宗教。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表达了威廉四世所建立的现代宗教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他指出:“当基督教想自命是科学时,它的形式就是神学。神学的实质,特别在当代,就是调和和掩盖绝对的对立。”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391、535、446 页。这与《宗教批判笔记》中摘录的观点极其相似。其三,促使恩格斯关注政治运动。鲍威尔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极强的革命性,他认为国家体制是基督教最后的“避风港”,只有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造,宗教才能被彻底铲除。恩格斯在《宗教批判笔记》中同样对此作了吸收,在笔记的结尾处恩格斯摘录了基督教与国家的关系。1842年7 月,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中,恩格斯提到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就是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和鲍威尔三人,并得出“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391、535、446 页。的结论。
最后,恩格斯借助宗教批判向唯物史观迈进了一步。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中,恩格斯将历史比作一根螺线:“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弯曲绝不是很精确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107 页。这种历史观有着极强的黑格尔哲学色彩,恩格斯一直尝试将白尔尼和黑格尔联系在一起,使黑格尔哲学更具革命性,进而明确普鲁士国家的未来发展。随着《宗教批判笔记》的完成,通过对宗教史的辩证分析,恩格斯在历史观上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论证历史的方式虽然仍是一种唯心史观,但无疑为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可能。在恩格斯的视野转向无产阶级和政治经济学之后,唯物史观才最终形成。值得关注的是,如前文所提及的伯恩斯坦误认为恩格斯的《宗教批判笔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组成部分,因而将其编页15—40 放入其中,这虽然只是一个误读,但也从侧面表明此时恩格斯对鲍威尔宗教批判的摘录和分析与成熟时期有颇多相似之处。
结语
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完整反映了青年恩格斯从虔诚主义走向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过程,补齐了恩格斯转向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前夜的文献细节,也展现出恩格斯独特的写作风格和研究旨趣。同时,站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上考察恩格斯早期摘录笔记可以发现,恩格斯拥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审思基督教起源与发展以及当代困境等问题。
客观来看,恩格斯对问题的思考重点与逻辑进路确实与马克思存在差异,如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时,更多地对基督教的形成时间、教义的作者等方面表现出兴趣,而缺少对宗教精神的抽象分析。虽然此时恩格斯很可能只是处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但与同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宗教的摘录笔记《波恩笔记》②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Ⅳ/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76,p.293.相对比,就可以发现二人思考角度的差异性,这种“有差异的同一”极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导致了西方马克思学发现的“恩格斯问题”。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连体婴儿”,我们在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贡献等问题时,既要聚焦于文献学对恩格斯个人思想的深入剖析,又应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