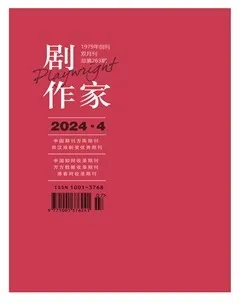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主角》如史诗 “主角”有遗憾
摘 要:话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先生的同名小说,2022年斩获第十七届“文化奖”,整体的观感大气、震撼、壮阔,呈现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美感,可圈可点之处俯拾皆是。该剧最亮眼的是巧妙地利用戏曲“一桌二椅”的经典程式理念,以戏曲虚拟空灵的写意手法对话剧舞台进行切换自如的场面调动,实现了现实场面与虚拟时空的无缝对接,创造了一个“时空叠加”的新的舞美范式。但遗憾的是,话剧《主角》中的主角在与戏曲的“缠绵悱恻”中,并未呐喊出自己的魂,三处有硬伤:主角的表演欠火候,未演出角色的魂;主角未成长,缺少成长弧线;主角形象模糊,不饱满,不经典。
关键词:话剧《主角》;忆秦娥;秦腔;主角
话剧《主角》改编自陈彦先生的同名小说,小说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话剧则是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之后,陕西人艺“茅奖三部曲”系列推出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2022年斩获第十七届“文华奖”。该剧采用编年体的形式,生命场域横跨人生40年,讲述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如何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迎风而上,逆风而行,从一个11岁的放羊娃到51岁登上“秦腔皇后”宝座,悲壮震撼而又华丽惊艳的一生。创作者以悲悯的情怀,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鞭辟入里地在舞台上大胆地进行了曝光,对“美的毁灭”抱以深深的同情,对人的命运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话剧《主角》整体的观感大气、震撼、壮阔,令人啧啧称奇。原来话剧竟然可以这样写,这样演!这样不顾一切地气势磅礴,直击人心!该剧呈现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美感,可圈可点之处俯拾皆是。最亮眼的是巧妙地利用戏曲“一桌二椅”的经典程式理念,以戏曲虚拟空灵的写意手法对话剧舞台进行切换自如的场面调动。一个圆场,已过千山万水;一人一骑,恰似百万雄师横扫。从灶房到舞台,从舞台到尼姑庵,从尼姑庵到家,导演以境随人走的调动手法,将不同的时空幻化出一种蒙太奇风格的美。在同一个时空里,这边厢,单团长和刘红兵正为要不要生孩子在讨论争辩时,那边厢,忆秦娥一个圆场已怀孕,再一个圆场已生子,实现了现实场面与虚拟时空的无缝对接,创造了一个“时空叠加”的新的舞美范式。 “戏中戏”的结构使戏曲表演与话剧表演共用同一个舞台空间,这对舞美设计提出了挑战。为方便展示两种不同的表演模式,舞美设计采用“出将”“入相”的悬吊中式门楼设计,使用16根柱子在舞台后半方构建起传统的戏曲表演空间。柱子在舞台上不断变换位置,时而成为支撑起“出将”“入相”的戏曲舞台的“顶梁柱”,时而又构筑起话剧舞台的其他场景或角色活动的空间。全剧仅以16根简约的柱子,通过34次变幻,便把一代秦腔皇后53个厚重悲壮的人生场面鼎力托起。话剧与戏曲的勾连,使《主角》在形式美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遗憾的是,话剧《主角》中的主角在与戏曲的“缠绵悱恻”中,并没有呐喊出自己的魂。
主角的表演欠火候,未演出角色的魂,这是话剧《主角》的硬伤。全剧以主人公忆秦娥曾主演过的六部秦腔剧目《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狐仙劫》《同心结》《梨花雨》为骨架,纲举目张,铺陈渲染其厚重悲苦的一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结构安排?因为秦腔是主角人生的魂。浩瀚庞杂的秦腔剧目中,忆秦娥为什么只对这几个剧目情有独钟?因为她不是在演戏,她是在演自己的真实人生。《杨排风》中的杨排风和她一样都是出身低微,都是在同别人的较量中大显身手,才开启了不同凡响的人生。《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与许仙情投意合,却因法海处处苦作对头而东奔西走,爱而不能相聚。忆秦娥与封潇潇因排演《白蛇传》,在顾盼生辉中懵懂初尝爱情的甜蜜,却不料忆秦娥被调到省团,从此与“许仙”天各一方。在省秦腔剧团,忆秦娥被“钦点”为《游西湖》李慧娘的最佳人选。戏中李慧娘因爱慕风流倜傥的裴郎,在贾府惨遭屠戮,化作怨鬼复仇;戏外忆秦娥日夜思念心上人封潇潇,却遭官二代刘红兵多次纠缠威逼,无奈只得委身下嫁……忆秦娥为什么能成为一代秦腔皇后?因为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演秦腔,秦腔是她的生命支柱。秦腔是她,她是秦腔。然而遗憾的是,话剧《主角》中主角的表演很是欠火候,未演出角色的魂。尽管演员在排练期间,进行戏曲身段训练长达两年时间,但作为主演的90后年轻演员并未在自己的表演中揣摩到主角忆秦娥与秦腔文化之间深度的灵魂交流。她的表演肤浅、流于表面,缺乏层次感,没有准确地传达出放羊娃时的忆秦娥和作为一代秦腔皇后的忆秦娥在扮相、肢体动作、心理变化等方面发生的质的变化。不管是作为武旦的杨排风,还是作为正旦的白娘子和李慧娘,主角的表演连形似都没有做到,神似就更是一种奢望了。主角的表演只是大致勾勒出了武旦或者正旦其行当的粗线条轮廓,她没有读懂角色的内在情感诉求,她不是在演人物,而是在演行当。即便就是演行当,她的基本功也很不到位。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一招一式这些程式化的基本功,她的表演都很僵硬,像极了当下没有情感程序输入的数字化仿真人在表演。演白娘子耍水袖,她只是为耍水袖而耍水袖,没有带入白娘子的情感抒发,缺乏正旦的端庄雅致、“美中有意”。没有将水袖行云流水、交横飞舞的韵动之美赋能给忆秦娥,展示其之所以成为秦腔皇后的惊艳过人之处。演杨排风耍花棍,举棍力度拿捏不到位,不应一下子将棍忽地举起,而是要若有所思地缓缓举棍,中途稍作停留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力将棍举起。这一棍不仅要举起武旦的威猛刚烈,更要举出一代秦腔名伶似千斤重、悲壮的艺术人生。忆秦娥之所以成为秦腔皇后,并不是因为她有闭月羞花之貌,而是因为她有过人的秦腔艺术才华。她的才华越是闪耀夺目,她的人生就越是灾难重重,整个剧作的思想深度也就越发凸显。所以,主角的表演越是神似,就越能打动人心。作为一部话剧,既然舞美设计上已经融入了戏曲的创新元素,在主角的人选上,完全可以起用功底扎实的戏曲演员来担当主角。波澜壮阔的整体剧作框架像极了一袭华美宽阔的衣袍,没有点儿人生阅历和舞台功底,怎能支撑起历经四十多载风风雨雨的这身战袍?!话剧《主角》的主角人选,面孔可以不鲜嫩,但一定要有经秦腔文化艺术熏陶后沉淀的一种气质在,绝对不能是娃娃脸一路走到底。
既然秦腔是忆秦娥的生命底蕴,唱腔绝对不能缺席,而且中国传统戏曲的核心艺术也在于唱腔。但在话剧《主角》中,忆秦娥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从头至尾,忆秦娥的秦腔才华只是在跑圆场、耍花棍、甩水袖、吹火等秦腔的几个基础动作上做了蜻蜓点水式的表演。话剧《主角》中出现的秦腔唱段,均是以幕后伴唱的形式出现,尽管也有渲染氛围、推进剧情的作用,但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没有彻底地发挥出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可以设想,如果主角选取秦腔《游西湖·鬼怨》的一段或者最关键的几句在台上倾情演唱,不仅会让秦腔皇后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而且也会为话剧《主角》的整体美学风格增色不少。《游西湖·鬼怨》的唱腔以苦音二六板为主,旋律下行级进,节奏徐缓,音调凄切怨怜。如此时愤、时悲、时恨、时怜,把李慧娘含冤被杀(忆秦娥受诽谤被人诬陷)、怨气满腔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唱腔从高音区开始,先以苦音尖板唱首句:“怨气腾腾三千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一个“怨”字劈空而来,旋律激越、凄厉,具有秦腔鲜明的高亢激昂的艺术特点,同时也唱出了忆秦娥性格中刚强不屈的一面。最后又以低音区歌队帮腔的形式,缓缓重复“三千丈和怒满腔”这几个字,体现李慧娘被冤杀(忆秦娥被人诽谤诬陷)的无奈和哀怨之情。此时此刻,李慧娘就是忆秦娥,忆秦娥就是李慧娘。由此可见,演员一旦与角色结合在一起,这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带着一种充满光环的魔力与神性。
话剧的另一个问题是主角未成长,缺少成长弧线。从11岁的乡村放羊娃到51岁唱响三秦大地的秦腔皇后,忆秦娥一直是一副面孔示人:坚强。但这种坚强是被时代的裹挟和推搡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本能。相信在某一领域成为主角的人,大多都是在被嫉恨、被诽谤、被不断打倒又不断爬起,在一次次的绝望崩溃中,还不忘“咬定青山不放松”。问题的关键在于,被打倒后再次爬起来的动力来自哪里?这才是坚强与坚强之间的最大不同,也是找到让观众念念不忘的忆秦娥“金手指”的最核心之处。对忆秦娥来说,她的人生由两个宇宙体系构成:外在的宇宙体系是被裹挟的悲苦的现实生活,内在的宇宙体系是秦腔艺术世界的丰盈与温暖。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特质就在于向美、向好、向善的“高台教化”功能,这也是秦腔的文化精髓所在。秦腔文化暖人的曙光才是忆秦娥抵御外在一切悲苦的坚实堡垒。剧中戏台坍塌,伤及人命,忆秦娥内心愧疚万分,梦中被牛头马面审判,就是来源于传统戏曲中鬼神常常充当伸张正义化身的惯例。就此而言,剧中莲花庵这场戏的出现其实对于忆秦娥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莲花庵主持说“其实,世上每个人都是可怜的”,她的这句抚慰之词也还只是停留在忆秦娥的外在宇宙系统中。真正让忆秦娥重返舞台、重振斗志与七零八落的生活厮杀的动力,还是应该来自于她的内在宇宙体系。但遗憾的是,整部剧作一直都是在强化外在宇宙对她生活的干预,而没有深入剖析她的内在宇宙体系。故而忆秦娥内心一直没有觉醒,连她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她为什么要唱戏?为什么要当主角?著名主持人董卿曾在《朗读者》节目中说:“人这一生,一定要有一样东西,拿来回答自己的生命。”忆秦娥拿什么来回答自己这一生的生命?她自己一直没有想明白,她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魂魄和天命所在。单靠外部宇宙体系能量的支撑,忆秦娥根本不可能登上秦腔皇后的宝座。
话剧《主角》具有史诗般宏大的叙事框架。纵观中外文化发展史,但凡一部皇皇巨著,都会出现一位英雄的主人公与之相匹配,人们往往因为这些英雄的光辉形象而不断缅怀经典巨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有救赎芸芸众生、戎马一生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荷马史诗》中有希腊联军第一勇士阿基琉斯。但在具有史诗品格的话剧《主角》中,我们对于主人公忆秦娥形象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除了被外部世界强加给她的生存的坚强本能外,找不到这一形象照耀世界的精神火炬之所在。在话剧艺术人物长廊中,更是没有找到属于她的坐标图谱。即便在不具备史诗品格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中,野蛮、泼辣、善良的虎妞,还有她那根乌黑发亮的大麻花辫,也能牢牢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忆秦娥的美应来自于内部震撼人心的力量,她的生命质量不在于40年广度的无限延伸,而在于深度的精神的光芒万丈。
“爱之深责之切”,总体说来,话剧《主角》还是瑕不掩瑜。在悲悯情怀的底色下,话剧《主角》勇敢地扛起了戏曲与话剧深度融合的开路大旗,开辟了具有陕西方言风格的“陕派话剧”新道路,体现了对话剧民族化道路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责任编辑 姜艺艺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