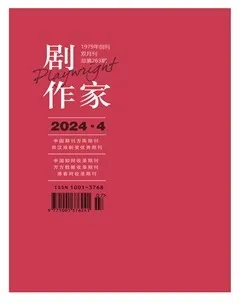孟小冬: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摘 要:2024年4月,话剧《孟小冬》在京剧名伶孟小冬封箱之作演出地中国大戏院上演。剧中,孟小冬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被浓缩在告别演出前的16小时。话剧弱化了情节的悬疑而加重了内心世界的描写,刻画出一个“一生傲骨”的坤生形象。孟小冬、梅兰芳、杜月笙等角色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着青衣、小生、老生的情感纠葛,艺术的追求与情感的期盼、纷乱的时代与嘈杂的舞台交织,演绎出一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传奇。
关键词:孟小冬;心理叙事;情怀追溯;生旦角色
上海,4月,牛庄路。狭窄的马路上车辆拥挤。不远处是闻名遐迩的大世界、时尚的来福士广场。人民广场上人流如织。今天的夜上海与七十多年前一般灯火辉煌、霓虹闪烁。但这近百年中,这座城和城里的人却已几经沧海桑田、物是人非。
中国大戏院。77年前,一代“坤生”“冬皇”孟小冬在这里封箱演出,轰动上海滩。77年后,一群人来这里看话剧《孟小冬》,寻找那个很久以前的故事,寻找那个早已隐入历史烟尘,却仍将传说留在人间的神秘女子和她周围的人。
昏暗的灯光,倾颓的匾额,老式留声机里传来苍凉的余派老生唱腔。戏,开场了,开场的戏中,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戏中戏传来的咿呀声响。
当话剧《孟小冬》的大幕缓缓拉开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混沌之感。故事的主线从1947年9月8日早上6点开始,围绕孟小冬即将封箱告别舞台的16小时展开。短短16小时,浓缩了一代奇女子“冬皇”一生的爱恨情仇,也牵扯出了杜月笙、梅兰芳、福芝芳、姚玉兰、余叔岩等“奇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一个云谲波诡的时代和扑朔迷离的舞台。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话剧《孟小冬》是一出没有悬念的戏。大幕拉开,随着一束束定位光渐次亮起,戏中人平淡地诉说起各自的生平、遭际、结局,如同诉说别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故事,如同台上唱过的那些戏。锣鼓敲响之前,剧本已然写定。然而,台上的那些人——生旦净丑,依旧忘我地沉浸在各自的角色中,呕心沥血唱着自己的人生——如同他们在台上塑造过的角色。
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还是野史逸闻,孟小冬都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在话剧《孟小冬》的故事里,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人生。但是,在舞台上,这一出《孟小冬》想要告诉观众的,不是那些书上记录的、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而是传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个比我们能看到的外部世界更加风起云涌的内心。重要的或许并不是他们如何选择,而是他们为何这样选择?
光辉耀眼的“旦”
话剧《孟小冬》是一出“旦角”戏。孟小冬是青衣、福芝芳是正旦,而着墨不多的姚玉兰,更偏向于武旦。
京剧舞台上的老生孟小冬在生活中,至少在今晚的话剧舞台上是大青衣。“一身傲骨,半世苍凉。风华绝代,广陵绝唱”是戏词,更是孟小冬一生的真实写照。她的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清冷气质。台下是芊芊弱质,台上却英气勃发,无半点脂粉味。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的情感纠葛,比台上的戏来得更曲折,令人津津乐道至今。然而,也许人们看到的只是台上的风光,绯闻的香艳,鲜少有人真正走进过她的内心世界。脱下戏服,摘下髯口,抹去油彩后,是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女作家闫红曾有一本写张爱玲的文集,起名《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这个题目放在孟小冬的身上尤其贴切,但即使千疮百孔,依然九死不悔。脱下戏服的孟小冬是弱势的。在那个特定的社会中,女性被天然贴上了“弱者”的标签。而一个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女性,更是可供人任意欺凌的绝好对象。她们毫无来由地接受着恶意的揣测、流言的中伤,却无处伸冤、反抗。孟小冬在京剧舞台上风光无限,却无法摆脱这一“弱者”标签。但是,处于弱势的孟小冬又是强大的。“傲骨风华”不仅是台上的唱念做打。台上的爱恨情仇无一不是台下性格的外化与投射。选择“坤生”注定了她选择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但即使头破血流,孟小冬也始终不曾放下自己的高贵。她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骄傲而决绝的。在最当红的时候,为了追求真爱,对舞台说放弃就放弃,只求做一个男人背后的贤妻良母。风雪之夜,身披孝服的她在梅府外吃了闭门羹,心在彻骨的寒冷中渐渐死去。她没有哭闹,选择了转身离去,并不提自己的付出和牺牲。深陷流言与诉讼,她倔强地不向任何人救助,苦苦支撑、偿还债务,在这个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中,用缄默不言对抗世界。最终,在登台前的最后一刻,她拒绝了金兰姐妹姚玉兰的挽留,拒绝了知己杜月笙的善意,拒绝了戏迷的热情,毅然决然地留下了舞台的绝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她走得那么干脆甚至不近情理。她选择了最辉煌的那一刻,在如雷掌声和如潮鲜花中谢幕。她的一生看似跌宕起伏。但其实早在选择“坤生”的那一刻,她的目标就已经无比明确地摆在了面前。得意时,失意时,挑班唱戏也好,告别舞台也好,人前背后她始终不曾放弃的就是对艺术的追求。这种追求只为自己的心。
如果说孟小冬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青衣大女主。那福芝芳则更像是舞台上的正旦。端庄肃然,却让人觉得无法亲近。人们提起福芝芳这个名字,多数是在说到梅兰芳的时候。似乎,她只是梅兰芳名字背后的一个注脚,却很少有人想起,她也曾是台上颇具名气的花旦,曾与梅兰芳拜同一个师傅学艺。和孟小冬一样,她也因为选择梅兰芳而放弃了舞台。只不过后来孟小冬又回到了舞台,而福芝芳做了一辈子“梅太太”。她的身上也有孟小冬一样的傲骨,但更多了一份韧劲——女性的柔韧。对于不明真相者,她常被视作梅孟感情的破坏者、绊脚石。尤其梅府吊孝那一晚,她的无情常被人诟病。但是,在话剧《孟小冬》中,恰恰她才是最清醒的那一个人。与打着“梅党”旗号、轰轰烈烈为梅兰芳制造新闻、造势的人们相比,她才是默默地、不求回报地爱着梅兰芳的那一个。她对梅兰芳的深情并不比孟小冬少。只不过孟小冬的“知音”更多给了台上那光鲜亮丽、艺术世界的梅郎,而福芝芳更懂得台下梅兰芳的软弱与无奈。在整场戏中,福芝芳都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以致让人觉得她是个生性凉薄、一心只求保住梅太太地位的“榭寄生”,直到全剧临近尾声中的那一场情感的爆发,内心的倾诉,才让人们真的了解了这个女性——她的爱同样如此炽烈。福芝芳并非传统意义上依附男性的贤妻良母,她的不言背后是强大的内心。因此她能够忍得下委屈、历得尽苦难。因为她很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还有姚玉兰,虽然笔墨不多,但却将一个大气侠义的江湖女子勾勒出来。姚玉兰的身份特殊,也有些敏感——她是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四姨太,也是孟小冬的金兰姐妹。两人相识于微时,是十几岁结下友情的“手帕交”。姚玉兰在孟小冬最落魄的时候请出杜月笙为她解围。面对“丈夫”对闺蜜毫不掩饰的爱慕之情,姚玉兰不仅毫无醋意,还主动充当说客,发自内心地劝她留在杜月笙身边。在剧场中,就听到有观众“吐槽”姚玉兰这个人物不真实——相比福芝芳而言。哪有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如此宽容?但事实上,姚玉兰与杜月笙之间的关系要比“爱情”复杂得多。他们更像是一种彼此欣赏的“合作关系”——也颇似今日人们常说的“蓝颜知己”。姚玉兰比孟小冬年长,在京剧舞台上不如孟小冬那么出色,漂泊在各个码头之间,她尝过的人情冷暖比孟小冬更多,因此也比孟小冬更懂人情世故。她不像孟小冬那样剑锋凌厉,容易伤人、伤己。她的爱恨情仇不像孟小冬那样非黑即白,而是明白了底线之上有些感情并不要说得明明白白。她和杜月笙之间未必有什么蓦然心动、激情澎湃,只是在相处之后明白彼此“合适”。这是两个都活得无比通透的人——杜月笙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行事爽利,知道他需要什么该为他做什么的人在他身旁,而姚玉兰也需要杜月笙这样一个为她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更难得的是,虽然是彼此“需要”,这两人之间还有一份难得的“尊重”。杜月笙能够在姚玉兰面前光明磊落地谈论孟小冬,并非无视姚玉兰的情感,而是明白姚玉兰的情感落点不在此处,因此与她商量此事也毫无隐瞒。
色彩驳杂的“生角”
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如同舞台上,有生角也有旦角。与孟小冬、福芝芳、姚玉兰这样的“旦”对峙的,便是“生”。老生是杜月笙、余叔岩。而舞台上的“名旦”梅兰芳是小生。
在话剧《孟小冬》中,梅兰芳的形象是不那么讨喜的。与京剧舞台上那个辉煌耀眼的梅大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生活中的懦弱与延宕。在艺术上,追求极致完美的梅兰芳是个锐意创新、充满斗志的探索者;而生活中,面对爱情与家庭,他却进退维谷,得过且过,甚至被“梅党”任意摆布,最后则既负如来又负卿……这个“梅兰芳”与以往大为不同。人们熟悉的,是贵妃醉酒的雍容华贵,是虞姬饮剑的干裂决绝,是天女散花的超凡脱俗。然而,在孟小冬的面前,这个毫无瑕疵的“旦”却将“生”的弱点、缺点尽显无疑。或许,这就是真实人生与传奇故事的差别。“梅党”和戏迷渴望的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孟小冬渴望的是一个知音相契的伴侣。但最终,留给他们的只是曲终人散的落寞。但如果问孟小冬悔不悔?应该是不悔的。毕竟,当正德皇摘下李凤姐鬓边海棠的那一刻,当霸王望着舞剑的虞姬的那一刻,她所渴求的相知相惜,已经得到了——在生活中得不到的,舞台上弥补了。
与梅兰芳形成张力的是“老生”杜月笙。这是一个鲜见正面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他是出现在孟小冬生命中的一道光、一团火。如果说,梅兰芳是那个艺术世界里给孟小冬带来光的“梅郎”,杜月笙更像是现实生活中一次次救她于危难之中的守护者。杜月笙对孟小冬的感情很执着,也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或许对于这样一个终年生活在欺骗、阴谋、杀伐中的强人而言,孟小冬的磊落傲骨于他也是一道光。而孟小冬在舞台上塑造的那些帝王将相、忠臣义士,以及戏台上那些超越世俗的纯真的爱情,是这个令人闻名色变的“枭雄”内心最柔软的渴望。杜月笙守护孟小冬,守护她的傲骨,守护她的初心,何尝不是在守护自己已经永远失去的梦想。
舞台上的第三位“生”——老生余叔岩,则是一种舞台与生活的合一。和那些纠缠于爱恨情仇不能自拔的俗世男女相比,余叔岩很潇洒——潇洒得略有些不真实。身穿长衫的他总是在孟小冬最痛苦、最迷茫、最绝望的时候出现。在话剧《孟小冬》中,余叔岩更像是孟小冬的精神图腾,在一次次即将陷入无尽深渊时,如一点星火,重新点燃孟小冬内心的追求。当孟小冬为自己的最后一次登台准备时,镜中的他与孟小冬重合在一起,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最终一一迭现——唐明皇、正德、程婴……在这一刻,戏与人生,难分难解。
众声杂沓的“龙套”们
在光辉夺目的“旦角”和色彩驳杂的“生角”之外,舞台上还有一群来去如风的“龙套们”:自以为是的“梅党”、捕风捉影的“记者”和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龙套们的加入让这出整体风格沉闷的话剧有了一丝诙谐之感,也让话剧带了一丝音乐剧的轻快之风。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去如风。他们没心没肺如同小丑,他们以最崇高的理由进行最卑下的窥视。滑稽可笑的他们却是悲剧的最大推动者。他们将别人的人生当作一出戏。起哄、看热闹,甚至,亲身“下场”编戏,试图左右旁人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旁人的幸与不幸只有精彩或不精彩的分别,却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感受。甚至,那些自诩事事以梅兰芳为重的“梅党”,在剧中恰恰是最令人反感的一群人。即便去除对于他们的小丑式刻画,他们的行为本身也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反思。有一个正义的“动机”,我们便有资格“导演”别人的人生吗?人生,毕竟不是一出戏。
而这一群龙套们,在台上反映的更是一个时代。看话剧《孟小冬》的时候,总会想到另两个人。那个写下“人言可畏”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和“越剧十姐妹”之一的筱丹桂。在这个黑白混淆、人情冷漠的时代,女性不易,伶人不易。阮玲玉、筱丹桂死于流言之下,更坚强的孟小冬逃过来了——却也曾遍体鳞伤。
幕落,话剧《孟小冬》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是孟小冬封箱之前的16个小时。那些不断闪回的瞬间,更是一个女子抗争平庸,追求情感、艺术极致的一生;而那些鱼贯而出的人物——春秋战国、汉唐宋明,更是茫茫古今的岁月与悲喜。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舞台上,那些穿着戏服、戴着髯口的老生们演的是故事里的事。台上的孟小冬、梅兰芳、杜月笙、福芝芳、姚玉兰、余叔岩,演着自己,把自己演成了故事。而台下的我们,看着故事,或许有一天,也会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2024年4月,上海,中国大剧院,有一场话剧《孟小冬》……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