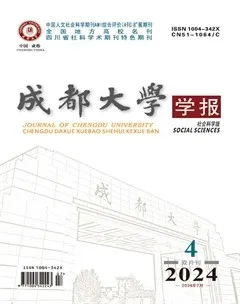作为事件的文学接受
摘要:传统观点将文学接受视为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还原或文本对读者的影响,这缩减了接受活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在事件论视域下,接受作为文本与读者的遭遇事件而发生。冒牌读者与开放性文本是接受事件发生的前提条件。接受作为事件发掘出接受者同一自我之中的他者,造就一个新的自我的同时生成通向现实的另一条路径。接受者回返到现实得以生成的过去,动摇现实的存在根基与确定性,重置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创造出新的知觉对象与知觉方式。接受作为事件揭示了意义生产之非重复性和不可还原性,释放出接受活动中的偶然性、不可能性和非现实性,由此走向一种非决定论的文学接受观。
关键词:文学接受;事件;现实;虚构;偶然
中图分类号:I04;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4) 04-102-13
文学事件论是文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接受反应研究是文学事件思想的重要构成,但事件视界下的接受反应或接受反应中的文学事件与传统接受论有何区别?它是对接受哪一维度的拓展和哪个层面的揭示?这一点仍未得到阐明。传统接受反应研究往往单向度地从读者或文本着手,或考察读者对文本与作者意图的还原与恢复,或探索文本施加于读者的效力与影响,要么将接受反应缩减为读者与作者两相契合的“一致之思”,抑或将其归约为经接受而生成的情感结构,这些观点预设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称与契合关系,以恢复和重构的双重活动缩减了接受反应本有的复杂性与现实性。将接受反应研究等同于对作者意图的恢复或文本效力的追踪,实际上是对接受反应的向下还原与向上还原。a 然而,接受反应中总有一些比作者的意图更深又比文本的效力更浅的盈余,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单向影响难以穷尽接受反应中的所有景观。“事件的起源隐藏于黑暗之中”a,文学作为事件有其难以为接受者穷尽的幽灵性与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源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根本不对称”b。接受是对文学意义的回收,事件性则是对这种回收的拒斥和回收之后的残留。文学事件论的出现为重新发现接受反应活动的复杂性提供了契机。
文学事件中,接受反应产生于文本中的隐含作者与“冒牌读者”(The mock reader)的正面遭遇。“所谓阅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邂逅的运动”c,是文本事件与阅读事件的纠缠与碰撞,是读者迈入另一未知世界且前途未卜的历险活动,接受中的可能遭遇“极大地超越了我的认知功能,我的情感自我、有时使身体自我也处于冒险之中”d。文学事件中的接受—反应是过程与中介而非结果与前提,文本与接受者被卷入其中,经历一场双方都不能预知结局的冒险。读者被拉出日常生活的惯常经验秩序,“突然闯进了一个一切只能由偶然性和偶发性来表现的世界”e,熟悉的视域将会关闭,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中闪烁着诡谲离奇的异世风光,那里有被劈为善恶两半仍能自由活动的梅达尔多子爵,也有对母亲之死无动于衷的局外人默尔索,有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生存法则,也有为我们熟悉的人情世故,这些景观只有在与之相对应的接受反应中才会呈现出来。事件论视域下,接受是一种呈现和展开的过程活动,“是作为始于一定时空中写作的行动而存在的”f,它是借助文本再一次发生的写作事件,是“响应写作表演的一种阅读表演的形式”g。接受是文本意义被激活与重置的行动事件,接受者的每一次进入都会“带领作品走向已习惯的思考领域的边界”h。
对接受者而言,进入文学事件意味着跨出自我并走向另一种生命持存,意味着在另一个世界中发现我们从未怀疑过的自我构成及存在边界,松动其根基,重置其构成,至少不再毫无知觉地生存在自以为了解但却所知甚少的“自我”框架中,让自我由先验的无意识主体变为被意识的客体对象。进入文学事件“包含着一个重塑和更新某人思考基础的意愿”i,意味着暂时悬置作为先验前提的自我,被迫卷入一个我们可以知觉但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中,以近乎“离身感知”的方式看到在另一个世界中骤然暴露出的自我边界,看到异域事件逐渐软化与销蚀附着于我们的信仰与期待,“从外部世界身上剥去其僵硬的异己性”a。卷入文学事件的接受者从过去自我的延长线上分离出来,逐渐呈现出一个无前见的赤裸自我,又在接受事件中装配上新的信念。经历一种作为事件的接受活动意味着孤注一掷,准备失去并准备获得,履足其中的人看似依旧如初,但其自我构成与存在边界已经发生了只有自身才能察觉的巨大变化。进入文学事件需要稳定而不顽固的自我构成及绝对好客的态度,那些只是在门口观望并随时准备撤身离开的人无缘进入事件的中心,因而不能开启文学冒险的旅程。文学之于他们只是生命之外的纸质文本,而不是另一种生命生成的可能。
一、接受事件的发生前提
冒牌读者(这是沃克·吉布森的术语,艾柯称之为标准读者,二者是异名同指)是接受者进入文学事件的身份设定,是在阅读中产生的接受者的第二自我。这意味着读者愿意遵从文本的行进逻辑,参与到阅读冒险中去,签下脱离原有自我的契约,从而“踏上了新的冒险历程”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人”b,这包含两方面的要求:其一是具有足够吸引力与开放性的事件的邀约。在文学事件的感召与诱惑下,读者愿意冒着可能损毁现有自我的风险,“连续不断地邂逅身为他者的自己”c,投身于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之中。而一个不成功的文学事件则不能提供具有影响力的邀请,读者拒绝进入文学事件,“拒绝戴上那样的面具,拒绝扮演那样的角色”d,文学事件所在的世界还未展开就已经崩塌。
其二是读者对自我的定位与期许,即我是谁和我要成为谁,这影响着文学事件的展开及其可能效力的施行。坚不可入与弱不禁风的自我同样不能正确地开启文学事件,前者在文学事件与自我构成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明白无误地将“文学体验中的模拟世界和日常经验中的真实世界区别开来”e,导致事件世界时时受到现实规则的入侵与干扰,屏蔽与驱逐了现实规则之外的可能经验,并将其斥为荒谬与虚假;后者则无限放大了文学事件的可能动量,读者自我在冒险中被完全击毁而不能复生,这影响了其他读者对文学事件的期望与判断f,可能导致文学事件在政治或宗教力量的干预下走向湮灭。接受事件的发生需要两相契合的读者与文本,读者需要保持“一种不会妨碍高度警惕的独特的被动性”g。冒牌读者的理想形式是“他在读许多本书并对它们的语言世界作出响应时就变成了许多人”a,在文学事件结束时拥有了包含异质却不致走向分裂的杂合主体。
文学事件为冒牌读者开辟通向新世界的路径,同时还为其“打开通向重新发现被湮没的经验的大门”b,让读者在遨游新世界的同时能回顾所经行的来路,察觉自我蜕变与生成的历史,在被难以驾驭的力量裹挟着的同时又保持着重返归路的希望。文学事件引导感觉的更新和被压抑的旧经验的复现,在文学事件中接受者遭遇生活拒绝给予他或禁止他发现的东西,或者复活那些对他充满意义但已不可复得的经验遗迹,“在日常现实之外去展现另外一个世界”c。所谓在现实之外,意指接受事件中出现了与既定现实中的经验序列不同的新的可能,但同时它也在现实之中,文学作为一种虚构“其实是能够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只不过还不具备其发生的场合”d,指向那些本有可能成为现实但由于被我们忽略而坍缩的可能性。它是当下现实有可能生成的另一种面向,是未成形的、未现实化的现实。
与其说文学事件开启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异空间,毋宁说它找到了生成现实的另一种可能,破解了坚不可摧的、独断的现实神话,踏上了恢复其他可能性的道路,回到了当下现实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的原始境域中,为其规划一种新的生长路径,并导向现存固态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平行现实。文学事件的展开过程是另一种现实的生成过程,也是已有现实逐渐坍缩乃至消灭的过程。接受作为事件的吊诡之处在于,就逻辑而言多种现实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因为从原初可能到既定当下存在无数条生成现实的路径,也就具有无数种变成真实的现实;而就实存而言,现实的生成只能是一种消退与新生的复杂运动,是“一种隐与显、表露与掩盖之间既互相控制又互相扩展的相互作用”e,一种现实在其他可能空间的坍缩中形成,一种路径的开辟伴随着其他行进路线的阻塞与湮灭。伊瑟尔论述了文本中的否定和空白的产生与消失,正确地揭示了接受事件中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转化,文本中空白的填补和不定点的连缀消灭了其他的空白和不定点。接受作为事件揭示现实生成的偶然性,又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生成的必然性。
与其说接受事件通向未来,毋宁说它在重新制造过去。“人类现实不仅是新事物的产生,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过去(批判的、辩证的)再生产”a,通过对现实生成路径与生成条件的探寻、怀疑与重置,宣称当下现实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存在,在重返过去的旅途中揭示“现有现实是唯一现实和必然现实”这一断言的不可靠性,赋予参与者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与观看姿态,让接受者进入现实的外围和夹缝之中,解除固有的观看方式而向更多的可能性开放,让他们在应当冷漠处热忱,在应当热忱处冷漠,在视距的推远与拉近之中生成一种新的触摸现实的方式。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以游手好闲者弗雷德里克的观赏视角将充斥着血与死亡的1848 年革命转变为一场与读者无关的戏中戏,严肃的历史事件被转化为可欣赏的戏剧表演,死亡的残酷性与革命的必要性受到了质疑,真实的革命行动变为对之前革命行动的戏仿,文学事件是对革命的双重戏仿,接受者参与其中的看戏心态又构成对戏仿的戏仿,即他知道这是一场戏剧“表演”,因而他也在“表演”观看。
文学是一种“面向未必可以被还原为意义的事件而敞开的一种复杂的装置”b,在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之间制造出居中的裂隙,动摇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关联,又将它们置于一种戏仿式联系中,相应地改变了接受者面向历史的姿态与在现实中的生存姿态。事件论是一种“后”理论,它强调差异性、解构性和对秩序的反叛,将接受理解为事件继承了福柯对现实秩序合法性的质疑,继承了德塞托和朗西埃对文学解放潜能的肯定,在形式主义浪潮之后重新赋予文学介入现实的重要功能,并将文学的意义由简单的揭露或批判提升至对现实根基的动摇和重塑,在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意义上肯定文学与现实的同构关系。同时,它还破解了先验的主体观念,认为文学接受不是先在的固定主体吸收和容纳外部经验的过程,而是反过来,正是从文学中获取的经验不断生成、重组并更新着主体的架构。只有在肯定文学的现实性与主体的可变性的基础上,文学生产出的差异才拥有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事件重新激活了文学关注现实的伦理维度和塑造主体的教育功能。
二、接受事件的生成路径
现实自称具有完美的外形和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它矢口否认其生成过程中的艰辛努力与黑暗历史。现实只是通过否定自己的起源才形成了它们现在的样子,只要回过头去摧毁了起源,它的统治的合法性便无可动摇。现实只有宣称普遍性才能掩盖其历史根源,因为那些新格局的形成要依赖那些曾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只有当现实通过切断与他者和不被承认的过去的关联而获得自主性时,它才能等同于真实,也才能代表某种天然合法的真理。文学事件使现实得以形成的条件可视化了,从而造成一种特殊的自我意识,它并不轻信现实的宣言,而是退回到对其存在条件的逐步探索与检验中去。“文学能够探索并且动摇人们最深层面的共识”a,发现不可动摇的现实中的偶然性与他者,让被释放的他者向我们讲述现实生成的秘密,由此将目光投向现实的暗处,期待和发现被宣称为不存在的东西。
进入文学事件意味着从现实的确定状态回返至未定状态,丧失原本无可置疑的坚实的立身之基,进入现实不可知的和神秘的缝隙之中,发现日常现实所遮蔽的古怪和奇异之处。或者反过来,重新思考我们对什么是古怪、什么是正常的固有界分,揭去遮盖在现实表象上清晰而有秩序的假面,发现现实原来才是最古怪的这一可怕的事实本相,并对现实变得古怪的原因加以解释。这一原因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偶然的、随物赋形的,“新的背离是无法从可能的创新中被预测的”b,接受者只能在被卷入事件并遭遇他者的过程中才能知道究竟是哪些存在被现实所隐去,哪些他者仍有重新复活的机会。在接受者的不断行进之中,文学事件的视图也不断发生变换。因此,文学事件的接受呈现出一种混沌状态,每一次遭遇都会有不同的入口、路径和由之生成的新的世界图景。
接受事件的狡黠在于它勾画出一幅现实得以生成的可能图景,这一可能图景悖论性地既存在于现实之前作为其前提,又存在于现实之后作为其结果。它自反性地回到过去,寻找到那些与现实并立的还未坍缩的他者,以此动摇现实的独一无二性;问题在于只有当他者坍缩、现实生成之后,接受者才能拥有这样的后见之明。要是现实图景根本就不存在,就不会有接受事件发生的空间,“其映射含有无数种可能的方向,但基于该文本,只有一个方向能够浮出水面”c。接受必然只能是一种非自主的、部分的意义复活行为,接受者不得不以特定姿态和特定视点进入事件之中,事件世界的无限性在接受者的行进中缩减为一种有限的可能性。更奇异的地方在于,文学事件的展开过程便是其自身存在根基的消亡过程,它一边生成一边消亡。接受者进入事件遭逢那些被剔除的偶在之物时,偶然性就被置换为必然性,接受者走入暗处逐渐复活那些死去的他者时,事件世界的流动性与无定性就被转化为另一种现实固定下来。事件世界的逐步明晰伴随着一个新现实的诞生与其他可能性的死去,事件走向了自己所要反对的固定实存,一种新的统治秩序重新杀死了事件。接受者在事件的世界中打捞起现实中的不可能性并将其转变为事件中的可能,这就是事件的自我生成与自我撤销,就其实存而言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就其效果而言,它使得任何一种天然固定的存在都成为不可能,“事件的现象化使读者认识到,这种历史循序渐进的目的论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这样,他对世界的明确无误的因果关系所抱有的自信便一扫而光了”d。
接受事件把各种原本确定无疑的历史事件作为重新构造的对象带到近处,展示出一种连续性历史的人为特性,又破坏了历史真实与叙事真实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揭示了现实的虚构与虚伪。事件从不否认自己与偶然性相关,现实却常常将偶然的虚构伪装成必然的真实。在此,真与假的标准被置换过来。接受事件中接受者以偶然性构造偶然的世界或思考这个世界,它以此为自己创造世界,生产知觉对象的现实与知觉自身的现实。俄国形式主义力图通过知觉的非自动化“把一种完全不合惯例的缺乏快感的知觉强加给读者”a,通过新奇的知觉造成现实潜能的流溢,但被知觉着的现实仍旧是那个现实,变换的只是知觉方式,并且知觉的方式始终在现实的框架中被给予,依托于现实的知觉形式造就了知觉对象,其实质是以一种变形了的异名同指的知觉隐晦地将现实再度合理化。因此,“陌生化的技巧这样就有可能再一次失去它的批评功能”b 而转化为现实的合理化工具。
接受事件中被解放的不是知觉而是知觉对象,形式主义的路径被翻转过来,不是人们以第一次见到事物的眼光去关照对象,而是一个新的对象和新的现实骤然侵入到习以为常的知觉中,直接的、给定的知觉习惯无法辨认骤然遭遇的知觉对象,猝不及防的知觉只能听任偶然之物的摆布。划定知觉边界、知觉范围的现实规则被冲散,日常生活中的“相关的、有意义的相似性与偶然的、虚设的相似性”c 逐渐被模糊,在过去现实中稳固的、连续的、有一定逻辑的知觉体系和知觉能力反而变得不真实,清晰稳定的知觉世界因偶然和例外的知觉对象的现身而骤然崩解。因此,在接受事件的卷入者身上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这个世界——表面上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模样——在另一个人的眼睛里会显得很不一样”d,接受事件的解放功能就在于使人反讽地认识到现实之真实性的欺骗性。在接受事件中,事物突破了语言和意义之网,带着一种根源上的不明确性和意义上的不可规约性,“事物到来了,作为无意义的、无情感的事件出现”e。
在事件论视域下,接受是施为而不是传达,是创造而不是反映。接受事件中主导的是冒险性因素和面对即将到来的未知物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动摇了知觉的同一,引动和激发出不连贯性、不稳定性、盲点与压力,骤然出现的不能被思考、不可被言说的东西导引出一种非还原性的知觉可能。接受事件重新配置了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幽隐难寻的部分被推到舞台的中央,显而易见的反而成为行动的背景。现实之不可能性与现实性在于其倒果为因的机制,“结果被假定并被诠释为其自身原因的原因”a,现实简化了结果与原因之间的连接回路并在特定的二者之间指定了对应性关系,磨平了“通常可以指望的东西与特殊情况下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真正张力”b。接受者在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样不自由,现实世界中的习以为常的规则在文学世界中被陌生化,显示出我们一直以来拖着何等沉重的镣铐前行。
但接受事件与日常事件之间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因为“文学并不总是在事实和虚构、艺术与历史、想象与信息、空想与实用、梦想与说教之间清晰划界”c,它作为一个可能的中间地带协调与再划分现实与虚构的距离,事件的潜能就潜藏在已经跳出现实且尚未在别处落脚的悬空地带。文学事件并不通向完全不可知的异域世界,而是呈现出现实的表现形态与形成过程之间的不对应关系,在其中自我与他者的偶遇生产出可能的意义秩序,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构成可能性的每一个成分的实现。接受的意义存在于“两者之间的非重复性、非同一性和非一贯性”d 所激起的惊诧、接受与认同之中,但并不仅仅包含主观心理状态的变化,它更是真实世界未完成部分的预演性重构,“事件性表现为一个微型宇宙,在它促狭的空间之内凝缩了整个可能性世界”e,接受者以从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和面向事件的反应方式回应并塑造自己的现实。
接受事件的发生要求“负责地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不把作品可能的用途放在一个网格中的阅读……也不会把判断传递给作品或作者……这是信任阅读中的不可预测性和向未来的开放性”f。因为我们无法从现有世界来推断对未知世界中他者的义务,这意味着接受者只能在文学的生成与展开过程中行进,体验“事件的发生过程”g,在接受活动中将文本创生活动“表演”(Performance)出来,即以表演的方式重现文本事件的创造过程。这种重现不等于对作者意图的恢复,也无需寻求与作家意旨的契合,而是对文本自身形成过程的回溯式恢复。这种恢复活动包含“赋予意义或者抵制、减弱意义的意图”a,指向与文中隐含作者的正面遭遇以及关于意义的争夺、斗争、协商、妥协与双向改造。阅读重现写作事件的同时也对其进行转译(translation),它是对在某一历史时间被生产出来的作品的真实生成方式的转译,也是对作品创造过程的真实体验的转译。说得更明白些,阅读活动戏仿式地表演了作家的创作与文本的生成,这是一种必要但不忠实的表演,真实的创造活动和作家注入文本中的原始意义作为被悬置的所指,在阅读与接受的延异活动中得到重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与文本是被复活了,只不过已经不再是复活之前的那一个了。
这一表演过程由伊瑟尔所谓的“本文的结构来引导”b,读者进入文学事件的姿态和遭遇文学事件的反应“会受到他正作出反应的作品的重塑”c,文本中作者的预设会把接受者的“习惯性倾向作为不适合的东西加以排斥”d。意义就在文本构成和读者响应的双向互动之中产生,呈现出一种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间性效果,“既体现(本文)效果的结构,又体现(读者)响应的结构”e,但又不等同于本文意义和读者响应。“文学事件没有那种存在于自身中而使下一代无可逃遁的必然结果”f,文本结构和读者响应只是从外部暗示意义缘什么而起和意味着什么,诉诸文本结构有将意义消灭在固定语言框架中的风险,求之于读者反应又会造成意义的奇异性在日常经验中的稀释。但接受者却只能经由这些路径迂回地发现意义的存在踪迹,因为它“不能被归结为某种现存的东西”g。从逻辑上来说,将文本结构和读者反应视为原因与开端、将意义的产生作为结果与目的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结构与反应是接受事件发生与演化的不同结果,接受事件将自己的印记打在文本与读者之上。因果逻辑应当被扭转过来,正是在接受事件中,文本与读者才逐渐生成。
“作品不是一个占有某种意义或一系列意义的客体或符号结构,而是一个事件的行动,也是一个行动的事件,那么我们是同时指写作的行动—事件和阅读的行动—事件”a,接受意味着触摸到文学与读者之间不可归纳的关系,意味着判断文本的无数特征中哪些才是应当被发现和被重视的,这种判断与期望总是在事件展开的过程中因遭遇不可预测的他者而受挫,“在其中每一步都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b,那些前所未见的或无法解释的实体、观念、形式引起接受者的惊异。进入接受事件意味着遭遇或承受某事,暴露自身并接受改变,接受事件起源于主体内部和主体外部的一样多,让我们在摒弃一些东西的同时也从遮蔽中带来一些模糊的感知。接受作为事件会超越现实预先编织的意义的秩序,实现对日常意义的重置与再造,达到一种不寻常的符号深度与语义密度,为一种读者内心酝酿已久但无法表达的思想提供了形式。“事件开启了意义和情感的新的可能性”c,那种体验可以是在回顾往事中骤然发现的,也可以是在漫无目的的前行中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在这个层面,文学既不建构现实,也不表征现实,它在将我们卷入接受事件中的过程中提供给我们一种把握现实的新尺度。
将接受理解为事件意味着肯定意义秩序的复杂性、混沌性与可能性,其对现实的认识是在将其与文学相比照并在事后反思中获得的。接受者在此过程中对文本的合法性和现实的合法性进行双重质疑,通过揭露现实的运转逻辑和文本为经验赋予意义的方式,使读者获得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之明。因为接受总是一种卷入其中的有限视角的参与活动,接受者无力应付与文本相遇时产生的所有可能元素与相互影响,他被自身的行进习惯和不期而遇的他者所形成的合力推着行进,会陷入认知盲区和经验的死角。通过现实与文本的比照,读者意识到日常意识阈限之下或之外的存在,意识到现实经验的有限性和自我认识的不可靠性,那些接受者习焉不察的无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与他发生关联的偶在之物,这些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历时与共时地与接受者进入同一个事件,或者与其不期而遇,或者不远不近地对他产生非接触式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事件是一种鲁迅所谓的“呐喊”,重要的不在于喊出的内容,而在于喊叫本身及其对被惊醒者的震动。
三、接受事件的施为效力
进入文学事件意味着对文本内部空间的开辟和时间的延展,这种空间性实际上“体现在作品累进式的、无间断的线性结构上”d,这一结构构成文本的基本样态,伊瑟尔称其为文本的召唤结构。召唤结构并不居于读者之先,而是在读者进入文本时被意向性地发明出来,“文本所谓的事实都是由阅读创造出来的”e。就其发生而言,召唤结构附着于文本的创造;就其实存而言,它总是现实化于接受者出现的场合。分处两个不同时间的文本与读者生产出对话的空间,由此产生穿越性的时间错置的结构,重置了“一部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与实质意义之间的可变的距离”a。阅读既是对文本的恢复又是对文本的创造,将文本从一种名词性的稳定结构转化为动词性的流动过程。社会历史批评询问文本是关于什么的,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询问作品本身是什么,这些提问方式都暗示了一种将文本当作静止的、无时间性客体的看法,文学事件关注的是文本意味着什么和在接受活动中发生了什么,语言和意义的透明性和自明性被夺走,我们体验到一种过去感或空间隔离感。
文学接受是一个反复进行而不会重复再现的事件。“经验读者(empirical reader)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本文所暗含的标准读者的类型进行推测”b,并依据自身在接受事件中的经历构想出一个制造了文本事件的标准作者,经验作者、标准作者、经验读者、标准读者四者之间构成不对称的交往关系,接受事件就发生在多重主体交往活动的中间地带。文学事件论是对偶然—必然、表层—深层结构模式的反讽,它拒绝将意义系在一些不可更易的深层结构之上,“反对本文实质上表现了‘什么东西’也就是反对某种特殊的诠释——可以根据‘本文的内在连贯性’揭示出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c,读者、作者和文本的神话在接受事件中都无立身之地,任何决定性的力量都会“退到舞台侧翼”d,卷入一种共享的意义建构活动。接受事件的发生是多点接触而非单向度的读者使用或文本影响,它重新清理了内与外、关联性和非关联性之间的秩序,突破了意义的惯性和解释的秩序,每一次接受都将之前的文本及意义世界置于受怀疑的境地。文学事件中接受者的行动也会触及到文本空间的暗处与缝隙,撞破文本不能说出或意欲隐藏的秘密,接受者由之可能掷出文本不允许提出的问题,动摇不能被质疑的支撑框架,事件世界可能反倒因为读者的非预测行为而改变。
文学事件既质疑现状又设想可能,并设法将可能转化为现实,这种作用是通过语言与现实的断裂和重新组合而实现的。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被革除, 产生了一种“碰巧而随机构成的任意性”e,语言的重置更新了词与物的连接模式,由之激发的对现实合理性的再审视产生出重构现实的力量,开辟了从虚构走向现实的通道。现实与幻想、偶然与必然本来就只有一墙之隔,二者常常相互渗透并重造彼此。接受作为事件打破了现实提供的可能选择的集合,改变了接受者进行选择的前提,扭转了被规划好的选择路径,在虚构世界中恢复了以词造物的神奇魔力,催生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生产与现实中同样真实的体验,并由这种体验导引出欲将现实改造为此的期望和行动力,隐秘地形塑和制造了它许诺和期待的东西。
文学事件正是那种“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目的,改变我们所遇到的人、事和本文的用途而改变我们自身的东西”a,是一种开发偶然性、质疑必然性、并追问其何以被划分为偶然和必然的思维方法。“事件就是已实际发生者的不可能方面”b,在文学事件中,接受者的目光通向过去与未来,可以看到不在场的事物。接受作为事件意味着不仅要我们回答文本所提出的问题并发现其可能答案,还要求我们探查文本何以提出这些问题以及不能提出哪些问题。接受者并不被动承担给定的意义,而是在接受中发现并创造意义,要求我们将文本中被弃置的偶然视为至关重要之物并与现实秩序加以比照,虚构与现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效果,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不言自明的自我主体、现实世界和文本意义是成问题的。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事件的接受者陷入一种存在主义的境地,他丧失了“一个可以观看和感觉一切事物的‘意识中心’”c,因而既无法在事件中听从先知式的作者的教谕,也无法遵从自己的内心,因为事件中的偶在之物已经宣称了这二者同样不可靠。
文学事件关涉的对象“绝不仅仅是自我,必须把个人之外的意愿纳入考量”d。就接受活动的过程或归属而言,将接受理解为事件意味着拒绝高扬主体性的浪漫主义文论创造的天才式作者,也解除了接受美学视域下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决定权,同时也反对将意义理解为深层结构的形式主义理论。从这一点来看,事件论破除了原有的机械还原论和单一因果解释论,更强调生成论和分形的复杂因果解释,接受活动由执其一端的主观论与客观论走向居中的、调解的事件论。就接受活动的意义而言,事件论反对将文学与现实相隔离的审美无功利论,而是承认与肯定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但这种关联既不是自上而下的由特定意识形态主导的强化或合理化,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感性解放与秩序颠覆。因为这种观点预设了文学与现实的二分并认为文学存在于现实之外,且为文学赋予了一个外在的目的。事件论视域下,文学存在于现实之中,构造现实并超越现实,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经验的意义秩序和体认现实的可能途径,但同时它又暴露了这些意义的不完整性和不可靠性,为后来的意义生产预留了空间。
简言之,一种单一的、毕其功于一役的归因论应当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接受者卷入其中的混沌系统论和事件生成论。
(责任编辑:刘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