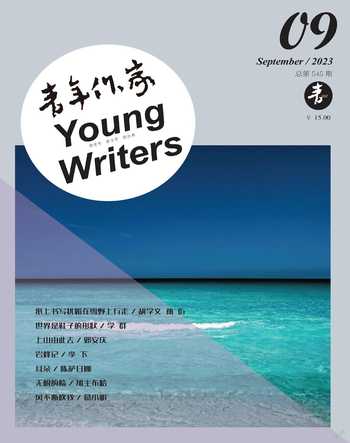江有沱
卢鑫
夜展开身子,停伫沱江边。以灯影制造的人工大月亮,循环展示圆缺盈亏,悬挂于泛橙光的简阳小森林之上。我们边走边聊。行走利于幻想,闲聊益于映照。那轮摇移之月,呈银色,极其炫美。它将平顺的时间肆意摇动,令时间自由翻穿。时间一去不复返的逻辑,让位于意识的小舟。事情慢慢在变化。越来越暗的江浪扑打沱江南北堤岸,发出细吻微吞声。芦苇嘶嘶响动。大伙儿正把彼此的阅读史、写作史、生活史,对诸事万般看法,从漫长思绪清单中牵出,犹如抽捋心灵深处一根根隐秘游丝。
夜的渐浓,我们从地下通道冒出头,发现它已在小城上空恭候多时。我们在转弯处的空坝就坐,吃上一碗冰粉。嘴上言说的句子,如花瓣落下,形成倒影,又被勺子舀碎。此乃时光五彩缤纷的余味。
初夏已经来临,日子清爽、风韵犹存。午后的前锋村,鸡在路边扇动翅羽,打起快意的呵欠,它们旁若无人,扑扑啄啄草丛里的养分。一只两个月大的阿拉斯加小宝宝被主人抱起,睁开好奇的小眼睛,热心与陌生人握手。同行友人边听话筒里的村况介绍,边端个玻璃大杯沿湖慢走,惬意喝杨梅冰水,而后折返村里小水吧归还晶莹之杯。来此地过周末的孩子们趴在水畔,专心钓吃腻了白色豆腐饵的小龙虾。可惜毫无收获,纯属浪费心情。我用小网帮他们舀起缓慢游动的一条。与此同时,三五老人坐在空坝藤椅上,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草坪音乐此起彼伏。时而有大叔高唱《爱拼才会赢》。万莹会闽南语,她拿筷子夹锅边馍馍,给出公正评价:“发音心适!”时而有穿白色休闲衣裙的老婆婆尖唱《青藏高原》。地里扯草的农人们回家换鞋,无法忘怀带来远古呼唤的歌声。我们在布棚里埋头吃柴火鸡,谈种番茄的大棚,对比哪个省辣椒更辣,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操心不已。
其叹也歌,其啸也歌,时光随之倒流。上午站到龙泉山最高处,可以远眺这块盆地四围神幻而灵动的雪山。无穷无尽的分分秒秒陪伴川内数条江河流逝,雪山们至今皑皑碧峰寒。它们如同专注倾听锦城丝管的热心观众,多年来从不擅自离席。试图完整讲述此番悠悠抱朴之史,需要作家运用大量省略号。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剥开一颗颗硕大的橙黄色枇杷,就剥开宴安自逸的新生活点滴。
我第一次注意到,凿开龙泉山、引水入简阳,是盆地历史结构上难忘的一环。想起妻子以往语焉不详的叙述。半个世纪前,那时她还没出生,她听长辈们说,她的祖母,或许正是挖掘隧洞的大众成员之一。对民众来说,打通龙泉山,给大盆凿一个隧洞,让都江堰那古老、科学、超前的水利枢纽生发新用处,让岷江水冲破屏障,灌溉农田,他们必须亲自见证。
于是大伙儿用简陋的铁锤、钢钎,提着马灯开工。祖母与其他人一起,把撮箕里的土石倒进板车运走,像王屋太行下那个神话家族一样,拿起锄头挖土。她神色激迈的脸庞魅力十足。我们无从得知叩石垦壤,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具体力量。后来发生意想不到的突变。某个大雨滂沱、泥石冲刷的下午,祖母身体受损,她多处骨折,伴随着多处伤痛。幸好大伙儿把她抬进华西医院,一位医生亲戚为她接骨。半年后,祖母方才养伤痊愈……工程一如既往地进行,终于灿烂阳光照耀喷薄的水渠。噢!这些珍贵的水流为盆地省城增添活力。历史每天在文化馆内陈列。民众请愿书、伟人批示文件、当年的挖土工具,使我们闪回昔日光景。
“我不能看这些。”安庆兄哽咽,墙上,开渠前,受旱群众在泉氹排队挑水的照片显眼,“看到这些,心情都受不了。”
次日我们到尤安村、荷桥村。作孚先生民國写就的乡村建设文字,躺在尤安村图书室。荷桥村办公楼贴满孩子们的心愿。如“满书包零食”“不吃萝卜!”“希望妈妈每天都可以抱抱我”“长大想当雨(孩子写的就是‘雨,可能当时不会写‘宇字)航员”等。还有想要游戏皮肤的,有想天天睡懒觉的,有不想做作业的……我把这些村落的状态拍下,发给身在重庆高山的母亲。我老家位于重庆边上的深山小村,地势远不及这里平坦,父母返乡搞种植业,多年来,他们种下满山的菊花。
走进临靠大水库的“悠然岛”,时光在蓝雪花的摇曳中变得轻盈。老板已来此经营六年。她包下整座荒山,做成休闲山庄。养花,种草,砌石阶,培植几亩金丝皇菊。喝着菊花茶,吃着圣女果,我把视频发给在老家同样种了金丝菊的母亲看。这时,加主布哈爬树摘来几个杏子,我吃得如同一位眉眼皱缩的老太太,差点没把牙齿酸落。
回程的火车上,忆及两句题于简阳文化馆墙壁的诗歌:“万载衣冠付冥寞,路人无语奠椒浆。”第一天,登电梯站在文化馆二楼栏杆边,俯瞰一楼土地空间规划。缩小版的简阳模型铺展,灯光璀璨,这样的俯瞰视角,很像巨人奥特曼的视角。于是我幻身为一个沉默的巨人,回忆艰难往事,思考未来难解的谜题。我看见这块土地上,龙垭曾有各色动物生老病死,互相伤害,互相成就。数万年前,暴雨来临,它们曾躲在树下、洞穴中一张一翕。林地中的东方剑齿象,也有了动静。它们将断裂、散乱的骨块重新组装,全身一点一点长满脂肉。我仿佛看见,这些远古的生灵,一步一徘徊,翻越小山,迈步沟谷,迟缓地行走在天府之国、四川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