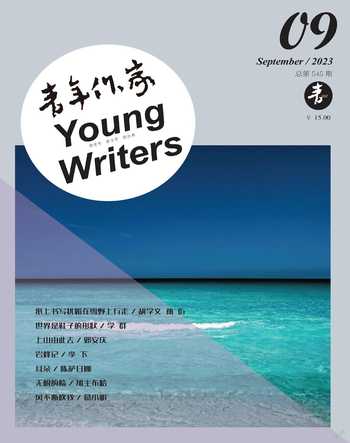春 见
“耙耙柑。”你说。
“好。”我离开你的床前,打开病房的门,出门前又看了你一眼。
南城的风凌厉刺骨,我匆忙从西城赶来。飞机落地,速度逐渐降下来,我看见舷窗外,渐渐飘起了雪花。这在西城是难得一见的景致,我曾专程去往北方感受。走下楼梯,跟随人群往摆渡车走去的时候,我渐渐两眼模糊。想起多年前写给她的一首诗里的两句,那年今日,人面桃花,那么陌生,却又那么相似。
雪花仍在飘洒,随风斜斜地扑过来,落在身上、地上,转眼就化了。我穿着长风衣,脖颈裸露在外,两手相拥瑟缩着往前走,仍旧无法取暖,双手已经冻僵了。这么冷的天气,我问你想吃点什么,你说想吃耙耙柑,我出来买。
市医院在老城中央,交通便利,医院边上的店面,几乎都是旅社、快餐店和水果铺。我穿过几张疲惫的面孔,向水果摊走去。每个铺子都装备齐全,各式水果,以及装配好的果篮,几乎应有尽有。我并不需要这些,你想吃耙耙柑,可是接连问了好几个店铺,都没有。急切的老板不死心,争相向我推荐其他水果,被我一一回绝。我只好继续找下去。
果然一无所获。印象里它们总会摆在果架上的某处,即使自己没有看到,只消问问老板,他定会指引你到它跟前。它就是一种橘子,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独特,大多数个头比我的拳头还大,用白色包装纸包起来,卖得比普通橘子贵很多。我最初吃到,是因为前女友喜欢。她总是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吃的、用的,比其他女孩子更在意和欣赏它们。比如毛蛋,比如在宜家,她总能在一大堆造型各异的动物抱枕中,选中我觉得最丑的那种。大约在这一点上,她更称得上是“以丑为美”的典范。如今一切已成過往,我有了新的女人,在一起两三年,正准备结婚。
拿出手机,搜到最近的一个商超,我招手打了一辆的士,往那里直奔过去。我只想尽快找到耙耙柑,称几只带回来。
医院附近,不知为什么总是显得破旧拥挤,的士行进缓慢,喇叭声四起,但路上的行人好似无动于衷,继续着他们的动作和速度。司机默不作声,我忍不住骂了一句。春天刚来不久,本以为一切都欣欣向荣,生机勃发,没想到一觉醒来,我就收到了她发给我的消息。
医院到商超的路并不远,穿越拥挤的人群后,汽车很快就在一个商场附近停下来,我扫码付了车费,开门走下车。不是周末,商场里人也很多,暖气开着,大家的脸上都很惬意,我想,这才是我们应有的表情。幸好超市里有耙耙柑,我在导购的引导下,来到那个货架前,发现耙耙柑并不贵,只是普通橘子价格的三倍多。挑了几个拿过去称重时,我才明白当初认为它贵的原因:每个的分量都有大半斤,三四个耙耙柑,三十多块钱了。
走出商场,天空似乎不再飘雪,我打算走回医院。这几天真像一场梦,从收到她的消息,到最终成行,历经周折,耗费了很多心力。来到医院,看见病床上的她,无以诉诸的悲伤,似乎在那一瞬间就决口了。我并没有当着她的面哭泣,而是当我来到洗手间,试图用冷水洗去路途的疲惫时,发觉脸上的水珠总是擦不干净,尝试了好几次,才发现自己在流泪。太冷了,好像悲伤和神经的运转都麻木了一样,悲伤涌溢,带动肌肉不可遏制地痉挛,然而神经却麻木了,难以从心到脑,把它们传递过来。
零星雪花积在角落,灰白一片,仍未融化。不见细雪飘洒,但寒冷无孔不入,没走几步,提着袋子的手已经冻得快没有知觉,我不得不换一只手,可不到一会儿,这只手又这样了。
穿过冗长寂静的楼道,我推开门,发现你的头侧向左边,似乎在看着窗外阴郁的天空。我走到床边才发现,你的这个样子其实是睡着了。我把耙耙柑放到门边的桌子上,病房里开着暖气,我在椅子上坐下来,又起身,想看看从你这个角度,能看见窗外的什么。一棵树叶落尽的树,枝丫的最中间,有一个用细枝筑的鸟巢,即使在阴天,也显得突兀,漆黑。
回到椅子上,周身的寒气逐渐褪尽,低沉的情绪似乎又回到了我身上了。看着此刻白床单下不施修饰的你,面容上的斑点更加明显,发丝干涩,摆出生硬的曲线,尤其嘴唇,已有几条细小的裂痕。你的睡眠总被梦侵袭,不知道是怎样的梦,让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不时会抽动一下,但始终没有醒来。
这个模样让我心痛如绞。
多年前遇见你,你刚从学校毕业,来我们单位应聘教职。我刚好负责人事这一块,与应聘者联系,尤其与你联系得多。你那时青春洋溢,刚读完了博士,眼睛很大,闪烁着纯净的光芒。你很漂亮,报名时负责收集材料的小伙子看见你的照片,在人事处惊呼起来,不一会儿这种赞叹就变味了,言辞里夹杂着戏谑,眼里流露出不可言说的神色。
身在其中几年,我以为自己也麻木了,偶尔也会加入这种调笑,对某个陌生或熟悉的人,说些模棱两可意味深长的话,有时候会忽地一惊,半途便以有事为由退出,回到电脑前或离开办公室。我讨厌这样的自己。我不知道自己出于自私还是什么,在你应聘的中途,就把你劝退了。也许是自私吧,我只想把你的美保留下来,不要被其他人糟践,也许我也只是想把你据为己有?现在想起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向单位提出休个长假,他们都很诧异。那么多年,我的假期从未休满过。也许在他们眼里,我已提前步入独身老年人行列,没有亲密的人,似乎也没有亲人朋友(怎么可能呢),没有夜生活,除了看书(并不知道我写作),已一无所有。这些年我的感情并不顺利,来来去去,对寻找另一半已没有了信心,失去了兴趣,直到王薇的出现。
领导签完字,并没有把假条推过来,而是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堆场面话,最后旁敲侧击,他不相信我休假的原因是探望双亲。我的双亲仍在外省一个遥远的乡下,依赖着几分薄地讨生活。但除了按时打钱外,我并不想见到他们,这些年因为催婚,我和他们几次翻脸,上次从大年初一离家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我坚持说是,最终把请假条要了过来。兴味索然的领导把假条给我的时候不忘提醒,把工作交接好,不要耽误了。
单位放行是意料之中的,我最不知道的是怎么向王薇解释。她也是学校老师,每天都在学院里,工作认真,也严于律己。她比我更早来到这里,我对她的了解并不多,后来在同事的口中陆续听到关于她的一些消息,单身,未婚,甚至都没人见她处过对象。这些八卦消息,往往是传得最快的,我对她并不好奇,听多了甚至也会厌烦。直到有次开校级职工大会,我偶然在会场见到了她,当时同事就那样随手一指。并不像其他人口中那样荫翳,她反而有种别样的清新。
其实她和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眼给我的感觉,都与其他人不同。
我时常会怀疑自己,比如这双眼睛,在面对你时,我不清楚究竟是你眼里的光给我的印象,还是我看见的你,自我生成的感受。这就像鲁迅评论《红楼梦》主题时那段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什么样的眼,就看见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
你那时背着一个黑色的小背包,穿着格子裙出现在面前,手里捧着一堆资料,说话的声音,谦卑,但又对陌生人充满信任。这世间有多少人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呢。何况是我。与你的目光对视之后,我就不敢再看你的眼睛,那里面有我无法抵挡的东西。或许我也自视清高,可是在你的面前,我那么轻易就被击溃了。我的心里一定藏有那不可告人的东西,肮脏龌龊,保留有一丝羞耻。
那时我就想与你有更亲近的关系,就是这种心里作祟吧。是的,我曾想得到你。那时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是,既然自己尚未结婚,也没有和谁正在相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第一次见到你就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心底那些幽暗的东西作怪,还能有其他解释吗?也许你遇到过如我这般躲闪的眼神,又或许遇到过更多大胆的眼神。它们侵犯,掠夺,粗鲁而毫不在意,但它们并没有把你吓退,你放弃,是因为我。
我深夜里给你打电话,没有想过你是否睡下了,也没想过你身边是否有其他人。那时你对这份工作充满期待,在前两个阶段的竞争中过关斩将,好的学校,很有优势的学术背景,极具竞争力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课堂表现(我是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的),自信又滔滔不绝,得到在场评委的高度赞扬。
显然你不像有的人那样,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觉得志在必得,胜券在握。那次面试结束后,你给我打电话,语气谦恭,就像第一天过来交材料,小心翼翼地探听成绩。我就像个公事公办的老顽固,没有给你透露过多的信息,嘱咐你耐心等候。听见你的语气,我竟能想起你的神情,我又何尝不为你感到开心呢。
事情原本这样下去挺好的,可是当我亲耳听见某个主任在谈论起你时,言语及眼神中流露出那股令人作呕的东西时,我才恍然发觉,事情并不简单,在你我想象的生活之外,有个更加真实残酷的世界。你我几乎都无能为力。
那晚我喝了酒。那个臭名昭著的人,这么久了,却仍旧稳坐钓鱼台。他的钓钩,在我看来,几乎就要钓住你了。我喝着闷酒,越想越绝望。我听说过很多人举报他,但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似乎更加有恃无恐,愈加明目张胆。我独自把酒瓶一次次举起,直到酒尽瓶空,我鼓起勇气,拿出电话,劝你放弃。
我不知何时站在窗边出神,你的呻吟把我惊醒,我转过头,看见你微睁着眼,也在看着我。你眼里的微光一闪一闪,看着像泪光。
“好点了吗?”我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你在脸上挤出笑脸,两个浅浅的酒窝出来了。“还好。”你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想给你倒杯水,你说:“不用了,不渴。”我想起刚刚买的耙耙柑,从桌子上拿过来,说,“我给你剥一个吧。”
“放这儿吧。”你说,“现在不想吃。”你从被子里抽出左手,对着床头柜指了指,上面放着各种药片,一本反扣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我把桌面稍微整理了一下,把没有看几页的书合上放好,再把橘子放在上面。印象里你读过这本书,但我现在并不想和你聊它。看着你唇上似乎因缺水翻卷的死皮,我又问了一句:“想喝点水吗?”
你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我们多久没见了?”
时光逝若流水,我在心里确认了几遍,说:“五年多了吧。我记得那年春天,你实在受不了家里的烦扰,离开西城回到南城老家,就近找了个学校。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以为很快能再见,谁曾想到多年后,再见是这副模样。”
你的目光好像又潮湿了一些,眼睛从我身上移开,看着雪白的天花板,自言自语般。“那个时候真软弱,去西城就是为了逃避爸妈,没想到他们把我逼得更紧,让我还是乖乖回来了。真是命运如此。”
我曾听你说过你的家庭,年幼时甚至成年后的无力感,母亲的阴郁,父亲的暴烈,活在家庭阴影中的恐惧。你想摆脱,但摆脱不了。有次你对我说,当父母因为某件小事在家里大闹的时候,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躲在被窝中,捂住双耳,试图逃离,可杯盘碎裂的刺耳声传到你这里,比刀割还难受。我记得你当时神色平静,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想,如果窗户外没有防盗网,我会立马跳下去。”
王薇是个直性子,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她的职称晋升之路一直不顺。但我们俩走到一起,可以说是王八绿豆,对上眼了。
提起这个,又不得不回到我曾说过的,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内在的某种联系,仅需通过眼神就能领会,明白彼此心性相通。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大概都是这种隐秘的关联在发挥作用。我们都与周围的人显得格格不入,对某些事情保持着本能的愤怒,能够相互体谅。
那次散会后,我和她是走进食堂吃饭的教职工里位数不多的两个。我打好饭菜,看她面前的座位空着,就走过去,在那里坐下来。她起先是惊诧,汤匙含在嘴里,送进口中的食物还来不及咀嚼吞咽,两边的脸颊鼓起来。我做了自我介绍,她没有,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她的名姓。
那顿饭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开头我和她打了招呼,末了,她比我先吃完,留下一句“慢慢吃”,就径直离开了,留下我鼓胀着口腔嗯嗯应和。
后来我又在食堂碰见过她几次,渐渐两个人就固定坐在了一起。我事后想了想,从前那么多日子,我应该在食堂中见过她,只是没有人和我说起,并不认识而已,我总是独自一人走进食堂。
最先得知我和她“在一起”,还是在同事的口中。不知道哪天吃饭被他们撞见了,回到办公室就开始听起自己的八卦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嘛,当我觉得好笑又无力解释时,是否内心在渴望你之后,又对她心生期待?
这是一个并不骤然的过程,我们逐渐平复了内心的怨愤,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彼此的身上。她并不知道我曾對其他人动过心,和她走到一起,似乎也因为迷恋两人间的相似之处,她更在乎现在的我,喜欢彼此依偎,踏实安恬,生活可以确定的部分。我是否一直在欺骗她呢?但我从未做过背叛她的事情。曾经迷恋过其他人算是背叛吗?我也曾这样问自己。在遇见她之前,这种迷恋已然消失,并未困扰我的生活。反而是她的“出现”,让心底某些模糊的东西重又泛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快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候我害怕去想其中的关联,生活中似乎有很多东西,不应该那么固执地追根究底,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你认为生活里的脏东西,在有的人看来,那就是甜蜜。
反之亦然。
你那时接到电话,似乎并不震惊,就像迟早会知道,只是消息提前得太早。那一刻我仿佛也明白了更多的你,一个不是我眼中所见、另个模样的你。听我说完,你平静地说:“好的,知道了。”
我以为你并不想放弃,又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气馁,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睡意全无。没过两天,你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到咖啡馆坐坐。那时录取结果并未出来,但似乎这也并无影响。接完电话后,我在想,你会和我说些什么呢?
在咖啡馆刚坐定,你就说你放弃了,不是因为我说的那些,而是因为我。
尽管咖啡馆里没什么人,几乎寂静无声,我的耳中还是一阵轰鸣,许久无法恢复正常。两个陌生人,一个人的重大抉择,怎么可能是因为另一个人呢。你说完这句话,一直看着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眼神却忘了躲避。心里有个东西可以确定了,你就是我以为的那样的人,我没看错。
你这句话也让我感到释然。我本对你怀有的幽暗心绪,顷刻之间好像被一扫而光,两人相处时的紧张感也没有了,变得放松。仿佛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忽然就融通了,消失了,让直视和交谈变得轻松,简单。
我没有问你原因,我们的话题也从此荡开,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成为了真正的朋友,没有欲求,但又彼此牵系,我拿起书时会想起你,走在路上时也会想起你,甚至躺下,也会想你是否还在灯下阅读。我知道你就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一个人,你也像我一样,很难找到一个与你心意相通、值得彼此托付的人。我们太像彼此了,无法成为恋人。
某些阒寂的暗夜,我会在空荡的床上睁开眼睛,幻想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想象总是那么美好,以致在与你见面的某些时候,我甚至有向你表白的冲动。也许我真的那样做了,而你只是当作玩笑话,任它随风飘散。
我一直在与自己的欲念作斗争。那个时候总在想我们无法相爱的原因,什么样的人合适与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也许每个人天生就顾影自怜,喜欢临水自照,他(她)要么孤独终老,要么会找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就像是镜中的你我,互为映照。我想我们哪怕真的在一起了,分开会是必然结局,那在一起又有何意义?
不论白天抑或午夜,那些忍不住的时刻,我们都表达过对彼此的思念,就像我们都曾坦然地对彼此说过“我爱你”。
我们找不到不爱的理由。我们也找不到在一起的理由。
我是带着你的影子和她在一起的吗?我不清楚,当然王薇不可能知道。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为此感到内疚。
我们在一起,并准备结婚了,接到你的电话,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王薇的感情并不像我一样细腻,或许是我太过细腻了,以至非要在男女之间,确认一种纯粹的友谊。那是友谊吗,还是失败的爱?
我想过撒谎,想过逃避,就像不得不承认她和你之间的联系一样,为自己找借口,尽管这些很难说清楚,无法非是即否。王薇身上有她独特的部分,你与她的相似或许将我们拉近了。但与你的不同之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愈加地习惯和依赖她。她比我勇敢,正直,并能付诸行动。这个我逐渐迷恋的女人,我怎么忍心伤害她呢?
事情迫在眉睫。许久之后得到你的消息,又是这样的消息,我如何能不感到惊慌。那一刻我甚至覺得,你在我心里的重要性甚于她。死让我感到惊慌。
那天甚至来不及等到下班回家,我独自在校园里走着,既想早点告诉她,又不知道如何说起,踟蹰犹豫。来到学院,刚好看见王薇从洗手间出来,她看见我,嘴角微抿,显露一丝笑意,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之前从未在上班时候找过她,我感到歉疚,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不敢看她的眼睛,只好低下头。她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一些并不愉悦的东西正在蔓延,等着我开口。总是这样,她单刀直入,我半天憋不出一个屁。好在她有耐心,见我仍旧沉默,她说先去办公室坐坐吧,转身就要进去。
“我要出差去探望一个朋友。”我终于说出口了,没有谎言。
“去吧。”她似乎并不想知道更多。
“一个女性朋友,她患了……癌症。”这两个字,穿刺着我的喉咙,我很难说出口。
她的神情稍有变化,但仍保持着一贯的清冷。“去吧,早去早回。”
“我想……我想陪她一段时间。我向学校请了长假。”
她的神色又变了,清冷的脸上有了惊诧,眼神中流露出些许陌生的感觉,也许这种陌生,是她眼中的我的陌生。她看着我,仿佛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
西城的天气舒适,但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冰冷,是燥热,还是麻木。我又说了一遍,仔仔细细,声音放缓了一些。还未说完,王薇转身离去,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我了解越多的你,就越是惊讶。你比我历经的更多,很多于我而言,都是至暗时刻,都是肉体与心灵的深重折磨,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于你而言,我的人生简单得像一张乱涂乱画近乎空白的纸。除了写作时那些臆想、诚恳与痛苦之言,我还有什么能打动你?
这么多年过去,时间不止在你脸上增加了皱纹,疾病也在你的身上展露真面目。我不清楚这是忽然显现,还是在它漫长的折磨中逐渐显形,你的变化让我不忍目睹。
陪伴你的这几天,你一直在回忆过去,那些与我有着丝缕关联的事物。你的父母每天都会过来,可每次都待不了多久,你的沉默似乎蕴含着什么更深的寓意,他们陪不了一会儿就会借口离开。而离开前,总会和我使眼色,让我走出病房,让我倾听他们的感激、疲惫和忧虑。他们把我当成救命稻草一样,期望给他们女儿最后的慰藉。
而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在医院附近租住的宾馆,夜里似乎总能听见外面传来的哭声,患者好像更愿在夜深人静、万物阒寂时离去。我也在等待王薇的消息。那天她离去,关门,任我怎么呼唤都不开门,也不回应。一路上我都在打电话,给她发信息,她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我想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是同样的反应吗?我感到矛盾和歉疚,来到南城后,我几乎没有合眼。
你变得越来越虚弱,这个病好像一下子把你拉垮了。说不了多久,你就要闭上眼休息,那本放在床头柜上的书,反扣在那里,你已经看了三分之一。
我坐在那里,等候,倾听,大多时候都愣愣地看着窗外。雪花时有落下,不远处的梅园,里面的梅花稀稀疏疏地,正在开放,一点点,像鲜红的火焰。街上的人还是穿着冬天的衣服,仿佛春天仍遥遥无期。
相比于多年前,你的话更多了。我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有时候你会向我求证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关于某本书,关于西城,或关于某件久远的事情。我的悲伤压抑多于回忆,我想和你聊聊现在,或者未来,但这个话题怎么才能说出。直到有次你喝水后,似乎若有所思地看着某处,我才主动问你:“这些年,一切都好吗?”说完我就觉得自己很愚蠢。
回过神来,你淡然一笑。“我结过一次婚”,你说,“不过很快就离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遇见了对的人,但最终会发现并非如此。说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生病后,曾告诉过他,但他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也没问候过一次。不过没关系。他后来又结婚了,还有了孩子。”
“我也准备结婚了。”我说。
你很惊讶地看着我。
“嗯。我遇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但又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说……”其中的细微我尚且没有理清楚,就说出口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你不应该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应该,究竟是我没有说出的,还是已经说出口的。不管怎样,我好像确实做错了什么。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回想那些年与你有关的点滴,那些亲密的时刻无非是并肩走在路上,或者相对而坐,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举动,就是你离开西城的那天,我送你去车站,在进站前,我把你叫住,拥抱了你。此后彼此虽有电话,我们却像两个倔强赌气的人,谁都不肯先主动联系对方。
也许这些年我们真的失去太多了。
你变得少言,还有些局促不安,总是怔怔地看着窗外。
桌子上的耙耙柑少了两个,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已经被你吃掉了。“以前只和你吃飯,喝咖啡,见你吃过葡萄,苹果。我给你剥个耙耙柑吧。”我说。
你忽然就笑了,说:“你买的不是耙耙柑,是丑橘。”
“怎么会呢?”我说,“我以前吃过的就是这样子,表面皱巴巴的,超市也不可能搞错啊……”
“不常买的人,经常会混淆,耙耙柑和丑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耙耙柑的皮肤不会这样丑巴巴,像得了什么重病……”说到这你也停了下来,不再开口。
我看你的眼里噙着泪,神情开始有了多年前的样子。正欲抽纸巾递给你,没想到你说:“早点回去吧,不用天天陪在这里,你来看我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你说话时并没有对着我,而是双眼迷蒙地看着窗外。
“你别多想,”我说,“我已经和她说清楚了,是她鼓励我来的。”我撒了个谎。
你转过头,看着我眼睛说:“我累了。”
手机传来叮的一声,那么久了,它终于有了动静。我说:“你睡一会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你侧脸躺在床上说:“没什么了,你早点回去,这些天我看你也没睡好,也累了。”
回宾馆的路上,我拿出手机。消息是王薇发来的,她说,我们得谈谈。
我把电话打过去,她把电话挂了。我回信息说,我回去后和你好好谈谈,把心里藏着的,想到的,都告诉你。
春雪又落了下来,比前几次更加急促,雪白。我忽然又想起写给你的那首诗最后几行:你看它们就要飞过来了/飞过来了——/我害怕它的白。
【作者简介】李路平,生于1988年9月,江西赣州人;作品发表于 《青年文学》《散文》《天涯》《诗刊》《长城》《星星》《美文》等刊,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小说月报·大字版》选载;现居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