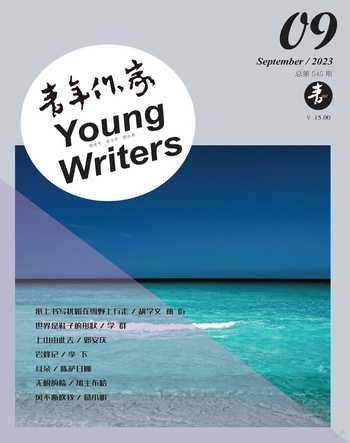简阳漫行
李下
大巴在路上。远看,野杏胡乱缀在枝上,像稚子的画,浑圆又稚拙。每一颗果肉都用了心,仿佛神笔马良,提笔那刻便在期待成熟。座上习惯凝视语言与记忆的朋友们,把目光送去,逡巡在树下,遥想解馋的时机。
不消片刻,车停在简阳市规划馆外。三五结队的青年,径自迈入一座历史与未来垒砌的空间。简阳的前世今生,在此显露:以文字碑刻,以壁画泥塑,以讲解之清扬,以科技之炫目,宛然另一座“天府”在岁月中显现。
恕我拙笨,对数字和名人不够敏锐,好些简阳的具象描述没有演化为准确的记忆。若借搜索引擎强行说之,词句也会因干瘪而露怯。只说一件令我动容的壮举,上世纪70年代,为解干旱之苦,简阳欲引岷江灌田,遂全民举铁锹、擎钢钎、背竹篓,以人肉之躯,凿穿龙泉山,两年有余,“东灌”功成。规划馆称其为当代“愚公移山”,名副其实。闻听工程种种,恍惚间萌生一念,恨不能生于斯,只因这等工程是天然的叙事矿藏,牢固且丰腴,稍一采撷或考究,便能滋蔓出无数动人的父辈乃至祖辈故事。可以说,这个工程至少藏着一部恢宏的长篇小说。当然,这只是一念,我非借此苛责故乡的匮乏,只是表达一种钦羡。
稍后,道路送我们至乡下,前锋村以黄昏相迎。虽属黄昏,太阳却直剌剌悬着,没有归山之念,反煽起风,掠池塘而来。扑面的风,以五月之名,提前召唤仲夏,在西南大地烹煮出燠热的蒸汽。对这份热,我不愿领情;可对桃杏而言,它们求一己繁盛,向天地讨要光热,可不管你们这些被节气规训的人类。
天不久潲色了。风和人一样止步,它静候夜晚的“热岛环流”,我们静候晚餐。各有各的心事,互不干涉,也不嫌弃。只是我们攘进帐篷欢宴时,想必风是无奈的。它窃听不得那些关于文学和青春的感伤,也无法化入酒肠,在觥筹与酒气间,窥探那一张张与文学有关的脸,究竟显出何等神色。
酒足饭饱,口齿却缺一味酸甜。那是路边的野杏勾致的,因为不得逞,便一直惦着。
饭后,同几位朋友散步,像沸水咕嘟一样吐露各自的文学传承。长久以来,只与心对晤,或借笔抒怀,很难有同伴一起畅谈普鲁斯特或马尔克斯。怎料在简阳,我们这些异乡之客,竟能轻易地进入文学,不必担心辞不达意,无需拘泥遣词造句,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发乎于心,余则爱咋咋的。这种久违的畅快使我不惮于孤身面对异乡的夜晚。
次日,大巴继续驮载我们行至简阳深处。尤安村率先闯入视野。红砖地面敞亮迎客,联排民居以一种不易勾画的井然规划布局。身在其中,不觉迷惑,只是恼恨自己不识草木之名,又懒于借手机搜证,只能干巴巴地欣赏各家门前那一丛浓绿和时而飘至头顶的碎花。对人间名词的匮乏和无知,使我羞愧。那便低下头去,藏身人群,听别人讲。
幸亏桃树解救了我。当得知桃子可采,青年们跃然而起。陡然间,尤安化身花果山。一群“泼猴”上蹿下跳,尤以男人顽劣,扯拽树枝,将卖相尚可的桃儿一并拢去。洗洗便吃。说是没农药,看桃树们野性难驯的样子,也不像有药。我本不嗜吃,但食色本能和游戏姿态作祟,便无暇多想,只管尝来。吃桃之余,瞥见墙壁上到处有繁复艳丽的彩绘,或似马蒂斯画风,只是添了乡趣,韵致不凡。
出尤安村,往荷桥、协议两村去。沿途,山壁土丘上的杏,一再现身,执拗得紧,非要揽我这个客。今天,我的心思倒不在它们身上,而在摇滚。说来惭愧,我听流行远大于摇滚。但“摇滚”光看字形,就觉得火辣辣的,像岩浆,像沸水,一副泼开来去的气势。“流行”如溪流,平滑有余,热烈不足。车座上,好友在侧,从摇滚讲到“万能青年旅店”,谈及他们的专辑《冀西南林路行》,说是借鉴了艾略特《荒原》的叙事结构。我读过《荒原》,印象隐约,大体忘了。但因着这个说法,使我眼里的万青不再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万青,而是《荒原》的万青了。
好友不惜流量,为我播放万青,其中一首《山雀》,“大雾重重,时代喧哗造物忙;火光恟恟,指引盗寇入太行。”四句歌词,黄钟大吕,我虽不解其义,但汉字摆在那里,就有一种不可撼动的力量。这是只属于诗歌的力量,从《诗经》上查考方能体会。
山西亦有太行,为何是万青入太行,而我却长久地忽视了这两个大道至简又耳熟能详的文字?
我还未想出个所以然,悠然岛就到了。该名取自陶潜诗句。陶潜为我所爱。他所言的精神境界,“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向来是我的理想之境。只是我一介俗子,难以致之,只能辗转凡尘,挤出些力气做点喜欢的事情罢了。
这么没志气,恐怕也配不上喜欢陶潜。算了,不说他,改说岛,这岛实为一处田园居所。落英没有,芳草正茂,从一条曲径上去,竟撞见活生生的杏树。我们拥上去,或采摘,或捡地上熟透的。彼此不客气,对杏树更不客气。昨日的心心念念终于成真,反倒没了那种渴望。人真奇怪,或许只是我奇怪。吞嚼几颗,杏终于遁去,遁入肠胃,也遁入昨日。
当晚,简阳以海底捞盛情款待。觥筹交错间,倒忘了滋味,只记得各位师友无不谦卑热情,哪里有什么文人相轻。只是我羞于沒什么作品,不敢声张,只是躲在人后,敬酒也吃酒,甘愿一醉。
我的确醉了,但步子不显,还能言谈。搭上俩友,走上街头,径直来到一处广场公园,我们像瓦尔泽一样散步。说起出版和文学之事,也说埋藏已久的情感。我们轻易地推心置腹,像没交过朋友的傻子。我乐于做个傻子。
广场对岸丘陵连绵。陵上有一轮庞大的月。庞大不是文学笔法,是真的大,因为是人造的,所以大得出奇。都能看出它假,但它就自顾自地亮着,还模拟月相,来个圆缺转换。我们就那样走着,在圆缺的反复下,好像漫过了岁月的筹算,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遥不可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