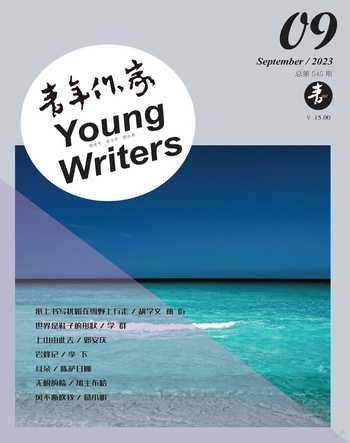寻找座位的人
2015年8月29日下午,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在长庆站等38路公交车,手机响了,是一个我尊敬的前辈。前辈说,在B城,他熟悉的一家单位正缺一个文秘,问我愿意去吗。
“愿意。当然很愿意。什么时候上班?”
“下周一就可以。”
长庆站是G城最为拥挤的公交站台之一,因为地处城中心,在这里等车的人总是很多,学校又在终点站,为了抢一个座位,我总是侧身站在街边的站沿上,高举着脖子朝车开来的方向张望。汗水成股地从额头、鼻尖钻出来,既不合时宜又无所忌惮地在我脸上涂满了一道道沟壑和山峰,偶尔,嘴里会渗进一股黏乎乎的咸,锋利而霸道,让人忍不住颤一颤。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嘴里都是这种近乎苦涩的味道。我从手提包里取出特意准备的手帕纸,叠一层,再叠一层,先铺到额头,再是鼻尖,然后就是整张脸。纸再次回到手里时,像刚涨过一次海潮。38路车终于冒出了尖,先是一个红色的半圆和圆,而后便一步一个脚印地飞驰而来。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一个闹钟在催,快点,快点,冲到最前面去。我飞快地朝四下扫一眼,一边预判车辆停靠的位置,一边绷紧了身子随时准备如箭一般笔直地射进去。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冲刺路线,快速来到站台边不那么聒噪的地方。
38路车慢悠悠地停下,起步的瞬间,打嗝似的边走边摇。原本拥挤的人群如溃开的大堤,转眼消失在炎热的街头。在G城三年,一年十二个月,从五月到十月,有半年时间都在过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挣不开逃不掉如无数堵厚墙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热,谁都愿意在室内呆着。车已经开远了,很快,站台上的人又再次繁盛起来。我站在人群之外,久久不肯挪动半步。电话早挂了。我翻了翻通话记录,和前辈的通话不到两分钟,就在这两分钟里,我把自己的未来交付了出去。
我捋了捋头发,脸热乎乎的,似乎有些发烫。要知道,等九月份开学,我就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大四学生了。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就业季,连续两个周末,我都奔走在G城的大街小巷。那天下午,我吃完午饭就出门了,按照计划,我需要买一双面试穿的高跟鞋和一套衣服。听往届毕业的师姐说,高跟鞋一定要單根,五厘米最好,白色、杏色、黑色都行,衣服也要端庄、成熟、优雅,至于颜色,也一定得稳重大方才好。我从一家服装店走进另一家服装店,不断地脱衣服,试衣服,头发早就毛燥燥地蓬松起来,天又热,额前的刘海也软塌塌地贴着脑门。
等逛完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我的手里还是只有一个包装盒,那是一双米色高跟鞋。试鞋的时候,抬头、挺胸、收腹,右脚迈出去,左脚再跟着迈出去,在镜子前转个圈,正面看了,侧面和后面也要看,还好,小腿后的肌肉只是微微鼓起,线条虽不够流畅,却也没有过分引人瞩目。穿这样的鞋子难免受罪,仿佛咬着牙把脚塞进一个精巧的容器,要抬颌,要开肩,要挺背,要收腹,一举一动都得按规矩行事。才试穿了一会儿,我的脚底板就浮起一层雾气,脚后跟也浅淡地晕开一团绯红。
“新鞋都磨脚,可是好看呀。”导购语带尖刻,整张脸只有嘴在动,好似说着一个举世皆知的真理。我站在鞋架前默不作声,佯装不去看那些豆大的黑色标签,每看到入眼的鞋,却忍不住要拿每个月的生活费去换算一番。
鞋店里人来人往,我围着鞋架走完第二圈,再一次回到了最初试穿的那双鞋子前。就这双吧,材质虽然硬了点,胜在好看,价格也能接受。我犹疑着把鞋拿到收银台,收银员一手提鞋,一手扫码收钱,而后,盒子一盖,袋子一装,把鞋递到了我的手上。
衣服还是迟迟未定。有正式一点的衣服吗?每走进一家店,话还没说完,我却先低了头。我找的时候导购也在帮我找,当我抱着一堆我看上的和导购推荐的衣服走进换衣间,每次上身前,最先做的事就是看吊牌,要是价格太高,还没穿心里就先有了数,再好看也不要。
当穿上那些按图索骥找来的衣服时,我看到的是,镜子里的那个人,由于身材过于娇小,再小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都要空荡荡地多出一圈,再加上少有时间如此郑重其事地装扮自己,从进店到出门,始终眼神瑟缩,身子紧绷,手放在两侧不行,放在腹部也不对,让面部表情也越发慌乱。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抱歉,等会,又空着手走,那多不好意思啊。等再一次低下头,衣服和人也一发不可收拾地奔向了两个极端。确实不合适。
买衣服的挫败感日益膨胀,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能做什么呢。绞痛感从小腹出发,一路蜿蜒到头皮、脚心,巨大的疼痛贯穿全身,我将要被命运的风吹到哪里去呢?又或者,压根就没有单位要我。直到前辈的那个电话。
彼时,我正在G城的一家事业单位实习。单位就在长庆街背后,下了38路车,拐进左手边的那条小巷子,在第一个路口右转,步行两三分钟就到了。巷子是老巷子,实习单位也藏在几栋老楼里。从一扇铁门进去,再笔直往前,穿过一道玻璃门,上了二楼,左手边的第一个办公室就是了。
实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暑假来临前,我将修改了数十遍的简历挂到招聘网站,直到放假,依然少有问津。我把这件事说给了一个前辈,前辈说,他试试。没过几天,我便接到了前辈的电话,他说,已经联系好了,放了假就去吧。
我的那把椅子是临时安放进这间办公室的。正因为临时,办公室又窄,每进一个人,椅子便挪一次,每出一个人,椅子还得挪一次。挪椅子需要技巧,腰弯到一半,两只手拿住椅子的两边扶手,小腿顶在坐垫边缘,根据需要或左或右,或前进或后退。那声音很轻,像点水的蜻蜓,一遍又一遍地贴着水面飞行。
整个夏天,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八点,我都会准时从学校宿舍出发。公交车迎着太阳奔驰而去,金色的光芒跳荡成无数的浮尘,窗玻璃也微微在抖。上班就是,每当你睁开眼睛,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座位在等着你。21年里,曾有无数这样的座位短暂地收留过我。日子一临时就难免动荡,随之而来的便是慌张,甚至整个人都成了惊弓之鸟。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我第一次走进大铁门的那一刻起,那口气就一直吊在我的喉咙里,我近乎惯性地缩紧了身体,脚步声、咳嗽声、谈话声、笑声……所有的声音于我都是一场风暴。那就笑。也只能笑。见了谁都笑。
我成了单位里那个开门的人。每天早晨,放包,烧水,打扫屋子,然后,静坐在所有的座位之中。每一个座位都有它们要等的人,唯独我。我日复一日地走进这间办公室,日复一日地不属于这里。窗帘上的日色由浅渐深,屋子里的光有如收到一半的伞,正无可挽回地变得黏稠而浓烈。一天将过,那些座位又一次地空了出来。每次关上门的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要再看那些座位一眼。
我是中午到达B城的,拖一个半人高的行李箱,穿一条红色连衣裙,马尾快扎到头顶。红裙子是接到前辈的电话后特意买的,七百五十元,是我大半个月的生活费。朱砂的红,棉麻材质,裁剪修身,长及脚踝,一旦穿上,便滚火般在我的身体上蔓延。那是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成为自己的时刻之一。恍然间,另一个女人从镜子里钻出来,款款走向我。
当年升入高中的第一节数学课,数学老师和我们的第一面就是穿的红裙子。她说,红色代表热情,她热爱教书,也热爱我们,所以,她就穿着它来见我们了。说完,圆滚滚的苹果肌便爬上了她的颧骨,跟着,大大的眼睛慢慢收窄,黑亮的眼仁一点点陷进眼窝,恰如若隐若现的雀斑。那时,数学老师参加工作不过三四年,第一站就是我们学校。她和那条红裙子结成同盟,以火的姿态进入我们,绚烂而决绝。那天过后,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当我走向属于我的座位,要是也像这样,那该多好。
B城是山和水的城,一条大江沿山穿行,江两岸的山不断拔节,最终把这个临江而建的只有几条街的小城裹进了山的腹地。到B城后的第一顿饭,是在江边的一家饭馆吃的。饭馆只有两张门脸,往深里走就是包间,包间不大,灯光也暗,一推开门,米色的墙布上便暗影重重。十个人里,除了送我的朋友和接我的前辈,其余七个都是新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夹菜,举杯,身体始终保持前倾的姿势,肩膀微夹,耳朵、眼睛、嘴巴全部打开,身体里仿佛塞满了火柴。燃烧自己需要勇气,我怀抱虔诚,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新单位的第一餐就是一道即兴考试题目,隆重也好简单也罢,被评判的意味挥之不去,谁都可以做那个伸筷子的人,唯独自己。在此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是跋涉了近四百公里奔赴而来的异乡人。饭桌上,我不断地被问话,不断地被欢迎,在人群中,被问和被欢迎天生就带着距离,我红着脸,绷直了双腿,未答先笑,用最大的认真把自己和盘托出。
寂静是从热闹过后开始的。包间里,人声渐次冷落,杯盘的哐当声一声倦过一声,终于,长长久久地安静了。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撕开了我在B城生活的第一道裂缝,在所有的声音里,我还是听见了那一道细微的回声。那是属于我的声音。极其幽微,极其认真,吱,吱,那是尘埃落定的声音。
新单位在一条老巷子里,进门是一个小院,门口正对着的是几间平房,门的左手边是一栋三层的楼房。据说,早些年前,这里曾是政府招待所。我被安排在二楼的办公室,正对着楼梯口。办公室的外墙上有一面巨大的落地镜,每朝楼上走一步,镜子里的那团红就轻颤一下,像是有无数的惊雷在脚下爆开。怯意从身体里醒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从此,我就要在这座城留下来了。
考虑到我是外地人,单位特意安排了同事小秦带我去找房子。小秦大我两岁,比我早到单位一年,身高一米八多一点,小平头,长得却很孩子气,眼睛弯弯的,像是随时都在准备笑。小秦把电瓶车推到院子中间,我坐在后面,身体后仰,有意无意地在我们之间泻出一条江河。然而,还没出城,就被交警拦下了。
交警说:“最近在严查,电瓶车不能载人,要没收。”
小秦的眼底闪过一丝忧伤,很快又笑了一脸,影子似的跟在没收电瓶车的那个交警身后,委屈地说:“电瓶车是单位的,我也是出来办公事,要是没收了,我没法向单位交差。”
交警不理。天底下谁不是在委屈地活着,就比如他们,在烈日底下,当身体里的盐从骨血里渗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在苦苦煎熬。我不敢看小秦,只好咬着牙藏着脸跟在他的身后。小秦的声音嗡嗡的,进一步退三步,在漫长的交涉过后,小秦把脸转到了背光的地方,用巨大的背影把我挡在了他的世界之外。
“我们走路去,没多远了。”小秦背对着我说。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含糊着问了一句。
“再看吧。”小秦驼着肩,走到了太阳底下。
小秦带我去的地方在城边,两三层高的民房沿着马路一字排开,马路两侧的水泥坝子被太阳晒得灰扑扑的,过一辆车,就仿佛升起一个虚妄的黄昏。大约走到第七个门面的时候,小秦停下来说,就是这里了。
从小门进去,跟着小秦穿过一条长长的昏暗的楼道,上了二楼后,小秦指着其中的一个房间,说:“这里之前也是住的一个同事,上个月才离开,你要是觉得合适,我帮你把东西搬过来。”
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矮桌,大概是窗帘过于厚重的缘故,连光线都在矮矮地瑟缩着。我站在门口,久久地凝视着这间屋子。就在这间屋子里,那个未曾谋面的同事在这里吃饭,睡觉,日复一日把自己裹挟在日光残留的暗影里。在灰暗的底色下,连同那些岁月,都已喑然失声。我也要这样吗?再抬头时,小秦已经不在二楼了。我跑下楼,跟在他身后低声说:“太远了。”
“那就只有去我那里看看了。”
出单位左转,巷子的尽头是一条主干道,沿着主干道右转,走300米左右就是小秦住的那个小区了。说是小区,其实也就是两栋6层高的居民楼。从小区外面看,灰色的水泥墙面业已变成深灰,在时光的淘洗中,原本细腻均匀的沙石渐渐扩张成无数硕大的毛孔,日日年年,像有无数张巨嘴张口拼命吮吸日益稀薄的人气。
小秦住在5楼左手边的一个套三。小秦说,本来,还有一个同事也要住进来,就在搬过来的前一天,他去了别的城市。那间屋子在马路那侧。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却被小秦收拾得很干净,连经年的木地板都袒露出幽深的光泽。还有,一拉开窗帘,就能看到蜿蜒的江河和无数的远山。在我的老家,也是这样无穷无尽的山。在离开老家的很多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那些山。还有,那些只有山才能给予的安全感,像是一种血脉,深深地埋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之下,它們无时无刻都在等着被唤醒。
小秦房间的门正对着进门处,房间右侧是浴室和洗衣台,左侧是卫生间。房间的右侧有一个小窗,也早用报纸封得严严实实。
“你干嘛住这个黑屋子?”
小秦的腮帮子不经意地鼓了一下,很快弯着眼睛说:“我觉得挺好。”
我低低地“嗯”了一声,之后,便是隆重的静谧。嘶嘶声缱绻着从我和小秦之间蔓延而过,再升起,然后铺开。我慢慢明白过来,我们还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我把行李箱搬进房间,开始擦灰,铺床,声音不大,听着却刺耳。我只好又一次地裹紧了自己,脚尖点地,连呼吸都藏了起来,我只想捂住所有的声音,就像当初实习时那样。
那天的晚饭是在楼下饭馆里吃的。暮色笼罩着整个小城,细雨淅淅沥沥,昏黄的路灯滚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像是氤氲着一段遥远的往事。那顿饭吃得很安静,结账的时候,小秦说什么都不要我给钱,他说:“就当是给你接风嘛。”吃完饭出门,我又一次问起了电瓶车的事。
“再看吧。”说完,小秦就离开了。
小秦的背影在雨夜里变得模糊,我慢慢朝小区里走,等到了楼下,却忍不住偷偷朝背后望了一眼。街上空荡荡的,还在营业的店铺夹杂在紧闭的门店中间,像是总也不肯闭上的眼睛。我抱着双臂打了一个寒颤,绒毛般的雨珠裹在红色的连衣裙里,一挨上身就软绵绵地塌陷了。等到了明天,我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座位。一想到这里,每朝5楼爬一步,都像是在朝圣。
在B城的日子缓慢而平静。每天上班,回家,生活比一条线还要笔直。最开始,单位给我在小秦的对面加了一把椅子,正好在门后。来来往往的人从门外进来,又出去,看见我,总要问一句,来新人了呀。我便站起来,点头,问好,双手叠放在腹部,那姿势,标准得赛过酒店门前的迎宾小姐。如此折腾了一周,再有人来问,站还是要站,身子却懈怠下来,一条腿暗暗靠了办公桌,直到人家都出门了,脸上还挂着半个笑。
小秦的活不多,要么是搬个箱子,要么是送个文件。大部分时间,小秦都趴在对面盯着电脑出神。有时候,小秦醺着大半张脸,头也点得勤,可一有人走近,他又立马坐直了身子。来人眼睛一沉,又飞快地抬起,再一斜,就叫人心生冷意。在这座办公楼里,这样的眼神无处不在,它们各为中心又相互串联,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磁场,被那些目光钳住的,不止是小秦,还有我。
九月还没过完,秋意就深浓了,门口比办公室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更能感知风,张扬,坚硬,浩荡。来到B城后,我再也没穿过红裙子,要么黑要么深蓝深灰,一律把自己藏起来。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学会了融入人群,除了小秦。住进5楼的出租屋后,我和小秦很少碰面,不管我是早归还是晚归,他都消失了一般匿在那间黑屋子里,不说话不开灯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国庆收假,办公室开始调整人员,小秦被调到了其他科室,我换到了小秦原先坐的位置。小秦的新科室人多事少,是众所周知的边缘科室。大家都说,小秦是被“流放的”。搬科室那天,小秦将资料整理好,扔掉桌上那瓶喝到一半的冰红茶,看了我一眼就离开了,脸上还是挂着笑。
办公室的其他人仍在埋头做事,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团火忽地蹿到了我的脸上,既庆幸,又不安。心想着要不要送送他,但两条腿依然软塌塌地弯在桌子下面,直到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我还是以小秦出门时的姿势坐着。他一定会怪我的吧。
电瓶车被没收的第二天,我刚进单位院子,就又看见那辆电瓶车了。我悄悄问过小秦,怎么要回来的?小秦垂了眼,轻描淡写地说:“找了一个朋友。”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小秦吃完饭就去找人了,他周旋了半个晚上,腰从一个人面前弯到了无数人面前,才终于把车要了回来。这是跟小秦交好的一个朋友来出租屋的时候说的。那时,我正坐在房间里发呆。我想过要郑重地跟小秦说一句对不起,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下了。算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双手撑着下巴,像是从一个好长的梦里醒来。光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我坐在所有光的中间,开始从一个名字变成一种身份。没有什么比认清自己的孤独更让人孤独。我没有再想下去,至少,留下来的人是我。
不到一个星期,单位又来了新人,还是坐我的对面。来人是单位精挑细选,从B城层层筛选出来的。70后,个头不高,中等身材,皮肤稍黑,架一副金属细框眼镜。他说,喊他小张或者张哥都行。张哥修电脑很有一套,什么疑难杂症都能解决,唯独对文字材料不太精通,恰恰单位当时在B城广撒网的由头,就是为了招一个文秘。
我和张哥都在试用期。早上八点半上班,当我八点十分到单位,张哥已经打扫完办公室了。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又开始在身体里回荡。怎么办?怎么办?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在B城,除了前辈,我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可是,就这样贸然地去找前辈,好像也不太合适。再看张哥,正气定神闲地坐在对面敲着键盘。那就比他再努力一点,剩下的,听天由命。
加班越来越多,回出租屋的时间也从晚上十点到了凌晨两三点。不止周一到周五,就连每个周末,我几乎都是留到最后的那个人。B城的夜晚宁静而深邃,细细地听,仿佛还有江水流过的声音。回出租屋的路上,我总爱仰着头看星星,亮汪汪的,像无数深情的眼睛。在那些夜晚里,我曾短暂地忘记过我的身份。直到有一天,单位让我去领文件,拿到手里一看,正好是关于招聘文秘的事,只有一个名额。
张哥依然早到,谁找他帮忙都笑眯眯的,却有人在私下里说,光会干活有啥用,那写的都是个啥。我默默听着,忽地生出一种同命相怜之感。我们都是被命运卷到这里的人,我们都是挣扎着上不了岸的人。
一个下午,单位安排张哥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送文件。出门时,他敲了敲我的桌角,说:“一起吧。”我跟在他身后,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落在他的肩上,仿佛有一张网正从四面围上来。
他说起了他的大学。他说,他本来是他们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哦。”我并不相信。
“大学那几年,我是班长,成绩又好,就算不保研,也可以优先分配到大城市里的好单位。我都没去,回来了。不过,这也是没办法,我父母身体不好,得回来照顾他们。说到底,我还宁愿还在镇上教书。学生们都喜欢我,又容易出成绩,工资也比这里高。可我老婆在县城打工,孩子又刚上高中。谁想得到,半辈子过去了,左右不過一个没办法。”
“你呢?你怎么办?最好是早点找个人问问。”张哥忽地说。
“我?”从领回那份文件后,我就明白了,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张哥也不是。车已经出城了。我摇下车窗,葱绿的田野浮起一层烟色,风拍打在脸上,像撒了一地的玻璃屑。冬天就要来了。
再次见到前辈是在江边的茶楼,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墨色的江水,还有,一个似有若无的黄昏。我和前辈默然对坐,房间里,不时弹跳出叮叮的脆响,那是茶杯触碰玻璃桌的声音。
“只是,心里总觉得没底。”我坦白道。
“得有耐心。”前辈抿了一口茶,他脸上的深灰渐渐褪去,变成了浅黄。七点半了,江水荡漾着把灯光从很远的地方送过来,那依然是一张能给人温暖的脸。
转正的事迟迟没有说法,三个月的实习工资却一并发了,三千六百元,和小秦一样。不同的是,小秦还有一部分工资由县上发,算下来,不到三千元。
“够吗?”我问小秦。
小秦摇了摇头。这样的工资他领了十五个月,如果继续留在这里,这样的工资他还将天长地久地领下去。
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房租,每个月五百。房东是一个中年男人,刚住进这套出租屋的时候,我请小秦帮忙联系过他,看能不能发了工资再给房租。他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一次,我依然是请小秦帮忙把房租转给他。
三个月就是一千五百元,近乎工资的一半。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的复杂和简单,一个剪不断理还乱,一个不过加减乘除弹指之间。我关掉灯,在窗边坐下来,月光斜斜地射进屋子,在那一丛光影里,我和那把椅子连在一起,所有的阴影硬成骨头,就像我们从来都不曾分离。我摸了摸那把椅子的靠背,无论如何,它曾在这个夜晚属于我。
决定离开是在十二月初,送我的人还是小秦。我坐在后座,总觉得有一爿目光在席卷着我。此时,小秦站在行道树下面,整个人陷进了巨大的阴影里。我朝小秦挥了挥手,他还是没动。
昨天晚上,是小秦第一次回家后没有直接回他的黑屋子。他坐到客厅的餐桌前,对我说,在这里,他找不到属于他的座位。
这一次,小秦没笑。他耷拉着眼睛,头发也软绵绵地塌在头顶,像一只悲伤的山羊。
“那为什么不走?”
“我从小就成绩不好,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只读了个专科。毕业那会儿,我投了好多简历都没人要,父母年纪也大了,天天就盼着我有一个结果。我没法告诉他们,压根就没单位要你们的儿子。临到要离校了,听说这里还要人,所以就来了。你说,我又能去哪里呢?”
“至少……”
“嗯?”
“你在这里还有朋友。”
无尽的树在路边拉开巨幕,车里变得斑驳,我靠在窗玻璃上,现在和过去连同所有的光影飞驰而去。你怪我吗?这是我一直想问小秦的话。但还是开不了口。
细碎的雨点彷徨起来,在车窗上,有江河在不断地裂开,汇合,又裂开。我仿佛看见了我的数学老师,那个曾经穿一身红裙子出现在我生命里的女人,她早就不穿红裙子了。在我读大二那年,她专门给我发过一条信息:我们的一生,终将会把最爱的那种颜色丢掉。那条信息一直被我保留到现在。
从B城回学校后,我还是在等。一扇门开了,一扇门又关了,我总在想,也许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下一个始终没有轮到我。我就这样不停地走,在烈日下,在细雨中,在晨昏里,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汗水巴巴地从额头上冒出来,花了一个小时化的妆滚成粉的汗黑的泪,我背转过身,忐忑着把镜子凑近再凑近,在动荡的日子里,连面孔都变得可憎。然而,还是只能等待,无穷无尽地等待,填表、做题,然后失联。周而复始。
毕业后,几经辗转,我回到了最初的实习单位。还是原来的办公室,还是那张临时搬进去的凳子,不同的是,我再没有地方可回。
领导看我只身在外,提出将走廊尽头闲置的那间办公室改作单人间,也算一个落脚处。房间收拾了近一个星期,防盗窗要安,窗帘要换,破损的地砖也要重新贴。办公室里不时传来吱啦呜啦的机器声,那些声音穿过漫长的一天,结束一个又一个黄昏,我默默坐着,目送每一个人离开。等走廊都空下来后,我飞速锁好门,紧紧捏住开门的钥匙冲到另一扇门前,当锁孔里的迷障散去,我光似的溜进门,把整个身子贴在门后,再泥一样地软下来。我终于开始属于我自己。
屋子里只有一张书桌、一张床。我在网上淘了一个简易衣柜、一个电饭煲、一个鞋架,即便如此,屋子里也十分拥挤。八月的一个深夜,我淌着汗醒过来,窗外只有零散的几点星光,单薄,易碎。我伸手摁了摁床头的开关,夜色沉重,丝毫不见散开的迹象。再摁,还是深不见底的黑。一阵惊慌闪过,等坐起身,打开手机一看,才知道是全城停電。
哦,原来只是停电了。浑身的每一个关节都在变软,一起软下来的,还有始终支棱着的两只耳朵。我闭上眼,想要再次睡过去,床却着了火一样,挨到哪里,哪里的肌肤就慌慌地冒汗。就是热。叫人绝望的热,坚固而倔强的热。我只好站到窗边,等着风经过。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等到风,就像是这间屋子已经被风遗忘。
临近毕业,我曾接到过小秦的电话。那天下午,我刚吃完晚饭,正疾步穿过宿舍楼下的闹市。道路两旁,无数的灯把打印店、服装店、小吃店和化妆品店串成了一片耀眼的白,我低着头,比任何时候都渴望黑,漫无边际的黑,汹涌着淹没一切的黑。我只想把自己藏起来。
电话响的时候,我也跟着抖了一下,像是被一串惊雷炸开。小秦说,房东又在喊交房租了,你再给他说一下,你走了。
“没有人再住进来吗?”
“没有。”
“那你还住那屋?”
“嗯。”
“就是想把自己藏起来。”一阵沉默后,小秦说。
“为什么?”
小秦像是没听见我的话,自顾自地说:“你走后不久,张哥也回去了。”
这是我和小秦的最后一次通话。唯有黑关照万物。在潮水般的静谧中,所有的轮廓隐身,包括身份。此刻,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主动住进黑屋子里的人。他说,他就是想把自己藏起来。我也是。住进这间屋子后,我在喉咙里囫囵歌声,我对着窗外边打手势边接电话,我把淋浴喷头裹进叠得如豆腐块一般厚的帕子里。在这栋楼里,没有座位的人是可耻的,我只能掐灭所有属于我的声音,用最大的虔诚把自己埋了起来。
到单位入职后,每逢生人,见了我,总要问,新来的?
我点头。
“哦。”一番打量之间,来人连腰杆都硬朗了几分。那些哦有如气泡,不断地往我的身体里嵌,我开始变得很轻,近乎透明,在走廊里,在办公室里,在每一个我经过的地方。
那条红裙子被挪到了衣柜的最深处。一年后,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它才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快要忘记它了。磅礴的红已然黯下去,被白色的灯光一漂,通体浮上一层麻乎乎的浅白。我坐在床上,铺平,凝视,久坐,最终把它叠成小块装进了袋子里。在三百多公里外的家乡,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座位。至此,我将结束所有的辗转,重新着陆,而这间屋子,在我交出钥匙的那个瞬间,它就不再属于我,就像我们怀抱谜底,堕入永夜。
【作者简介】王亦北,生于1994年,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主要进行小说、散文创作,有作品发表于《四川文学》《草原》《西部》《滇池》等刊,有作品被《长江文艺好小说》《散文选刊》等选载;现居成都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