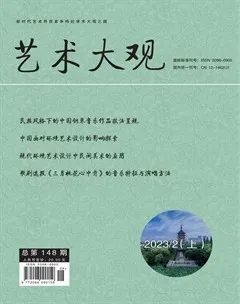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新探
摘 要:四川藏族聚居区地处四川省西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地域舞蹈文化千姿百态。四川藏族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舞蹈中保留着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让我们可以回望过去,追本溯源。对其进行新的探索,有利于保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更好地滋养文旅事业发展,激发创新活力,起舞新时代,奏响新乐章。
关键词: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3)04-0-03
四川藏族聚居区是中国第二大藏区,主要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和雅安市宝兴县、石棉县、平武县等部分地区。聚居于此的藏族人民能歌善舞,被世人誉为“歌舞的海洋”。文献与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就已有先民活动的痕迹,约在原始社会后期,西北氐羌先民就沿着岷江、雅砻江及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河谷通道南下,逐渐向川西地区迁徙,过程中不断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结构层次多样的文化体,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之地自然产生千姿百态的民间传统舞蹈文化。直至13世纪2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基本完成,藏民族内部交往日益增加,日益趋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藏文字的统一使用和藏传佛教对群众宗教信仰的巨大影响,直接促使原来不同部族间的特征与差异逐渐消失,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藏民族心理素质、道德规范、审美范式和民族情感。
四川藏族人民在长期改造极端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坚毅刚强、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也磨炼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片土地独特的山,独特的水,独特的人,自然孕育出了川西高原特色鲜明的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文化。
一、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代表性舞种
藏族民间传统舞蹈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世界舞蹈文化艺术圣殿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四川藏区的舞蹈文化从藏族文化母体中脱胎而出,在藏族主体文化覆盖下呈现出多样性特质。农区、牧区、林区、半农半牧区县在这片热土上交错,木雅藏人、白马藏人、尔苏藏人等支系文化百花齐放,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四川藏区和而不同的民间传统舞蹈图景。纵观各地舞风情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舞种主要有“卓”“谐”“雅卓”“热巴”和“羌姆”等,共同记载着藏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
(一)各美其美的“卓”
“卓”是自娱性舞蹈的集大成者,汉语俗称“锅庄”,是四川藏区流传最广泛的舞蹈之一。“卓”继承了我国古代“乐舞”的基本属性,融舞蹈、音乐、诗歌于一体,诗乐舞相得益彰。从舞蹈视角切入,可见在整体风格趋同的前提下,一地一风情,一寨一特色。“卓”的表现题材十分广泛,歌颂劳动,礼赞爱情,依恋家乡,嘲讽世俗,感恩幸福生活等,充分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不拘泥于表演场地,舞者牵手搭抱,弯腰垂手,围圈随歌齐舞。“北路卓”手势多变;“南路卓”搭臂弓腰;“东路卓”姿态潇洒从容,糅合着嘉绒藏族的舞风;“达尔嘎”典雅庄重与自由洒脱并存;白马“卓”步伐沉稳厚重;硗碛“卓”舞风原始古朴……他们共同诠释了四川藏区“卓”各美其美的风貌。丰饶的草原寂静辽阔,喧嚣的城镇人稠物穰,无论是热闹欢庆的盛会,还是孤烟寥寂的帐圈,凡有人烟之境,就会有“卓”的歌声与舞步时常相伴,飘荡于蓝天白云下,蹁跹在绿草鲜花间。在四川藏区相对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卓”释放了生命的悲欢,升华了世俗的常态生活。
(二)别具一格的“谐”
藏语中的“谐”乃载歌载舞之意,具有诗、琴、歌、舞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特点。因舞蹈时使用“毕旺”(弦胡)伴奏,故汉语又称“弦子”。在藏区,弦子二字可谓是与巴塘生长在一起的。“巴塘谐”不仅早已成为四川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也是维系群众间情感关系的强力纽带,唱响了民族团结的赞歌。此外,甘孜州北部的“格达谐”也是“谐”舞中的一抹亮色,以发源地甘孜县为中心辐射周边,因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饱含红色元素的深情而闻名雪域。“谐”的体裁格式一般与内容韵律相呼应,以诗咏志,以琴传心,以歌载道,以舞言情,基本队形特征为“围圈起舞,右旋而转”,歌词通俗易记,舞姿婀娜舒展,娱乐性强,群众参与面十分广泛。就舞蹈韵律而言,女性以柔美见长,昂头挺胸,挥袖而舞,给人以健康优美之感,而男性则柔中带刚,更显豪放和英姿雄壮。颤膝、屈伸、“三步一撩”“一步一靠”再加上长袖的甩、盖、托、绕等,构成了“谐”的典型动律特色,充分反映了藏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本美学思想,即追求形体美、动作美、韵律美与和谐美。
(三)“雅卓”与“热巴”
“雅卓”特指甘孜踢踏,其源头的发生与来自西藏的“堆谐”紧密关联。据《甘孜县志》记载,甘孜踢踏约在400多年前,由甘孜本地进藏学经的僧人学习并带回故乡,初期在寺庙内流传,后来传入民间融入世俗生活,在当时就是代表着融合与创新精神的舞蹈形式。“雅卓”的核心踢踏动律在继承了西藏地区“堆谐”足下舞步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了大量本地“卓”舞的元素,充分解放上半身,拓展上肢舞动幅度,同时进一步升级脚下动作难度,发展出踏点节奏复杂、突破原有速度的技巧,形成了豪迈洒脱的舞蹈风格。
“热巴”又称“铃鼓舞”,因表演时男舞者手执铜盘铃,女舞者执长柄鼓道具而得名。作为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综合艺术形式,“热巴”集舞蹈、音乐、说唱、杂技于一体,过去由藏族民间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流浪艺人表演,他们又被称作“高原吉普赛人”。关于“热巴”起源,最早可追溯至3800多年以前,由远古苯教师举行宗教仪式时的击鼓法舞演变而来,同大多数藏族民间传统舞蹈一样,经历了从宗教仪式中逐渐脱离,慢慢发展成为单纯民间艺术形式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四川藏区以巴塘县为主的地方还可见到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的“热巴”艺术团体在世袭相传,其中就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藏族舞蹈家欧米加参。在进行舞蹈段落的表演时,表演者手中的铃鼓道具与舞蹈动作配合协调,并可根据鼓点的不同变化形成不同的舞蹈组合,舞姿粗犷豪迈,伴奏明亮高亢,后期还发展出“蹬腿倒立”“躺身蹦子”“原地旋转”等高难度技术技巧动作,极大地丰富了“热巴”的技术性与观赏性。随着社会生活不断进步与发展,目前四川藏区已难寻“热巴”民间流浪艺人的活动痕迹,但其艺术精华仍然以群众广场表演、舞台艺术创作、课堂教学实践、非遗保护传承等更多元的方式,活跃在广阔天地间。
藏族民间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宗教往往构成艺术表达的主要内容和原动力,并渗透融入艺术的审美层面,而艺术也成为宗教的一种具象的表现形式,成为宗教信仰与情感的载体。舞蹈动律上,可以看见一些与当地其他歌舞艺术融合的痕迹,整体风格粗犷雄壮、气势宏大,跳跃动作基本贯穿于各个角色中,表演现场笼罩在肃穆的宗教神氛围之下,庄重威严。
除以上几种代表性民间传统舞蹈,在四川部分藏族地区还流传着反映狩猎的“沙尔普吉”,平武县白马藏族的祭祀性舞蹈“跳曹盖”,宝兴县带有原始风貌的“雅绒茨列”等[1],极具丰富的色彩。
二、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非遗保护中几点问题
我省官方对四川藏区民间传统舞蹈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的全面普查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为保质保量地完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简称《集成》)编写工作,我省民族舞蹈学方面的研究专家林堃、杨代华、胡祺桢等奔走于四川藏区的每一寸土地,访遍具有典型性的藏族村寨,历时十余年,共收集整理了9大类42个舞种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卓”类19个;“谐”类2个;“雅卓”“热巴”“藏戏舞蹈”各1个,“羌姆”5个,寺庙舞3个;民间祭祀舞6个;其他类4个。[2]经慎重筛选,最后确定了23个舞种入选《集成》,仅从数量上看,藏族舞蹈篇是我省种类最为丰富的篇章。斗转星移,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政府正式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这一基本文化政策。随着国家在宣传和实施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成就,民间传统舞蹈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积累了诸多中国认定的经验。历经二十余年持续努力,截至2021年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公布,符合完善的挖掘、收集、整理、申报程序,根脉清晰,谱系明确,尚存活态形式或传承人,明确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的藏族民间传统舞蹈种类共有121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3个,省级项目35个,市(州)级项目44个,区(县)级项目31个,民间原生形态的舞蹈样式基本全盘纳入保护体系,涵盖了当年《集成》中所记录舞种的95%以上。然而在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项目当下具体的保护传承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改进的方面。
(一)传统舞蹈项目分类的标准
从非遗项目认定层面来看,传统舞蹈项目分类的原则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鉴于大多数民间传统舞蹈诗、乐、舞一体的共性,项目主体在进行申报时需充分考虑其所属类别的依据,特别是市(州)、区(县)一级的认定,更需要延续国家级项目未列入明文规定的概念区分,与国家级、省级分类法则保持一致性。如“谐”类,以格聂神山命名的“格聂弦子”就归属在民间传统音乐的类别下,虽然符合相关申报文件要求,但从艺术专业层面而言,未能实现识别、分类标准的一以贯之。
(二)整体性保护
关于整体性保护的问题,省级非遗项目“达尔嘎”即为其中典型。嘉绒藏区歌舞统称“达尔嘎”,原则上是马奈锅庄、马尔锅庄、博巴森根、阿口日翁等多种地方性舞蹈的集合。而在实践中,“达尔嘎”“马奈锅庄”“博巴森根”“阿口日翁”等均由不同地区分别申报成为不同的传统舞蹈项目,从原来的从属关系逐渐演变为并列关系。仅“达尔嘎”的保护而言,狭义专指某一种具体的舞蹈后,难免存在完整性不足。此外,以锅庄为例,每一种锅庄所包含的舞段十分丰富,通常一首曲目代表一个舞段。在实际的资源挖掘过程中,将某些锅庄具体舞段识别成独立项目的现象,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舞种与舞段的关系需进一步廓清。
(三)填补部分项目传承人空缺
传承人缺乏是贯穿非遗保护工作的难点与痛点所在。经调查,四川藏区目前约40%的传统舞蹈项目存在只有“非遗项目”没有“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保护与传承后继乏人。诚然,舞蹈作为一种民间群众集体性活动,群体活态传承的方式可以有助于延续文化根脉生长,但舞蹈艺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进行表达,个人表演风格特色对项目的传承保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培养、发掘具有强烈个性化特点,并熟悉掌握藏族民间传统舞蹈“规矩”“知识”“意涵”的传承人迫在眉睫。
(四)传承人认定模糊
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多数民间艺人地位相应地得到了显著提高,有些舞蹈技艺突出的民间艺人甚至被歌舞团直接吸纳,成为专业演员,充实专业队伍,其中一些艺人还被派往专业艺术院校接受舞蹈训练,进一步拓展了对肢体语言的驾驭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可溯源的第一代或第二代传承人。而那些没有民间艺人背景,在文化馆站工作或拥有专业舞蹈教育背景,掌握传统舞蹈技艺的“二老艺人”群体是否可以被认定为传承人?具体什么样的掌握衍生形态的“二老艺人”可以被认定?这类问题还有待在接下来的认定实践和认定条文中进一步明确。
以上几点仅为笔者从实地调研中总结的局部现象。四川藏区非遗舞蹈保护工作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仍需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推进。保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才能更好地滋养文旅事业发展,激发新时代文化创造活力。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已然成为新晋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文旅代言人丁真一条与传统舞蹈内容相关的短视频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松破百万阅读量。舞蹈文化已经依托自身视觉传播和身体传播的特性,成功启动了线上传播的助推器。四川藏族民间传统舞蹈作为一种集诗、琴、歌、舞、服饰、道具的综合艺术形式,未来还有文创衍生的打造、舞蹈知名IP生成等巨大空间等待开发,进一步拓宽多维度的传播路径,让传统舞蹈突破常规的表演空间的场域,真正渗透入百姓日常生活,助力文旅融合,赋能旅游发展。
卡瓦洛日神山巍峨壮观,九曲黄河第一弯静静环绕,苍茫的森林和无垠的草原赋予了川西高原蔚为壮观的自然景色,彩袖飘荡、舞步飞扬,绚丽多彩的民间传统舞蹈又使这里呈现出一脉相承、绵绵不息的文化气息。相信在未来,四川藏族聚居区的民间传统舞蹈必将一以贯之地延续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紧密相连,身心不离,起舞新时代,奏响新乐章。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下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3.
[2]林堃.四川藏族舞蹈概说[J].西藏艺术研究,1988(01):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