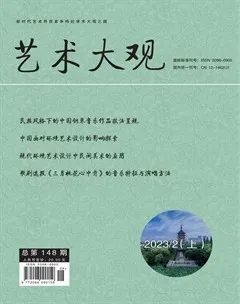柴可夫斯基风格流派刍议

摘 要: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Пё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俄罗斯音乐史上,柴可夫斯基是与“强力集团”处在同一时期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充斥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色彩,斯特拉文斯基称其为“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但和以“强力集团”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所提倡的“反对对西欧音乐的盲目崇拜”等观点相比,他的作品无疑是西欧化、国际化的,因此学术界对于其风格流派归属也一直未有定论。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将柴可夫斯基与俄罗斯民族乐派代表人物格林卡、“强力集团”放在一起,却又明确指出他们之间“在艺术主张和创作风格上有区别”[1],可见关于其风格流派归属的问题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本文将从柴可夫斯基两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着手,探讨其风格流派归属。
关键词:柴可夫斯基;民族乐派;风格归属
中图分类号:J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05(2023)04-00-03
一、时代背景
19世纪以前,音乐对于俄国来说是一种外来输入品,各大音乐会被外国音乐家所垄断。直到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出现,不仅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激发了俄国音乐的发展,俄国作曲家们逐渐意识到宗教题材和民间音乐是他们民族取之不尽的瑰宝。19世纪以来,一众俄国作曲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仍坚持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反对对西欧音乐的盲目崇拜,首当其冲的是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他将俄罗斯音乐提升至能够与西欧音乐相提并论的地位,之后在“强力集团”①、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共同努力下,俄国音乐体系逐渐被建立起来,在世界上崭露头角。
在柴可夫斯基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之前,“强力集团”就已在俄国音乐界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继承了格林卡基于俄罗斯自身音乐创作的初衷,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民间音乐素材,尊重西欧古典乐派及浪漫乐派的成果但反对墨守成规的学院派风格,大力主张创新与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的作品中都透露着鲜明的民主倾向,同情农民,厌恶、反对沙皇腐朽的专制统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俄罗斯音乐必须坚定地走民族道路,民间音乐是民族精神最强有力的载体。
柴可夫斯基作为俄国音乐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俄国第一个完全成熟的“专业”作曲家。他所就读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办是西欧音乐文化引入俄罗斯决定性的一步,因此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除了随处可见的俄罗斯民间音乐元素,也常常具有国际性。在俄罗斯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分化出两个对立的派别:以“强力集团”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和以柴可夫斯基为代表的“西方派”。
二、人物简介
1840年,柴可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从小他便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他童年时期所生活的乌拉尔地区民歌悠长,成为他早期的民间音乐启蒙。1850年,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进入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后因不能忍受官场的阳奉阴违而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音乐事业中。恰逢19世纪6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艺术领域空前繁荣,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柴可夫斯基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该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毕业后,受安东·鲁宾斯坦的举荐,他前往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他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致力于俄罗斯音乐教育发展,为彼时并不成熟的俄罗斯音乐教育体系编写提纲、制定教学计划、翻译教材等。这段时间里,他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幻》和《第一弦乐四重奏》、舞剧《天鹅湖》等。
1876年,他与梅克夫人建立了长达14年的通信友谊,并在此期间创作了庄严序曲《1812》《意大利随想曲》等作品以及其最成功的歌剧作品之一《叶甫根尼·奥涅金》。
柴可夫斯基晚期的艺术创作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超高的艺术造诣,代表作有歌剧《黑桃皇后》《约兰塔》、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等。1893年,他创作了享誉世界的《第六“悲怆”交响曲》,不幸的是,在这部作品首演一周后,柴可夫斯基染病逝世。
三、从作品中看柴可夫斯基
(一)民族性——以《1812序曲》为例
关于“民族乐派”的内涵,比较有权威性的解释目前有三种:一是格林卡提出的:“题材必须是民族化的,不仅是题材,音乐也必须是民族化的”[2]; 二是《牛津音乐简明词典》中给出的定义:“强调以音乐民族因素为标志,伴随着政治性独立运动而产生和发展的”;三是《西方音乐通史》中提到的“立志于发展本民族音乐,分别在各自的创作中采用民族的题材和形式,反映民族的风情和精神,并与民族独立或复兴民族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1]
柴可夫斯基从小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长大,他早期的作品多反映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曾说:“我避免使用外国的题材,因为我只熟悉也只理解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姑娘、俄罗斯妇女。”早在他就读音乐学院时便为自己最喜爱的俄罗斯戏剧《大雷雨》创作了一首管弦乐序曲,以此表达他对沙俄黑暗社会的反对态度,集中反映了其民族性思想。
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他结识了“强力集团”的成员们,也因此在那时期作品的题材与风格受到了“强力集团”的巨大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与这个致力于发展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集中创作了一批以俄罗斯民间音乐为主题、富有强烈民族性的作品,早期的一首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便是在巴拉基列夫的指导下完成的[3]。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通常直接引用俄罗斯的民歌曲调为主题,诸如《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一钢琴协奏曲》,也包括笔者将要着重介绍的一部伟大的作品《1812序曲》。
《1812序曲》是柴可夫斯基于1880年为了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这一历史事件,应尼古拉·鲁宾斯坦之邀,为毁于1812年战争中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重建落成典礼而创作的一首大型管弦乐作品。柴可夫斯基用音乐表现了从和平的生活,到战争的发生,再到俄军击溃法军,体现出俄国人民胜利的喜悦。他在作品中利用旋律和配器塑造了俄国与法国这两个鲜明的形象:通过法国歌曲《马赛曲》的引入代指法军的艺术形象;对于俄国音乐形象的塑造更是贯穿全曲,乐曲的引子以一首古老的正教赞美诗《主啊,拯救你的子民》开始,由中提琴和大提琴演奏,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平静安宁的生活(见谱例1)。
随着乐曲的不断发展,俄军战胜了法军,一支俄罗斯婚礼歌曲《在大门旁》出现,由长笛和英国管奏出,富有热情,曲调欢快轻松,充满朝气,舒缓了战争紧张的氛围,同时体现了俄罗斯人民乐观的精神(见谱例2)。
最后伴随着炮声与教堂的钟声,俄国国歌《天佑沙皇》的主题出现,彻底宣告了俄国人民的胜利。
在这首作品中体现的民族性,柴可夫斯基其他诸多音乐作品中也皆有体现,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中将民族风情体现得淋漓尽致[4]。
(二)浪漫风格——以《第六“悲怆”交响曲》为例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说柴可夫斯基就是民族乐派?
从作品内涵来看,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与其说是民族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对自我情感的宣泄,尽管在他的作品里不乏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我们仍不能单纯地称之为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从写作技法来看,与“强力集团”的“不太专业”相比,柴可夫斯基接受的是欧洲古典、浪漫乐派典型的作曲技法教育,而彼时以巴拉基列夫为首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们强烈地排斥西方严格的“学院派”传统,这也是为什么柴可夫斯基最终与“强力集团”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在柴可夫斯基创作后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创作理念,认为创作应该为作品服务,追求音乐的美和音乐的艺术性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因此他毫不避讳地在创作中使用西欧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与元素,不再局限于民族音乐的创作。正是因为柴可夫斯基注重将民间音乐与世界音乐相结合,才促使他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国际性作曲家。
这里以他最后一首作品《第六“悲怆”交响曲》为例进行论述。
柴可夫斯基一生共创作了六部交响曲,前三首总体基调以乐观为主,第四、 第五和第六交响曲,同时也被称为柴可夫斯基的 “悲剧三部曲”。这三部晚期的交响作品都旨在表达作曲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黑暗社会现实的矛盾,有一定的哲学意义。《第六“悲怆”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悲剧交响曲的完结篇,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他交响曲成就的最高体现,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曲子,赋予了其很高的评价。
1889年柴可夫斯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很想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交响曲,它也许可以算是我这个创作生涯的终结……”[5]自此,柴可夫斯基便一直酝酿这部新的交响曲。1890年,柴可夫斯基一直以来精神上的盟友梅克夫人来信,暗示终止对他的资助,1891年无私支持自己音乐事业的妹妹也不幸离世,朋友、亲人的相继离去,包括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不断提高而带来的压力都给彼时的柴可夫斯基带去莫大的精神打击。[6]
全曲共有4各乐章,第一乐章是一个b小调的奏鸣曲式,由一组四个音的动机展开,b小调灰暗的色彩让乐段更具戏剧性和悲剧性;第二乐章包括优雅的快板、D大调的复三部曲式,柴可夫斯基首次将圆舞曲带入交响乐的高雅殿堂中,丰富了交响乐的表演手段,其构思来自俄罗斯民谣,这也体现了其作品中内隐的民族性气质;第三乐章是谐谑曲与进行曲混合而无发展部的奏鸣曲式,象征着正与邪两种力量的斗争;第四乐章是一首安魂曲,同样是充满阴郁色彩的b小调,象征着一切憧憬和希望均化为乌有,悲痛与凄凉笼罩着一切。巴拉基列夫曾评价:“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而这部作品无疑是对他个人悲痛人生淋漓尽致的刻画[7]。
尽管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民族元素,但他的创作风格仍然是建立在西欧古典音乐和浪漫音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够单纯地看音乐中运用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感受作曲家通过音乐表达了什么,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作曲家将发展本民族的音乐作为己任,表达强烈的民族情感,而柴可夫斯基更多的是对个人情感的宣泄。归根结底,他的作品本质上是在表达自己,在他作品中的民族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为表达个人情感而服务的[8]。
四、结束语
保罗·亨利·郎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中提道:“个别作品的世界价值并不是和它们的特殊的民族性成正比例的。[9]”他认为我们应该区分音乐的两种价值,即民族性和西方普遍意义,这两种意义正是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作曲家们一直争执不下的症结所在。保罗·亨利·郎认为,一味地排斥西方音乐的成果,只是将民族的因素套用在音乐中,是一种虚假的民族性质。一如欧洲其他国家的听众不能理解西贝柳斯对于芬兰而言的神圣之处,一味地将创作封锁在民族的禁锢里而不顾音乐的普遍性,其世界价值将与之民族价值不成正比。而柴可夫斯基正是将民族的与世界的音乐进行结合,俄国还没有任何一个音乐家比柴可夫斯基更具有国际性。
民族乐派本身就并非与浪漫乐派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纵观西方音乐发展的长河,民族乐派也是在浪漫主义的发展中孕育的,与浪漫主义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民族元素对于早期的浪漫主义而言也只是一种表面的方法。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或沉闷,或明亮,都是在借助民族的题材与内容表达个人的情绪,是一种对自身情绪的外化。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柴可夫斯基更偏向浪漫主义风格。
参考文献:
[1]于润洋,主编.西方音乐通史(修订版)[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
[2][苏]塔·罗佐瓦,著.格林卡[M].金兆先,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
[3]龚钰.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民族性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1.
[4]陈琳钰莹.浅析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从格林卡到斯科里亚宾[J].黄河之声,2019(14):84-85.
[5][美]埃弗里特·赫尔姆,著.柴可夫斯基[M].王泰智,沈惠珠,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6]彭静.殊途同归[D].湖南师范大学,2014.
[7]叶松荣.文化自觉与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音乐[J].东南学术,2020(06):160-166.
[8]付晓玲.深沉而动人心弦的悲怆之美——论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艺术魅力[J].名作欣赏,2006(09):89-91.
[9][美]保罗·亨利·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