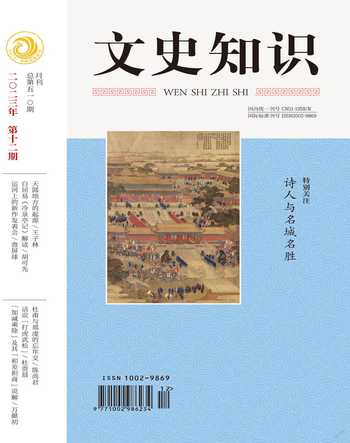风中烛与炳烛游
孙华娟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们要回顾一下有关古代照明的常识。
先要从照明材料说起。其实照明所用原本就跟炊爨所用的柴禾一样,但有细微的不同。薪和柴我们今天可以混称,但分开来讲是有区别的。《礼记·月令》:“(季冬之月)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郑玄注:“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给燎。”也就是说,薪指炊爨所用的大柴,柴指细小成束的小木(也可以称为蒸)。薪和柴一为爨薪,一为烛薪;一作炊爨用,一作照明用;一粗,一细。做饭用的爨薪通常是大块的,照明用的烛薪多为细小的木柴、竹木枝,还有麻秆、苇草之类,以其易燃,把这些材料捆扎而成一束束来照明,就是所说的烛。大烛,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庭燎、坟烛,在地曰燎,执之曰烛。为了让火把更明亮,有时还要给捆扎成束的柴、麻、竹、苇灌上蜜或蘸上油脂,让火光更大更持久。蘸取的油料最早多用动物油脂,但烟和味道都大,后来植物油的提取技术发展了,多改用植物油。渐渐地多用油、少用麻苇,就出现了后世的油灯,并且东汉后期已经出现了长条柱状的虫蜡、鲸蜡等材料做的烛,称为蜡烛,但造价高,不易得,民间普通人家一直主要依靠油灯照明。就像王献唐《古文字中的火烛》一文所说,初时烛即火把,继以灌油膏,改进为油烛,又加以盘承接,有柄有座,以便执放,乃利用古豆形,加钉锲为之,为汉灯之始。灯可以插膏烛,也可以插蜡烛,又有油灯,它们先后演变,但各形制并行不废,并非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诗歌都与烛有关。
汉乐府有《怨诗行》,是与《薤露》《蒿里》《泰山》《梁甫》《北邙》同类的葬歌、挽歌,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是它的重要表现内容。我们看《怨诗行》古辞:
天德(一作道)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乐府诗集》卷四一)
与天道的悠远相比,生命是多么短暂。人生百年,却像风中的火炬。风中之烛的比喻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奄”同晻,即暗,不明亮。风吹炬火,使之飘摇暗淡。生命就像风中的炬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吹得暗淡甚至熄灭。这一比喻立刻让我们过目不忘,它搅起了我们所有的经验和蓄积的情感。比喻永远是捷径,它不用详细的描述叙写而瞬间引动我们的共情,不用条分缕析但直接指向我们的理性,它说,A和B是多么相像啊。随着作者所指引的方向,我们望过去,事物如同瞬间被闪电照亮。
建安七子之一刘桢有一篇残诗延续了“风中烛”的比喻:“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仍然是说人生百年飘忽不定转瞬即逝,如同风中之烛。但“炯”字一般指明亮,这让诗句的意思变得有些含糊,不那么明确,不如乐府古辞中“奄若风吹烛”清晰。另外,刘桢这篇残诗与阮瑀《怨诗》很相像:“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不无可能,刘桢原篇就是《怨诗(行)》,也属于挽歌。阮瑀“漂若河中尘”也是比喻,但远不如风中之烛贴切精彩。好的比喻,我们往往一见、一听即知。它们往往立刻就能显出人的文学天分,就像衡量天才的便捷尺度。比喻需要感受力和悟性,修辞者凭借直觉几乎立刻就抽取出不同事物的特性,并在两桩原本毫不相关的事物间建立联系,所以比喻又特别需要明敏的联想和卓越的抽象能力,而这种抽象能力主要是诉之于人的理性。精彩的比喻因此是感性与理性完美的交互为用,既体现收集意象的能力,又考验连类而及并加以分析和抽象的能力。一个比喻往往只有一句话,却需要修辞者电光石火之间把握和了悟一切。它经常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后人对它的沿用可能成为滥调,因此被读者忽略也就不奇怪。总之,刘桢诗显然沿用汉乐府古辞中“奄若风吹烛”这一比喻,虽然未能推陈出新,但显示了他对该修辞的心仪和推崇。
当然,乐府古辞《怨诗行》里还有些细节值得探究。比如,烛一定是火把吗?有没有可能是蜡烛?蜡烛要到东汉后期才出现,它本身也并不适合用于室外环境,古人即便在室内也是长期以炬火或油灯照明。唐代诗文中还常见描写在油灯下苦读的情形,韩愈《进学解》“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写的就是油灯,膏,就是油脂,代指灯烛。唐代以前诗文中的“烛”可以涵盖火把(炬)和油灯,但很少或基本不会作为对蜡烛的专门称呼。几乎可以肯定,乐府古辞里的“风中烛”说的是炬火。当然,油灯和蜡烛变得常见以后,用风中的油灯或蜡烛来比喻生命可能更有柔弱危脆之感,火把作为烛的本义反而不大被我们想起了。
《古诗十九首》里有一篇与乐府古辞《怨诗行》大致同时,基本情调也相似: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一作炳)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文选》卷二九)
“秉烛游”,“秉”或作“炳”,“炳烛”更可能是原文。曹丕《与吴质书》“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李善注本《文选》卷四二)即引作“炳”,是也。烛仍指火把,炳烛意谓点起炬火,这比单单拿着火把(秉烛)具有更强的动作性和视觉性。点燃火把是一个很有主动性的行为,也并不柔弱。炳烛而游展现的是人在洞达生命的短暂脆弱以后选择对抗命运,比起《怨诗行》“奄若风吹烛”的无能为力,自有豪情在其中。但此处“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与《怨诗行》末尾“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所表达的情绪是一样的,既然人生这么短、忧愁那么多,生命柔脆、来日难期,我们何不当下就随心所欲、及时行乐,既然白日已逝,就让我们在漫漫暗夜里点亮炬火,连夜行游。
火把需要小柴细薪合成捆,举凡竹木枝、蒿茎、麻秆等材料都可以,再浸上油脂以助燃,有的叫作“麻蕡”。直到唐代,人们夜行还经常用火炬照明,其中桦树皮又是做火把的上乘材料,人们把这样的火把称为“桦烛”。白居易《早朝》诗有“月堤槐露气,风烛桦烟香”,这里的烛就是桦树皮卷成的火把,燃起来还带着桦木的清香。无论麻蕡还是桦烛,加了油脂,烧起来明亮又不易熄灭,虽然依旧是“风中之烛”,却有猎猎的气势,非油灯或蜡烛可比,撑得起炳烛夜游的豪兴,汰去了奄若风吹的黯淡。
和汉乐府“风中烛”一样,古诗里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炳烛游”也是比喻,与前一句相连,说人生欢乐常少忧伤常多,就像白昼短而夜晚漫长,那么炳烛夜游就是在艱难忧戚的人生里勉力去追寻欢乐。“炳烛”一词之前在典籍中已出现过,但并非用来指夜以继日的遨游,而是指老而好学。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刘向《说苑·建本》)
晋平公年老了,想要为学又怕时光已经暮,盲人音乐家师旷说,为什么不点起火把学习呢?老而好学,正像夜晚点起火把,虽然不像早上和中午的太阳那么明亮,但总好过在黑暗中摸索啊。这里所说的烛当然也不是蜡烛,而是火把、炬火。炳烛夜游就是从这里变化来的,却一改原来的勉力勤学而为及时行乐,颓丧中不无豪宕。不知是汉乐府风中之烛这一比喻更早,还是从炳烛为学而来的炳烛而游更早,但这两个比喻都从照明而来,而各有其动人心魄处。
陶渊明《归园田居》组诗其五也与烛有涉,但无关比兴: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一作继)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该组诗的前一首,陶渊明写他去山中游玩,看见从前的井灶变成了遗址荒墟,砍柴的人告诉他,几十年前这里繁盛的人烟都消失了,他悟到“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这里是承接上一首,写他心情晦暗,独自沿着崎岖山路返回。一路上碰到清浅的山涧水,他就在里面涤洗双脚。回到家中,漉出新熟的家酿,又准备了一只鸡,他邀请附近友朋来家中闲谈。傍晚日色昏暗下来,就用烧饭的柴薪代替明亮的火炬。围炉对酒的夜谈是欢乐的,整个夜晚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天就要亮了。陶渊明不再写风烛的悲慨,也不作炳烛夜游的豪宕,他只是招邀亲朋,围炉夜话,烧起一膛炉火,照亮人生的暮夜。
面对人生的凄风苦雨,我们手无寸铁,陶渊明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就像这首诗里表现的一样,他抵抗人生短暂和虚无的力量来自温暖的世俗人情。崎岖跋涉中,自然界为他奉上了清清涧水,他自己则有胼手胝足建立起来的家园,家中有新漉的家酿,还有那温暖的一膛炉火,以及可以随时相聚的亲朋好友。荆薪就是炊爨烧火用的柴薪,烛还是火把。陶渊明说不用那明亮的细柴或麻秆的火把,我们只用薪火来代替灯烛,来作一场热烈的谈话,扺掌一谈就是通宵。要知道,《礼记·曲礼》里讲,如果晚上去拜望主人,要早些告辞,不要等夜深别人家的火把燃到头了才走,即所谓“烛不见跋”。“跋”,本也,也就是把,指火把的手持之处。在陶渊明这里,完全没有这些礼仪顾忌,跟好友可以不拘形迹,谈话也格外热烈忘情,把前一首诗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陶诗笔下这场景是多么温暖和自然,他只是直接赋写,不太在意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彩修辞,无意于比兴。和他灶膛里的荆薪一对照,风烛的比喻显得太低沉柔弱,比起他的围炉宵谈,炳烛夜游又显得过于刻意。柴火兴许不够明亮,却足够温暖。以炊爨之火同时作照明之用,也更有亲切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