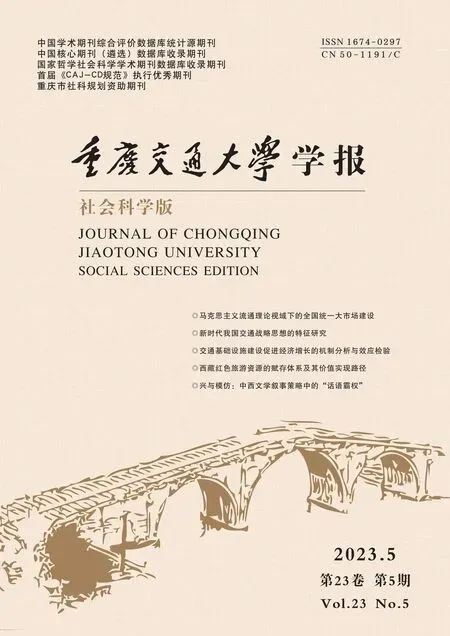拉什迪小说的身体书写与后殖民现实
刘春娴
(1.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西安 710128;2.广东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一、研究缘起
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享誉文坛、蜚声中外,也一度自取湮灭、树敌万千。他因成名作《午夜之子》(1981)三获英国文学布克奖而辉耀文坛,又因争议作品而引火上身,四处流亡。拉什迪在《撒旦诗篇》(1988)中对伊斯兰教的不敬和亵渎触怒伊斯兰世界,掀起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并招致文坛罕有的死亡威胁。《摩尔人最后的叹息》(1995)是拉什迪处于追杀令影响下的第一部鸿篇巨制,非常值得关注。拉什迪的作品具有广阔的文学效应,是文学榜单上声名显赫的宠儿。在书写方式上,他常用“马萨拉”(一种印度混合香料)式的后现代文学写作技巧来展现南亚次大陆的后殖民现实与文学内涵:前殖民宗主国与南亚政治风暴复杂丛生,西方文化与东方南亚次大陆文化错综杂糅,世界政治地图的中心与边缘相辅相成。
作为流散作家的拉什迪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生活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栖身于官方保护之中。这样一个流亡之人何以频频叙说母国印度的历史?又为何招惹诸多非议?到底如何评价拉什迪的文本创作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作为一个游走于多个地理疆域的作家,其作品充斥政治、历史、文化的种种烙印,是什么让他不知疲惫地描述东方与西方?又是什么让他坚持对无根家园的持续探索?带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拟探索拉什迪如何借助身体书写反映后殖民现实。
目前,国内外对于拉什迪小说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消费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政治美学批评等。大部分已有研究并未从身体批评的角度对拉什迪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颇具影响规模的后殖民研究也鲜有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身体维度。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焦点。彼特·布鲁克斯指出:“将身体写入文本一直以来就是文学的重要命题。”[1]1身体既是自然的身体(生理的身体),也是文化的身体;既特指个体的身体,又泛指群体的身体;既是人类的身体,也可以是隐喻意义上各种事物的身体。身体出现在文学语境中,既是文本之上对身体的物质性再现,也是文本之外对身体的意义延伸,早已超越生理医学的范畴,与身份困惑、社会文化、性别政治、权力规训等话题形成深度共谋关系。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文学中的身体转向“在与文本的每一次碰撞中都形成了万花筒随机图案”[2]。后殖民主义文本以文本内容为载体,勇敢介入现实政治,强调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我国学者张晓红教授指出:“后殖民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机,区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利用文学想象来拆解殖民现实和重建后殖民现实。”[3]小说中,身体表达了拉什迪的后殖民生活经验,在文本深层构成拉什迪文本诗学的内在标识。
流亡状态下的拉什迪曾描述其文学书写之要旨,在广义上来讲是“试图去描述‘我’来自的世界和 ‘我’走进的世界,以及这两个世界如何碰撞”[4]200。这个“我”亦东亦西,也非东非西,或实或虚,又亦真亦幻,透视一种身体视角和身体经历。显然,身体书写是拉什迪文学创作的重要策略,是作家审视追杀令背景、后殖民环境和跨文化语境下个体生存与民族创伤的重要维度,在文本中有着建构、解构和表征的多重功能,为拉什迪作品解读提供一个崭新的角度。本文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身体书写放置在拉什迪小说文本中分析,从混杂的身体、罹患疾病的身体、创伤的身体、规训的身体展开考察,解码拉什迪编码于文本政治中的后殖民现实。
二、混杂的身体
拉什迪本人的移民生活经历使得他对移民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情境给予特别关注。他说“与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是一个历史的混血儿”[5]376,透露出对身体主题的热切关注。“处处有家,处处无家”可以用来总结拉什迪的流散人生状态。1947年他出生于印度穆斯林富商之家,14岁前往英国拉格比公学求学,毕业后举家迁徙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定居,随后孤身返回伦敦并加入英国国籍。在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悬赏重金的追杀令阴影及英国警方严密周全的专项保护下,拉什迪过着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并“到处流浪”(9年更换56个住处)。2000年以后,拉什迪结束逃亡生涯,移居美国纽约。身体的不断移位塑造了拉什迪,丰富其作品体验,使小说创作在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空间之间穿越。身体的不断错位使他反复徘徊在“以印巴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6]之间,反复感受着心理的种种“失落感”和“不确定感”。可以说,拉什迪的文学版图烙上了他本人的足迹,作品镌刻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美国等不同地理空间的种种痕迹,形成万花筒般复杂的“大杂烩”。拉什迪笔下形形色色的主人公身体里一脉相承地流淌着“混血”基因,眼花缭乱的人物故事反映光怪陆离的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变迁,裹挟着后殖民与后现代的杂糅特质。作为混血儿、移民者、流散者,他们同时属于两个世界,身份是东方色彩和西方元素、“印度性”和“英国性”或多或少的拼贴。
一方面,拉什迪作品中具有生物性杂交意义的主人公是一个个“拉什迪式”的边缘人,拥有混杂的生理身体。《午夜之子》中的萨利姆(Saleem)是东西方混杂的混血儿兼私生子,父亲是代表英国殖民统治的梅斯沃德庄园主,母亲则是印度低种姓街头流浪艺人的妻子。他是英国与印度私通的“杂合物”,长着东方人的耳朵、西方人的头发。出生之日萨利姆又被女助产士玛丽刻意调包,与另一名同时生产的新生儿湿婆互换身份,因而摇身变成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萨利姆由此成为“上层与下层、高贵与低贱、富足与贫穷、政治与妖术”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东西方元素的血脉混杂、人为刻意的社会阶层错置,成为拉什迪的肉身再现。《羞耻》的叙述者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Omar Khayyam Shakil)是终身幽居在尼沙浦尔大宅里的三姐妹之一与某位不知名英国白人军官的私生子[7]4,由始至终不知其父母分别是谁,仅可以肯定是英国殖民者与沙克尔三姐妹之一的混血儿,同样流有东西混杂的血液。《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的主人公莫里斯·佐格意比(Moraes Zogoiby)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血儿,一个多元文化“历史的私生子”,父亲亚伯拉罕是谣传曾被西班牙阿拉伯人玷污了血统的犹太后裔,母亲奥罗拉是葡萄牙裔的天主教徒,祖上血缘也不纯净。正如莫里斯说:“我既没有成为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教徒。我两方面都是,又都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天主教徒,一个天主教犹太人……一个真正的孟买大杂烩。”[8]102《她脚下的土地》中维娜·阿芭萨尔(Vina Apsara)不停地变换家庭,更换了五次父母,仍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家[9]。她是印度人与美籍希腊人结交的混血儿,父母离异后母亲再嫁美国人,这场失败的婚姻以母亲自杀而告终。随后,维娜在美国、印度等不同的亲戚家辗转流浪,从备受虐待的印度亲戚家逃脱以后,来到小说叙事者的家中。“她”如空中的漂浮物、水中的浮萍一般,脚下根本没有属于她的土地……这些主人公个个都拥有一副不确定的身体,成为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存在,也是拉什迪无家可依、无处可归的生存观照。正如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在《逆写帝国》中指出,混杂性是所有后殖民文本的基本特征[10]185。混杂性也构成后殖民环境中个体的基本特征。所有人都是混杂的,处在一个大熔炉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新事物进入世界的方式[5]394。文本中,拉什迪以混杂性的人物身体书写表现其创作中的后殖民文本特征,表现了后殖民环境下的个体生存状态。
另一方面,混杂的身体是拉什迪肉身的文本再现,将其文化无根的镜像投放在诸多小说主人公身上。流动的身体在流动的空间中不断移位和反复错位。拉什迪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创作中的空间:“我没有一块地盘……有根的作家都有他们的地盘, 他们的作品从那里源源不断产出,他们更是不断探索那片土地,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我却没有这样的一块地盘……每当我要着手写一个句子时, 都不得不虚构出一块土地来, 虚构出一块供我立足的土地来。”[4]93这种文化无根状态转为笔下一个个灵魂未能安顿、精神未能安立的无根之人和流亡之徒。萨利姆因身份问题不断被迫流放,奥马尔成为那个认贼作父的家庭逆子,莫里斯被父母扫地出门……叙事主角身上种种流动、流散、流放的身体经历,无不源于拉什迪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反复错位,并由此带来失落的身体体验。对于身居异国他乡,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错位感让他频频回顾记忆中的家园,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他在《想象的家园》中描述的“迷失的家”(a lost home)[5]9永远回不去了。于拉什迪而言,心理上的迷失感因文化错位和文化断裂产生,是一种更复杂的失落感。家园记忆的断裂感使拉什迪以一种“破碎”“碎片”“裂变”的形式去观照印度和世界。萨利姆被迫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更换肉身栖息地,由此产生的社会疏离感最终导致个人异化。莫里斯叹息:“我头晕目眩、迷失方向……我被毁了。我失宠了。这恐怖击碎了宇宙,仿佛它是面镜子。我觉得仿佛自己也破碎了。”[8]269总之,无根人生、流散人生、错位人生是拉什迪自我境遇的真实写照,也是后殖民印度社会现实的再现。混杂的肉身体验让后殖民社会中的个体经历身体流散与社会疏离,由此导致个体的情感错位与道德异化。
三、罹患疾病的身体
在文学想象中,身体的疾病症状经常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修辞手段而被援引至文本。疾病具有可见性和空间性的文本喻指功能。苏珊·桑塔格在其批评文集《疾病的隐喻》中反思结核病、艾滋病和癌症等如何在社会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只是身体的一种生理性疾病转化为一种道德批判,甚至是政治压迫的过程[11]。拉什迪的小说出现各类与疾病相关的因素:呼吸疾病、肺部疾病、生存体验、死亡意识,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生理身体的可见性和空间性因素。小说的身体主题体现为叙事上对身体症状的描述,并以此来表现身体的隐喻过程和喻指意义。
小说中最特殊的疾病意象是肺部疾病。《午夜之子》中,鼻子是最突出的意象。外公阿齐兹巨大的黄瓜式鼻子被描述为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相遇的地方;萨利姆继承了这种形状的鼻子,也具有特殊的嗅觉功能。“拖鼻涕”“吸鼻子”的萨利姆神通广大,具有通灵的本能,在后来印巴战争中充当嗅探犬的角色。鼻子也是呼吸的地方,“人的生命如同呼吸一样,在一呼一吸之中,个体生命与整个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2]123。通过鼻子的呼吸,拉什迪寓意个体与世界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在后殖民时代,任何个体都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正像在烹饪时要入汁入味一样,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都在互相渗透。”[5]394
从《午夜之子》辉耀文坛的灿烂人生到《摩尔人最后的叹息》追杀令之下的黑暗藏匿,拉什迪小说的呼吸方式发生转移,即从鼻子由外至内的主动呼吸转变为从肺部由内至外发出的声声“叹息”(sigh)。呼吸的意象是拉什迪对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哲思的文本回应,表达了对肉体存在的另一番思考。无可奈何的声声叹息既与小说题目呼应,又与小说内部的摩尔人组画呼应,从而构成扑朔迷离的羊皮纸。《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反复出现与“肺”相关的呼吸问题,具体表现为家族里总有人肺不好:父亲亚伯拉罕有哮喘[8]78,贝拉死于肺癌[8]4,麦娜死于窒息[8]47,摩尔人的肺经常不能正常呼吸[8]51。身体上的肺部呼吸指涉呼出意义上的话语表达,暗指宏大历史叙事下官方话语和权威话语对个体声音、个体表达的抑制,导致个体身上出现种种不能呼吸的经历,直至窒息死亡。
此外,乐观病与冷冻病是小说中颇有意思的疾病意象。《午夜之子》中反复提起萨利姆的父亲阿赫默德的乐观病。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印度取得独立以后,伴随着尼赫鲁满怀信心的演讲:“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印度的雄伟大厦,在这里她所有的孩子都能好好的生活。”[13]146这些话语使得当时整个印度民族都患上乐观主义疾病(optimism disease),似乎印度瞬间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随后,小说更是断断续续地以聆听者的角度呈现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午夜的钟声响起,印度苏醒过来,获得了自由……一个时刻到来了,一个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从旧世界跨入了新世界,一个时代就此结束了,一个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的精神得到了解放。”[13]144笼罩在阿赫默德身体之上的乐观病使他奋力投身房地产,日日驻扎在办公室忘情工作,企图以个体的意志重新塑造印度。充满曙光的序曲过后,印巴分治接踵而至,带来不同宗教教派的激烈冲突。身体成为经受外界影响的最大载体,在穆斯林财产冻结令下,阿赫默德的身体陷入极冰状态:他的生殖器完全失效,总是提不起劲。这使得他躲在办公室里日夜消沉,萎靡不振。乐观主义最终蜕化成身体的疾病——冷冻病。身体的疾病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历史的疾患重叠呈现,各种叙事混杂“搅拌”(chutnification),构成蜂窝状的文本结构和发散式的文本效应。这些表现在个体身上的疾病隐喻后殖民印度政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印巴分治、克什米尔争端、军事冲突、宗教纠纷等。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投射在独立后的印度个体身上,外化成为罹患疾病的身体,隐喻国家政治身体出现种种问题。
四、创伤的身体
拉什迪小说塑造了不同形式的身体创伤,并让其成为心理创伤的一种外化。从地理疆域来看,无论是对移民者还是非移民者,印度都表现了一种后殖民创伤经历。对移民者而言,他们来到新的国度,既想快速融入新的国家,但又无法磨灭母国家园的记忆。在非此非彼的肉身经历之间,人人都是“受伤的生灵”(wounded creatures)[5]12。这些“受伤的生灵”既有个体身体上的外伤,也带着群体性的心灵伤痛。对南亚次大陆非移民者而言,经过多次殖民入侵、暴力战争、文化迁徙的洗礼,印度民族已然成为一个受伤的民族。正如V.S.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的描述——这是一个幽暗国度。“人无完人,就此意义而言,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5]12从时间维度看,殖民时代的印度,个体都饱受着民族独立运动所带来的种种外在创伤——因战争和暴力运动所形成的生理创伤;后殖民时代,印度则感受着长久的心灵创伤——一个破碎的家园、一个受伤的民族、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
其一,创伤的身体以碎片化的形式进入文本。《午夜之子》中一张“穿孔的被单”(perforated sheet)透视了观看身体的目光。外祖父阿齐兹医生在婚前给外祖母纳西姆诊治时,出于对穆斯林女性深闺回避制的考虑,纳西姆家人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竖起一张床单,并剪开七英寸大小的洞,以便观察患病部位。阿齐兹在治疗她的身体疾病时,通过碎片化的想象逐步拼贴起她的样子,并开始想象她的整个身体。这是拉什迪后现代主义解构策略之一,将身体分解为碎片意象,以此指涉叙事的碎片性、模糊性和不完整性。而来自心灵的创伤则外化成为身体伤痕。小说中,萨利姆的外祖父在失去宗教信仰以后,心中永远地留下一个洞。创伤的身体在《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表现为横亘家族几代人的身体残疾。天生残疾的莫里斯“右手如棒球一般,力大无比,并以两倍普通人的速度成长和老化,迅速地新陈代谢”[8]140-141,“与阿喀琉斯的故事”[8]150形成互文反应。被标记和被毁坏的身体既是历史记忆的铭刻,又隐喻对现实的反抗。这些残缺的身体作为“事件铭写的表面”反复出现在文本中,诠释后殖民环境下的个体如何被构建为“不正常的人”而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沦为备受排斥和压迫的边缘人。通过身体书写,后现代叙事中残缺、断裂的故事形式取代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下的人物生活状态,让悲剧性和污名化构成残障主人公们的命运底色。更进一步来讲,拉什迪有意无意间使用身体创伤来隐喻后殖民的帝国肌体及印度文明:无论是肌体还是文明,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失去信仰支柱,身体的殿堂必然破落。
其二,个体身体伤痕是民族创伤的寓言。作为个体的萨利姆是民族的象征,其“面孔就是全印度的地图”[13]292,他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年轻的萨利姆象征和隐喻年轻的印度,老化、残疾、破损的萨利姆则观照后殖民印度社会现实。残缺破损的身体构成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萨利姆经历跌宕起伏的家庭变故,不断经历身体的残缺破损:因一缕头发被生生地拽掉而留下一道秃顶,因父亲的一记耳光而整天嗡嗡作响的失聪左耳,因一次争斗而被门夹断所遗留的残疾中指,因一次空袭被银痰盂砸中头部而丧失记忆,因对妹妹贾米拉的感情而一度导致的性无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断发现自己身上的裂缝越来越明显。他未老先衰,31岁就裂痕斑斑的身体成为危机四伏的印度现实的隐喻。在这种意义上,萨利姆就是印度的化身,他身体上的裂缝是古老的印度蒙受创伤的外化。显然,这些身体外在的伤痕折射一种后殖民社会现实:人不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存在,是残缺的个体(partial beings)[5]12。在这种状态下,莫里斯不停地叹息:“我已经毁了”,“生活已经毁了”[8]269。创伤的身体表面上看是萨利姆、莫里斯等残障主人公的身体,深层结构上喻指受伤的印度。这样的身体就是彼特·布鲁克斯所说的“文本化身体的经典塑造”[1]5-6。而后,身体破败不堪的萨利姆被强制接受阉割手术。这一身体经历隐喻后殖民时代印度接受帝国中心主义“文化强制”的意识阉割,彼时的印度在各个方面对英帝国主义展开无意识的模仿和认同。最后,萨利姆以备受暴力创伤的个体身体经历宣告民族主义理想的正式破灭。在拉什迪绘制的历史画卷中,独立后的印度次大陆经历分裂、战争和政变,并没有走向尼赫鲁式的自由、文明和进步。民族主义理想的破灭向外表现为身体的破败,向内形成一种长久的心理创伤。创伤之于印度,成为一种不断反复的体验。
五、规训的身体
规训的身体是被殖民化、性别化、族裔化的身体“面面观”。规训的身体是将身体现象植入政治历史坐标体系当中,向文本外的文化空间延展,讨论文本的社会生产过程。福柯的权力话语在这种解读中熠熠生辉:“人的身体总是强制性地被体制化,被意识形态化,以满足道德和权力的功利性要求,道德和权力要求身体归顺或是控制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网络之中,历史和现实却在不断地毁灭着人的身体,不断使人的身体发生伤残,历史在人身上留下的印记便是历史摧毁人的身体的过程。”[12]125身体并非仅仅指向生物学意义和自然属性,也指涉在具体政治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由权力话语所规训的文化身体。萨利姆的身体写满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和历史,但是作为个体的他并没有影响印度的政治历史进程,而是受制其中。印度的政治和历史现状不断扼杀萨利姆的可变性,使得他无法从其中脱离,最终毁灭他的肉身。
被权力所殖民的身体,具体表现为身体处于社会管控的特殊场域,要求身体变得驯顺、被动,能够被操纵、塑造、规训,任由权力摆弄,对身体进行规约,从而使其失去独立性。对于规范的偏离则会在身体留下痕迹。小说文本中,偏离规范的身体会被刻上诸如“畸形”“怪异”等标签,具体表现为:第一,不同种族间的通婚是对印度传统社会规范的偏离,玷污了种族血统。小说中出现的异族通婚,均被定义为非主流的、边缘化的婚姻,最终直接导致其后代“杂交者”或“私生子”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身体异常、残缺甚至毁灭。第二,不平等的种族性别关系阉割了性别气质[14]。例如,《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的女性纷纷从印度传统社会“忍辱负重”的家庭边缘走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处于父权制核心的男性往往在家庭生活中“忍气吞声”[15]。第三,权力注视/凝视下的女性身体——一种禁闭的身体体验——是被规约和驯顺的突出场域。前文提及《午夜之子》中“穿孔的被单”,表现了男性目光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小说突出两个细节——接受西方医学教育的阿齐兹想要凝视女性身体的医学需求,以及他的凝视目光对接受传统穆斯林教育的女性身体的亵渎。在西方社会,凝视的目光编码凝视主体的认知、征服和同化的欲望。阿齐兹只能透过一个七英寸大小的洞,通过一次一次出诊检查纳西姆身体的不同部分,从而拼凑起纳西姆的形象。在这里,阿齐兹无法将纳西姆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他只能通过想象和零碎记忆拼贴组合。他迫切想要注视她完整的身体,而被单另外一头的纳西姆对阿齐兹的一切均无所知。这里编码传统印度社会中不平衡的男女权力关系:女性作为男性主体凝视的客体,始终处于“被看”的状态。《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童年奥罗拉处于软禁期,在墙上绘画印度母亲,以这种女性身体经验代表被殖民、被软禁的国家政体经历。另外,摩尔人系列组画中出现女性的裸体,而绘画的观看者均为男性。于是,绘画变成性别阅读,成为权力注视和凝视下的身体[16]。凝视之下,女性的身体沦为被动的客体,被权力所控制和规训,失去独立的超验性和自主意识。
第三世界的女性身体甚至沦为后殖民权力规训下贱斥的身体。位于“边缘的边缘”的女性身体特别显眼地出现在《羞耻》中,呈现一系列特色迥异的边缘女性形象:“铁裤处女”阿朱曼·哈拉帕(Virgin Ironpants Arjumand Harappa)叱咤政坛,“好消息”海德(Goodnews Haide)勇于争取婚姻自由,“羞耻”的化身苏菲亚·齐诺比亚(Sufiya Zinobia)采取魔鬼妖女式的暴力反抗……拉什迪为何总要刻意颠覆印巴传统中的女性形象,为何总频频让这些处于“边缘的边缘”的女性走入文本的“聚光灯”?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及后现代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恐怖的权力》中最先提出“贱斥”(abjection)理论,指出贱斥是一种摆脱、游离于主体和客体两者之间的状态,是一种强烈的厌恶、排斥、抗拒之感[17]。这种源自身体反应的感觉,也常常象征着秩序。文学文化批判中贱斥常用来表述边缘化的群体,如有色人种、残障人士、被殖民者、罪犯等。“自我身份边界的高度不稳定,容易走向贱斥”[18]123,“引起贱斥的不是肮脏或疾病,而是干扰身份、系统和秩序的东西,不尊重界限、位置与规则的东西,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模棱两可的、混杂的东西”[18]123。后殖民权力规训下女性的身体就是被贱斥的身体,企图以“不稳定的身份边界”来干扰男权政治所建立的“秩序”,最后成为被权力规范、压制、驯服的载体。
这些备受贱斥的女性身体常常与美丽和情色紧密关联,成为一种消费符号。身体的符号化激发了帝国扩张时期的身体消费兴趣,也显示作为“边缘的边缘”的女性群体在后殖民空间寻求生存的努力。在拉什迪的众多文本中,第三世界的女性身体总是充满异域情调,满身的胡椒味满足了殖民宗主国对东方人的想象。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女性代表性感、妖媚和性欲旺盛。对女性身体描述充斥着快感和欲望,拉什迪小说试图迎合这种消费观,有意将东方印度编织成一个异域快活的身体汇聚场所、一个感官王国。对东方女性普遍的性欲叙述更表现了一套具有殖民色彩的西方话语体系,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语境下的新型身体消费:把东方印度看作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性属身体,边缘化和他者化构成帝国目光之下的印度性。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最早从身体与肤色之间对应的关系来审视被殖民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及其折射的文化观,以及民族身体形象与殖民主义话语之间复杂的共谋关系。他指出:“肤色是种族的最易看见的外部特征,它变成了标准。”[19]自柏拉图和笛卡尔的灵肉分离、二元对立的意识哲学以来,西方社会逐渐发展种族优劣的观念。白人殖民者认为自己是脱离肉体的超脱理性所在,被殖民的黑色人种则被标记为逆来顺受、卑微低劣、被动无声的“身体人群”,被定义为缺乏理性、野蛮落后的他者。这种观点认为殖民统治代表一种理性的种族身体,被殖民的印度则被建构为野蛮的他者身体。《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的外祖母埃皮法尼亚坚持认为帝国统治给予印度秩序、文明和法律,帮助他们摆脱肉体的困境,让他们从卑劣的“种族身体”上升至文明的殿堂。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强制”下的白人中心主义论断。这种论断进一步深化被殖民种族无知、落后的刻板他者化印象。拉什迪以此展开对帝国统治下被殖民命运的深刻思考: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就是被权力所殖民、控制、规训的客体存在,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身体控制。帝国的凝视对印度进行无意识的文化强制,让印度在西方知识规训之中逐渐失去印度性,并逐渐无意识地模仿、认可和同化帝国中心主义。可以说,印度被殖民的命运从政治殖民演变为文化殖民。
六、结语
拉什迪以身体书写的方式呈现后殖民时期印度的社会现实与问题。在他的小说中,东西方文化混杂的身体再现流散而无根的后殖民生存状态。罹患疾病的身体隐喻印度政体建构中由种族冲突、宗教纠纷所产生的政治问题。创伤的身体内化为民族主义理想破灭后形成的心理创伤。被规训的性别身体表征了印度“被边缘化”与“被他者化”的性属身体,表达了拉什迪对后殖民印度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印度从权力规训、消费和凝视之下的帝国资产转化为帝国遗产。这份遗产使后殖民时期的印度在无意识中完成帝国文化强制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印度性始终笼罩于帝国中心主义的强大规训之下。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