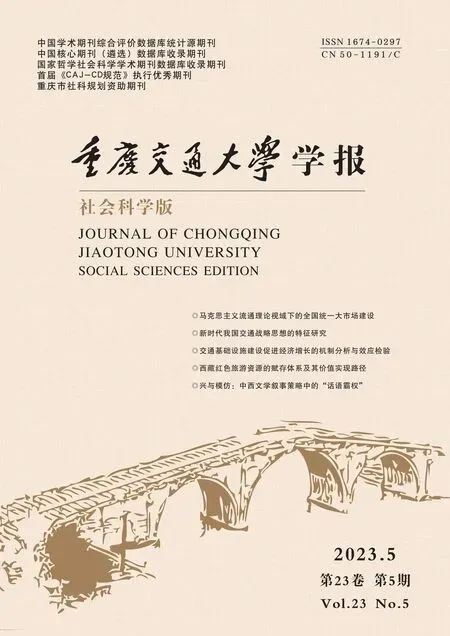疾病与社会排斥
——克莱门斯·J.塞茨小说《英迪格》解析
张 潇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2021年德语文坛最高奖项“毕希纳文学奖”颁给奥地利作家克莱门斯·J.塞茨(Clemens J. Setz, 1982—),他成了该奖历届得主中除汉德克(Peter Handke)外最年轻的作家。数学与日耳曼语言文学出身的塞茨创作了一系列小说、短篇、诗歌与戏剧,先后获得不莱梅文学奖、莱比锡图书展奖、威廉·拉贝文学奖、克莱斯特文学奖等众多奖项。毕希纳奖颁奖辞说道:“他通过惊人的多面性与多元性,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以及颇具诗意与语言创造性的丰富想象,展现出一种激进的当代性,一次次证明了伟大文学的美丽与特质。他通过长篇和短篇小说反复探索着人的界限。他那令人不安的露骨文辞直戳我们当下生活的核心,因为它遵循着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感冲动。”[1]此外,作家父亲工程师的职业背景与作家本人少年时代对计算机技术的痴迷,使得其语言展现出独特的科技感、游戏性、鲜活度与广泛的互文性;母亲的医生身份以及作家本人在残疾儿童研究所、寄宿学校与老年人护理中心的社会工作经历,则使其对个人与社会、疾病与健康等重大人生问题有了深刻认识与感悟,促成其从享受独来独往到投入社会生活的转变[2]。
塞茨的代表作《英迪格》(Indigo,2012)获得当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与2013年德国经济文化组文学奖“文本与语言”,引发德语和英语文学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小说以双线交叉叙事的方式,分别从曾任教于一所患有英迪格疾病儿童隔离中心的老师塞茨和一位曾为该中心患病儿童罗伯特的视角,描述隔离中心儿童的生活状况,塞茨探寻儿童被转移真相以及被传癫狂杀人等一系列事件。作家使用纪录片与悬疑片的技巧,穿插临床病历、研究人员的采访稿、典型病患的诊疗记录与赫比 (J. P. Hebe)小说手稿等真实与虚构的文件插图,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与生物学角度探讨英迪格病与患病儿童的种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乐于并长于“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探讨当下与当下现实”[3]。作家本人与一些文学研究者都认为,这部10年前创作的小说于今天仍有极大意义,不仅照应全球新冠疫情,其揭示的“不得不保持距离,以及人在更深层面上的传染性”问题也使作家扮演了一种“先知”角色[4]。
下面将基于社会排斥的缘起、内涵、类型、成因与后果等理论观点,探讨小说中对患有英迪格疾病儿童实施社会排斥的缘由、手段与结果,思考作家笔下疾病主题的特点、意义与作用,总结作家的思想观点,并通过探究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呈现与评价方式,思考当代疾病主题小说的独特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社会排斥理论简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等西欧国家经历了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阶级结构与社会利益关系变化,面临着新型贫困问题。法国学者勒努瓦(René Lenoir)在《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1974)一文中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法文“Les Exclus”原指被保险制度排除在外者,勒努瓦将精神病患者、身体残疾者、(有)自杀(倾向)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吸毒与滥用药物者、越轨犯罪者、多问题家庭、单身父母、边缘人、反社会者等都纳入被排斥者范畴[5]。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发展,欧洲社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边缘化现象,各国开始从政策层面回应社会排斥这一社会事实;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之外的国家与众多国际组织普遍关注社会排斥这一重大问题,并用相关理论范式分析本国的相关社会问题[6]。
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政策研究者与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侧重点各有不同。2004年欧洲理事会提出:社会排斥是某些个人由于贫穷、缺乏基本技能和终身学习的机会,或因受到歧视,而不能得到工作、收入和教育的机会,被推到社会边缘,无法全面参与社区和社会网络以及各项社会活动,难以触及权力和决策团体,经常感到没有权利以及不能控制影响他们自身生活的决策问题[7]。珀西-史密斯(Janie Percy-Smith)总结社会排斥涉及的具体层面,如政治(民主参与与政治权力受限)、经济(贫穷与失业,不能享受住房、土地、信贷等)、文化(文化歧视、种族或文化中心主义)、公共服务(不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与资源、医疗健康服务等社会保障)、社会(不能正常参与社会交往与社会生活实践)、空间环境(较差的居住条件与环境质量、弱势群体集中化与边缘化)、社区与邻里(公共服务减少,邻里支持网络丧失)等[8]。布查德特(Tania Burchardt)则突出被排斥者社会公民身份的不完全实现和对社会生活的不完全参与[9],并将其主动参与社会公民正常活动的愿望与需要作为社会排斥形成的前提之一[10]。麦克唐纳(G. MacDonald)和利里(M. R. Leary)同样关注排斥者的归属需求,认为社会排斥是指在社会互动中,个体被其想与之建立关系的他人或团体拒绝、分离、排斥或贬低,无法得到渴望的关系或满足归属的需求[11]。个体的关系与归属需要无法在群体或他人中实现是社会排斥现象的核心方面[12],可见,社会排斥也涉及人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其次,社会排斥是无形的,如地位、权利、自尊、期望等的丧失[13]。此外,社会排斥是一个累积性、连锁性、循环性的过程;是个人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各种不利因素累积的结果[14];是一个动态过程,某些劣势导致某些排斥,后者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社会成员在某一层面遭受的排斥往往会使其在其他层面也遭受排斥[15]。
促成社会排斥的因素有社会阶层、种族、肤色、宗教和政治派别、收入、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地理位置、童年关系、个人习惯和外表等[16]。李斌概括社会排斥的六大生成机制:“自我”生成论,由社会下层人员自身行为与态度造成;社会结构生成论,由社会结构本身的不平等性造成;劳动过程创造论,经济发展中人员与信息交换强化员工的参与趋势,对“场外人”产生排斥;社会政策创造论,社会再生产导致群体与个体优劣势的累积,后者又被社会政策强化;意识形态认可论,由传统文化意识、现行法律与政府安排造成;社会流动反映论,人们从劳动力市场、贫困与富裕等状态间的流动性影响群体间的排斥[17]。
关于社会排斥的后果,景晓芬总结了四个方面:导致贫困,这是最直接的后果;不利于社会整合,被排斥群体对社会的认同与凝聚力被削弱,独立、自由与自我意识的发展促使其通过具体行动表达不满;造成被排斥者巨大的社会焦虑与心理压力,产生自卑、失去尊严与地位之感,陷入自我封闭状态;违背社会公正原则,被排斥者的权利与机会被剥夺,其他群体不合理地获得更多利益,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目标[18]。
就小说《英迪格》而言,疾病是社会排斥的直接诱因,患病儿童是社会排斥的具体对象。下面拟分别阐释小说中社会排斥现象的缘由、手段与后果,思考社会排斥理论的内涵与应用,以及社会排斥作为文学现象与社会问题的异同。
二、排斥的缘由
《英迪格》具有十分明显的虚构性,前述社会排斥的六大生成机制与小说情节难以实现一一对应,但仍为读者提供启发。首先,被认为具有辐射性的英迪格疾病无疑是患病儿童遭受社会排斥的直接原因。患病儿童遭遇排斥是完全被动的,纯真无辜的儿童不仅对自己的疾病及其影响一无所知,他们反而被动地承受着成长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如隔离中心一棵与众不同的树那样:它“分明遵循简单的原则生长,向上,分叉,如此等等……这根疯狂的异枝或许是受地下水流、磁场或者光线的影响吧”[19]76。可见,患病儿童对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既无法预料,又不愿其发生,也无法抵抗。相对地,排斥的缘由与出发点则更多是作为大多数的“健康人”对疾病本身的错误认知。
小说中的疾病被命名为“Indigo”,该词源自希腊语“indikón”,在德语中意为“das indische”(印度的),是一种源自印度的植物中提取、现在亦可人工合成的靛蓝色,它作为颜料与染料的历史悠久,并对基础色彩理论的建立与有机化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但在数学老师塞茨看来,却是“最可笑的”“十足荒谬”[19]23的一个指称,因其无法起到一般命名应当达到的作用,即帮助人们认知某事物并将其范畴化。这体现了正是由于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疾病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首先体现为怪异的症状:患病者无一例外是2000年前后出生的儿童;他们与正常儿童相比没有任何外在异常;本身也无任何不适,却会使靠近者“头晕、腹泻、发皮疹,重则导致所有内脏的永久性损伤”[19]22,且症状随距离缩小而加重,甚至已故儿童的尸体必须火葬,否则不能埋入公墓,以免继续伤害健康人。
英迪格疾病的神秘性使人们对其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正如司汤达《阿尔芒斯》中,奥克塔夫的母亲拒绝说“结核病”,她怕一旦说出这个词,儿子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人们甚至只能用首字母“I-疾病”“I-儿童”(以下均使用该表述)来谈论。如桑塔格所言,疾病“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19]7;人们会出于认知不足与对疾病传染性的恐惧,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大疾病赋予消极意义,“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19]53。而这种认识层面上的消极赋义与疾病本身是否具有传染性并不直接相关。小说中对疾病名称的选择与确定——人们避免以首例患者姓名“罗彻斯特综合征”命名或采用类似“艾滋病”等本身具有歧视色彩的指称,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疾病与患者的消极认知。
对疾病的恐惧与消极赋义根源于对“他者”的界定与敌对。人们会“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做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21]88,并且“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21]121-122,疾病最终被等同于邪恶和不洁。小说中,人们对I-疾病与I-儿童污名化与妖魔化的最极端表现,即对I-儿童尸体火葬。因为火在西方宗教与文学传统中兼具惩罚与净化的作用,如《圣经》中天火烧灭罪恶之城索多玛,地狱中不灭之火刑罚异教徒,以及《神曲》中永火折磨罪恶灵魂。
排斥他者意味着与他者保持距离。个体与同类中的其他个体以及与异类之间都会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这是动物在发展进化过程中普遍培养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小说中多处出现“proximität”(英文proximity)一词,该词原指时间或空间的临近,文中指“安全距离”。“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的封锁区半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封锁区半径重合,人们就会陷入恐慌,继而不断拉扯、吼叫。”[19]442塞茨老师到隔离中心任教之前,在当地一处“距离意识与学习中心”做研究工作,隔离中心的I-儿童之间也要时刻遵行这一原则,连其中思想最为叛逆与先进的成员也极力鼓吹“安全距离”说。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排斥不仅局限于小说中的I-儿童等特殊人群,也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普遍现象,隐而未现,却无处不见,针对的对象可以是一切相对于排斥主体而言的他者。
与促成社会排斥的一般因素如能力缺乏、贫穷无业、越轨犯罪等相比,小说中I-疾病本身的真实性一开始就被作家悬置。不仅塞茨老师始终质疑其真实性,相关看法也缺乏科学依据,“或许只是一种臆想”,“专业文献中鲜有提及,提及涉事者时也只给出姓名的首字母,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123-124,甚至一位英国母亲误判儿子病情而引发一时轰动。即便如此,出于对未知他者的恐惧与错误偏激的认知,人们仍断然将I-儿童一概送至隔离中心,将其从健康人的活动区域中排除。
此外,Indigo(靛蓝)独特的实际应用场景也赋予其一定的社会隐喻与讽刺意义。一方面,靛蓝有医疗保健功能,作为中药成分,可辅助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牛皮癣、喉咙和喉部感染等疾病[22];另一方面,它在日本传统医学中被用作抗炎物质,如武士穿着用靛蓝染色的衣服来治疗伤口,靛蓝染色的毯子和衣服是送给新生儿以保护其免受疾病侵害的传统礼物[23]等。可见,作家用一种原有医治功效的元素来命名一种疾病,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还需注意的是,Indigo还指一类(通常是儿童)不适合现有社会体系、与众不同、天赋异禀、象征人类未来与希望的世纪“超人”(1)相关观点可参见:JAFFE K.Indigo-erwachsene.Wegbereiter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M].Hanau:AMRA,2008; HUPPERTZ SV.Indigo-und kristallkinder:Die Kinder des neuen bewusstseins[M].Dürrholz:ausZeit,2010;VAN HELSING J.Die kinder des neuen jahrtausends:mediale kinder verändern die welt[M].Fichtenau: Amadeus-Verlag,2021;MARTENS A.Ein Indigo zu sein ist ein geschenk[M].Norderstedt:BoD,2022等。。小说中也有多处暗示:作为I-儿童代表的罗伯特时常将自己想象为蝙蝠侠,成年后的罗伯特果真成了一位成绩斐然的画家;其他所有“拥有英迪格蓝色气场的孩子们”都拥有“巨大的潜力”,尽管在隔离中心时未能接受正常、充分的教育,但在离开隔离中心后,无一例外地在各个领域取得斐然成就。他们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智性的存在”,标志与引领着一个新时代,“一个鱼的时代”,甚至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它”[19]52-53。将I-儿童与灯泡类比——“他们就像灯泡。未来某个时刻就会油尽灯枯,他们的影响力将消失殆尽。大部分发生在成年阶段早期”[19]196-197,则可视为对构成社会主要力量的成年人的讽刺:后者受过教育,心智成熟,自诩健康道德,握有判断与支配外物的权利,实际上却平庸无能,不能促进世界与文明进步。这样看来,作为进步性、革新性力量的I-儿童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及人的既有地位和观念产生冲击,必然遭到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健康人或普通人诋毁、排斥与打压。这与桑塔格的观点“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21]65再次形成呼应。新旧社会秩序的对立与强弱关系也通过I-疾病的一个奇异特点折射出来:患病儿童本身感受不到痛苦,出现各种症状的反而是周围的健康人。这也说明,小说中的I-疾病并非作为一种有医学可能性的现实状况,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学隐喻得以呈现;人们对I-儿童的排斥行为实则基于自我保护与利己主义的集体性错误认知,是对社会革新力量的排斥。
三、排斥的手段
就实施社会排斥的施动者而言,学界现有研究中鲜有系统全面的阐发。方长春的定义“(社会排斥即)以某种(人为设置的或潜在的、自发形成的)机制限制一些个体或群体获取特定资源”中所言的“某种机制”是一种较为灵活宽泛的表述。伏干则指出:“在社会排斥的概念体系中,施动者通常没有被明确指出,而是通过在概念形成过程中‘谁被排斥’和‘排斥出什么’来建构施动者”,有时“无法将社会排斥的施动者建构在某一特定对象主体上,而是施动者被一个被操作化了的抽象主体所代替”[19]112-113。小说中,作家并未直接提及政府、制度与结构问题在排斥过程中的角色,所涉各方——隔离中心管理与研究人员、教师、医生、I-儿童的家人,也未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直接表露排斥意图,而是用看似合情合理、符合公共利益的理由掩盖与美化实际的排斥行为。这说明:第一,社会排斥可以在有限的范围与层面产生,往往根源于意识、认知与情感的排斥;第二,社会排斥具有累积性与连锁性,一方发出的排斥会激发其他多方共同排斥,排斥因而总是一种集体行为。此外,实施排斥的个体在与其他实施排斥者的隐秘“合作”中会陷入一种对自身行为的无意识,并将排斥行为常态化、合理化与隐秘化。这一点通过小说中的一个类比映射出来:“比如一家专门生产武器的公司,做着把神经毒气爆破筒卖给秘密公司等一些毫无人性的黑暗勾当,但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是善良、友好的公民,只是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并且会在下班后心满意足地坐在电脑前,观看普通电影里善良女人的悲情戏。都是正常的男人、女人,为人和善,很好相处,甚至相当理智。”[19]439
探究社会排斥的手段时,可参照理论部分总结的社会排斥实现的具体层面,即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服务、社会、空间环境等。就小说内容而言,I-儿童遭受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社会与空间环境方面。
为I-儿童设立的隔离中心是对其进行社会排斥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隔离中心位置偏远隐蔽,人们要经过“一条黑暗的、被诅咒了的林中道路”才会发现它,并且“永远也不要希望里面关着的精神病人会康复”[19]76;隔离中心内部“空气黏稠、沉重,宽大的窗户从不会打开,任何角落里都能闻到刺鼻的油漆味和地板清洁剂那股具有攻击性的气味”[19]62。可见,隔离中心的周边环境与内部居住条件相当恶劣,人们通过将I-儿童边缘化与集中化实现排斥的第一步。就隔离中心的核心任务而言,I-儿童与外界彻底隔绝,见不到隔离中心之外的任何人,无法与父母和同龄人交流。隔离中心剥夺I-儿童正常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权利与机会,并通过一个与众不同、自我封闭的场所,为严格实行纪律创造了必要前提[24]160-161。
严格的纪律规定不仅旨在切断I-儿童与外界人和事物的联系,而且也为限制I-儿童之间的联系。I-儿童私下跑出自己房间,与其他孩子交谈的行为会受到惩罚;在玩方格游戏时要严格遵守独特的游戏规则,精准地站在五点梅花形的连接点上,“孩子们之间永远保持着出奇一致的距离,此外,也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没错,这正是孩子们的悲剧与胜利所在”[19]197-198。尽管隔离中心负责人鲁道夫博士——用德语范围内已成禁忌的希特勒之名,不乏讽刺意味,认为该游戏“非常有益于康复”[19]215,但其弊端显而易见:其一,空间上的绝对距离限制I-儿童间的交流,造成其心理疏远与情感冷漠,更无法促成群体聚合力与团队精神;其二,同样的衣服反映出隔离中心对I-儿童个体的高度同质化认识与要求,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心对I-儿童编号并用绝对数值量化的做法上。
方格游戏体现的同质化管理方式符合福柯所言规训机制中常见的空间利用法,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进而“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24]162。因此,可以说隔离中心是为了遏制被排斥儿童中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实施高效控制,以规训与纪律的形式限制甚至剥夺儿童的自由选择权,不容其逃脱与反抗的监禁场所,相比修道院、军队、学校而言,是更为谨慎、隐蔽与有效的实施纪律的机构。
对儿童的终极排斥手段则是作为小说另一高频关键词与第五章标题词的“转移”(relozieren)[19]221。该词源自拉丁语,部分对应德语中的“versetzen”,即“将……移至或置于某种(消极)境况中”,暗示被转移至的新环境的恶劣。隔离中心工作人员乔装打扮被转移的孩子,像给葬礼上的孩子化妆以使其应对艰难处境,但这只是面对外界与患病儿童的掩饰、欺骗与美化。相关人员对被送去的环境含糊其词、避重就轻,“合理利用英迪格潜力协会”的会长鲍姆赫尔说道:“孩子们会被善待。至少是相对好地对待。有吃有住,不受酷刑……我也不知道,是有战略意义的建筑旁的一所学校,还是一间监狱。”[19]323协会将“有吃有住,不受酷刑”当作可以执行的标准,可谓对人道主义与博爱原则的轻视;协会对I-儿童的“利用”则反映出利己主义原则。
这种利己主义的表现十分明显。在I-疾病为人所知之初,市场上出现一系列相关主题的T恤、杯子等商品;媒体争相报道与杜撰离奇事件以赚取利润;美国布鲁克林地区的大批年轻母亲甚至排队售卖自己患有I-疾病的孩子,以换取钱财和补给品;甚至连隔离中心的负责人也感叹道: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建材市场。货架、货架,到处都是货架,每排货架上都摆满了工具,人们可以任意取用,直到将其用坏。您想想动物们吧!只要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动物,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永远是“我们能不能吃它”这一问题。在我们人当中也是如此。一个小孩出生后,人们便会思考:这小孩有什么用处?对我有什么好处?[19]385
可见,人与人之间盛行着一种工具性对待原则,一种将自我以外的一切存在为我所用的倾向。而这种对人的异化与工具化会进一步发展,造成被利用者的痛苦与损失。比如一群原本单纯善良的富家孩子在社会消极环境的熏染下,成了毫无怜悯之心的自私自利者,他们主动接近克里斯托夫,并非为了陪伴安慰,而是以其为工具,进行“勇气实验、流汗疗养以及锻炼忍受能力”[19]287。在作家看来,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是欧洲人久已有之的通病,贯穿包括殖民掠夺、民族融合、民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等阶段的欧洲文明发展全历程,并已深入骨髓、难以革除。作家借布鲁塞尔专家费伦茨之口,以看似模糊暧昧,实则辛辣冷峻,并具有一种荒诞美学的语言说道:
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可以折磨别人,只要这能缓解我们的头痛。我想,我们出了问题。很可能出在我们的遗传基因上……可能在于我们经受过的众多疫病。我们是最先建立城市的……不知何时起,我们就出问题了……我们祖先那更加强健的身体有着一种“硬件缺陷”。思想沿着怪异的轨道展开……比如我们喜欢听别人哭喊[19]412-413。
作家借此表达对欧洲文明发展的批判性反思,指出排斥是权力博弈与利益争夺、确立强势地位与满足优越感的动力、手段与结果,不仅见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也会产生于种族与文明之间。
最后,在隐秘的施动者中,家人尤其是父母对I-儿童的排斥起到重要作用。塞茨老师初到隔离中心时,希望从I-儿童的家庭环境与成长经历寻找患病原因。小说第五章记录了一条令人唏嘘的报道:一位疑似患有I-疾病的五岁女孩被父母锁在家里并遗忘,几天之后饥渴而死。男孩克里斯托夫儿时,爸爸由于无法承受心理与身体压力,某次以买烟为借口,彻底离开母子二人,而这种“某次买烟时一去不返”的年轻父亲不计其数;克里斯托夫的妈妈同样持有一种绝望心态,“我不抱任何希望。坦白地讲。我是现实主义者”[19]125。父母至亲从身体上的远离与躲避、情感上的抛弃与放弃,都构成对I-儿童极大的伤害。这在作家看来无异于一种隐性暴力,然而“家里的暴力是最常见的。一个人最初接触到的人际关系即与家人的关系。每个孩子都被交付父母,其生命由此开始。这个初始阶段中隐藏着诸多贯穿其一生的极端成分。邪恶、破坏和折磨与健康和安全最接近的地方就是家,二者在家里相辅相成、难以区分”[25]。
四、排斥的结果
社会排斥不仅涉及人的物质需求,也涉及精神与心理需求;不仅导致被排斥者无法(充分)获得各项权益与服务,也体现为地位、权利、自尊、期望等丧失。小说中,对I-儿童的社会排斥造成如此多的后果,以下扼要列举两方面。
(一)社会交际(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冷漠
隔离中心I-儿童的整个童年时期到成年阶段早期都“在他的I-空间、他的专属区、辐射区里度过”[19]78,缺乏必要的社会交际生活。住在家中的克里斯托夫同样被母亲“监禁”起来,他认识与参与外面世界的渴望只能通过三台望远镜来实现,人际交往也仅限于与一个同患I-疾病黑人男孩的书信往来。在遭受坏小孩捉弄与欺辱时,克里斯托夫没有躲避或反抗,反而一再落入前者的圈套。与其说他缺乏社会经历,不识人的恶意,不如说他情愿遭受恶待,也要与自我和疾病之外的世界建立联系。长期遭受显性与隐性排斥的I-儿童,在隔离中心严格纪律的约束下早已形成躲避人群的本能性反应机制,“(马克斯的)后退躲避似乎是无意识的举动,一种自然反应,就像人们下决定时摩擦双手,或不耐烦地等待时跷起二郎腿时那样”[19]191。此外,塞茨老师就特定人群遭受排斥举过一个极端实例:登山者们保持距离前行,一位队友突然身体僵硬、意识模糊,而其他人为了保存体力、节约物资,既未出手相救,也未及时求救。这种排斥行为反映出人际关系之冷漠,根本上出于人类自卫自保、自私自利的本性,如小说中罗伯特所引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那句“人与人之间恰如狼与狼”[19]188。这种排斥、冷漠与残忍最终导致I-儿童的社交恐惧和社交无能。罗伯特在隔离中心的短暂生活期间变得敏感易怒,甚至有了迫害妄想症的表现:他因个人画展偶遇欣赏者的询问而惊恐不已,久久不能释怀;与女友分开后疑恨暗生,闯入昔日好友之家大肆破坏;对曾经的数学老师始终抱有恐惧、怀疑、轻蔑与排挤的态度。
而在I-儿童内部,同样存在这种冷漠与疏离。孩子们尽管处于一种甚至多种形式的共同体关系中——居住在一起者组成的邻里共同体,或具有一致的思想倾向与(因患同种疾病而可算作)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友谊共同体[26]中,却由于严守距离原则,缺乏真实有效的交流,彼此间没有同病相怜的安慰,没有同甘共苦的盼望,没有得到保护与理解的安全感,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情感相系、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相反,他们不得不承受“让人作呕的那种自己是唯一一个被人们这样对待之人的感受”[19]78,在困惑、迷茫、绝望与麻木中度日。
(二)话语权与自主权丧失,认知与情感受挫
对I-儿童患病与否及其严重程度的判定是除I-儿童外多方外部力量联合作出的,作为多数的一般群体对作为少数的特殊群体在认知与情感层面的排斥可谓对后者实施排斥的第一步。讽刺的是,关于I-疾病尚无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或检测手段,一切医学假设都可能是谬见,一切旁观者的描述也不可靠,各样的科学实验与调查研究非但没有澄清I-疾病,反而加深人们无理的臆想与固执的偏见。而“当一个医生把一种人体状况诊断为疾病时,这一诊断就能够而且常常改变病人的行为。因此,患病是一种人为创造的状态,这一状态和他们对实际情况的理解相一致”[27]。小说中,作为患者的I-儿童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自己是否有病的发言权与决定权被完全剥夺,属于自己的身体也被他者的认识与论断异化。处于感知与认识世界、培养认知与判断能力关键阶段的I-儿童不得不依附于外界对自己的评判,被动建立模糊甚至错误的自我认知。
不仅如此,人们对他者的界定与妖魔化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21]88。甚至可以认为,前述克里斯托夫甘心接受坏孩子的捉弄,是因为认同他人对自己不洁、有罪的定断,认为自己不配拥有自尊与希望,甚至理应蒙受偏见与羞辱。这种荒谬且危险的观点“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21]43-44。该问题一方面导致父母、亲人对I-儿童身体与情感上的双重离弃,使其不得不适应孤独绝望的处境,甚至如同待宰的羔羊,毫无反抗地服从命运安排。罗伯特在生物老师办公室杂志封面上看到逆来顺受的蚯蚓——“铁丝穿过它们的头部和大脑……但此处的这种生物不管经受多么残忍的凌虐,都丝毫不会想到复仇或自卫”[19]207时,甚至得到一种比宗教能带来的更大的安慰[19]218,旨在赦罪与救赎的宗教似乎已无法为遭受社会排斥的I-儿童提供安慰与出路。另一方面,这也致使社会各方因为对I-疾病与I-儿童的绝望态度而不愿在资金、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隔离中心仅仅致力于对I-儿童的隔离与控制,并未积极探索认识I-疾病并寻找治疗方案,诊所与各处研究中心进行的动物实验毋宁说是一种欺骗性的表面工作。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21]111诚然,I-疾病本身并未给I-儿童带来痛苦,却导致社会各方的排斥,从而造成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在鲁道夫博士看来:“这个世界对社会权力与机会有限的孩子来说和对我们常人来说是不同的……在这些事上,没有圆满的结局,只有公平的结局。”[19]211事实却是,社会排斥反映出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客观存在着,而所谓的公平总是对作为大多数的健康人利益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既未探讨社会排斥的解决手段,也未提供被排斥者获得慰藉与帮助的有效途径。这一方面揭示出社会排斥这一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是发挥了文学作品激发读者独立思考与自由阐释的特长。
五、结语
与《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丧钟为谁而鸣》等传统疾病小说相比,奥地利作家克莱门斯·J.塞茨的代表作《英迪格》赋予疾病独特的样态与内涵。英迪格并非黑死病、鼠疫等真实历史事件或已有临床实例的医学现象,而是一种结合疾病表现与疾病想象、社会现象与文学创造的诡异可疑的虚构疾病。小说非揭露社会矛盾、呼吁人性美善的战斗檄文,而是寓荒诞于真实,寓幽默于沉重,隐晦而巧妙地指涉社会排斥问题。作家深入人的天性本能与社会性的合理之处和阴暗方面,表达人道主义情怀与对欧洲文明发展历程的批判性思考。基于对小说中疾病与社会排斥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排斥并非基于实证事实,而是人们出于恐惧,基于对他者的界定,以及面对他者的自卫与利己本能作出的反应。这一心理根源表明:排斥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难以通过文明的进步根除;其对象并不限于特定的弱势群体,而可以是相对于排斥主体而言的一切他者。小说中“病人”之健康与“健康人”之痛苦的反讽式对比,则抛出了健康与疾病的界限、疾病的判断标准与判断者等问题。此外,英迪格儿童的特殊性与康德、歌德、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将天才或超人与疾病联系,以患有或战胜疾病来升华生命的理念形成隐秘呼应。可以说,排斥亦可是既有社会规则下的多数人对作为少数的革新力量的敌对。
第二,在排斥的实施问题上,排斥是对特定少数群体的范畴化与边缘化,有显性与隐性实现形式。隔离中心剥夺患病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以机械性的同质化管理与严苛的纪律要求对其规训;父母的身体与情感疏离作为隐性暴力加剧社会排斥;陌生人的捉弄、社会各方以病取利的行为更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工具性对待原则和极端利己主义。排斥总是多方合作、互相激发的社会性行为,并会在产生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中被常态化与合理化。排斥是权利博弈与利益争夺、确立强势地位与满足优越感的动力,手段和结果,不仅见于特定社会群体之间,也会产生于种族与文明之间。
第三,就排斥的后果而言,疾病既是儿童个体与社会的联系纽带,也导致其社会关系恶化与崩溃。受排斥儿童不仅缺乏必要的社会参与经历,社会交际无能,形成创伤后自我封闭的自然反应机制,导致群体内部的疏离、冷漠以及共同体意识的淡薄,他们也丧失对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决定权与自由发展权,在排斥环境中被动形成模糊、错误的自我认知,陷入自卑、孤独、迷茫、绝望与麻木的处境。
小说《英迪格》的现实意义不限于创作当时与当地,而是能为全球后疫情背景下,甚至各个时代的读者提供关于人性、社会与文明的思考。读者可以借此探讨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何对待对社会大多数有不利影响,却同时需要保护的少数群体?如何认识家庭与社会各方对病患等弱势与边缘群体的责任和负担?如何为患病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教育?如何平衡本能情感与社会共识、自由发展需要与纪律规训机制,以及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如何达到社会平等、认同、接纳与融合,促进理解、博爱、守望相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文学在其中可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
疾病虽发生于个体,却总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在个体之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疾病与边缘人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建立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涉及人性与存在等根本问题,不仅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经典主题,也为当代作家所重视。作家的另一部小说《女人与吉他间的时光》(DieStundezwischenFrauundGitarre,2015)、Peter Härtling的小说《思维游戏者》(DerGedankenspieler,2018)、Martin Schäuble的小说《纯净之国》(Cleanland,2020)、Jasmin Schreiber的小说《马里亚纳海沟》(Marianengraben,2021)、Juliane Pickel的小说《驼背的狗》(KrummerHund,2021)等近年来优秀德语文学作品均以疾病与社会为主题。这些新疾病小说通过灵活新异的表现手段与叙述技巧,赋予疾病更加多元多面的意义,在为读者带来特殊的审美体验与情感慰藉的同时,也从文学角度为描述、探讨甚至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宝贵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