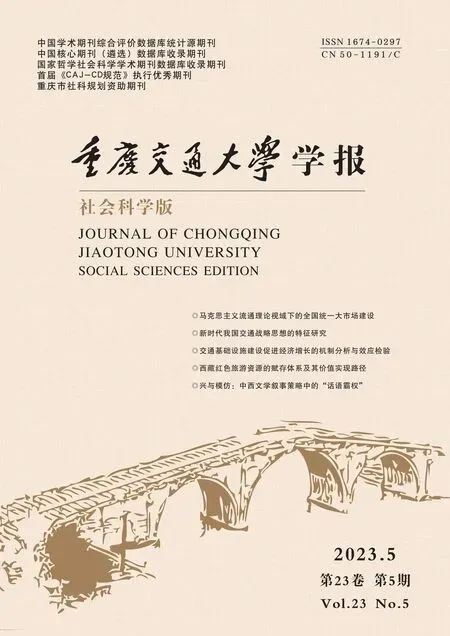兴与模仿:中西文学叙事策略中的“话语霸权”
刘秀哲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话语霸权”往往作为政治性话语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实则不然,文学叙事中同样会存在话语霸权,并且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深刻地反映文学的演进与变革。那么,如何通过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来表达文学的功用,中西方文学有着不同的叙述策略:中国往往选择“兴”的手法来抒情叙事,西方更倾向于以“模仿”来表达。
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罗大经认为“诗莫尚乎兴”[1]113;朱熹则认为“会得诗人之兴,便有一格长”[2];杨载更是誉兴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3]。可见,兴作为叙事策略的重要性,绝非他者所能及。同样,西方学者极为重视模仿,赫拉克利特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首次提出“艺术模仿自然”[4]89;亚里士多德以模仿作为文艺的本质,认为“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4]11;阿多诺虽然认为艺术模仿现实仅仅是一种表象,但又肯定在艺术表象背后的否定性契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兴与模仿两个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概念,在文学叙事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同中国谈诗必曰兴,西方谈文学必曰模仿。长此以往,兴与模仿便贯穿中西方文学叙事的始终,无法被其他概念、范畴所企及,进而取得话语霸权地位,也使二者的比较成为可能。不过,二者虽然在文学叙事中同样具有话语霸权地位,且可以互为参照,却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该于同中见异、异中趋同,唯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兴与模仿的本质和区别。
一、 何为“话语霸权”
探讨文学叙事策略中的话语霸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什么是话语霸权,如何理解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其实,话语霸权并不是一个单纯词,而是合成词,是由话语与霸权组合而成的一个新概念。在西方语言中,“话语”一词源于拉丁语discursus,含义是讲话、谈话。巴赫金将话语指向言语层面,它与发话人、受话人,以及“由发话人所发现的词语中的人”相关,而不与语言层面产生联系;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巴赫金的话语体系,并在意识形态上使用话语一词,指的是“话语结构(discursive formation),是一个陈述(statement)的分散系统。它不是一个和陈述处于同一水平的结构。话语构型只是对不规则的陈述分布进行规则化”[5]。其中寄寓了某种权利意识,唯有在权力的运作下,陈述才能够成为现实,并使话语拥有权力。拉克劳与墨菲所谓的话语与巴赫金、福柯的不同,他们认为话语“是一个来自链接行为的结构性差异总体。然而,这个总体却是永远都无法完满实现的。话语永远都是一个无法完全固定下来的过程,该过程是在一个话语场域内通过链接而发生的”[6]Ⅵ。这意味着话语只有在话语场域内才有意义,一旦离开话语场域,客观世界就陷入一片混沌,不再显现具体的意义。虽然历史上对于话语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无论哪一种话语体系都不能否认话语的本质特征——言说,在文学领域内同样如此。话语作为一种叙述功能,始终存在文学叙事之中,并以特殊的方式——文学话语在显现自身的同时表达丰富的意旨。
与话语体系的流变并无二致,“霸权”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也并非一成不变,该词源于希腊语egemon,含义是领袖、统治者。19世纪开始,霸权主要在国际关系范畴中使用,用来形容一国对他国的支配行为。随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将其发扬光大,使其超越国际关系的范畴,“介入阶级与社会结构分析,延伸到文化领域”[7]540,并提出“文化霸权”概念。虽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称之为文化霸权,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而是与国家、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与运动战等多个概念错综交织,内涵深邃而复杂。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进一步发展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形成“话语—霸权理论”,是指“霸权可被看为话语或一系列话语的扩张而成为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orientation)和行为的统治性视域,它在因对抗力量的存在而变得凌乱不堪的语境中把不固定的因素链接到部分固定的要素之中”[6]101。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霸权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一样,有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关联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在该领域内由于话语的扩张,霸权逐渐显露并形成,随之上升为社会价值取向。与西方不同,中文语境对霸权的理解往往带有贬义,与操纵、控制、侵略等词语联系,甚至1990年代之前在诸多文献中并不常见霸权一词,而是被译成领导权,这显然与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有关。实质上,霸权并非总是与凶残、野蛮、霸道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语境相关联,在文学语境中也是如此。
于中国而言,霸权抑或话语霸权无疑是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并不存在此概念,即使存在话语霸权现象,也往往与西方所谓的话语霸权相异。例如,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话语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领域形成一种话语霸权;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宋明之际,宋明理学家将孔子的话语奉为圭臬,成为文化领域中不能质疑的权威话语,借以推行儒家的礼教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它的发生与形成往往有特定的时代语境。所以,即使这种话语霸权在封建社会主要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旨归,但其所具有的积极的礼乐教化作用同样不容忽略。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以儒家为代表的话语霸权逐渐处于濒临解体的境遇。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儒家为代表的话语霸权彻底失去根基,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此后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而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优秀的传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国人的一言一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文化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共融的方向发展,中国话语一直存在,但是霸权现象不复存在。
在中国,对于霸权一词的使用可追溯至梁启超。他早在《欧游心影录》(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中便使用“文学霸权”一词,借以描述“欧洲文学潮流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动,由浪漫忒派(浪漫主义)向自然派(自然主义)的逐渐流变,不见欺压各派、唯我独尊之意”[7]541。但仅就文学领域而言,我们所使用的话语霸权既不指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也不指向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霸权理论,亦与汉代、宋明之际以儒家话语为指导的霸权,以及梁启超的文学霸权均不同。在文学领域中,话语霸权首先表现出自身独立性,是审美无功力的文学叙述策略;其次才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属性,参与社会治理;最后,在文学中使用话语霸权,往往更倾向于话语叙述,表现其作为话语叙述的不可或缺性,而不是偏重于霸权的独特性与异质性。因此,话语霸权作为文学叙事策略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贯穿于文学叙事的始终而不可或缺。
不可否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叙事策略中的话语霸权始终存在,但对于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我们不能狭隘理解,除了要合理取舍其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还应看到其中所寄寓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表达情感的倾向。
二、作为话语霸权的“兴”
在中国,文学叙事往往强调隐而不是显,即强调文学应以一种婉转、隐蔽的形式来表情达意。文学如何做到婉转、隐蔽且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既使文学起到表情达意的效果,又使文学不失其为文学的特性,便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作家往往借助叙事策略来实现这一目的,在众多的叙事策略中,中国首先选择以“兴”的手法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谢榛曾曰:“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8]即兴在诗歌中的运用可以使诗达到绝妙的境地。可以说,诗要用兴,是中国作家及文学理论家的共识。长此以往,谈诗必曰兴,可谓中国文学叙事的一种常态,兴在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地位随之确立。
何为兴?在文论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周礼·春官·大师》的“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9]610,到《毛诗序》的“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9]610;从郑司农的“兴者,托事于物”[9]610,到郑玄的“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9]610;从刘勰的“兴者,起也”[10]601,到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11];从孔颖达的“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引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12],到朱熹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13]。可以说,在中国关于兴的论说绵延千载不衰,但究竟何为兴?历来学者又莫衷一是。陶水平在《“兴”与“隐喻”的中西互释》一文中认为,兴“包含‘起兴、感兴、兴发’与‘兴喻、譬喻、比类’两层最基本的含义”[14]99。这一概括总体上列举了古人关于兴的基本内涵。与作为文学叙事策略的兴而言,无论是“起兴、感兴、兴发”之意,还是“兴喻、譬喻、比类”之意,其所具有的话语权较之他者更略胜一筹,事实也确乎如此。
古人虽然对于何为兴有争议,但在文学表达上关于兴的见解却极为相似。傅玄曰:“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15]他认为兴是以婉约的方式来表达宏富的意旨,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钟嵘曰:“宏斯三义(指兴、比、赋),酌而用之……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6]47强调在诗中运用兴可以将诗的意蕴发挥到极致。郑樵曰:“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17]认为兴为诗之根本,唯有在诗中运用兴,诗才能称其为诗。葛立方曰:“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18]强调兴之于“工诗者”自古以来便是不可或缺的。贾岛在《二南密旨》中认为,兴在诗中除了具有“起兴”的作用外,更在于“感物”,并将诗中所有的意象都赋予兴的意味。可见,在文学中使用兴历来为文学家所看重,更为文学理论家所标榜。虽然上述关于兴的见解并非完全是针对兴的表现手法而言,但其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运用于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成为文学家的共识。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强调:“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为章。 当其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19]显然,叶燮是从诗歌发生学的意义来谈兴,意在表明唯有兴至,其意、辞、句方可至,唯其如此,诗方可成。可以说,兴之于诗所具有的属性是其他文论范畴、概念、命题所不具备的,同样也是无法企及的,包括与兴并举的“赋”“比”皆是如此。刘勰便认为,“比显而兴隐”,“比小而兴大”;孔颖达则认为,“比浅而兴深”,诸如此类的见解不一而足。也正是源于兴作为表现手法具有意蕴深厚、包举万千的特性,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才会出现谈诗必曰兴的现象,而兴作为文学叙事策略中的话语霸权才得以确立。
兴作为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除了体现在诗歌创作手法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其所具有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的特征上。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0]孔子从诗的功用上阐明兴的作用在于激发人的心志,起到道德教化的功用。郑玄在孔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9]610郑玄将兴与“美刺”相结合,虽然给兴蒙上一层政治色彩,但强调兴具有含蓄隽永的特征,在实现政治目的之外使诗具有审美色彩。虽然后人想要极力摆脱兴的美刺功能,但这一理想的实现并非易事。到了魏晋,刘勰依旧强调“兴则环譬以记讽”[10]601,从本质上并没有脱离兴的美刺功能,但是美刺的实现要以含蓄隽永为前提。就本质而言,兴具有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的特征,一方面与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相关,中国人在言说中往往更倾向于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真切想法,这样既符合受众的心理特征,也符合言说者的用语习惯。另一方面与中国的礼法文明相联系,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如何婉转而顺理成章地劝谏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兴的运用则化解了这一难题,其所具有的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特征在劝谏时既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又起到劝谏的效果,可谓两全其美。这样一来,兴的使用就超越其作为创作手法的地位而延展到其他领域。此外,赋也同样用兴,如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的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21],即强调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这种讽谏的发生恰是以兴为中介。所以,兴所具有的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特征为文学叙事提供另一种可能,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应用。长此以往,在文学叙事中兴所具有的特征便潜在地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即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思想与情感。
兴在文学叙事策略中话语霸权的形成不仅与文学创作活动密切相关,文学接受活动同样促进兴作为话语霸权的形成。首先,文学中兴的使用,能够起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言简意赅的表述方式更能为人所接受。钟嵘认为“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16]47。其次,文学中兴的运用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其写景状物求其神似而不求形似,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写景状物时以“‘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10]693-694,显然要好于直接的景物刻画。从接受角度来讲,兴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也是“赋”“比”所不能及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说:“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1]113言外之意,兴所强调的是含蓄、隐蔽,而不是直白、急切,由此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进一步推动兴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唐代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也谈道:“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22]虽然他没直接表明兴在诗歌中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作用,美刺的功能,含蓄隽永、韵味无穷的特征,但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批判齐、梁间的诗,认为诗不可无兴,以此能够发现他对兴的推崇。换言之,文学创作最终要面向广大读者,而读者将阅读感受反馈给作者,以此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进步,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与意义。对于兴而言,其作为文学叙事策略在文学中的广泛运用,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形成话语霸权,在文学接受上同样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
从文学的创作、表情、达意以及接受来讲,兴作为一种话语霸权始终存在。即兴无论作为一种表现手法还是一种诗学观念,它本身便是一种话语。它在文学叙事策略中如何形成一种霸权,其实是理解兴作为文学叙事策略中话语霸权的关键所在。兴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其霸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首先,兴作为一种话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语义不断丰富,而其所具有的霸权正是建立在兴的语义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其次,文学创作与接受为兴作为一种霸权的实现提供可能,在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互动之中,兴得到广泛应用,其所具有的霸权属性逐步确立,最终在文学叙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话语霸权,成为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叙事策略。
三、作为话语霸权的“模仿”
文学起源于模仿吗?是,又不是。文学的本质是模仿吗?是,又不是。之所以下此判断,是基于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丛概念,很难用单一的学说来界定它为何物,或许阿尔都塞关于艺术起源的“多元决定论”,以及沃特伯格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关于艺术概念及本质的28种梳理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即便如此,文学与模仿的亲缘关系是无法割舍的,这一问题从古希腊至今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衍生出关于文学是自由的游戏、情感的表现、“有意味的形式”、情感的符号、无意识的表现等学说,模仿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依旧没有缺席。或许从最广义的意义来讲,任何一种文学形态都有模仿的影子,这也造就了模仿在文学叙事中所具有的话语霸权属性与地位。
与兴类似,西方关于模仿的记载在古希腊时期即已存在。模仿最早起源于祭祀活动,经过前苏格拉底时代先哲们的艺术总结,逐渐与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相联系,赫拉克利特首次提出“艺术模仿自然”,从唯物论的角度将模仿纳入艺术创作体系,为“模仿说”在艺术中的长足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模仿已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范畴,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雄霸西方文艺理论界两千余年。在柏拉图时代,技术与艺术并未严格区分,柏拉图对于模仿的理解虽然涉及艺术层面,但究其根本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观照模仿,更倾向于技术层面。柏拉图认为模仿并不具有真理性,并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它和“真实体隔得很远,它在表面上像能制造一切事物,是因为它只取每件事物的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还只是一个影像”[23]72,所以“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23]76。显然,对于柏拉图来讲,模仿与他的理想世界相隔甚远,所以他要否定模仿以及“模仿诗”。即便如此,模仿作为一种现象已经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并且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文学创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柏拉图关于模仿的界说不仅引发西方几千年来有关模仿的论争,也为模仿在文学叙事策略中所具有的话语霸权属性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也是柏拉图的第一位“反叛者”,提出与柏拉图截然对立的模仿观,大加赞扬模仿。作为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诗学》即是以模仿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论述的。《诗学》开宗明义:“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4]3亚里士多德对模仿的认知作出全新的诠释:一方面,他从现实主义的高度强调艺术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而不仅仅是僵化了的自然;另一方面,他认为模仿并不是机械地复制,而是通过个别来表现一般,通过特殊来表现普遍,揭示文学的内在本质与规律。所以模仿构成亚里士多德文学理论的基础,在其文艺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之后的若干世纪中,西方关于模仿的论述或认同,或反对,大抵上是沿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向前推进的。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模仿一词,但在古希腊时期,模仿在文学叙事中并未形成话语霸权。稍后的古罗马时期,文艺理论家贺拉斯与普罗提诺在不同程度上也强调了文学与模仿的关系,而真正将模仿发扬光大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达·芬奇针对绘画提出了“镜子说”,认为“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24]。镜子说就其本质而言是模仿说的变种,虽然达·芬奇是针对绘画而提出的,但同样适用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类型。达·芬奇强调画家应以“自然为师”“师法自然”,但不能仅限于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应在此基础上注入作家的理性,用艺术去反映现实的普遍规律。从他的论述来看,模仿是强调真吗?显然并非完全如此。他旨在强调在真的基础上饱含情,表达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由自然所引发,并通过模仿体现出来,最终注入艺术创作之中。包括18世纪的狄德罗,他强调“自然有时枯燥,艺术却永远不能枯燥;模仿自然并不够,应该模仿美的自然”[25]。这种将模仿由强调本真上升到审美,标志着模仿发展到另一个高度,成为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模仿的话语霸权属性逐步形成,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定型。
19世纪是现实主义高度发展的时期,世界文坛上先后涌现出像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等一系列文学大师,他们旨在以文学创作去揭露现实的黑暗与社会的腐败,真实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的蝇营狗苟,以及平民阶层的悲惨遭遇。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即是以模仿为中介,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真实描绘反映社会的黑暗。别林斯基强调“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它的任务不是矫正生活,也不是修饰生活,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活表现出来”[26],并且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高、更具表现力,即艺术应该上升到对社会进行批判的维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与别林斯基的观点相左,他认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类似印画和原画,“印画不能比原画好,它在艺术方面要比原画低劣得多;同样,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27]。车尔尼雪夫斯基意在强调再现与模仿的差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艺术创作终究要以现实为蓝本,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潜在的模仿。也正是在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28];列宁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29]。可以说,模仿对于文学的介入已远远超越其自身的意义,达到表现世界、解释世界的高度,在文学叙事中所具有的话语霸权地位是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
上述论断绝非危言耸听,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浪漫主义即使标榜以作者的主观意愿从事文学创作,但作者的主观意愿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则往往与客观现实相关。被誉为“桂冠诗人”的华兹华斯从浪漫主义视角出发,颠覆了传统模仿说的理论体系,认为诗的本质在于“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30],但情感流露的根据何在?显然,它并不在诗人的主观意识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华兹华斯笔下的田间地头与山乡湖畔。自然成为华兹华斯创作中的一个高频词汇,他正是以此为根据对资本主义异化文明展开批判。可见,颠覆并不等于抛弃,而是一种扬弃,他保留了模仿的合理性内核,即文学创作应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并以此为武器对社会的丑陋与腐朽展开批判。同样,从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作品中也能够窥见模仿的身影。他曾说:“戏剧应该是以一面聚集物象的镜子,非但不减弱原来的光线和色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聚集起来,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31]可见,雨果认为文学通过对物象的集中聚集,“不仅可以准确地表现现实,并且强化它的色彩,增加它的生动性,给人以‘真实’的感受”[32]。在现实创作中雨果也践行这一理念,《巴黎圣母院》通过对道貌岸然、蛇蝎心肠的克罗德,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埃斯梅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等人物的塑造,揭露华美外衣掩盖下宗教的虚伪与肮脏,以及底层劳动人民的友爱与善良;《悲惨的世界》更是融入法国的历史、革命、战争、道德、宗教、法律等,揭示人类在与邪恶的不懈斗争中保持着人类本性的纯洁和善良。雨果笔下的巴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对这一时代缩影的展现虽然充斥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对于现实物象的展现毫无疑问是以模仿为中介的。可见,模仿作为文学叙事中的话语霸权,并不是强行植入文学创作之中,而是潜移默化地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并显示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当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随着西方文论的转向,特别是“语言论的转向”,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传统文论的权威,以往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当代社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当然,文论家在建构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传统文论思想。苏珊·朗格强调“原始艺术的动力就是想去模仿一种自然形式”[33],并以一种特殊的符号表现出来,在本质上已然是强调艺术所具有的模仿性,只不过艺术在实现自身的这一过程中添加了新的形式与情感。鲍德里亚的“仿象”理论同样延续了模仿的叙事话语,并由真实上升到超真实的一个高度。可以说,模仿作为西方文学叙事中的一种话语霸权,自古希腊至当代社会一直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形成西方文学叙事传统,从未缺席。
四、“兴”和“模仿”的殊途与相通
中西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性造就了文化的异质性。与中国文学叙事中强调韵味、意境、古雅、圆融不同,西方文学叙事更强调反映、表现、再现、真实等。因此,在文学表达上中西方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便不尽相同,中国往往以兴作为叙事策略,而西方则形成模仿的叙事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立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有着浓郁的亲和感,在对天地万物感知的过程中往往强调玄览、心斋、坐忘,通过“观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方式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国古人这种感知天地万物的方式是基于朴素的天地万物有机整体观之上,强调人对天地万物的感应与感兴,兴即“意味着在感兴活动中生成审美意象和意境,达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14]102。西方受地域条件限制,形成独具特色的海洋文明,为了生存,西方人更加强调冒险精神,强调对天地万物的探索。与中国的“天人合一”“大化流行”观念不同,西方人更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强调以实践方式去揭开天地万物的面纱,还原其本真样貌。显然,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是无法完全感知并掌握自然的,所以西方人便萌生出模仿的观念,以模仿的方式去认识天地万物,求得生存。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类早期的活动均与巫术有密切关系,兴与模仿也是如此。兴是会意字,《说文解字》曰“兴,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虚陵切”[34]373,《九经字样》释“众手同力能兴起也”[34]374,表示“‘同心协力举物起舞以祀神灵’的原始巫舞仪式文化”[14]101-102,寄托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具有愉悦神灵的作用,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模仿的指向性没有兴明确,在巫术活动中主要“指的是巫师所表演的祭祀节目舞蹈、音乐与唱诗”[35],目的或许在于愉悦神灵,但具体情形已不可考。可见,兴与模仿的起源均与巫术活动关联。
此外,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策略,兴与模仿均具有寄情于物的特点,以及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作用。兴作为一种修辞最大的特点就是寄情于物,刘勰曾说“观物兴情,情以物兴”[10]52,中国诗歌咏物必然会起情,以此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模仿同样如此,苏格拉底认为“画家和雕刻家要把人物高兴与忧伤、高尚与下贱、慷慨与鄙吝、谦虚与骄傲、聪慧与愚蠢的‘心境’与‘感情’恰当地表现在他的‘神色与姿势上’,让它就像活的一样”[36]。显然,苏格拉底所强调的不仅仅要模仿得逼真,更主要的是艺术家在作品中所寄寓的情感并表达出来。文学既非感性的创造物,也非理性的创造物,而是二者的融合,前者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感知上,后者更多地表现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中。钱穆曾说:“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草木鸟兽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也。”[37]足见诗通过“比兴”所具有的以物起情的特点,使人熟识“天地间草木鸟兽之名”,以此达到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目的。无独有偶,狄德罗曾说过:“既然因果关系很显然地摆在我们面前,……模仿得愈完善,愈能符合各种原因,我们就会愈觉得满意。”[38]狄德罗所谓的“符合各种原因”就是强调模仿的真实性,达到了真,即意味着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与解释。
可见,就哲学理论基础而言,兴与模仿的异质性显而易见,但就其在寄寓情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等方面,二者又具共通性。无论是兴也好,模仿也罢,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其自身的意义及内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所以在比较二者的异质性及共通性时,应秉持辩证的观点,避免发生误读。
五、结语
兴与模仿分别作为中西方文学的叙事策略和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虽然各自的发展路径有别,但亦有众多相通之处。就其作为文学叙事策略而言,二者在寄寓情感、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方面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西方文学叙事中,二者均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成为文学叙事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当然,在认识二者共通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一为“忘象”,一为“具象”;一强调“心物相交”,一强调“主客二分”。兴与模仿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是文学叙事所不能忽视的,对如此重要的课题进行比较研究,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关键是我们能够在不同语境下关照二者,同中求异,异中趋同,以期寻求二者在中西方文论发展过程中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