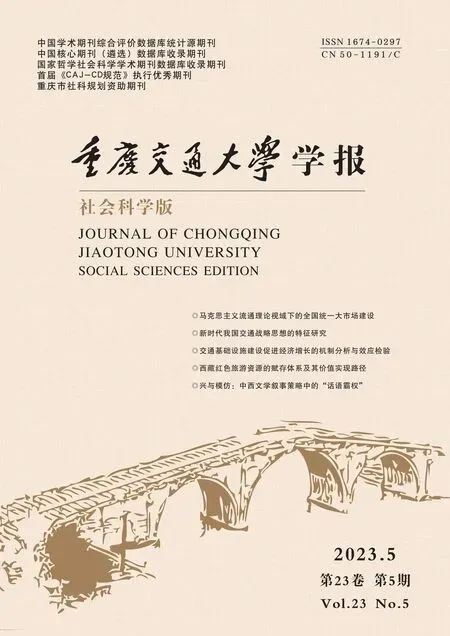伊恩·麦克尤恩《坚果壳》中的空间博弈
申 圆, 张海霞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022)
一、引言
英国当代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坚果壳》(Nutshell,2016)以21世纪的伦敦为背景,以一个胎儿叙述者的视角讲述母亲和叔叔如何密谋杀害父亲、侵占父亲祖宅,以及自己如何为父复仇的故事,堪称当代版的《哈姆雷特》。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小说的评论集中于叙事研究和伦理研究。穆勒(Wolfgang Müller)援用认知科学中的感觉—运动概念,探讨《坚果壳》的第一人称叙事特征[1];怀特(Robert White)从互文叙事的维度,指出《坚果壳》是对《哈姆雷特》“激进的、创造性的改写”[2];陈大为认为《坚果壳》在主题、形式和结局中都体现出对《哈姆莱特》的戏仿[3];尚必武从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心理两个层面考察《坚果壳》中的非自然叙事[4],并分析“坚果壳”的伦理隐喻及其和人物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悲剧的关系[5];曲涛和张亚楠从不可能世界、叙事话语、人性伦理三个层面,揭示非自然叙事形式背后隐匿的、书写人性阴暗面的伦理内涵[6]。
除互文叙事和非自然叙事外,《坚果壳》还具有明显的空间叙事特征。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下生成的意识流使时间碎片化,胎儿叙述者置身母腹,却能时刻感知、思考外界发生的事,叙事情境的切换导致线性时序的中断。同时,叙述者思想的跳脱造成视域的变换,小说中诸如坚果壳、房间、监狱、欧洲、世界等空间意向构筑起叙事上微观和宏观并存的空间结构。叙述者的视域由母腹、祖宅等核心移至欧洲和国际世界等外围空间,或由外围空间返回核心空间,借此突出人物的空间位移、空间记忆和空间想象。小说的标题取自《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上帝啊!倘不是因为我总做噩梦,即使把我关在一个坚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的。”[7]坚果壳作为统摄全文的空间意象,指向麦克尤恩对空间的一种关切。福柯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8]空间是流动的、不断生成和变幻的,空间归属的不确定性导致《坚果壳》中人物心理稳定性的断续。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成为人物意欲争夺、占有、拓展的焦点。人物对空间的诉求以及他们对失去空间的恐惧贯穿文本始终,他们因空间而展开的较量构成空间博弈。麦克尤恩通过对空间博弈的书写推动叙事进程,借此表达他对21世纪时代语境中人类命运的关切。
“博弈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参与者依据各自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的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9]2在空间博弈中,参与者依据不同的信息谋划空间归属,空间象征着存在,空间成为博弈的目的。小说中,空间博弈的形式是多元的,既有父母因争占空间展开的“二人博弈” (two-person games)[10]159,也有胎儿叙述者、父亲、母亲、叔叔等“多人博弈”(n-person games)[10]207,还有人在“自我”和“他者”二元对立思想支配下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对峙,即“扩展型博弈”(extensive form games)[11]。这些空间博弈的形式强调逻辑策略所能带来的利益,淡化情感的重要性,突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隔阂导致的严峻后果,揭露形形色色的空间策略背后的荒诞。
二、空间博弈的建构:空间想象与博弈策略
《坚果壳》中空间博弈的建构涉及情感阵营划分。一方面,母亲和叔叔以背叛者与密谋者的身份被胎儿叙述者设想成博弈的对象,置身母腹的空间局限及与父亲联合的愿望,使其勾画出身体的位移和父亲魅影的复现,但这种空间想象的虚幻性反衬出胎儿叙述者势单力薄的现实;另一方面,母亲利用父亲对她的情感依附,与叔叔合谋侵占父亲祖宅。父亲对打破情感均衡的恐惧使母亲的博弈策略奏效,从而加剧情感阵营的分化。
空间博弈的建构首先体现在胎儿叙述者通过想象重塑自己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感受身体的实存,在思想上对可能的空间侵占形成防御,改写敌强我弱的局面。他设想自己28年后体格健硕、动作敏捷,叔叔克劳德相形见绌。他能够揪住叔叔的脖子,把他扔进汉密尔顿街积满落叶的水沟。在故事层,胎儿叙述者仍处于“前身体”阶段,他虽具有敏锐的知觉意识和思维能力,但并不具备正常的行为能力,身体的不在场意味着“前身体”和空间之间尚未形成建设性的关系,母腹发挥空间政治学的效用,规定胎儿受制的姿势,使他无法进行空间拓殖。而在胎儿叙述者的想象中,身体是完整的,可自由腾挪,可生成能量,从而使其他人的活动发生空间位移,改变其命运轨迹。父亲约翰原本与母亲同住在汉密尔顿街建于乔治王朝时期的家族宅邸中,但因母亲孕期坚持要有自己的空间,父亲在肖迪奇区租了三间房子,并为此负债。由于叔叔和母亲的私情,叔叔与母亲同住在父亲的宅邸,父亲被驱逐出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胎儿叙述者设想成为青年的自己能够在与叔叔的博弈中掌控局势,帮父亲夺回被侵占的家族宅邸,每个人各得其“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空间的重构中得以体现。这种想象实现的基础是胎儿叙述者变为成人后的身体的实存。由于身体的在场,时间、空间、能量之间产生互动,空间开始具有生产性的意义:“能量的支出只要在世界上造成了某些变化,无论多么微小,都可以被视作‘生产的’。”[12]179小说中,想象的身体摆脱孱弱的窘境,能量的支出被用于生产新的主体间性。麦克尤恩使用“安置”一词来描述胎儿叙述者在想象中对父亲的空间安排:此时,身体—主体业已形成,“我”不再是单纯的先验的主体,对世界不仅有认识能力,还有改造的能力;“安置”折射出身体—主体中蕴藏的能量,这种能量使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合,使能量投射到想要投射的对象身上,形成身体的权力场域,重新安排父亲的命运。身体的自由呈现使“我”克服被囿于母腹的空间焦虑,“我”开始拥有博弈的资本,“我”的空间扩张,而叔叔的空间萎缩,空间占有度的对比凸显“我”对空间博弈结果的期待。
另外,胎儿叙述者通过类似“魅影复现”的幻想,试图改变叔叔和母亲的精神空间,令他们为弑兄、弑夫的罪行感到不安,解构他们的心理图示,使他们在与父亲的影身人物的博弈中溃不成军。“我”幻想父亲在被叔叔和母亲谋害后,脸上浮现恐怖的表情,仍穿着死去时的衣服,站在楼梯下,他用干瘦的手掐住叔叔的脖子,直至叔叔窒息。随后,他将母亲的脸拉近身旁,用腐烂的嘴唇吻母亲。母亲被恐惧和厌恶击垮。之后,父亲放开她,踏上归程。在博弈中,“参与者”“信息”“策略”左右着“行动”,牵涉“结局”。作为重要的博弈方,父亲的影身人物已识破叔叔和母亲的阴谋,掌握博弈对手的类型和行动的知识,将与死亡相关的“地下世界”的信息传递给处于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人,而关于“地下世界”的信息并非博弈双方所享有的“共同知识”,叔叔和母亲对父亲影身人物的策略没有准确的信息,双方构成“不完全信息博弈”,叔叔和母亲突然被抛到一个虚实交织的空间,恐惧感油然而生。此外,胎儿叙述者利用听觉打探外部世界,尤其留意母亲和叔叔为与父亲争夺空间的对话。对话反映的情势左右着胎儿叙述者的命运,决定着他未来的空间图示。
母亲和叔叔的密谋围绕如何占取父亲的祖宅而展开,这种空间博弈的建构牵涉“承诺”与“威胁”。母亲认为分居是为了给彼此“成长的时间和空间”[13]11,而父亲认为给予妻子所需要的空间是明智的,自己对既有空间的放弃意味着对妻子的尊重和爱,让步构成一种可信的承诺。然而,父亲没有觉得妊娠晚期的母亲坚持让他住在别处有悖常理,因其不愿打破婚姻呈现的稳固表象。稳固指向博弈中的均衡,是“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合”[9]23,打破均衡可能会导致危机,所以父亲臣服于“现状的暴政”,维持现状已成为他的惯习。比起空间的让与,对母亲意愿的违背更令父亲无所适从,那意味着更深的隔阂。母亲是这场空间博弈规则的制定者,拥有掌握父亲情感归属的特权,这种特权通过母亲决绝的态度得以表达,其中暗含着一种可信的威胁:倘若丈夫未顺从自己的心意,他将失去与自己对话的权利。“她觉得抛弃和移交应该由她来定夺。”[13]67母亲对空间博弈的建构即是对夫妻之爱的解构。父亲答应让与的空间不是普通的处所,而是他儿时的住所,“大多数人绝不会允许伴侣将自己从儿时的屋檐下赶走”[13]12。家宅将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人在被抛弃于世界之前,就已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中”[14]。家宅无可替代的庇护性加深人对存在的感受,构成“存在空间”,即“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示体系’,它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且,‘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15]。在母亲和叔叔的密谋中,占有父亲的家宅,使父亲与作为“存在空间”的家宅分离,破坏“存在空间”建构的记忆诗学,割裂父亲的过去与未来,是空间博弈必须迈出的一步。家宅即将易主,不仅使父亲遭受流离失所的际遇,也使胎儿叙述者心生感伤。胎儿叙述者的命运通过家宅和父亲的命运牵连在一起,空间的丧失可能造成的消极心理及代际影响却通过“我”的叙述呈现。母亲和叔叔谋财害命的阴谋是利用空间建构的,二人意欲用空间策略锁定胜局,将利益置于情感之上,“零和博弈”的心态使威胁取代协商。
三、空间博弈的过程:重复博弈中的表演与变数
博弈参与者获取信息不均等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数次反复,构成“重复博弈”,其中每一次博弈构成“阶段博弈”。“每个参与人在每个阶段选择的策略依赖于其他参与人过去的行为。重复博弈让报恩或报仇都成了可能。”[13]188。小说中,母亲与叔叔的密谋包括若干环节:先是令父亲搬离祖宅,然后设计毒死父亲,变卖祖宅,分钱,抛弃孩子。胎儿叙述者以倾听、感受、推断等方式观测“重复博弈”的行进轨迹,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在母腹中做出一系列干扰动作,为父亲复仇。当胎儿叙述者听闻母亲和叔叔占有父亲祖宅之后还要变本加厉地毒杀他,并将“我”“安置”在某个地方,“我”与母亲、叔叔之间的空间博弈不再停留在臆想阶段,而是决意行动起来对抗。“我”关心的已不再是某次“阶段博弈”的暂时损益,而是“重复博弈”的最终结局和影响。因为“安置无非是抛弃的虚假同源词”[13]42:父亲将饮鸩而亡,“我”将被置于死地,“我”和父亲都逃脱不了被母亲丢弃、成为“他者”的命运。整个空间博弈的过程,即是“我”和父亲在空间上与母亲日渐疏离的过程,母亲不在场的空间成为意指空间,象征着分隔和厌弃。“我”与父亲同母亲在空间上的界限建构、生成、扩张的过程,即“阶段博弈”逐步演进的过程。
空间是情感的寓所,情感的变化打破记忆主体对记忆客体原本的印象和认知,与记忆客体相关联的空间因此改变情感的印记,空间所承载的爱意由浓转淡,奠定小说中博弈的“复仇”基调。在首轮空间博弈中,母亲利用父亲对自己的爱得偿所愿,父亲搬离祖宅。在第二轮空间博弈中,父亲带着女诗人艾洛蒂前来祖宅拜访,并提出母亲搬去叔叔在樱草山宽敞而漂亮的房子。艾洛蒂的加入改变父亲在博弈中被动的局面,她即将与父亲共享同一空间,这种在场性象征着空间博弈中关系脚本的改变。特定的空间情境促使博弈中情感矩阵的生成。父亲与艾洛蒂一同步入祖宅的情境指涉人物间的关系转向,创设父亲移情别恋的潜文本,附带表演的氛围。新的女主角隆重登场,原本的女主角即将退场,“主”与“客”身份的重写都在父亲事先编排的关系预演中设定。当“拜访”的情境按父亲的构想真实呈现,母亲憎恶和愤怒的情绪在这一情境刺激下被瞬间强化,从而加速母亲和父亲的情感分野。母亲觉察到,父亲与艾洛蒂谈论诗歌时的契合度已超越“礼仪脚本”这种用于寒暄的公共协调模式,超越“请”“谢谢”“对不起”等通用的话语,变为倾注了特殊情感的诗歌意象。如“猫头鹰”,父亲和艾洛蒂都将其视为对灵性的隐喻,为两人建构新的联合叙事做好铺垫。在“拜访”情境中,艾洛蒂年轻貌美的形象,父亲做出胜利者的姿态,建议母亲搬去叔叔住处的语气和神情,母亲对父亲和艾洛蒂关系的猜度,都参与构建第二轮空间博弈中新的关系图示,表演的戏剧化效果通过情境的营设和人物对情境的即时反应得以实现。
母亲选择用愤怒的脚本表达谴责。由于艾洛蒂的助阵,父亲在第二轮空间博弈中反败为胜,挫伤母亲,但也激起母亲的嫉妒心。空间中的关系事件因嫉妒的怒火被重新阐释:丈夫搬出祖宅,搬去肖迪奇,是为了与艾洛蒂幽会。他腾出屋子,以便弟弟克劳德住进来,就有了充分的理由甩掉自己。母亲对艾洛蒂的敌意投射到父亲身上,她心意已决,“我想要他死,明天就得死”[13]71。母亲联想的发散性使她开启从“体验情感”到“制造情感”的历程,“制造情感”导致非理性的行为模式,加速第三轮空间博弈发生的速度,女主人身份遭到否定之后的惩罚和规训。父亲回祖宅整理东西,叔叔和母亲趁机将含有乙二醇的防冻剂加入奶昔里,父亲驾车回去的途中毒性发作,急救途中不治身亡。母亲和叔叔在警察上门盘问时,声称父亲是自杀的:诗歌创作失败、出版社倒闭、债务缠身、妻子与弟弟同居、受牛皮癣折磨、患抑郁症,身心的重创使父亲服毒自尽。母亲和叔叔为了不露破绽,改换父亲过世时的现场空间,利用车厢制造父亲自杀的假象,导致暗流博弈生成。汽车后座地板上立着的塑料泡沫杯、瓶子旁丢弃的买饮料的收据、显示几万镑透支额的银行账单、一张账单上模仿死者笔记写的“够了”的字迹、掩饰牛皮癣的手套、刊载着对父亲诗集恶意评论的报纸,一系列的物体在空间中陈列,展示死者生前经历的失败片段和决意自杀的证据。车厢象征着支配性的空间、权利的空间、淹没复调的空间、真理被谎言挪用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收据、账单、手套、报纸等都成了“失败”的表征,“失败”和疾病、创伤、沉默、死亡联结,指向能量消耗殆尽的熵化结局,否定失败作为人生必经之事的正常化意义,没有人为失败的“污名化”情形正名。父亲以失败者的身份死亡,暗合母亲和叔叔“败者必亡”的博弈逻辑。
“重复博弈”在最终结局揭晓之前充满变数。尽管第三轮空间博弈以叔叔和母亲在父亲喝的奶昔下毒暂时取胜,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使他们的协作关系面临破裂的危险。叔叔将父亲置于死地而后快,以期能按计划变卖祖宅,母亲听闻父亲死讯后却感到心痛。她开始怀疑自己在这场博弈中的共谋角色,而叔叔认为母亲表现虚伪,说她将父亲留在了伦敦郊外的马路边上,任凭他躺在草丛里,腹中全是毒药。“草丛”这一空间凸显爱的荒芜,强调母亲和叔叔在博弈中利益的一致性,提醒母亲否定共识,使用不合宜的沟通脚本只会颠覆同盟的维系,引起后患。母亲认定自己是这桩罪行中的无辜者,她对叔叔说:“我不会让你卖掉这栋房子,成为有钱人。”[13]122叔叔嘲讽道:“不,不。我们可以一起成为有钱人。或者,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蹲在不同的监狱,穷困落魄。”[13]122母亲的言辞否定了叔叔在博弈行动中作为有价值的参与者的身份,叔叔则用或选项道明合作博弈对双方的益处,以及非合作博弈要付出的自由成本。坐牢的恐惧使母亲妥协,她按叔叔设计的证词排练了三遍,但当总督察和警官上门调查命案时,母亲和叔叔却在回答同一问题时口径不一,说明他们的行为失去“同步敏感性”,即每个行动不能“紧接上一行动平稳进行,对前一行动给予确认并对后续行动发出邀请”[16]。
“同步敏感性”的丧失造成博弈同盟者之间相互指责的脚本生成,妨碍博弈表演原初的观赏性。叔叔试图用“整齐划一”的戏剧化策略维持一场骗局,而母亲在关键时刻却上演违背叔叔意志的“反剧实践”,她在与警方博弈的舞台上打断演出,并对台词提出异议,终结与叔叔互惠互利的叙事。谋杀父亲的事情败露后,母亲和叔叔决定出逃。就在二人等出租车的空当,“我”奋力用指尖划破子宫壁降生,阻止他们的逃跑计划,二人面临身陷囹圄的窘境。在最后的“阶段博弈”中,“我”凭借身体的狂欢所实践的空间革命颠覆原本的博弈节奏,从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掌握所有博弈参与者的命运。小说中,若干场“阶段博弈”的本质是“负和博弈”,即“参与者博弈之后损益总和小于零的博弈”[9]27。“我”、母亲、父亲、叔叔作为博弈参与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没有胜者。他人被定义为实现自我目标的工具,而“负和博弈”中“他人为我所用”的工具主义使空间成为“输”“赢”的象征符号,也使幸福从存在走向虚无。
四、空间博弈的结果与影响:均衡的解构与边界之殇
个人主体间空间博弈的结果是打破均衡,即无法实现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合。对抗思维导致非合作博弈生成,每个博弈参与者都在自己的策略空间计算损益,无法实现家庭中关于责任契约的“共意”,复仇主题贯穿文本始终,人物的记忆、动机、心绪、行为都被非合作博弈的执念裹挟。小说中空间是复仇的媒介,人物利用空间建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使彼此成为“相互疏离的存在”,表现出关系失能的主体间性。对胎儿叙述者而言,复仇并没有带来欣快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时空所寄寓的未来无从把握的恐惧。小说结尾以“一片混沌”终结,空间博弈结局指向的命运浮沉消解了胜负的意义。复仇聚焦对移情与赋权的否定,而复仇这种“零度移情”的行为意味着“你将不会有这些意识:将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预测他人的感情和行为?即你的移情机制处于零度水平……你认为仅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百分之百正确,那些持不同信念的人都被你判为错误的、愚蠢的”[17]。“零度移情”构筑主体间的心理空间壁垒,博弈者无法通过自己与“他者”的关联来更新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在人物对空间的争夺中,复仇的烈焰也灼伤复仇者本身,主体间建设性的关系难以生成带来的失落感对胎儿叙述者“母腹博弈”的成功实施构成反讽。
小说除个体在母腹、祖宅等核心空间博弈外,还涉及不同主体在更宏观的区域性空间和国际世界的博弈。首先, 城市空间的分化,即支配性空间和城市边缘主体所属空间的生成,导致城市内部空间博弈发生。权力机构的权威话语伸展着“再现空间”的逻辑,这种空间逻辑“与生产关系和那些关系置于其中的‘秩序’紧密相关,因而与知识、符号、编码和‘前面’的关系密切关联”[12]33。权力缔造所谓的真理,压抑来自边缘的声音,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促成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空间总是并且只能是由隔离、在场和缺场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18]小说中,具有社会阶层分野的主体间的隔离、“再现空间”所强调的权力的在场、具有革命力量的纠正角色的缺场,都使城市秩序岌岌可危。“城市里遍布用来盛放炸弹的木桶,集市中出现被当作炸药的孩子。据说在奥地利,七十一名移民被遗弃在路边一辆上了锁的货车中,任凭他们惊慌、窒息,生命枯萎。”[13]83被当作炸药的孩子以生命为“沉没成本”,上演生死博弈,生命作为空间博弈的投入再也无法寻回。被遗弃的移民被视若城市的寄居者,具有“流浪汉”身份,而“流浪汉必须被隔离开,因为他们受损的身份会损害环境,甚至这种影响会延伸到作为环境一部分的‘正常’人。因而以社会价值为依据的空间层级分化对宿主人口来说是极其重要的”[19]。被遗弃的移民在场与“再现空间”所构建的井然有序的城市表象相矛盾,城市“流浪汉”的污名化显示被规训者难有容身之地的境遇。城市边缘主体命运的不可控性影射渗透着生死空间博弈的残酷。
其次,小说中胎儿叙事者听闻的国家、地区、种族间的冲突已超出个人主体间的空间博弈范畴,指向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的“集体自我”空间扩大的欲望。“我”在收听广播时,曾听一位国际关系专家分析糟糕的世界局势:局部战争愈演愈烈,新式武器层出不穷;欧洲面临生存危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抬头;大量移民遭受磨难[13]24。空间成为“自我增益”的工具,领土扩张者对空间的侵占反映其难以靥足的权力欲。“对于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由宽敞的感受带来的满足不过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会随着获得空间的增大而消退。”[20]宽敞感的幻灭揭示空间侵占者作为行为自决主体对共生型关系格局的否定,影射其零和博弈思维,即“博弈双方损益总和总是相加为零;倘若一方占优,则另一方必定处于劣势”[21]。面对空间所有权的争夺,零和博弈背后非此即彼的逻辑抹杀共情空间生成的可能。
最后,全球生态空间的变化反映人与自然的冲突,解构两者和谐共存的状态。小说中,胎儿叙述者论及“慢性暴力”这种“不可见的、进展缓慢的损耗性暴力”[22]。“气候变化、极地冰雪消融、有毒的农业、呈弱酸性的海洋、带尿味的海啸”[13]25,人类对自然日积月累的伤害生成慢性暴力,而这种伤害对人类具有反冲力。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方关联体”[23]在城市语境中被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所解构,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普遍性的灾难,人类凭借慢性暴力与自然展开博弈,但生态环境的恶化透露出事与愿违的结局。小说中,人际、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矛盾借由空间博弈表现出来,而博弈的结局缺少共赢,反映出博弈优势方过度关注自我而造成的边界之殇,以及搏弈劣势方因无力抗衡而面临的存在之危。
五、结语
麦克尤恩以负和博弈的逻辑框架建构人物共在却非共情的空间,有界实体对他者的普遍怀疑导致关系汇流的错位及意义共享的中断。小说中,人物援用、听闻的各种制衡策略源于自我中心意识,倚重工具理性,关注利弊得失。当反乌托邦取代健康的关系联盟,博弈胜利者亦将面对熵化的未来,满盘皆输的结局透露出空间策略意义的虚无。博弈成为游戏的隐喻,家庭共同体成员间本应具有的互相信任的情感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在空间博弈中归零。麦克尤恩的空间博弈书写观照个体命运的同时,观照家庭与文明的危机。空间博弈的建构承载着胎儿叙述者校正家庭伦理关系的渴望,也透露出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空间博弈的过程体现个人利益与共同体精神的对峙,以及这种对峙对主体间性的消极影响;空间博弈的结局为负和博弈,即得不偿失,凸显认知与行动偏差对共赢结局造成的障碍。小说中博弈参与者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他人的有用性,为实现对空间的占有而反复谋划,但共在伦理的缺失使空间滋生区隔的边界。麦克尤恩在《坚果壳》中的空间博弈书写以解构共同体的方式,反衬出他者伦理和责任意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