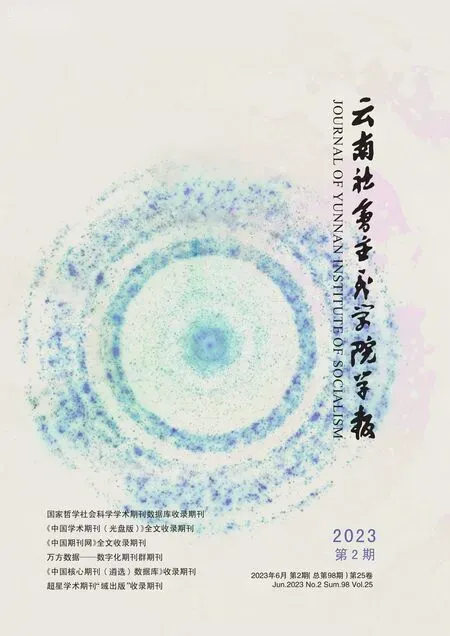从“想象的云南”到“形象的云南”
——论曾昭抡《缅边日记》对云南的“发现”
余梦成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缅边日记》是曾昭抡于1939年3月11日至25日沿滇缅公路旅行并考察云南边境地区的记录。全书采用游记散文的形式,全面而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滇缅公路的沿途情形,并以“他者”的视域考察书写了这一时期云南独特的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和历史文化,以“路”为纽带,将沿线各地的高山大川、地域文化等串联起来,共同构建了战时云南边地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让“想象的云南”变为“形象的云南”,为今天人们“想象云南”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资源,对认识云南乃至是整个西南边疆地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曾昭抡《缅边日记》的关注和研究均有限,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缅边日记》所表现的“边地”(边疆)与“中心” (内地)文化的多元融通,所彰显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如曹静漪的《曾昭抡〈缅边日记〉的云南边地文化书写》、马俊山的《〈缅边日记〉:西南边疆的发现与民族认同》;二是《缅边日记》写作的科学性与美学风格的独特性,以及其中所呈现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意识,如石健的《理性、雅兴共融的云南风土描绘——曾昭抡〈缅边日记〉解读》、陶冶的《〈缅边日记〉读后》;三是通过曾昭抡等人对“西南边地”的科学考察和文学实录,分析他们对“边地中国”的形象建构及其史学价值,如杨绍军和张婷婷的《西南边地形象的想象建构——以罗常培、费孝通、曾昭抡的考察记为中心的讨论》、董晓霞的博士论文《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但有关研究相对忽略了曾昭抡作为一个外来作家对云南本土神秘的自然景观、风俗民情、历史文化的关注与揭示。因此,本文以作家的“云南发现”为基点,对《缅边日记》所构建的“云南形象”进行探讨,以揭示抗战时期云南风景、云南文化的独特价值。
一、滇缅公路:《缅边日记》的写作前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落入日军手中,日军为孤立乃至消灭中国的抗战力量,封锁了中国的沿海口岸以及东部等地的陆路交通干线,大幅削弱了中国与国际的联系。随着武汉、广州等地的陷落,中国海上交通全线断裂,就连大后方的滇越铁路也因越南沦陷而被阻断,国际援华物资如何进入中国成为一个难题。为了维系持久抗战,开辟与打通中国连接国际的后方通道,滇缅公路的修筑被提上了日程。“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责成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一年内修通滇缅公路,打通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从1937年12月至次年8月,云南各族人民组成20万修路大军,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开辟了一条由生命之灵和血肉之躯筑建而成的‘血路’——滇缅公路,为中国沟通国际联盟,运送援华物资,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①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书写筑路者的英雄气概与精神品质,表现他们赤诚的爱国心与家国情,是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文化追求和著作主题。如王锡光在《公路是血路》中颂扬道:“民众力量真伟岸,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百万雄工中外赞……”②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1—212页。,杜运燮在长诗《滇缅公路》中写道:“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普通现实,/试想没有血脉的躯体,没有油管的/机器。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就是他们,冒着饥饿与疟疾的袭击,/(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锹铲,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③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3页。他们以笔墨书写了一段伟大的历史,歌颂那些在筑路过程中默默奉献的每一个人。
1939年3月11日,正值寒假,曾昭抡先生同好友林可仪、冯君远、沈叔成、陈昭炳、蔡竞平等人组成“滇西旅行考察团”,走滇缅公路,从昆明到畹町(途经楚雄、下关、保山、芒市、遮放等地)进行了长达15天的实地考察,并对沿途的山川风物、人文地理、民族风俗、地域文化等做了详细记录,写下了多达8万字的游记散文《缅边日记》,成为后来人们认识云南边境——缅边(滇西)地区的重要文学史料。关于《缅边日记》的写作缘由,曾昭抡也进行了说明:“滇缅公路成功以后,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人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来因为滇缅公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尤其很少踏进。我们平常听见关于那地方的,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实的神奇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感缺少。我这次得着一次不易得的机会,趁着寒假的时候,搭某机关的便车,去那里跑了一趟。”④曾昭抡:《缅边日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页。可见,滇缅公路首先为曾昭抡《缅边日记》的写作提供了一条行走与考察的现实路径,并成为促使他写作的动力之一,而对滇缅地区的神秘向往,对云南神奇故事的关注与想象,则为他此次考察提供了隐性的文化路径。基于对滇缅公路的书写欲望和“发现云南”的文化动因,曾昭抡开启了他的缅边之行,以科学谨严的态度,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整理,一路记述,书写了一段行旅往事,揭开了一个地方的神秘面纱,发现了边地民族的风俗历史,具有独特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二、自然景物、民风民俗、历史文化:《缅边日记》的“云南形象”
在《缅边日记》中,曾昭抡对云南边疆的“发现”与书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自然景物、民风民俗与历史文化。它们既契合外来者对云南的“异域想象”,同时又揭开了云南地域的神秘面纱,为人们“想象云南”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自然景物:于细节的张力中凸显美感
长期以来,云南在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它拥有自己的民俗文化、方言土语、历史气息,同时靠近东南亚各国,其文化系统、历史构成较为多元复杂,“被看作理所当然的边疆”①布小继:《现代云南边疆的旅行书写及其文化意义论析——以丁文江、艾芜、缪崇群、邢公畹、马子华等作家作品为中心》,《学术探索》2020年第3期,第87页。,甚至是“异域”,因而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与神奇因子,成为20世纪以来众多作家探索和书写的一个重点。现代作家以云南文化为中心的文学书写数量多且类型丰富,如艾芜的《南行记》以“淡黄的斜阳,峰峦围绕的平原,寂寞的微笑”②艾芜:《南行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页。,塑造了小城昆明的魅力与孤寂;马子华的《滇南散记》以“白茫茫的岚雾平铺在山谷中间,千年的藤葛纠缠在老树的腰间,奇异的鸟影飞跃在树梢和岩际”③马子华:《滇南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0页。,展现了普洱一带山林雾气缭绕的神秘风景;邢公畹的《红河之月》以“疏疏落落的星星,朦胧的青灰色的连峰,剪影一样贴在蔚蓝的天幕底下”④邢公畹:《红河之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7页。,表现了红河之夜的“静”与红河之月的“亮”;罗莘田(罗常培)的《沧洱之间》以“苍山一共十九峰,以清碧溪,层峦叠嶂中有崔气象。洱海凭栏远眺,沧波百里,风气涛涌,奔腾澎湃”⑤罗常培:《沧洱之间》,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05—107页。,描绘了苍山的奇与洱海的势,展现了云南边疆地区雄奇壮丽的景象;冯至的《阳光融成的大海》书写了抗战时期昆明的自然景观,以“可爱的小溪,热闹的雨季,萧疏的深秋,平静的夜”⑥冯至:《阳光融成的大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54页。,表现了云南秀丽的山乡景色;李拂一的《十二版纳志》以“广大无垠的森林”⑦李拂一:《十二版纳志》,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第61页。,展现了西双版纳地区神秘辽阔的自然景致。他们对云南的自然景物都作出了深刻的体验和书写,风格各异且多姿多彩,构成了一幅幅色彩艳丽的“云南风景画”。
相较于上述作品,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比较独特,他写云南风景,不在于描摹高山大川、江河奔腾,而是于细节处记录并刻画出云南最真实的自然风貌,别有一番风物表现和审美情趣。即使面对那些风景名胜和千年古刹,他的目光也总是聚焦于细节的深度描写,营造出风景的画面感,让风景“声音化”“音乐化”,以此表现云南独特的景物和自然。如周良沛所称赞的:“一般的游记,总是要费心于大山名川、古刹幽寺的描绘。可他写名胜,又另有一副笔墨。如写大理,‘点苍山的脚山(foot-hills),那山大部分是由花岗石构成,在别处很是少见。两边的山上多长得有树,有的地方很密。洱河的水是异常地清,静处作极美德碧绿色。因为水流得很急,水中又散布着许多大小不等得石块,水从石上冒过,到处激起瀑流(rapids),深绿得水上罩着许多白色的浪花,再配上两旁有树的山和弯多坡陡弯急得险路,真是一幅笔墨无法形容的美景’,有另一番的审美情趣。”⑧曾昭抡:《缅边日记》,第4页。曾昭抡的《缅边日记》将视点下沉至容易被忽略的石块、水流上,以细节的诗意展示这一地域独特的风景。
当然,在《缅边日记》中,曾昭抡除了向读者展示云南独特的山山水水和自然风光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将云南的风景实体化,让“想象的云南”变成“形象的云南”,让可感可知、可触可听的“云南形象”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丰富读者“云南想象”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纠偏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边疆文化的“愚昧”“落后”等刻板认知,为边地“正名”。如在“芒市风景线”中,他这样说道:“芒市,在没有来这里以前,我个人心目中的想象,以为芒市一定是一处不知怎样荒凉的地方,或者甚至像沙漠似的。可是来到这里,立刻就发现了我自己的愚笨。芒市不但是不荒凉,而且是一路来最美镇市。美丽、清洁、安静一这是我拿来描写芒市的形容词。整个的芒市,仿佛就是所天然的大公园。路很宽,房屋不多,店铺更少。到处所见都只是自然界的美景……”①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9页。,这样的景物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中心” (内陆)地区的人们对“边地”(边疆)地区“落后”“封闭”等地域文化、民族形象、城市面貌的曲解和想象,进而破除那些长期处于城市文化中心的人们对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愚昧”“野蛮”“鲁莽”等“边民”形象的想象和误解,对推动构建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观和建设大一统的国家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民风民俗:于独特体验中表现真实
在《缅边日记》中,曾昭抡记述了三个少数民族—— “摆夷”(今傣族)、“崩龙”(今德昂族)和“山头”(今景颇族)的民风民俗。对这些边疆民族,他的视点更多地聚焦在这些民族的服装和风俗上。尽管过去也有一些书籍和笔记记录了这些民族的服装文化、风俗人情,但由于这些书本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记述往往喜欢炫耀神奇、制造神秘,而牺牲了部分的真实性。对此,曾昭抡以科学谨严的态度对这些地方的民俗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和搜集,整理了几个民族独特的民风民俗,对“他者”认知云南独特而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中“山头”(景颇族)是最富有诗意的民族,对于这一名字的由来,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喜欢住在山上,另一方面则是象征着野性,这种“野性”可以从他们的装束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山头”(景颇族)男子把嘴唇染得血红,成年男子还会在头上扎着红布,背上背着一把刀或是一支枪,当路边有车辆通过时,他们会握拳挥刀,大喊大叫,以表示仇恨。当然,这并不是说“山头”(景颇族)人就是“坏人”,在修建滇缅公路的时候,他们也在参加做工,帮助修公路。他们带刀,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生存和饱腹。至于他们的装束,则是这个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此外,“山头”(景颇族)男子还有一种民族习俗,就是文身(Tattoo)的习俗,他们身上多雕刻花纹是深蓝色,大半刻成龙的形状。而曾昭抡书写这一民族独特的服饰装束、民风民俗,其目的除了说明这一民族的独特性与民族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提出关于那一时期的边疆民族治理问题,他认为:“边疆可能有的民族问题实在并不难解决,只要恩威并施,同时把交通赶快积极地建设起来,一切就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了。”②曾昭抡:《缅边日记》,第112—116页。
当然,他更多关注的还是“摆夷”(傣族)这一族群的民风民俗。因为“摆夷(傣族)人最是驯良,并且最和汉人接近。芒市街上,满街都是他们的踪迹”③曾昭抡:《缅边日记》,第85页。,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并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人情。现在的人们已经纠正了以前“滇边的边区是‘夷人’的地方,瘴气很盛行,不适宜汉人生活。他们甚至相信,来到这地方的汉人,要不赶快离去,终究非死在这里不可”④曾昭抡:《缅边日记》,第86页。的错误观念,而且许多汉人来移居于此,很大程度上已经同化了摆夷(傣族)的风俗。就《缅边日记》中所记载,那时摆夷(傣族)人和汉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妇女的服装不同、社交比较自由、只礼佛而不敬祖宗”⑤曾昭抡:《缅边日记》,第117页。三点。比如在服饰上,摆夷(傣族)妇女的服装大致上可以分作三类:“女孩、少女和妇人的服装。十二三岁以下的尚未成年的女孩上身着短袖,下身则穿着裤子,这种装饰,表示自己尚未成年,男子不能随意同她们开玩笑。成年的少女,则上身着短袖,下身穿着裙子,表示她可以充分享受社交自由、恋爱自由的幸福。而已嫁的妇人,所穿衣服和少女完全一样,不过她们的头发总是打着辫子挽作髻状,并用一条黑布层层缠绕起来,而这黑布,则是作为忠贞的象征”①曾昭抡:《缅边日记》,第121—123页。。可见,摆夷(傣族)的女性服装具有特殊的伦理意义。总之,无论是“崩龙”(德昂族)、“山头”(景颇族)、“摆夷”(傣族),还是其他边地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人情,对此我们应当持以虔诚的态度,尊重并“发现”这一独特的风俗景观。
(三)历史文化:云南的土司书写
“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在统一的领土范围之内,积累历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经验后所形成的对南方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处进行特殊治理的一种制度。”②张浩浩、王振刚:《民国期刊所见学人对西南土司问题的探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75页。云南由于地处西南边区,毗邻越、缅、老等东南亚国家,民族多样复杂,土司制度存续时间久远,“如果从元代算起,云南的土司制度存续了600余年。即使是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土官③土官是土司制度地区政权机构的土职官员的统称,是中央管控与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与内地经制有异的特殊地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呈现。云南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自明代起设置土官,据《明史》记载:“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土官的任职主要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主要由汉人担任,“世袭土官”主要由地方土酋担任。起计,土司制度在云南也存在了570余年。”④李正亭、孔令琼:《民国时期云南土司衍变与国家融入》,《民族论坛》2019年第1期,第9页。因此,云南土司制度成为历代学人和“边疆考察者”们的重点书写对象。在曾昭抡的《缅边日记》中,出现了不少有关云南土司制度的记录性文字,从中可见云南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具有积极意义。
在滇西潞西县(今芒市)境内,一共设有两位土司,一位在芒市,称为“潞西芒市安抚使司”,一位在遮放,称“芒遮板,遮放宣抚副使司”。滇缅公路尚未开通以前,滇边的土司,在当地人的心中,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土司出门路过的地方,夷民们全都要排队跪地迎接,而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滇缅公路开通后,“芒市、遮放的土司即废除了这一繁琐礼节,滇边土司与当地平民间的阶层逐渐模糊,统治阶级与平民间此前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也逐渐被填平”⑤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4页。。另外,此前提起土司制度,在不了解这一地域文化的人眼里,土司不免被打上“土头土脑”的形象,但实际上,通过曾昭抡先生的考察与实地接触发现,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土司形象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土文化”,甚至比内地更加接近现代文明,他们在滇缅边区所看见的土司,“不但不土,而且穿西装、住洋房、坐汽车、打网球,比我们一般的大学生还要摩登些”。⑥曾昭抡:《缅边日记》,第82页。从这些,均可见云南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现代转型。近代以来,由于“英法等西方列国的步步紧逼使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云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国防前沿,云南土司制度存续的地区恰好处于最前沿,因而被赋予特殊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国家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⑦李正亭、孔令琼:《民国时期云南土司衍变与国家融入》,《民族论坛》2019年第1期,第9页。。据曾昭抡先生的考察及其同当地边区各土司的谈话,抗战期间,土司统辖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爱国心,对于抗战的认识,绝对不在汉族人士之下”⑧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5页。,他们能组织本土居民防御边疆地区,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缅边日记》“发现云南”的意义
曾昭抡的《缅边日记》以缅边公路为纽带和路径,对滇西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发现”与“认识”云南乃至整个西南边疆地区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路”的纠偏:中缅交通
过去,中国和缅甸的交通,向来是以北路为主。先由昆明往西,路线略微偏西北,经过安宁、禄丰、楚雄、镇南、祥云、凤仪等县,到达下关镇,而后从下关往北,有一条路,经过大理、邓川、洱源、鹤庆等县,直达丽江,这是滇北的交通干线。往缅甸去的路,并不经过大理,而是从下关起,大体上采取西南方向,向保山去。到保山后,折向西去,到腾冲。从腾冲又改向西南方向行走,经过盈江,出中国境内,到达缅甸境内的八幕府(今八莫地区)。这是历来人们对中缅交通要道的认识,以至于现在许多地图和书籍,都把现在的滇缅公路画在上述的北路路线上。但曾昭抡先生实际考察和实地行走后发现,“现在修建的中缅交通——滇缅公路,并不在北线上,所走的不是‘北路’,而是‘中路’。即从保山起,背道而行,向西南方向行,经过龙陵县,再经过芒市、遮放两地,达到中缅交界的畹町,然后越过两个交界的畹町河,进入缅甸境内,再行193.3公里,即可达到腊戍,和缅甸境内的铁路相接了”①曾昭抡:《缅边日记》,第5页。。曾昭抡先生的实地考察,对滇缅公路进行了路线纠偏,为后来人们认识与行走滇缅公路,提供了新的真实路径。
(二)建构国家:边疆地区的问题发现及治理措施
边疆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国家历来都非常重视边疆治理。曾昭抡的《缅边日记》,对边疆地区部分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观察和记录,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1.滇西的烟祸问题②据相关文献记载,鸦片早在明清时期即由缅甸、越南等诸东南亚国家传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最初主要是用于治疗疾病。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侵略者借鸦片以蚕食中国民众抵抗力的残酷手段,导致鸦片大量涌入与栽种,造成了云南的烟毒泛滥,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滇西地区(如西双版纳、保山、德宏等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以及古商道“蜀身毒道”的存在,便成了西方侵略者的首选目标,导致滇西地区的烟祸滋生。为了解决云南地区的烟祸问题,1916年,云南省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禁种条例,申明:“如地方官查获有烟,则种烟人民予以枪毙,烟地充公,该管团保撤职究办;如省道复查发现有烟者,加惩地方官,予以撤任停委处分;如经会勘发现烟苗,则道尹撤任,地方官予以枪毙;并规定军队补助查铲烟苗和补助行政官办理困难事件。”20世纪20年代,为了从源头上治理烟毒泛滥的问题,云南政府还实施“寓禁于征”的政策和颁布“烟亩罚金”制度,并在昆明成立“禁烟局”,试图通过政府的强制执行以查禁地方烟毒。1936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三年禁毒、六年禁烟”的通令,云南地方积极响应,制定颁布了《云南全省实行禁运鸦片章程》,禁止百姓私运鸦片,并派出大量稽查四处调查,如若发现民间私存鸦片,一律没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告》,而后云南省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禁绝鸦片实施办法》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指示》,并成立“禁毒委员会”,组织民众在全社会开展反鸦片烟毒的斗争运动,云南地区的烟祸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在芒市时,曾昭抡等人就看见当地人在夜晚烧山,“他们大约是相信土地烧完后即可转肥,可以接着开垦,于是当地农民不断地进行着烧山活动,树烧完后烧草,如此反复,直到可以开辟成土地,种植粮食。但烧完后的山,却是千疮百孔,一块块土地被烧焦,仿佛癞子一样,这样烧山毁坏森林,实在是可以取缔的事情。而且从保山以西开始,他们烧山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能种鸦片”③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0—71页。,于是造成了滇西地区鸦片泛滥,烟祸严重。虽然是时云南的禁烟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滇东和滇南地区已经完全没有烟苗的痕迹。但在滇西地区,仍有些地方滞留着烟苗,尤其是“由保山县城西去,坝子上的肥田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种着鸦片。我们走过的时候正值罂粟花开,一望到处都是盛开着白花或者淡红色的鸦片田。再往西去,经过龙陵、芒市、遮放,直到畹町,沿途看见山上的斜坡田许多是种着鸦片,而且往往是最肥沃的田。……至于吸鸦片的习惯则更是普通,据我们观察,由腾冲、保山一带雇来芒市、遮放的修路工人,许多都抽大烟。街上许多商人也抽烟”④曾昭抡:《缅边日记》,第136页。。这些是基于对滇西地区边疆治理问题的重要发现,而曾昭抡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基于他相信国家、政府的治烟行动的力度,云南省政府也正在制定方针并继续积极推行,相信烟祸在短时间内就会变成“明日黄花”,而他特地把它写下来,也是为了让人民早日觉悟,帮助政府把烟彻底禁绝。
2.滇缅公路的利用问题。“路”是边疆治理的纽带,路的开辟是笼络与整合边疆,进而治理边疆的有效路径。然而,就滇缅公路而言,抗战时期,由于相对混乱的管理体制、高昂的运输费用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导致滇缅公路的运输并不通畅,除了军事物资、医药物资等战略物资的运输以外,其他物资的运输并不多,利用率不高。尤其是下关以西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使用,就连遮放如此重要的边疆地区,邮政也不通,使得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极不方便,因而他希望将来西南公路局把这段路整理好了以后,会对这一点加以纠正。另外就是滇缅公路的西段,在雨季时期山上土质容易塌陷,造成了部分运输停顿,造成经济损失,于是他提出“合理的办法就是把路彻底修好,让它成为不怕天气变化的路”①曾昭抡:《缅边日记》,第139页。。
3.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我国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的关键问题之一,解决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②张娇、谢清松、金炳镐:《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5页。而边疆民族问题则是重中之重,它直接关系到我国边疆稳固、国土安全。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华民国’的组织中,是允许而且切愿,在中国居住的各族同胞,不问其种族如何,共同努力,肩起国家的责任来,并没有丝毫的歧视观念”③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5页。。而且,少数民族的爱国心并不比汉族弱,因而,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曾昭抡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在于,我们站在“汉人的立场来说,要怎样可以和边区内的各少数民族发生更密切的感情,以取得更彻底的合作”④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5页。。另外,他还思考了国家如何消除各民族间的摩擦问题,进一步提出:“为着免去种族间的摩擦起间,政府当局应该毅然地下一次决心,把夷、苗等含有鄙视性的民族名称一律废除,改用他们自己所定名称的译音。培养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同时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似乎是唯一彻底的办法,可以化除过去各种民族间或有的猜疑和摩擦。”⑤曾昭抡:《缅边日记》,第75—76页。或许一律废除民族名称的问题过于绝对,但是他所思考与提出的减少民族摩擦,促进民族交融与发展的策略,对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四、结语
曾昭抡先生以其严谨的科考精神和实践精神,在西南联大时期,对云南滇西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以游记散文的形式写下了《缅边日记》,发现了云南独特的自然风景、民风民俗与历史文化,一定程度上“纠偏”了人们对云南边地乃至是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认识,让“想象的云南”变为“形象的云南”,赋予其真实的文学体验与历史书写;并进一步发现了边疆地区的烟祸问题、公路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对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除此之外,曾昭抡先生在战时还组织参与“西康科学考察(1939)”“大凉山彝区考察(1941)”等西南边疆科学考察活动,出版了《西康日记》 《滇康道上》 《大凉山彝区考察记》等游记散文,这些作品“全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民族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生活、民族风情等多方面情况,是战时自然和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和科学价值”⑥戴美政:《曾昭抡评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