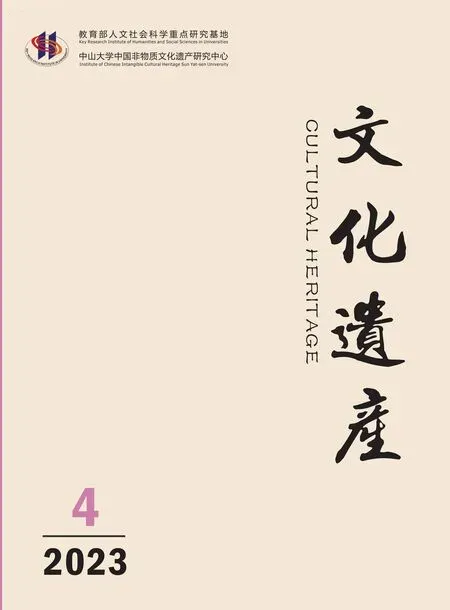董每戡与二十世纪戏剧学*
段金龙
董每戡先生(1907-1980)是我国戏曲研究的名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戏剧作家和戏剧导演。其在戏曲方面有学术著作《中国戏剧简史》《说剧》《五大名剧论》《〈笠翁曲话〉拔萃试论》和话剧创作《C夫人肖像》等存世,是20世纪中国戏剧学术研究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学者。他提出“以演剧为核心的舞台观”,并以此指导其剧史书写,打破了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所确立的“戏曲文学史”的书写范式,构建起自己独有的“剧史体系”,实现了戏剧研究的本土化自觉和学术创新,在戏剧学界独树一帜。因此,无论从其个案本身的深入研究而言,还是从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宏观研究而言,对董每戡进行学术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从王国维到董每戡:20世纪戏剧史书写的观念拓展
戏曲学术研究,除却一手史料的运用之外,观念更可以主导一定时期的学术主流。如王国维所撰述的《宋元戏曲史》即是“戏曲文学史”之代表,而董每戡披荆斩棘,另辟蹊径,转变观念,以“演剧性”为统摄前提撰述了从艺术发展出发的“戏剧艺术史”,从而完成了剧学研究从“文学本位”到“剧学本位”的观念转变。
(一)王国维“文学本位”的“戏曲文学史”书写
在20世纪以来中国从事戏曲研究的第一代学人中,无论从学术成就、学术影响,还是代表性上,首推王国维与吴梅。如浦江清所言:“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先生与吴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1)浦江清:《悼吴瞿安先生》,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页。钱基博更是指出:“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评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依俞为民论,吴梅和王国维分别代表了“旧曲学的终结与新曲学的兴起”(3)俞为民:《中国古代戏曲学的分期及其理论形态和美学特征》,《艺术学研究》2009年刊,第429页。,依苗怀明论,“他们代表了两种独具个性的研究范式,为后人提供了可以选择的不同典范”(4)苗怀明:《中国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与现代学人群体的形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然而,尤为可惜的是,由吴梅开创的曲学曲律研究——这一更为戏曲本位的研究却后继乏人,极少有学人去自觉地继承。虽然吴梅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卓有建树的弟子,但他们从研究路径而言却主观回避或放弃了吴梅坚守的曲律本位研究,反而步王国维戏曲研究之后尘,这使得王、吴二人开创的研究范式有了截然不同的走向和命运:吴梅开创的研究范式从自身起步创建即是高潮,自其去世以后逐渐式微,几乎成为绝学;而王国维开创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成为后辈学人遵循的金科玉律,一方面也成为后辈学人不断尝试超越的对象,同时因这一范式所形成的观念致使其成为许多后辈学人学术研究的藩篱,长期囿于其中而无法突破。
如《宋元戏曲史》作为王国维戏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为传统的戏曲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其所确立的研究方法,为开拓新的学术门类提供了范例,尤其是他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确立了元代戏剧的地位,从文学审美的高度评判元代戏剧的价值,这也标志着我国戏曲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王国维所注重的“文学性”对后辈学界的影响,最直接的便是催生出袭王国维治学之观念而补王国维之缺史的学人及接续之作,这其中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和卢前《明清戏曲史》最具代表性。
卢前曾在其《中国戏剧概论·序》中将中国戏剧史比喻成两头的橄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5)卢前:《卢前曲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2页。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所选取的只是这“曲的历程”中的一段,即元代杂剧。其作为一部断代史著,王国维因自身所持文学观念对“曲的历程”的明清两段戏曲研究形成了主观回避,更不用说出于“橄榄”两端的元以前和清以后的戏曲艺术了。
基于此,对明清戏曲做史势在必行,青木正儿正是出于补王国维戏曲研究之缺史的动机著述了《中国近世戏曲史》,他在是书“自序”中记述了一次他与王国维关于元代与明清两代戏曲文学的讨论:针对王国维“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的观点,青木正儿则提出“元曲既灭,明清之曲尚行,则元曲为死剧,而明清之曲为活剧也”(6)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著,蔡毅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因此,为明清戏曲做史依然必要且有价值。而卢前撰写《明清戏曲史》之动机也是如此,他在是书“自序”中说:“海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行世且二十年。余髫年读其书而慕之。欲踵斯作,拾其遗阙,尘氛栗六,未遑从事。庚午,居蜀中,讲授曲史,因采陈编,续为七章。”(7)卢前:《卢前曲学论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
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和卢前的《明清戏曲史》虽然从体例上稍微突破,但研究之观念、方法、路径完全遵循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而这一认知甚至随着“一代之文学”的观念传播成为整个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客观上完全规避了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艺术体质。
(二)董每戡“剧学本位”的“戏剧艺术史”书写
面对学界整体沿袭王国维戏曲研究观念并在其基础上接续书写戏剧史的普遍现象,董每戡在《中国戏剧简史》前言中称:“在王氏和青木两人之后,国人也有不少剧史一类的著作问世,惟都不免作文抄公,人云亦云,确是事实。”(8)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董每戡文集》(上),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而董每戡的这一判断确也指出了戏曲研究尤其是戏曲史书写的症候所在。
董每戡明晰地看到前人研究戏曲的偏颇,在《中国戏剧简史》的“前言”中指出:“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所以他独看重元剧。我以为谈剧史的人,似不应该这样偏,元代剧史在文学上说,确是空前绝后,无可讳言;但在演剧上说,未必为元人所独擅,总不能抹煞前乎元或后乎元各期的成就;而且一种东西的成长,一定有它前面的历程和后边的发展,把事物孤立起来看未免危险!何况我们所谈的是戏剧?”(9)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董每戡文集》(上),第156页。因此,他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戏剧观”,即在兼顾“文学性”和“演剧性”的同时甚至更强调和侧重于“演剧性”,他指出:“戏剧本来就具备着双重性,它既具有文学性,更具有演剧性,不能独夸这一面而抹煞那一面的。评价戏剧应两面兼顾,万一不可能,不得不舍弃一方时,在剧史家与其重视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分,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10)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前言”,《董每戡文集》(上),第156-157页。而这一“戏剧观”则是“把‘戏剧研究’放在‘演出艺术’的平台上进行,超越一般学者看成文学的单一视角。”(11)叶长海:《往事:董每戡先生的来稿》,《愚园脞语》,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第46页。而重视戏剧“演剧性”的场上意识也正是董每戡对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基本判断后的本质反映,陈平原在《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一文中回顾百年中国戏剧研究史时,就认为“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与“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一起“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12)陈平原:《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因此,董每戡以戏剧舞台意识为统摄,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戏剧形态为重点通过《中国戏剧简史》与《说剧》共同构建起“剧史”脉络,同时以李渔、汤显祖等的戏剧理论作为自己“演剧观”的理论佐证与升华,并以元、明、清三代的五大名剧评论为剧论实践,从而构建起自己独有的“剧史体系”的三大理论系统——剧史论系统,剧话论系统,剧作论系统,马必胜对这三大理论系统概貌进行了“纲要式”简介:
一、剧史论
1.主导思想:首先是《中国戏剧简史》所创立的“ 剧史家”之说,其次《中国戏剧发展史》为构建“剧史体系”而提出的剧史著述的二条规则与三点企图。
2.核心理论:以演剧性为第一要素的“本体论”。
3.代表作:《中国戏剧简史》《中国戏剧发展史》遗稿“前言”“明代艺人的演艺”与《说“礼毕”——“文康乐”》。
二、剧话论
1.主导思想:李渔是我国戏剧史上唯一的戏剧艺术理论家,他懂得“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迥异于曲论家们,能论剧本怎么作,甚至能论戏剧怎么演;同时,他又是一位戏剧艺术实践家,对戏剧艺术的实践丰富,懂得舞台,懂得观众,使我们还不能“以人废言”,尤其不能废他的戏剧理论,因为它都由实践中来。
2.核心理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
3.代表作:《说“玉茗论剧”》《〈签翁曲话〉拔萃论释》。
三、剧作论
1.主导思想:“戏剧行为才是剧本思想性的佐证。我们必须从整个剧本中去探索,就整个剧曲有机的组织中去吟味;体会出他的思想意义。”
2.核心理论:“‘就戏论戏’说”。
3.代表作:《琵琶记简说》《五大名剧论》(13)马必胜:《南戏乡亲 董每戡传》,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363-365页。
董每戡所构建的这一庞大而又相对完备的“剧史体系”,无论从“史”的角度,还是从文本的角度,都较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无论从观念而言,还是从方法路径而言,亦较前人有所重大突破,完成了自己“剧学本位”的“戏剧艺术史”书写,而他以“剧史家”立场为戏剧做史,也“标志着学术界在戏剧研究方面的新变革。”(14)黄天骥、董上德:《董每戡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
对于戏剧整体史和通史的书写,虽然有周贻白所著《中国戏曲史略》为第一部中国戏剧通史的说法(15)如丁明拥认为:“这是第一步划出中国戏剧通史概貌的史著。该著以发展的眼光,把戏剧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分门别类考察了歌舞、俳优、乐曲等戏剧中最本质元素的发展历程,以及‘百戏’之后的各个阶段戏剧的发展情况。”参见丁明拥《周贻白与20世纪中国戏剧史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第49页。,但该著依然将书写时段截止于晚晴花部的崛起(具体到关于皮黄剧的来源于现状的讨论)。而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则直接延伸至民国时期,将话剧也纳入了中国戏剧史的范畴进行整体考察与书写,更显其整体史与通史之一味。
二、董每戡及其剧学:20世纪 戏剧学史建构中的缺失环节
纵观20世纪戏剧学的研究,学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有苗怀明的《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16)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解玉峰的《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17)解玉峰:《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陈维昭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18)陈维昭:《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李占鹏的《二十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19)李占鹏:《二十世纪发现戏曲文献及其整理研究论著综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张一帆的《“剧学”本位的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范式之转型》(20)张一帆:《“剧学”本位的确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范式之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皆以20世纪戏剧学为对象进行了整体研究;齐森华《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一文则在肯定了前辈学人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以往的研究,对此缺少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把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21)齐森华:《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3日。刘祯、张静的《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中则专列“20世纪上半叶戏曲研究小史”一节,对该时段代表性戏剧学人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以及主要贡献和成就做了较为允当的评述。(22)刘祯、张静:《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上、下),《戏曲研究》第58、59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另一方面也有苗怀明和赵兴勤、赵韡等人以戏剧学人为主要对象的个案研究,进而对20世纪戏曲研究群体予以关注。其中苗怀明的《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一书以戏曲研究创建时期的两代学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4位在20世纪戏曲研究史上有着重要建树、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的学人进行了集中探讨,通过对他们成长历程、学术成就及治学特色的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勾勒出20世纪戏曲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总结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23)苗怀明:《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而赵兴勤、赵韡则以“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为总题,挖掘并撰写了关于民国戏曲研究大家的系列论文,对民国戏曲研究做了更广泛地群体性关照。(24)散见于各类报刊,且还在持续补充中。
但较为可惜的是,苗怀明所选取的“戏曲研究十四家”,董每戡并未上榜,而赵兴勤、赵韡进行的“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系列选取范围更大,现已论及近二十家,董每戡依然未能入选。这一方面与董每戡长达二十八年的“沉寂”与平反后的猝然离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对于20世纪戏剧学人群体研究因主观遴选所造成的客观遮蔽。而令人欣慰的是,李占鹏《20世纪曲学史研究》一书选取了20世纪有代表性的10位学人进行评述,其中董每戡入选。作者用“病手推文、埋首诂戏的苦难剧史家”来形容董每戡,并从剧史、剧论、剧评三个方面评述了董每戡曲学研究的特色及其价值。(25)李占鹏:《20世纪曲学史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董每戡的入选至少证明受到了著者的关注,而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董每戡在20世纪曲学史地位的论定。
董每戡作为20世纪的戏剧学大家,以其三百余万字的理论著述、独树一帜的“剧史观”以及“剧史体系”的建构,在戏曲学界独树一帜且有广泛的影响,无可争辩地成为20世纪剧学研究不可绕开的一个大家,他也应该获得与其学术贡献相匹配的学术地位。那么对董每戡及其剧学进行学术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扭转上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学界对董每戡研究相对缺席的情况,进而对其学术贡献及其学术史地位进行重估。另一方面以此个案研究来反观民国戏曲研究的群体,以期更全面、科学、理性、正确地对民国时期戏曲研究的学术群体予以肯定和评价。这对于整个中国戏曲学术史乃至整个戏曲史研究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董每戡及其戏剧史著作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其剧学研究的推进,亦有利于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学的研究历程,进而反思当下戏剧研究存在的某些问题。
三、董每戡剧学研究对20世纪戏剧学整体研究的启示
对于董每戡剧学的个案研究,无论是对董每戡的“重新发现”也好,还是具体到其剧学研究也好,都为我们对20世纪剧学整体研究的反思提供了可能,亦为当下戏曲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拓展学人个案研究
赵兴勤、赵韡在《重绘民国时期戏曲研究思想地图》一文中对目前就20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时写到:“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继承、辨析与深化,戏曲研究也是如此。而当前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于王国维、吴梅这样的巨擘(核心圈学人),或长期在高校(科研院所)执教的名家(主流圈学人),一定程度地忽略了其他戏曲研究学者之成果的挖掘和整理。在戏曲研究史上,20世纪上半叶活跃着一批不容忽视却久为忽略的‘失踪者’,他们曾在戏曲的不同研究方向上开风气之先,领一时风云,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已少为人知,以致有学者将因袭误认作原创。这种学术史地位与研究史现状之间的悖论,说明目前的学术研究史版图还远远称不上丰富和完整。在这个意义上,‘泛主流圈’和‘辐射圈’的戏曲研究人物,就是一座少为人关注的学术富矿。重绘民国时期戏曲研究的思想地图,离不开对这一批学人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他们建档立传,既是学统之赓续,也是释放那湮没已久的‘边缘的活力’。”(26)作者在将20世纪上半叶的戏曲研究者划分为“核心圈”“主流圈”“泛主流圈”和“辐射圈”四个层级。所称“核心圈”学者,是指研究史上有着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精神、创辟戏曲研究的一二巨擘;“主流圈”学者,是指各有专攻,在某一个或几个 研究领域取得过非凡影响且开枝散叶、瓜瓞延绵、追随者众多的少数大咖;“泛主流圈”学者,是指确曾有功于学术发展,足以开宗立派,但被各种历史原因埋没的些许人物;“辐射圈”学者,是指主攻方向并非戏曲,然学识渊博,偶尔“跨界”便能一鸣惊人的少数通儒 。参见赵兴勤、赵韡《重绘民国时期戏曲研究思想地图——〈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二十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虽然董每戡被划分为“主流圈”学人,但与其一同入选的其他学人相比,明显受关注程度要低一些,学界对其研究的力度也较之不足。依据“其学术兴趣与研究旨趣,影响一大批及门弟子及追随者,以致形成相应的研究群落”的判断标准,董每戡似乎也较为不符。(27)陆键东在其《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1956—1980)》一书中说:“1980年2月24日,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史教师进修班开班。该班是‘文革’结束后(甚至可以说是1949年后)第一个全国范围的戏剧史教师进修班,参加该班的年轻教师,相当部分人日后成为所在院校‘中国戏剧研究’的重要力量。该班主持者王起教授,受到这一群年轻教师的拥戴。王起播下了火种,赢得了应有的尊崇。而董每戡就这样在此紧要的转折关头,与重开新局的弘业擦肩而过,错失了最后一次颠覆半生命运寒薄格局的契机。同时,更是错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足可书写历史、觅得传承衣钵者的人生良机,终至其身后名山之业很快湮没。”“董每戡于1980年2月13日逝世,他与这一切失之交臂,仅仅11天。”见陆键东《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1956-1980)》,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541页。这也是导致对其研究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但即便如此,留有丰厚著作的董每戡理应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学术上的一颗明珠,取得与其学术贡献相匹配的学术地位。然而这一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单就以董每戡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成果也才是近10年陆续出现,终于将董每戡回归于20世纪的戏曲学术版图之中。
被划分为“主流圈”的董每戡被“重新发现和评价”尚且如此曲折艰难,更何况那些属于“泛主流圈”和“辐射圈”甚至徘徊于之外的许多学人,则更是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所以发掘20世纪戏曲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尽最大可能地拓展有价值的个案学人研究,则是释放“边缘的活力”,赓续学术传统的有力保证。
另外,学人个案研究还需要将目光扩及“非戏曲学人”群体,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各有学术高地,或小学,或经学,或史学等等,但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成名成家的同时,多多少少与戏剧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这一“非戏曲学人”群体的戏剧学挖掘,对全面呈现20世纪戏曲学术版图也有着很大的补充作用,值得关注。
(二)从整体视域构建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
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研究,学界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成果。
就整体著作史料的整理出版,有程华平、黄静枫主编的《民国中国戏曲史著汇编》(28)程华平、黄静枫主编:《民国中国戏曲史著汇编》,扬州:江苏广陵书社2017年。和黄天骥主编的《近代散佚戏曲文献集成》(29)黄天骥主编:《近代散佚戏曲文献集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三晋出版社2018年。,这两套“大书”不仅分别收入了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和《说剧》,同时还收入了20世纪其他最具代表性学人的戏曲著作和重要史料,为进行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就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则有陈维昭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该书旨在以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表演和理论所做研究的历史进行描述。(30)陈维昭:《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戏曲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该著作于新世纪初出版,对20世纪中国戏剧学术史有了一个宏观的描述,属于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中国戏剧学术史首次进行回顾与总结。然该著属于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明确限定于古代文学,其分卷也是遵从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文学四大样式,故其撰述的“文学性”是其基本视域,《戏曲卷》也不例外。因此该著依然是笼罩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之下进行的“戏曲文学学术史”,其与以综合艺术的视域构建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追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就20世纪中国戏剧史学进行梳理的有丁明拥《中国戏剧史学史稿》,该书对中外关于中国戏剧史进行撰述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评述与研究。作者通过对20部“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戏剧史著做系统性研究,探讨了他们在中国戏剧史学史上的地位、影响和赓续、互文的关系;通过对诸位作者所秉持的历史哲学和使用的学术方法进行回顾和检讨,试图对既往的戏剧史著研究进行系统性整理。”(31)丁明拥:《中国戏剧史学史稿》“封底”,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
就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研究则有两部博士论文直接以此为选题进行研究。一是汪超红的《20世纪戏曲研究论略》(32)汪超红:《20世纪戏曲研究论略》,浙江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此文重点对20世纪戏曲研究版图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如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青木正儿、张庚等)及其著作进行了客观评述,但对研究者进行的逐一个体评述,实质并未达到真正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二是黄静枫的《戏曲史纂论1900—1949》(33)黄静枫:《戏曲史纂论1900—1949》,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该作属于20世纪戏剧学整体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全文从著史的学术环境与史纂动机、模式著史的历史书写、史著内容的历史呈现、戏曲史家的主体参与、学术关系的传统沾溉与现代垂范五方面展开20世纪上半叶戏曲史纂活动的考察,最后还对评估时的史料局限与模式偏颇进行了总结与反思。综观全文,对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研究比较整体,也颇为系统,取得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可谓是20世纪中国戏剧学研究的新创获。但从实质来说,该文的研究理路和逻辑演进更多的还是限于戏曲史学的范畴,从其论文题目亦可说明。
所以,就目前而论,学界依然还未成出现一部完备的“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等类似的著作,也即意味着依然没有完成对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构建和总结,而无论是历时性梳理还是共时性研究,也都还存在极大的挖掘空间。因此,齐森华先生“把加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的疾呼依然振聋发聩,需要后辈学人继续努力去完成。
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因戏剧与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不同,也使得各个时期的研究者所持戏剧观不同,刘祯、张静将之简单勾勒出一条线索:“文学性(王国维)——俗文学性(郑振铎)——戏曲之舞台性(周贻白、董每戡)——戏曲之文化性(任中敏)——戏曲之综合性(‘前海学派’);从时间上看,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几个主要阶段:王国维(世纪初)——郑振铎(30年代)——周贻白、董每戡(40—80年代)——任中敏(50年代)——‘前海学派’(80年代)。”(34)刘祯、张静:《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原文中未列及董每戡,笔者认为董每戡对于古典戏曲注重舞台性的研究路向,可以与周贻白一齐成为此时段的代表性学者,故将董每戡列入其中。而在这条线索和时间段内,董每戡作为主张“戏曲之舞台性”的代表学人之一,也无疑与周贻白先生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条线索的重要一环。因此,对董每戡及其剧学进行个案研究,也即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利于助力于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性建构。
(三)戏剧史的多元化书写
戏剧史的撰述向来不止一种写法,每位学者根据自己所秉持的戏剧观念、创作理念和研究方法,自会撰写出不同侧重于样式的戏剧史。而戏剧史无论仅关乎学术,还是被应用于教育,其多元化的书写也都是应有之义。而董每戡的戏剧史撰述即为戏剧史的多元化书写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就戏剧史的学术意义而言,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以及被遗失的《中国戏剧发展史》都能够以唯物史观进行理论统摄,进而对戏曲的起源、形成、发展等讨论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也正是“尝试完成一部史论兼备的戏曲史著的努力”和对“20世纪的戏曲史书写开始追求更高的史学目标”(35)黄静枫:《要素抽离与分途洄溯:20世纪上半叶戏曲生成史纂论》,《戏曲研究》第101辑,第254页。,使得董每戡及其剧史书写成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模式撰述的一个拐点,其戏剧史撰述不囿于前人书写模式,而是回归戏剧之本体,以“剧”的“艺术性”覆盖前人以“曲”的“文学性”,将戏剧立于舞台演于观众之前的本质属性与其在历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下所产生的形态样式的演化变迁相结合,勾勒出真实符合“剧史”特征的戏剧史。而这样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方法上,也都对后来者关于戏剧史的多元化书写提供了启示。
就戏剧史的教育意义而言,戏剧史的撰述其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界,它还与普通高等学校的戏曲教育密切关联。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在我国艺术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以提升学生艺术素养为主要目标的戏剧教育,教授给学生的也理应是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尤其是立于舞台的表演,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刻体会到“无声不歌,无动不舞”(36)齐如山:《国剧漫谈二集·地方戏怎样变成大戏》,《齐如山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1826页。的艺术魅力与美感,而非是被“戏曲文学”代替了的“戏曲”,但恰恰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戏曲教育却长期深陷于这一误区,正如贾戎所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戏曲教育与其说是艺术教育,不如说是文学教育,这和传统的‘曲文学’研究观念密切相关。在过去的研究中,戏曲的艺术本体曾长期被遮蔽掉、隐匿掉,然而,戏曲并不是文学所能完全涵盖的。回顾近百年来的戏曲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历史上一直有一批学人坚持从舞台表演性出发撰写戏曲史,他们的戏曲观和写作实践为我们今天的戏曲教育和教材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37)贾戎:《戏曲史书写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戏曲教育、教材建设的思考》,《戏曲艺术》,2010年第1期。而“坚持从舞台表演性出发撰写戏曲史”董每戡即是代表学者的其中之一,而且他以比“文学性”更重视的“演剧性”和“舞台意识”构建了自身的“剧史体系”,这无疑对戏剧史回归本体的撰写路径与多元化书写方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综上述论,通过对董每戡剧学研究,把握其剧学特征,并对其剧学贡献和影响做以较为准确的评估,进而肯定其在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对董每戡剧学进行个案研究,来反思20世纪中国戏剧学研究路径及整体价值,同时对当下戏剧学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即促使我们对20世纪戏剧学进行拓展学人个案研究、加强整体研究以及戏剧史的多元化书写,以期更好地助力于20世纪中国戏剧学的整体性建构以及当下戏剧学的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