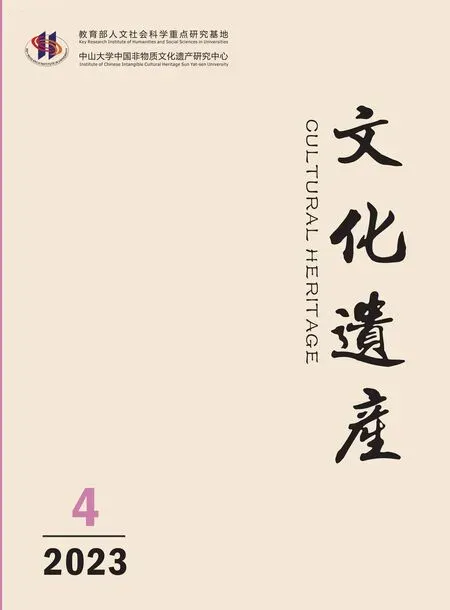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及其与地方关系的重构*
裴齐容 张骁鸣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自产生之初,就表现出了与地方的紧密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将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两方面的地方要素定义为非遗的核心构成部分,强调了地理、自然和历史条件作为非遗创造的具体的地方性情境(1)戴俊骋、李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地方建构》,《旅游学刊》2019年第5期。。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则将非遗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不仅有其所属的群体,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场所,具有明显的空间、地方属性(2)吴康:《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地理研究》2009年第5期。。
地方性(placeness)是地方的独特性,是特定时间与空间跨度中的地方特征(3)唐顺英、周尚意:《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地理科学》2011年第10期。。有了人、时、空统一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才能完整地构筑起地方性的全部意义(4)陶伟、程明洋:《地方性空间与旅游发展中的地方性研究:从空间与空间句法谈起》,《旅游学刊》2013年第4期。。地方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本土文化特质、反映地方人文地理要素的属性,是地方文化感知、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的地方性具体体现在族群、社区等核心传承群体及区域(5)宋俊华:《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认定何以可为》,《文化遗产》2022年第4期。,即人的主体性要素,还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实践性要素(6)张骁鸣、周淑君:《当我们谈“保护”时,我们在谈些什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若干核心概念的讨论》,《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20年第2期。,以及带有地方文化符号表征的物质性要素。对非遗地方性的保护,对内有利于地方集体记忆的传承、文化认同的形塑,对外则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播,以及特色旅游名片的打造。
然而,以往关于非遗的研究多将地方作为非遗发展的背景或常数,将地方性视为非遗整体性的一部分,忽略了快速变化的媒介环境对地方空间的冲击、各类生产实践及传播场景对非遗地方性要素的影响。譬如,短视频已成为非遗视频化生存的主要形式,将物质性的非遗转化为虚拟空间中的凝视对象;文创商品则成为非遗物质性的主要载体,商品属性与文化属性成为非遗发展的一对博弈关系;旅游等大型活动则是非遗对外进行文化宣扬的重要场合,也是非遗本地化与全球化相互冲击的场域。非遗与地方的关系在各传承、传播场景中已然发生重构,由此产生非遗跨时空传播与地方性建构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策均提出了适应媒体融合趋势、加强非遗传播的关键任务,将非遗作为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及文化名片进行宣扬;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非遗生产实践和传播却出现了形式同质化、内涵片面化和地方“匿名化”的典型矛盾:如非遗短视频为吸引更多流量,而大量使用猎奇文案,导致非遗的地方文化内涵未得到真正的阐释,成为一个被快速迭代的视觉产品;而充斥在各大旅游景区的同质化“非遗手工艺品”,则被游客戏称为“义乌小商品”,既缺席了本土的实践场域,也模糊了本土的文化要素。
因此,本文从非遗地方性的主体性、实践性和物质性要素出发,从媒介环境的物质、活动和媒体的角度,探究非遗与地方的关系在商品、旅游和视频等场景中的重构,刻画其传承、传播的时空演变机制,从中解析非遗传承、传播与地方性建构的典型矛盾,是为加强非遗与地方的联系,使得非遗的保护利用在适应当下媒介环境的同时,不失地方文化内涵特质、不失地方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从“地方制作”到“全球化生产”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看,非遗与地方的关系由“地方制作(local making)”转变为“全球化生产(global production)”,丰富的在地化的生产全程萎缩为全球化商品生产中对地方性元素的有限运用,由此带来关于非遗文化商品化的焦虑与争议。
此前在地理研究中,多针对非遗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7)徐柏翠、潘竟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8年第5期;程乾、凌素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科学》2013年第10期。。然而,非遗既产生于可测量的地理空间环境,也生长在由人赋予意义和内涵的地方。地方为非遗的生存发展提供人文地理环境土壤;非遗也赋予地方内涵,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地方是在空间中由人创造的“有意义的区位”(8)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王志弘、徐苔玲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4、56页。,“人”作为主体,赋予了空间意义,空间因而成为地方(9)Yi - Fu Tuan.Topophil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xii.。
非遗的产生既根植于地方,又随着传承人及族群的流动与再扎根,以及以手工艺品为载体的商品流通,产生了跨地方性的关系。跨地性实际上是在地方与地方的联系上实现的(10)Massey Doreen.“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no.6 (June 1991):24-29.。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活动,人是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和根本(11)陶伟、蔡浩辉、高雨欣、张楚、江映珍:《身体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实践》,《地理学报》2020年第10期。。基于地方的物质和身体的实践是一种包含“人—物—地”之间关系的网络,非遗的商品制造实践可促进三者之间关系的强化,从而实现非遗生产的延续性(12)黄素云、陶伟、蔡浩辉:《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地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11期。。非遗的传承本质上是技能的流动,人作为拥有流动能力的个体,能够携带非遗技能进行流动,而非遗与传承人的流出与流入如何影响地方的发展、如何影响非遗的传承,还需深入探讨(13)陶伟、蔡浩辉:《21世纪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回顾:兼谈地理学可能的贡献》,《热带地理》2022年第1期。。非遗本身也可能在所属区域之外的地方产生聚合,以商品的形式呈现,由其他非本地因素组成。以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这一国家级非遗为例,在本土传承人的银器锻制实践过程中,非本土的市场订单、甚至是制作材料,都聚合在当地的非遗生产过程中,在跨地性的视角下,非遗以地方为中心,而不局限于特定地方,它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地方性的传统文化事项,而是成为从传统文化中异化的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经济政治产品(14)魏雷、朱竑:《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地理学报》2022年第2期。。
非遗跨越了其生长的地理区域,借助商品这一媒介流动迁移之后再度嵌入地方,而此时的地方已不局限于原生环境,非遗及其实践的各个环节嵌入全球多尺度的“社会—空间”网络当中(15)Natasha Webster.“Rural- to- rural translocal practices:Thai women entrepreneurs in the Swedish countrysid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no.56,(November 2017):219-228.,其生产材料、传承主体、实践场所都经由全球化过程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本土,工业化、技术化使得非遗的生产逐渐“去地方化”,由此带来关于非遗的开发保护与原真性的争议。
“原真性”保护观点认为,如实记录、完好保存、完整传承是非遗保护的首要原则(16)刘德龙:《坚守与变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几个关系》,《民俗研究》2013年第1期。,地方性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重要标准。此类研究注重从非遗自身的传承体系进行分析与记录,认为非遗保护对地方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有积极意义,多将地方视为“恒常”的、“固着”的环境,是不变的,即认为地理环境未发生重大改变,非遗只需持有在地存续状态。传统研究范式中对非遗在地性的认知惯性阻碍了人们去认识和探索非遗实践的生产性和竞争性(17)魏雷、朱竑:《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地理学报》2022年第2期。。
从市场经济角度出发的“生产性”保护,以非遗的活态性为保护原则,产业结构多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近,从寻求历史的客观“确凿”转向探寻文化意义的“真实”,即活的价值(18)高小康:《社群、媒介与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三要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此类研究以保护开发为基础,以旅游产业、文创产品、文化传播等为研究对象,从中解读非遗的地方性元素。在此类研究情境中,非遗不是地方性的全部呈现,而是地方性元素的局部运用,对应不同的媒介载体,地方性成为一个可灵活变通的表现方式,地方也成为一个动态的、可与其他空间交融共生的地方。
然而,除了基本的形式功能与符号象征,非遗实践成为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地方性成为可供选择的元素之一。非遗被日益简化为文化商品,嵌入人们的消费生活之中,在生产、传承的过程中而缺乏地方情感的诉说。
二、从“地方实践”到“全球化凝视”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用看,非遗与地方的关系由“地方实践(local practice)”转变为“全球化凝视(global gaze)”,由日常生活的地方性传统转为被旅游者凝视的审美对象和被权威者评估的项目,由此带来与本土生活脱节的问题。
非遗作为强烈的在地化的存在,在全球化、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既是地方区别于他处的标志,也是本土与外来交流的对象,这在旅游的活动场域中体现得极为明显。非遗在当代被赋予了承载地方感、建构现代性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机制(19)张原:《从“乡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遗产的现代性承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非遗营造出共同体历史连续性的日常经验,能够促进个体社会认同的形成(20)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录评级中,可看出非遗既是区域性的文化,同时也是文化全球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遗产”正是非物质文化的一种现代性话语表达(21)潘宝:《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但遗产化作为一种外部干预,加剧了遗产与地方性之间关系的异化。对非遗的概念界定、类型分类、层次评级,一方面强调了非遗之于地方的重要性、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从普世价值的角度将非遗推向全球化、普遍性的层面,其地方性与全球化、现代性的关系由此处于不断调和、相互协商的过程中。在现代语境下,非遗由其所属区域的文化“小传统”走向国家文化“大传统”,其地方性已不仅仅局限于所属区域,而成为在传播上更为广泛、在认知上更为普遍的大众文化,地方性一方面被强调,一方面被模糊,成为全球地方化影响下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成为一种权威话语体系,亦变成日常生活场域中脱嵌出来的地方性传统(22)庞兆玲、孙九霞:《从脱嵌到再嵌:民族手工艺遗产的保护发展实践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甚至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作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方性,而作为“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被赋予了广泛的公共性(23)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在“遗产”的公共性和全球化过程中,旅游发挥着重要作用。非遗的旅游开发,有原真性保护的博物馆旅游、以及民俗节庆展演等形式。将非遗的地方性视为同原真性一般静态、完整的博物馆式非遗旅游,强调非遗被严格地置于现代社会空间之中,作为“橱窗”或“壁龛”里被凝视的客体,与人们的情感和认知有一定的门槛和距离。实际上,在这种机械嵌入观的保护逻辑下,非遗并未与现代社会发生实质的互动,只是作为一种记录性的知识而存在(24)庞兆玲、孙九霞:《从脱嵌到再嵌:民族手工艺遗产的保护发展实践研究》。。
非遗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原本与本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备实用功能,由于增长全球化、现代性的加速进程,以及权力、资本向经济文化的扩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逐渐由生活场景向被建构的地方空间叠写转变(25)郭文:《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地理研究》2020年第11期。,如具备世俗功能和神圣空间的节庆仪式,原本是从日常生活中演变而来的“非日常”情境,由于被“遗产化”、纳入官方权威话语体系,或因旅游产业等的开发,而成为本土生活的一个客体,虽供游客凝视,但与原住民无关。以仡佬族祭祖活动为例:在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祭祖活动成为悬置于族群之上的社会文化重构活动,官方建构了“自上而下”的认同,但却难以得到“自下而上”的认同(26)杜芳娟、陈晓亮、朱竑:《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地理科学》2011年第12期。。
非遗的实用功能被现代化生活所淹没,而成为一个独立于日常生活的客体,被凝视、品评、被审美化。非遗作为一种文化代表,成为权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旅游的媒介作用中构造了全球化和地方性相互碰撞的场域,在地化的传承转变为在地化的旅游体验,而地方却成为空间叠写在“意义之上的意义”,与本土生活脱节,缺乏真实情感的共鸣。
三、从“地方传承”到“全球化扩散”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看,非遗与地方的关系由“地方传承(local succession)”转变为“全球化扩散(global diffusion)”,由本土的传播、认知向由媒介传播建构的另一个全球化网络空间迁移,与实际的地方脱嵌,由此带来非遗内涵认知的单一化、地方性被消解等问题。
非遗的传播、传承方式一般面向特定的空间与社群,但以视频等新媒介技术为主的媒体传播拓展了非遗的时空范围,同时带来媒介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此前研究多认为,一个边界清晰的空间可以成为认知和保护非遗的载体(27)UNESCO:Basic Texts of the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16 Edition). (Paris:UNESCO,2016),1-19.,地方有时还会专门划分区域以表示非遗存在的空间,如作为非遗类型而存在的文化场所和文化生态保护区(28)王淑佳、孙九霞:《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地理学报》2021年第4期。,将空间场所作为非遗类型进行展示、践行与保护。然而,媒介技术的介入,却将非遗产生的物理空间挤压,转向媒介建构的虚拟空间。现代性的时空压缩,不仅改变非遗的展示、传播路径,也改变其传承的固有方式,如许多传承人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在全国各地“收徒弟”,言传身教的非遗传承变成媒介技术影响下的线上娱乐课堂,其传承的成果有待考究。而以旅游这种需要具身体验的行动为例,当今,媒介技术的多方位应用,也使得非遗旅游中具备了超越时空的虚拟体验和镜像虚拟,如非遗的数字博物馆等,但是,非遗旅游若以全新体验技术之名去地方化,导致非遗与地方的脱节,不但不能增进游客对地方的了解,反而可能削弱人们对地方的认识,甚至成为障碍(29)戴俊骋、李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地方建构》,《旅游学刊》2019年第5期。。新媒介技术动态演进之快、信息过载,让人难以充分细心品味传统媒介时代的“慢”体验与“深”意义(30)张骁鸣、邓瑞珺:《媒介环境学视野中的旅行发展趋势断想》,《旅游学刊》2020年第8期。。
有学者认为:若不遵循“文化根植于地方”这一前提,则非遗只能是漂浮在空中的想象(31)耿波:《地方与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当代问题》,《民族艺术》2015年第3期。,如同George Ritzer所言的“全球在地化”进程及其文化多元化结果最终不过是“无本之木”。生产性的保护将非遗置于不同的时空中,甚至依托不同媒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不以严格的区域界限为保护发展的原则。但“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的非语境化,在这一过程中,内容丧失其原有的灵韵,每被传播一次,意义便衰减一次,直至变成了其他的意义(3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庄仲黎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9年,第5页。。”因此,在数字媒介建构的虚拟与超真实中(33)孙九霞、罗意林:《跨越时空的旅游“新村民”:他者的数字化自我呈现》,《西北民族研究》2022第2期。,需警惕媒体对非遗解读的碎片化、表层化倾向(34)李毓、谢兆雪、曹秀丽:《旅游企业自媒体叙事对民族非遗传承的作用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年第1期。,也要避免网络流量挤占的非遗项目的生存空间(35)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4期。,导致非遗与地方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
由非遗与地方的关系发生重构的场景可知,传统的非遗在地性的地理空间已经发生变化,受到新媒介技术的影响,由此产生日常生活方式、非遗传承、传播处境的变化(见表1)。非遗的地方性在现实发展中已不仅仅是静态的原生地理环境与发展背景,而成为一个不断与外界产生交融、与各类媒介产生反应的重要维度,地方的边界被拓宽,形式更灵活。所以,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处于“建构(making)”的过程,应将其视为一个“动词”而非“名词”(36)David Harvey.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Temporality,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7,no.4 (December 2001):319-338.。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与地方性建构的典型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传承传播体现出其时空演变的机制,但也与非遗的在地存续、地方建构形成矛盾的张力。作为一种时空叙事的方式,传播被认为是“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过程中,不同媒介、场景的共同作用,将会对非遗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产生影响;同时,正是传播的时间或空间的偏向,产生了非遗与地方的关系重构或矛盾,由此对非遗在当下的地方性建构产生影响效应。为探究不同传承、传播场景背后的时空特征与逻辑,本文从时间、空间的结构出发,从传播的“界面”的角度,为非遗与地方的关系解析构建“人—时—空”一体的分析框架,从而刻画非遗跨时空传承、传播与地方性建构的典型矛盾表现,从成因的解析中挖掘非遗媒介传播与地方性建构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非遗传承、传播与地方性建构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完全消极的、片面的,而是从马克思对矛盾的哲学概念阐释出发,将矛盾视为一个中性词,以辩证的态度看待矛盾,既看到其中的冲突、对立与难以调和,也看到其中相互成就、相互融合的部分,以此展开非遗与地方的关系探究。
(一)时空叠写
民俗节庆是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当下的适应与发展,是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叠写,民俗节庆的每一次活动均是历史的更新与更替。借由媒介技术的发展,民俗节庆的地方性文化意义内涵不仅在时间中获得重新阐释的机会,也可能在媒介空间中被解读、改写或被扭曲。例如广东潮汕地区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习俗仪式,如“出花园”成人礼等,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仪式过程中,是地方文化历史与个人家庭发展历程的交替,然而,仪式中的讲究细节则可能在网络上被解读为复杂且无意义的琐事,甚至带有地域歧视与文化偏见。地理空间与媒介空间共同叠写了关于习俗的当下社会接受涵义。
原本,时间和空间的同时在场是人地关系的基本形式,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具身认知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中的“空间感”在虚拟空间中也会越来越多地回归(38)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2019年第12期。,而各地域圈层、空间区隔也并非持有严格的边界,而是具有互渗的规律,在媒介的传递与转化中,产生相互作用的效应。因此,空间和时间在媒介的作用下相互重叠、嵌套。
时空的重叠显示出非遗传播与地方发展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作用。如非遗文创商品等通过受众可接触的、可进入的形式,将非遗的时空压缩为具象的表征,并试图通过实用、灵活的方式再度进入人们的生活,叠写其在现代生活的实用价值和审美内涵。节庆活动及旅游是以地理空间中的实际参与行为形塑人、非遗与地方的时空重合,而视频中的非遗与地方虽为平面展示,却有着网络文本建构的多面形象。网络媒介空间中的地方形象塑造、文化内容传播,共同叠写了地方和非遗的文化名片。地理空间与媒介空间中的非遗和地方的含义是否产生明显区隔,则是媒介的时空“叠写”是否重构或解构了非遗的地方性的关键。
非遗传播的时空叠写类型,一类是意义的叠写,即不同空间中对同一非遗项目的解读,或不同时间中对同一非遗的意义诠释的叠加;另一类则是行为的叠写,如线上的非遗传播对线下地方旅游的影响等。这两个层面均围绕人作为非遗传播的主体展开,由于主体认知及空间行为产生于不同的媒介环境,易产生非遗地方性内涵被扭曲的矛盾。
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非遗本身即是地方历史的产物,在同一时空中叠写了历史与当下、虚拟与现实的非遗实践内涵。商品、旅游、视频等传播场景,均是在同一集聚时空中展开非遗的时空叠写的意义,为非遗地方性的实践性、主体性要素注入新的解释。
(二)时空延异
非遗在传承、传播过程中,形态和意义都随着社会发展需求而不断变化。如广东潮州木雕等手工艺非遗项目,原本取材于地方的日常生活,但随着人工成本的增高以及制作时长的增加,手工艺品变成手工“奢侈品”,出现与普通人生活产生区隔的情况。随着项目传承式微、传承人生活拮据的情况出现,在旅游开发中将手工艺品打造文创小商品的形式,尝试令非遗从日常、实用的角度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但作为文创小商品的非遗,有的不能完整保留其工艺,有的不能完整展示地方的文化意义内涵,然而,随着商品的流通和旅游的开发,这些零星、碎片化的地方性元素,有可能组成了人们对这一非遗地方性的理解,这一“脱嵌—返嵌”的过程,造成了非遗在时空中的形式和意义变迁。另外,诸如新创节事等“被发明的传统”一样,在时空中演化的非遗实践也可能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从而建构非遗在媒介传播、时空延异之后的地方性。
当下媒介环境的典型特征即是所有东西都不再有标准呈现或一次性“定格”,而是在不断地被媒介传递、变形、转义、重构、再生。德里达发明了“延异”一词,用来表示一种动态发展的差异,“延”体现了时间性,“异”表现了空间性,而“延异”则是时空的统一(39)黄鸣奋:《后结构主义与超文本理念》,《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延”是非遗活态性的常态,但“异”则体现出其地方性内涵可能变得模糊。
因此,探讨非遗传播时空延异的演进过程与影响因素,需从非遗本身的历史演变出发,结合地方的背景变迁,探究非遗的物质性、具身性等特征在媒介技术影响下的变化与重构。非遗的地方性在媒介环境的长时间演变中,易变得模糊,需通过对传承内核、传播内涵的重视和强调,以人和地方日常实践的关系来解析这一典型矛盾。
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非遗的传承发展具有活态性,因而其地方性不是原真性的代表,而是在时空中动态发展的。文创商品、旅游开发等形式即是对非遗的创新利用。时空延异是非遗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传承、传播形式的“异”,能否带来非遗地方性文化内涵的“延”,则是需辩证看待、具体分析非遗传承与地方性建构的时空演进机制。
(三)时空错置
出于文化宣传、旅游开发等目的,地方有时会采用时空集聚的方式集中展现非遗,但如旅游中的大型民俗节庆表演等形式,则可能为了表演形式而忽视节庆仪式的内涵,成为一种时空错置的表演。非遗及其所属的场景环境成为如福柯所说的在文化生态大环境中嵌入的异质空间,即“异托邦(heterotopias)”“没有生态环境的活态只能算是表演。”
然而,“一种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在特定场景中具备了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发展的具体条件,这个场景便可能成为这种文化依存的当代家园(40)高小康:《社群、媒介与场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三要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所以,这种时空的错置并不一定是完全消极、错误的非遗实践,而可能是非遗在新时代的应激反应。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天天泼水节”为例,景区内不断生产制造的“泼水节”既可能是消极的文化变异和去地方化(41)李毓、孙九霞:《结构化理论视角下非遗表演的地方性建构——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天天泼水节”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也可能是积极的文化生产和地方性建构,非遗的民俗表演成为一座“流动的博物馆”(42)张洁:《流动的博物馆:旅游民俗表演与文化景观的再生产——以贵州丹寨万达小镇“非遗”展演活动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时空的重新组合、重新放置,是非遗的活动场景中对空间意义的重新阐释,从而对非遗的空间实践、时间维度注入新的定义。民俗艺术节、非遗主题的会展活动亦是同理,通过空间的错位放置,获得非遗地方性内涵的社会效应。
因此,不应以预先的价值判断来评估非遗传播的时空错置的后果,而是从其错置的表现形式中,围绕非遗的地方性这一重点分析对象,探究在时空错置之后的地方性表现、与地方的联系等,从中挖掘可能的创新机遇。
从物质空间的角度出发,非遗的活动场景多以时空聚合的形式出现,但这一形式也有可能产生时空错置。这种因时空错位产生的冲突影响和社会效应,既是直接揭示了非遗与地方关系重构的矛盾,也从侧面显现出非遗在传承、传播过程中可能的发展路径。
(四)时空延展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在物质空间中受限的非遗实践,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获得延展。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东潮州古城区的迎神拜神活动尝试通过“线上直播祈福”的形式进行,传统大型民俗节庆的“在场”参与方式经由媒介技术的转化,成为一场在线上转播的活动,人们不仅“在场”,且“流动”了起来。非遗与人的联结由线下氛围感知转为线上的精神共通与文化共融,同时也带来传承方式与范围的改变。微信公众号文章《在快手,252万名用户在记录非遗》描写一位画糖画的手工艺人,因为糖画视频在“快手”平台的传播,他不仅在全国收了三百多个弟子,而且与远距离的人们产生了情感的交流。“有新人结婚,他会精心制作一个用糖制作的‘囍’字,视频中,悠扬的背景音乐和婚礼现场的热闹场景,透过屏幕传递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慢慢发现这其实是在传递和扩散甜蜜的过程。”(43)“在快手,252万名用户在记录非遗”,地球知识局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x_7ccmogJN9ySL4b HhD8xQ,访问日期:2023年7月4日。
以往研究关注物理时空在虚拟空间中被压缩的情况,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时空扭曲”的形式。如历史悠久的非遗文化以娱乐轻松的视频风格呈现,枯燥辛苦的非遗制作过程被浓缩为短暂的、甚至是带有节奏感的几秒几分,而作为非遗原生背景的地方则成为网络传播中的一个标签、文案中的一个地名;大众旅游更是通过短暂、即时的参与和反应,以观看表演、消费体验等方式认知非遗。这种时空压缩导致的“时空扭曲”削弱了地方身份的代表性意义和定位再生产(44)谢沁露:《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媒介地理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在非遗的时空传播过程中,由各媒介类型模式造成的时空压缩,需通过在地化、具身性的深度文化体验,从中展开地方的文化意义和非遗的精神内涵。
然而,虚拟空间中带动的非遗在物质空间中的流动,使得地方的文化意义内涵获得更广泛的延展,如非遗电影、视频中的文化故事,扩展了非遗的认知感受途径与范围,由此可能带动的非遗商品流动,使得非遗的商品属性、文化属性得到发挥;而旅游则是带动非遗的地方性展开跨地性交流的可能。由此可见,虚拟空间中对非遗实践时空的“压缩”是其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在时空压缩之后的时空延展,则是非遗媒介化生存带给地方性建构的新的机遇。
因此,既要关注非遗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也结合其在现实空间中的反应与结果,解析在虚拟空间中被削弱的非遗物质性、实践性等要素在现实空间中回归、延展的方式和路径。
从虚拟空间的角度出发,非遗的数字化保存和记录即是非遗时空延展的机会。非遗视频将非遗的传播认知范围无限扩大,且可多次转发、重复播放,并通过其他文本题材的再创作,获得地方性建构的更多范围和途径。非遗传承、传播在时空延展中的虚拟流动与现实反应,共同作用非遗在当下媒介环境中的地方性建构。
传播媒介既可以折叠空间、浓缩时间,也可以展开空间、重复时间,进行时间及空间的文化意义叠写。非遗经由媒介传播,不仅在时间上获得传承传播的历时性,也在空间的传播范围广度上获得共时性,地方性则是在这一时间和空间跨度中的稳定的非遗内核。通过对非遗传承、传播与地方性建构的典型矛盾的表现刻画与成因解析,可进一步深化对非遗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结 语
对非遗的地方性保护是非遗传承、传播的重要任务。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上通过并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提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八大纲领之一是“推广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尽快解决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认知严重欠缺的现状。”(45)黄莉敏:《地理学介入“非遗”研究:内容取向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的响应》,《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7期。因此,在传播与媒介领域中激活和强化地方感和地方性,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有益的范围之内,不仅可以成为对抗和消解传播全球化、文化同质化的利器,而且对传承美德和社会建构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6)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对非遗传承、传播的时空机制探究、正向引导,既是繁荣和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地方所采取的种种保护传承措施,本质是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文化生态(47)陈恩维:《地方性知识与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基于广东勒流“扒龙舟”的考察》,《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在非遗与地方的关系于各类传承、传播场景中已然发生重构的现实挑战下,应从“人—时—空”一体的框架中挖掘非遗地方性的物质性、实践性与主体性要素,从非遗跨时空传承、传播与地方性保护的典型矛盾解析非遗与地方的新关系、新场景,以融合发展的动态视角找寻非遗与地方加强联结、共同建构的路径。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