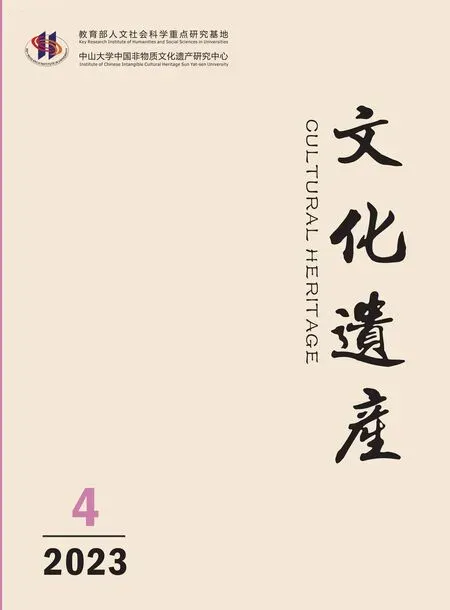试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中的月光马*
李明洁
所谓“纸马”,王树村有简明的介绍,“‘纸马’是因过去祭祀天地神灵、创业祖先时,必附一匹马的图样作为受祭者的坐骑以便升天而得名。后来人们便把祭毕焚化的各种神佛图像,统称作‘纸马’”(1)王树村:《民间纸马》,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6页。;“纸马以纸本为载体,以神像为表现中心,自唐代产生以来,虽曾与纸钱混用,却有超越楮币的特殊功能——往往以图像直观地表达延神送神、敬神如在的神秘观念”(2)陶思炎:《纸马本体说》,《年画研究》2013年秋季号。。作为民间祭祀专用的纸品,纸马至民国初年仍颇为盛行,是大众民俗活动中的日常用品。但在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和现当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之后,纸马逐渐淡出,目前仅在一些地区留有遗绪,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侧身于木版年画保护之列。
在纸马中,有一大类属于自然神崇拜,其中就包括为中秋节祭祀月神特制的“月光马”。尽管现在中秋节继承了吃月饼和家人团聚的传统,但“拜祭月光马”这一民俗活动却销声匿迹了,连作为民俗文物的月光马也难见真迹。
因缘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的“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 Paper Gods Collection)(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藏门神纸马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电子档请见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 本文引用的纸马图片都得到了该馆书面的版权授权,皆为惠允使用。,内含多款1930年代北京地区的月光马。以这套祭祀纸品为物证,结合相关文献,民国初年的北京中秋节俗或可复述;以月光马为依托,还原以纸马为标志物的节俗生活并重估其历史价值,有助于准确理解民间信仰与文化记忆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民间信仰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身份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将直面目前纸马研究中一直语焉不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纸马作为民俗文献和民俗文物,其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中秋节与月光马
“中秋节形成最晚,在汉魏民俗节日体系形成时期,中秋节日尚无踪迹。唐宋时期因时代的关系,以赏月为中心节俗的中秋节日出现,明清时中秋节已上升为民俗大节”(4)萧放:《中秋节的历史流传、变化及当代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到近现代,北京地区中秋节的记录更可谓俯拾皆是,从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到民国时期蔡省吾的《北京岁时记》(5)王碧滢、张勃编:《燕京岁时记:外六种》,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等,都对当地中秋拜月的祭品、仪式等有详尽描述。对外国人而言,中秋节的全民欢庆和丰富的拜月习俗,因其异域特色而格外引人注目。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产生了大量以西文撰写的中国民俗文献,北京风俗无疑是焦点。比如,艾伯华《中国年节》有专门一章“中秋节”(6)Wolfram Eberhard,Chinese Festivals (New York:Henry Schuman,Inc.,1952),97-112.,民间传说和丰收庆典的记录尤其详细。《岁时》中的“八月”(7)J.Bredon and I.Mitrophanow,The Moon Year (Shanghai:Kelly &Walsh,Limited,1927),391-424.中文版可参见何乐益、裴丽珠、米托发诺《中国的风俗与岁时》,杨沁、王玉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第455-478页。一章,记录了中秋时节相关的神话和仪式,还附有北京及其京郊社戏、舞狮、售卖兔儿爷以及拜祭月光马等系列节俗活动的照片。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于1925年至1926年在北京访学,之后编撰的《北京风俗图谱》中就有中秋拜月仪式的画像,上有月光马的示意图(8)青木正儿:《北京风俗图谱》,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36页。。1939年到1945年战争期间,日本在华情报机关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拍摄了三万多张纪实照片,其中有1939年北京中秋节的4幅照片,包括记录儿童拜月祭祀的场景一张,月光马赫然居中(见彩图1)(9)华北交通数据库创建委员会,http://codh.rois.ac.jp/north-chian-railway/iiif/original/3704--23977-0.tif/full/full/0/default.jpg,访问日期:2022年9月19日。。中外多样的文字和图像文献为复建民国初期北京的中秋风情,尤其是理解至少延续到1930年代的月光马拜祭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除了大量民俗文献中的文字描述、极少数月光马的示意图和若干模糊的风俗照片外,作为拜月仪式主角的月光马原件却相当鲜见,不少相关研究(10)陈晨、邓环:《北京中秋祭月及月光码文化习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4期。只能去检索并综述囿于概述性质的“岁时记”,而对月光马本身的研究尚付阙如。
所幸明清以降北京地区的月光马,尚有少量传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北京卷”,收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版的月光马3张和王树村收藏的清代版1张(11)刘莹:《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北京卷》,武汉:湖北美术美术出版社、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41-144页。,很能代表北京地区月光马精细庄重的印制风格和当时流行的构图格套;亦有学者有机缘得见真迹并做了初步介绍(12)邰高娣:《北京民间年画中的“月光马”研究》,《民艺》2022年第6期。。图像文献为与文本文献的对照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两者的结合能为管窥当时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信仰的概貌提供帮助,有助于消解看图说话的任意与口说无凭的尴尬。但如果要进行历史学的详论和人类学的深描,图录所含的信息要点恐仍失之大略;止步于图像志解释,让原本活态的仪式必需品沦为民间印刷品遗物,恐又架空并虚掷了纸马这类特殊图像的圣物功能。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的捐赠者是美国人富平安(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女士,她年轻时旅居北京,“1931年我就到东四牌楼那儿的‘人和纸店’,买下了他们能有的每一张印品”(13)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A Look at Home Worship(Nettetal,Steyler Verlag:Monunmenta Serica,1991),11.。她笔录下当年对当地人的访谈,在她的专著《北京纸神:家庭祭祀一瞥》中结合中西文献,记下了每张纸马的图案、尺寸、意义与用途,这份几乎是前无古人的细致纪录,为这份藏品提供了人证与物证兼有的历史原真性,包括明确的藏品信息、收集时间、地点、经手人和使用者经验。“中国纸神专藏”中有月光马4款5张,与目力所及的图像文献相比较,此4款不论是在款式还是图案上,都涵盖了清末民初北京地区可见之品类,完全有资格成为典型性的独立个案。
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针对哥大“中国纸神专藏”中的月光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成为可能,并由此将会改变仅有文字概述和零散图像而难以展开确凿讨论的局面。比如:对1930年代的北京人而言,中秋节拜月时多用什么样的月光马?这些格套的流行说明了什么?它们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意义吗?换句话说,这些纸马用例仅仅只有艺术史上的价值吗?它们是否还具有历史学、民俗学乃至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意义?故此,从对这套月光马逐一进行图像学的阐释开始,本文将关注点扩大到它们更多面向上的综合性价值,聚焦其图案内部的所指关联及其对应于仪式组成部分的功能逻辑,厘清月光马如何承载并表达出祭祀者的愿望,并讨论拜月仪式在当初的社会规矩之意味以及作为文化传统对当下中国之意义。
二、“广寒宫”里的玉兔和观音
文字文献中论及月光马概貌者以《燕京岁时记》较为完整:“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棋,作红绿色,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一并焚之。”(14)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页。这段文字描述了月光马的图案、尺幅和使用方式。与彩图1比较,大略相类,可见民国初年的月光马确是沿袭前代刻板而来,结构要素较为稳定。然而,实际上的月光马却是一个符号极为繁复的综合图像,百姓对于日常祭祀用品的熟视无睹以及士人对于所谓民风俚俗的轻视,使得更详实的文字文献难见踪迹。富平安的《北京纸神》里有针对1930年代北京月光马的罕见细读,但需要评判性地分析她的断言,也需要审慎评判当代国人后续图录的阐释。
(一)神殿“广寒宫”
北京地区月光马的种类有少量为独体式,大多为分段式,最下面也是核心的部分,是“广寒宫”图案,即想象中的月宫形象。“月光马”也有被整体称作“广寒宫”者,本文为行文清楚,以“广寒宫”特指描述月宫的图案部分。它是月光马形制中的必选项,位于底端;为竖长方形,顶部中央由右及左一般刻有“广寒宫”三个汉字,以左右两条边线和底线为界,内切一个圆形,代表月亮。月中绘有程式性的三组画面,“花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1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玉兔身后以大朵祥云衬托令其凸显,执杵捣药、左向人立,成为月光马不可或缺的核心标识。
在圆形图案被切出的长方形的四角,广寒宫以多种图像语言彰显了其作为“圣境”之性质:下方的角落是相对统一的图样,绘有彩云拱卫着的海涛山峦,象征月神升降之所;而上方双角的图案则相对多样化,但都是以神灵之像加持,以示神界。
彩图2(16)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138.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2日。下半段的广寒宫图案的左肩为北斗七星,右肩为南斗六星,所谓“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中间是太极图案,这是起于秦、兴于汉,延及魏晋隋唐之道教礼斗之风的映像。彩图3(17)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185.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2日。中广寒宫图案的上方为四大天王,造型如佛教寺庙前四大金刚,《在阁知新录》中说,“凡寺门金刚,各执一物,俗谓风调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者顺也。”(18)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10-811页。。星转斗移、风调雨顺,对上天的祭祀及祈福是自然崇拜的基本内容。
彩图4(19)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186.html。另有一张同款可见: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187.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品中有两张同款,有可能当时较为流行,它的下半段是广寒宫图案,是双层复合的版式:上层的三尊佛像应为“华严三圣”,释迦摩尼托钵端坐中心莲台,左边是手捧经卷的文殊菩萨,右边是手托如意的普贤菩萨。最右是韦驮护法,最左护法是托塔李天王的形象。下层在圆形月宫的两肩各有4位仙官,他们究竟是何来头,还颇费思量,泛指星君的可能性较大。在法兰西学院藏品中见到民国初年“中法汉学研究所”搜集的以“广寒宫”独立成像的月光马,上端两肩各绘有6位男神,由此猜想月光马上陪侍星官的数量可能也有虚指的,“道教的星辰司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更加注重的是祈请的目的,因此可以依据不同的需求祈请不同的星神出场”(20)孙伟杰:《“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富平安为此请教过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专家安妮莉丝·布林(Anneliese Bulling),她推测这4位仙官是支撑天庭的四根柱子(21)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A Look at Home Worship(Nettetal,Steyler Verlag:Monunmenta Serica,1991),219.,但这极有可能是有关“四柱神煞”的误听和误解,反过来说明这些神像恐怕确与星命相关。
彩图5(22)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204.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2日。是四款月光马中唯一没有“广寒宫”字样的一幅,但神像的类型最为多元:第三段仍是广寒宫图案,其上端最中心是和彩图4一样的一铺三尊加两位护法式样的造像,只是在释迦摩尼身后添加了伽叶和阿难两位尊者,左右再环伺有四大金刚,属于神佛天团之加强版。
这些来源丰富的神像被组合刻印到“广寒宫”上,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而言,这些背景图像都已经被简化为了可识别的符号,不是借由象形去道明能指(即具体的神灵),而是示意性地去强调所指(即抽象的圣境),其用意是显明的:广寒宫是神灵之所,是庄严圣殿,是拜祭和寄托的人心之所向;当然也间接地反映出中秋节本就是围绕着月亮崇拜的多重叙事的合流(23)袁咏心、向柏松:《中秋节的多重叙事与合流》,《文化遗产》2020年第5期。,证明了在民间崇拜中道教、佛教和依托于神话传说的民间信仰实际上杂糅于一体的事实。
值得留意的是,在存世的许多月光马中,捣药之兔不过是嫦娥的陪衬而已,如孙家骥捐藏的《太阴皇后星君》和《太阴月光》(24)何浩天:《中华民俗版画》,台北:历史博物馆1977年,第20、21页。、王树村藏山东聊城的《月光》(25)王树村:《民间纸马》,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2页。,主角都是宫娥执扇簇拥之嫦娥;而在北京地区,“广寒宫”是众神簇拥的固定格套,兔子的图像是月光马上的焦点和重点。这个前景主体,是京派月光马的视觉符号;民间艺人制售的“兔儿爷”更是将北京月光马的这一标志性编码凸显到了极致。清代让廉在《京都风俗志》中说,“有顶盔束甲如将军者,有短衫担物如小贩者,有坐立起舞如饮酒燕乐者。大至数尺,小不及寸。名目形相,指不胜数。”(26)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在全国范围的中秋习俗中,玉兔如此这般的至尊地位,恐无出其右者,可视作清末民初的京派月光马之特色。
(二)月光菩萨亦或水月观音
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跌坐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也”(27)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清代富察敦崇说,“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28)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页。这些文字文献说明,月光马上除了有玉兔的广寒宫外,上端应该还有“月神”作为核心意象。佛道两说,各有依凭。在佛教传说中,兔子以身祭获得了佛祖将其转世到月亮上永生的奖励,月光遍照菩萨是药师佛的右胁侍,自然掌管着捣练长生不老药的玉兔;而嫦娥奔月神话,早在汉代就定型了嫦娥作为月神即太阴星君的地位。哥大“纸神专藏”中有2张构图近似的《太阴星君》(29)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025.html,另有一张近似同款可见: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125.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6日。(彩图6乃其一)单幅纸马,就图像而言,它们几乎是“广寒宫”图案的互文变体:圆形代表皓月,灵芝、兰草、祥云和海涛隐喻月神之永生及其月宫之神圣;所不同的是,兔子不是人立而是趴下,太阴星君凸显而出成为了画面的主角——她慈眉善目,面如满月,但并非“如菩萨像”,因为她头戴的“梁冠”是源自秦汉的古代汉族帝王大臣的礼帽,此类冠饰仅为道教神像或者民间神灵所常见。
《帝京景物略》和《燕京岁时记》所载明清月光马暂未发现完全吻合的图像文献佐证,但到民国这么短的时间就消弭于无形也不大可能。王树村藏清代开封纸马《月光菩萨》是较为接近《帝京景物略》的版本,但为方形构图,宫娥、月光菩萨、捣药玉兔,由左及右横向排列,左右对联为“敬天地风调雨顺,贺日月国太(“泰”之别字)民安”。(30)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王树村另藏内蒙包头《广寒宫》一张,疑似仿刻北京月光马而来,上下分段式,“广寒宫之上,画观音坐于莲座,前有善财童子,后有龙女合掌侍立。”(31)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下),第815页。自唐代吴道子、清代如山和丁延的绢本彩画,到清李丁氏的缎本丝绣以及王世英画刻石墨拓,善财拜观音,加上龙女或韦驮并以水色和池莲相衬的形象(32)中国书店:《历代观音宝像》,北京:中国书店1998年,第2、96、108、125、136页。,逐渐成为民间极为认同的观音视觉符号。哥大所藏彩图2中观音手持净瓶跌坐莲台,善财跪拜于左,龙女立礼于右;彩图5最上端的图像以怀抱婴儿的观音为中心,荷叶上立杨枝净瓶,左立龙女,右下跪善财,右上云端另有韦陀护法。两幅都是经典的观音构图。那么,有意味的问题出现了:明清北京月光马上的月光菩萨为何到清末民初会被观音取代了呢?
民间信仰的特点在于为我所用,并不执念于教派之制式及区别,将月神太阴星君绘成概念化的菩萨像,甚至附会成当时百姓热衷的与月亮相关的水月观音像,这当然可以视作明清刻版之遗绪及其变形,但也需要格外留意满清以佛教为国教、与汉文化相关的道教被抑制以及观音信仰彻底世俗化和程式化之大势。因而,这样的变异发生在清末民初作为帝都的北京,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哥大藏月光马中的观音像,应该就是这样的来由,玉兔的凸显和汉文化传说中的嫦娥的隐形以及观音菩萨的显身,是一体三面,恐怕是权力、信仰和习俗的博弈使然,文化传统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经由符号委婉呈现了出来,连月神也是经由借喻(玉兔)和隐喻(观音)才被曲折指代,但用月光马来拜祭月神,这一自然崇拜的本质,连同借用图像表达念想的仪式做法,并未改变。
(三)丰收节、团圆节与自然崇拜
月神掌控潮汐、指导农事,是农历年的凭依,是民间信仰中无可争议的丰收守护神。中秋节适逢秋收,够多够好的农产品提供了表达虔诚的丰富祭品,用以酬谢大自然尤其是月神的眷顾。此习俗至民国不变,蔡省吾在《北京岁时记》中写道:“临节,街市遍设果摊,雅尔梨、沙果梨、白梨、水梨、苹果、林擒、沙果、槟子、沙果海棠、欧李、青柿、鲜枣、葡萄、晚桃、桃奴,又有带枝毛豆、果藕、红黄鸡冠花、西瓜。九节藕、莲瓣瓜供月。西瓜参差切之,如莲瓣。”(33)王碧滢、张勃编:《燕京岁时记:外六种》,第233页。前列果品极言丰收之盛,“又有”二字之后则属供品之列,有兔子喜食之带枝毛豆、表示永生的鸡冠花,指向的是广寒宫中捣不老之药的玉兔;莲藕借喻月神之莲座(“九节藕,内廷供月例用”,乃帝都特有),西瓜更是切成形似莲座的莲瓣状,指向玉兔侍奉(从图像的角度讲是所标记)之月神。
“太阴星君的生日是农历8月15日,是丰收节;收获时节人们感恩于她,所以也是感恩节。感恩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祭品中最重要的是放在离月光马最近的月饼。”(34)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A Look at Home Worship(Nettetal,Steyler Verlag:Monunmenta Serica,1991),215.富平安从美国人过感恩节的家人团聚习俗,来理解中国人过中秋节的团圆风俗,以他者视角准确识得了“庐山真面目”。“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彻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3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以五仁月饼为代表,以分享丰收果实的形式,“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俗世幸福在拜祭月神的神圣仪式中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丰收,是大自然意义上的大团圆;团聚,是人伦社会的大圆满。北京纸马多为方形,以圆形来构图者稀少,仅有与天象相关的三种,即太阳星君、太阴星君(附月光马及其“广寒宫”)和星科,这本身就显示出其以稀为贵之属性;而以人世团圆的盛大仪式来热烈烘托者,唯有月神崇拜而已。大团圆,在中国人心目中之价值,由此可见一斑。以玉兔为核心意象,以秋收酬谢月神为主要环节,哥大藏品所代表的民国月光马,以历史进程中变化了的图像语言辗转宣示并导引了在百姓心中带有神圣品质的丰收节兼团圆节的仪式。
三、月光马上的娘娘和财神
除“广寒宫”的图案之外,哥大藏月光马的上部还有一到两段图案。与广寒宫的自然崇拜所表达的敬天畏神不同,这些图案表达的则是对俗世幸福的渴望。值得留意的是,当月光菩萨被描绘成水月观音时,一个隐含但重要的转换就已悄然发生了——酬谢的对象(感谢神已给予)变成了祈福的对象(请求神再赐予),中秋节的神性祭拜仪式由此带上了浓重的人性欲望的意味。
(一)娘娘
实际上,兔子以及月宫蟾蜍的意象都与生殖有关,关涉妇女隐私,加上阴阳信仰,北京民间长期流传“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这就使得原本就带有生产繁衍意味的丰收庆典仪式成了“女性专场”,被附丽了格外强烈的女性特质,“月亮是妇女的保护神,娘娘也是妇女的保护神,两者的结合使得这张月光马(作者注:指彩图3)对女性而言特别有神力。”(36)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A Look at Home Worship (Nettetal,Steyler Verlag:Monunmenta Serica,1991),217.
就当时的民间信念而言,“多子多孙,是中国人的大愿,甚至是最大的心愿。因此,许多人向神灵祈子。”(37)Henry Dore,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Shanghai,China:T’usewei Printing Press,1914),1.子孙绵长,宗族繁盛,成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女性权力与义务的因果交集,1930年代北京以纸马为信仰载体的娘娘崇拜系统(38)李明洁:《哥伦比亚大学“纸神专藏”中的娘娘纸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曾盛极一时,以天仙娘娘为至尊。彩图3的上方,正中持笏端坐的正是天仙娘娘,左右各有宫娥持羽扇侍立;两顶华盖之下,眼光娘娘手捧巨眼于左,子孙娘娘怀抱婴儿于右。纸神专藏中另有两张同款的“天仙娘娘”(39)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eastasian/paper_gods/collection/NYCP.GAC.0001.0005.html,访问日期:2022年10月23日。的单张纸马,也是这样的三尊一组构图。
(二)财神
财神形象出现在家族团聚的中秋节仪式中,明确表明了国人对尘世幸福的向往。“中国纸神专藏”中月光马上的财神共出现于2款3张。当然,彩图3天仙娘娘的脚下已经出现了盛满金元宝的“聚宝盆”图像。
彩图4的上段直接出现了两尊财神像:文财神比干左持如意,着青绿朝服;武财神赵公明右持利剑,着大红朝服;两侧分立胡人侍卫,卷须赤面;前设“聚宝盆”,内有珊瑚象牙等奇珍异宝。
彩图5是三段式,中间是关公“夜读春秋”的场景:关羽披甲侧坐,凝读几上《春秋》,左立周仓持刀,右立关平奉印。民间尊忠义仁勇的关羽为武圣人,是民间崇拜的财神,更是商贾之家的行业神;加上“关”“官”谐音,亦含财禄双求之意。与拜祭娘娘和观音的月光马相比,供奉财神的月光马上,兔神贴金箔以示神圣,彩图4和彩图5皆然,彩图5关圣的面部也被贴金,相对而言,无疑属工致之品种。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现实的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中秋节俗的变化更是明显。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40)萧放:《中秋节的历史流传、变化及当代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月光马是时事变迁敏感又直白的观念“试纸”,巨细靡遗地展示着与它们共同生活着的人们的品位和价值观。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有一张上端是“达摩渡江”图像的清代月光马(41)邰高娣:《北京民间年画中的“月光马”研究》,《民艺》2022年第6期。,达摩形象在民俗版画中极为罕见,恐为禅宗崇拜者所好;王树村收藏的明版北京月光马上端尚有“身着官服的文曲星坐于松下,前有魁星立于巨大的神龟头上,手执毛笔指向象征金榜题名的金斗”(42)Shuncun Wang,Paper Joss:Deity Worship Through Folk Prints (Beijing,China:New World Press,1992),148.图案,但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民国初年的月光马就连这样看似形而上实则功利的格套都不再流行了,月光马上唯有“娘娘”和“财神”二尊,几无例外,这倒是与民国香火极盛的北京东岳庙在岱宗宝殿两侧设广嗣殿和阜财殿两大配殿的设置呼应,反映出当年民间信仰中最大公约数之共识,说到底,民众为之劳碌不息的人生观内涵基本定型,不外乎多子多福与富贵荣华而已。
四、从月光马理解仪式中的纸马
纸马的研究若止步于图像学的描述,就可能导致将其混同于单纯装饰性的民间艺术品之虞。相对而言,月光马是纸马中较为精致繁复的一类,这与中秋节仪式及其诉求的丰富性相呼应;对月光马整体图像包括广寒宫及其娘娘和财神等图案的识读,有助于较为直观地显示祭祀专用纸品与民间信仰仪式之间相互依存的证成关系,从而较为全面地揭示纸马于当时、于当下、于民艺、于民心之价值。
(一)纸马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化
纸马大多是百姓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人生关节,按需去“请”的,因此因人而异;而“请月光马”则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的全民之举,它在1930年代北京中秋节庆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使月光马成为涂尔干意义上的历史性的“社会事实”。这种约定俗成的必须的“邀请”是拜月仪式化的第一步,意念中的月神通过月光马的“被请(‘买’的敬说)”,真实地现身于人间。
仪式化意味着有规定的程式。如上文所述,广寒宫的图案规定了祭品中的必选和可选品种,规定了供品的摆放位置甚至切割与分享的方式;而月光马上的其他神像,实则在反复泛指或实指“神的存在”。拜月仪式中最重要的行为是跪拜并许愿,都必须“面对神”,实际上就是面对月光马。仪式中的“眼神交流”本质上是对自我愿望的反省。既然神灵“看着”我们并准备倾听和帮助,我们就必须真切、诚实地面对自我的愿望。
“神灵的凝视”是中国祭祀艺术的传统构图,北京纸马作为古早的品类,基本上都是面向朝圣者的正面脸部特写。值得玩味的是,月兔只是月神的形象代言人,它只能侧身而立接受礼拜;而月光马上其他的神像本尊,则全部是正面形象。其他宗教的圣像艺术也有类似的造型,“中世纪的绘画,尤其是圣像绘画,主要是采取了一个‘内在观者’的角度。也就是说,所画的圣像朝向一个想象的、存在于被描绘的主体之中的,面向看画人的观察者”(43)B.A.Uspensky,“‘Left’ and ‘right’ in Icon Painting”,Semiotica 1975,13.1,33.。彩图3在这一点上有夸张的表达,上端的娘娘(包括宫娥),“在这些娘娘的衣服上都有黄色的、眼睛形状的补丁,中间有黑点。”(44)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A Look at Home Worship(Nettetal,Steyler Verlag:Monunmenta Serica,1991),217.它们和眼光娘娘手捧着的眼睛一模一样,是神注视着凡尘俗子的眼睛,无所不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图像化了的隐喻,即:神全身心地注视着你,你应该虔诚祈求。需要略作辨析的是,宋元时期的绘画中,卖眼药者常被画成“衣着具眼睛形象的”,“帽子上、衣服上、口袋上满著眼睛”(45)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357页。,但这张月光马上,不仅眼光娘娘而且所有人物形象上都绘有眼睛,其意义就有所溢出,暗含了无数的“内在观者”,从想象的神界注视着信众。纸马也由此把可望不可及的神灵拉到了人类的视线之内以及当下的意念之中。也就是说,仪式过程中的纸马,通过强调与神对视,为跪拜、祝祷等肢体动作赋予了精神意义,帮助人们达成了与神灵的交流。
(二)纸马与民间信仰仪式的特殊性
制度性宗教的圣坛,如佛寺和道观都是已建的、稳固的;而民间的神圣性却是临时构建的,这其中,纸马就扮演着神圣仪式的标记功能——“请”来的纸马作为核心元素,与祭拜所必须的针对性供品联合起来,迅速构建起人与神之间的当下关系场。中秋时节,月光马被张挂起来,一下子就转化了日常的生活空间和工作场所的性质,家庭、商铺和工坊由此成为临时性的拜月“圣坛”;而多变灵活的拜祭场所也需要与之相适宜的神圣标记,月光马的尺幅因此也有大有小。彩图2的月光马宽27.5厘米、高44厘米,适合小家庭使用。彩图3宽37厘米、高87厘米,彩图4宽45厘米、高84厘米,适合大家庭使用。彩图5是在整张纸上印制的,宽50厘米、高123厘米,这种全幅带关公形象的月光马,在祈财的同时表达了对商业公信的推崇,为商家首选。可见,民间拜月因地制宜、各家各样、常中有变,这些“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以月光马为标记的。与中秋节民间的拜月仪式相对应的,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大典,“考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46)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页。北京“夕月坛”建于嘉靖九年即1530年,位于紫禁城以西,设有神厨、钟楼、祭器库、具服殿等建筑。秋分亥时,主祭夜明之神,配祭二十八星宿等星神,以羊猪为牲。以宣示社稷正统、皇权威仪的祭月正祀,其时间、地点、仪礼都有一定之规,且是一成不变的。
月光马对于拜月仪式的时间、地点、供品和祈福目的的符号标记性,前文已有描述;而其作为仪式“开始与结束”的象征性需要着重提及。月光马的张挂,意味着临时祭坛的确认;而拜月之后,月光马的被焚化,则标志着临时祭坛完成了礼仪功能。礼成神退,临时祭坛在拜月时所强调的神人关系回调至原有工作生活场所中的日常人际关系,与亲友分享月饼和供品的环节才可以开始。没有纸马,临时祭坛如何建成?神灵何以降世?没有纸马,崇拜仪式如何进行?何以始终?由此可见,纸马的有无,成为神圣与世俗的界标。
五、作为价值观载体的民俗文物
上文对北京1930年代月光马的试读,并不只是“图说”历史,也不只是“见证”历史,而是希望可以看到纸马本身的形式意志,希望纸马透露出的过去时代的织理,成为超越文本历史的历史,能为今日所知。
(一)月光马与“记忆之场”
他者之眼往往能提炼出那些自我文化中被熟视无睹但深意存焉的事实。“由于月亮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是女性主导的,代表阴,属于水、黑暗和夜晚等女性元素,所以,中秋节是女性的节日,而且要在夜间庆祝。它当然不是最壮观的中国节日,但无疑是最浪漫的。”(47)Wolfram Eberhard,Chinese Festivals (New York:Henry Schuman,Inc,1952),97.这种天上人间的浪漫勾连,在月光马上得以充分呈现,所有的祭祀活动都是对它的反应、解释或者衍生。在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进一步说,在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中,“这种想象力的高度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古代民间传说复杂的象征意义。在一个比其他国家都有更长历史记录的文明里,许多有趣的古老的经典神话在中国代代相传,人们的礼仪和习俗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一点都不奇怪。”(48)C.A.S.Williams,Chinese Symbolism &Art Motifs:a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n Symbolism in Chinese Art through the Ages (Tuttle Publishing,2018),27.
仅以哥伦比亚大学所收藏的4款为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月光马及其所代表的中秋拜月仪式,是一个自我照应、自我生成的巨大的符号系统。这4款月光马,至少与“中国纸神专藏”中的以下5类纸马存在紧密且直接的关联,包括:财神(17款23件)、道教神祇(10款12件)、关羽(5款6件)、娘娘(4款5件)、佛教神祇(4款4件)和观音(2款2件)等,每一类图像都有若干因袭不变的稳定格套,早已成为民间信仰中权威性的视觉符号,而月光马的构图(即人物造型和组合配对)都是建立在与这些独立格套相互参照的基础上的,例如,彩图3的意涵,只有放在太阴星君与四大天王、天仙娘娘和本命星君及其各自胁侍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中,才能得以完整解读。
在这样的意义上,对所有这些包括月光马在内以及与之相关的图像的识读与印象,都属于国人有关民间信仰的“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种互动着的文化记忆甚至可以从记忆的反面即遗忘(部分遗忘)得以印证。“我们的民族记忆失去了鲜活的实在之物,这迫使我们用既不天真也不冷漠的眼光去看待它。曾经神圣的事物这么快就不复神圣,而且当前,我们也不会再去利用它们。旧的符号不再激起激进的信念或热情的参与,但它们的生命并未完结。仪式性转而成为历史性,一个曾经支撑我们祖先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事物的关系纯属偶然的世界。图腾式的历史变成了仅供评点的历史:这是一个‘记忆之场’(lieux de memoire)的时代”(49)Pierre Nora,Realms of Memory: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7.。在当下中国内地的城市里,月光马已经销声匿迹,人们似乎也已不知其为何物,但这一习俗还是残存在各种中秋节的细节里:月饼和水果仍是中秋佳节最受欢迎的食品和礼品;月亮、嫦娥和玉兔转移到月饼模子或者月饼盒上,成为最常见的装饰图案;人们通过微信等手机小程序转达月圆人圆的祝福。2022年中秋在青海、甘肃等地的调研显示,当地拜月时仍保持着将西瓜或者蜜瓜切成莲瓣状的习俗,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实际上是月光菩萨宝座的隐喻。意识形态的介入、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观念的更迭,都无法改变中秋节作为民俗大节的地位以及敬畏自然、推崇家庭价值的文化内核——这是世界华人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二)作为价值观载体的民俗文物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中的月光马为理解纸马在民间宗教仪式中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既纯粹又全面的典型案例。“因为对人的研究,其要义在于参与性,即必须深入人的意图、信仰、神话和诉求,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不与他们对话,而仅仅只是从外部去描述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那注定是会失败的。”(50)Ninian Smart,Secular Education and the Logic of Religion.(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8),104.通过讨论月光马的艺术形式(包括质地、形状、纹饰和文字等因素)与社会、宗教和思想的关系,将纸马回置于拜月仪式的原境中,纸马对信仰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双重建构功能得以彰显。
“在宗教信仰与实践中,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通过被证明是代表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能与世界观相适应以应对实际的事务,从而在智力上变得合理;而世界观被呈现为一种为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而特别安排的现实事务的形象,而在情感上变得令人信服。宗教符号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是隐含的)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基本一致,并以此相互借力维护了彼此的权威。”(51)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2017),96.月光马无疑完美地印证了格尔兹的这一论断。中国百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一种具象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并通过崇拜仪式得以充分表达与确认。这些图像创造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精神抚慰和指引,在记录民间生活伦理的同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道德支援。宗教信仰、社群生活和意识形态互为支撑,巩固了各自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历史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记忆由此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月光马作为中秋节“记忆之场”中的重要元素,以档案这样的物质形态,不可争辩地印证着一段历史、一段风俗的存在;而风俗,本质上是从社群生命的精神状态而言的,评价的是某个地方或某个时代的整体行动方式。因此,纸马的价值若止步于民间艺术品,显然是舍本逐末。那么,作为历史的残片,民俗文物的价值究竟何在?
就历史事实而言,月光马曾是祭祀活动的必需品,其可触可视的特征如色彩、尺幅和纹样,都在不断变化,这是思想转化的外化;它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去相信和实践,而不是纯粹为了感官上的赏心悦目。月光马在民俗社会中稳定的功能和象征意义,使其具有重要的宗教和伦理内涵。民间祭祀仪式中的艺术产品,本质上都是为了表明被祭祀者的象征意义或祭祀者的精神诉求,都是社会价值的物化媒介,是具有强烈社会规约意义的宗教、礼仪象征,因此是价值观的载体。从现实变化着眼,当民间信仰仪式本身残破消失之时,月光马从民俗用品转为民俗文物,不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们是曾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图像物证,而且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世界各地的华人每逢中秋,家人团聚、拜月祈福,祝祷风调雨顺、天人圆满,节俗的社会功能及所践行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今天,物质性的月光马已然是民俗文物,不再实际出现,但那些曾明示其上的精神诉求,仍顽强地延续着与中华文化特性直接相关的社会性、宗教价值和美学内涵,此时月光马就转变为价值观的信物了——隐含在月光马上面的、以图表意的日常感性和文化诉求,是从祖先那里承继而来的观念的依凭和契约,是文化身份的再次确认与代际继承。以往的历史是今天人们思想的一部分,这才是以纸马为代表的民间信仰仪式纸品成为文化遗产的无法被遮蔽的真正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