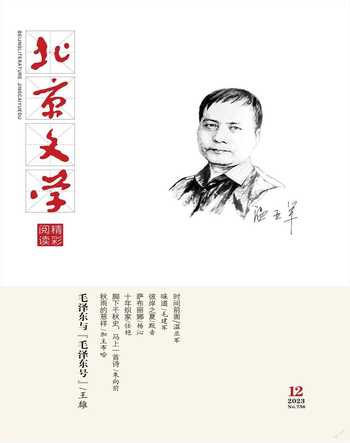在自己的身体里放养野兽(评论)
卢桢
我曾以“故乡”和“孤独”二词解读加主布哈的诗歌,就他的近作而观,“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象群组持续再现,形成照亮诗人精神内宇宙的又一道光。牵涉时间要素的句子,几乎潜藏于每一首诗的字里行间。作家静心潜入古老的时间内部,回到命运的源发之地,和先民一道诵念着祖先之名,小心翼翼地规避着由雷电传导而来的疾病抑或厄运。《寻根记》中,抒情者不断找寻着“不在场的根”,攀上“神话的阴坡”去探访祖先笃姆。《一场仪式》里,主人公“穿梭于浸湿的神祇”之间,从彝人的灵魂故地探求自我的文化身份。经由诗歌内部“复活”的一场场仪式,最终使精神主体锁定了文化的根脉。
詩人有如巫师一般,他掌握了时间的密钥,可以将轻盈的时空游动和厚重的文化寻根结为一体,为精神存在觅得栖所。面向日常性经验的“此在”时刻,加主布哈擅于营造经验之上的超验境界,凝神于对自我形象的独到观照。《晚风》中的“我”独坐山头,与自然为伴,和自我对话。他所停留的“山头”,在《自己的山脉》中得到更为细腻的形塑。抒情者笃信“我是我自己的群山”,要“在自己的身体里/放养野兽的野”。这句诗已然揭示了诗人的诗观,他刻意和琐碎的日常经验保持了显在的距离,而专注于运思自我的心灵时间,修缮精神空间内部的房屋。其屋门如同一面滤镜,亦如彝族文化中的“瓦萨”,日常生活的物象和古老族群的记忆透过它们得以过滤。留存在精神时光屋内的,是一个个缩小了的真相,是动物、植物、自然万象的神性彼此交融、相互转化之后诞生的感觉世界。在诗人笔下,“自己的身体”来自现实又超越了现实本身。深入它的内部,多见野兽、石头、风、火、雪等主题语象,它们同“我”一样,融合了兽性与神性,正是抒情主体的外化形态。
和直抒胸臆、靠事态化意象阐述情感体验的诗人不同,加主布哈经常采取远取譬的方式,架设多组意义奇诡的意象群落。雨水降临凡间、石头冥想未来、巫师诵念咒语、湖泊向世人敞开自我……种种意象的蒙太奇叠合交错,共同支撑起诗歌的梦幻结构。如梦似幻的段落间,分明又有一种情感向中心敛聚,使精神的能见度趋向澄明透彻。诗人畅想建立一个值得依靠的、稳定的价值空间,即使文本内遍布着各种流动着的不稳定要素,他还是希望通过对语言平衡力的驾驭,令“情质”和“形质”共生,达到人与诗歌互相成就、肉身和精神相互统一的自足之境。
作为生长在山脉之中的时间漫游者,加主布哈始终沿着心灵的路向,从内向型的写作维度出发。他一方面放逐了晦涩的意象和深奥的语词,以单纯朴实的笔调运思地方性诗学;另一方面则锐意强化着个体的文化想象力,以及对鲜活质感事物的超拔感知力。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开放姿态,持续为身体内的“野兽”输送精神的钙质,或许正是加主布哈的写作旨归。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