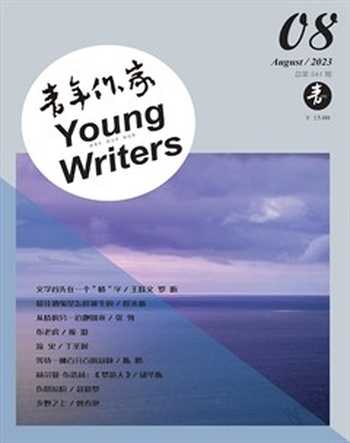田永刚 孙澜僖 袁丰亮 罗莉琼 权静宇 罗璐瑶
田永刚
对 谈
山顶的黄昏,还是有别于山下的
一个孩子爬上来,就长大了
他看得出高低、远近
能面对空荡的山谷和无垠之地
静静地坐下来
如果你在山顶遇见
那个观落日的背影
可以走上前聊上几句
命运煮酒,晚霞作餐
几声晚归的鸟鸣作曲
轻风能承担起种种无言之痛
待谈到了小城、街巷和前日灯火
最先说起梦境的人
一定也愿意傍山而居
那时候,人间已老,草木枯黄
而此刻,谈兴将尽,夜幕笼罩
登高之人,已没什么放不下的
若是可以
若是可以,不要记录重逢
相信我们还可以再遇
若是可以,不要赞美初见
所有故事的结尾都已昭示其中
我们还是要喜欢那个暗喜的自己
像爱过的你,像认真告别过的黄昏
时间是能拐弯的流线
每个曲折处,都会模糊处理
甚至会重新构图、定义
所以才有多少个这样虚惊的时刻啊
明明听见了声音
那处却空无一物
明明都在生命里
却静止得像记忆
孙澜僖
凌晨四点钟的鸟鸣
一圈圈 首尾相接
撞击厮搏 鸟鸣
叫出了一连串的阴天
寒鸦数点
我平躺在床上
谛听——
夜雨秋涨的
那个黎明
谛听——
酒意潮退的
那封书信的
回音
以笔为枪
三尺见方的光影中
我翩翩起舞 花拳绣腿
清醒 也梦了三场梦
肉身里多出块小小的骨头
无一处不滞塞 拥挤
饿
沉默
于是剔骨 多余的
冷暖我不念你
江河知道你
数年后 以何种身份
再见你
袁丰亮
长城视野
峭壁之上,长城的灰砖站成
旷世的留影
山野裸露弯曲的脊背
从前的时光守着方正的垛口
一些碎石、残砖,磨损的台阶
早已耗尽铁马勇士的冲动
旧城墙延续的版图和疆域
刻下象形文字的碑记
此时的松涛、风声、鸟鸣
汇成历史和现实的合奏
这龙腾的阵势
沿山形为我开辟新路
胜利者,为忠勇的灵魂祈祷
衰落者,为固执的自己铸造新剑
透过砖石灰蒙的视线
请接受云朵的投影,青苔的隐喻
用沉淀的文字抬升视野和高度
低头细数攀爬的台阶
今天,无论谁走过这里
都会记住那些壮志未酬的知己
镜中的现实
镜子能照出真相
也隐藏真相
镜子的魔法从有形变回无形
时间的印记只留存过去
苍茫的日月有多少风蚀和堆积
现实的征迹在风中隐去
生活有多变的色泽
只隔着一层水银的薄片
旧时的丽影
偶着浓妆
行程与行程叠加的印迹
在裸露的脸上显形
镜中的现实
也许藏在意外的纹痕中
有时,也是碎裂时刻的一声尖叫
罗莉琼
我听见鸟雀声
是的,我确定。应该是鹭鸶。它们从密林里或者溪水旁
传来的歌声,让脚下的石梯有了向上的冲力
让白云的翅膀有了出处。
你还在老鹰崖看落日怎样撬动天空的吗?
你还在为落日的盛宴激动而泣吗?你眼里的落日
是怎么跌进一首情歌里的呢?
黄昏被鸟鸣吵醒。体内闪电被岩石擦亮
它们打破惯常,直到打破夕阳
直到山谷拿出各种乐器,以及乐器之外的空寂
与己书
——天晴带伞。
中年的身体,外形:笨重,肥硕。内里:气血不足
若用放大镜,镂空处,布满蚂蚁巢穴。所以
钉子穿过骨头,连接钙化部分时,要遇雨躲雨。
再不要像年轻时,在雨中行船。中年的躯干
一小部分,已接近于泥塑。遇水易坍塌。要注意
河水高过堤岸时,就等时间,从脚踝处漫过
半生已过。不等花开了。不等鸟鸣了。不等稻草人
重新活了。马蹄已响,秋风已来。体内的阳春三月
需要鬓间雪粒擦亮。所以,亲爱的中年人
一半是山,一半是土
一半深入悬崖,一半扛着落日
权静宇
泸定桥
陡峭崖壁,湍急河水
把我从睡梦中赶出
站在大渡河西岸
一切那么平静
铁索冰冷隐藏多少热血
也诉说过往
无限地向她靠近
脚似踩着棉花
今夜我要大醉
去点燃那颗玲珑心
在道坞遇见自己
我把有趣的灵魂献给了
除自己以外的所有
却不知灵魂的制造器会反噬
黑夜告诉我
远方是唯一的修理工
逃离了钢筋水泥向远方奔跑
懒散的小马驹拨动了自然密码
雪山、草原、寺庙……
穿过胸膛打开心门
一点一点修补着
至少能让灵魂短暂的平静
与自己相遇
罗璐瑶
晚风吹
风吹麦浪
风吹往任何一页古事
看山南雨暗、山北风冷
看窗前的微風和不曾睡去的你
让哪一晚才能成为最后的夜景
正等晚风吹,吹入我的头颅
包裹着身体再次穿透我脚下的土地
我是我,我也成为一抔泥沙的部分
直到每颗沙粒讲完故事都要记录入册
反复翻阅日月沉沦,让往事复现
你看,这时间短得好像
一粒麦子从左到右的距离
岁首
春有朝露而立,大雾四起
像一朵云在白夜前酩酊大醉
像我蜷缩在被子里,一字一句缝补
织出诗意的雏形,给春日添置件外衣
许久不见。报春鸟潮湿的倾诉
将万物声声催促,站在枝丫俯视
季节的复苏开始与动静有关:
冻泉开始流淌,秧芽开始破土
一朵花与一朵花的竞艳
从第一波春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