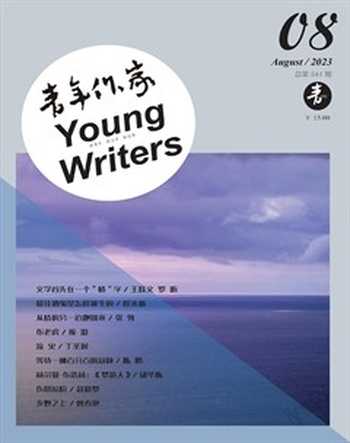故人故园
2008年秋天以后,我父母的家就搬到了西南大学校外,在原北碚文星湾大明纺织染厂旧址处新建的学府小区。他们奋斗了一生,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归宿,这一住就是十四年……
从我们家乘电梯下楼右拐,有两条路可达学府小区门口,一条是左边的车行道,一条从右边花丛中的小路穿过中庭,在大门口与车行道会合。大门左边的人行天桥可通校园内,一进校园就是西大出版社刚刚落成的新大楼,然后是曾经的美术学院(现在的管理学院)那栋非常别致的像城堡一样的老建筑。“城堡”的前面是一个美丽的小花园,有草坪、矮树、石雕、椅子……还塑着一尊孔子的雕像。从花园的右边走下石阶,再向右朝六号门走下坡去,在还未到门口的地方向左走上那个苍老的石阶,就来到了那棵青桐树的附近……这里现在是一块小小的休闲区,那棵树应该还在,嗯,应该就是那一棵……
刚才我领你们走的是我的一趟逆光之旅,大约也就四五百米的距离,耗时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分钟,然而顺着来时,我却走了四十年。没想到四十年就走了这么小小的一段距离,将来似也没有远徙的可能,年少时心比天高,志在四海,竟没想到此生大概会终老嘉陵山水,终老西师故园……
一
我在《西师的童年》一文中曾写到:“当年四新村的那些老居民楼也早已消失……”其实并不十分确切,我童年的房子确实没有了,但马路对面现在还剩几栋当年的老楼,它们看着比记忆中更加陈旧、衰败、安静,里面曾经有那么多亲切的笑脸和熟悉的声音,如今谁还住在这里呢?有些道路还见当年的开端,却找不到曾经的去向……故园并非灰飞烟灭,而是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似是而非,像极了我们现在的中年人生。就说六号门吧,还是童年时的那道后门,门口那个小小的传达室依然还在那儿,就是用几块水泥板子和一些砖简单砌成的一间小房子,小时候我经常进去玩……有一次父亲把家里一个不要的旧藤椅送给了传达室的师傅,传达室的师傅非常高兴,很长一段时间都看到他舒舒服服、趾高气扬地坐在那个藤椅上值班。我想如果要把这个类似临时搭建的传达室拆除,恐怕要不了两天时间,但它居然可以屹立几十年不倒!或许就是因为它太不起眼,太渺小了,学校里有那么多大事,谁也不会去打它的主意,它因此而得长寿,像极了一个饱经沧桑、惯看秋月春风的拾荒老人……
我的父母都是这所大学的老师,一个是书记,一个是所长。他们都是曾经的那个年代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讲奉献,讲大公无私。尤其是母亲,多年以后我才有所领悟,原来她就是焦裕禄,她就是孔繁森,她就是卢作孚,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无名的罢了……因为如此,父亲不仅要忙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还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即便如此,他还在经常忏悔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如母亲高!我出生那会儿,母亲还是辅导员,每天我还在睡梦中她就上班去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又已经睡着,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着她的面,就不認识了。后来突然有一天见到了,我疑惑地看着她,叫了声阿姨。其实父亲同样很忙,有一次他去外地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我也不认识了,开口叫他爷爷。
母亲上班忙工作,下班也忙工作,她和同事在下班的路上谈工作,走到分岔路口还可以聊几个小时。父亲叫她回家吃饭,她说马上,还有最后几句话,但这最后几句话又可以说很长一阵,于是父亲经常抱怨道:“明明就几句话的事情!”母亲对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极为陌生,有一次父亲叫她去买米,她就去了,一会儿空着手走了回来,原来没拿粮票,她又去了,又空着手回来,又没拿粮本(八十年代初买米必须的两件东西)……可见她从未买过米!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母亲担任学院书记期间,院里一位教师的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要说这种私事根本不在单位领导的职责范围内,但女方却经常来找母亲反映情况,倾诉感情。母亲来者不拒,经常一下午,一晚上地陪着她逗闷子,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没想到斗米养仇人,后来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未如她心意,就跑到我家来闹,也不管母亲还在吃饭,而且出言侮辱,最后忍无可忍的父亲将她一顿痛骂,轰了出去,从此便再也不来,这件事就这样荒诞地解决了。母亲对学生更是没得话说,几十年大浪淘沙,桃李满天下。有一次我的一位曾经的老师用一种颇为无奈的语气对我说:“你妈妈对学生硬是(重庆话,意为“真是”)好得不得了!”然而谁又能想到,多年以后学生们对她的每一句感恩和赞扬,都转换成了她对我的愧疚与忏悔……
由于疏于照顾,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再加上那个年代医疗条件较差,也许是在一次输液或打针的过程中被感染了乙肝。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这个病治不好,只能控制不让它发作,但对免疫系统肯定会有一定的伤害,因此对我是雪上加霜。就这样,童年和疾病总是牵连在一起,让我觉得周围的景物都有些阴郁黯淡,让我从小就显得有些深沉内敛。我爸还经常故意逗我说:“别的孩子都在太阳下跑来跑去地玩耍,就你一个窝在屋里吭吭地咳嗽。”重庆各个级别的医院都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给我看过病的名医也可以排出一个豪华阵容。那时候我对死亡逐渐有了一些感知,最初是有一天早晨,我从阳台看见对面坝子上停着一张盖着白布的床,周围一动不动地坐着几个陷入沉默的人……邻家的小元不懂事,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场景让他惊骇莫名,便四处嚎叫着宣传说:“这里死了人啦!”当然很快就被他妈撕扯了回去。接下来几天那儿就搭起了灵棚,奏起了哀乐,还能隐约看见有一盏幽幽的煤油灯……这大概就是我对死亡的最初印象,后来我去医院,第一件事就是古怪地打听太平间的位置!我中学时写过一篇叫《医院》的散文,我后来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看了以后惊讶道:怎么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在想这个问题呢?
在所有的医院中,我最熟悉,也最感亲切的是西师的校医院,它朦朦胧胧地被认为是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时的校医院十分简陋,就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很旧的黄房子,一楼验血打针,二楼看病输液……我曾有两次较长时间的休学,其中第二次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大医院住院治疗结束后回家休养,还须每天去校医院打针。那段时间我就成天独自一人往返于去校医院的路上,医院几乎每一个医生都认识我,有一次我偶然听见一个医生在我身后叹息道:“这孩子……”但我心里并不觉得苦闷,虽然远离了在学校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的热闹生活,但我喜欢校医院的宁静,和那熟悉的消毒水与青霉素味,以及来回路上美丽的风景……
在那个堪称豪华阵容的医生名单中,有一位姓陈的老中医让我至今难忘。他其实并非医生,而是生物系的一名工人,自学中医,颇有造诣,比医院很多正规医生看病效果还好,很多人都慕名去找他看病。每次我生病爸妈就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地放在自行车上,推着车朝他家走去。他住在西师后校门旁边的教职工楼里,开门的往往是他爱人,看见病人来了她只朝里面喊一声“老陈”于无论黑夜白天,陈医生都会神采奕奕地坐在他客厅的那张桌案旁望闻问切,自信地断病开方,挥笔在一张小小的处方笺上写出一些很难辨认的符号。陈医生的家非常简朴,墙上挂着一个永远在左右摆动的摆钟……他确实医术高明,几乎药到病除,对病人常有拨云见日之感!最关键的是,他看病分文不取!有一次过节我和母亲提了袋水果去表示感谢,他都坚决不收,正僵持之际,我一把抢过水果袋就往楼下跑,并生气地对母亲说:“人家不要你还鼓捣(重庆话,意为“非要”)送!”惹得他们都笑了起来。后来陈医生名声越来越响,终于被北碚的康复医院聘为了名老中医,找他看病的人更是排起了长龙,据说半夜都有人去排队抢号。多年以后一个和暖的春天下午,我在校园里散着步,无意间又走到了当年陈医生居住的那几栋房子周围,看见一个老人正静静地坐在一堆被丢弃了的旧家具中间,周围鸦雀无声……不知道陈医生还健在吗?还住在这里吗?回想起来,是他最早给了我对中医的直观印象,也为我建立起了对中医的信任。
当然我还得和乙肝做长期的斗争,但所有医生的结论都差不多:“半年复查一次,防止恶化,彻底治愈是不可能的,这是世界难题,除非……”说来也奇怪,我三十岁后身体倒逐渐皮实了,也仿佛越来越健康,2022年在一次单位的常规体检中,我的乙肝表面抗原竟然神奇地自然转阴,而这也就是医生所说的那个“除非”。那又是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拿到体检报告后,我在医院前面的广场上要了杯清茶坐下慢慢地喝着,感觉服务员和周围人们的面孔都充满了善意。温暖的阳光让我有些昏昏欲睡,几十年光阴,一幕幕往事仿佛都在空中穿梭……这世间的很多事物,包括某种疾病,有时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是一个谜,来得莫名其妙,去得无缘无故。我又想起我被查出乙肝而不能上幼儿园的那些日子,父亲就经常一个人带着我去离家不远的桃花山闲逛散心。那时的桃花山正在大兴土木,建居民楼,父亲别出心裁地捡了不少黄土,回家做成各种精致的车子、坦克、房屋……然后一排排地放在阳台上展览,陪我度过了那些寂寞的时光。而后来建成的那些居民楼里,住着多少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还有看着我们长大的叔叔阿姨,那些熟悉的平台、拐角、走廊又藏着多少昨天的故事……多年以后我才有所领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西师以及后来西大的校园,将注定成为我此生的桃源!
二
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不好说,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甚至有些单调。比如有七年时间,我都从三号门穿过那条叫水岚垭的马路,去下面的西师附小上学,又有六年时间,我又通过校园北面的一个围墙豁口去位于文星湾大桥北桥头的西师附中读书,十三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一段西师幼儿园的史前史,时间在那儿几乎是凝固的。西师幼儿园是大园中的小园,园中之园,我病情好转以后就去了那儿。第一天上幼儿园,所有的孩子一开始都呆若木鸡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老师们把早饭端了上来叫我们吃,只有一个孩子哆哆嗦嗦地端起碗来喝了一小口牛奶,又抖抖索索地把碗放下……從此我们开始在这里建立起对世界的最初认识,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斑斓的世界。一天一个叫支支的小朋友很得意地对我们说,他知道什么是“晚霞”!那是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支支在走廊上用手指着无垠的天空给我们解说着:“……这里是大晚霞,那里是小晚霞……”结果我还是没懂他的意思,我以为他指的那个树杈那儿就叫“晚霞”,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又把他拉到走廊上,指着树杈那儿说:“看,晚霞!”支支愣了一下奇怪地说:“哪有?”
我在《西师的童年》一文中曾介绍过西师附小那个非常小的校园,同样,时间在里面也爬得比蜗牛还慢,七年(含预备班)就爬了两次楼梯,从预备班到三年级是左边那栋老楼,四年级到六年级是右边那栋新楼,一年更上一层楼……在那儿学过的课程中,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恰恰是当初不怎么重视的音乐课。音乐课从不参加期末考试,当然更不会参加最终的升学考试,和语文数学这些生死攸关的科目比起来,它最“没用”,但却是给我们童年带来最多色彩与感情的课程……学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设在老楼的底层,每次我走进那间教室都仿佛进入了一个淡蓝色的世界,或许是教室那别致的窗帘营造的效果,让我从最初就感觉到,音乐永远是人类的一种梦境!教室里用的全是长条桌和长条凳,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成一排排。教室前方安放着一架风琴,它正在等待音乐老师的到来……音乐老师是一位姓邱的年轻女老师,她上课十分生动,热情似火,看得出来她热爱她的职业,把学生都当成她的孩子。她会经常拍拍这个孩子的脑袋,揉揉那个孩子的脸颊,带动大家全身心地融入到音乐的世界中……然而她身体恐怕并不好,有一次她说道 :“别看邱老师在你们面前活蹦乱跳的,回家就瘫到床上了!”
那时流行歌曲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平时唱的都是邱老师教的歌。尤其音乐课刚刚结束,甚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都会惯性地唱着哼着才学会的歌,颇有余音绕梁、缕缕不绝之感。到了五六年级,升学压力已经很大,我们每天早起晚睡,白天上学,晚上补课,但歌声仍未消失。记得有两个特别爱唱歌的女生,我每次在晚上去补课的路上都会迎面撞见她们,她们总唱着邱老师教的那首非常好听的《银色的马车从天上来》。几年以后,其中一个女生患白血病去世,香消玉殒于花季,只有那永不磨灭的歌声飘荡在过去,飘荡在现在,飘荡在未来的永恒时空中!
上了西师附中以后,学习负担就更重,竞争也更激烈了。早晨起来上学都是一路小跑,后来那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因为哪一步对应哪个坑哪个凼都已形成了机械记忆,就像高水平的按摩师一下就能精准地点到人体穴位,我上学的脚步就像打字机,也像行走的踢踏舞……那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考试分数和排名方面,慢慢变得不那么单纯起来。事情还得从小学高年级说起,当时我是校足球队队长,一天放学,突然有个隔壁班的女生跑来告诉我想送我一个足球,那时还很懵懂幼稚的我就问她为什么要送我足球?她就笑着说:“你要不要嘛?”我还是反复地向她追问送足球的原因,问了一路,最后球也没送成。后来那女生也读了附中,却不知为何“声名远扬”,成了众人眼中的“霉星”!没人愿意跟她说话,跟她一起玩,连看见她都要躲,做操的时候,她周围方圆几米以内都属于无人区,班主任为此事开过好多次班会都解决不了……我一直搞不懂大家歧视她的原因,就因为她成绩差吗?这能成为理由?因为她长得丑?感觉她也就是一个相貌很普通的女孩子,而且在我看来有些比她还丑的女的都在嘲笑她的丑……没人能够明白……在多年以后的朋友聚会当中,已经成年的大家回忆起这件事,多少流露出一些对她的愧疚与忏悔,有一位同学还说:“你们哪个敢说当初没有歧视过她?”他说的当然不确切,我就没歧视过她,我还知道有哪几位同学帮她说过话,有一位老师甚至说:“你们这样做比拿刀杀人还要可恶!”但后来我跟那女生也不熟了,她总是面无表情,很难看到她开口说话,每次遇到她我都善意地对她点头微笑,她也对我淡淡地一笑,能感觉到,她心里真的冷!此时她也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喜欢任何人的资格!
这样的事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它既有深厚的历史共性,也有独特的时代个性……我暂时只能说,在工具化教育的大背景下,在以考试分数为杠杆的应试教育体制中,教育的人本论在我们这一代依然没有得到落实,真正的人文主义教育也很薄弱……即便相比较而言,由于西师的人文底蕴,我的母校可能已经算是全国最人性化的中学之一了……
三
在重庆乃至全国,很多人都慕名“西师的园子”,慕名它的绿树成荫、花草掩映、区域广阔、鹭飞虫鸣。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得天独厚……西师的校园本就很大,2005年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以后,又将中间的一个五一所(一个军事研究基地)并了进来,对于一所学校而言,就简直大得难以形容了……每年寒暑假期间,学生们大都走了,整个校园出奇地安静、空旷!此时在校园里走着,很久才碰到一个行人,教室和食堂都失去了往日的热闹,零星有那么几个学生……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校园的空气也是一级的好!而这样的氛围到了晚上就更加浓烈,尤其是春节前后那几天,整个校园简直空寂无人,却又亮起了一排排的灯笼,挂起了一串串的彩灯,感觉西大的新年,在人间以外!记得我才到《红岩》杂志社工作的时候,编辑部集体去我家做了一次家访,当车行驶在宁逸的西大校园中时,大家都纷纷被这里独特的环境吸引住了,散文家吴佳骏率性地一拍大腿说道:“这里很好,适合安放思想!”他说得没错,有多少数不清的日日夜夜,我背着书包徜徉在空旷的校园中,看到哪个亮着灯光的自习室有空位就走进去坐下,然后拿出书包里装着的《西方哲学史》《小逻辑》《美学》《双城记》《时间的玫瑰》《北欧现代诗选》……身边是一起安静学习的年轻人,此时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窗外是行进中的夜,仿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大约有十年时间,也就是我从初一到研究生的成长阶段,我们家住在桃花山的文渊湖畔,就是我小时候生病父亲带我去捡黄土的那一带附近。我们家住顶楼,视野很好,周围绿树环抱,青山掩映,无论春夏秋冬,窗外都是一幅大自然的天工杰作、美丽画卷。早晨,还在被窝里就听见窗外大自然的声音,那是由各种鸟类、昆虫和蛙合奏的轻音乐,让人内心感觉特别空灵。楼下就是文渊湖,一块人工石上有西大著名书法家秦效侃先生题写的“文渊湖”三个字,还有文学家曹廷华先生写的《文渊湖铭》。湖畔垂柳依依,白鹭翱翔,时常有默默读书学习的大学生,有闲逸的对对情侣。在大学里生活居住,经常也能听见悦耳的歌声与琴音,有一次我突然听见楼下传来歌声,探头望见一个女生正在湖岸来回踱步,兀自地唱着一首王心凌的《羽毛》,她唱得真好,整个场景宛若一首情诗一样醉人……
余光中先生有“高楼对海”之吟,我这就算是“高楼对湖”吧。那时我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房间,只有几平米,紧凑地挨放着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柜还有一个小衣橱,仅可容膝而已,但只要关起门来便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小天地,不管外面是狂风骤雨,还是寒冬酷暑,皆无法扰我静思。又因为住在顶楼,小屋便有一种悬空之感,可载我宇宙遨游……
桃花山的夜晚孤独而寂寞,远远的几盏路灯默默地照着空旷无人的马路,零星的几家小卖部里透出灯光和人声,我从某个黑暗的角落走到另一个黑暗的角落,却又有无比的温馨和安全感。此时思绪也在黑暗与寂静中翻飞,看见一排黑漆漆的房子就想到《呼啸山庄》,感觉到一些奇怪的动静就想起《百年孤独》,那些历史和文学中的幽灵开始在我眼前闪现,在我耳畔漫语……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老师终生神往莫斯科,他说那里是真正的思想者的家园,他给我们讲到莫斯科的冬天被大雪覆盖,那里的人们仿佛精神哲人一般地思考着人与宇宙的关系……我听了以后心里想,不用去莫斯科,这样的感觉西大就有!
四
当然这样的感觉也是慢慢才出現的。我曾经是一个学习很用功的学生,对老师没有怀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们人生的价值与目标已被完全交给了学习成绩,我没有怀疑。这时我又遇到了那个曾跟我讨论过人生意义的小来,就对他说提高成绩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小来则说:“不对!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健康地成长。”后来我才醒悟,小来的认识比我高了不知几倍!他想得非常深刻,他不以学习为唯一目的却长期是尖子生,后来考上了北大。我把学习作为头等大事换来的却是成绩的不断下滑,中考一败涂地,还落下一身的病……老师本来是比较喜欢我这种学生的,因为学习刻苦又比较听话,他也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来,第一恐怕还是身体原因,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学习的负担与压力是逐渐升级的,过来人大概都心头有数,没有一个好身体是扛不下来的。我尤其受不了那种连续作战,因此越是到了初三高三就越容易掉链子!另外应该还有思维方法和习惯的问题,我和大多数同学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容易想到一边去……虽然我的记忆力特别好,但往往记住很多没用的东西,比如某年某月某天发生了什么事,和谁在一起,说了句什么话……要考的重要知识点反而记不住……
于是初三过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一片迷茫和颓丧中翻开了几本文学书籍……十五六岁本来就是一个少年人刚刚对这个世界敞开怀抱,拥有极强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年龄,虽然我们这代人的这种感受已大大减退,过早地受到了现实欲望的消解,但曾经的激情总会留下一些痕迹……由于阅读,我作文水平进步很大,并开始喜欢上了写作,又因为心态的放松,成绩也开始逐渐回升。一天,父亲从街上回来,甩了一本书在我面前说道:“你喜欢写作,看看人家都出书了,你要好好学习!”我低头一看,面前是一本《韩寒作品集》……当年我隔壁的小玉,此时已成长为附中文学校刊《年轻潮》的主编了,一天她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文学才华的同龄人,叫韩寒!不久后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就去小玉家跟她聊文学,聊韩寒,她像个迷妹一样地夸韩寒文章写得好,人又帅!我也觉得韩寒写作很有个性,跟我们写得都不一样。接下来就是自我欣赏和相互欣赏的时间,我把我的文章读给小玉听,小玉把她的文章念给我听,那天下午她屋里的空气,就像室外的阳光一样欢乐!然后我们又开始互相撺掇着看要不要去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
不久后我们迎来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叫张爱明。他本来是来临时救火的,因为上一任语文老师被突然调走了……当时的张老师还不到30岁,却来头不小,在附中已有“活字典”的美誉,当时无论哪个老师碰到我们都说:“这下教你们的是高手了……”张老师中等个子,戴着眼镜,微胖,总是一身标准的黑色中式制服,是一副最朴素的学者打扮。他的头发总有些凌乱,这跟他的形象也很配,上课的时候我同桌的女生便颇为仰望地说道:“学者!学者!”在我看来,张老师的外形和他的内心是高度统一的,也就是说表里如一,或者如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他学识渊博,谦和儒雅,深受中外优秀文化的熏陶涵养,更具中国传统君子人格的风范!我们今生有幸,能在青春与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使我们对人生,对历史,对文学,对学术,对信仰……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认识。
平时经常看见张老师手不释卷地在走廊上不紧不慢地跺着步子,嘴里念念有词,或是点着根烟独自在一旁沉思……他上课就是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从不需要那些张牙舞爪的“现代武器”助阵。上了他的几节课后我有所领悟,所谓“活字典”,关键在一个“活”字!张老师的知识储备固然比一般的语文老师都要高出不少,但如果仅仅是可观的知识量则只能成为“数据库”。张老师学贯中西,承接古今,博览百科,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各种知识典故他信手拈来,各种诗词古文他倒背如流……但他绝非卖弄知识,而是把渊博的学识都融入到他独特的教学中,常常新见迭出,妙语连珠,这都源自他善于独立思考。张老师的课同样情理交融,他善于讲故事,故事中饱含着他的生命情感。他讲他喜爱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讲屠格涅夫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人生,讲自己上大学时是如何受到李泽厚的影响,讲钱理群退休以后到处去宣传鲁迅精神……
然而,真正更大的收获恰恰还在课外。如果张老师觉得你还不错,他就会跟你多说点话,有时候甚至是在早自习上,他也不管学生要背英语或做数学题,经常跑到我跟前来好一通发挥,让我感觉到,原来课堂上的他不过是冰山一角!慢慢的,他开始讲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吐露自己的一些心声。他生于1972年,上大学是在九十年代初,他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与激情,给我的毕业赠言是引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多年以来,我与张老师都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正当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解了那个神秘的课外世界的时候,张老师又开启了新的课程……事情又得从好几年前说起,当时智能手机的时代刚刚到来,我们互加了微信。不知是谁给他拍的那张微信头像的照片,他叼着根烟很拽地站在那儿,这就已经和我们心目中的张老师形象不太一致了。平时他在朋友圈出语犀利,批判尖锐倒也很正常,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回复别人的一条评论写道:“你娃(重庆土语)不懂……”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显然颠覆了他在我心中的固有形象,这还是那位彬彬有礼、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张老师吗?是他变了?还是因为师生的角色关系使我对他了解得还不够全面立体?后来我们又多次相聚,感觉他对曾经的理想主义已不大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他看我迟迟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实在着急,便叫我要学会撩妹。我说您当年教我要为天地立心,可没教过我这个呀?……我们曾经经常交流读书与做学问,但近些年我再给他推荐什么书,或者一些新的学术观点的时候他已显得没有了兴趣,他竟然说他现在已不读书了。我纳闷地想他这么爱读书,又读了这么多书怎么就突然不读了?他只说:“不读了,越读越蠢!你进入到那个知识结构体系就会……”
我一直在琢磨张老师的心路历程,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余秋雨分析君子人格的文章时不竟眼前一亮:
在万般冲击中,君子还在。他们在伤痕累累中改变着自己,顺便也改变了“君子之道”。
他们当然憎恨那些冲击文明的暴力,但是被冲击的文明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他们不能不对原先自称文明的架构提出了怀疑,并且快速寻找到了那些以虚假的套路剥夺健康生命力的负面传统。因此,在艰难的生存境遇中,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撕破虚假,呼唤健康,哪怕做得有点鲁莽,有点变形,也在所不惜!
简单说来,他们走向了顽泼,成了顽泼的君子。
——余秋雨《走向顽泼的君子》
我认为顽泼的君子仍然是君子,而且比君子更真實,也更深沉!我开始意识到,像张老师这样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传统君子人格的知识分子那里其实有相当的典型性。鲁迅晚年就有明显的顽泼倾向。君子走向顽泼,其中仿佛存在着某种规律,而这样的人格走向当然也必根源于诞生它的社会文化土壤……
五
故园很大,无形的故园更大。多年以来,我都时常会与来自故园的友人在天涯重逢。
最早结缘的,是我高中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殷合伦先生,毕业于西师文学院七七级。高考我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殷老师对我说:“在重师我有一个同学叫董运庭,有机会你可以去拜访他。”后来上了重师才知道,董老师已在科研处及研究生处担任处长,行政工作繁忙,我们已没有机会听到他的课了。而当时在重师风光正劲的则是正担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周晓风教授,后来我了解到周老师好像也是西师文学院七七级出身,就又去向殷老师打听,殷老师说:“哦!他是小班的。”(由于同学年龄差距大而分了大班小班)后来又得知,文学院著名的酷评教授张育仁先生也是西师文学院七七级学生。我大学组织文学社团活动,曾针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专业特色搞过“中学语文怎样教”的讲座,为此联系过巴蜀中学著名的欧平老师,殷老师又说:“那也是我的同学!”研究生我考回西大,文学院院长刘明华教授、赵伶俐教授、余纪教授、李茂康教授,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董小玉教授统统是他们七七级。后来我又到重庆市作协《红岩》杂志社工作,作协散文创委会主任吴景娅老师也是他们同学。之前我又在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室实习过一段时间,在昆明市文联认识了著名批评家冉隆中先生,没想到一报履历竟也是——西师文学院七七级!您看,不过文学院的一个年级就与我有那么多结缘,一个学院有多少年级?一个大学有多少学院?更多灿若星斗的杰出校友的姓名,就不必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吧……我只能说世界真小,故园真大,故园以世界为疆,世界以故园为家!
此时此刻,我又来到了那棵树的旁边……在记忆里,我童年老屋的后院正中长着一棵高大笔直的青桐树,而眼前的这一棵已和记忆中的不太一样了。周围环境已大大改变,它还是它吗?几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离它太远,而那些故园的故人们呢?或许他们有的已经走得很远,却恐怕今生也走不出故园,这将是我们共同的宿命与叹惋。或许有一天,又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树下玩耍,他们又将从这里出发,拥有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与明天。
【作者简介】刘鲁嘉,生于1983年4月,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硕士。作品发表于《四川文学》《星星》《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刊;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