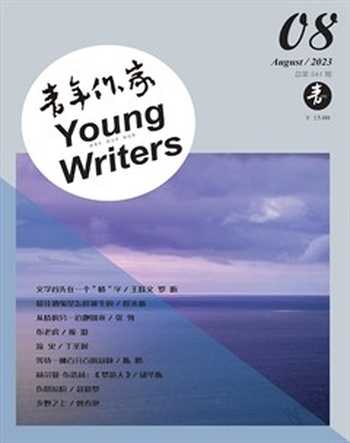知了
我正在路上走着,听到身后有人喊我的小名。日月市知道我小名的人不多,何况,既然是小名,就不是谁想喊就能喊的。这个声音腐朽而又陌生,腻歪得像个假音。我没有回头,浑身骤起一层鸡皮疙瘩。
“佳,我昨晚梦见你了。”那个声音在继续,听起来怪怪的,有些瘆人。
路上已经有人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不得不回头,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小跑过来,嘴里还冒着白气,站在了我的面前。由于距离太近,白气变成了口气,一种空心萝卜沤在泔水中的味道,逼得我不由得后退了两步。
佳,中年男人油腻的脸上溢满了惊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杰啊。
现在的人,怎么都变成了自来熟,为了达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目的,睁眼说瞎话都这么自然、理直气壮。问题是,你冒充谁不行,非要冒充杰?杰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他大腿根有个瘊子,他知道我屁股上有颗痦子,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属于烧成灰也认识的兄弟。眼前这个人,脸蛋圆圆、浓眉大眼的,模样倒是和杰有些相像,但也只是形似,离神似差了一个日月市。
“说吧,找我什么事?”梅在泾渭路的包间等着我,已经催了两次了。我有些不耐烦。
“你是佳吗?你没发烧吧,几天不见就跩成了这样?”中年男人气呼呼地,伸手要摸我的额头。
我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冒充杰的男人倒打一耙,竟怀疑起了我的身份,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事说事,我忙着呢。”对于无聊的人,我一向没有可贵的耐心。
“佳,你变了。竟然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年油腻男表情很痛苦。
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表演。
“你是佳吗?我的话只能对我的好朋友佳说。”男人继续痛心疾首。“我是佳,但不是你的好朋友。”
也罢,男人见我态度坚决,退而求其次,只要你还是佳就好。这时候,忽然刮来了一阵风,风里还裹着雪花,冷飕飕的。男人缩了缩脖子,又四周看了一眼,不知道在看路上的熟人,还是在看飞舞的雪花,问:“你知道梅在哪儿吗?”
我心里一惊,马上从男人的脸上觉得自己失态了,只好也看了一眼四周,把责任抛给了风雪。风缓了,雪却急了,顺着马路跑。马路尽头,是一家茶秀,梅正坐在一间叫“梅”的包间里等我。茶秀的老板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几行很雅致的诗。诗虽优雅,却不养人,只好开了个小茶馆藏身,除了卡座,仅有的四个包间分别以“梅”“兰”“竹”“菊”命名,以显自己文雅的“前身”。
“不知道。”我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的却是,现在关键不是我知不知道梅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这个中年油腻男是怎么知道我正走在和梅约会的路上的?
“这样吧,咱们有一阵子没见了,前面有个茶秀,我请你去喝杯热茶,去去风雪。”中年男人又缩了缩脖子,指了指马路尽头。
“你还认识梅啊?”我盯着飞舞的雪花调侃道。
“你没事吧?”中年男人一脸犯贱的样子,又想伸手摸我的额头,看了看我严肃的表情,放弃了,就是不认识你我也认识她,她是我老婆啊。
梅确实是杰的老婆,但不是他的老婆。现在的骗子都很专业,功课做得比参加“非你莫属”节目的应聘者还要到位。我不想再搭理他了,再拉扯下去就该暴露梅的行踪了。
风雪把人都赶进了屋,现在这个天还在外面行走的,都是在生活中留下了痕迹而又想“毁尸灭迹”的人。对于面前的这个男人来说,我要做的就是隐匿梅的痕迹。梅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招人喜欢,男人女人都招。不是因为性格,实在是她的容貌长得太招人了。虽然她认识的人有限,但认识她的人数以万计。我不再搭理他,竖起风衣领子,两手插兜往前走去。那时候,雪还没有在地上扎根,只是覆盖了薄薄的一层,青砖砌成的路面说白不白,说黑不黑,一副随机应变的样子。我前行的每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了黑黑的印记。茶秀越来越近,中年男人亦步亦趋。不能再往前走了,我突然掉头踏上了回头路。中年男人没有丝毫的犹豫,圆圆的身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继续一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后。看那样子,我要不说出梅的下落,他就会一直跟我耗下去。
手机响了,不用看,肯定是梅打来的。我加快了脚步,雪花变成了雪片,片片有力,迎风打在了脸上。
“电话响了,电话响了。”中年油腻男人紧赶几步,用背挡住了风雪,两只眼睛贼溜溜地看着我说,“佳,你的电话响了。”
我有些心虚地看着他说:“我听见了。”
“听见了为什么不接?”他紧追不放。
“和你有关系吗?”我绕过他,继续往前走去。
“不會是梅打来的吧?你让我看看,是不是梅打来的?”他又是一阵小跑,企图拦在我的前面。
从高中开始,我就有一个爱好,喜欢雪,更喜欢在雪天跑步。参加工作后,这个爱好慢慢地被散步替代了,不是爱好偏移了,而是气候变暖,很少能看见雪花了。今天,是日月市难得的雪天,是时候复习一下学生时期的功课了。我先是虚张声势地伸了伸胳膊,然后两只胳膊甩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回环,撒腿向前跑去。我在启动的一刹那,看了已经并肩的中年油腻男人一眼心想:你不是自称是杰吗,在学校的时候,杰可是一直和我并肩在雪地里撒欢的。
我是逆着风雪跑的,风撞在脸上,生出令我喜欢的痛感;雪片变成柔软的小手,熨帖在身上,说不出的舒坦。我全身的血液被激活了,迎风的脚步变得大步流星。前面是个十字路口,我在右拐的同时,看了身后一眼,止不住地笑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个胖胖的中年油腻男正在泛白的人行道上像乌龟一样地爬行。我甚至能看见他嘴里冒出的粗粗的白气,就像老式火车头上冒出的气体一样,即使他是杰,如今也变成轨道上的慢车了,而我是高铁,是动车。高铁和老式火车没有竞技的必要,我放慢了脚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另一条路向目的地走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梅是喜欢慢车,还是喜欢快车呢?踏着满地的雪片,我无声地笑了。
“梅兰竹菊”茶秀有个后门,连着我脚下的路。我本来是要走正门的,让中年油腻男一搅,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后门。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此时此刻对于我和梅的关系来说,走后门似乎更为合适。现在,我和梅只隔了厚厚的一毡布帘。梅在里面,我在外面。我知道里面温暖如春,我是踏着风雪来的。为了梅,即使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梅永远是一副揪人心的表情,她面前咖啡色的小茶杯上溢着丝丝热气,手机放在茶杯旁边,背部微屈,眼睛一动不动盯着桌面,不知道是在看手机,还是在看热气。直到我坐在她的对面,她才抬起了头,目光幽远得好似从远古而来。她明明在看着我,我却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到内容。幽深和空洞此刻那么奇妙地结合在她的眼睛里,使得她的整个状态慵懒而颓废。
“路上有点事,来晚了。”梅和杰结婚后,很少主动联系我了。这次突然打来电话,一定是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我生怕把她从梦境中唤醒,她此时的状态是我最喜欢的,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无助、迷茫、可爱、温暖、媚人。
梅的目光终于聚焦在我的脸上,她的眼泪蓄满眼眶,“佳,你知道吗?杰不见了。”她站起来,双手抓住我的胳膊。
按理说,这时候我不应该幸灾乐祸,但在心里,我却实实在在感到了一种意外的惊喜:这个结果难道不是我一直渴望的吗。杰早就应该不见了,从他和梅登记那天起,我的眼里就再也没有他了。最起码我的心里一直是这样祈祷的。
“什么时候的事?”当着梅的面,我表现得和梅一样焦急。
“一个多月了,他像夏天的知了一样在冬天消失了。”梅的表情很神秘。我的脑海里飞速地显现出那个中年油腻男,眼睛却快速地看了窗外一眼,仿佛那个油腻的男人正站在窗外。
我的目光没有逃过梅的眼睛,她侧身看向了窗外。一块巨大的玻璃横亘在眼前,上面挤满了水汽,使得窗外一片混沌。梅就在这一刻尖叫了起来:“佳,快看,知了。一只又大又黑的知了!”
我有点为梅担心了,现在是冬天,蝉是夏天的精灵。我用双手把梅按在了对面的布艺沙发上对她说:“喝点茶,你太紧张了。”
梅有些粗暴地打掉我的手掌,又站了起来说:“佳,你快看,知了的翅膀上还印着雪花呢?它正趴在玻璃上往里面看呢?”
一颗男人脑袋的轮廓出现在朦朦胧胧的玻璃外,两只眼睛圆鼓鼓的,眼球恨不能贴在玻璃上,猛一看,还真有点像知了的眼睛。这双眼睛和这颗脑袋,刚刚和我在风雪中较量过,他显然看不清里面的情景,正着急地努力着,一副不甘落于下风的样子。我凑过去往玻璃上哈了一口热气,那颗讨厌的脑袋和那双讨厌的眼睛一起消失了。
“知了飛走了,我们也该走了。”我笑着对梅说。我们是从正门离开的,这个名为“梅兰竹菊”的茶秀,以“梅”命名的包间位于最里面的位置,透过它里面的玻璃,能看见我来时的路。
泾渭路是日月市的主干道,仅单向就有四个车道,我拉着梅,急匆匆地穿过了斑马线,站在马路这边回看马路那边,“梅兰竹菊”茶秀在风雪中也显得有些模糊了,更别说那个矮胖的中年油腻男。我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甩开油腻男,在这条路边的一个小巷里,藏着一个心理诊所。从梅的种种迹象来看,她很有必要去那里坐坐。诊所的主人静是我的朋友,我想,她一定很高兴认识梅这个新朋友。
人如其名,静是个很安静的女人。她开这个诊所,好像不是为了生意,而是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寻找一个安身之所。所以,她的诊所门口既没有名称,也没有指引牌,她所有的顾客都来源于朋友介绍。诊所没有顾客临门的时候,她就把自己扔在厚厚的垫子上,让自己的身体肆意变形,做着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高难动作。我带着梅推开门的时候,她的身体向后弯曲,小巧的脑袋从两腿后面伸出来,下巴支在垫子上,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门口。我虽然不了解瑜伽,但还是知道这种反向曲身的高难度动作不是谁都能做的,它已经大大超出了瑜伽的难度,进入到杂技的范畴。
看到我身后的梅,静的眉头明显地皱了一下,脸色平平地问道:“有事,还是来找事?”
我把梅往前推了一把,“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认识一下?”
“没兴趣。”静又看向了门口。
幸亏是梅,也只有梅才不会计较。不但没有计较,梅围着静转了一圈,脸上全是兴奋的表情,嘴里不停地嘀咕,这样也行啊?身体得柔软到什么程度?梅蹲下身来对静说:“你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行不?”
“我的收费很贵的?你承受得起吗?”静保持身形不动。
“多少钱无所谓,但你得为结果负责,包教包会?”梅说。
我正不知道如何向梅解释,但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看心理闹成了学瑜伽。我喜欢这样的误会。
静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是那种简单的整洁。里面没有什么摆设,显得空荡荡的,使得不大的空间竟然有了空旷感。屋子里只有一种颜色,白色,是那种素白,和正在窗外飘舞的雪片一个颜色。梅似乎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白,已经像一只小鸟一样兴致盎然地满屋子乱瞅乱转。她身形轻盈,眉目含春,真成了我眼中的一枝梅,在满屋子的白色中翩翩起舞。
“她是心理上的毛病,还是身体上的毛病?”静碰了碰我的胳膊,低声问道。她已经把脑袋从两腿间撤了回来,一个打挺就轻盈地站在我的身边,目光却在梅的身上。
“丈夫失踪了,可能受此刺激,眼前出现了幻觉。”我小心翼翼地说。
“你还知道她有丈夫啊?你带她来是两肋插刀还是想趁人之危?”静不屑地瞥了我一眼。
静对我一直这样刻薄,我没有搭理她。
“还用治吗?出现幻觉不正好吗?幻觉中你就成了她的丈夫,不正遂了你的愿吗?”静不依不饶。
我从静的话里听出了转机。别看静的嘴损,专业却是一流的。
“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满脸期待地望着静。
“想得美。”静又撇了撇嘴,她的唇边有一颗小黑痣,撇起来很好看,除非你住在她的心里,而且从未离开过。
静的眼睛变成了一湖水,湖面上涟漪潋滟,包裹了我。我知道自己在她的面前难以遁形,只好实话实说,我在不在她的心里不清楚,她一直住在我的心里。
“上帝不会把诚实的人拒之门外”,静审视病人一样的目光里终于有了一丝笑意,“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静是个不婚主义者,一向对婚姻家庭不感兴趣,在她这儿,不存在道德方面的谴责和审判。我问她:“为什么?”
“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静看着站在心理学研究示意图前沉思的梅问我。
“原因多了,不想生儿育女,不想相夫教子,不想锅碗瓢盆……”我的手臂有力一挥,做了结论,总之一句话,不想承担一个女人来到世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静的目光从梅的身上移到了窗外,雪片像只无头苍蝇在玻璃上乱撞,静的声音像从门缝吹进来的冷风,一下一下敲打着我的耳膜。“如果找不到让我心甘情愿进入围城的人,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对家庭和婚姻忠诚。而不忠诚,是对共处围城里的人最大的伤害。”静的目光转向我,“你们都是信奉家庭婚姻的人,难道不应该捍卫他人的尊严和名誉吗?”
这真够讽刺的,一个发誓终生不进围城的不婚主义者给拼命想挤进围城里的我上了一堂关于维护围城尊严和名誉的课。我突然感觉到有些冷,这才意识到屋内没有开空调。我不禁缩了缩脖子,打了一个喷嚏。
脸颊上还留着汗迹的静拿起了遥控器,一边开空调一边还不忘教育我,“看见了吧,一个满头大汗的人是体验不到别人的寒意的,即使你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暖风在屋内攻城略地的时候,静用手勾了勾我,又指了指梅,小声说:“看见那张图片了吧,那张让她安静下来的图片上共有七个分类,分别是:生物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测量心理学,你知道她关心的是哪个方面吗?”
“难道你知道?”我觉得静在故弄玄虚。
“当然,她一定在琢磨认知心理学。”静的语气很肯定。
“具体说说。”我对她一直从事的这个枯燥的领域突然有了兴趣。
“所谓认知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比如感觉、知觉、记忆、语言和思维等,它是人类心智活动的‘软件结构和工作方式。”静看着我,停住了话头。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我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她的丈夫没有失踪,只是她认为失踪了。换句话说,她的丈夫属于被失踪,她想让他失踪。”静越说越玄乎。
“怎么会呢?”看着静一本正经又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雪片似乎飘进了屋内,变成水,一直飘进了她的脑子里。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未被满足的部分,时间长了,这种未被满足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潜意识就会促使当事人刻意地在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群中寻找,以代替现实中的人。她是,你也是。”静用手指着我。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突然不想让静给梅治疗了,我觉得再待下去就会被静扒光了衣服,我走过去抓住梅的胳膊一句话也没有说,拽着她就往外走。静动也没动,冷眼看着我气急败坏。倒是梅,一边挣扎着一边喊道:“我不走,我想跟着静学瑜伽。”
雪花小的时候,路上的行人稀稀拉拉的。现在,漫天飞雪,马路上的人反倒多了起来。每个人的脸庞都红红的,是那种兴奋的红。梅一看到雪,立马甩掉我的手掌,一头扎进雪地里。她呼吸急促,仰面朝天,满脸绯红,如一朵开放的梅花融入到人群中。我的眼前一阵恍惚,繼而看到千万朵梅花在漫天大雪中兀自绽放。
这时候,我突然闻到清新的空气中弥漫了浓烈的油腻味,紧接着中年油腻男迎面走过来,他显然已经看见了站在雪地中的梅。不知是什么心理,我下意识地躲在了临街门店前的柱子后。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梅和中年油腻男的目光穿过漫天的雪片聚焦在了一起,两个人都有些猝不及防。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会相信的。两双目光只在人群中碰了一下,就各自慌张地躲开了。两个本该熟识的人,现在却像陌生人一样在马路上擦肩而过。更为离奇的是,中年油腻男从梅的身边经过时反倒加快了逃离的脚步。如此虚幻又荒唐的场景让我感受到了被欺骗,就像一桶汽油遇到了火苗,我的火气被点燃了,几个箭步,便横在了中年油腻男的面前。
“佳,你在这儿啊,你看见梅了吗?”他惊喜地喊道。
我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贼喊捉贼的小偷。
“佳,咱们以后再聊,我还要去找梅呢。”油腻男躲开我的目光,也绕开了我挡在面前的身体,蛇一般在人群中扭动着走了。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直到看见他钻入了一个门面房——一个没有挂名没有指引牌的心理诊所。我的心里释然了,我知道他也是静的病人。病人总是令人怜悯和同情的。回过头,我看到梅僵在了人行道上,仰面朝天,任凭从天而降的白色精灵浸洇全身。
“该走了。”我在梅的身旁站了好一会儿了,见她没有反应,只好督促了一句。
梅低下头,神情紧张地看着我说,“佳,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梅说完,满脸期待地望着我。
“看见杰了?”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梅躲开了我的目光,“我看见一只胖胖的知了向我飞了过来,我想抓住它,路上的人太多了,它一下子就飞了过去,没有了踪影。”梅神秘地看了我一眼,把目光冲向了天空,“它一定飞到天上去了,被漫天的雪花埋葬了。”
实际的情景是,当知了从你身边飞过时,你都懒得回头看一眼它逝去的背影。我不想当面揭穿她,更不想听她胡言乱语了,不由分说地抓住她,把她拽向了回家的路。梅满脸的不愿意,一边被动地跟在我的身后,一边嘴里嚷嚷道:“我不想回家,家里只有知了,没有杰。我要去找杰……”
我站在楼下,看见梅屋里的灯灭了,才转身走开。雪片没有变小的意思,在路灯下愈发晶莹剔透了。路上的人们都回家去了,我却孑然一身地行走在大街上。积雪已经很厚了,踏在上面吱吱吱地叫,好像被踩痛了。我在雪花痛不欲生的叫声中返回到了静的门前。门玻璃里面虽然蒙了一层雾气,却难掩满屋的灯火通明。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果然看见中年油腻男坐在静雪白的沙发上,那神态像极了趴在透明玻璃上的一只胖知了,眼凸、嘴尖、腹黑、翅亮、浑圆。我没有搭理静,冲着中年油腻男说:“你不是到处找梅吗?走,我带你去?”
中年油腻男眼睛一下子亮了,就像灯光下知了的翅膀,“佳,你终于承认我是杰了?”
“你是不是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梅在哪儿。”我瞪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佳,别开玩笑了,我正在看病呢。你在一个淑女面前如此大喊大叫,很不礼貌的。”中年油腻男说。
“你到底去不去找梅?”我干脆把大喊大叫进行到底。
中年油腻男把脸上的最后一丝笑意留给了静,“大夫,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以后还会来找你的。”一边说着,一边拉开玻璃门溜进了雪地。等我赶到门口,中年油腻男已经身影全无,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也许,他真变成一只知了,飞到漆黑的天上去了。
我退后两步,伸手一拉,把头顶的卷闸门踩在了脚下,也把这个小屋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回过头,见一向矜持的静跟换了一个人似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还好意思笑,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在一起,也不知道自重。”我气呼呼地说。
静极力抿住嘴,用手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紧闭的大门说:“好像现在的情况比刚才更糟。”
“能一样吗?我们俩可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同学。”我继续气呼呼地。
“你是故意狡辩还是选择性失忆?”静说,“你不会忘了,梅和杰也是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在这个芸芸众生中,我们可是互相能喊对方小名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那也不行。我不允许你再和他们接触,尤其是那个胖胖的中年油腻男。”我自知理亏,气急败坏地把自己扔在沙发上。屋子里的光线在我的叫喊声中变得暧昧起来,静的身体偎了过来,两只胳膊搭在我的肩头,长长的眼睫毛在我的面前一阵忽闪,“多少年过去了,贼心还没有死啊?”
静的呼吸静静地喷在了我的脸上,透着一股干净的芬芳味,一直芬芳到我的心灵深处。我的心脏第一次在静的面前没有了节律,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和心跳,我继续大喊道:“你这个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独身主义者,你破戒了?”
静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两只耳朵,声调袅袅地说:“你给我听好了,我宣布,从今天晚上起,退出不婚者行列。”她收回一只胳膊,保养得像少女一样的纤细手指调皮地在我的鼻梁上一刮,脸上莞尔一笑,“知道为什么吗?世界这么大,我想去围城里看看。”
【作者简介】宁可,陕西岐山人,著有小说集《羊在山上吃草》《此处无声》《明天是今天的药》,长篇小说《日月河》《日月洞》等;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