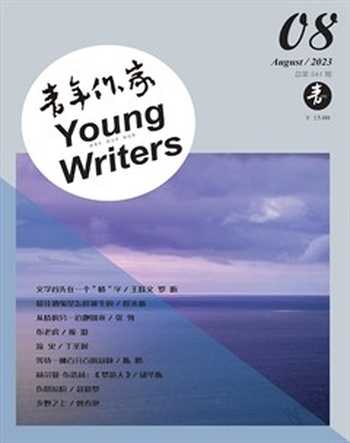走进同一条河流
一
如果一个村庄有一条河流,有一条像荆河那样,把宋家泊村半抱在怀里的河流,那么村庄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牲类,每一棵庄稼,背依河流的庇护,勤劳、生长、检点,遵循着村庄的品格和原则,从不打破一条河流和人类之间相守相在的默契。
村庄与河流,水土交融呀。一个女人却因为千百年来的风俗,从一个村庄来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条河流来到另一条河流,都是挣脱不开的命运。嫁一个好男人,做梦都会偷着乐;嫁一个二郎八蛋,一辈子都是一地鸡毛。
姥爷当过封家岭村长,当过浯河区区长,终因大字不识前程到此为止。母亲与父亲相识,难道是姥爷做的媒?父亲退伍后来浯河区工作。姥爷看中了父亲的哪一点?肯定是可怜他孤身一人。
封家岭老村,无独有偶被渠河半抱着。1974年发洪水,老村才从渠河沿上搬到206国道边。对老村,我只有模糊的记忆,甚至记不清姥娘家的门口,因为那时我只有6岁。秋末,所有的庄稼颗粒归仓后,空气里的味道有了一些改变,除了炊烟的味道,就是牲口粪的味道,如果还有就是风的味道,一股股粗喇喇吹来,村里的男人立马在家准备绳子、镰刀和小车,不用问,要准备收树行子了。封家岭总是捷足先登,我和大姐被大舅家的表姐提前一晚叫去,大姐是主力,我是凑热闹的。渠河滩比荆河滩宽,槐树、杨树、平柳、栗子、棉槐条子、蜡条,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植被,唯一多的就是一片片的细荻,淡紫淡红的荻花,在渠河的水声里飞舞着。荻秆收回去做箅子,荻花塞到棉鞋里取暖,还有拿回去做枕芯的。
每一个女人不过被动地按照祖辈的生活方式生存下去。17岁的母亲从渠河边上的封家岭,嫁到荆河南的六爷家,据说是用父亲给的高粱换回了我的大妗子,这样说,姥爷就不是单纯可怜父亲,他内心里同样隐藏着贪婪,当然更多是无奈。和我爷爷是亲兄弟的六爷,招赘到一河之隔的曹家泊,同意母亲进门,同样是因为粮食,还有父亲那点退伍金和寡淡的积蓄。当时部队给了多少粮食,主人公早就远去,很难搞清楚,再说能有多少呢?
姥爷也许觉得对不起父亲,给他们准备了回宋家泊盖新房子的梁檩木料,六奶正好借此给大叔盖了新房。当父亲的粮食财物和母亲的陪嫁完全被六奶据为己有,六奶就不是原来的六奶,她的心变了颜色,只要到了饭点就骂骂咧咧,若是父亲不在家,只要母亲拿起一个地瓜煎饼,就会啪的一筷子打掉原本在姑姑手里的饭食,指桑骂槐。母亲在晚上点着煤油灯想做点针线活,六奶躲在母亲的窗户下学鬼叫,直到母亲吹了灯吓得蒙到被子里。黑暗中,母亲瑟瑟发抖,冰凉的土炕上,她做梦都想回自己的老家。
也许荆河是母亲回家的唯一通道,每次来河里洗衣裳,母亲都会痴痴地望着对岸,它延伸着母亲对生活最大的希望。滴水成冰的冬天,父亲去城里开会顺便回家添件衣裳,看到母亲瘫坐在石磨旁,她从凌晨两点就起来独自推煎饼,她的双脚早就冻成了木头。他把她抱到炕上,把她的脚放到火盆上,她已经感受不到热度了。无尽的绝望,像一波波河水,从母亲的心里涌出来,回宋家泊吧,至少有老少爷们帮衬着。
二
清晨,太阳从荆河的水面上掠过,水鸭扑棱棱飞起来。尽管母亲不知道荆河从哪里来,但姥爷告诉过她,荆河和渠河最后是汇集到潍河去的。仅这一点,就让母亲哀愁的面庞上露出笑容来。终有一天,她和她的亲人都会在潍河集结。父亲和母亲,都会变成荆河的守望者。
村里人提起母亲,才多大呀,就受了这么多罪。他们刚回宋家泊时,借住在和猪为邻的放置犁耧耙具的闲屋里,说是屋,其实就是一间敞棚子。母亲不当回事,过日子还有不受罪的?只要能有自己的家,吃再多的苦也值当。
准确地说,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夭亡的两个都是女孩,父亲也算奇思妙想,给第二个女孩起名“女”,“女”是我们姐妹中长得最俊的。她俩都被扔到荆河的荒阡子上,母亲只要走近,就会听到小孩的哭声。两个孩子在母亲的岁月中,长成了刺,长成了流动着的水。
几年后,一个我叫叔叔的人偷走了父亲的残废证,这个叔叔没有爹娘,多数时间在我家吃住,他偷的不是残废证,而是夹在证里的十几元钱。父亲被撤掉贫协主席,有人上告说他是假党员……痛苦的父亲溜达到荆河边,河水哗哗流着,发出空洞的回响。我很难把父亲与自杀二字联系起来,他在我们眼里太坚硬了,就像一块石头。母亲告诉我的一个细節,又让我对父亲的坚强产生质疑,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他“假党员”,哪里都可以假,唯独党员要一尘不染。他决意去闯关东,没有钱买车票,就爬火车,却摔下来跌断了腿。回来母亲都没认出他,满脸灰尘,棉袄破了几个洞,棉花向外翻卷着。
有一段时间,父亲迷上赌博,家里仅剩的半斗高粱都被赌伴收去。母亲抱着大哥回到娘家,姥娘给拾掇上吃的用的,让小姨送回来。他一个孤苦孩子也不容易,从小参加革命,被人说出假来,心里能是个滋味?小姨送了一次又一次。她的一句话掷地有声,没有恁姥娘,你们这些小子还不一定来世上走一遭。从父亲的身上,我再次验证了浪子回头金不换说得在理,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勤俭、守时、悲悯,做事做人都有原则。
我从小就是个喜欢幻想的女人。经常在荆河北崖,勾画出三间茅屋,院子里种植着夹子桃花和石榴树,我和他坐在石凳上数着荆河上空的星星。要是哪天我被父母挨整,就添加上一条小船,和他一起沿着荆河出逃,我俩一个坐在船头,一个坐在船尾,船上挤满各种声音,水声、鸟声、芦苇摇动叶子的声音,小麦拔节的声音。其实,我最怕的就是母亲的喊叫声。
三
我太喜欢回忆了。回忆可以说是我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的现实世界,有时是一块破碎的玻璃,有时是一句说不口的话,这句话或许会让我的人生翻个个儿。
若把人生比喻成一口井,尽管我只看到巴掌大的蓝天,却把念想放飞了出去。每年我都要回老屋几次,那两扇老旧的木门,手刚摸上去,眼泪就出来了。父亲母亲的手、哥嫂姐妹的手、邻居的手、那只黑狗的爪子,还有那只花猫的爪子、小毛驴的蹄子,包括家里的每一个物件,都从这扇门里走出来又走进去。推开门,满院子都是父母的气息,只要这个老屋还在,他们的气息就在。
土从墙上落下来,木格子窗户只有住过这屋子的人还能看出蓝漆的颜色,屋山墙裂开一道道大缝。我摸摸我们用过的桌子,摸摸母亲用过的风扇,从东屋走到西屋,恍惚间,耳边吹过母亲如羽毛一样的呼吸。二哥喊着,你怎么敢进去。老屋若是倒了,我的心就该彻底流浪了。
父亲十三岁那年,在荆河边遇到一支带枪的队伍,同行的小伙伴都吓跑了,只有他留下来,给队伍指清楚要去的地方,从此,他就与队伍建立了联系,成了县大队通讯员。甚至可以说,荆河在某个节点,把父亲推向一条光明的道路。1946年的宋家泊战役,因寡不敌众,在得到命令时,父亲和几个小战士借助荆河树林的掩护,安全撤退。县大队和区中队,有多名官兵牺牲。每次来荆河,父亲蹙起眉毛,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在他的心里,一直活着。
我家的几块地都在荆河滩上,凭父亲的“干部”身份,是可以选好地块的,当时母亲没少发牢骚。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父亲对荆河的感情。那些回忆,包括奶奶渡过荆河改嫁的辛酸,在父亲的光阴里,都是痛呀。
每次写到荆河,才觉得自己最像父亲,他倔强的性格遗传给了我,最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父亲在一块田里从不单纯地种植一种庄稼,要么种两种,要么种三种,地头上还要埋一些爬豆、红豆种子。地里出现最多的往往是母亲的身影。我高中毕业那年,南河滩上种植着花生、地瓜;东河滩上种植着玉米、高粱、大豆。秋假里掰玉米,一到天晌,母亲就让我回去做饭,吃了给她捎点来。这是她一贯的做法。我竟然一个人回了家,留母亲在满坡的玉米地里。收玉米的季节太阳多毒呀,玉米叶子刷拉刷拉,划在脸上像刀子。等我捎饭回来,母亲的脸晒得通红,咕咚咕咚喝下半壶凉开水,地上摊着一堆堆黄玉米。
多少年后,母亲在我的梦里穿行,荆河滩上的玉米也在我的梦里穿行。
四
儿时的荆河像童话。春风刮过田野,荆河的精神从内里迸发出来。布谷鸟抑扬顿挫的叫声回荡着,慢慢地,布谷鸟的叫声从荆河滩去了村庄,人们传送着,该播种了。河滩上叶子细长、叶廓上带一丝红边的“簸箕柳”,随着布谷的鸣叫,鼓着劲长。孩子们掐下来一截做成柳哨,柳笛的声音把春天所有的繁华推向高潮。大人采了簸箕柳嫩芽,揉捻、炒制成簸箕柳茶。麦收时节,家家会烧上一大锅,用水筲挑到地头,茶香麦香搅合在一起,人们在烈日下挥着镰刀,喜上眉梢。母亲总会在荆河滩上找到大片的篷子菜,回家焯了,用蒜拌着吃,有时也做成菜饼。篷子菜吃起来,有点生硬的感觉,母亲却对它情有独钟。
荆河滩上的百草皆可入药,哪个孩子不舒服,母亲挖来芦根、车车菜、婆婆丁、野茄子,熬水喝下,孩子又活蹦乱跳了。她把莎草的根茎挖出来,用火燎去根须,晒干收藏起来。庄里的女孩月经不调,母亲让她们配着艾叶熬水喝,喝下去肚子也不痛了。她一个普通农妇,竟然从大自然中找到中医之道,都是被孩子多逼出来的。
到了夏天,香蒲、水葱、芦苇、薄荷、荇菜把荆河围起来,孩子们泥鳅一样在河中心游来游去,用小抄网就能把鲜活的鱼儿打捞上来。母亲们在河边洗着衣裳,喊着小心呀,小心呀。从东河拐个弯,南河里的水流子相对细一些,在父亲的陪伴下,半个钟头就能拾一水罐米蛤蜊,拿回家洗净,打鸡蛋做汤,鲜美的味道会飘满半个村庄。端午节,从荆河里摘一抱苇叶,家家都包三角粽子,即使放进粥里几片,浓浓的粽香也会让你立即“崩溃”。母亲总忘不了将香蒲叶子和艾草一块放在屋檐下,说可以辟邪。盛夏的早晨,荆河滩被一层层的水雾笼罩着,低矮的灌木丛边,到处是找幼蝉的孩子,回家的时候,长硬翅膀的蝉兒吱吱叫着。
秋天的河水总会变瘦,那些香蒲却蔓延成一片海。水鸟从蒲根处钻出来,天空绿得发亮。冬天的河水才真正安静下来,槐树、柳树、杨树、榆树掉光了叶,任凭人们欣赏一棵树的骨感。这个季节,对于母亲来说,是种煎熬。大姐经常瞒着父亲,和村里的一个姐姐去东河拾干树枝子,树行子那时是公家财产,掉落的树枝也不能拾。可烧火柴又是燃眉之急,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钻进树行子搂草,拾树枝。
母亲担心两个女孩害怕,站到东岭上唤狗。一声声“乖、乖”,叫得刺耳。
父母是如何把我们兄妹六个养大的?捉襟见肘的日子,他们能受的都受了。他们永远是我的榜样,遇到难事,我从来没想自己是个女人,只想到我是一个母亲。
父亲去世那年,经常说一句话,人啊,死了后还得去荆河趴着。一个病痛到身心不能忍受依然不喊一声痛的人,照样没有做好面对荆河的准备。荆河,在父亲心里,不单单是一条河了。
父亲走后十一年,母亲也葬在了荆河边上。他俩汇合,让我坚信,荆河是生命的解码者。天地一体,荆河流淌成一条看不见的线,连着父亲的命运,连着母亲的命运,甚至连着我的命运。此刻,在我毫无察觉间,荆河波涛汹涌,父亲母亲长成了河水,从荆河,一路向北,汇集到潍河里。
【作者简介】宋兆梅,山东诸城人。著有散文集《老家》《在时光的身后》,长篇小说《相州王》《古琴》,传记《王愿坚》《李仁堂》等,现居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