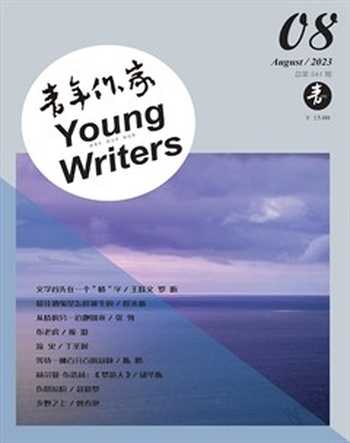伤心凉粉
我认识凉粉的时候,只知道它是用来吃的。直到走进古镇洛带,我才知道,原来凉粉还能用来伤心。然而,从知道到明白,竟用了我在成都落地生根的二十多年光阴。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大学毕业时意气风发的青葱少年,如今已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大叔。唯独那一碗伤心的味道依旧如同初恋,每一次吃,都觉得十分特别。
“伤心凉粉”,只有在洛带吃才能伤心吧。每年我都会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以至于不用导航也能准确找到古镇最靠近步行街口的停车场,即使今天已有多条快速路从成都市区通到洛带古镇。
一
“哎呀!”
“哎呀呀!”
“哎呀呀!……”
“啷个恁改辣!(四川方言:意为怎么那么辣)眼泪水都给我辣出来了!”
“辣吧?辣就对了!不辣咋个叫伤心凉粉!”
那一年夏天,当我们在洛带广东会馆回廊的阴翳下,第一次吃到“伤心凉粉”,家人朋友全都辣得大呼小叫,甚至双脚跳。关键是作为重庆人,尤其是嘉陵江边吃火锅长大的几个男人,自认为吃辣还是有几分本事,但在普遍以麻为主的成都平原,第一次被一碗凉粉辣得直冒汗、直掉泪,很伤心。
这碗凉粉看上去与其他凉粉并无二致,碗里白色的粉条上,淋上一层火红的辣椒油,洒上芝麻、香菜等配料,白里透红,红里透绿,往嘴里送上一口,有人就开始吼吼吼地叫起来,然后是双脚跳起来,汗水泪水把最矜持的女同胞们也搞得面红脖子粗。然而,越辣越想吃,越吃越过瘾。等到全身大汗淋漓,嘴巴喉咙毛孔甚至心肺全都最大弧度打开,有种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感觉时,再来一碗冰粉或者冰镇酸梅汤下去,整个人就变得彻底通透,别提有多畅快和难忘了!
妻子说,原来“伤心凉粉”就是辣得伤心啊。
岂止是辣得伤心。简直是辣得触目惊心。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场景如同电影胶片,就在眼前。
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吃过这碗凉粉的人,都记住了它独一无二的名字,也记住龙泉山下那个叫洛带的古镇。后来我向山西来的诗人朋友介绍这座古镇时,煞有其事地端出这碗凉粉,然后不容质疑地告诉他,认识洛带,必须从一碗凉粉开始。
美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地理之间、甚至人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中国人说到吃,脱口而出便是“民以食为天”,从孔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到《尚书·洪范》八政之首曰食,千古农耕为饱肚,人们历来把吃饭当作头等大事。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为了一口吃的,长时间远距离游荡在大地上,到人类慢慢驯养动植物来保证肚皮不挨饿,再到温饱之余有了精神娱乐审美需求,唱歌跳舞酿酒祭祀。
二
现在,对眼前这碗凉粉,和卖这碗凉粉的老板而言,仿佛又回到了它和他的出生地。老板姓陈。他说他的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一带跋涉而来的客家人。原来一碗“伤心凉粉”的背后,是一条路的艰辛。
客家是一个古老的民系。客家这一称谓,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称为客家人。客家人作为汉族的分支,是汉族民系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也影响深远。
郭沫若曾在《我的童年》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是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据考证郭沫若祖先原居福建宁化县龙上下里七都,即今宁化縣石壁镇石壁村。1939年,郭父去世,他在《先考膏如府君行述》一文中自述:“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今乐山市)铜河沙湾镇。”由此可知,郭沫若祖先应于1781年,即清乾隆四十六年自宁化迁入四川。此时,正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后期。
客家先民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至宋逐渐南迁的汉人在赣江、汀江、梅江冲击而成的三江平原上形成了客家民系,发展成了赣州、汀州、梅州、河源、惠州、韶关、深圳等客家主要聚居地,成为汉民族八大民系中重要的一支。为与当地原住居民加以区别,这些外来移民自称是“客户”“客家”“客家人”。
历史上,客家曾有六次大规模南迁,其中第四次迁徙,发生在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随郑成功到了台湾;有的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据统计,全球约有8000万客家人,其中约5000万人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海南、湖南、浙江、香港、澳门、中国台湾等地的180多个市县,约3000万人散居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孙晓芬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一书称,现在四川定居的客家人有两百余万,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客家移居四川的人数,占当时总移民数的第二位。
厘清这段历史,我忽然又有了新的发现和疑问。那就是,在“湖广填四川”这场影响清代四川历史乃至今日四川民情文化的移民运动,无论是官方还是当事人,他们用的不是“移”字,也不是“迁”字,而是一个“填”字。
一字之别的背后,到底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这不能不说汉语的神奇与伟大,在强调表义功能的同时还能强调状态和程度。“移”和“迁”的字面意思都差不多,“迁徙”“转移”“挪动”“改变”“转变”“变动”,仅表示移动状态,而没有字面意义背后的为什么“移”或“迁”。但“填”字却不一样了。“填”的字面意思是“把空缺的地方塞满或补满”,如填塞、填补、填充、填空。很显然,需要“填”的地方出现了巨大缺口或亏空。
循着这样的逻辑,我在清人魏源的《湖广水利论》中,终于看到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由来:“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兵燹之灾。从崇祯六年(1633)张献忠首次入川攻克夔州等地算起,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平定吴三桂叛乱,战乱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政权更迭频繁,全川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十室九空。比起战乱逃亡更严重的是洪水猛兽、大旱饥荒以及“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横行,种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到康熙时期四川人口仅剩九万余人(也有史料称剩几十万人)。
这个数字的背后,代表着曾经千载繁荣的四川,彼时经济社会民生已极度凋敝。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曾在唐代杜甫笔下“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有着“扬一益二”称号的锦官城成都府,“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道存”(孙錤:《蜀破镜》卷5)。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由广元入境赴任,“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六孑遗,郭衣菜色”,往昔田园,尽皆荒芜。每每“行数十里,绝无烟爨”,“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后来,他由顺庆(今南充市)、重庆而达泸州,溯流而上,“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川东各州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惟见万岭云连,不闻鸡鸣犬吠”,完全是一派荒芜景象,表里山河没一块完整、干净、平安的地方来安放一张小小书桌。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四川“遍地皆虎”(欧阳直:《蜀乱》),虎患严重到“古所未闻,闻亦不信”。史料记载,彼时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县治、学宫俱为虎窟”(嘉庆《南充县志》卷6)。北周年间因盐设县的富顺县,虎豹“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乾隆《富顺县志》卷5)。往日四川经济社会的中心成都一带亦无例外。位于今天成都正府街的华阳县衙,时常有老虎豹子公然在堂内堂外大摇大摆闲逛,别说有人击鼓喊冤了,自从县太爷和衙役被叼走几个后,再没人敢来衙门办公了。春熙路附近的“震旦第一丛林”大慈寺一带,也是虎啸丛林。《蜀龟鉴》作者刘石溪对此作过一个估计:川北、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四川“农业尽废”“米珠薪桂”“斗米数十金”。
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三
这样的灾难,四川历史上曾无数次上演,十室九空的惨烈大悲剧,明末清初时期竟然高达三次。
创造了三星堆、金沙等冠绝古今、灿烂辉煌文明的古蜀先人,还有多少土著后人留存至今?历史的风烟从来给不出答案。
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自秦灭巴蜀以来,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大移民来填补人口的巨大窟窿,从而重新升起平原丘陵的袅袅炊烟,恢复残败凋敝的民生。因为人口就是生产力,靠鸡生蛋的方式繁衍人口,再等娃长成劳动力,不仅慢如蜗牛,而且所剩人口基数太小,对等待耕种的广袤田地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道奏折中提议迁湖广人士填四川:“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然无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请”(《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就在同一道奏折里,张德地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移民措施,他说:“各州县人民,虽册籍有名,而家无恒产,出外傭工度日之人,准令彼地方查出汇造册籍,呈报本省督抚,移咨到臣,臣即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解释说,这种无业无产的游民,在他省是累赘与肇乱的包袱,到川省业农,由无产而有产,自为良民。“在于蜀省,(由)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一举两得,无逾于此”。魏源所述“湖广填四川”的“填”字,就从这里而来。
这一个“填”字的来源,成为整个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
在这之前近两千年的四川历史上,移民浪潮就从未断过。蜀地有史可查的最远移民潮,出现在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时期。往日僻静的蜀道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相邦吕不韦,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卓文君的先祖)、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这些身份不同的人背井离乡赶往蜀地,强大的秦国令他们不得不走在了一起。秦国名将司马错灭巴蜀,将水土丰饶、百姓富足的巴蜀作为大后方,为秦王朝的统一提供充足钱粮。巴蜀灭亡后,如何改造巴蜀?秦人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革。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基于此,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子孙延续下来,一直到秦始皇时代,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形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此后的秦末汉初、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四川地区无不是依靠移民来唤醒土地上的烟火气,来恢复旧日的辉煌。崎岖险峻的蜀道上,终日可见衣衫褴褛的迁徙队伍,原本人烟稀少的蜀道彼时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
从这点来看,马背上得天下的清政府,制定的恢复四川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三板斧”:招抚流亡,移民实川,鼓励屯垦,倒也跟秦惠文王的法子如出一辙。
然而,蜀地遥远,蜀道艰险,这一路走来,又岂止是一碗凉粉的伤心。
据现存资料记载,声势壮阔的大移民运动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纷纷涌入四川定居,并沿江河通道形成浸润式分布的格局,前后绵延达一两百年。
以清代的交通状况而论,从东路而来的移民,主要以湖北宜昌为集散地,分水、旱两路入川。水路溯长江而西行,经巴东、巫山、奉节、云阳而达四川万县。但水路费时费财,且沿江道路崎岖险峻,匪患时有,非人多势众者莫取,因而主要为贩货入川的商人或携家迁徙的士族所采纳,更多的贫苦百姓则沿旱路入川。
旱路由宜昌过江西行,经野三关、恩施、利川,再北上过江至万县。抵达万县之后,即可一路西行,经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大竹、渠县、南充、蓬溪、射洪、金堂而达成都。由南路入川的移民主要以贵州铜仁、思南、湄潭(今属遵义市)三地为集散地,并由此形成三条线路。由北路入川的移民主要以陕西汉中、紫阳两处为集散地,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紫阳翻大巴山经城口、万源、东乡、达州、渠县、广安、合川而达重庆;西路则由汉中翻秦岭经广元、剑阁、绵州而达成都。清代初年,西路曾由昭化沿嘉陵江而下经阆中,再西折经三台、金堂而达成都,以避剑门关之险。同时也可由阆中继续沿嘉陵江而下,经南充、合川而达重庆。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被作家罗伟章写进其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的后记里:
“也不知历经几世几劫,在某个晴朝或雨夕,一行人拖家带口,从大巴山扑去的方向,疲惫地走来。这是明洪武二年事,湖湘民众‘奉旨入川。老君山被母亲遗弃,而今又迎来母亲奔赴地的子民。这群人若再坚持一下,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到不了成都,至少也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开江县——那只需再翻几座山,再渡几条河即可,但他们太累了,不想再走了。于是止步息肩,安营扎寨,斩荆伐木,寒耕暑耘,鸡鸣和炊烟,捧出一带村庄。村庄卧于老君山的肚脐眼,也像肚脐眼那样小,小到失去了方位,你可以说,村庄的南方坐落在北方,东方坐落在西方。可它竟叫了千河村。这名字让人遥想:先民所来之地,定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他们被迫离开故士,就把故土的名字打进行李,落脚后又含进嘴里。不仅如此,给孩子取名,也大多含‘水,江、河、湖、海,喊一声,到处都应。事实上,那整片地界,既无江也无湖,自然更没有海;河只有一条,需站到村东黄葛树下,目光沉落至900米深处,才能见到那条瘦弱的飘带,随山取势,弯弯绕绕,绕到天尽头。”
四
陈老板的伤心凉粉,据说是洛带古镇上“最为伤心”的凉粉。尽管这“伤心”并非其祖上“湖广填四川”时一路走来的艰辛,我更相信妻子所言,他家的辣椒比其他家的辣椒更辣的缘故。同样是移民后人做出来的凉粉,同样也是四川凉粉里的佳品,广元、南充等一带叫川北凉粉,但只有在洛带,凉粉才被冠以“伤心”的名号。
关于凉粉的起源,有人考证其最晚出现在宋朝。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体散文《东京梦华录》中,记录当时的北宋都城汴梁就有“细索凉粉”。当然,凉粉出现的确切时间似不可考,但伤心凉粉的来历却是有板有眼。一说是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下,客家人举家或举族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迁徙到四川,安顿下来后,一口一口吃着祖传的凉粉,忆起跋涉之苦,想起病逝离散的亲人,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湿衣衫,手里的碗,因此而变得沉甸甸的,吃进嘴里的凉粉,也混合了泪的苦咸,所以叫“伤心凉粉”。另一种说法则更加动人。被誉为“田边地头、锅边灶头、针尖线头”的客家妇女,在一家大小都进入梦乡后,她还独自一人在磨房里磨豆做凉粉,磨着磨着,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下来了。混合了泪水做成的凉粉,当然就是“伤心凉粉”了。
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个名字都会让人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对于美食而言,店家都希望取一个吉利又讨彩的好名字,比如“红烧狮子头”;又如成都一家“苍蝇”馆子,给泡菜取名为“迟来的爱”,成为顾客最“爱”。但在龙泉驿作家凸凹看来,美食要有文化,就得编故事。他认为,“伤心凉粉”不过是从内江来的客家商人编的一个故事,只是这个故事无论哪个版本,都抓住了人们的好奇心,从而用悲催“逆袭”了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成功使味道“出圈”。
尽管如今陈老板已搬离游客必打卡的广东会馆,但“伤心凉粉”已成为洛带最有名的一道小吃,也成为成都甚至中国知名度都很高的一道名小吃。游客到洛带,必吃一碗“伤心凉粉”。当然,在成都,在四川,在中国,也只有洛带的凉粉叫“伤心凉粉”。
这碗能让一个镇因“伤心”而闻名的凉粉,又有着怎样的“逆袭”之路呢?
事实上,在客家人到来之前,洛带古镇就已在龙泉山下安营扎寨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成都“东山五场”之一,洛带古镇最早在三国时就成街,名为“万福街”。后诸葛亮兴市,更名“万景街”,在宋初已成为地区性集镇。其得名也有两个美丽的传说。一说三国时蜀太子刘禅在镇上玩耍,为捉鲤鱼而不慎将玉带掉入八角井中,故得名“落带”;还有一种说法,此地有一条“天落之水状如玉带”之河,故称“落带”,后逐渐简化,约定俗称“洛带”。史料中,“洛带”二字最早见于唐末五代人杜光庭《神仙感遇记》所载“成都洛帶人牟羽矣”,说明“洛带”之名成于唐末以前。
沧海桑田。如今的洛带古镇,与四川其他古镇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洛带是一个客家文化的川西遗存,是成都近郊保存最为完整的客家古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镇上的居民大约有九成是客家人,客家人之间交流使用的是客家话。毫无疑问,他们能来到四川,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产物。但细考客家人的入川移民史,却意外发现,这个移民群体的大规模来川时间,不是发生在清政府前期施行鼓励移民入川政策的时间段,而是在四川经济业已恢复、人口业已充裕、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流民入川的情况下,他们仍冲破重重阻挠来到四川。这似乎带有几分冒险和“趋利”的性质。
对闽粤客家人入川求富的心态,雍正十一年(1733)广东龙川县往川的客家人告帖曾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往川人民告帖
字告众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同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思得我等祖父因康熙三十年间,广东饥荒逃奔他省,走至四川,见有室闲地土,就在四川辛苦耕种,置有家业。从此回家携带家口,随有亲戚结伴同去,往道来贸易,见四川田土易耕,遂各置家业。从此我等来去四川,至今四十余年,从无在路生事,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况且我们去了四川,并不曾抛荒了广东田土,减少了广东钱粮。
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杨永斌折。
这份告帖,实际上是一份宣言书。它向世人宣告其入川的目的就是“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他们不是逃荒的难民,而是“各带盘费”的朝廷良民。写告帖是为了冲破地方官拦阻,集众拼力往川。当时闽粤客家人地区流传着一种说法,“川米二钱一石,肉七文一斤”,在“川省浮于地,闽粤满于人”的情况下,四川无疑是闽粤客家人心目中的天堂,吸引无数“村民竟有变产欲去者”。闽粤地方官的结论是:闽粤客家人之所以不听从地方官的“再四劝谕”,是因为听信了“川地米肉多贱于粤”以及“川省地士膏腴,易致富足”的诱惑所致。
不论闽粤客家人是重利求富而入川,还是因其他原因而入川,大量的移民涌入,人口的猛增,推动垦殖,使耕地面积日益扩大。在普遍的小农经济和典型的大户经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乾隆年间,四川的场镇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场镇,按移民的原籍文化传统,建立起同乡(同籍)互助的会馆组织,并与邻省的移民会馆,展开不同风俗的文化竞赛,场镇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一批重点城镇很快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都、重庆是最大的两个多元化的中心,自贡、内江则分别是最大的盐业经济中心和糖业经济中心。
因大量经济性移民的客家人涌入,曾经在闽、粤、赣等省普遍存在的“土客对立”现象,在四川更多地表现为“会馆并立”现象。清代四川的会馆遍布城乡各地,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仅在洛带一镇,就有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和客家博物馆等,形成了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大观园”中的一支奇葩。洛带古镇四大会馆生动演绎了内涵丰富的客家文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诞生“伤心凉粉”的广东会馆是全国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宏大的会馆之一,其风火墙建筑风格在四川少有;江西会馆在整体布局和建筑美学方面都颇有价值;湖广会馆较完整地反映了湖广移民的创业和社会生活;川北会馆则集中反映了川北移民的社会生活,其尚存的万年台,是成都地区会馆建筑中唯一保存較为完整的。
五
一碗“伤心凉粉”的背后,又岂止是一条路的伤心。
“湖广填四川”最直接的结果,不仅使曾经富足安逸的天府之国又回来了,更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十分活跃、政治上相对宽松、文化上兼容并包的新型“移民社会”,它对清代以后四川历史的发展,奠立了非凡的文化根基。
随着移民到来的,除了人,还有新的农作物、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高产粮食作物红薯、玉米、马铃薯的引种,全面缓解了川人食用、饲养、甚至酿酒用粮的压力,为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沱江流域的甘蔗种植和榨糖业,得益于清初福建移民引入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甘蔗种植与榨糖技术的引入,则与广东移民有关,此后沿江发展,泸州、江津、江北等地皆有种植。烟草在明代时四川就有人种植,后因战乱遭到破坏。康雍乾三朝闽粤客家移民,将烟草再次引入四川,推动了四川农村烟草种植与制作。
六
一碗“伤心凉粉”的背后,又岂止是一道菜的伤心。
今日名扬天下的川菜,因为辣椒随移民的到来,川菜从此有了灵魂。历史上古典川菜的主要特征有三个:其一是臭恶犹美,即喜食腐臭的食物,其二是尚滋味、好辛香,其三是在食物烹调中喜用蜜。三个特征中只有第二种被一直保留。“尚滋味”一是指爱好多种味道,二是指尚特味。早在西周时古蜀国所产的茶和蜜中,就可以看出四川饮食习俗中所体现的“尚滋味”这一点。“好辛香”则主要是指历史上四川饮食中花椒、姜、食茱萸等调料的大量食用。有研究表明,唐宋时期的四川饮食风味以麻和甜为主,明清以前四川饮食文化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尚滋味,好辛香”。随着清中后期辣椒的传入,逐渐统一为“尚滋味,好辛香”的四川食俗。
辣椒在明代末年传入中国,最早用做观赏植物和药物,随着湖南、湖北的移民进入,辣椒才来到了四川。今天川菜麻辣香鲜的风味也是在“湖广填四川”的基础上形成的。湖广籍移民长于“红烧”和北方移民长于“火爆”的烹饪方式传入四川,才有了红烧肉、宫保鸡丁等菜肴。现代川菜中的麻婆豆腐、水煮牛肉、回锅肉等集中出现在清代中后期,这主要是各省移民进入后将各地烹饪方式融为一体的结果。
跟“伤心凉粉”的故事一样,被誉为川菜第一名菜的回锅肉,就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们发明的菜肴。清初之际,背井离乡填川而来的移民们,每逢年节都要煮肉祭祖。祭过了,东西不能浪费,肉汤里下点萝卜白菜,肉块切片回锅快炒,就成了一道美食。
虽然“回锅肉”的诞生是不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带来的还众说纷纭,无证可考,但另一道巴蜀人都非常熟悉的调料——郫县豆瓣,它的诞生就与移民浪潮有着撇不开的关系。清咸丰年间,郫县城南街的益丰和豆瓣作坊老板突发奇想,将鲜辣椒加入豆瓣酱。在此之前,传统豆瓣酱是没有辣椒的。意想不到的是,放了辣椒的豆瓣酱格外可口,酿造出的辣椒豆瓣酱,不放任何香料却香味醇厚;不用任何油脂却油亮爽润;不加任何色素却光泽美观。郫县的辣椒豆瓣酱,从此成为川菜最重要的调料。
文化总是在交融中传承与发展。“湖广填四川”移民将各地各民族不同的饮食习俗带到四川的同时,移民自身饮食习俗也在当地的影响下,慢慢发生着变化。这种饮食习俗的融合变化,在迁居四川的客家人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客家人由于原多居于山高水冷、地湿雾重地区,故多用煎炒,少食生冷,菜肴有“鲜润、浓香、醇厚”的特点。但在迁居四川后,这些客家人的饮食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客家人聚居的成都洛带古镇,客家人的特色饮食大多以麻辣为主,以客家家常菜酿豆腐为例,传统的客家酿豆腐在煎炸后放入葱花、香油等焖煮至熟,洛带客家人则是加入八角、五香、辣椒等进行焖煮。最为典型的,就是那个辣得人双脚跳、吃得人“伤心落泪”的伤心凉粉。
七
一碗“伤心凉粉”的背后,又岂止是一个词的伤心。
如今已109岁高龄的文化巨匠马识途,1997年在重庆直辖后的重庆市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说:“川渝自古一家亲,分开的是行政区划,分不开的是血脉亲情,我们都在同一种方言下写作!”马老所说的方言,就是四川方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诸多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语言文化上的渗透。现代四川方言,就是流行于巴蜀地区的蜀语与湖广为代表的移民方言融合的产物。
比如“邋遢”,四川人说“邋里邋遢”,“邋遢”此词及义项在宋代汉语中已常见,今还见于江西南昌、星子、武宁、袁州、樟树、新干、抚州、南城、黎川、景德镇等大部分地方,及湖北咸宁、赤壁、大冶、通城、通山、崇阳,湖南平江、洞口、耒阳等地的赣方言中;亦见于湖南长沙等地的湘方言,湖北武汉等地的西南官话,上海、江苏苏州等地的吴方言。
又比如“老几”(什么人;什么东西,有蔑视的意味),指人、家伙(不太尊重人的说法),见于南昌、抚州等地的赣方言中,亦见于湘方言、湖北武汉等地的西南官话中。
再比如“肋耙骨”,指肋骨,见于江西南昌、湖南醴陵等地的赣方言中,亦见于湘方言、客家方言、四川成都等地的西南官话中。
漫漫入川移民路,一路走来的艰辛,也催生了许多令人心酸的“新词”。最典型的莫过于“解手”。对于上厕所,川人有叫“改手”“解手”,又叫“上茅房”。关于“解手”的历史传说,目前为止,有两个说法影响比较大:一是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说;二是清初“湖广填四川”说。两个传说的主要内容大致都差不多:由于移民迁徙路程漫长,途中有人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朝廷便派人强行押送,为防止再逃跑,便想出用绳子把一个一个移民的双手拴住的法子,像牵蚂蚱一样牵着前行。途中有人想上厕所,就得请随行官兵帮忙解开绳子,等到方便完后,再讓他们重新绑上。慢慢的,次数多了,“解手”就演变成了上厕所的专有代词。
顾颉刚先生曾对此做过一番考证。前文谈到清政府“湖广填四川”的三板斧政策是:招抚流亡,移民实川,鼓励屯垦。顾先生考证认为,最初的“招抚流亡”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清廷不得不强行遣返在外地的四川流民,这些人许多不愿再回去,于是清廷便用武力押送回去;有一些是到了四川又逃回去的临近省份移民,为的是偷吃移民三年不用交税的“政策红利”;还有的是作奸犯科之人被充作移民。凡此种种,被迫迁徙者,皆用绳子捆绑,一个牵制一个前行,如果有人想要方便,就会对押送的官兵说:“报告大人,请把我的手解开,我要尿尿(或我要拉屎)。”时间长了,移民把报告语简化成“我要解手”。后来,移民到四川的湖广人,就把方便说成“解手”。四川话发音奇特,把“解”(jiě)的读音发成gǎi(改)。所以,四川人把上厕所就说成解(改)手。
如果说这些方言词语的来历不乏民间演义之说,那么移民带来各自家乡的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民国《大足县志》载:“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用客家话,曰‘打乡谈;与外人交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民国重修《安县志》说,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安县就有广东腔、陕西腔、湖广宝庆腔和永州腔。民国《三台县志》说,三台有宝庆乡谈和广东土语。
在四川方言形成的过程中,川剧也伴随着“湖广填四川”的步伐而产生、定型。川剧原是流行于四川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的戏曲剧种,伴随清初移民实川,外省地方戏曲的声腔——昆腔、高腔、胡琴、弹戏与四川民间曲调灯戏相融合,在长期发展中逐渐采用四川方言念唱,异源合流,同台演出,相互影响,共融共生,后来统称为川剧。川剧的五大声腔正是在这样的融合发展中,为适应南北移民的文化需求以及其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而同台演出并逐步综合为一的。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四川的会馆和茶馆的兴盛,为四川方言、戏曲等口头语言艺术的产生、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场所。如今在川渝地区家喻户晓的巴蜀笑星李伯清,几十年来还保留着赶场(这也是一个移民方言词语)的习俗,他最常去的就是“水陆要冲”双流彭镇老茶馆,与老茶客们喝浓茶、抽叶子烟、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为闲聊)。说是体验生活,其实是向民间老百姓学习“语文”。而他走上散打评书之路的发迹之地,就是被称为川剧戏窝子的百年老茶馆——悦来茶馆,也就是正在改扩建中的锦江剧场(又称成都川剧艺术博物馆)。
八
有人说,甜的味道是妥协,只有辣才会有悲伤的往事。时光匆匆,当年走过的路、翻过的山、蹚过的河,陈老板和他的先辈,谁也记不得路边香樟树的眼神。但无论你站在洛带的哪个会馆、哪家书院、哪个店铺,甚至是客家土楼的屋檐下,在你站立的地方,只需来一碗“伤心凉粉”,一条路、一道菜、一个词、一声腔调,就会和你不期而遇,在你伤心落泪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出生地。
所以我说,认识洛带,还得从这碗“伤心凉粉”开始。
【作者简介】赵晓梦,诗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钟山》等刊,著有长诗《钓鱼城》《马蹄铁》等。曾获十月诗歌奖、《北京文学》诗歌奖、《诗刊》科尔沁诗歌奖、郭小川诗歌奖、中国长诗奖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