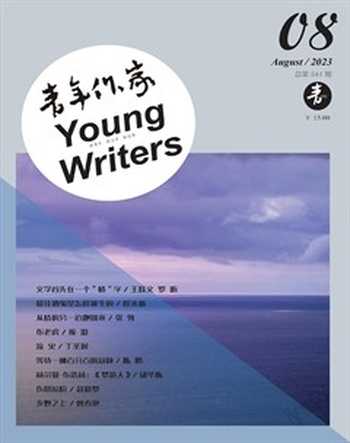从桥的另一边跑回来
下午五点多,我从街上回来,把车停好,爬到五楼的家中。客厅里弥漫着油烟味。女儿在看电视,屏幕上有一群小马,生得五颜六色,还会说人话。女儿喊声爸爸,奔过来,抱我一下。我摸摸她的头。她快速回到沙发里,依旧看那群小马。
厨房传来抽油烟机的轰鸣。我走到厨房门口。门开着,她正炒菜。我把门拉上。她做饭时总是不关门。我刚转身,门又开了。她说,你关什么门啊。我不说话。她说,等会儿就散了。我还是不说话。我发过誓,离婚前不和她说话。
我告诉女儿,今晚我不在家吃饭,去外面吃。她看我一眼,问我去和谁吃。我说出马辽和王哲的名字。她说,你又要喝酒。我说,不多喝,耽误不了明天出车。我坐下和她一起看电视。此刻小马们正围着桌子,不知在为谁庆祝生日。一分钟后,我看明白了,是那只紫色的小马的生日,她留着长长的马鬃,样子很像我的朋友王哲。
我走出家门,来到楼下,吞吐着白气,快步走到小区门口,骑上一辆共享单车。雾霾浓重,黑夜早已降临,空气中有股焦糊的气味。我坐了一整天,腰有些痛。此刻,她应该已经炒好菜,独自坐在桌边吃饭。女儿吃过了,在幼儿园吃的,她一天三顿都在那里吃。这幼儿园是她选的,收费挺贵,我勉强负担得起。今天晚上,我逃离了她的饭菜,奔赴一桌酒肉,却并不开心,相反有些沮丧。自从开上出租车后,这感觉总会像风一样吹到我头上。
八年前,我在一次詩歌活动上认识了马辽和王哲,我们互相欣赏,于是组成一个小团体,时不时聚一次,喝点酒,聊聊天。这对我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那些乘客,恐怕谁也想不到,这个弯腰驼背的出租车司机,曾经写过诗。八年前,我还没有开上车,也不认识现在的她,是个风华正茂的单身汉。这八年间,我结了婚,生了孩子,而后丢工作,开上出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都被马辽和王哲看在眼里,但他们始终认为,我的生活还过得去,起码值得这么过下去。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过了。
刚到饭店门口,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许东!我扭头寻找,看见马辽。他正倒车,脑袋伸到车窗外。他下车,打开后备箱,拿出一瓶白酒。他说,看,陈酿。车灯很亮,但我看不清这是瓶什么酒。
在包间坐定后,马辽把酒放在桌子中间,随手一推转盘。这是一瓶衡水老白干,玻璃瓶泛绿光,金属盖子上有黑斑,标签纸跟在火上烤过一样,泛黄,边缘发黑。马辽说,你仔细看看生产日期。我凑近看,一行歪斜的数字,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我说,89年的。马辽说,对,跟王哲同岁。王哲还没来。他在影视公司做导演,工作时间不固定,刚才发信息说在办事,办完就马上过来。那是几个年轻人的公司,王哲是合伙人之一。
马辽说他前几天收拾自家库房,发现这瓶陈酿,当时没舍得喝,今天突然想起,这酒刚好出厂三十年,该由过三十岁生日的王哲喝掉。我表示同意。我们一边看着这瓶酒,一边等王哲。
马辽点上一根烟,问,最近你写得多不多?我摇头说,没写,灵感少。马辽叉开腿,向后仰,脖子架在椅背上,说,我一天至少一首,跟拉屎一个频率。服务员进来,要我们点菜。我接过菜单,看见许多菜肴的照片,都很好吃的样子。我说出菜名,该点哪道菜,让马辽定夺。依照惯例,最后是他买单。我和王哲对此没有意见。马辽应该很有钱,具体有多少,我不清楚。我们之间不谈钱,隐隐约约的一条规矩。
我们点好菜,服务员出去。马辽看看手机,说,王哲正打车过来。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喝上几杯后,我的状态会好点。
马辽说,许东,我发现你脱发很厉害。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说,是的,你也一样。马辽说,咱俩都秃,但样式不同,你是前面秃,我是中间秃。你看你的发际线,都退到脑瓜顶了,让我想到一个词,晚景凄凉。
我从三十岁开始掉头发,掉了十一年,终成这秃顶的模样。遗传。过世的父亲,早已为我打好样本,我也会只剩脑后的一弯残发。马辽点头,认为我的预言无比正确。他比我大十二岁,头顶已光可鉴人,可周围一圈,包括前额上的头发,仍健在,还挺硬的,根根直竖,都是白色。他留着两毫米的胡子,胡子也是白的。他说,有次我在家洗澡,冷,打开浴霸,光线很亮,洗着洗着,猛然看见下面有了一撮白毛,我很悲伤,想起一句唐诗——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这可是头一回,在此之前马辽从不承认自己的衰老,可见那撮白毛的冲击力着实不小。马辽比我大十一岁,已年过五十。他总是对我们说,许东,咱俩看上去差不多,真差不多。我不置可否。其实,我心里有点介意,犹如心头也长出了白毛。
王哲终于走进包间,他头发稠密,满头小波浪卷,应是时髦的发型,根本不存在变秃的迹象。他嘴唇下方扎着一枚钢钉,让他显得很酷,有点不好惹,实际上他性情温和,时常紧张害羞。他冲我们笑,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有个破事儿。
我对服务员说,上菜吧。马辽把那瓶酒转到王哲面前,让他仔细观看。王哲说,我正需要喝点,老白干,67度,好。马辽提示,看生产日期。王哲终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我说,倒上吧,整瓶都是你的。王哲说,没问题。
前些日子,王哲拍了部片子,还请我和马辽去客串,演两个混迹在KTV里的流氓。片子拍完后,他去北京做剪辑和后期。投资人在北京,对王哲很欣赏,每晚都叫他去喝酒。经过那段时间的磨练,王哲酒量大增,白酒能喝一斤。这是酒后投资人告诉王哲的,他本人并不清楚,因为喝到一斤头上,他的记忆已模糊不清。王哲讲出这件事,说明他能喝的原因和实力。我和马辽频频点头,我们通过这件事,已经看到王哲的光明前途。他的人生轨迹正沿着我们的预期稳定发展。
除这瓶老白干,马辽还带来两瓶威士忌。我们一般喝白酒和啤酒,很少喝洋酒。马辽说,最近我爱喝这个——喝这个得加冰。他找服务员要冰块。服务员说没有冰块。我说,就这么喝吧。马辽说,不加冰会很难喝。他语气坚定。王哲说,我去旁边的超市买点冰棍。说完他晃着一头小卷发走出包间。
两分钟后,我的手机亮起,进来一条微信,打开看,是艾琪发来的。艾琪是王哲的老婆。她问,你们在哪个包间?我把包间号告诉她。我对马辽说,艾琪来了。我们都觉得蹊跷,艾琪应该和王哲一起来,而不是跟我联系,找我问房间号。她很少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我们见过,在某次诗歌活动上,她也曾写诗,与王哲结婚后,就什么也不写了。
我们正说此事,包间的房门被人推开,艾琪进来,拎着一个大蛋糕。她说,这是我给王哲买的生日蛋糕,祝他生日快乐。她把生日蛋糕放在桌子上,扭头走出去。我离开座位,追上她问,你不和我们一块吃吗?她说,昨天下午,我和王哲离了。我的脑子飞转,说,那更该吃了,散伙饭嘛。她说,我男朋友在下面等我。我说,好吧,这还挺突然的。她往前走,消失在拐角。
我回到包间,看着桌上的生日蛋糕,蓝色的盒子和丝带,透过覆盖着塑料膜的部分,看见圆形的蛋糕,奶油上盖着一层黑巧克力,上面有生日快乐的英文。
马辽说,我没想到买生日蛋糕,一点也没想到。我说,我也没想到。马辽说,他们真离了吗?我说,问一下王哲。马辽说,不要问,他只需要安慰,我也离过婚。我说,理解,你说得对。我们好像只能这样说。服务员进来,放下一盘酱牛肉,打破生日蛋糕与三瓶酒对峙的局面。
王哲回来,带着一袋子冰块。看样子,他没遇见艾琪及其男友。王哲坐下,注意到桌上的生日蛋糕,说,你们买蛋糕干嘛,不用。我说,是艾琪送来的。王哲说,不可能,我俩刚离婚,昨天下午去办的。他停下,不再继续说话,仿佛在等我和马辽接茬,但我俩谁也没开口。如果喝了酒,我俩肯定会说几句的。
我点的五个菜全部上齐。王哲将冰放入酒杯,再打开威士忌,倒进去。冰块浮上来,漂在酒上。他瞪着酒杯,张开嘴,塞入一个冰块,嘎嘣嘎嘣地嚼。我把那瓶老白干拧开,鼻子凑到瓶口,深深吸气,酒味浓烈。马辽伸出手臂,我把酒瓶递给他,他也闻了一下。我们都想闻出三十年陈酿的独特香气。我没闻出来。马辽说,真他妈冲。
王哲,祝你生日快乐!我和马辽举起威士忌,王哲举起老白干,我们一饮而尽。第一杯,肯定是要喝干的。要不然,我們的话题无法打开。威士忌很凉,落到胃里,依然很凉,酒味里混着甜味,更有冲击力。王哲咳嗽起来,像岔气一样。他两手按住桌面,用力憋气,压制着咳嗽,脸涨得通红。他摇头,表示没事。我们吃几口菜,喝下第二口酒。
我感受到,因为蛋糕的出现,气氛变得与往日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该聊什么?王哲要不要将他与艾琪离婚的整个过程讲清楚?看得出来,王哲在沉默地思考,从他的脸上,看不到难过的神情。
王哲赞叹完老白干的浓烈,又喝下两口,沉吟半晌,终于说起正事:昨天本来要去北京接着做后期,投资人打来电话,说片子没过审,先放一放。这一放估计就没戏了。我很郁闷,想干件什么事,能让我生活发生改变的事。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让我四肢发痒。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恨不得找东西撞上去。回到家,我听见艾琪正打电话。我站在客厅里,她躺在卧室的床上。我开门很轻,她没听见。她说着说着,竟然笑起来,笑声还很大,挺夸张的,甚至还有点淫荡。我坐在餐桌前,听着她的笑,突然决定和她离婚。离婚这事吧,她以前提过,说跟着我生活压力大,老失眠,总想哭,但我没答应,主要是因为怕我爸接受不了。现在我下定了决心,不再顾及任何人的感受。于是我走进卧室,打断她的笑声。她惊叫一声,急忙挂断通话。我俩对视了一会儿,我率先打破沉默,说咱离婚吧。说完我就笑了,她也笑了。我发现她真是个很爱笑的人。
说到这,王哲停下,点燃一根烟。我和马辽端起酒杯,我本想再说祝你生日快乐,但忍住没说。冰镇的威士忌入口甘冽,带着一丝甜味。王哲买来的冰块本来是给小孩们吃的。马辽对王哲说,笑是对的,你也应该笑。王哲说,我没笑,我也不想让她笑,我说你他妈别笑了,这有什么好笑的,她说,幸亏没要孩子。
我接话,因为没要孩子,所以你们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要了孩子,那做什么都是错的。王哲说,关键是,我听她这么一说,竟然有些后悔,后悔没要个孩子,我想如果有个孩子,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丧了?我说,没用的,真的,没用的。
王哲点点头,继续说,我提出离婚,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好像一直在等我开口。她开始收拾起东西,先是衣服,然后是化妆品,零零碎碎的,非常多,都没东西装。她让我去楼下的小超市要几个纸箱子。我跑到楼下,找到小超市的老板,问他有没有多余的纸箱子。超市是夫妻店,今天是男老板值班,他很胖,喜欢拍着肚子叹气。我常来买烟,算是熟人。他问我干什么用。我说,不过了,分家,装她的东西。他又问,要离婚啊?我点头。他拍了拍肚皮,若有所思,说,兄弟,你终于发现了。我问,发现什么了?他叹了口气,她,你媳妇,有事儿,是不是?我问,什么事?他问,难道你还不知道?我说,我他妈的知道什么?他说,一个男的,个子挺高,留胡子,像搞艺术的。我说,你把话说明白。他说,你媳妇常和一个男的来我这买菜,看那意思是上楼做饭。我的心翻腾了一下,点点头,说知道了。胖子找了三个纸箱子,还有两个塑料筐,问我行不行。我说行,真是太谢谢你了。临走时,我站在超市门口,想了一下,扭头对胖子说,那是她弟弟。胖子正笑眯眯地盯着我,冷不丁听见这一句,愣了一下,什么?我重复道,那是她弟弟,不是第三者。在电梯里,我还在琢磨,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撒这个谎。你们肯定不理解,从超市出来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真的成熟了,是个男人了,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像个孩子。
马辽问,然后呢?你回去之后,是不是质问她了?王哲摇着头说,没有,那是小孩子干的事,我成人了。我问,那你什么也没说?王哲说,没有,真没有,那个留胡子的男的是谁,我能猜到,是陆丁,我哥们儿,他有老婆,去年我们俩家一起去泰国玩过,他俩搞到一块,倒是有这种可能。马辽问,那你能忍?王哲说,不用忍,我根本没生气,心里超级轻松,没负担,也不沮丧,一片空明。我说,我能理解你,来干一杯。
话说到这里,必须要干一杯。王哲的遭遇让这次聚会变得意义非凡。冰块快化干净了,酒变甜了。王哲说,我抱着五个箱子,像个收废品的,走进家门,站在客厅里,感觉房间变得陌生了。这房子是结婚前我爸买的,算是我的房子,因此需要离开的是她。她会去哪儿呢?陆丁那里应该不行,没听说他离婚。应该是回娘家吧。她在卧室里问,拿到了吗?我回答,拿到了,5个,够吗?她说,应该够了,没想到我的东西会有这么多。我到卧室一看,床都满了,全是她的东西,主要是衣服太多了,这些年来,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在淘宝上买,每天至少下一单。鞋也不少,堆在床下,目测有四五十双。我和她打包,一个拿,一个装,配合默契。然后又一起下楼,把箱子放进她的车里。她开车,我坐副驾驶,开出小区,前往民政局,前年领结婚证的地方。路上,她说,咱俩不像去离婚。我问,那像去做什么?她说,像去露营,更像去夜市摆摊。我说,你开快点吧,人家下班早。她说,咱们应该吵一架。我说,不吵,为什么要吵?她说,别人都要吵死了。我说,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她说,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说,该变道了。开到民政局,一问,人家让我们先回去冷静冷静,这叫冷静期,一个月。我说我已经够冷静了。他们说,不,你们这是典型的冲动型离婚。我看没辙,要回家,她拉住我说,咱们找个人,就不用冷静一个月了。说完,她跑到卫生间待了一会儿,出来后对我说,搞定了,咱们可以马上离婚了。于是我们再次找到工作人员,人家打印出两个证书,砰砰,打下两个红章。她让漫长的一个月缩短成几分钟,这种能力可以做制片人了。手拿离婚证,我翻开看,看不出任何潦草的痕迹,脑门上冒出一层汗,于是就用这个小本当扇子,扇了两下,却没多少风。现在想来,当时我有种置身事外的超脱之态,像一个局外人,正冷眼旁观,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内心也毫无波澜。我甚至想到,今天发生的很多事都很有意思,将来可以写进剧本里,拍出来。由此而来的,是对事件背后那些隐秘信息的追问。我问她,你刚才去打电话,怎么说的?她正盯着离婚证出神,一时没听明白,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求别人办离婚证,这事很有意思,你刚才怎么说的?直接说你要离婚?难道不用解释一番吗?她说,我觉得这事一点意思也没有,你竟然觉得很有意思,还算是个人吗?唉——
说到这里,王哲发出一声长叹,转着酒杯说,她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继续喝酒。身上有了酒意,正是最舒服的时候。王哲接着说,就在我们快要吵起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爸打来的,说是祝我生日快乐。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她听说这件事后,不再纠缠于刚才的话题,也说了句生日快乐。离婚的事,我没告诉老爷子,怕他一时接受不了。我和她在民政局门口分手,她开车走了,我步行,往家的方向走,走着走着,感觉那个我才回到身上。正好走到一家便利店门口,门口摆着音箱,正放时下流行的《沙漠骆驼》,我停下脚步,跟着节奏跳了一段。
马辽拍起桌子,笑着说,王哲,你瞎编呢?王哲说,没有。马辽问我,许东,你信不信他刚刚说的话。我说,听着像编的,你这离婚的效率也太高了。王哲说,真让你们听出来了,这就是我编的,是我下一部短片的故事。
马辽出去上厕所,他说自己上岁数后就开始走肾了。桌子旁只剩下我和王哲,我俩相视一笑,碰了碰杯,各自喝下一口。王哲问,你家庭生活挺好的,是吗?我说,正闹离婚,主要是我闹,真的。他说,理解,男人也有离婚的权力。我说,过着没劲,想死。他又点头,沉默一会儿,问,你开车时,脑子里会想什么?我说,会想如果自己是乘客,那该多好。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假如我的出租车有种魔力,能互换人生,比如说,你打上我的车,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变成你,你变成我,咱们去过对方的生活,假如我过腻了,就天天去街边打车,如果打到你的车,再和你换回来。他说,你这创意可以拍成短片。他又问,让你产生那种念头的人多吗?我说,每天至少能遇到一个。
马辽回来,坐下来,打断我和王哲的话题。我们恢复到正常的节奏,像以前那样喝起来。我们的话题离开艾琪,马辽聊起他公司里的事,这是他总也聊不完的话题。
十一点半时,我收到老婆的微信,问我怎么还不回家。我没回复,抬头说,散了吧,明天早起,我还得送女儿去幼儿园。马辽说,还有蛋糕没吃呢,王哲,王哲,吃蛋糕吧。王哲缓慢地抬起头来,说,蛋糕,吃不下了,想吐。我说,那就不吃了,带走,你明天再吃。马辽离开包间,去买单了。
我们走在和平路上,头顶横着一座高架桥,桥上有路灯,照得很亮。我知道,往前走一个路口,再右转走两百米,就是王哲居住的小区。他走路晃晃悠悠,紧闭着嘴,似乎在极力压制着醉意,嘴唇下的鋼钉撅起来,一闪一闪。干掉整瓶威士忌的马辽,依然说着话,只是舌头发硬,吐字不清。
走了一会儿,马辽和王哲跑到高架桥下,对着桥墩撒尿。再往前走几步,就到转弯的路口了。送王哲回家后,我和马辽再打车走。
我们走到路口。高架桥在此低了下去,有个入口,车辆拐入后往上爬行,越过最高点,消失在另一边。王哲停下脚步,指着右边的街道说,那边是我家,你们走吧。我说,一起走,送你到家。他说,不用,我自己能走。他把蛋糕推给我,说,这个你拿走吧,让你女儿吃。我说,不,你的生日,应该你吃。他说,吃掉这个蛋糕,我就真他妈老了,我不吃。说完,他仰天叫了两声,哦——哦——
我想裸奔,要不,一起吧。王哲把蛋糕放冬青上面,冬青长得茂密,看上去也很干净,他盯着我和马辽,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睁大眼睛,看着马路和人行道,没有行人,偶尔有出租车开过。我摇头说,不了,太冷。马辽也摇头说,王哲,你回家睡觉吧。我俩都保持着足够的理智。王哲说,就不该问你们。他后退两步,做出将我们疏远的姿态,自顾自地脱下衣服,上衣和裤子塞给马辽,内衣则交到我的手中。我说,穿着裤衩背心吧。王哲摆手,嘴里嗷嗷叫着,脱掉全部的衣裤,又穿上鞋,所以他并非一丝不挂。鞋能保证他的奔跑顺利完成。冷风中,他的下体摇摇摆摆。他看看手机,指着高架桥说,马上就12点了,我从高架桥的这边跑上去,再从那边跑下来,刚好跨越30岁。我们点头,马辽表情木然,好像十分严肃,我想笑,但没有,我说,好,你加油。王哲拍了两下手,奔跑起来,他的屁股在路灯的照耀下像一张苍白的面孔。他很瘦,是三十岁的男人不应该拥有的瘦。他大腿后面的肌肉一收一紧,爆发出力量,让他越来越快,似乎只有几步,就跨到桥上,抵达那个最高点。王哲转身,冲我们招手。我们挥舞着他的衣服。他转身,晃着屁股跑下去,身影消失。
马辽说,这小子跑得够快的。我说,咱俩要跑的话,都跑不过他。他说,你差不多,我肯定不行。我把王哲的衣服放到一丛冬青上,又把那个生日蛋糕拿过来,放在旁边。马辽掏出烟,我俩一人一根,都点上。我们抽着烟,望向高高隆起的高架桥。王哲迟迟不现身。我们往前走了几步,沿马路牙子蹲下,烟已抽到一半。风吹得更冷了,我感觉酒劲散了些。我掏出手机,眼看着马辽也掏出了手机。我们一手拿烟,一手操控手机。我老婆又发来微信,依旧问我怎么还不回家。过12点了,这时间已经不属于王哲的生日。我还是没有回复。烟抽得只剩屁股,扔到地上。我们站起来,活动几下身体,都打了两个哈欠。
从时间来看,王哲早就应该跑回来了。马辽说,给他打电话吧。于是,我拨通王哲的手机。他是拿着手机去裸奔的,我看得非常清楚。可他没有接听,难道他还在跑吗?风太大,听不见铃声。在这么冷的环境下,一个不穿衣服的人能坚持多久?王哲已经坚持很久了,再坚持下去,恐怕就要冻死了。
我一手拎上生日蛋糕,一手抱着王哲的内衣,马辽拿着王哲的上衣和裤子,我们走上高架桥。这里风大,吹得我直缩脖子。年过五十的马辽呼呼直喘。我们到达最高的地方,这里空无一人,往前面看,也是空无一人。一辆车开过去,车窗里的司机转脸朝我们看。车里就他一个人,他也不是王哲。桥的护栏有半人高,上面有铁架子,放置着花盆。暖和的时候,会有鲜花从花盆里长出来,现在只有硬邦邦的土和枯枝败叶。马辽站在护栏边,试图往下看。我明白他的意思,靠近护栏,视线被花盆挡着,看不到下面。
我们朝前走,走到高架桥下面,先看南边,马路边停放着一排共享单车,朝上看,看到桥上的路灯、铁架子和花盆,再去北边看,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昏暗的光。我们扩大寻找范围,马辽在北边,我在南边,先向西,再向东,各走一百多米,都没看见王哲。
行走几百米后,我觉得疲累,坐在一辆共享电动车上,对面的马辽招呼我过去。我扫视着四周,从高架桥下穿过。马辽蹲在地上,說,他肯定还活着。我点头,我怎么能否定呢?马辽又掏出烟来,给我一根。我说,腾不出手,不抽了。我都戒烟好一阵了,开上出租车后就再没抽过。马辽吐出烟雾,说,这小子爱耍把戏,他肯定打车走了,这会儿早到家了。我说,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呢?马辽说,喝多了,回家就睡了。我觉得马辽说得有道理。马辽又说,该走了,明天早起还得给他们开会。他把王哲的上衣和裤子塞进我的怀里,说,这衣服,你明天还给他吧,你整天开着车,方便。我说,行,肯定能路过他家。
马辽掏出手机点了几下,他发出一条语音信息,给你发位置了,把车开过来吧。我问,谁?你司机?他说,不是,司机早下班了,是我老婆,开她自己的车,从十点开始就在酒店外面等着了。我问,你怎么不说?他说,不说这个,多没劲,咱们在一块,不得多聊点有劲的事吗?
其实,那些没劲的事,马辽也没少聊。据我所知,他的老婆比他小十五岁,本是他公司的职员。
我俩蹲在路边,没一会儿,开过来一辆红色的奥迪。车门一开,出来一个穿风衣的女人,个子挺高,扎着马尾,干净利落。她快步走到马辽跟前,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马辽说一言难尽。我打招呼,喊一声,嫂子,你好。她看我一眼,点点头。她的眉毛很细,嘴唇很红。马辽由他老婆搀扶着,进入车内,坐到副驾驶的位置。我坐后排,把衣服和生日蛋糕放一边。车厢里有股好闻的香水味儿。车要开动时,我问,咱们这样走,行吗?马辽说,不知道。其实这相当于说可以走,赶紧走,别再找什么王哲了!马辽下定决心一样说道,走吧。
女人问,怎么回事?马辽说,一个朋友,刚刚去裸奔,跑没影了。她笑着说,你这朋友太有意思了。马辽说,刚看他光着屁股往桥上跑,我突然有股冲动,也想扒光衣服跑一跑。女人说,你可别,一身烂肉,太吓人了。
车向前开,沿着桥下行驶,调头,经过路口,停下等红灯。我看着车窗外,王哲脱衣服的地方,此刻没有人。车又开动,快速爬上引桥,路面开阔起来,我盯着外面,在这桥面上,没看见任何一个人。
一路上,女人不断自言自语,讲她在车里无聊的状态,埋怨我们喝酒的时间太长。她语速快,句子与句子之间不停顿,吊着一口真气,说个没完。我听得累,侧目看马辽,他低头睡着了。女人察觉到马辽的表现,用胳膊肘撞了他几下,让其醒来,听她继续说下去。
车开到我的小区门口,我下来,拿着衣服和生日蛋糕。马辽说,许东,回去好好休息,王哲应该没事。我说,好,你慢点。我目送他们远去,进入小区,走进家门,客厅的灯亮着。我把生日蛋糕放到厨房,又找了个超市用的大号塑料袋,把王哲的衣服装好。简单洗漱后,我躺到沙发上,很渴,又爬起来去喝水。我喝着水,又拨通王哲的电话,依然没人接。
沙发很软。天快亮时,我听见女儿的笑声,睁开眼,看见她站在床边,举着一根手指,指尖上有奶油。她让我赶紧起来,去卫生间里照照镜子。我很累,头疼,而且恶心。我被女儿推进卫生间,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我的脸上涂满奶油,显得滑稽又陌生。女儿笑得更欢实。我也笑,刚要洗脸,她说,你先别洗,再看一会儿。她继续笑。老婆进来,看我一眼,没有笑。我又盯着自己的脸看了一会儿,眼袋已经大过眼睛。
老婆和女儿分别吃下一大块生日蛋糕,他们让我也吃一块,我摆手,又躺倒在沙发上,深陷于宿醉之中。老婆让我赶紧起来,送女儿去幼儿园。我勉强坐起来,眼前的电视左右晃动。
我们下楼。我拎着装着王哲衣服的大塑料袋。女儿问,这是什么?我说,王哲叔叔的衣服。她眼神茫然,可能没听清,却没继续问。每次去幼儿园,她的情绪都有点低落。老婆问,王哲的衣服怎么在你这里?我没说话。她也不再问。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我把车开到二环路的高架桥上,送老婆上班。
我们住在城市的西边,她的公司在东边,走高架桥是最便捷的。今天是周一,又正值早高峰,车很多,慢慢地堵着,只能一点点地蠕动。听广播说,前面有个事故。她坐在我旁边,划拉着手机,突然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说话?你这叫冷暴力,你知不知道?我也想好了,等忙完这段,咱们就去离。我按了下喇叭,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喇叭声,并不多我这一下。
太阳正在爬升,阳光越来越刺眼。突然,我仿佛看见王哲从对面跑过来。他满身都是阳光,虽然没穿衣服,但看上去很神圣。应该是太阳给了他很强的推力,让他奔跑的速度远超常人,简直是脚下生风,从我车窗外疾驰而过。老婆喊,别愣着了,开啊!我回过神来,看见前面空出一大段,急忙踩下一脚油门,车蹿了出去,她发出一声尖叫。
【作者简介】张敦,本名张东旭,生于1982年2月,河北枣强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曾获孙犁文学奖、贾大山文学奖;现居山西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