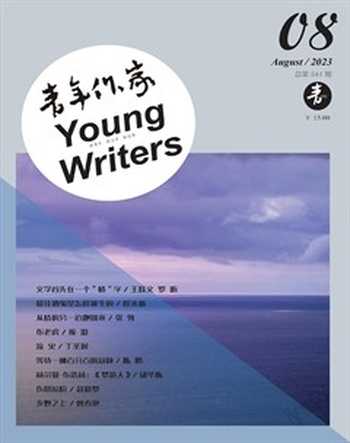你的样子
一只银鸟自西向东孤独地飞翔。它飞得很高,很慢。我仰视着,希望那是一架飞机,可无论怎么看,都不像飞机。它就是一只鸟,我叫不出名字的大鸟。
这三年,我一直在关注一架飞机。飞机飞着飞着,不见了。电视、报纸、网络,新闻铺天盖地。Y国、M国、W国派出军舰、搜救船、海洋打捞船,分区分片,将太平洋大西洋搜了个底朝天。大家争论不休,相互推诿,谁也不肯为此事负责。交接的空域、恐怖分子、一颗从水下起飞的导弹、某超级大国、神经病飞行员、一百多名乘客、海外神秘基地、整个科创团队、最先进的量子通讯技术、外星人……各种说法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可能性,不知哪一条是真的。
飞机上坐着我的女友。
海里没有找到飞机残骸,海面发现了一些漂浮物,可无法证明是这架飞机的。找了一年后,飞机拥有者的M国宣布,终止所有官方搜索。但亲友们仍然满怀希望。于是便有了专家们的各种猜测,有的甚至引用平行宇宙的理论来证明这架飞机仍在飞,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飞,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时机突破结界飞回来。
我居然相信了。等消息的同时,足迹几乎遍布城市及周边所有高山、高楼、高桥、高塔。每到最高点,我伸出的双臂,冲天的头发,既是发射器又是接收器。当思念化为一阵阵强劲的脉冲时,我相信,平行宇宙的女友绝对有感应。我们有过多次这样的感应。她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她的时候,思念便如狂风般阵阵呼啸。耳边的风、张开的翅膀、滑翔伞的颜色,都会奔向同一个制高点。我要让女友明白,防火墙、黑洞、暗物质、平行宇宙,谁也阻挡不了我们之间的联系。
前不久,突然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上只有一排字。像日文,又像韩文。我姐说,像火星文,尽是蝌蚪。我姐摇着头走了。摩斯密码,喃喃细语,耳边的娇弱气息,立即蜂拥而至。
对着火星文发了一天一夜的呆后,我决定再作一次尝试。
一片眼巴巴的天空,幽蓝,深邃,沉寂。几颗绝望的星星,孤独,暗淡,忧伤。萤火虫一样的飞机,在湖边钢筋丛林里游走。不知不觉,就到了大湖公路桥最高点。一湖平静的水,半湖睡着的船。月亮沉在湖底,像一面古老的铜镜。没有风。这么高的桥,这么宽的湖,应该有风。风去哪儿了?小轿车不带风,带噪音,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由远及近,由近至远。
观湖平台上有人。一个女人。长发,三角鼻翼,瘦高个儿,一身黑长裙。手上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动不动。
我姐笑。阿弟,你这薄如蝉翼的身材,一捅就破,要不要上点桐油?我也笑。阿姐,不用借翅膀,我在空中绝对比别人滑得远,滑得自在,即使跌在地上,也没别人跌得惨。扔出去,水上至少能打三个水漂。
长发女孩要把自己像炸弹似扔出去,还是跟我一样,等风来?
去年,相思山的狮子岩上,风化的姿势,思念跟悬崖前的鹰一起盘旋。一眨眼,一只巨鹰站在眼前,张开温柔的翅膀,将我紧紧搂在怀里。那一刻,我哭了。号啕大哭。
此刻,我只能将隆隆的心事藏在前方不远处的铁路桥上,没打算告诉桥顶那两盏警示灯。那丁点儿的光芒还不足以让我迷恋。我不是游离在灯周围的飞蛾,我是一只安静的猫头鹰。
长发女孩到底想干啥?我的每个紧张的毛孔,都像喘不過气的鱼嘴。我来桥上,除了尝试接头外,还想努力驱散心中那片黑色的忧郁。我没有想不开,不想从湖里被捞起时如一头泡得发白的猪,让啧啧的人摇头叹息后,很快将我忘了。我发过誓,要死,也要像大雁,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一头撞在高高的悬崖上,死得绚烂,死得与众不同。
我想,女友可能没上飞机,飞机起飞前发那条信息,只是故意逗我玩。女友喜欢逗我玩。每个月消失几天,她将自己隐藏在漫长的等待后面。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检测到我的思念指数和煎熬频率。每次消失前,她都能找个理由,跟我吵上几句,然后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关上手机;或者去闺蜜家疯一两天;或者背上驴包,独自去无名山头住一夜,享受虫鸣鸟叫的美妙。最久的一次,她带上全套滑翔伞装备,去了河南。直到把我逼疯,才出现。这次消失这么久,我没想到。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马上要见到她了,上桥的过程中,心一直在怦怦狂跳。
“你来了。”
“我来了。除了我,还会有谁,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长发女孩太像女友了,身高、五官、体型,说话的腔调,飞来的眼神。长发女孩想要跟我说什么?要我作活着的见证者,还是要为她传递某种信息?
“你是?”
“你女朋友呀。”
不是惊喜,是惊吓。
“看把你一大男人吓得。”两个清澈的小月亮瞬间照得我一身惨白。我想明白了,我还有大把的青春大把的光阴没挥霍。“你来了,你就是拯救我的天使。”
这些话,好像在哪里听过。听过不止一次。女孩走近一步,我后退一步,她进一步,我再退一步。
“你还是怕。”女孩又走近一步。我挺了挺胸膛,没退。
“我叫邵红。”女孩拢了拢长发,慢慢伸出右手。五根并拢的瘦长手指,像女鬼的手指。手掌却又不像女鬼的手掌,柔软,有温度。瞧你这点出息。邵红将发亮的大屏手机送到面前:“来,加个微信。”开头,我一直盯着她手里那团黑乎乎的东西,以为是块砖头。
“我没带手机。”我说。出门时,我特意将手机放在家里,生怕手机电磁波干扰我跟女友之间的感应。
“那好吧,我留个联系方式。我住馥园路15号。很好找的,记得找哦。”邵红用化绵掌扇动一手月影。转身,轻飘飘走开,一会儿便将桥头隐藏在一大片朦胧的夜色中。
不问问我是谁,难道早知道我是谁?还是,谁也不必知道谁是谁?只是一次偶遇,一次再也不见的偶遇?
富人的馥园路15号,我不去,憋着尿,也不想尿馥园路15号的墙根。那地方,是我的伤心地。女友带我去过一次。那个坚持要我叫她阿姨的人,一进门就审犯人一样追问我的家世、年薪、房子,父母在不在。她即使不说话,眼中也透着一丝丝刻薄。没坐上几分钟,我就站起来哀悼我的不幸。女友打气,她不是我妈,做不了我的主。
可我能做自己的主。想走就走,想飞就飞。
我向往天空,喜欢在空中自由自在翱翔,谁也阻挡不了我的热爱和追求。参加各种滑翔伞比赛赢得奖金,是我赖以为生的手段。执着、有创意、勇往直前成了组委会宣传我的代名词,我被当成形象大使之一,个人竞赛照挂在官方网站首页。但不是每次比赛都那么幸运,很多时候,外出比赛变成了我省吃俭用的自费旅游。
我忍不住去了航空大楼。航空大楼像根又细又尖的刺,刺得天空血红。我姐是航空大楼的清洁工,跟保安不同。满脸粉刺的保安狐假虎威 :“你找谁,请出示证件。”“我没带证件。”“不能进。”我在门口拦住一个大波浪,很没礼貌地打听:“你认识邵红吗?”大波浪的眼神很怪,看我像看一个怪物。我不是怪物。大波浪才是。大波浪不说一句话,眼一瞥,头发一甩,大屁股对着我,刷完门禁卡,迅速钻进黑洞似的门。我猜,里面肯定怪物成堆。我姐会不会变成怪物?我狠狠扇了自己两耳光。随即打电话,把姐姐叫来。
“啥事呀,这么急?”姐的嘴角上掛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大燎泡。忍不住想将大燎泡挤破,我的冲动挠出一阵猴急,还好,被接下来的克制揪住了尾巴。我嘿嘿地笑。
“想你了。”我说。
姐绷着的脸从嘴角开裂,像一盘刚出炉的爆米花。“缺钱打个电话,何必跑一趟。”姐将嘴角扯来扯去,扯出了一个接一个风箱,呼呼风急。我说:“就想见见姐。”姐不信,迅速将一脸爆米花抹走。没来得及打扫,紧接着又炸出一颗,热乎乎的。“到底啥事,说呀。”我不能让姐失望,说出了心中的迟疑。
“打听一个人,你们公司有叫邵红的女孩吗?”
姐的抬头纹挤出一丝丝惊讶,数不清。
邵红要做我女朋友。我按女友的模样,如数家珍地将邵红描述了一遍,总算将姐的抬头纹抹平。接着问,“邵红在吗,我想见见她。”
“烧糊涂了吧。”
我的额头迅速被清洁工的铁扫把扫过。没痛感,怪事。
“邵红和女友到底什么关系。你说,她们会不会是双胞胎?”我摸了把好久没剃的络腮胡,笑得像个花面狸。接着,说了女友失踪的事。好像没说。又好像说完飞机失踪,还没来得及说女友在飞机上,就被姐的话打断。
“怀疑邵红是你女友,假装不认识你,跟你玩游戏?”姐问。
“想起来了,女友玩游戏时用过不少化名,邵红是其中之一。”
“别想了。邵红不长你女友那样。你描述的女孩叫林灵,不在公司,三年前,去了海南。”
邵红不叫邵红,叫林灵了,而这个林灵竟然远在海南。好吧,我接受。可林灵为什么自称邵红,而不是李红、朱红、杨红呢?是不是航空公司刚好有这么一个人,那个叫林灵的在暗示,找到邵红就找到她了?那天晚上,林灵给的手机号我到底记没记,或者,她根本没给手机号?这脑袋,一到关键时刻就不好使了。
姐冷冷加了一句,“你要找的邵红,三年前飞机失事,没了。”
“邵红没了,真的假的。姐,别骗我。”
邵红不在了。那么,林灵又是谁,林灵才是女友玩游戏的化名?看来,馥园路15号不去不行了。林灵为什么冒充邵红,是不是想告诉我,要继续跟我玩游戏?
开门的是一个满头卷毛的小男孩,一双好奇的大眼睛,让我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我。我儿子?我有儿子吗?我跟女友说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必须是儿子,必须长得像我,最好一头卷毛。这三年,女友一直躲着,是想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可眼前的小男孩至少有五岁。我外甥?都说外甥像舅,姐什么时候有了孩子,我怎么不晓得?小男孩一只手拿着纸飞机,一只手把着门,不让进,警惕地问:“叔叔,你找谁?”我还能找谁,找这间房子的主人。她说她叫邵红。后来,她又不叫邵红,叫林灵了。
“我找林灵。她在吗?”
家里全是纸飞机。茶几上、沙发上、地板上、墙上,五颜六色的纸飞机展翅欲飞。吊扇下还挂着一个飞机模型。我看了看小男孩,又看了看门上的阿拉伯数字,没错。小男孩纠正说,“不是纸飞机,是我妈折的千纸鹤。”我穿越了吗,我遇见了小时候的我?我家住1区3号楼,什么路不记得了,只记得门牌上有个15的数字。我是路痴,记不住路,却对数字敏感。我记得圆周率小数点后五十位数字,各种火车和飞机上一连串英文符号和数字。我还记得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攒够零花钱跟几个男同学一起烫了爆炸头。就因为一个叫林灵的女孩说我烫头好看,像她喜欢的一个男明星。我妈拦在门口说,家里不养狮毛狗。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满大街撵我。我上蹿下跳,左冲右突,将挡着的人墙撞成一只只东躲西藏的丧家狗。我姐后半夜在楼梯旮旯里找到我,摸着乱糟糟的卷毛笑,说我迟早会变成光头。
一个年轻女人踮着脚,跳着芭蕾舞似的,点过满地纸飞机中的空隙,跳到门口,手里摇着一把大葱,说:“阿弟,你又犯病了。”
好好的,怎么会病。得病了能在家下载翻译软件,还一连下了好几个?火星文输进去,翻译软件试遍,蝌蚪还是蝌蚪,在电脑里躺着,一动不动。蝌蚪生了病。蝌蚪的病毒把电脑感染了。鬼电脑也是,这么快起了霉。
“你脑袋才起了霉。”姐一边笑,一边在我眼前摇大葱。
脑袋起没起霉,姐说了不算。阳光说了算。阳光在公园泛滥,在手指间游走,抓不住。阳光下的叶子,白鹅般的紫。叶子上有名字,一片叶子一个名字。没有林灵。叶子下面只有蘑菇,真名叫真菌,或者叫甄君,不知是微信名还是抖音名,蘑菇长得像叶子。树枝已经光秃秃,像个癌症患者,这是真的。上吊瓶,打针。药该死的天牛。谁在耳边絮絮叨叨,烦不烦?树干上包着白衣,小名叫白大褂。据说白衣是某某某高徒,公开身份是医生。一个声音高叫着。可上午的月亮还挂在树上。月亮里有小屋、兔子、望夫石、滑翔伞,还有花生、吴刚、桂花酒、马丁尼。好多看不见的秘密。树枝上什么时候来了只鸟,好像那只银鸟,它遮住了月亮。没有风,风被冻住了。
张开翅膀,就来了风。又一个声音高叫着。
白衣拿起碗口粗的针筒,对着耳边喊,李仪容,醒醒,醒醒。我没易容,只是化装了。请尊重我的选择,三年前我就说过,我想两人过,不想一个人过。我想去翱翔。我喜欢比翼双飞的壮阔,喜欢心跳加速带来的视角冲击。
我讨厌火星文。就像飞机讨厌鸽子一样。我用简体中文向滑翔伞运动管理中心发出电子邮件,我要到天上找到最爱。运动员证、身份证、会员证,该有的我都有。我只缺健康。我要迅速恢复被霉菌侵蚀过的身体。
走进训练馆,好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进进出出,张牙舞爪。尽跟健身器械过不去。汗水,汗味儿,汗禢儿,挥洒,挥发。混合,交织,荡气回肠。窒息,难受,无奈,恨不得给每人一拳头。我看着埋着头的那个短发女孩,一阵阵冲动,一阵阵惶恐。始终找不到上前搭讪的理由。只能像大猩猩一样,出门后,一次次无声擂自己的胸部。
我和飞行伞、救生伞、头盔、护目镜、伞鞋、手套,一起飞到了起飞场。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玫瑰红短发,就是玫瑰红。林灵,这模样已深入脑髓,不管多久,在哪儿,永远忘不了。我像飞鸟一样飞过去,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人员、呼喊我名字的粉丝,他们仰着头,像一颗颗青黄的草莓。我在空中踩了一脚急刹车,平稳落在红头发女孩面前,像飞马收起双翅一样收起我的两臂。
“喂,假装不认识不是?”
“你谁呀?”林灵看着我,满脸傲视。将参赛证朝我一举,参赛证上的头像跟我女友一模一样,头发颜色不同而已。头像下三个方块繁体字。讨厌的繁体字。两个字不认识。啥时候改的名字?说话呀,你是林灵吗,你怎么会不是林灵,翅膀硬了是不是?想反悔明说。你不是林灵你是谁?当初在训练馆追女友,靠的就是死皮赖脸,死皮留着,一定要将赖脸进行到底。我伸出手,摸摸眼前的人是不是虚拟的,脸是不是依旧细腻、光滑、温暖。为啥长成女友的脸。
“你好,我是007,詹姆斯邦德。很高兴认识你。”
林灵低着头,继续摆弄她的器具,对我的热情与幽默置若罔闻。
我只能看着我的手在空中石化。
林灵第六顺位,我紧跟在后面。运动员一个接一个在起飞平台上下饺子,在又长又宽的峡谷中向前滑行。峡谷中溪流蜿蜒流淌,犹如一条又细又长的白花蛇。滑翔伞忽左忽右,时而向上漂浮,时而向下穿越。我努力控制滑翔傘的刹车绳,尽量保持不偏离航向。我看见两只大鸟在滑翔伞顶盘旋,估计是某种大型猛禽,鹰或者秃鹫。它们一定嗅到了什么。鲜血的味道,腐肉的气息?不祥的预兆迅速涌上心头。林灵红蓝相间的滑翔伞已偏离航向,向我右手边滑去。那边没有降落点,她想干啥,为什么选中右边的高山,那里隐藏了什么秘密?这是她早计划好的路线?我想喊,抠了抠喉咙,喊不出声。眼睁睁看着红蓝相间的滑翔伞渐行渐远,没入到一片郁郁葱葱之中。
组委会像个鸡窝。一群忙忙碌碌的鸡仔,叽叽喳喳,来来往往。放下电话,拿起手机。这群人递传真,递纸条,递可乐咖啡,递快递,随手扔下手中物件,丢手绢似的。电脑上的飞行轨迹,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满屋穿插游荡。电脑屏幕往下的曲线,往左往右的曲线。一条条蠕动的虫。一只只八爪手。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墙上挂满愁眉苦脸的大头照,灰暗冷色调镜框,一副副无人哀悼的笑容。女孩不少,没有红头发,没有惊喜的脸。鸡仔们埋头四处啄食,不理我。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寸头,麻子脸。我点头哈腰。我满怀期待。“叫啥名字?”“啊,没这人?三个字,两个字不认识,好多笔画,不知道念啥?你们干啥吃的,再找找。”麻子脸一脸严肃。又问:“你是她什么人?到底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问人家干啥。嫌俺们这儿不够乱吗?”
颁奖会上,喜洋洋的奖金广告牌,红光满面的奖杯,一起击鼓传花。直上直下。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证、志愿者证、工作人员证,一起交头接耳。时光一直在无原则地流淌,似乎在传递某个不祥的信息。刹那间,被流动的喜悦遮盖得严严实实。一场意外,不能说。就是一场意外,别到处瞎说。麻子脸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划开一道道横七竖八的血痕。人群中穿插着披肩红、辫子红、刘海红。个个像歪脖子火鸡。“不能将头发剪短些吗?”我控制不住了,逮着一个就歇斯底里地吼。
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忙个不停。电视、手机一起着急。山上,山下,涌动的人流。红头发、黄头发、红蓝绿头发,满脸带血的笑,一起构成毕加索的画。手机在床上小仙人似地跳。电视埋怨姐的声音太小。“报个平安不会呀?急死我呀。到底在干嘛呀。听不见我说呀。”终于完整听清了一句话。“你还好吧?”姐姐问。“我还好,没意外,没出现幻觉。女孩确实像林灵。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含含糊糊说啥呀。失踪,失事,什么乱七八糟的。早点回来。那个叫林灵的,托人问了。”“哦哦。”电视起劲地播竞赛花絮,插播救援实况,担架上刚有人躺着,广告强行占领屏幕。黑妹牙膏,晚安床垫,五粮液,金龙鱼压榨花生油。头痛,没带药,我要去药店了。
怎么感觉发生意外的是我。
三年,是个植物人也该醒了。
如果你不害怕,你就会无所畏惧。火星文被破解。谁他妈这么厉害。
姐异常热乎起来,日日问寒问暖。“没事出去走走,别一天到晚宅在家里。姐担心,姐为了你好。”“姐你别说了。”挂满各种比赛照的卧室,墙上玫瑰红画笔写的生日快乐,温暖如玉的小手,手机屏保上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闹铃上连串的银铃笑声。支离破碎。真相在姐嘴里。你要接受。你要吃药。你还要吃药。你不能多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跨不过去,飞过去。
姐的话豁然开朗,如醍醐灌顶。飞海南。那边,有时隐时现的林灵,即将浮出海面的女友。
坐在飞机窗口边,很快合上了眼。一路小颠簸,人老在现实和梦境之间切换。窗外有架飞机,与我坐的飞机并驾齐驱。女友坐在那架飞机窗口边。瓜子脸,清晰、白净,鼻梁笔挺。表情时而惊喜,时而恐惧,时而失望。拿出手机正准备打电话问,女乘务员马上过来告诫。“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再看窗外,一团像飞机的火烧云出现在天边。看得心痛,一阵阵痛。我只好再睡,希望阵痛很快过去。女乘务员轻柔的声音再次响起。不知说了句什么。我没在意,我在意的是她胸前的工作牌,猩红,凸起,醒目。邵红,乘务员。不会吧。我揉了揉眼睛。林灵,乘务员。不会吧。我再次瞪圆了眼睛。某某某,乘务员。两个字不认识。调戏人不是,欺负人不是?脸躲在兔子头面具后。今天什么节,飞机上有节目表演?枪口正对着我,像一个黑洞。洞中的脸尖嘴猴腮,狰狞地笑。谁跟我一样待遇。糟透了。得想办法逃出去。巧了,飞行伞、救生伞还在背上。哼,跟我玩,嫩点。我不管不顾跳出舱门,我制造了自由,顺便制造了风。对面飞机的舱门也打开了。一只红蓝相间的大鸟张开翅膀,朝我飞来,绕着我上下左右飞行。像跳舞的蜜蜂,像采花的蝴蝶。
终于破境了。很庆幸,掌心上有双温暖如玉的手。我一直记得它的样子。
【作者简介】杨震,1967年3月生于湖南岳阳,小说发表于《湖南文学》《啄木鸟》《创作》《短篇小说》等刊;现居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