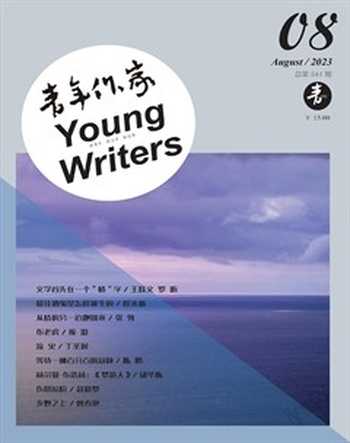意在象之外
谋求一个曲折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严肃文学的追求,在这方面,短篇小说尤甚。就我阅读过的短篇小说来看,故事都很简单,到底是体量有限,相比中长篇的杂漫,短篇更强调瞬间的爆发力,如同百米赛跑之于马拉松。爱尔兰作家特雷弗曾说,短篇小说是一瞥的艺术,像印象派绘画,它的力量在于其隐藏的东西和它写下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这种隐藏,一部分借助留白,另一部分,则是通过意象的设置。意象是意念和物象的审美契合,是一种表意之象,使其内涵丰厚,具有多种阐发的可能。
互为镜像的生活
有个人不小心掉进了一口井里,井很深,井壁光滑,且仅有一人宽,掉入者只能保持那个站姿。倘若无人营救,便只好站着死去,像一截木桩。他当然要大声呼救,最终来了一位好心人,讓人绝望的是,好心人搬起旁边的井盖封住了井口,出路再无可能。
这是短篇小说《井》的核心意象,也是整部作品得以成立的支点,有趣的是,这支点是“我”灵机一动胡诌的梦,梦是虚构的产物,关于井的梦便是虚构的虚构。因此,“井”只是一个虚体空间。这个值得玩味的虚体空间很形象地展示了“我”的生存现状——“我”的老婆对“我”没有多少感情,“我们”很久不讲话了,“我”儿子得了肺结核,“我”老丈人也快不行了,“我”爸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要钱。麻烦一个接一个,让“我”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我”悄悄从南方来到北方某地寻找在玩具厂打工的老婆,遇到一个在等按摩女的陌生男人。通过“我们”断断续续的交流,一鳞半爪地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本质上说,陌生男人的生活是“我”生活的完全镜像,同样是很年轻就结了婚,婚后他在北方打工,老婆去南方城市做按摩女,夫妻关系相当疏离,因为孤独、寂寞,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和一个按摩女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感情,这按摩女不是别人,正是“我”千里迢迢来探望的老婆。互为镜像的生活,二者都是千疮百孔的。
作为《井》的核心意象,我们可以将这个深坑视为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无论是变成甲虫无法逆转的格里高尔,还是永远无法走进城堡的K,实际上都被困于一口同样的深井。
小说里有个很趣的反转,故事最后“我”告诉陌生男人,那个关于井的梦不是虚构,是真实的,掉进井里的人也不是“我”,盖上井盖的才是“我”。因为“我”理解错了井底之人的意思,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并为此开心不已。
个人认为短篇小说里所谓的神来之笔在《井》中便是此处,作为读者,我们不妨将“我”的这番说辞视作一种瞬间的顿悟,井底之人是最初的“我”、本原的“我”,当生活的“井”将我们围困,我们自然希望有一个外部力量前来营救,他者的力量终是有限,更何况,将我们困于井底的不是外力,恰恰是我们自己。就如同我们一直诟病的现代人的生活,孤独、无力、不知所向,本质上看,现代人的生活不正是现代人给自己挖的井吗?
《井》是一个很标准的短篇小说,故事非常简单,甚至都无法称之为故事。阅读的过程中我数次想到了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卡佛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口井,同样作为困境的象征。
小说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故事,过于巧合的偶然性缺乏真实感和可信度,显出极强的人工穿凿痕迹;第二是语言方面,作者通篇使用了短句,大约是受极简主义风格的影响。问题当然不在于句子长短,而在于断句方式,比如这段——
“我老婆晚班,等天亮后再过去。到时,门一开,一两百个女工涌出来,她们从我身边走过,把我挤过来挤过去,但是,她刚出现,我就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你说,她会感动吗?”
很难想象现实中有人是这样讲话的。另外,人物语言和叙事话语的界限过于模糊,给人一种很做作的感觉。这一点其实和前面那一点是一样的,还是人工穿凿的痕迹太重。
灵魂的休息区
阅读《去森林的这天》的过程相当舒服。作者用舒缓的文字,营造了一个淡淡哀伤的冷白色世界。先说语言吧,这篇小说的语言倒也没有特别出色的地方,但,那种不是修饰的朴素和冬天的萧瑟,以及故事的整体氛围相当贴合。实际上,教创意写作这些年,在课堂上,我最不愿意讲的便是语言。总觉得这东西很难说明白,你无法孤立地去说哪种语言是好的,哪种语言不够好,语言,是最需要放到整体语境中看的。李白就喜欢用那些大的词汇,“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我们不仅不觉得空洞,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也因此建树起大气磅礴的语风,说到这里,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语言,其实是作者个性气质的文字化。
怎么说呢,这篇小说,表面看上去有些松散,几乎没什么情节,甚至连题目《去森林的这天》也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散文风。作者写了一个小女孩对冬天的期待,对下雪的期待,对去森林过冬的期待,这些期待都是环环相扣的,下雪代表着冬天来了,冬天一来,他们就可以去森林过冬了,也就有了合理的,从之前叫人窒息的生活中逃逸的借口。她的父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吵架,世界上当然不存在时时刻刻吵架的夫妻,但,作为受害者,她的敏感神经,会将那种频率放大一万倍。只有冬天,只有落雪的日子,只有森林里的小木屋,才能让他们喘息片刻。实际上,在森林中,父母也会持续争吵,就是说,这块所谓她的灵魂的休息区,从来就没有真正让她以及他们安宁过。本来也是如此,生活的本质绝不会因身处闹市还是深山老林而改变丝毫。依托外在环境的改变,实际上,什么都无法改变。我想到了卡佛的另一篇小说《需要时,就给我电话》,一对感情濒于破裂的夫妻为了挽救婚姻,把房子租了出去,一起到加里福尼亚北岸的帕罗阿尔多去度夏。本以为,在不同的地方,两人能够燃起重新开始的希望之火,却最终在一句“这,没用的,面对它吧”之中,而分崩离析。
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一块灵魂的休息区,不是吗?
值得说的还有峭壁上的山洞。和《井》中的井一样,山洞是这篇小说的重要意象。井是幽深、光滑、危险的存在,山洞同样的幽深,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那个没有父亲的小男孩却说,山洞里住着卡拉。卡拉是什么呢?卡拉是他的保护神,每当他挨欺负后,都会跑到山洞里,跟卡拉倾诉。而卡拉又总是保护那些备受欺负的小孩子,在他们难过的时候,会帮他们出气。多么美好,又多么叫人心碎的一厢情愿。在小男孩看来小女孩也是被欺负的孩子,理由是,她父母总在吵架。他的逻辑简单且顺理成章——所有被欺负的小孩都不快乐,她不快乐,所以,她也是备受欺负的小孩。然而,女孩并不接受这种说法。闪烁间,我们得以窥见,女孩在男孩面前的某种优越感,毕竟,她是有父亲的。因此,她不需要去山洞见卡拉,更不需要跟卡拉倾诉。《千与千寻》中,小千在父母变成猪后告诉自己,这是梦,梦会醒。好像是,不接受现实,现实就是虚妄的,不接受父母情感破裂的现实,家,就还在。
山洞是小男孩灵魂的休息区,正如,森林是小女孩灵魂的休息区那样。小说最后,在去森林的路上,他们家车子出故障抛锚了,父母又在为车子为什么会出问题而大吵其架。女孩走出车子,走下公路,穿过一片白桦林,走到一面峭壁前,“扒开枯草,手指触碰到枯草上雪的冰凉,枯草后面没有山洞,还是石壁。”这可真是神来之笔,生活的真相恰恰在此,我们追逐试图赋予的意义,其实都像那空空如也的石壁,所谓山洞,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附加。纵然如此,女孩还是遇到了卡拉,不同的是,卡拉不是如父亲般的男人,而是如母亲般温柔的女人,她用温柔的手抚摸了她冻僵的脸。这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安慰,在“不信”如晴空下那巨大的暗影笼罩于我们上空时,残存的一点儿“信”便显得难能可贵。
就这样,小女孩从梦中醒来对父母说她看到卡拉了。
徒劳以及重复
2020年初,西双版纳十六头大象集体北迁的话题长期占据热搜榜,关于迁徙的原因众说纷纭。
短篇小说《流火》讲述的并不是关于迁徙的故事。小说中,唯一和迁徙有关的人物叫柳梦梅,没错,和《还魂记》里那位由广东一路北上,最终迁徙临安的状元帅哥同名同姓,但非一人。由于二者终局的大相径庭,此柳梦梅和彼柳梦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对照关系。现代人的柳梦梅是一个欠着两万块网贷的无业青年,说他一事无成,似乎有些求全责备,毕竟,他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幸存者。
《流火》的框架很大,假如填料充分的话,甚至能写成一个长篇小说。作为短篇,作者的构思很有意思,小说中没有一个核心主角,三个人物,柳梦梅、冯梦龙、丁圣润并列,我们不妨称其为“平行主角”。三人都是失败者,但,失败和失败是不同的,后二者好歹还有一份工作,并且都有一个渺茫的希望。人生所谓的意义感,大约就是这个东西,渺茫,却不至于绝望。于是,三个被困于“井底”的人展开了一场厮杀,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有顶级掠食者才是最后赢家。
这篇小说里有个关键数字——三:三个人物、三条线索,以及由象群、人物和神话构成的三个世界,三个层级。象群北迁的故事是通过媒体报道呈现的,是虚写,类似于背景,影影绰绰;夸父逐日和西西弗斯两则故事构成了近乎于隐喻的神话世界。三者在精神气质方面是共通的,它们彼此映照,形成共振关系,让这篇故事极其简单(根本没什么故事)的小说产生了众声喧哗的交响乐的感觉。
值得思考的是,东西方神话故事比比皆是,作者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夸父和西西弗斯?现在我们来看看二者的异同:夸父追日强调的是执着和意志力,西西弗斯推着石头上山,则是宙斯对其傲慢的一种惩戒,二者的共同点是悲剧性和重复性。没错,“重复”是这个小说的另一个关键词。
“熟悉就会带来无趣。他不想无趣地行走,值班,下班回家,重复且重复。”
“没日没夜的虚无当然会催使自己制造刺激的事情。”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强迫性重复”。细细想来,现代人的生活,无非是从这一口“井”跳入另一口“井”,又从那一口“井”跳进其他无数的“井”,周而复始。所谓意义则像峭壁上的山洞,有还是没有,你自己说了算。
象群北迁的最终结局是安全南返,它们走了这一圈,意义是什么呢?没人说得明白。也许,连象群都没弄明白。
窥伺人性的窗口
现代社会的商业越繁荣,人们就会越焦虑。商业的本质之一就是制造和贩卖焦虑。比如,教育机构制造升学焦虑,整形机构制造颜值焦虑,保健行业制造健康焦虑。现代人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填满。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某次演讲时说,现代人的焦虑,基本都是源自对于身份的焦虑。
短篇小说《亲子鉴定师》讲述了三段关于亲子鉴定的故事,为了证明被证明者恰如其分的身份,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们纷纷选择了这家鉴定机构,如山铁证砸在每一个被鉴定者身上,引起一系列山崩地裂的连锁反应。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更是信任危机的时代,我们画地为牢,活成一座座孤岛。
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对于视角人物的设定,“我”是一位职业亲子鉴定师,借助职务之便,“我”得以窥伺一幕幕荒腔走板的人间闹剧。这一特殊职业如同一扇开向人性深处的窗口。“我”则象征着一种强势的介入力量。私底下,无论“我”多么富有人情味和恻隐之心,表现出来的,却永远只是也只能是职业的冰冷。正如纳粹狱警,在被问到,你是否知道,你們是把囚徒送往死亡?对方冷静地回答,当然知道,但新人要来,老人要给他们腾地方。因为我们是看守,看守的职责就是不让他们逃跑……
汪曾祺老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职业是对人的框定,是对人的生活无限可能的限制,是对自由的取消。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就会死在这个职业里,他的衣食住行,他的思想,全都是职业化了的。
那么,那个自然、个体的人去了哪里?
下面谈几点不足之处,作为短篇小说,《亲子鉴定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是小说的视角问题,有一处明显的硬伤,小说通篇都是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但在写到保安时,有一段心理刻画,“她早已经死了呀,保安在心里说道。他仔细地打量着男人,终究还是想起了什么,再一次望向男人,眼神之中竟有了一丝惶恐与不安在慢慢滋生……”这里变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造成叙事混乱;其次是故事,这三段故事目前都只停留在故事表层,缺乏及里的深度;特殊的素材并没摆脱猎奇效果,少了关于人生普遍性问题的挖掘和深化。
【作者简介】李苇子,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硕士,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当代》《花城》《大家》等纯文学刊物;有作品被《海外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著有小说集《归址》,现任教于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