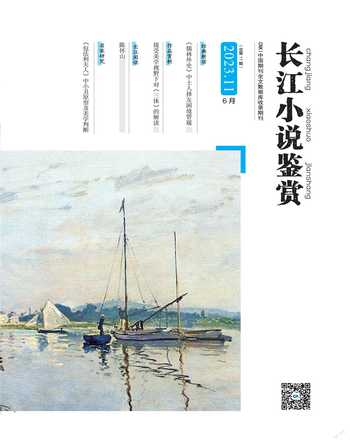“大书”与“小书” 《辞源》与“文章”
[摘 要] 本文立足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经历,对其在《从文自传》中提及的“大书”“小书”、《辞源》、“文章”之语进行阐释,讨论故乡湘西与“新书新杂志”所代表的两个世界给沈从文的影响,以及他对身处的文坛环境的态度,并以此探索沈从文如何认识新文学的力量,进而建立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自身的文学观念。
[关键词] 沈从文 《从文自传》 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61-07
1932年秋①,沈从文完成了以“我”为主题的写作《从文自传》。在回顾成长历程时,沈从文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1],“小书”“大书”是塑造了沈从文“自我”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概括了他作品的渊源,可以被视作其对自己的文学观念的陈述。在沈从文笔下,“小书”“大书”之别是用以给儿童开蒙的书本与他的故乡所代表的自然世界的区别,更是两种认识世界、与世间万物建立联系的方式的区别。
一位印刷工人让沈从文有机会阅读了“新书新杂志”,使他对“新文学”出版物所蕴含的“新的人生智慧光辉”倾心,这种向往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做司书时接触到的《辞源》。一位秘书官将这本“宝书”介绍给他,令他爱不释手,之后他们与老书记合订了一份《申报》,沈从文由此发现了一个充满“生词”和新知识的世界。种种陌生的阅读体验带来的震撼最终促使他远赴北京求学。以《从文自传》的问世为界,在沈从文早期的文学实践中,也能看到种种对于“小书”与“大书”的具体阐释。
一、“大书”:文学家的想象以外
沈从文在自传中提到,儿时逃学四处游荡的经历塑造了他“倾心于现世光色”的性格,实际上这只是故乡作为“大书”的意义之一。沈从文对“大书”——乡土世界塑造人的方式——的关注早已有之。自步入文坛开始,他就力图凸显一个在自然与“人事”方面极具丰富性、神秘性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独特的运作方式,即那里的人们对生活的把握。在多篇小说中,沈从文特意强调湘西的情形难以用文字描摹。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的开头写道:“不知道麻梨场麻梨的甜味的人,告他白脸苗的女人唱的歌是如何好听也是空话。”在描绘媚金的美时又说:“生长于二十世纪,一九二八年,在中国上海地方……的文学家……但请他来想想媚金是如何美丽的一个女人,仍然是很难的一件事。”[2]《婚前》描述五明的心理时说:“他的行为,他的心,都不是文字这东西写得出。”[3]这不仅是因为湘西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偏僻,城里人很难见识湘西人的真实生活,乡土生活尚未被新文学的“正统”所认可,用以讲述它的语言、形式仍在探索中,且当时的“文学”本身与湘西有巨大的隔阂。沈从文所說的“文学”特指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文学”,这是与文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有着统一的语言文字“规范”。毫无疑问,落后于时代脚步的湘西与“新文学”所属的环境相差甚远,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生活展示了当地人与“文学”的距离。
湘西人的生活是物质的,人们有与自然难以割裂的联系。在湘西世界里,情人们的爱欲受天气影响,农人、孩子时常与动物对话,人与水有很亲密的关系,人由自然孕育又无意识地与自然交融互动。湘西人获得的经验完全来自感官而非抽象思维,尽管在范围上是“狭窄”的,却较现代人的感知更为精细。欲望是沈从文湘西主题创作重要的部分,感官的、肉身的满足对他笔下的人物来说不可或缺,由欲望建立的关系总洋溢着饱满的情绪。湘西世界中还有离奇、神秘的因素,被归于“迷信”的想法体现在生活的多个方面。湘西人在偏僻的地域中这么浑然地生活着,“一切仿佛皆是当然的,别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永远全是这样”[4]。凡此种种都指向了“前现代”的人生样式,且不独湘西如此,“中国的大部分的人,是不单生活在被一般人忘记的情形下,同时是也生活在文学家的想象以外的”[5],这种生活样式在中国的乡野具有普遍性。
因而,五明没读过城市学生所需的性行为指南也不能作诗,却受好天气的影响无师自通得到了欲望的满足;四狗与女子调情时,含蓄高雅的古诗词并不应景,反不如一首措辞大胆的山歌。那里没有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替代它的是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表达爱欲的歌谣俗曲、关于神明的节日习俗、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仪式,五明面对阿黑的“表演”甚至也能算作“诗”。“大书”既展现了乡下人的生活方式,又展开了关于文学定义的探讨。张新颖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更大,与“天地”的概念相关;刘志荣认为,沈从文对文学的理解与“文”的概念有关,“文”容纳了“天文”“人文”的范畴,有与世界连通的生气[6],这也与“现象”构成的湘西世界、湘西人“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状态相呼应。
另一方面,尽管沈从文一再强调湘西世界是被排斥于文学之外的,但现实是中国农村已开始受到新事物的“侵入”,因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不是全然与世隔绝的地域。随着社会变迁的发生,许多乡下人离开故乡与外界接触,另一些人则从城市来到乡间,于是人们获得了陌生的知识,对未知的领域展开想象(作家本人的经历就展现了这一过程)。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不得不关注到两个世界的交汇。
《建设》中的工人不懂什么是“匣子”“盒子”;三三不明白护士的制服、体温计、计量单位“度”;萧萧从祖父口中得知了“女学生”的生活,却将汽车、电影院想象成“匣子”“庙”,并对这种夸张、不受拘束的生活产生模糊的向往,以至于在梦中成为女学生的一员……他们通过实际经验或他人的讲述,接触到一些新词语、知识,却又无法理解新式社会的真实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复杂而神秘的心情得到凸显。见到陌生的城里男子时,三三展开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她关注着城里人的白脸;在得知那位青年男子去世后,三三有了一种被现代人称为惆怅或伤感的情绪,它依旧借助日常性的行动得以表达。《一个女人》中,丈夫的离家、种种人事的变动让三翠“惶惑”,这种情绪则是由梦的内容的变化呈现。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带给人物心理的变化或成长,他们却不能理性地认识到这背后的意义或缘由。沈从文作品的内涵与出色之处,正是对两个世界的交汇处展开的描述,在“前现代”的环境中,一些难以解释的情感、欲望在作者笔下浮现,沈从文写过着“结实”生活的人物行动中的停顿、延宕,写他们的泪水和梦境。在叙写时,作者并没有使用都市题材作品中常见的长篇议论、讽刺或人物独白,只是含蓄地讲述暧昧、难以捉摸的心理。
对于都市读者来说,沈从文展现的“大书”无疑是陌生而具有异质性的,不过沈从文的书写中也有他们熟悉的因素。金介甫认为,沈从文以生活为“大书”之语可能与陶行知的理论相关,而他对原始文化、民间传说的兴趣则是受到了周作人的影响,他们都从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和人的道德[7]。当沈从文试图以现代语言展现湘西生活时,他难以完全复现那些原始的思维方式,他的书写是在现代人的视野下展开的“文学家的想象”,通过人类学的知识、“新文学”的技巧对人物心理进行剖析。
二、“小书”:“趣味”与“技术”
初入新文坛,沈从文尚不熟悉这一套新的机制,不知道如何使用标点,不懂外语与外国的理论,在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时,他还未掌握各种来自西方的文体间的区别,将散文式的作品算作小说。经过大量的阅读和一系列的尝试后,沈从文渐渐了解新文学场域中的规则,对文坛的潮流保持着一定的敏感度。在学习与写作的过程中,沈从文也接受了“五四”以来确立的“文学”的概念,并形成了对新文学的评判标准。在之后被收入《沫沫集》的一批作家论中,沈从文提及了“文体”“形式”“组织”等术语,且由《论郭沫若》一文批评郭沫若的“文学手段”只适宜于檄文、宣言,不适宜于小说[8],可见沈从文理解了何为“小说”不可或缺的特质,获得了一套系统化、专业化的文学知识,他也借助这些术语来传达自己的态度。同时,因为发表了大量作品而成名的沈从文已然参与到新文坛之中,并在其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在创作时,沈从文愈发注意作品的形式、结构,关注讲故事的技巧,这使他获得了大量读者,成为“职业作家”,他的作品“成为目下中国年青人的兴味所在的东西了”[9]。
作为创作者与大学文学课教师的沈从文又在作品中流露出对新文学体制的不满。沈从文以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体验为素材,写了一批都市题材的作品,要想了解新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样貌与暴露出的困境,这些作品是很好的研究对象。
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不断扩大、出版业的繁荣,对一代青年读者来说,“文学”(尤其是“内面的”,探索青年最希望了解的人生、恋爱问题的作品)在帮助获得知识和人生经验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学书籍逐渐成为当时青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沈从文在早期的一些都市作品中植入了当时流行的人名、书名、报刊名等,在叙事中也有意强调书本对于人物行动的影响,这显示了当时的人从报刊、小说、“恋爱宝典”等中得到种种关于人生的知识,名词、话语、观念的快速传播,影响甚至塑形了他们的生活。“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学来的他那一分感想”[1],然而,“新書是什么呢?一个故事,流点眼泪,叹一声气,算是新的成就么”[10],一些书籍满足了读者对新鲜感与趣味的需求,但不能带来深入心灵的影响。
如果说沈从文早期的湘西题材作品展现了极其宏大的“文学”世界,那么其都市题材作品则暴露了“文学”变得极其狭窄的境况。这类作品多从个人生活出发,带有“自叙传”色彩,表现了穷困知识分子物质与情感生活的困顿。姜涛指出,《松子君》通过一系列的手法展现当时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空间,又通过“我”的嘲讽从内部颠覆、间离这庸俗的文学消费的循环[11],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也展现了这样的意图。当沈从文将主人公设计为文人时,他常常将其困难的写作状态暴露出来,《一个天才的通信》是此主题下较为典型的文本。它以作家给编辑的书信为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写作的写作。在都市题材作品中,沈从文时常在叙述中夹杂几句议论、感慨,而这部作品中叙述的停顿是特别的。主人公需要以长篇稿件换稿酬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因而在讲述自己生活的困苦时,他不时停下来发出“我写这些写了三行……十万字是三千行或一百三十页,眼前我对那所期望的数目,距离是如何远近,我应当明白了”之语,宣告自己已写多少字,距离稿酬有多远。同时,因为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他也不得不中止叙述,发出“我不写下去了,我得小心防止我鼻孔的血流到这纸上”“我头实在不行了。真要炸了。我实在愿意抄一点什么来补足这通讯字数”的感叹。主人公自述反复写“日头”“流汗”之语“原来是我一种技术。我正要别人从我这唠唠叨叨中发现我是怎样的无聊”[12]。姜涛从一些作品中的“硬写”叙事看到新文学创作变为“内部的符号循环”。而《一个天才的通信》对“硬写”处境的呈现更为直接,主人公一开始就无意认真创作,直言只是为稿酬而写作,还将其当作引以为傲的“技术”,对于无聊、苦闷甚至敷衍、“凑字数”的写作过程的暴露,解构了“幸福写作”(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超脱现实功利的创作过程)[11],表达了对日趋封闭化的新文学书写的抗议。
如果不将《从文自传》中提到的“小书”局限于开蒙的课本,那么也可以将市面上售卖的、与读者的趣味相关的、由作者通过一定“技术”而生产出的作品视作“小书”。面对新文学这方面的困境,姜涛提出,沈从文的态度是“赋予文学生活一种‘脱域之后‘再嵌入的历史品质”[11],在讨论他的态度之前,本文先考察沈从文是如何接受“小书”传递知识的模式的。
三、《辞源》:掌握“新名词”的“秘笈”
《从文自传》不仅强调了“大书”的影响,还暗含着自己如何学会阅读新文学这类“小书”的叙事。与秘书官成为朋友后,沈从文听他劝告放下粗野的话,去学世界上的好事情,秘书官又将自己了解的新兴事物教给沈从文。使用粗话俗语是乡下人自然的习惯,他们并不熟悉另一套更文雅的表达,而秘书官口中包含中外各国的“世界”对乡下人来说更是陌生的。秘书官不仅在对话中悄然打开了沈从文见识和想象力的边界,还向他介绍了《辞源》与报刊,即帮助人掌握分布于“世界”中复杂精细的知识的方法。这之后,职务上的需要又为沈从文带来了发现传统的契机。他在铜器、旧画、《四部丛刊》《四库提要》中遨游,萌生出对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对本民族的过去逐渐有了认识,让他有“不安于现实的打算”,而姨夫关于“哲学”等的谈话使他“幻想更宽”[1]。这些教育让沈从文发现原来那“结实”的世界可以向历时、共时两个方向延展开去。
产生“内部精神生活变动”的沈从文进入新报馆做校对后,发现“新书新杂志”为他的好奇与困惑提供了一种答案。学习了白话文、掌握了“新文学”的表达方式之后,沈从文“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他不仅钦佩新式人物“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的抱负,感叹“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也被新式出版媒介的效率所惊讶。他发现“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的存在,仿佛自己与“新人物”非常熟悉,并通过向《民国日報·觉悟》寄信捐款给“工读团”来和另一片土地上的人发生联系,此行为也帮助确证了他跻身于这新世界的可能[1],这样的阅读反馈正与安德森所述的报刊文字、现代小说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相吻合[13]。最终,“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促使沈从文前往北京,“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1]。
在描述自己“内部”的转变时,沈从文频繁使用的词汇不再是“看”而是“学习”,且他常常使用“渊博/无知”的对照叙事,他最重要的“学习”途径是阅读书籍,而沈从文对“宝书”《辞源》的态度有意味地象征了他向书本学习的方式。
《辞源》由商务印书馆“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编纂而成,其内容是词语的起源和用法[14]。孟悦的研究指出,《辞源》的问世其实富有深意,此书诞生的背景是“明治语汇”(用日文翻译的外国词语)的传播愈发广泛,使新的词义对词语本义有所“侵占”,它们的背后是“以语词为表征的现代文化实践”。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隐含着对“文化霸权”的干预,此书展示了翻译词语的历史源流,试图以此消除翻译带来的新用法与已有用法之间的隔阂,这“提供了向符号现代性挑战和批评的方式”[14]。然而,对秘书官和沈从文来说,《辞源》是一部使人便捷了解词语含义的宝典,是用以夸耀自己知道“不拘一样古怪的东西”的工具,沈从文从中学到何为《淮南子》、氢气、参议院等,但他似乎不甚注意这些中西名词的渊源,也不明白西方概念被译介进入中国意味着什么。
沈从文们的反应代表了一种较普遍的对新名词的接受方式。在考察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时,王德威注意到其中的辛先生有一本秘籍,它分门别类地记录了外国书籍上的词汇名称,有了它就能将一切西学书籍翻译得清楚流畅。在王德威看来,这“能够轻易地把所有新的词汇、观念、知识转换成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的“秘笈”代表了知识分子对“启蒙法宝”的想象[15]。而沈从文们对《辞源》乃至其他涉及西学知识的“小书”的态度,以及文坛试图引入西方文学形式、理论而不加消化、深思的做法,不也正是“秘笈”式的吗?
如果不局限于讨论西方知识的引入,可以发现,在沈从文正式进入新文学场域后,他和他的书也在不经意间扮演了《辞源》的角色。沈从文的第一部文集《鸭子》中的一些作品含有方言土语,作者在《赌徒》的正文前附上了“这也许太专门了,非另做一篇骰经作注不可。因其字字须注,反而不下注解!乡土性分量多的东西,纵注也很难使外乡人体会”[16]的说明;《论冯文炳》一文中,沈从文也说自己希望通过小说“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17],这暗示了沈从文的创作类似于解释湘西世界的“辞典”。此外,进入大学教书后,沈从文开始讲授小说史、小说习作、新文学研究方面的课程,这意味着曾经对“新文学”茫然的他已完成身份转换,有资格面向一批与从前的他相似、从各地聚集而来的学生传授知识,为了给学生示范,他还创作了多篇“习作”。
不论是对自然世界,还是对以新文学为代表的世界,沈从文都已经驾轻就熟,于是他与他的读者、学生构成了知识传递与接受的关系,“秘笈”式的接受再次出现。一方面,沈从文赢得了读者的推崇,不过许多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带有“误读”的成分。他们没有意识到沈从文想要刻画的是另一种人生形式,只是为故事的传奇性、趣味性所吸引,或是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关注乡土生活,更有批评者指责他是“以轻飘的文体遮蔽了好多人的鉴赏的眼”“诱引着读者们于低级的趣味”,认为他是主动迎合读者而创作的作者[18]。另一方面,沈从文的学生们问他怎么写文章,“逼到我(沈从文)开书目一纸”,却“不相信我劝他‘去生活的话”[19],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速成的“秘笈”。
某种程度上,在人们借助“小书”获得新知的时代,文本进入文学空间而成为读者简单获取一些知识、满足自身趣味的载体,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也是文学日益符号化、商业化的处境导致的。沈从文希望文学以自然的感染力影响读者,而不是竭力追逐读者的兴趣、时代的潮流,然而由于他在小说组织上使用了一定的技巧,又触及了人的爱欲,许多读者仅仅被小说叙事层面的内容所吸引。“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20],沈从文意识到他的作品在接受层面的“失败”,这“失败”又与其他种种因素一起使沈从文展开了对文学的限度与力量、对自己是否继续选择文学的思考。
四、“文章”:“抽象”价值的寄寓
事实上,自开始创作以来,沈从文就多次对自己的作家身份产生动摇,他在书信、杂文中提到不愿再写作,希望做一个匠人、军人,或回故乡生活。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创作,并且由一位多产的作家转变为成熟的作家。面对“小书”象征的现状,如姜涛所说,沈从文的姿态是“脱域”之后“再嵌入”,有一种从内部审视、反思的意识。
刚开始创作时,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重在传递地方性知识、风俗,而这片地域孕育的精神价值在作品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被誉为文体家的沈从文不断尝试各种形式,以确认文学的效果,到《龙朱》《凤子》这样的作品问世时,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世界又呈现出另一方面的样貌。龙朱象征着“诚实,勇敢,热情”的“民族健康的血液”[22],《凤子》则提及不会消灭的“神性”,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和爱”(《凤子》中人物表达爱慕时,使用的不再是“不雅”的歌谣,而是诗意的话语)[23]。在描绘了湘西物质式的生活方式后,沈从文又试图对其赋予意义,他为他的人物增添了善良美好的人性,他的小说更加注重结构的组织,在趣味故事的叙述中增添了哲思的内涵。对乡土“抽象”价值的展现与都市现实、现代社会的弊端自然形成对照,不过凸显城乡对立并非他的终极意图所在,沈从文希望以文学表现“人生的形式”[20],通过虚构更深刻地唤起读者的想象,让他的作品发挥的作用不局限于“辞源”而成为“文章”。
《从文自传》中有“若猜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1]之语。在描述自己的写作时,“文章”是沈从文喜爱使用的词语,在杂文、文论、书信中,他常常以“写文章”指称自己的小说创作。参考研究者对相关概念的梳理可知,相较于“文学”,“文章”与前文提及的“文”相关,从古代文论的表述来看,“文章”容纳了自然万物,它与“文”一样反映了中国“文学”概念的缘起。进入20世紀后,“文章”的语义逐渐转变为“散文体”,而由西方输入的“文学”占据了“文章”原先的含义,并为中国带来了一种更具系统性、学科性的“文学”概念[24]。沈从文使用“文章”或许只是出于习惯,不过此概念流露出的对于古代文论的“回归”又与他的创作暗合。《文心雕龙》有“人文之元,肇自太极”“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之语,容纳天地的“文”与形而上的“道”相关,蕴含着终极性的追求[25]。而沈从文对文本内部艺术性(“章”)的重视,对小说中“抽象”的强调都与古代文论的思路相似,都隐含着对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反思。形成了这样的文学观后,沈从文在回顾过去时也使用了相应的叙事,他讲述自己在宇宙万物中发现了“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1]。对于“抽象”的领会也奠定了他后期文学活动的基调,他之后在《习作选集代序》中直言想建造供奉人性的小庙,在小说中寄托汲取湘西的品质而重建文明的态度,都可以追溯到此时形成的文学观念。
于是,沈从文的“大书”之语也就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既说明了湘西人认识世界的原始的、非逻辑的方式,又说明了湘西之于现实的力量,这本书不仅提供了许多地方性知识,还暗藏着智慧与道德。另外,“大书”一词本身也暗示了沈从文眼中湘西世界与现实的关系:当沈从文回过头来叙述湘西带给他的影响、展现出的品质时,湘西已经被他在特定的视野中“对象化”了,它本质还是“书”,在这一层意义上,“大书”一词与沈从文对于文学的期待相近,它描述了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力量与限度的把握。
注释
① 这一说法来自沈从文在1980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从文自传〉附记》。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从文自传[M]//沈从文全集 13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M]//沈从文全集 5.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沈从文.阿黑小史·婚前[M]//沈从文全集 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 沈从文.我的教育[M]//沈从文全集5.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旅店[M]//沈从文全集 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8] 沈从文.论郭沫若[M]//沈从文全集 16.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 沈从文.19301105复王际真[M]//沈从文全集 18.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 沈从文.春天[M]//沈从文全集 6.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1]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 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M]//沈从文全集 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3]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 孟悦.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15]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6] 沈从文.赌徒[M]//沈从文全集 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7] 沈从文.论冯文炳[M]//沈从文全集 16.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8]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M]//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邵华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19] 沈从文.19300318致王际真[M]//沈从文全集 18.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0]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 9.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1] 沈从文.杂谈 六[M]//沈从文全集 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2] 沈从文.龙朱[M]//沈从文全集 5.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3] 沈从文.凤子[M]//沈从文全集 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4] 李建中,孙盼盼.文章与literature:中西文论如何言说“文学”[J].学术研究,2017(5).
[25] 刘若愚,杜国清 .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孙丽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