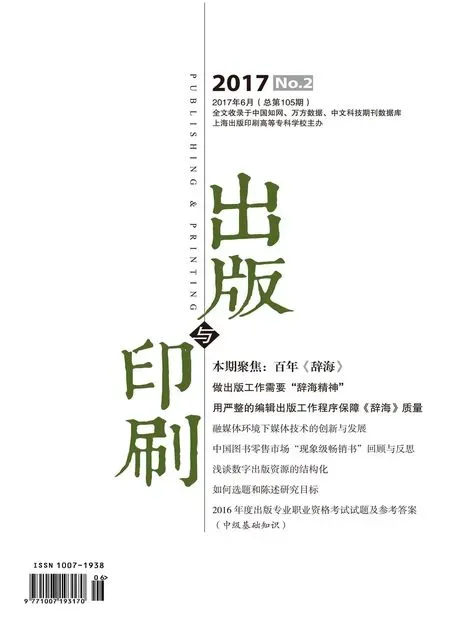《辞源》修订工作散记
乔 永
《辞源》修订工作散记
乔 永
《辞源》是商务印书馆的镇馆之宝。《辞源》第三版的修订,商务印书馆《辞源》项目组做了大量创造性工作。本文从准备、认识、模式、育才、百科、注音、体例、书证、成绩、遗憾、问题、聘人、开发等方面,回顾了这次修订工作的一些做法及其得失,为大中型辞书编修提供践行借鉴。
大型辞书;辞源;辞书修订;商务印书馆
《辞源》是我国近现代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在近现代出版史与印刷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辞源》始编于1908年。1915年的初版,不仅为现代辞书之嚆矢,其装帧插页也采用了彩色印刷技术,领出版与印刷风气之先。其后修订多次,陆续出版了续编、正续编合订本和简编本等。1958—1983年《辞源》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由综合性辞书转向古汉语辞书。1983年,四卷本《辞源》修订本全部出齐。20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新世纪的首次修订,这一次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修订,我们有幸参与了《辞源》修订项目的准备、启动、编辑直至最后出版的全过程。《辞源》第三版出版已近两年了,辞书界的朋友在一起还经常谈起《辞源》的修订,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回顾、讨论和思考,认为有关《辞源》前贤的奠基之功和崇高精神应该费点心思,好好写一写。
拙作《辞源史论》对《辞源》出版的百年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但当时为了配合《辞源》新版的新闻发布会,编写和出版的时间紧迫,有些问题、想法还来不及系统梳理。这次,《出版与印刷》的编辑同仁给我出了个题目,要我在《辞源史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一下《辞源》第三版的修订工作,给《辞源》和其他大型辞书的修订以理性的借鉴。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静下心来,对十多年来参加《辞源》修订的组织工作和编辑、出版的情况进行了一番梳理、取舍和思考。借此不揣鄙陋,将所思所想与同道分享。
一
2007年2月,商务印书馆全面启动《辞源》修订项目,成立了《辞源》修订领导小组和《辞源》修订项目组。以此为标志,《辞源》修订本(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其实,对《辞源》修订的研究、思考与准备,远远早于2007年。在1983年《辞源》修订本出齐后,总纂吴泽炎先生就在考虑重新修订。他有一个深远的打算,他说:“我们打算根据新《辞源》的内容,再一分为五,出《辞源简编》《辞源语词编》《辞源成语熟语编》《辞源订补编》《辞源资料编》,和《辞源》相辅而行。最后再加修订,精益求精,永无止境。”如果吴老的这个计划完成了,后面的修订就方便多了。可惜当《辞源》修订本出版后,编辑们陆续转到了其他图书的编辑工作中,吴先生的这个计划落空了。
20世纪90年代,有些编辑也曾试着做过《辞源》简编本,可惜由于部头大,拖的时间过长,也夭折了。只在刘叶秋先生的带动下,出了一本《成语熟语词典》。这些遗憾希望今后不再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惦记着《辞源》的修订。1999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酝酿《辞源》新一次修订,并启动了商务印书馆辞书语料库项目,着手为新一次《辞源》的修订做好资料和人员的准备。2003年8月,召开了《辞源》修订论证会,邀请曹先擢、唐作藩、王宁等先生讨论修订事宜,但由于主编人选、时间进度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2006年,《辞源》修订工作得到中国出版集团的支持,被中国出版集团定为“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出版项目。2007年,《辞源》修订项目正式启动。《辞源》修订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重排《辞源》修订本,对硬伤进行挖改;第二步,展开修订工作。项目组决定出版《辞源》修订本的重排本,并做了一定的修改,对《辞源》的字形、注音、释义、引文、出处、标点及体例格式等技术性问题做了全方位研究。为了纪念《辞源》编纂10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09年9月重排版正式出版时改名为《辞源》纪念版。
自2009年《辞源》纪念版出版,到2015年12月《辞源》第三版完成并出版,历时整整八个年头,历经杨德炎、王涛、于殿利三任总经理的关心与推动。2007年,杨德炎总经理任修订领导小组组长启动修订;2009年,王涛总经理全力推动,并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有了资金保证;2010年,于殿利总经理拨出《辞源》项目组办公用地,全力支持。至此,为《辞源》修订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了资金和工作场地保障,做好了资料和人员的充分准备,促成《辞源》修订工作的最终完成。
我很幸运,一进入商务印书馆就被安排做《辞源》修订的资料准备工作,着手进行《辞源》与《汉语大词典》的注音比较研究。2007年,进入《辞源》修订项目组,参与了《辞源》纪念版和《辞源》第三版的整个修订和出版工作。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我们不仅熟悉并记住了《辞源》编纂的前辈陆尔奎、傅运森、高梦旦、杜亚泉、方毅、庄俞、孟森、刘秉麟、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的英名,还深刻地体会到前贤们对《辞源》的忘我奉献精神。《辞源》是商务印书馆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始终激励着商务的后辈辞书人。
二
要修订《辞源》,必须先熟悉《辞源》,认识《辞源》前贤的奠基之功。《辞源》为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守正出新” 百年主旨,提供了全新的颇具文化特色和内涵丰富的鸿篇巨制。
《辞源》始编于1908年,1915年出版,历时八年编纂,“使用资料10万多卷,耗资13万银圆”[1]5。《辞源》是中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大辞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汉语工具书。《辞源》正文以单字字形、笔画为排列依据,将复词附于单字字头之下。这种排列方式,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大型辞书编纂的基本模式。当年,主持《辞源》编纂工作的陆尔奎说:“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他强调了辞书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一语中的。[1]16
其后,《辞源》历经了多次修订。1922年,方毅和傅运森主持《辞源》续编的修订,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7年,傅运森和唐凌阁主持《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修订工作,1939年,《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在香港出版;1947年,商务印书馆筹编专供一般读者使用的《辞源》简编,1949年,《辞源》简编出版。30余年间,续编、增补、合订、简编等,都是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完善,但体例和宗旨都没有改变。[1]5-8
1958年,中央出版工作计划决定修订《辞源》《辞海》,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并对三者进行了明确分工,确定将《辞源》修订成一部大型综合性古代汉语辞书。至1983年9月,《辞源》修订本四卷全部出齐,历时25年。《辞源》修订本单字仍按214部首排列,收词条已达9.7万余条,总字数1000余万。[1]8《辞源》修订本由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主持编纂,前后400多人参加修订工作。其中,吴泽炎20余年为《辞源》做了30余万张词条卡片。1994年,《辞源》修订本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1]8-13
通过对修订资料的检编,我们加深了对《辞源》的内容和民族文化性质的认识。《辞源》涉及面十分广泛。它以214部为经,始一终亥,通过214部首编排,以1万多字头和10万多复词的释义包括书证,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字、词、语,以及附着其上的广博的传统文化。全书1200万字,内容丰富详赅,人物风俗、山川地理,几乎尽揽其中,纵横勾连,既汇聚了语言文字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高雅的文化,也让传统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服饰文化等内容登堂入室,既呈现经史子集,也蕴含了诗词曲赋,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渊源和参差多态的风貌。《辞源》编纂者与历次修订者始终秉承着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宗旨,勤奋耕耘,一字一历史,一词一文化,字斟句酌,用字和词语为载体,传播着知识,传播着文化。
我们理解到,修订《辞源》不仅仅是一本辞书的修订,更是对古代文化知识的重新审视和阐释,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一项文化工程。我们每天徜徉其中,博览群书,欣赏和享受千年文化的盛宴。而在以后的修订过程中又不断从千百词条的查证、修补中充分享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快乐。《辞源》修订完成以后,我们深深感受到,《辞源》不仅仅保留和传承了中华文化历史的财富,也是我们商务人给后人留下的一笔永存的精神财富。
三
《辞源》第三版历经八年修订,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7—2010年是准备阶段,项目组准备研究资料、文献语料,将铅排本改为激光照排版,完成词语百科分类,以及编辑、编务培训,项目组拟定修订方案与体例。第二阶段为2011—2015年,聘请主编、分主编和修订人员,完善体例,完成试修订,完成审稿、编辑加工和排版,修订工作全面展开并完成。
一般辞书的编纂与修订,主要由编纂者或修订者操觚完成,出版社编辑只是负责常规审稿、编辑加工和编务工作。但《辞源》的这次修订,除了修订者、审稿者的努力,《辞源》修订项目组编辑继承了商务印书馆辞书编纂的历史传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这次修订工作可以说凝聚了学界三部分专家力量。一是由主编和审稿专家组成的审稿力量,二是由分主编和修订者组成的修订力量,三是商务印书馆《辞源》项目组的编辑力量。[1]22
项目启动前,项目组编辑们就分工合作,花了多年时间深入地对《辞源》修订的历史、宗旨、体例和释义、书证等进行研究,对百年来历次修订的字头选择、注音模式选择等都做了详细考察,编辑们合作申报了《辞源百年修订与现代大型辞书研究》社科基金选题(连续三年没有申报成功,成为遗憾)。这些研究工作为《辞源》的修订提供了很多工作思路和建设性的意见。
本次修订注重顶层设计,聘请了何九盈、王宁、董琨三位主编,负责整体方案和体例制定,对稿件进行终审,对修订质量全面负责。并在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聘请20余位知名学者担任语词十二集和百科各组的分主编,围绕各个分主编组建了100余人的修订队伍。这支队伍的许多专家后来又成为《汉语大词典》《辞海》的修订者,使很多辞书都受益。
大型综合性辞书修订都有“条条”“块块”之分,按部首顺序分部为“条条”,把某些学科领域的词目从各部首中取出来分科汇集,就是“块块”。
《辞源》收录的全部是古代汉语词汇,以字带词,语词与百科并存。正是考虑到该书的文化特性,本次修订坚持按“条条”和“块块”结合的模式修订,于是以此采取了相应的修订组织形式。“条条”以《辞源》的十二集分十二组,每集由分主编负责;“块块”分三组,也由分主编负责。编辑组同样也分成词语组和百科组,分别与修订的“条条”组与“块块”组对应。于是“条条”和“块块”同时铺开,开始了修订组与编辑组紧密配合的全程大流水作业。
根据本次修订“以条为纲,条块结合,块并入条,及早统合”的指导思想,总体上以十二集为轴,三组的百科条目、注音和字形字头与增补的内容,完成后归入十二集统稿整合。各组修订人员分工明确。分主编负责各集修订工作,包括任务分配、进度监控和质量把关。各集的修订人员负责该集内容修订,完成修订后由分主编负责审稿。项目组的责任编辑与资料人员为分主编和修订人员服务,提供相关资料,负责稿件流转,进行稿件编辑加工等。修订稿完成后由分主编审稿、签字,交予审稿专家审稿,最后由主编定稿、签字,交责任编辑编辑加工。先完成的先发稿,根据各集进度流水作业。责任编辑还要负责与主编和审稿人衔接。
这条修订流水线的重中之重在分主编。回想起来,由于各个分主编聘任的修订人员情况不同,有的请同事或同门师兄弟,有的请学生,执行力各有差别。与各集对应的责任编辑负责发稿、收稿、验收,再交审稿专家审定,最后合稿,编辑加工。流水作业,20余组,100多人,都必须分别对待,落实到人,其中甘苦,外人难以体会。
修订刚开始不久,项目组的编辑就着手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对字头的选定、对注音模式和字音的甄别等。在修订体例的制定过程中,编辑与修订者一起写样稿,与审稿者一起审样稿,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修订稿的试修阶段,编辑提前介入,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并提出问题。修订工作全面展开后,编辑更是全程跟踪修订者、分主编、审稿者的修订进度,确保修订质量。
四
大型出版项目对出版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一百年来,《辞源》的编纂和修订为国家和商务印书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出版专业人才。
这次修订基本上贯彻了“音义契合,贯通古今”的《辞源》修订思想,并且首先从项目组编辑开始践行。这不仅是修订的需要,也是“实战”中锻炼、培养辞书编辑队伍的方法。
在修订《辞源》过程中,我们逐步加深对辞书文化的认识。以前,对《辞源》的开创者和百年以来的历次修订者了解得不多。这次,通过整理《辞源》百年以来的各种资料,我们对《辞源》修订历程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从20世纪初主持初版编纂的陆尔奎、方毅,合订本的傅运森,到修订本的吴泽炎、刘叶秋等人。每当看到他们曾经改动过的稿件,就揣测他们修改时的心态、理念,心中充满尊敬与感激。(这些资料郑州大学图书馆保留了一些,很多流落到了社会上,令人遗憾。)《辞源》不仅使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出现了繁荣,而且也开始呈现出文化事业上的辉煌。每一次,这些杰出的辞书人物的涌现,都会使商务印书馆的辞书队伍和辞书重镇的模样渐显。可以说,《辞源》修订工作是延续着前贤们的伟大事业,延续着传统的辞书文化。
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撰与修订历经百年,每次都带动了一拨一拨编辑人才的成长,使得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队伍不断壮大。在这次新的修订中,怎样做传统文化的编辑,怎样站在时代的高度,推动辞书文化的发展,是日日萦回在我们脑际的问题,到现在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让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在这次《辞源》修订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能力。
几年的孜孜以求,爬梳剔抉,与修订者、审稿者的共同工作,探索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辞源》百年来历次编纂与修订的先贤时俊们的了解。也由此证明,我们个人的选择只有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作为一名编辑,一生中可能会编很多书,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流传后世的书,不是所有的编辑都能遇到,特别是像《辞源》这样出版百年的大型辞书。我很荣幸,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后续的维护与开发,与文化传播的崇高事业同发展,这种经历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与快乐吗?赵克勤先生曾经说:“要感谢时代,如果《辞源》早几年修订或者晚几年修订,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什么事了。”
五
《辞源》百科条目和注音问题是这次修订中的两大难题。
《辞源》是一部以字头和词目形式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大型辞书。修订之始,我们就比较了目前大型辞书的特点,将所有百科词条按人名、地名、器物、服饰等分类,有4万余条。有些词目内容是大家都熟悉的,很多词目内容是大家不熟悉的,由于参与的修订者多数是高校从事汉语史研究的专家,对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百科诸如动物、植物、器物等较少研究,如果这些条目放在以十二集为轴的“条条”中修订,修订者肯定生疏而费时,必有疏漏或失误。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了“条条”和“块块”结合的模式,在高校、社科院组建了百科的专修队伍,聘请社科院历史所专家和高校熟悉古代文化的汉语史专家学者,进行专项修订和专项审订。由于有相关专家的操作把关,这些百科条目的修订质量和时间就有了保证,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辞源》的注音问题也是一样。注音是辞书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性也特别强。修订注音前,我们就对现有的大型辞书注音模式做了研究,收集到了全部古代注音资料和现代大型辞书的注音模式。研究到位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例如,选哪一种古音理论作《辞源》的注音的指导呢?经过对理论的研究和对各种辞书注音的反复比较和细心鉴别,我们认为,王力先生关于古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理论较成熟,较合适,而且在《王力古汉语字典》中也有实践,被大家普遍接受,认为可以据此实施。这个注音体系对汉语语音史的发展变化有较好的说明,有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语音的演变和发展。《辞源》注音体系独特,与字形、释义关系密切,力求反映汉字音义的历史演变,做到音义契合,古今贯通。[1]133考虑读者需要,注音分为三段:现代音(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中古音(据《广韵》和其他韵书)+上古音(上古韵部)。
由于修订者关注点不同,水平不同,对现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理解与标注有差异。除在修订方案中制定详细的体例,请修订者严格参考执行外,鉴于修订者的古汉语音韵学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另组织了审音专项组,采取了修订者通修与专项审定双管齐下的办法。审音组历时5年完成对1万余字头和10万余辞目注音专项的审定。最后,由项目组编辑和审音的专家负责,将修订者和专项审定者的结果比对,找出异同,发现并解决问题,力求辞书注音准确、完美。
当然,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修订项目组的工作量。修订组增加了字头、审音和专项百科的修订人员,《辞源》修订由原计划的百人增加到150人,投入的经费也相应增加。
六
体例和书证是《辞源》修订中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每本辞书必须有编纂的体例,没有体例就成不了好的辞书。《辞源》当然也有自己的体例,但当年编纂之时,并没有留下很多书面的条文。2007年《辞源》修订项目启动以来,我们下大力气做了《辞源》百年历史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可以说对《辞源》百年的历史和目前的现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知道了《辞源》初版的优点在哪儿,修订本的优点在哪儿,它们又有哪些不足,怎样弥补,这次修订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还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通过几年的研究,我们对《辞源》都已谙熟于心。基于前期的研究,2009年制定《辞源》修订方案体例时,我们能就修订目标、修订宗旨、修订体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时进行完善,有了修订可遵循的体例,这样避免了中途返工等问题的发生。
《辞源》新的修订编制了详细的体例,从内容到形式规定了此次修订的原则与要求、编排方式、字形取舍、音义注释的样式与书证选取的原则,以及插入图形与符号使用等需共同遵循的做法。[1]205
书证是大型辞书释语的重要内容,而引用古籍的书证向来都比较复杂。《辞源》引用的全部是古籍的书证,如何选择古籍和书证,选择哪一个版本的古籍,对辞书的质量至关重要。初版和修订本等过去的历次修订,由于引书的来源不同和制作书证卡片的人所依据的版本不同,造成《辞源》的有些书证出处不尽统一,如《左传》和《左氏春秋》,《白虎通德论》和《白虎通义》,《辍耕录》和《南村辍耕录》,《荆川集》和《荆川先生文集》,《还魂记》和《牡丹亭》,等等,这些书名在不同词目的书证中出现。它们其实是同一种书,只是书名不同罢了。此外,还有版本的问题,如《杜工部草堂诗笺》和《杜工部集》,《白香山集》和《白氏长庆集》,等等,这些内容涉及对语料如何整理的问题。
2009年,通过梳理《辞源》修订本全部18万条书证,我们统计出了4000余种引用古籍文献,以从多、从准、从优的原则采用使用最多的引书格式,做出了每种文献引书书证的体例,编辑了《辞源引书格式》,请每一位修订者参照执行。
一般来说,《辞源》所收的词目,以及释义和书证所依据的资料,都应该是较好的和较完整的古代典籍版本。根据《辞源》满足读者阅读的求真和求源的原则,如果能在已有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一个与字头、词目的最接近使用来源的书证,那是最好的。这样的书证不仅可使读者正确地理解释义,而且可从根本上保证辞书的质量。因此,《辞源》这次修订在引用书证方面,下足了功夫,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得力于对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商务印书馆的电子语料库功不可没。
七
我们按时完成了《辞源》第三版这个“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项目,为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献了礼。
《辞源》是百年来不断创新的成果,包括编纂理念创新、内容创新、编纂体例创新、释义和注音创新、书证选择观念上的创新。[1]10这次修订,是在《辞源》已达到相当高度的基础上展开的。修订者们继承了历次修订的传统,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又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机科学的检索手段,故无论是字头、词目的数量,还是释义、书证的质量,抑或排版、装帧,都比前版有所提升。[1]17
新版《辞源》收字头14210个,复词10万余条,插图1000余幅,附录7种,另有拼音和四角号码索引,总共1200万字。我们为修订《辞源》编撰了《辞源研究论文集》《辞源研究资料汇编》和《古汉语资料索引》等三本资料书。另外,我专门撰写了《辞源史论》,总字数近300万字。这些副产品为《辞源》和其他大型辞书的修订,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它们和新版《辞源》一样,为读者、为辞书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为热爱《辞源》的读者提供了新的精神食粮。
有关著书立说,章太炎先生曾说过“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名言。辞书编纂借鉴已有辞书的经验,这方面后出转精的例子很多。《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从《辞源》吸取过营养。而《辞源》新的修订,又广泛采撷这些辞书的精华,更上一层楼。《辞源》居五大辞书之首,历经多次修订,如何做到“后出转精”,文字内容与编校质量超过前版,我们都深有体会,其中有两点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的语料准备和学术研究的领先。
后出的词典借鉴先出的词典,有其普遍性、合理性和必要性。[2]大型辞书无论编纂还是修订总是后来居上的。《辞海》晚《辞源》20年出版,与《辞源》竞争,吸取了《辞源》的优点,在字头义项分立和书证来源上比《辞源》初版有所进步。同样,《辞源》1939年的合订本、1964年的修订稿,也吸取了《辞海》的优点,释义书证更加精密。新的修订,一定要做到“后出转精”。我们这次修订也不例外。
我们针对曾有过的“《辞源》无源”的批评做了深入研究,下了功夫。《辞源》这次修订就特别强化语词的探源,查明语词的来源和始见例。编务人员在《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电子语料的基础上,核查全部书证,主要做了全部书证择优更换工作。修订者根据《基本古籍库》等计算机语料,全部重新校订了书证,对发现初版的和修订本的一些文字差错和缺漏做了改正。
《辞源》是现代读者通向古代文化的桥梁,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国学热、传统文化备受青睐的今天,《辞源》的修订可为推动传统文化的精准传播服务,也为学习、研究和应用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八
回顾《辞源》修订的过程,也留有很多的遗憾,有许多工作可能做得还不到位,或做得不够好。也有些问题,当时想到了,但限于人力、物力而没有做,这些遗憾都只能以后多加注意,并力争弥补。
做一个大型辞书资料库,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收集了百年来研究《辞源》的书籍和论文,收集了与辞书编纂有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还有文献、书证等资料,下载了1万余篇相关论文,我们想把这个做成数字化资源,供修订者使用,可惜人力和时间都不允许,这次就没有完成。
我们也曾想把《故训汇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按字头剪贴,附在每一个《辞源》字头下,供修订者修订时参考比较。最后也由于客观原因,只剪贴了《故训汇纂》。这个工作以后还可以继续做。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10余位编务人员坚持了4年将《辞源》所有字头和复词词目在《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中检索一遍,按语料时间选取6个例句,供修订者与原书证斟酌对比,考虑释义或书证的修订。
我们还对全部百科词目进行了分类,共64大类4000多小类,对收字收词的释义、书证等都有帮助。
在字头和复词的收录方面也有点遗憾,就是《辞源》的修订工作虽历时八年,但在时间安排上仍显仓促。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应该尽可能再从容一点。由于《辞源》篇幅的限制,还造成了某些百科辞目收录不全,留下了缺憾。修订项目组应该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关注字头和词目。如动物类词目,修订本已有4000多条了,限于篇幅,严格控制新增数量,很多便只能割爱了。与之相对应的是百科插图,我们准备了3000余幅图,限于篇幅,只用上了1000余幅图,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
九
大型古汉语辞书修订,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选择优秀的修订者和审稿者。修订的人找对了,修订工作就成功了一半。《辞源》修订有三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一支是修订者队伍,由修订者和分主编组成,十二集,每集设分主编一至两人,修订者5—8人。另一支是审稿队伍,由主编和审稿专家组成,共10余人。还有一支是编辑队伍,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编务人员组成,负责稿件流转、检查,以及编辑加工,这是修订工作运转的核心。在修订过程中,修订专家、审稿专家和编辑三方面人员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辞源》争光添彩。
《辞源》修订很难,修订者不仅要熟悉古汉语文字、音韵、训诂和古代文化知识,有较好的学养和古文功底,而且要有很强的责任心,真正爱惜自己的名誉和学术生命。只有这样的专家,在辞书修订工作中才能甘坐冷板凳,不浮躁,不敷衍,遇到疑难问题会找工具书、找别本,甚至请教同行专家解决。如果修订者的修订工作不到位,甚至出现讹脱、误增、误释、误读、破句等“夹生饭”,该改的不改,不该改的乱改,审稿者和编辑面对这样的稿子只能叫苦不迭。
修订者共100多人,人数多,来源复杂。有高校的教师,有科研院所的研究员,有在职的年轻教师,有退休的老专家;有北京的,有全国其他城市的。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投入不同,诉求也不一样,例如,高校教师希望能算工作量,要求提供原新闻出版总署的项目书、项目证明等。针对这些问题,项目组竭尽全力,密切协助,处理好各种关系。
无论是聘请修订者还是审稿者,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有用人的遗憾,影响工作。例如有个别修订者迟迟不交稿,或者修订不到位,分主编、审稿者也偶有疏忽,致使稿件进入编辑加工阶段还存在诸多错讹、不规范等问题。又如有些专项的部分内容的修订,有些修订者新增加的内容少,修订也不到位,有些该改的没有改。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在编辑加工阶段吃了不少苦,虽然是极个别的情况,影响却很大。这是今后其他辞书修订时应该注意的。
辞书修订要见真功夫,要求修订者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要求修订者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些专家虽然功底很好,但囿于时间或责任心还不够,没有核对文献资料,没有使用最新的材料,或者没有按照修订体例执行,虽然我们在编辑加工阶段竭尽全力加以弥补,但也留下些许遗憾。出现这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原因很多,可能还和高校教师的生存状况有关,高校要考核教师的科研论文和工作量,修订辞书在某些高校既不算科研论文也不算工作量,而且稿费相对比较微薄,这也影响到个别专家的积极性。
大型辞书修订在试修订阶段物色修订者时应该下足功夫,不能只依赖推荐专家的意见。前期试修订、试审稿,项目组应该做好一对一的培训工作,而不能仅依靠分主编转述。我们虽然开了30多次会议,主编、编辑也尽量跟修订者多沟通,现在回想起来,前期对修订者的了解还是要更充分一些才好。
十
大型辞书编纂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推进。辞书编纂方法的进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而有些问题学界有争论,必须在编纂过程中对读者有个交代。怎样吸收专家意见,集思广益,考验着修订者、审稿者、编辑者的能力和良心。
巢峰先生曾有大型辞书修订“三分修订,七分管理”的话,我们深有体会。例如,在字头和词目的选择上,修订体例虽然有明确的要求,要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新增内容。但由于新增难度大,修订者在收录的标准与数量上把关不严,标准没有很好地统一。有些部首缺失了一些理当收录的词目,而混入了少数不当收录的词目。某些修订人员对词目选择随意性加大,而一审、二审等修订审订者未能严格审查把关。最后,项目组编辑只好自己从语料库、书证中爬梳整理,新增字头共2000余个,再交专人编写,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在词条撰写的标准上也不够统一,如有些百科词条的内容义项设置欠一致,从而导致词条内容的要点的把握各自为政,甚至造成要点残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还是在于修订者的专业水平不够,责任心不强,而审稿者又把关不严,一时失察。
《辞源》资料的收集上仍有很多遗漏。一是台湾近几十年相关的《辞源》资料收集得很少。二是对已经收集到的资料,真正吸收到修订中的也不多。学无止境,书难尽美。还有某些字头分合、书证的辨别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当然,修订过程中专家们也有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给《辞源》添了彩。特别是2015年初,请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审读的四校样的意见,有很多非常中肯、到位,当时由于时间紧无法全部吸收,只有留作下一次修订或做音序版时吸收采纳了。这也是今后辞书编纂更上一层楼的宝贵财富。
所以说,辞书编纂始终是遗憾的工作,学无止境,辞书编纂与修订只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十一
我虽然多年从事辞书的编辑工作和汉语史研究,有一些体会和总结,但都是零碎的,这次有幸和众多专家投入到《辞源》的大项目中,编辑的综合能力和水平都得以提升。回想起来,这次修订过程中一路走来,甘苦冷暖自知。我能担任编辑室主任和《辞源》修订项目组副组长,应该也是修订工作的最大受益者。修订过程中,我还主持了《辞源》审音项目组的工作,与审音专家一起拟定条例,决定取舍,受益良多。在后期,我还承担了《辞源》插图、四角号码、附录等修订任务的组织工作。修订完成后,扩大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可以做更多更难的工作。
近来,我回头再次仔细审读修订者的原稿、专家的终审稿和编辑的加工稿,揣摩、体会作者修改的原因,专家终审的取舍,以及编辑加工的咬文嚼字,收获更多,这是难得的经历与财富。回首与《辞源》修订者、审稿者、主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深深感慨学海无涯,有良师益友相伴,我们是何其幸福。我庆幸自己的青春年华能与《辞源》相遇和厮守,这是我的福缘和福分。八年之中,书里书外,不仅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史知识素养,而且积累了编辑大型辞书的经验。
《辞源》是商务辞书人永远的事业。商务的掌门人于殿利总经理、周洪波总编辑在设计方案时就让我们充分考虑后续音序版、电子版等版本的开发工作。为此,新版与方正字库沟通,更新了字头数据库。这些都是《辞源》修订对辞书编纂有益的探索。
《辞源》第三版及其优盘版、电子版出版后,我们即着手开发音序版,至今已经一年多,目前已完成音序的前期研究准备和编纂方案。当然,音序版的推进是艰难的,如音序版到底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排列方式,还是以《现代汉语词典》的排序方式,曾再三斟酌,与数字中心的领导、同事反复沟通,不断尝试。我审读并编辑加工了D母100页和R母100页,除注意单字注音顺序外,对复词排序、辞目与释义的照应以及书证的审读等反复咀嚼,非亲历亲为者所难体味。
《辞源》在我国近现代辞书历史上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在辞书编纂方法、编辑体例、语料应用、内容主体等方面,都进行了卓越的探索,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的示范作用。这一次的修订也不例外。
欣闻《辞源》第三版入选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编辑同仁无限感慨。
散记于此,请正于方家。
[1] 乔永. 辞源史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6.
[2] 徐庆凯,秦振庭. 辞海论[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