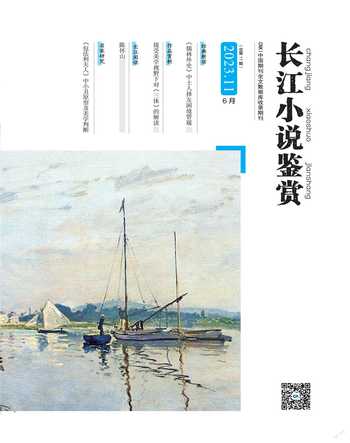论王旭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审美意义
[摘 要] 当代女作家王旭烽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这些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打破家族传统的女性;第二类是经历了痛苦的女性;第三类是反抗命运、张扬个体意识的女性。本文拟从这三类极具独特性的女性形象出发,梳理王旭烽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从中发现作家独特的审美思考与女性意识。
[关键词] 王旭烽 女性形象 审美意义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15-04
王旭烽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其在创作之初并未受到学界太多关注,直至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才算真正走进大众视野。除代表作《茶人三部曲》外,王旭烽还创作了一系列质量不俗的小说,这些作品既体现了作家对地域文化传统的热爱,又展现了其对时代转型洪流中的人情、人性的关注。
或许因为王旭烽自身的女性身份带来的创作倾向和审美偏好,其小说中女性形象占据了重要位置。作家善于书写女性的美丽,同情女性的不幸命运,注重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本文将结合小说文本,对王旭烽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打破家族传统的女性
以家族为母题创作小说,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中国的传统家族首先是一个父权的“等级制实体”,家族小说在书写家族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过程中,女性始终属于从属地位,是男性的附庸。“家族制度与父权统治是互为一体的,不管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少女,或是生活在贫民之家的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她们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女性在家族世界要么是显示男性权势地位的符号,要么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与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1]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是以陪衬者或牺牲者的形象出现的,然而在《茶人三部曲》及《望江南》中,王旭烽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家族女性形象。
第一类是母亲形象,她们是家族的实际掌权者。林藕初与沈绿爱这对婆媳,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小地主的女儿林藕初敢在婚礼当天解救被清兵追捕的长毛吴茶清,也敢在对无能的丈夫彻底失望后转而向吴茶清求子;她对权力的追求也毫不遮掩,一面努力振兴杭家的茶叶生意,一面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与崇拜,成为家族的实际掌权者。沈绿爱少时喜欢在乡野山间采摘野茶,又去上海见过世面,身上那种天然的野性使她过于强大也过于生机勃勃,杭天醉对其蓬勃生命力的害怕让她感到失望和无聊,继而将全部心思转移到家族茶叶生意上。沈绿爱光彩照人,对自身女性魅力有着绝对自信,在发现丈夫包养外室后,沈绿爱展开了对丈夫乃至整个杭家的复仇行动,然而这场复仇行动并无真正的赢家,夫妻二人皆伤痕累累、身心俱疲。沈绿爱可以在遇到理想爱人赵寄客时大胆追爱,也可以为了家族责任放弃爱情,在婆婆林藕初去世后成为家族掌权者,支撑着杭家的茶叶生意,在乱世中艰难前行。林藕初与沈绿爱不是那种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成全男人事业、赢得男人尊重的女性,她们有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追求。
第二类是女儿形象,她们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勇敢追求自我情感的表达。杭嘉草与林生、杭寄草与罗力、杭盼与曹家远的爱情故事在乱世之中显得更加浪漫而凄美。林生与杭嘉草一见倾心,然而林生共产党员的身份让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遭到攻击。杭嘉草并不畏惧死亡,爱使这个胆小而聪慧的姑娘变得勇敢,两人在茶神陆鸿渐的小瓷像前拜了天地,林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后,杭嘉草陷入疯癫状态,直至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下。杭寄草继承了母亲沈绿爱爽快明朗的个性,她与国民党军官罗力相识相爱,罗力因参加抗日战争南下,最后来到了滇缅边境。杭寄草的爱炽烈而纯粹,她追随着罗力的脚步,在一次次错过后,两人终于在边境重逢。杭寄草与罗力在漫长岁月中就这样长久地处于分离状态,直至满头华发才终得相守。杭盼与曹家远几乎复刻了姑姑杭寄草的爱情故事,身为国民党飞行员的曹家远退居台湾,多次想要返回大陆未果,历经艰难回到大陆后因身份的敏感和个人经历的特殊而被关押。无论是互相隔绝、不通音信的等待,还是未来希望的渺茫,杭盼并不感到痛苦,爱能够战胜一切。王旭烽曾说:“对我来说,人生是重要的,而在人生中,爱情是最重要的东西,除了爱情,亲情、友情、事业、生老病死等也很重要。当然,对于女人来说,爱情就构成了她的人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情爱是很重要的主题。”[2]作家将自己的爱情观投注在了自己塑造的角色身上,杭嘉草优雅、杭寄草明媚、杭盼纯粹,在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中她们并未迷失自我,反而愈发勇敢坚韧。
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中,一方面,家族中的男性家长掌握着话语权力,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第二十幕》中的尚达志等,由男性叙述的历史彰显着男性的价值观与立场,而女性则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在家族叙事中隐身。另一方面,家族中的女性或沦为作家揭露黑暗封建制度的工具,如《家》中的瑞钰、梅、鸣凤,《雷雨》中的繁漪等;或沦为家族斗争中的牺牲品,如《古船》中的隋含章,《罂粟之家》中的刘素子等;或以自己的牺牲成就男人的事业,赢得男人的尊重,成为男人事业的陪衬,如《旧址》中的李紫痕、《白鹿原》中的仙草、《第二十幕》中的盛云纬等。
然而在杭氏家族中,由男性所建构的性别权威、道德楷模和创造历史的神话被女性话语解构,传统男权本位的家族生活与家族伦理被打破,小说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本位意识。正如小说中所说:“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杭家之幸。三十多年前送来了林藕初,三十多年后又送来了沈绿爱。”[3]她们的命运有相似,有重复,然而她们却都选择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抗争、不屈不挠。她们拥有健全的人格,拥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七情六欲,她们是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而不是“符合男权社会规范的‘无我的空洞的能指符号”[1]。时代环境并未给女性提供尽情展示与宣泄的舞台,无论是杭家的母亲还是杭家的女儿,她们都从未逾越家族茶叶生意中关于女人不能到前台的规定,也从未想要与时代做“蚍蜉撼树”的抗争,正如王旭烽所说:“这些女性的悲剧,带着自觉和自由,有着独立人格的魅力,温柔而有韌性,是我最欣赏的江南女性。”[4]在杭家的大院中,她们敢于展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也不会因为环境的制约而郁郁寡欢,她们美丽、聪敏、坚韧、敢爱敢恨,她们对爱与自由的追求、对责任的坚守,展现出不同以往家族小说的女性魅力。
二、经历了痛苦的女人
在男性话语内部,贞女节妇是被歌颂的,而这种歌颂则是以被剥夺自我意识与言说权利为代价的。花木兰、穆桂英之类的巾帼英雄毕竟只是少数;苏小小之类清高自傲、至情至性的千古名妓,则更多地承载了历代文学家们浪漫的文学想象,并不会成为当时的歌颂对象。但在王旭烽的小说中,作家塑造了这样一群经历了痛苦的女性形象,她们虽经历了世道的蹂躏与蹉跎,然而却又保有纯洁与美丽,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使这些女性呈现出了神秘与可爱交织的面容。
改写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断桥残雪》,将故事背景放置在民国初年。小白本是从四川峨眉山妓院逃脱的妓女,投奔亲戚无门后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后因美色招致海师长的垂涎,又逃至杭州被小青和许宣所救,小青因救她惹来了海师长的报复,小白为救小青而死。《曲院风荷》中的女尼聊无,在出家之前为挽救家庭的不幸而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般的精神将自己舍弃了出去,出家是为了忏悔以洗净自己肮脏的身体,然而在赫明眼中,聊无与佛交融,“他仿佛看见一尊侧身的佛像,由一些灵动和起伏不定的弧线勾勒而成”[5]。聊无像是为救苦难而降生于俗世间的佛,皈依佛门是她的命中注定。《茶人三部曲》中的杨白夜,初恋情人的死亡以及父亲因政治迫害而受的折磨使她对人生产生迷茫,时代将她定义为有罪的女人,她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假如我们在中世纪,我就是被绑在十字架上被烧死的女巫。”[6]她在自我放逐中一次又一次地寻求自我的解脱。《斜阳温柔》中当归夫人有着纯善的心质和慧敏的头脑,作为亡国之君李煜的后妃,她虽在宫变中落下残疾,面容也毁了,却先后吸引了将军水丘执雷和吴越王钱俶的爱慕。
作家不厌其烦地塑造的这一类女性形象,一方面体现了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结合,美丽使她们陷于苦难,而苦难又使她们愈发美丽,相较于身体上的纯洁,作家更注重心灵上的纯净与美质,“而‘残雪意味着被侮辱过同时又是纯洁的美,它映照着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千疮百孔的生活”[7],显然,这里的美具有深刻的哲理意义。女作家丁玲于20世纪40年代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提出的思考,如今在王旭烽的筆下再次浮现,而作家的回答也是显而易见的,借用许宣老人所说:“可是我要说,这样的面容如今是绝不会再有了……现在不会再有这样一张既深情又羞愧,既守贞洁又解风情,因为经历罪孽风尘却反具可爱与神秘的面容了。唉,年轻人,是谁说过,我只爱那经历了痛苦的女人。”[5]另一方面,作家在两性关系的建构中体现出了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他们同情她们的遭遇,也沦陷于她们久经风霜后呈现出的美丽与悲戚的面容,他们真正将女性视为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思想、有独立人格与生命意识的个体,而不是只将女性当作自己爱欲的对象。
三、张扬个体意识的女性
近现代以来,文学创作对于女性地位与解放的关注也愈来愈多。对王旭烽来说,关注女性命运、注重女性自身发展也是其小说的重要内容。在作家的笔下,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对自我价值的诉求以及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寻觅,呈现出女性的个体意识。
《闯荡》中,迫于环境的苦闷,青梅子想要逃离江南小镇,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青梅子与周华明、元顺本是初中同学,周华明爱慕青梅子,但她却选择了多情活泛的有妇之夫元顺;在与元顺私奔途中,男人的懦弱展露无遗,他中途逃回,而青梅子却誓不回头,即使心里没底也仍旧向着未知的远方走去。《人精》中,端阳的幸与不幸完全是由她自己掌握的,为了不成为马兰婆婆的拖累,即使所嫁之人并非良人也仍旧嫁了过去,她受虐待后回到小镇再嫁,重复第一次的命运。端阳敢于选择,大有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品质,这其中蕴含着作家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虽然这种个人价值极其单薄。在《有关五个女人》中,作家以花喻人,并从“我”这个旁观者的视角讲述了有关五个女人的故事,小说中既“有对生命常态中的异态或极态现象的惊叹和迷惑,也有对人性复杂性的剖析和思索”[8]。《鸡冠花·拖来》的开篇描写了像一大摊暗红色鲜血在涌动的、奇诡的鸡冠花盛景,故事也由此展开,拖来母亲与拖来先后遭到了挑夫父子的奸污,拖来五年后外逃归来,在夜里杀死了那对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这样一桩血案,如拖来一般的弱势女子的悲惨命运将永远被掩藏在大山深处,始终没人在意。作家既表达了对人性的野蛮的控诉与批判,又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如果说《闯荡》《人精》等作家的早期小说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还较为浅薄,那么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则呈现出了更为独立自主的面貌,如上文提到的《茶人三部曲》《爱情西湖》等。王旭烽于21世纪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衣人》采用了虚与实两种叙事笔调,故事以雷峰塔为坐标,以现代男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一方面串接起了苏小小、白娘子和西湖边刘庄八姨太的故事,同时也再现了古城杭州的百年历史风云。经过科学考证的八姨太的往事与绿衣人叙述的八姨太与青年军官的爱情故事,既形成了两个叙事极端又重叠在一起,达成了一种纯粹的真与虚的复合。绿衣人用自己的女性话语解构了真实,提供了另一种言说方式。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达到了更深的层次,即提供女性言说历史的方式与可能。
从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至今,王旭烽已不再执着于用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女性生存的困境和女性的自我价值诉求。她的写作逐渐走向了圆融和谐的境界,女性个性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增强,打破外在环境的束缚已不再是女性的第一要务,她们开始向内寻求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自我言说的权利。《茶人三部曲》中,小茶在生命终止之际喊出的那句“我还有我”,对她而言或许只是一种无力的自我宣泄,然而在女性与那些既定的教条、命运抗争时,“我还有我”不仅是其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也是其最强大的武器。
四、结语
王旭烽笔下女性形象的形成大致来自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南文化与北文化的交融。王旭烽大致有两个创作场域,一个是其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富阳,一个是其十三岁时搬到的杭州。无论是富阳还是杭州,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都属于南方,这一地区的人文景观和历史底蕴带有浓重的吴越文化色彩,顽强进取、至爱自然、秀美壮丽是吴越文化的特点。但王旭烽并非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她的祖籍在北方,家庭环境使她深受北方精神文化的濡染。成长环境与家庭环境的双重作用,使作家既受到南方文化精神的影响,又受到北方文化精神的影响,在两种文化的熏陶之下,作家的创作兼具南方的清秀俊逸和北方的粗犷豁达,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体现在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这些女性形象既内敛秀美又顽强坚韧。
第二,作家自身的审美选择。“总体来看,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人类由男女组成,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强调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怎样,实际上作为男人也有痛苦,没有退路,不能流泪,男人若是这么叙述就陷入在男性自己当中,女性若这么叙述就陷入在女性里了。”[9]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其强调自身应该怎样时就会陷入自身的叙述之中,永远挣脱不了性别的桎梏。承认女人的生理天性并不代表接受既定的限制与束缚,基于此种审美选择之下,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不断做出新的尝试,由此呈现出了多元的女性形象群。
王旭烽是一位坚持自己艺术个性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个性特征。王旭烽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其特有的情怀和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观察和叙事方式,塑造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丰富了女性形象史中的文学范本。
参考文献
[1] 曹书文.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 王旭烽,李润霞.《绿衣人》:绝对的真实,绝对的虚构[J].中文自学指导,2005(1).
[3] 王旭烽.南方有嘉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舒晋瑜.王旭烽:且将新火试新茶[N].中华读书报,2022-03-09.
[5] 王旭烽.爱情西湖[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6] 王旭烽.筑草为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 孙雯.王旭烽:建造纸上杭州[J].文化交流,2022(8).
[8] 邢小利.从谜江到西湖——读王旭烽的小说[J].小说评论,2002(4).
[9] 曲茹.女作家三人行:陈丹燕、徐坤、王旭烽[J].作家,2001(6).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张迪,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