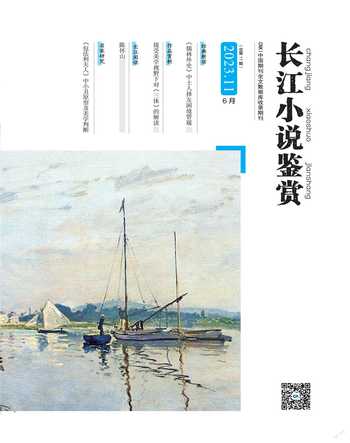魔幻古朴与现代色彩
[摘 要] 彝族作家英布草心长篇小说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诗化特征,其诗化语言表现为丰富的修辞性语言、庄严的诵经式语言、明快的歌谣式语言以及多样的哲理性语言。小说的诗化语言兼具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是彝族文化和汉语表述方式深层融合的产物,既带有原始、古朴、浪漫和魔幻的意味,又带有现代汉语简洁明了的中正情韵,是多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令其小说有一种融合古朴质感、浪漫风格、魔幻色彩和现代色彩于一体的诗意之美。
[关键词] 英布草心 长篇小说 诗化语言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11-04
当代彝族青年作家英布草心用写诗的方式来写小说,十分重视对语言的锤炼,并探索汉字的多种组合和多元表达。迄今为止,英布草心已创作长篇小说七部,包括《天堂悠云》《玛庵梦》《阿了》《归山图》,以及“彝人三部曲”《第三世界》《洛科的王》《虚野》。这些小说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诗化特征,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追求。诗化语言,即诗歌一般的语言,具有诗的美感和特质,是诗化小说独特美感的重要体现。语言的诗化不仅在于语言形式的诗歌化,还在于语言表达的内容和营造意境的诗意化。作者从小在四川大凉山长大,接受汉彝双语教育,汉语是他的第二母语。“文化混血”造就了多元时代的“文学混血”,这种“文学混血”在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之间不断寻求生存空间[1]。作者既写诗也写小说,他用小说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小说时,他用彝语思考,汉语写作,写出了带有彝族思维、文化和风格的汉语。他曾说:“当我用汉语创作,所表达出来的文字其实是穿越了两种语言模式,从而变成单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模式。”[2]他穿行于彝、汉两种文化之间,用汉语表达他对世界的认识、对彝族文化的溯源、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等,其小说既有彝语的原始、古朴、浪漫和魔幻,又有现代汉语的简洁明了和中正之美,构成了包蕴汉彝文化双重美感的诗化语言。
一、 丰富的修辞性语言
英布草心长篇小说综合运用了现代汉语常见的修辞手法,例如拟人、重复、比喻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灌注了汉彝文化的双重内涵,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使表达更为生动,显示出独特的诗意美,小说营造出诗情画意的情境。
拟人是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在他的笔下,世界万物都有人的语言、行动和情感,能与人进行对话。拟人手法的运用不仅是作者的刻意选择,还是作者脑中万物有灵观念的自觉体现。彝族人认为,世界万物都有生命和灵魂,人与动植物及非生物是平等的,人应该敬仰、崇拜自然万物。作者怀着一种平等对话的态度描写万物的语言、动作和情感,建构了一个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诗意世界。这里有孤独、寂寞地等待某个人到来的野梨树;有能够与司楚毕摩对话的山鹰;还有会唱歌的马刀。渣帝部落首领吉岳奥雷手里的马刀唱《看一只鹰远去》:“不过是身影,一点点变小。”这首歌是特可固人代代传唱的歌,会唱歌的马刀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帮助部落首领更好地赢得战争。
重复也是英布草心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重复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情感的递进表达,这造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节奏感,既能起到反复强调的作用,又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回响,形成重章叠句之美,帮助读者品味字词的美感、作者的情感和作品的主题。例如《归山图》写道:“他往前走去,有时是离开,有时是归来。当他离开,仿佛是归来。当他归来,仿佛是离开。他不知道什么是离开,什么是归来。仿佛他不曾离开,也不曾归来。”在短短的五句中,“离开”“归来”分别出现五遍,但并不令人感到啰唆,而是别有趣味。这一段话表达了作者对离去与归来的辩证思考,体现出两者的相对性。对小说主人公司楚毕摩来说,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处云游,走了一辈子,却发现又回到了故乡,故而他的离开,造成了归来的结果。小说中的离开和归来具有多义性,作者并没有说明从哪里离开,从哪里归来。结合司楚毕摩一生的故事,读者可以发现司楚毕摩一直走在学习毕摩经书、拯救众人灵魂的路上。这是一种永远在场的状态,既然如此,就无所谓离开,也无所谓归来。小说中的每一次重复都可以派生出不同的意义,引发读者的思考,将读者带入文字构造的诗意世界,体会文字之美。
英布草心还经常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比喻使语言形象生动,文字熠熠生辉。英布草心的比喻十分奇妙,或融入了彝族文化的种种意象,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奇特的比喻,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增加了小说的诗意。英布草心所用比喻的喻体带有彝族地方风物特色。例如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把女性比作索玛花,既有明喻(“不可知兹莫的女儿们像一朵朵艳丽芬芳的索玛花”),又有暗喻(“一簇簇艳丽夺目的索玛花开在侠则格村庄周围一块块凹凸不平的田野上”)。索玛花就是杜鹃花,用索玛花来形容姑娘的美丽是凉山彝族的习惯。此外,作者还赋予了“索玛花”这一喻体更丰富的含义:“虽然季节不一定是春天,各大首領与部落氏族用自己的真心实意走出一次次文明并开成一簇簇属于第三世界的索玛花。索玛花有红的、白的、粉的。索玛花在自己不同的颜色里展示第三世界的心灵。”此处的索玛花指的是一种精神世界,意在说明古代彝族各个部落不断地向前发展,建构了自身的精神文明。
在拟人、重复和比喻之外,小说还采用了排比、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性语言是作者对日常语言的深度加工,以彝族文化为根基,以汉字为载体,以艺术的手法进行凝练,形成别具一格的诗化语言。
二、 诵经式和歌谣式的语言
英布草心长篇小说还运用了诵经式和歌谣式的语言。诵经式的语言指小说中引用或创作的经文及经文一般的语言;歌谣式语言指小说中引用的民间歌谣和创作的歌谣一般的语言。一方面,作者直接引用彝族各类经书、史诗、民间歌谣的内容,如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毕摩经书《指路经》、民间叙事诗《妈妈的女儿》等;另一方面,作者借用史诗和经书的格律,用五言、七言的格式创作,使文本具有经文的性质,作者也借用民间歌谣的形式自创歌曲,借以传情达意。诵经式和歌谣式的语言旋律灵动,形成了一种音乐美,更重要的是作者用现代思维对彝族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穿越古今,有意通过经文和歌谣的形式抒发情感。
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彝族经典文献,尤其是彝族经文大部分是用诗体写成的,以五言为主,辅以三言、七言、九言等。小说直接引用经文,使其具有古老、庄严、神秘、魔幻的语言美。如《第三世界》引用了《勒俄特依》的“天地演变史”“合侯赛变”的内容,《洛科的王》引用了“石尔俄特”“雪子十二支”部分。《虚野》中引用了众多毕摩经文,如《请神经》《卜算经》《万物有灵经》等。在作者笔下,“毕摩们每一次吟唱的经文都是一首首狂放、炽热的歌谣,充满了诗的旋律”[3]。毕摩诵经声能将读者带入宗教仪式的现场,使其感受神圣、庄严、肃穆的氛围。
作者也借鉴彝文经典的言说格式,创作了一些诵经式语言。作者出生在四川大凉山,《勒俄特依》对他的影响很大。在《归山图》中,有一段描写发现我可毕摩的文字,可以看出《勒俄特依》的影子。小说写道:“发现我可啊,头似老虎头,脚踏四方山,齿尖含虎气,神眼看八方,神手探天地,青天当被盖,毕(念经)声响彻天,清风当坐骑,雨水当酒喝,冰雪做盘缠,要到我可山头取神铃,要去接受经书经卷。”《勒俄特依》开头一段也有类似的描写:“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不生草;中间无云过,四周未形成,地面不刮风。似云不是云,散也散不去;既非黑洞洞,又非明亮亮;上下阴森森,四方昏沉沉。”[4]以上两段话的结构相似,以五言为主,语言的节奏感一致,语言灵动、跳跃、具有诗性。作者笔下的诵经式语言集神话、艺术于一体,织成了一个诗意的宇宙。
民间歌谣是人类内在精神的一种表达,是世俗生活的一种诗化表现,其更接地气,且朗朗上口、情感真挚。小说引用了一些彝族民间歌谣,或委婉地表达情感,或直抒胸臆。例如《归山图》中,册册莫十七岁了,当地风俗认为,一个女子十七岁还没出嫁就要嫁给一块石板。在册册莫嫁给石板的当天,她边哭边唱起了彝族民间叙事长诗《妈妈的女儿》。这首长诗是凉山彝族的“哭嫁歌”之一,讲述了彝族包办婚姻制度下女子的悲剧故事。册册莫也是包办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她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由此感到十分痛苦和悲伤。借助歌谣,她抒发着自己的悲伤。歌谣语言朴实、自然生动、凄婉忧伤,具有音乐美和悲剧美。
小说创作了一些歌谣,这些歌谣借鉴了彝族民歌的艺术形式,吸收了彝族民歌和现代流行歌曲通俗明快、自由等审美特质,歌唱生命的激情,有的充满野性,有的蕴含灵性。如《归山图》中的一位名叫呷铁末的女性用歌声招待客人。歌谣是古莽山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形式,它将人们的日常对话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作者还创作了饱含情欲、生命力的情歌。如《第三世界》中的主人公带兵官鲁和潘卡大首领打冤家时,相互唱情歌助阵。这里的情歌,其实是双方的爱人写给他们的情书,当他们唱出来时,就变成了情歌。潘卡大首领唱的是自己的情人沙加拉太太给自己的情书,带兵官鲁唱的是他的情人甘栀妹妹写给他的情书。情歌既能增加己方的力量,又能伤害对方,情感越真挚,杀伤力越大。情歌的语言是诗的语言,流淌着饱满的爱意。
彝文经典、民间歌谣本身就带有诗意,对这些语言的引用或化用,既增加了小说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字分量,又增强了小说的诗意。诵经式和歌谣式语言能给人带来多重审美体验,既能令人体会到经文、民歌本身的语言之美,又能令人感受到主人公运用这些语言的艺术情境,还能感受到作者遣词造句的创作过程及蕴含其中的深厚情感。诵经式和歌谣式的语言,融抒情和叙事为一体,调动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将读者带入诵经和歌唱的现场,令读者体味语言及语言营造的诗意之美。
三、 多样化的哲理性语言
英布草心的长篇小说还通过哲理性语言来传达诗意。这些哲理性语言大量出现在小说中,浓缩了人生经验,传达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和对生活的认知。人生道理以填鸭式的训诫语气说出就会令人反感;但以诗化语言道出,则能将人生道理升华到哲学的高度。作者通过多种方式来构造哲理式语言,若按照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来分,在内容上,作者引用民间俗语和谚语,采用辩证式的语言;在形式上,作者使用疑问和反问等语句,创作出短小精悍的哲理句子。
就内容而言,一方面,小说经常引用民间俗语和谚语。彝族谚语被称为尔比尔吉,是彝族人对生活的凝练表达。民间俗语和谚语是民间智慧的一种表达,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哲理是它们的灵魂,丰富的诗意是它们的翅膀。例如,作者使用彝族谚语“人类重知识,虎豹图食物”,以此说明知识的重要性;使用“人间母为贵,五谷荞为尊”,说明母亲和苦荞在彝族人心中的重要地位;使用“屋内别说话,墙角有耳朵;野外别说话,树丛有耳朵”来说明隔墙有耳。这些俗语和谚语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朴实明快、朗朗上口,带有朴素的诗意美。另一方面,小说采用辩证式的语言论述问题,辩证式的语言适用于表达哲理,从而传达诗意。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作者通过辩证式的语言,描绘出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从而警醒人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当作者使用辩证的语言时,他得出的观点或结论不是极端的,这就具有一种和谐恬淡的诗意美。例如,“有时,你从一场梦里醒来,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没有了。有时,你从另一场梦里醒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就会陈列在你的面前,让你以为自己还在梦中”,这表现了人生的偶然性;“美是生命的福,也是生命的祸啊”则写出了美丽的双面性;“懂得平衡的人,自己的长短一般别人看不到;不懂得平衡的人,总亮着自己的长,殊不知也露出了自己的短”则道出了平衡对人生的重要性。
在形式上,小说通过构造短小精悍的句子表述哲理、传达诗意。作者偏爱短句,很少有长篇大论,即使有长篇大论,每一段中的句子也是短小精悍的。短小精悍的句子简洁明快,正是中国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一种表现。例如,“一个人在世上,从来处来,往去处去”,作者用禅意的语言,道破人生真谛;“最冷的,是人心,不是冰块”,“冰块”和“人心”进行对照,突出人心的冷漠;“没有绵柔的心情,再美的诵经也会如咀嚼砂砾”,则说明了人的心情对认知事物的影响。小说还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发思考,这些疑问或反问的语言,反映出作者对生命、存在、战争等各种问题的思考,也引发读者思考。在疑问句和反问句建构的思考空间中,读者可以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诗意的领悟。例如,“你遇到一个人,因为冥冥中有只手在牵引。你离开一个人,因为那只藏在冥冥中牵引的手断折了”。当人们把人的聚散离合归结于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时,就更容易接受生活中的各种如意或不如意之事。然而,果真有一双手在操纵着一切吗?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给出自己的疑问,从而引发读者思考,让读者在文本之外反复回味。英布草心长篇小说中的哲理式语言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使句子形象生动,营造出诗意的氛围,抽象思維则使句子具有科学性,两者的叠加使其小说语言带有感性和理性双重色彩,增加了小说美的特质和诗的意蕴,并通过哲理性的语言来表达“对天地宇宙和未知世界无止境的探索,以及对生死轮回和苍茫时空无极限的想象”[5]。
四、结语
英布草心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诵经式和歌谣式的语言以及哲理性语言,构建了一个诗意的小说世界。作者拥有彝族、汉族及世界文学等多重文化素养,他有意探索汉语的边界,对日常语言进行打磨,造成语言的陌生化,融合现代思维和彝族文化的传统思维,在文字的自律和自由之间达到平衡,形成多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语言风格,使其小说余味悠长。
参考文献
[1] 罗庆春,徐其超.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J].天府新论,1998(6).
[2] 李云.艺术是永远的情人[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7.
[3] 李晓伟.“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4] 冯元蔚.勒俄特依[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5] 何五基莫.试论彝族小说《虚野》的生态美学特征[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艾乐,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