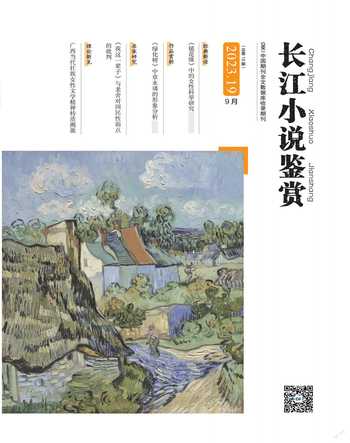论艾丽丝·门罗作品中独特的女性成长叙事
[摘 要] 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艾丽丝·门罗的作品对于现代女性命运的刻画和揭示极为深刻。女性逃离家庭、逃离传统是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过去的研究者多聚焦其以成年女性为主角的作品,而鲜少关注其描绘少女成长的小说的叙事模式。1968年出版的第一本经典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红裙子——1946》为门罗此类作品的代表作,“逃离”的主题内涵贯穿故事始终,但不同于现代女性成长小说中常见的主人公追求独立、平等、自由的叙事范式,女主人公最终逃离成为独立自主的“玛丽”,选择了自己本想逃离的母亲和社会给她规定的女性命运。门罗这一不落窠臼的女性成长叙事模式体现了其别具匠心的创作思想,蕴含了她对小镇社会现实的深刻写照和女性命运的独到理解。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 女性成长叙事 逃离 《红裙子——1946》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79-05
加拿大著名作家艾丽丝·门罗(1931—),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盛赞为当代少有的堪与契诃夫、莫泊桑、福楼拜等伟大小说家比肩之人[1]。迄今为止,她共出版了包括《快乐影子之舞》《逃离》等在内的14部短篇小说集。女性逃离家庭、逃离传统是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引发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国内相关研究中以朱晓映的解读最具代表性,在朱晓映看来,“逃离”是门罗展现“现代女性探索自我和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是“她们实现自我救赎与自我完善的一条路径”[2]。杜慧敏在《门罗小说“逃离”主题的哲学思考》中指出:“门罗对‘逃离的书写是作家对‘逃离人施以悲悯的方式。”[3]然而,此类相关论述中所关注的多为门罗以成年女性为主角的作品。成年女性为了追求自我,逃离婚姻、逃离传统的故事固然发人深思,而少女为了成长,逃离母亲、逃离既定女性命运的作品同样具有深意。本文选取收录在门罗1968年发表的第一本作品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描绘少女成长的短篇小说《红裙子——1946》,来探讨其中的“逃离”思想内核。
一、反抗“母亲”——象征性的逃离
女性主义先驱、法国思想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女性时间》(Womens Time)中犀利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女性主体同循环时间(cyclical time)相联系,她的人生是不断的循环和重复”[4]。多年深耕女性书写的门罗深谙这一女性生存困境,并在《红裙子——1946》的情节设计上巧妙地突显出来。故事以母亲在逼仄的厨房缝制红舞裙开头,又以母亲在厨房满脸期待等待参加完舞会的女儿回家结尾。这种首尾相扣的环形结构不仅象征着母亲(女性)生活的重复性和单调性,也制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因此,刚刚步入青春期,自主意识萌芽状态的少女对于母亲充满了疏离和排斥,而这种态度和童年时期的大为不同。
主人公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是喜欢和顺从的。幼年时,不管母亲给她缝制的服装款式有多奇特,她都会“顺从地穿上这些衣服”,并且“感觉还挺快乐”[5]。 这种顺从的根源在于孩童时期女孩同母亲认识上的“同一性”(“oneness”)。在孩童时期,女孩会认为自己像母亲并对母亲的形象产生认同,而母亲也对女儿有认同,仿佛在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童年[6]。但这种认识上的“同一性”会随着女儿青春期的到来而瓦解。进入青春期,女孩成长为少女,渐渐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面对母亲的权威,她不再是愉快地顺从,而是觉得压抑。试穿舞裙时,母亲把她拖来拖去,一会儿命令她转个圈,一会儿又让她走几步,一会儿又不许她动,这使少女十分屈辱,觉得自己“像个怪物木偶,被塞进一团红色天鹅绒里,眼睛大睁头发狂乱,颇有点儿精神谵妄的意思”[5]。母亲的权威和对少女主体性的剥夺让她分外羡慕好友郎妮,郎妮的母亲已经去世,郎妮平时由父亲照料。
除了令人窒息的母亲权威,少女闭塞的生活圈子、贫乏的人生阅历也让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惧,想要逃离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故事中,母亲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局限在厨房,缝制衣服、打扮女儿、休息喝茶、等待女儿。母亲并非不渴望外部世界,在缝制衣服时,她会把缝纫机尽量贴近朝外的窗户,这样她“可以看看外头,目光越过收割后的田地和光秃秃的菜园,看看路上有谁走过”[5]。然而,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母亲的世界除了这逼仄的厨房,就只剩下残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记忆,所以她一遍又一遍地给女儿絮叨她的过去,讲述她引以为豪的靠自己打工赚钱上高中的故事。可关于母亲的一切,在女儿眼里已失去了过去曾有的魅力和光彩。母亲属于过去,属于童年;而少女却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过去,摆脱母亲的控制,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但母亲明显没意识到女儿心态的变化,也似乎为了彌补自己当初没有华丽舞裙的遗憾,她狂热地为女儿缝制舞裙、修改舞裙,并拿出她珍藏的香水给女儿用。乔德罗认为:“劳动分工受压抑的一方注定要在后代身上再生这一压抑的状态。”[6]在男权制社会,社会分工决定了女性的首要位置是家庭,而家庭的主要贡献是教化年轻人传承男权制关于角色、气质和地位的规定。出于心理上的需求和社会身份的要求,母亲的职责是确保女儿女性气质的养成,这意味着她必须剥夺女儿的主体性。
女儿的第一次舞会是检验教化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场合,母亲自然倾注极大的热忱和心血,但少女却并不领情,她只想逃离,逃离母亲的安排,逃离母亲所代表的女性命运和女性气质。她想尽各种办法来避免舞会,她试着“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扭伤踝关节”;她在大冬天打开卧室的窗户,解开睡衣的扣子,并把窗台的雪涂在胸口,想要让自己冻感冒[5]。但是少女的这种“逃离”仅仅是一种姿态,只是象征性地同她的女性命运作斗争。因为在舞会到来的那一天,少女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强迫,主动做好头发、化好妆、喷上香水,穿好精心准备的舞裙和好友郎妮一起去参加了舞会。正如波伏娃所言,少女的内心是极为冲突和矛盾的,“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然而也没有完全拒绝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7]。
逃离母亲,抑或逃离舞会,都是少女在完全接受自己的女性气质之前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它不彻底、不深刻,折射了青春期少女在完成自我和成为他者之间挣扎的矛盾心情,同时也预示了她逃离失败的结局。
二、成为“玛丽”——被动的逃离
玛丽是少女在舞会时结识的一个高年级学姐,是舞会的组织者,也是学校体育协会的会长,常常名列校荣誉榜,且负责组织学校的诸多事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校园风云人物。
在参加舞会时,少女的恐惧应验了,没有男生请她跳舞。她精致的发型、妆容,夸张的紧身红舞裙,挤出的甜美笑容似乎都成为一种讽刺。她匆匆逃离舞池,一头躲进卫生间。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玛丽。出乎少女意料,平时看上去有点高不可攀的玛丽向她伸出友谊的橄榄枝,主动同她搭话,给她递来香烟,并向她坦白心境。玛丽鄙夷舞会上那些一心扑在异性身上的女生,认为把获得异性的青睐作为人生唯一的目标是一种愚蠢行径。对于自己的人生,玛丽有不一样的远大规划:她计划半工半读自己去上大学,然后成为一名体育老师。和玛丽的交谈让少女觉得“自己敏感的不快时期已然过去了”,因为她们“承受了相同的挫败感”[5],都是舞会上的失败者,但玛丽却充满了斗志,并且自尊自强。更为重要的是,玛丽关于未来的蓝图使少女开阔了眼界,消解了她那种等待他人来选择来评判自己价值的彷徨恐惧之情。她变得勇敢而坚定,“我发现,我不再那么害怕了。现在我决心再也不管舞会,不等任何人来挑选我”,变得不盲从而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再也不需要微笑,不需要为了好运气打手势。已经没关系了”[5]。
就在读者为少女的转变和自主意识的崛起而大受鼓舞,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主人公“追求真正女性自我”的女性成长故事时,故事却又突然发生反转[8]。
在女主人公和玛丽准备离开舞会时,因为误会,一名男生未经她同意便托起她的腰,不由分说和她跳起舞来。上一秒下决心抛开舞会,开启别样人生的少女几乎是下意识地便配合男生旋转起来,而且立刻就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身体没有发抖、手心没有流汗,面部表情调试成了那种和其他女生一样的“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这时,少女终于成为她渴望的那种“表情厌倦,冷淡,迷人”的成熟女孩——玛丽口中的“男孩狂”[5]。这种转折看似突兀,却又合情合理,印证了一个悲剧性事实:“女孩子,自童年期,不论是想滞留在女性气质的范围内,还是想超出这个范围,要实现或摆脱,却都有赖于男性。”[5]
成为玛丽还是“男孩狂”中的一员仅在少女一念之间,看上去是少女自主的抉择,但实际却不是,她命运的决定权在那名叫雷蒙德的男生手中。如果他没邀请她跳舞,少女也许会成为第二个“玛丽”,不以获得男性的青睐为生活的目的,而是勇敢地去追求自我,走一条母亲没有走过的路,脱离自己被动的次要者命运。和玛丽简短的相处虽然让少女看到了摆脱既定命运的可能性,也感受到了冒险的刺激和魅力,然而在她心里,玛丽其实和她一样,是绝望的舞会失败者,缺乏迷人的女性特质,因为她“脸上有粉刺留下的疤痕,牙齿往前突出”[5]。自从跨入青春期,母亲、同伴、社会几乎都在给她传递同样一个信息:做一个迷人的女性,去获得男性的青睐,这是每一个少女当下的首要任务。这种长期性的全面影响是深刻的,少女不会因为和“异类”玛丽一次短暂的相处就彻底改变刻入她骨子里的观念,成为“玛丽”只不过是少女的权宜之策,是她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生活的被动选择,她并非真的想逃离舞会。因此,她欣然接受雷蒙德的邀请,成为一名普通的“男孩狂”,抛弃玛丽,任她一人独自离开舞会。
逃离舞会,抑或逃离玛丽,都非少女自主的选择,而是她被动的选择。逃离舞会是戏剧性的,而逃离玛丽才是现实性的。这包含门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对于小镇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对于她们而言,对抗传统、逃离既定命运,实现独立自主之路远比顺应社会、完成他者使命要艰难得多。
三、成为“郎妮”——失败的逃离
如果说反抗母亲象征着少女对逃离他者命运的渴望,成为“玛丽”是作为一个舞会失败者被动的逃离,那么成为“郎妮”却无疑宣告着她逃离成为“他者”命运的失败。
郎妮是少女最好的朋友,一直是少女艳羡的对象,因为郎妮拥有迷人的女性气质。青春期身体的变化让少女感到尴尬和不适,觉得自己像一个浑身疙瘩、笨手笨脚的大块头,而郎妮“小巧、苍白、瘦弱”,她总是想“要是我像郎妮就好了”[5]。
少女对郎妮的羡慕也源自郎妮的成熟自若。郎妮已经率先完成成长为“女人”的社会化过程,提前适应了自己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命运,而少女还处在一个徘徊矛盾的阶段。刚刚跨入青春期的少女,会因为身体的變化、母亲的敦促,感受到自己女性使命的迫切性,但是对于少女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女性的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5],她留恋有着相对独立性的童年,对成为顺从的女人有欲望也有恐惧。门罗巧妙地将这一矛盾的心理特点通过少女舞裙的设计展现出来。母亲给她准备的是一件大红色的丝绒材质的束腰式舞裙,在《〈红裙子——1946〉中的感官之舞》一文里,塞布丽·弗兰切斯科尼表明,小说中舞裙的红色象征着少女“迫切独立的欲望”,象征着“成熟、身份和自我表达”[9]。但母亲又认为红裙子的款式似乎过于成熟,在舞会前一刻又给缝上一层白色的荷叶边蕾丝领口。充满孩子气的白色衣领和成熟的大红色束腰裙身形成强烈的冲突和反差,正象征着少女内心的冲突和矛盾。而郎妮的舞裙款式设计却是和谐的,舞会当天,郎妮身着“一件淡蓝色的绉绸裙,腰上有装饰性的褶裥饰边和蝴蝶结”,浑身上下充满女人味[5]。舞裙款式的和谐也象征着郎妮内心的和谐,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已欣然接受和适应,已没有反抗和矛盾。看到郎妮的裙子,少女暗自羡慕,觉得郎妮的裙子分外时髦得体,而自己的裙子即使没有荷叶边,都比不上郎妮的有女人味。白色的荷叶领象征着去性征的、自由的童年时期,对于自己舞裙款式的厌恶,恰恰暗含着少女迫不及待成为女人的渴望。
在舞会上,郎妮也率先完成自己的成长仪式。作为舞场新手的她,很轻松便赢得男性的青睐,被邀去跳舞,剩下少女一人孤零零被晾在一旁,觉得自己仿佛被好友抛弃了,被世界抛弃了。因此绝望的少女才逃离舞会,决定成为和郎妮不一样的玛丽。但这不是少女真实的想法和自主的选择,选择“玛丽”,逃离“郎妮”不过是因为自己经受了失败,是被动之举。所以当雷蒙德主动请她跳舞并送她回家时,她欣然接受并满怀感激,把他看作救星,因为他把她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5]。女主人公不过是万万千千普通少女中的一员,她追求的不过是完成社会给她规定好的角色:培养自己的女性气质,获取男性的青睐,然后开启自己被动的他者命运。经历了舞会前的惶恐、舞会时的绝望与意外,舞会后的少女终于达到内心的平静,因为有男孩请她跳舞、送她回家、和她吻别,她觉得自己并非人生的失败者,因为她完成了自己的女性宿命。
在少女看来,成为女人是她“不可言说的、沉重的义务”[5],她成功了;同时,她也以为成为女人就可以实现同母亲的割裂,从此摆脱母亲的掌控。她甚至认为,被男性青睐,完成使命,并和母亲划清界限,是开启了自己的新生,然而,她没有意识到的是,成为“郎妮”却恰好是完成了母亲的期待,成为母亲渴望她成为的样子。
成为郎妮,不过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女性逃离。
四、结语
“如何从现有的生活模式脱离出来,逃离社会和家庭为她们指定的未来”,这是门罗作品不断出现的主题[10]。在同名小说《逃离》(Runaway)中,主人公卡拉逃离了丈夫和家庭,然而在即将成功的最后一刻又放弃了逃离,回归家庭;《红裙子——1946》中所呈现的少女逃离和《逃离》中卡拉的逃离经历了相似的轨迹。小说开篇,我们可以感受到少女迫切想要逃离母亲、逃离自己成人仪式(舞会)的心情,和卡拉有西尔维亚——邻居家的大学老师作为指路人一样,少女碰到了自己的引路人玛丽,并站在了成长抉择的关口——是顺应自己的女性命运,成为温顺美丽的“郎妮”,还是逃离自己的女性命运,成为独立自主的“玛丽”?卡拉的选择是回归家庭,继续履行自己的妻子角色;少女的选择也是回归女性宿命,做一个寻求男性肯定的客体。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卡拉的逃离尝试和失败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是她“与自我幻想的浪漫偶遇”,是她“探索自我、完善自我的实践”[2]。不同于卡拉,少女的逃离尝试和失败都是其被动的选择,主动权在男性——是否能获得男性青睐左右着少女的成长抉择。不管是成年女性的主动逃离还是少女的被动逃离,都以失败告终,这正是门罗女性成长叙事的独特之处。
经典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往往要牺牲自我和个性,“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化的需要, 维持社会稳定和帮助主人公融入社会”[11]。从这一角度看,门罗在《红裙子——1946》中的成长叙事完全符合传统成长叙事的模式。但是经典成长小说以描写男性人物为主,而众所周知,父权制社会的秩序构建原則是保障男性利益,因此,男性的社会化过程与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社会化不会使男性“丧失个体的所有自主性”,而是使其在“个人内在的独特自我”和“整个社会中外在的共同自我之间”的不断交互作用中形成完整自我[11]。而女性不同,她们的社会化是完成女性作为次要者的命运,和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化的完成意味着放弃自己主要者的地位。因此,女性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往往是反社会化的,女性成长是“对父权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理性认识和自觉疏离,并在确立性别自我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女性主体性的回归”[12]。在《红裙子——1946》故事结尾,少女放弃成为“玛丽”的选择,即是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实现;选择成为“郎妮”,即接受家庭和社会为她预设的他者命运,完成了自己的社会化过程。这种对于经典成长叙事的模仿和现代女性叙事的颠覆构成了门罗作品独一无二的女性成长叙事特点,蕴含了她对于女性命运及小镇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见解,凸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质。
参考文献
[1] Byatt A S.Alice Munro:One of the Great Ones[N].Globe&Mail,1996-11-2.
[2] 朱晓映.逃离:后女性主义的自我探索[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4).
[3] 杜慧敏.门罗小说“逃离”主题的哲学思考——以《逃离》《机缘》三部曲为主要对象[J].湖北社会科学,2018(2).
[4] Kristiva J.Womens Tim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5] 门罗.快乐影子之舞[M].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 Chodorow N.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7]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 White B A.Growing Up Female:Adolescent Girlhood in American Fiction[M].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5.
[9] Francesconi S.Dance of the Senses in Red Dress—1946[M].A Roar from Underground:Alice Munros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ries de Paris Ouest,2015.
[10] Fulfort R.The Munro Woman:History as We Read It in the Stories of a Nobel Laureate[J].Queens Quarterly,2013(4).
[11] 孙胜忠.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12] 翟永明.成长·性别·父权制——兼论女性成长小说[J].理论与创作,2007(2).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陈琴,三峡大学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1yskf04) 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