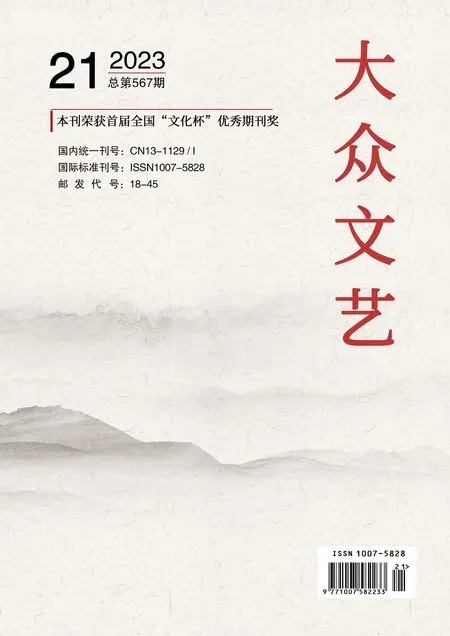浅析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的空间叙事及美学意义*
李 岚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一、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其对传统小说时间顺序线性叙事的打破,致使空间维度的研究被高度重视,体现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在小说形式和技巧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和创新”[1]。小说《到灯塔去》运用时空交叉和倒置的手法,使非线性的情节和内心独白涉及多个时间和地点,以“灯塔”为线索讲述了拉姆齐一家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生活经历,细致描绘了人物的内心意识流动与情感波动。
然而,伍尔夫的意识流技巧只是表层,表层之下呈现出空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背景,还进一步推动叙事,并呈现波澜变换的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出人物处于精神危机时代等深刻意蕴,传达作家的思想内涵。同时,伍尔夫作为“世界末日的美学家”[2],以物理空间、人物心理空间等空间类型及空间叙事建构小说事件所涉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关系,形成空间意识并营造了美学效果,传达其审美意图。
二、《到灯塔去》物理空间叙事
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因此空间也是叙事研究的重要维度,可以指物理空间及地理空间,如人们居住的房屋、领土、山脉等。在《到灯塔去》中,物理空间是叙事不可缺少的场景,我们不仅要探索不同的物理空间以及空间的距离对叙事的作用,还需了解叙事背后蕴藏的伍尔夫的思想内涵。
首先,小说中位于斯凯岛的海滨别墅是一个重要的物理空间,它是人物聚集活动且发生联结的主要场所。小说的开篇场景就设置在这所别墅的房间里,相关人物到灯塔去的想法也产生于此。在伍尔夫笔下,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充满生机的空间布景,周围有柔软的深绿色草地、点缀着怒放的紫花和悦耳的海浪声。事实上,由于这部小说带有的自传性质,赫布里底群岛上的斯凯岛是以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的圣•艾夫斯港为基础创作而出的,矗立在海湾的房子俯瞰着戈德雷维灯塔,是伍尔夫和家人暑夏度假时的愉快地点,正如她自己所说,“这部作品展示了我父母亲的性格、圣•艾夫斯的小岛和我的童年……”[3]。小说中对海滨别墅空间的生动描述无疑反映出伍尔夫对早期生活的回溯,暗示着对儿时的想念。
然而,这所房子在多年间见证了世界的变幻沧桑,与第一部分《窗》中房间内外和谐温暖的氛围相比,这个空间在第二部分《岁月流逝》中产生了巨大变化,也是小说情节发生转折的节点。房子因战争而遭到了破坏,房屋外曾经柔和的草坪沾满落叶,大海波涛叠起。伍尔夫运用大量文字描写夜晚的寒风和屋内的毁灭状,“噼啪作响的挂帘,叽叽嘎嘎的木器,油漆剥落的桌腿,发霉长毛、失去光泽、裂缝破碎的砂锅和瓷器”[4],一展战争残酷性。同时,这个空间的毁灭也映照着曾经空间的温馨,这里紧接着进行了时空跳跃,以空间里人们遗弃下的靴子、衣裙等进行叙事变换:“一度曾经多么充实而有生气,纤纤玉手曾经匆匆忙忙地搭上衣钩、扣上纽襟,梳妆镜里曾经映照出玉貌花容,反射出一个空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身躯旋转过来,一只手挥动一下,门开了,孩子们一窝蜂涌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灯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物理坐标,甚至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灯塔,这部分围绕着前往灯塔的具体旅程,即人物与灯塔的物理空间逐渐拉近的过程。同时,这也可视为人物的精神旅途,因为其承载了人物共同的希望。小说中的灯塔固定在海的远处,高大、坚实,在黑暗中闪光,具有永恒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小儿子詹姆斯童年的梦想、拉姆齐夫人的内心之光,以及拉姆齐的家人和朋友们的精神家园。小说的结尾部分,当拉姆齐先生等人一齐前往灯塔之时,此时个体与灯塔有着空间距离的拉近。詹姆斯近距离望向他朝思暮想的灯塔,思绪回忆瞬间将他拉到过去的时空里,他感受到“那灯光似乎一直照到他们身边,照到他们坐着的凉爽的、快活的花园里”。画家莉丽在望向前往灯塔的船只时,内心同样波澜起伏,认为当拉姆齐先生乘船离她越来越远时,她对他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直言“距离的作用多么巨大”。
小说中的物理空间及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交织推动叙事进程,展现情节内容、人物思维的变换。伍尔夫对不同的空间及空间距离的描绘,都是其在启发人们挖掘个人潜能、深入洞察客观世界,思考人与世界本质的联结。
三、《到灯塔去》人物心理空间叙事
空间不仅可以指物理空间、地理空间,也可指精神层面或社会属性的空间,呈现出多种维度的空间叙事。《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运用内心独白、感知印象等,描写瞬间感受、回忆、想象等,让人物直接诉说情感与思绪,展现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主观精神与客观现实的交织。
伍尔夫笔下人物的自我意识通过身体所占据的空间获得了空间性。书中不乏强调精神世界的语句——“在精神上和他距离遥远”,“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躯体或心灵置身于黑暗之外”。书中在描写拉姆齐夫人与灯塔灯光的关系时,涌现了大量对其心理的细致描写,对于拉姆齐夫人来说,“稳定的、长长的光柱,就是她的光柱”。虽然灯塔离她的物理空间距离很远,但当灯塔的光照射到她近距离的身旁时,她的心理空间已经与灯塔和灯光结合成一个整体,那灯光“深入探索她的思绪和心灵”;当她望向灯塔时,灯塔的光芒给她的内心带来无尽的欢愉,“好像它要用它银光闪闪的手指轻触她头脑中的一些密封的容器……狂喜陶醉的光芒,在她眼中闪烁,纯洁喜悦的波涛,涌入她的心田”。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空间叙事不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步,又因为主观意识也是对外界的反映,其能够展现出人物客观世界中的故事进展。
人物的心理空间会把过去、现在、未来穿插在一起,这种意识流技巧下意识的流动本身就具有空间感。“柏格森认为……只有用文艺的、诗意的语言,将心理时间的‘绵延’不加逻辑切割、不加理性改造地记录下来,才能传达内心的真实”[5],这使人的主观感觉和内心体验占据本体地位,因此记忆在人的存在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记忆不仅和时间有关,它的空间特性也非常明显……我们生活中重要的记忆总是和一些具体的空间(地方)联系在一起。”[6]伍尔夫将“到灯塔去”的时空旅程构建对曾经的回忆,前往灯塔的途中,詹姆斯回想起已故不能赴灯塔的母亲拉姆齐夫人,“他开始尾随着她,走过了好几个房间,最后他们走进一间蓝光映照着的房间”。同时,到灯塔去的前后经历也暗示了父子间关系的张力,在詹姆斯的这段回忆中,他意识到,“他的父亲始终在追随着他的思路,监视着它,使它颤抖,使它犹豫”,“他的父亲把它打了个结,他要逃脱的话,只有拿起一把刀子把它刺进……他们似乎又互相疏远了,各人悠闲自在互不相扰”。
小说中每时每刻的时间都充满了无序、复杂的思绪,思绪中不同、随机的事件可以延伸到随时随地,形成空间感。书中有许多“心理时间”上的绵延,以及对心理形成的新空间的偶遇与进入。在写到拉姆齐先生精神崩溃的心理状态时,“他所有的虚荣心……已经被粉碎了,被摧毁了。冒着枪林弹雨,威风凛凛,我们跃马前行,冲过死亡的幽谷,排枪齐射,大炮轰鸣——突然他和莉丽•布里斯库、威廉•班克斯面对面地撞见了。”在书写拉姆齐夫人对自我的探寻时,也呈现了精神世界的广阔无边、思绪蔓延的跳跃感与空间感,自由的幻想可以超脱现状,带她抵达时空交错的任意地点,“她内心……有许多她从未见识过的地方,其中有印度的平原;她觉得她正在掀开罗马一所教堂厚厚的皮革门帘。”
四、《到灯塔去》空间美学意义
《到灯塔去》中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叙事结构给人立体的空间感,文学作为艺术的时空体,时间与空间不停交叉与融合,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使文学作品成为一种空间视觉艺术。因此,这部小说呈现出一幅流动的意识、时间和空间的图画。伍尔夫对绘画的认知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她早期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和后期的小说《海浪》《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都可以看到文字绘画的影子”[7]。她自幼深受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影响,其中家庭中以及布卢姆茨伯里文人团体(Bloomsbury Group)中的绘画文化,尤其是强调光影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对伍尔夫的技巧产生极深影响。在此影响下,她坚持自身审美原则和立场,发挥她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认知的非凡才能,创作出的作品往往运用大量色彩,追求光与色的奇妙配置,以取得审美效果。
小说中,伍尔夫运用了大量与绘画有关的空间美学技巧,她在创作时就意识到色彩对物理空间及心理空间的塑造。书中的许多语句具有明显的说服力,尤其在描写莉丽在作画时对色彩运用的纠结之时,将颜色与画布上的空间、人物内心空间相连接。棕色的线条在画布上能够“围住了一块空间”,绿色和蓝色在莉丽内心深处形成“难以对付的、苍白的空间”,一种色彩与另一种色彩的融合不仅该展现画作外表的华丽,更应形成画面中稳定的立体感,于是“她开始用色彩一层层填补那片空白”。同时,与绘画、线条有关的词语和形式的频繁使用,不仅使得时空染上色彩,还产生了新的场景。在目光所及的视野空间,她将不同方位的物一一绘色,将面前一望无际的海洋绘成蔚蓝色,将远处烟雾中散发朦胧光线的灯塔绘成灰白色,将右边野草丛生的沙丘绘成绿色。这些着色的静物在光色的组合映衬下,构建出了新的空间,绿色的沙丘在海水的激荡下,“形成一道道柔和、低回的皱褶”的画面。运用同样的方法,伍尔夫在描写色彩斑斓的果盘在烛光光辉的映照之下时,构造出一个神秘的光影空间,“挺直明亮的光辉,照亮了整个餐桌和桌子中央一盘浅黄淡紫的水果……那只果盘似乎有着巨大的体积和深度,就像是一个世界”。不仅如此,伍尔夫还擅用对比色,如红色和蓝色:“走到厚实的树篱的缺口处,那儿用火红的铁栅防护着,它就像燃着煤块的火盆一般通红。在篱笆的缺口之间,可以见到海湾的一角,那蓝色的海水,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湛蓝。”色彩的对比突出了物体的相对位置,形成错落、冲击感极强的空间画面。
伍尔夫还运用了绘画中的距离法,将远景的虚幻和近景的真实创造出无限的空间。她精心描绘远近物体及其光色,远处光的折射传递到近处呈现出多样的颜色之时,无不呈现出空间感。当写到远处灯塔的光芒映照在波动汹涌的海浪上时,随着时间的流逝,天色变换,光影效果随之切换,被灯光照射的波涛从白日傍晚时“披上了银装”,最终变成“纯粹是柠檬色的海浪滚滚而来”。同时,风景会根据观看者的角度和距离而改变,前往灯塔的帆船随着航程渐渐变成岸上莉丽眼中海上那个“棕色的斑点”。同样,灯塔之于詹姆斯也因距离的不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形象与感觉,他回忆起儿时记忆中的灯塔“是一座银灰色的、神秘的宝塔”,放射着黄色的光芒;现在,当詹姆斯望向眼前的灯塔,“他能看见那些粉刷成白色的岩石……塔上划着黑白的线条”。在黑暗的夜晚,远处的灯塔放射出黄色的光,遥远的光包含着无限的空间之美,而当近距离观察灯塔时,它不过是一座栖息在岩石上光秃秃的黑白建筑。
五、结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关注空间问题,突出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及其与人物的联结和对叙事的推动作用。小说的情节主线是讨论明天是否去灯塔,但这简单的情节由不同的空间类型、人物的意识流动以及人与物间不同的空间距离等而被创作成一部小说,展现了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宏大的、流动的、变幻的世界,人物在客观世界中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局限性。同时,伍尔夫运用细腻的文字表达了内与外、远与近、幻与真、光与影的对比,渲染出各种空间距离和视角,使空间叙事有了生命力,使叙事呈现出画面感,引发联想和想象,产生空间的美学效果。由此,《到灯塔去》的空间不仅是小说情节发生的场所背景,同时助推故事情节发展,并呈现变换、辽阔的人物精神世界,传达作家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