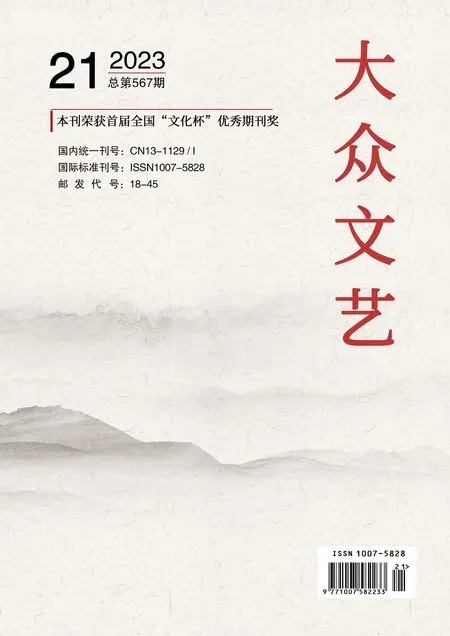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从学术走向大众
吴佳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
在中法人文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戏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中法戏剧交流中,受限于人员流动和语言壁垒,剧本翻译的作用更为突出。1735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翻译的中国经典《赵氏孤儿》,拉开了中国戏剧在欧洲传播的序幕。此后,法国来华传教士、法国本土汉学家陆续翻译中国戏剧典籍,法国学者、艺术评论界对中国古典戏剧乃至对中国古典艺术产生了浓烈的学术与艺术兴趣,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和评论。今天,在法国观看中国戏剧表演并非难事,从事中国戏剧研究的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今天中法戏剧交流高度发达的现象背后,中国戏剧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与中国戏剧典籍法译本的自身特点和传播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中国戏剧典籍法译本的产生与发展
(一)登场:马若瑟译《赵氏孤儿》
十八世纪许多法国传教士来到清帝国,他们不乏观看中国戏剧表演的机会,但除了耶稣会神父马若瑟之外,其他传教士对中国戏剧翻译的兴趣寥寥。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与视戏剧艺术为高雅文化的欧洲不同,戏剧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不属于高雅的活动,而更多是大众的娱乐方式,和传教士的本职工作也缺乏联系[1];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戏剧的审美原则与欧洲戏剧存在显著不同,尤其是与讲求现实主义的启蒙时代相比,中国戏剧装饰华丽、表演程式化、音乐夸张,令法国传教士难以理解乃至心生厌恶。
普遍认为,中国戏剧的第一部法译本是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发表于杜赫德神父编纂的《中国通志》第三卷。[2]马若瑟中文语言功底深厚,其《汉语札记》自称是“世界上第一部将汉语白话口语与文言加以区分并分别论述的著作”,又兼长期在中国生活,能够接触中国戏剧表演,具有得天独厚的翻译条件。[3]其译本对十八世纪的欧洲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4],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对中国戏剧中元杂剧兴趣集中的格局,还启发伏尔泰创作了《中国孤儿》。不过,伏尔泰成功的大幅改编将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引向了通俗小说而非戏剧典籍。
从今天的翻译要求看,马若瑟的译本并不忠实于《赵氏孤儿》原作。马若瑟译本广受批评的一点是,他认为唱段中包含欧洲人难以理解的修辞手法和历史故事,因而将43处唱段删去。[5]此外,他还改变了原作的场次,以适应西方古典悲剧的上下场原则。有学者基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体现的翻译原则提出了一种解释,即当时翻译的目的是取悦读者而非忠于原文,马若瑟的做法考虑了法国不通中文也对中国艺术缺乏了解的受众,强调阅读的舒适性(马若瑟甚至在剧本前面按照欧洲习惯添加按出场先后为序的人物表),而其保留少部分唱段则意在传递《赵氏孤儿》中贯穿的忠信等儒家思想。[6]这种做法无疑需要对法国和中国的语言、艺术和文化都具备深入的了解,加之天主教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礼仪之争、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马若瑟之后近一个世纪,法国对中国戏剧兴趣集中在对《赵氏孤儿》的改编与评价,翻译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亮相:法国汉学界的集中翻译
19世纪到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开始集中译介、研究中国戏剧。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家深入关注中国戏剧的形式特征,进行全译。其中,斯坦尼斯拉斯•儒莲于1832年贡献了第一部中国戏剧的法语全译本——《灰阑记》。此后,他又重译了《赵氏孤儿》前三幕,儒莲不仅翻译了唱段,还为其标出了演唱时的曲调。在其从事汉学研究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他对至少九部元杂剧进行了翻译。[7]效法儒莲,法国东方语言学校的第一位教授巴赞对中国戏剧进行了大规模的译介。1838年,他的译著《中国戏剧选》出版。作为汉学家,巴赞对戏剧的翻译主要收录于对元代研究的著作中,他还发表了对多篇元曲的赏析。巴赞的翻译处理介乎马若瑟和儒莲之间,既试图忠于原文,又尝试引起法国读者的兴趣,在大体忠于原作的基础上有时对段落进行删改移动,以保持剧本可读性。值得一提的是,巴赞在其《中国戏剧选》中还写入了自己对(主要是元代以来)中国戏剧史发展的介绍,使读者有可能对元杂剧的历史演变和表演形式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儒莲和巴赞的翻译再一次引起了法国学术界对中国戏剧的兴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中国戏剧在法国的传播,这两位汉学家功不可没。
随着19世纪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等机构的设立与发展,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戏剧表演的研究,为戏剧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资源。法国汉学刊物《亚洲杂志》和《学术杂志》曾连续刊登元代杂剧的译文,法国学术界对中国戏剧典籍的兴趣有增无减。元曲中主要作家作品陆续翻译为法语。法国译者更多寻求中国戏剧典籍原本,忠于原文的全译本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中国戏剧典籍法译本虽无此前马若瑟译本的轰动效应,却在规模、质量上有了显著提升,中国戏剧典籍以其文本全貌亮相于法国学界。
在此之后,随着中法人员往来的密切,中国戏剧典籍逐渐走向大众,它们以剧本和表演的形式在法国大众中更广泛地传播。一方面,不仅是法国学者,中国译者也开始推动中国戏剧典籍进入法国。例如,1929年陈绵凭借《中国现代戏剧》的论文,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陈宝吉翻译的《西厢记》在巴黎出版。另一方面,法国对于中国戏剧典籍的理解不再限于剧本文本,直接观看表演成为解读剧本的一种方式。1955年中国剧团第一次访问法国,参与在巴黎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此后,法国大众得以直接接触中国的戏剧表演,戏剧典籍也加上了插图成为广受欢迎的艺术画册,剧本则进入公共图书馆,可及性有了明显提升。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中包括了许多经典戏剧典籍,甚至颇多孤本和善本[8],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的流传不再依赖学术界的译介。
二、中国戏剧典籍法译本的作用变迁
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首先是以社会学研究材料的形式进入法国的。无论是马若瑟还是儒莲、巴赞的译本,都不是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翻译作品。法国学者戴特丽指出,直到20世纪初之前,法国对中国戏剧的评论不是基于中国戏剧本身的美学原则,而是采取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其与欧洲戏剧进行比较。[9]伏尔泰曾对《赵氏孤儿》提出“缺乏思辨和理性”的批评。汉学家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由于绝大部分汉学家抱着了解东方民族风俗的目的,又无从接触中国戏剧表演,只能研读中国戏剧典籍,对中国戏剧往往呈现出“盲人摸象”的特点。例如,法国历史学家让-雅克•安培批评中国戏剧“低级”[10]。儒莲、巴赞等汉学家由于翻译了较多的中国戏剧,对戏剧本身的特点较为清楚,但仍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巴赞在其对元代的整体研究中仍不免用法国的戏剧准则评判元曲。这种现象是语言壁垒现实与法国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法国学者,除了极少数来华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之外,无从接触中国戏剧表演,也缺乏丰富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他们对于中国戏剧典籍的认识仅限于文本,尤其是法文译本。而早期译本不重唱段、有选择性翻译等问题限制了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戏剧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试图从戏剧典籍中管窥中国的社会现实,关注戏剧的儒家伦理内涵与道德教化作用,而往往注意不到中国戏剧典籍虚实结合、借古讽今等特点。清驻法大外交官陈季同就曾以法文写就《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以比较的视角试图批驳“专横的欧洲人对我们古老制度和习俗的藐视”,但这不免也落入了文明比较的争论中。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启蒙学者对包括戏剧在内的中国文化看似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主要是尝试从中寻找、改编符合启蒙理性法则的思想资源,而与中国戏剧典籍的关系甚微。整体来看,20世纪初之前的法国对中国戏剧典籍抱有一种猎奇态度,但整体持负面的评价。
随着法国对中国戏剧典籍翻译的深入,中国戏剧典籍逐渐回归其本身的艺术作用。这与法国对中国戏剧的翻译、研究专业化密不可分。早期的戏剧翻译主要是由传教士、汉学家进行的,他们对中国戏剧的翻译是其众多翻译工作中的一部分,服务于其对中国社会风俗研究的整体。而20世纪初涌现了许多专门从事中国戏剧研究的学者和专著,学者研究的对象也从元杂剧拓展到京剧、昆曲等剧种,涵盖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剧本与艺人。[11]这一时期,随着更多学者、戏剧从业者接触到中国戏剧典籍,中国戏剧在法国不再仅仅作为介绍性的学术资料或猎奇谈资,而是成为戏剧研究的灵感来源乃至美学、哲学启示的来源,法国学界对于中国戏剧的关注从文学性转移到非文学性部分。[12]普遍认为,法国戏剧家阿尔托首先倡导中国戏剧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老子“虚实相生”的思想,并且强调导演而非剧作家的作用,在法国引起了戏剧的变革。[13]这一系列变化同样是社会思潮与现实条件变化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中法人员交流、中国戏剧翻译的发展,法国观众逐渐能一窥一部融音乐、舞蹈与歌唱为一体中国戏剧的全貌,在热烈的文化交流与学术讨论研究者也得以了解中国戏剧的表现形式、思想内涵。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自身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西方文明优越论相对衰弱,中国戏剧乃至东亚、东南亚戏剧在法国吸引了更多关注和讨论。一战后兴起的反思潮流对中国戏剧典籍的传播也起到推动作用。
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的传播似乎又复归于学术界,汉学者与戏剧学者分别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官方与民间的往来借着建交的东风蓬勃发展,法国汉学研究机构数量迅速增加[14],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专题研究层出不穷。汉学家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从早先的京剧拓展到其他地方剧种,南戏的研究兴盛起来,1998年雷威安的《牡丹亭》全译本就是一例。[15]许多经典戏剧典籍出现了新的译本。学者们还对中国戏剧的传播史进行了研究,对中国戏剧尤其是《赵氏孤儿》在法国乃至欧洲传播的学术研究尤其突出。戏剧学者则更多关注戏剧的表演,探讨戏剧的变迁、保存、传承等问题,许多法国青年学者加入对中国戏剧的研究当中。这些现象看似是中国戏剧典籍复归于学术界,背后折射的也是中国戏剧逐渐走向大众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中国戏剧典籍走向大众才吸引了更多学术关注、更细致的学术研究,以及服务于戏剧存续、审美价值的学术成果。
三、结论:属于大众的中国戏剧典籍
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的翻译与传播总体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从翻译文本的角度看,法国翻译的中国戏剧典籍呈现出由元杂剧经典向涵盖各历史时期各类地方剧种的变化。从译者角度看,中国戏剧典籍译者由少数传教士、汉学家向广大汉学学者、中国学者和当代翻译工作者拓展。从受众角度看,接触中国戏剧典籍译本的人群也从宫廷贵族、极少数汉学学者向研究机构中的汉学学者、戏剧学者和法国戏剧观众转变。从翻译目的角度看,从传递中国民俗、满足猎奇心理转变为传播戏剧审美价值、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从翻译技术角度看,也从传教士的节译转变为汉学学者的全译。这些变化背后的一条主线是中国戏剧典籍的大众旨归——中国戏剧是中国众多民间创作者、表演者的文化成果,是中国广大民众的娱乐项目,体现的是民众中普遍的审美原则。它在海外的不可能被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而必然随着法国大众文化素养、审美水平的提高而走向大众,这也符合了试图启蒙大众的思想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初衷。
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扮演的角色,折射出中法国家关系、法国社会物质和社会思潮变迁的种种特点,与法国从专制走向启蒙,从启蒙走向反思启蒙的社会进程是分不开的。法国对中国戏剧典籍的态度,从好奇与贬抑,到欣赏与尊崇,再到联系与保存,体现的是启蒙平等精神下文明优越论的退场,以及现代社会戏剧式微中的反思与挣扎。支配这些变化的依旧是社会价值的变化与大众审美的变迁。正如国汉学家蓝碁所指出的,中国戏剧在法国的翻译受到暂时性的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每个时代(法国)都会产生其对中国戏剧的翻译与再翻译。[16]时至今日,中国戏剧典籍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依旧为我们研究中法人文交流敞开着一扇窗,还有许多社会意义与学术内涵值得学界发掘与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