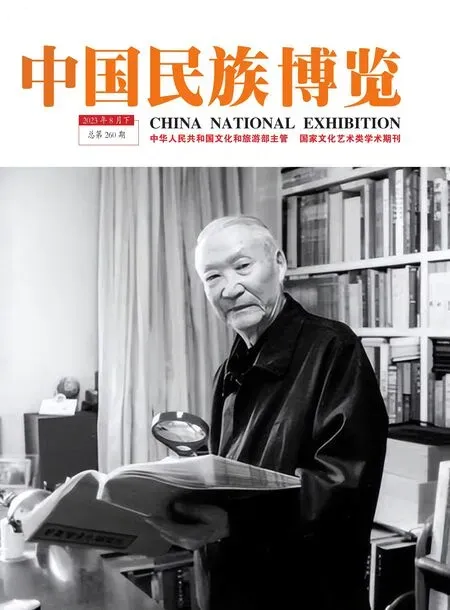蒙古马鞍工艺的美学分析
王英豪 张同健
(内蒙古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引言
蒙古族生活的地区历史久远、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时期的马鞍略有不同。在我国广阔的草原地区,形成了十分璀璨的游牧文化。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共同为游牧文化增砖添瓦。游牧民族十分擅长交流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与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各类马具也是其中交流的重要部分。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把自己的武器,如弓、矛、剑、盾、箭筒等都加以装饰,蒙古族人对自己的马也十分重视,其中特别注重装饰自己的马鞍。
一、蒙古地区马鞍工艺的不断演变
蒙古族人十分注重对马鞍上的制作,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马鞍的制作与装饰上有着高超工艺以及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在他们纯朴生动的刻画下,创造出遍布蒙古高原辽阔大草原上的岩画艺术,这其中不乏先民们关于牧马生活的记录。蒙古高原希什金诺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第一幅岩画就是马,新时期时代遗迹中也有马的骨骼,阳山岩画中也有许多关于骑射与马的岩画。在这些岩画中可以看出人们已经试图用各类手段对野生骏马进行驯服,反映出当时游牧生活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先民们对原始马鞍的探索也已经开始。
匈奴是我国文献中记录较早的游牧民族,其部落战事较为频繁,匈奴人著名的首领冒顿单于,就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骑兵,匈奴与汉廷“白登之战”,一次出动“精兵四十余万骑”,且色泽不同的马匹组成战阵,拥有大量战马的匈奴,那么肯定拥有相当数量的车马器具,在马鞍的制作上,也应具有了娴熟的制作工艺。[1]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所出土的青铜器中出土了大量马鞍构件,其中铜制的马衔风格独特,出土的马具上具有交错弧形纹、螺旋纹和几何纹等纹样。这些出土的金属车马器,反应了当时车马具的制作水平,其中的各类纹样装饰上的区别,也表现出了马鞍工艺的装饰效果。在同时期出土的马具中,还有部分石制马具以及骨制配件。生活在北朝的鲜卑等游牧部族,他们的畜牧业是十分发达,他们畜产品的皮革手工制品,特别是车马具等游牧生产生活器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在马鞍具类制作上,有了诸多完善,该时期鲜卑人使用的相关马具中,如缰绳、颊带、额带、咽带、马衔、马镳等已经基本完备。当时马镫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这一点从当时发掘的许多鲜卑人墓葬中出土的马具可以得到证明。特别马镫在战马上的应用以后,能够让人与战马连为一体,使战马更容易驾驭,马镫让骑在马背上的人解放了双手,使得骑手们能够在奔驰的战马上进行骑射,也让骑手在奔驰的战马上更加平稳,保护了骑手的安全。当时的马具工艺在制作材料到制作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十分精湛的水平。马鞍工艺的完善对人类文明进步上,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鲜卑人在马鞍的制作上,具有极高的热情,从制作材料的优质皮革、贵重金属,装饰纹样上的刻画上,到制作工艺的雕花、铜饰、鎏金等,这些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游牧民族美术特色,使得当时的马具制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手工艺精品。
二、马鞍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中原地区与塞外交往更为密切,在马鞍这类工艺品上也有所交流融合,但是在整体上还是有区别的。首先,中原地区的马鞍通常采用木框架和皮革包裹(牛皮、羊皮或马皮制成),形状较为扁平,适合于平原地带的战争。马鞍前端有高高的鞍弓,后端有高高的鞍垫,使骑手能够更稳定地驾驭马匹,并在战斗中更方便地使用弓箭。而北方草原地区的马鞍则以金属和皮革制作,形状较为圆润。草原地带的地形较为崎岖,马鞍需要更好的支持力和平衡力,以帮助骑手在战斗中更好地保持平衡。因此,草原地区的马鞍通常更加厚实,鞍垫较高,鞍弓较低,以保证骑手在马背上的稳定性。在马鞍制作上的区别,也体现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区别。此外,北方草原地区的马鞍上通常会有许多装饰,如银装饰、彩色缝线和马尾饰物等。这些装饰不仅能够使马鞍更加美观,还能够彰显骑手的身份和荣誉。出土的辽代时期文物中,车马器数量极多,反映出契丹人作为一个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在车马具上的重视。辽代车马器配饰多铜制品,大多马鞍具有百花草纹饰。还出土了大小有序、成组的铜铃,一般是长筒形状,这些铜制铃铛与近代蒙古车队防止夜间行车时牲畜离队而悬挂的铁铃铛相似。辽代中期鞍马饰品常采用银制,有的外表进行鎏金,表面常雕刻牡丹花纹以做装饰效果。契丹族是游牧民族,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契丹人的一生与马息息相关,契丹人和马同甘共苦,爱马就像爱自己的生命,所以装饰马鞍是契丹人生活的第一要务。在契丹人出行、作战等各项活动中,都与马息息相关。在文献记载,墓葬壁画和随葬品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契丹人的马。在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马鞍具。每具都有银马缰、银胸带、镶金铁马镫、包银木马鞍等精致华贵的陪葬马鞍。[2]契丹马鞍具的精致考究由此可窥一斑。由于其工艺的高水平,契丹人甚至将其作为与周边国家进行友好交往的国礼。辽代中期是辽代王朝全盛时期,对外交往达到了高峰。从已出土的契丹马鞍具实物来看,宋代太平老人《袖中锦》称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并列为“天下第一”,确实名不虚传。
三、元朝时期马鞍文化的美学特征
对成吉思汗时的鞍具,史书上也有记载,如:“铁木真在战中失其银饰鞍辔之骍色马,鞍马带上亦以黄金盤龙为饰,其鞍辔轻简,以便驰骋,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竖而后平,故折旋而膊不伤轻园,故是中立而不偏底调,故靴易入缀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断烂,调才踰一寸长不逮四总,故立马转身至顺”。[3]这种马鞍舒适美观。“那从未被驯服的骏马,在顺从于他的雕鞍下温和地徐行。”可见当时马鞍的制作已经到达了十分高超的水平。
蒙古部落出征时几乎是牧民自备马匹以及作战装备,可见当时的牧民对马具的制作工艺以及维护上已经普遍具有了相当娴熟的水平。在蒙元帝国停止扩张后,促进了亚欧地区文化传播,也吸收了其他民族工匠的锻造技术以及其他民族的工艺产品,这其中对马鞍纹饰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些蒙古族贵族开始注重对马鞍上的装饰,开始用金银等贵金属打造马鞍,来进行彰显身份,有些也在民间开始流行。在民间不仅对马鞍进行细致的雕刻,也有许多关于马的赞词和歌曲,表达有了好马后牧民心中的喜悦之情,更是产生了许多关于马的节日,如打马鬃节、马奶节以及那达慕大会等。
马鞍是蒙古部落十分重要的陪葬品,元朝时期蒙古族贵族十分喜爱金器,在现在出土的许多元代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金制马鞍饰件。1988年内蒙古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了一批蒙元时金器,主要是金马鞍饰件。其中金马鞍饰品一共出土,一组计6 件,全部由纯金制成。这套鞍具由前鞍翅、后鞍翅、前鞍桥和后鞍桥组成,装饰纹样具有蒙古特色。通体用锤揲法锤满了精致的浮雕卧鹿纹、花草纹、忍冬纹、缠枝牡丹纹等。纹饰精美、华丽,工艺精湛,具有突出的草原风格。马鞍用具上的各类图案是蒙古族人审美情趣的展现,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长期在大草原上过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经过艺术提炼,逐步产生了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纹饰图案。经常出现于马鞍上的有山水纹、云纹、树木花草纹等描摹自然物景物的图案。还有描摹动物的龙纹、鹿纹、五畜纹、蝴蝶纹、蝙蝠纹以及几何图案、吉祥图案等。[4]体现出蒙古族工匠们的高超工艺。
蒙古族马鞍制作工艺是千百年来牧人在草原独特的游牧环境下生产生活的结晶,是游牧民族先民们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经验的交流与积累以及部落间征战的产物。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人,在制作马鞍时十分注重实用性和艺术性。古代“契丹鞍”,具有“天下第一”之称,蒙古族马鞍同样享有盛名。元朝时有金鞍,北元阿勒坦汗时也有“镂刻的金鞍”。在生活中,蒙古族马具工匠们用自己精湛的工艺,运用各类材料制作出各类马鞍。有些制作精湛的马鞍上还有许多配件,如鞍韂、鞍花、鞍软垫、鞍辔等等。前后鞍桥都喜欢做各种装饰,绘制图象,骨雕镶嵌,贝雕镶嵌等,对于马鞭以及马镫的制作上也有独特的技艺。在春节时马头部还戴“毛林塔格乃”的刺绣装饰。马鞍不仅让骑马的骑乘人员更好的驾驭骏马,也让马在被骑行中感到舒适,一部优秀的马鞍,不仅能提高骑手的技艺,也更好的保护了马。马鞍具虽然不是蒙古族人的发明,但在蒙古族工匠的手中,但也在蒙古族马鞍工匠手中发展出多种门类。在现当代,蒙古族各个部落不同的马鞍制作款型也种类繁多,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工艺可以分为乌珠穆沁式、察哈尔式、孛尔只斤式、布里亚特式、达尔干嘎式、卫拉特式等多种类别。[5]这其中优秀的马鞍的制作工艺是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工匠不断传承与交流的结果。在亚欧大陆广阔的大草原上,鞍马器具的制作工艺在诸民族之间不断地传承和交融中不断进步,共同促成了草原马鞍文化的繁荣。
四、近代蒙古族马鞍工艺的发展
到了近代,蒙古族的马鞍制作也依旧继承了传统制作工艺,其制作过程包括选材、制版、缝制、装饰和润饰。近代蒙古族马鞍制作工艺与传统蒙古族马鞍制作工艺在材料选择、设计风格、制作工艺和功能需求等方面存在差异。近代马鞍采用更为现代化、科学化的合成材料,设计风格更加多样化,制作工艺采用机械化生产。而传统马鞍则使用天然材料,设计风格比较简朴,制作完全依赖手工制作。此外,近代马鞍功能多样,适用于各种骑行需求,而传统马鞍则主要适用于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骑行需求。虽然近代马鞍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但传统马鞍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对关于草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工艺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不仅在装饰纹样上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制作工艺上也显示出游牧民族匠人高超的技艺,凝聚了草原人民对于广阔草原独特的情感,体现出游牧文化的精神所在。然而,随着游牧生活的逐渐消亡与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马鞍文化正在逐渐地消失,对于马鞍民间手工技艺也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对日渐消失的蒙古族马鞍手工技艺以及传统马鞍纹饰美学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保护、传承、创新,是我们保护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有利于让我们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里保留好关于草原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