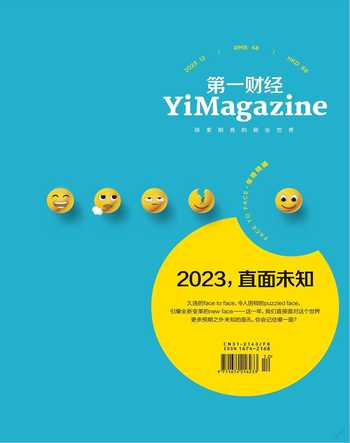经济学家赵耀辉: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任思远
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2023年经济学家赵耀辉关于性别平等议题印象最深的事件。
戈尔丁在女性劳动力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最新的一本书《事业还是家庭》,梳理了美国100年以来女性在事业和婚姻生育行为之间选择的情况,揭示了变化的原因,并指出性别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对历史的梳理,让同样专注于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赵耀辉开始思考中国女性面临的境遇与问题。
在此之前,无论中外,以“MeToo”运动为代表,从文化和观念出发的、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在公众中已经持续了数年。戈尔丁获奖,让更多人意识到家庭分工的性别不平等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与之类似的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1992年,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摘下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凭借的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结婚、离婚、生育等家庭现象的分析中,这也是家庭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作为经济学家的贝克尔同时也是社会学家,他开创了将微观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学分析的先例,对于种族歧视、犯罪、家庭决策等社会现象做了经济学分析。
赵耀辉是把社会议题带入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之一。1980年代末,她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彼时正是实证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盛行之时。在此之前,赵耀辉在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热衷于讨论当时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农村改革、国企改制、劳动力转移等。对这类问题的兴趣让赵耀辉在当时就养成了关心弱者福祉、去农村等地做田野调查的习惯,即便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十分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了芝加哥大学后,赵耀辉师从农业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他鼓励她使用微观数据研究当时中国正在出现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过程。
1990年代,赵耀辉回国,当她试图在中国开展基于微观数据的、与社会议题相关的经济学研究时,面临的难题之一是缺乏微观数据。她和团队从2011年开始创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追访数据库,希望收集能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
为了培养能使用这些数据的学者,早在2002年,赵耀辉就与加拿大的董晓媛一起牵头发起了中国女性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并建立起一个女性经济学者的联谊网络。这个网络为中国经济学界在此类议题上的进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一年的年末,我们与赵耀辉聊了聊戈尔丁对于研究中国女性性别平等进程的启发,也回溯了她本人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议题的历 程。
Yi YiMagazine
Z 赵耀辉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Yi读过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后,你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Z我一直关注性别平等的议题。之前看到的美国经济学领域关于性别分工等议题的研究是细碎的,而戈尔丁在这本书中对于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我对此很感兴趣,她的作品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女性面临的境遇和问 题。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美国女性100多年以前还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中“二选一”,到现在才有一些人可以做到兼顾。这样的平衡来之不易。另外,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变化和政治思潮也在共同推动整个历史的进程。
1920年代及之前,美国的已婚女性是不被允许就业的,那也是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时代。1940年代之后,这些限制基本消失了;1960、1970年代又迎来了女权运动。在这个进程中,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二战”后经济复苏,市场上劳动力稀缺,需要女性去就业。当一群人变得有价值的时候,之前压在她们身上的各种枷锁就会被打破。
Yi如果我们期待性别平等议题有进展,你是否认为主要还是该寄希望于市场的变化?
Z市场的变化是一个巨大推动力,但它的变化可能比较慢。在变化到来之前,我们女性也要在现有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争取工作的灵活性,等等。
Yi参照戈尔丁的研究,在平衡家庭与工作的问题上,你父母和你这代人之后的女性都面临什么样不同的境遇和挑战?
Z我父母那一代一生都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工作是被分配好的,孩子很小就上托儿所或者幼儿园,就业率的性别差异也小,比如夫妻双方都是工人,他们在工作上都没太多变化的可能性。但那时候管孩子、做家务都是女性的事情,女性和男性干同样多的工作,回家还要洗衣做饭。
到了60后、70后这一代,个体的选择变多了。1990年代我回国后,发现不少能干的男老师下海了,而相比之下学校里的工作更加稳定和灵活,所以有不少女老师留在学校。这时候两性的差别就显现了,有一个人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另一个选择去闯。不过,此时计划经济体制仍有一些留存,尤其是福利分房制度,早结婚的人可以更早排队等待分房。所以即便当时已经看到一些不婚、不育的案例,但我认为如果观测更大量的数据,那时候的结婚和生育率还是高的。
到了現在,80后、90后面对的是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例如他们不会再被分到房子,而且需要自主给孩子选择托育服务。这时候,年轻人的选择更加自由,但即便有女性自主选择去当家庭主妇,这种现象也不是主流。但与此同时,女性在权衡收益和成本之后,很多时候会觉得结婚或者生育没有吸引力。这成了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的原因之 一。
女性的个体选择背后,是她们面临高昂的生育成本。我们应该努力帮助那些想要结婚生子但面临成本压力的人。
Yi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过去的一年里你有没有修正过什么观点?
Z过去几年我一直比较关注的是如何为0到3岁幼儿提供质高价廉的托儿所,我觉得这是减少生育成本的最关键的方法。在读完戈尔丁的书之后,我越来越关注女性在家庭内的分工问题,即男性家庭观念的问题,就是他们如果不改变观念,还是期望由妻子做大部分家务的话,女性可能受不了,进而找不到和她志同道合的那個人。过去我虽然意识到这件事,但是没有很强调它,现在我认为中国存在传统文化与女性的能力和意识都已经崛起之间的现实冲突。相比女性的进步,男性的观念转变还没跟上。
Yi戈尔丁在书中将19世纪末以来美国女性平衡婚姻与家庭的进程分成了5个阶段。如果以这种视角看待中国女性平衡此二者的进程,应该如何划分阶段?
Z美国的进程是渐进的,而中国有一些骤然出现的、政策性的变化,这导致了女性就业进程的大幅度变化。
中国在公社化后,农村里的女性无论贫富,多数都需要下地耕作,集体负责照看小孩,城市里也一样,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城镇女性在当时就业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与工作相绑定,很多人(包括女性)会为了得到社会保障去工作。中国1950、1960年代突出的女性就业率是一个明显与美国不同的案例,也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女性发展进程与戈尔丁描写的美国的情形不同。
另外,这种明确划分阶段的工作,我们目前还没有研究基础去做。戈尔丁的结论是基于很多研究成果,但在中国的经济学领域,与生育和家庭相关的研究和数据都是非常缺乏的。比如在研究中,中国可用的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而在美国能追溯到200多年前。
我们需要的是微观的、个体的数据。例如在家庭与生育的领域,我们需要由个体的初婚时间、生育孩子的时间、就业、工资等详细数据组成的数据库。这种数据需要入户调研。中国历史上对于这种数据的采集还是不够重视,基于这种数据的经济学研究也起步较晚。
Yi你如何看待经济学领域由男性主导(尤其在中国)的现象?
Z其实不是经济学的所有领域都由男性主导,只是在传统的宏观、金融领域男性居多;像我们关注的家庭、劳动力等议题,很多都是女性主导的。中国的情况是,最新一辈经济学家中女性的比例相比20年前提高了,毕竟现在更多的女生能考上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很多女性也能够出国读博士。在高校里面,年轻经济学教师的性别比例已经有了很大改进。
Yi在你的观察里,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代际差 异?
Z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同样也是。我们那一代人里经常能见到一个人有两三个兄弟姐妹。如果是来自农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儿子能拿到更多资源是常见的现象,而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压制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变好了,很多家庭不需要再作这样的选择了。女性在不被压制的情况下,在认知、记忆、计算等方面的整体表现都是更好的,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当下年轻女性研究者比较自然地成长了起来,而上一代不是自然的情况。
也有一种从生产方式角度的分析。例如现在体力活越来越少,女性的劣势下降了;家庭电器,如洗衣机的普及,减少了家务劳动的负担;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女性表现更好的岗位。1920到1930年代,随着制造业兴起,销售、会计、文秘等工作在美国出现,女性的就业率和受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女性在文秘工作上有优势,因为更能理解人和说服人,她们也可以把销售做得很好。
Yi作为女性,在当时男性居多的环境下,你是怎样选择和进入劳动经济学领域的?
Z我觉得女性天生对于民生的、跟人有关的、实在的事情感兴趣,而非金融等宏观的议题。我选择这个议题,是因为1980年代末去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正好遇上劳动经济学问题成为美国学界的热点问题,导师都鼓励这个领域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界也经历了从基于宏观数据到基于微观数据做研究的过程。微观实证的经济学研究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微观数据变得可得,类似于全面的人口普查或者抽样调查;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的电子化。从1970年代开始,基于这两个条件的成熟,美国经济学对于这类数据的研究有了爆发性的增长。1980年代延续了这种趋势,尤其是出现了用微观数据来研究性别、种族差距等不平等问题的现象。
我在美国读书时,用经济学手段研究社会议题是非常主流的,但我在本科或者硕士期间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我感觉我当时接触到了经济学一个非常美丽的方面,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包括收入的、就业的表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打开了一扇窗。所以我在博士期间使用了北京郊区三个村的数据,研究劳动力如何从农业转到非农业,研究他们收入的决定机制。
在回国之后,数据的量和开放性就成了做这类研究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出于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心,以及数据的需求,我们做了十多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追访数据,样本覆盖在全国抽取的150个县区、450个村居的万余户家庭,每年有数百名大学生前往全国各地参与调研。
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能够使用这些数据的一群人。所以从2002年开始,我们花了十几年时间,做女性经济学家的培训。那时候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微观数据,同时有很多重要的议题没有人做,例如性别的收入差异、儿童的健康等问题。我们从全国各地找到了一批女经济学者,她们当时在学校里不太受重视,但又有很高的学习热情。我们就培训她们用微观数据去做和社会议题相关的研究,手把手教她们处理数据、分析问题、讨论回归。在这个培训项目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大网络,当时参加培训的人现在有不少成了这个领域研究的领军者。
Yi你在选择这个“网络”的人选时,为什么没有召集一些男性?
Z因为当时女性在学校里是被边缘化的,普遍遭遇升职难等困境,但她们又有很强的求知欲。另外女性在这种议题的研究上是有优势的,我们的女性研究者都非常踏实。这类研究的周期长,不容易带来名声,而且还可能被“说三道四”。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这些微观的议题不重要,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更重要的是宏观的“大事”。很多人可能更在意自己做的研究被人重视,而不在意其学术性。
所以,不那么看重名声,愿意踏实做事的女性就有优势做好这种研究,这一点在中外是有一致性的。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我的底气来源于看到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们、像加里·贝克尔这样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所以我不在意那些质疑我们的声音。
Yi女性经济学家们相聚讨论问题的氛围有什么特点?这些女性在原有系统里取得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
Z女性经济学家在一起就是姐妹的样子,大家非常亲,非常愿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种氛围好像不太容易在男性经济学家中间见到,他们更多是竞争关系。至于她们能够打破壁垒的关键,就是我们对她们的培训让她们能够发表论文,在学术评级体系中有了优势,她们自己有了信心。另外,她们也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了。
Yi你对于微观数据、社会议题的兴趣是1980年代末在美国萌发的,还是之前有其他的经历?
Z我一直对民生问题感兴趣。1980年代我上大学后,甚至更早的时候,因为看到了城乡差别,我一直很想知道怎么能够让穷人好起来。我在大学学经济学时,国内也很主张做田野调查和社会调查,我老家在河北农村,所以我寒暑假就经常去观察村民的生活收入等情况。
那时候国内的很多经济学研究出发点是想解决实际的问题。我关注的农村议题在当时是很被重视的,同样被讨论很多的还有国企改革等问题。
去了美国之后,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D.盖尔·约翰逊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著名的农業经济学家,研究了从1920年代开始,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业、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过程。我去到美国的那个时间点,中国也出现了农民工进城、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进程。所以他鼓励我研究这些问题。我印象比较深的经历是,当时有一些农民工白天打工、晚上睡在火车站,我去火车站采访,也去他们老家做访谈。
微观数据大规模兴起之前,经济学者比较多的是在研究宏观问题。19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经济起伏,促进了宏观领域的研究;近些年来,民生问题突显,媒体便开始关注实证经济学的议题。在这近30年时间里面,微观实证的研究在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新生代的研究者已经不像最初那样以女性为主,男性研究者也开始加入其中。